建设新经济正在如何形塑城市?
2022-03-11

所有人都在討论“创新经济”,但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是从哪儿开始的。虽然不稳定就业和数字化监控引发了对“新经济”的批判,但是那些在自发“科技社区”工作的人们更乐意用“创新创业”这样的激励话语。虽然观点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今天的城市是创造和对抗土地、劳动力、文化、资本等要素的重要之地,这些要素间的有力互动是新经济形成的基础,被称为“创新综合体”。
正如这个短语所示,新经济既有物质维度又有象征维度。城市领导者遵循着经济增长的现代叙事:在政府的支持下创造新点子、商业投资机会和就业岗位。这些“虚构”的预期让他们构想着一种人人繁荣的创新景观。
实际上,现实更具风险、更为复杂。这是在特定的文化和权力时代中,一个关于所有城市和和一个关于纽约的故事。正如早期的网络构成了现代城市中的火车站、地铁线路、路灯和下水道一样,今天的创新综合体正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中以字节的方式接连出现。
尽管发展新经济的过程大多在私营部门内展开,但城市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了让科技企业提供就业岗位,政府需要补贴商业投资和专门的职业教育。他们同时要为地产开发商设立科技中心和创新专区。他们还需要处理科技给地方市场和社区带来的“干扰”:叫车服务、房屋短租、自动驾驶、电动滑板车,以及企业为智慧城市建设而搜集的隐私数据。
作为权力中心,城市调动经济资源并使之转变为更大规模、甚至是全球性的投资。最先是在工厂,然后在摩天大楼,现在又在孵化器、加速器和联合办公空间,城市落地了很多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同时,作为文化中心,它们又创造了新的方式去想象、证明和适应这些变化,当然也会出现对这些新方式的抵制。
纽约以一系列特殊的经历和展望来迎接科技发展场景。尽管纽约市前后两位市长迈克尔·彭博和比尔·白思豪的做法有所不同,但他们的战略计划同样重要,因为他们正在研究如何利用新经济的叙事来促进增长。2002年到2014年间任职的彭博回应了企业的需求,而接替他的白思豪则利用增长来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但他们都将数字技术置于新城市产业政策的中心地位。两位市长都资助了试点项目和初创企业办公空间;都提出了一种依靠“公-私-非营利”伙伴关系的经济治理模式。
随着越来越多的纽约人和组织对创新产生兴趣,政府的公共部门、营利性企业的私营部门及教育、慈善和民间机构的非营利部门之间建立了重叠、扩散的合作伙伴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伙伴关系采用了“三螺旋”模式,在当地企业、大学和政府机构之间建立多元的正式或非正式合作,这在包括硅谷在内的所有科技研究中心都很常见。它们也代表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美国城市和世界经济论坛等高级别国际组织所青睐的治理模式。“公-私-非营利组织”伙伴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在纽约市出现,2008年之后,这个针对公共空间的筹资、管理和治理工具,也成了技术社群筹资、管理和对外展示的默认模式。
白思豪政府开始深入参与在全市开发“创新”空间的过程。房地产商和独立专家都认为,提供给科技和创意办公室的商业空间严重不足。在彭博执政期间,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已经开始设法在市属资产中为科技初创企业开设孵化器和加速器。他们与营利性公司和非营利性大学合作完成了这项工作:“三螺旋”在行动。白思豪政府延续了这一进程,但增加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社会”组成部分。一方面,新市长将把助力经济发展的创新点推广到全市各地,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和少数族裔聚居区。另一方面,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将在一个市中心位置开发一个劳动力培训的旗舰项目:“一个新的科技中心”,这个项目位于联合广场附近、熨斗区以南的市属土地上。
“三螺旋”模式将商界和研究机构高层的“思想领袖”与各类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负责人联系起来,促进了公私伙伴关系的形成。这些合作关系证实了科技“三螺旋”的价值,即企业、政府和地方大学之间的特定联盟。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和“三螺旋”将为纽约的创新综合体构建一个组织框架。
与许多其他美国城市不同,在寻找新的增长点上,纽约另辟蹊径。它将基于金融机构(financial institutions)、保险公司(insurance companies)和房地产开发商(real estate developers)之实力的“最火”领域(FIRE)的历史主导地位,转变为被纽约大学校长约翰·塞克斯顿(John Sexton)巧妙称为“火与冰[即智识(intellectual)、文化(cultural)和教育活动(educational activities),简称ICE]”的模式——这个描述城市经济新核心领域的术语给予了智识、文化和教育活动应有的尊重。
金融危机期间,政府的首要决定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战略规划智囊团: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的经济转型中心(the Center for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ET)。他们聘请了麦肯锡前管理顾问史蒂文·斯特劳斯(Steven Strauss)担任创始董事,他曾负责组织世界经济论坛。斯特劳斯不仅带来了作为纽约本地人对这座城市的批判性同情心,也带来了全球商界高层领袖的共识,即知识驱动和技术驱动的“创新经济”正在崛起。据斯特劳斯,随着纽约金融主导型经济的自由落体,经济转型中心迅速推动了城市的战略转型,转向“曾经介入不深的创业经济和创新经济领域”。但随着应用程序和社交媒体的出现,科技行业需要更多的软件工程师,超出了纽约市该领域原有的人才数量。
大规模地推动新劳动力的形成,需要当地学校和雇主的支持。出乎意料的是,这个主意是由经济发展公司的“游戏改变者”(Game Changers)倡议提出的,这是一个长达一年的系列咨询计划,对象包括300多名来自企业、社区和大学的领导。事实证明,就对经济有重大影响的事情,人们达成的主要共识“是工程。相对于我们想成为世界领导者的雄心,我们没有足够的科学和工程(能力)。这就构成了(城市的)短板”。
我们需要从几个层面理解这个短板。纽约需要数千名训练有素的软件工程师为科技公司工作,但也需要数万名具有专门职业技能的人,他们既能为各类公司做“创造性”的设计工作,又能进行日常的系统行政工作。对一个城市来说,“吸引聪明、有才华的人”是很重要的。除了改善城市的物质基础设施和文化生活质量外,彭博政府还需要帮助当地大学在学生和教师中培养更广泛的创业精神。
每一个目标都要求纽约市政府进行深入的劳动力培训研究,这促使经济发展公司开始寻找“比我们装备更好的组织”来与市政府合作。“(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将为其提供资源和组织领导”;私营和非营利部门的组织都开始提供培训。这个最广为人知的努力最终促成了一个旗舰项目,即在罗斯福岛创建一所工程类研究生院。彭博市长在一次纽约科技交流会上说,如果这项计划奏效,这所学校不仅会吸引世界各地“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其毕业生还将创办初创企业并留在纽约,长期推动纽约的发展。这个工程类研究生院最终被命名为康奈尔大学科技校区,它只是“纽约市更广泛的应用科学计划”中最突出的一项。从2010年开始,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资助了全市主要教育机构的一系列项目。它大力支持了纽约大学进军布鲁克林市中心的计划,推动其与理工大学合并,并资助纽约大学的城市工程和大数据分析中心建设;还支持了哥伦比亚大学晨边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校区的数据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的成立。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还鼓励了在纽约州立大学的几个校区进行小型创新机构的建设。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还资助了营利性的训练营,作为大学教育以外的一种更快、成本更低的选项。

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72 号船坞:“21 世纪数字时代制造业的发源地——创意和创新发生实验室……旨在将最先进的现代甲级办公基础设施与为合作者社区开发的独特设计美学相结合”
与此同时,名字相近的私立大学纽约大学推出了多项创业计划。正如“火与冰”(FIRE and ICE)这个缩写口号所显示的,大学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强化大学与初创企业之间的联系”;利用激动人心的编程马拉松,鼓励大学生们关注科技领域,而不是金融职业。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大学开始培养一支社会方面和智力方面都很多元的劳动力队伍。不仅是市长,科技界的每个人都在为社会多样性大声疾呼。人们普遍认为,这对纽约市和整个行业都有好处;促进多样性将使纽约更能吸引各类人才。
要找到正在显现的挑战公平增长的蓝图,你必须直接且批判地审视真正的城市空间形态是如何因创新投资而改变的。这些空间嵌入了风险投资家、经济发展经理人、大学校长和房地产开发商对经济增长的虚构叙述,而这些人组成了这个城市的“增长机器”。在纽约,这些人在一个最不可能、也是最典型的城市环境中——布鲁克林滨水的老工业建筑——建造了一个创新综合体。
在布鲁克林,曾经无人问津的滨水区从19世纪建造的废弃烟囱和仓库景观,变成了汇聚科技、创意办公室、媒体工作室和“绿色”制造业设施的发源中心。从Kickstarter在绿点社区的办公室一路向南扩展,穿过威廉斯堡的Vice Media,到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的斯坦纳工作室(Steiner Studios)和新实验室(New Lab),再到DUMBO的Etsy和Huge总部,一直延伸到日落公园社区的工业城园区和布什码头,那些洞穴般的仓库、古老的机械商店、发霉的水泥地板阁楼被改造成了数字制造、电视和电影制作、电子商务以及其他科技和创意工作的场所。“布鲁克林科技三角”被规划成一个构想出的创意区,用以刺激对历史街区内空置办公空间的需求;尽管广告过分夸大,但该地区的发展活力毋庸置疑。在短短的几年里,虚构的滨水区创新景观已然演变成了真正的布鲁克林“创新岸线”。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海军造船厂已经从曾经的10英里滨水地带(从北部皇后区阿斯托里亚到南部布鲁克林日落公园)的地理中心,变身为继旧金山之后美国发展最快的科技中心。纽约四大影视制作中心中的三个,包括斯坦纳工作室,都在附近,同时还有几个较小的工作室。纽约市两大科技公司都将总部设在这里,一家是拥有逾1000名员工的Vice Media,另一家是拥有超过700名员工的电子商务公司Etsy,此外还有数千家新闻、广告、艺术、设计领域的小型初创企业,以及从无人机到DogSpot(共享狗屋)等的數字硬件企业。就连亚马逊命运多舛的“第二总部”也选择了皇后区的滨水站点。
这座占地300英亩的海军造船厂的旧船坞和金属加工车间在20世纪60年代被美国联邦政府废弃并出售给纽约市,在20世纪80年代艾德·科克(Ed Koch)市长任期内,它被重新规划为小型制造商基地,慢慢地,被曼哈顿下城和附近布鲁克林的高房价/租金驱逐出来的企业将这个基地填满了。当时,那些很快会被界定为“创客”的艺术家和工匠们不再租得起SoHo的阁楼;他们只能把工作室搬到DUMBO,因为在那里收购了200万平方英尺旧工厂和仓库的房地产开发商戴维·瓦伦塔斯(David Walentas)找不到其他租户,他认定艺术家们会使这个地区更受欢迎。在威廉斯堡,地下派对、音乐酒吧和狂欢节正在将这个原本粗犷的工业场景转变成一个“酷”文化聚集的夜间景观。
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开发公司将朱利亚尼政府20世纪90年代的一笔资本补助金变成了源源不断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资助”,海军造船厂园区用这笔钱对一些陈旧建筑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并修复了园区内凹凸不平的道路。“投入得到了回报”,因为这些投资鼓励了长期的制造业租户留下来发展,也吸引了新的初创企业,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斯坦纳工作室。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开发公司开始利用城市的资助扭转园区几十年来的衰退局面。然后,纽约开始逐渐感受到创业和创客文化的兴起。
斯坦纳工作室帮助我们形成了一个关于城市未来增长的新想象,这种增长并不依赖于“传统经济”产业和工厂。这为聚焦密集型房地产开发的新伙伴关系的建立扫清了障碍。斯坦纳工作室所依赖的创新融资方式,整合了私营房地产开发商(道格·斯坦纳)、公共机构(市政府和州政府)以及一家非营利创业组织(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开发公司)。在某些方面,这与硅谷和波士顿128公路等研究中心的“三螺旋”模式没有太大区别,在那里计算机产业、政府和大学业已组成持续促进增长的联盟。但对像纽约这样刚刚开始意识到先进制造业可取性的城市而言,支持斯坦纳工作室的金融和制度安排大大改变了经济增长的主导叙述方式,以及定向补贴企业和部门的长期发展战略。纽约市政府从2004年开始支持使用数字技术的各项活动和产业。
值得记住的是,当时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开发公司正努力在城市新兴的“创新经济”背景中建设园区。事实上,当彭博政府在2010年宣布全球海选建设纽约的新工程院校时,海军造船厂也是四个候选开发点之一。但最终的中标者康奈尔大学和以色列理工学院绕开了布鲁克林的滨水区,而选择了罗斯福岛。失去了康奈尔大学科技校区这样的重大新经济项目,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开发公司将不得不发展自己的置顶吸引点——“新实验室”。这是一个在128号大楼旧造船机械车间内改造的空间,有一个飞机库那么大,Carmera和DogSpot等初创企业都在这里安营扎寨。
如果说斯坦纳工作室代表了在海军造船厂布局新经济的第一阶段,即市政府主导推动媒体制作业以对抗来自加拿大的竞争,那么新实验室则代表了第二阶段更大胆努力的部分,即吸引计算机硬件制造商入驻,其中很多企业将研发团队设在加利福尼亚或波士顿,将工厂放在亚洲。作为一个重建得非常壮观的工业空间,新实验室于2011年开始构思规划,并于2016年正式启用;它代表了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开发公司规划的一个转折点,通过将其与创新经济相连接,为城市的下一代制造业提供发展基地。新实验室体现了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开发公司的期望,即如果他们利用其充足的物业房产支持与初创企业合作,并使这些空间变得炙手可热,他们可以创建一个城市版的硅谷。

罗斯福岛的康奈尔大学科技校区
这些旧工业区的改造经验,部分是自下而上的,部分是自上而下的,形成了一个连贯的战略构想。世界各地的城市规划师、官员和房地产开发商都采纳了这样的想法:城市要吸引一批由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和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专业人士组成的“创意阶层”。通过相对低成本的安置策略可以吸引这些人的到来:修建自行车道、种植绿地、开设美食广场,以及开发其他既美观又环保的文娱设施。同时,这些策略也回应了本地官员和房地产开发商长期以来的优先任务,即为失去经济价值的土地寻找新用途、提供新的建造形式。这两个群体都从将城市土地转化为“增长机器”的过程中获利。房地产开发商出租办公室和出售房屋;政治家将关于就业和住房的承诺转化为选票。
然而,“创意城市”模式被证明不足以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人们开始努力制定新的经济发展战略构想。在日益高涨的创新和创业精神话语中,有关建设城市“创新区”的想法流传开来。这些地区将利用城市生活对年轻人群体的吸引力,不仅为科技公司提供机会去培养这些“人才”,也为建立社会网络提供了物理密度,常常促成科学和艺术间的合作。这种新型生产集群的愿景被浓缩在“城市创新区”(urban innovation districts)的模式中,城市创新区将由一个城市中的企业、政府和大学精英共同规划、协调和建设,以与物理上和社会上孤立的郊区办公园区形成对比。据《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2009年的一篇文章称,“趋势是培育有生命的、会呼吸的社区,而不是无菌的、偏远的研究筒仓”。
“创新区”很快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城市品牌。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人员从2010年开始推广“创新集群”,从2013年开始推广“创新区”。到了2016年,他们发现在谷歌搜索中输入“创新区”会跳出超过200万条搜索结果。仅仅一年后,我以同样的方式检索,发现了令人震惊的1.32亿条结果。
与此同时,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继续着自己的蜕变,从一个旧的工业空间集合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意社区”。除了为数字制造商开发工作空间外,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开发公司开始为科技公司建造办公空间,同时在园区边缘增加一整套全新的便利设施。这些举措都为已经在园区工作的公司员工带来了更多便利,并吸引了更多拥有年轻员工的潜在租户。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对周边居民开放了园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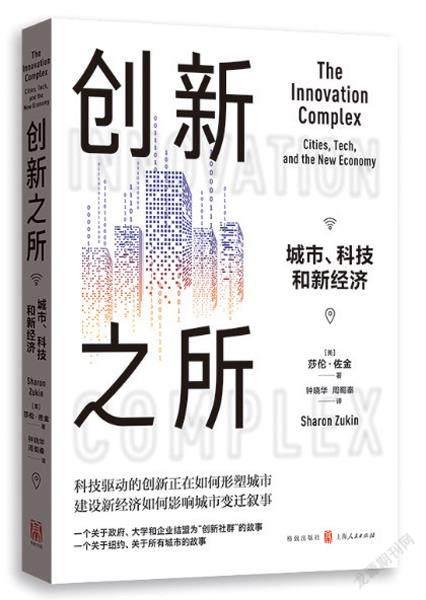
作者:莎倫· 佐金[ 美]。出版: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地方政府切实掌握着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发展资源。与美国的地方发展公司不同——拿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和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开发公司来比,中国的城市开发公司是国有营利性企业:它们是地方政府的风险部门,与私营部门的房地产开发商合作,承接众多项目。对土地和土地开发利润的控制使中国地方政府能够从实力上与国内房地产开发商、海外投资者和跨国公司进行谈判,这些主体对于建设创新综合体都至关重要。这些条件显然超越了纽约的机会结构。
政府也向风险投资提供了各种金融刺激,但亦在各个层面上对风险投资施加了各种各样的压力。深圳作为中国南方的科技领军城市,正是因为经济激励和政治自治的独特组合。在中国的其他城市也已开始推行试点项目,比如21世纪初在上海建设的创意产业园,21世纪10年代在北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附近建设的科技城,这些项目都成为创新综合体的国家样板。
通常情况下,中央政府通过推动创新的励志宣言来提供广泛的政策支持,比如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和2018年世界經济论坛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使用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中央政府支持这些声明,将一些意在“本土”创新的大型项目官方认定为“国家”空间,这为园区建设和人才招募带来了丰厚的资金,这些人才包括外国专家和在海外受过教育或正在海外工作的中国人。市区两级政府通过以优惠价格租赁土地、建设基础设施、向包括国内初创企业在内的企业提供直接租金补贴等方式做出贡献。尽管这导致了不同城市的地区间竞争,但这确实给许多中国城市带来了更多梦想成为“创新之所”的机会。
每个国家都希望通过发展尖端数字科技成为21世纪的引领者。嵌入这个普遍梦想的概念就是“创新”。如科技产业一样,创新源于合作和竞争,需要宽带、数据中心、实验室和办公室等更广义的基础设施。显然,各国政府和大型科技公司拥有建立这些基础设施的资源。但是地方官员同样起着关键作用。创新的蓬勃发展取决于城市的物理空间密度、文化多样性,同样取决于投资者、研究人员及培育创业者的市场地理集中度。然而,城市世界是复杂的。因为每个城市都想成为“创新之所”,地方官员们整理土地、培训从业者、招引产业投资者,这些要素将构成一个“创新综合体”,推动城市的经济增长。
纽约和中国城市之间有许多差异。但纽约的经历或许会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创新创业”这一话题在深圳和在奥斯汀一样为人熟知。公共、私营和非营利部门之间的组织伙伴关系,特别是当地企业、政府和大学的“三螺旋”合作模式,在杭州和在西雅图同样重要。软件和硬件的设计空间重塑了上海和布鲁克林的社会地理。
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纽约的故事,而是世界上每个城市都在发生的变化。了解科技产业的成长是如何发生的、科技公司是如何融入城市权力结构的,以及城市居民如何在从数字技术中受益的同时控制其使用方式,对每个人而言都至关重要。创新需要我们去比较经验和分享观点。而城市必须管理新技术和社会性社区的融合;它们必须将变迁的叙事从个人创业转向为了所有人的创新。
35495003382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