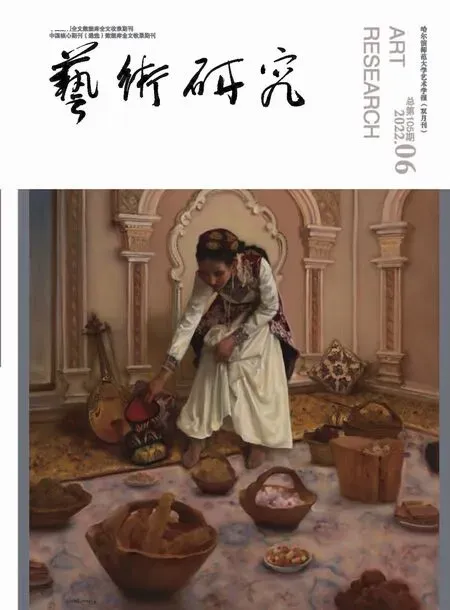新文科背景下古典舞“身韵”课程的探索建构
2022-02-27厦门华厦学院柯心宇
厦门华厦学院/ 柯心宇
2019 年,教育部中央政法委、联合科技部等13 个部门共同启动了《“六卓越一拔尖”激活2.0》,提出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旨在推进高校教育服务社会经济发展能力。在我国对于新文科的定义是这样的:它是以全球经济一体化、科技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为背景,打破传统文科思维方式,继承传统,突破创新、学科交叉相互融合、不同文化资源协同共享为途径,来促进学科的交互与深度融合,从专业分割到交叉融合,为新时代培养复合型文科人才。从而新文科建设成为了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任务。高校舞蹈专业的特色建设也从属与新文科建设,如何根据新文科的核心去促进高校舞蹈专业的建设改革成为了一个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故而舞蹈课程的建设可立足于新文科的发展背景下,从中国古典舞课堂训练的角度出发,就其课堂体系的多元建设路径进行探索。
一、古典舞的“来龙去脉”
“中国古典舞”一词在并不是古代传承而来,而是现代艺术的产物。作为“非直接传承”的中国古典舞艺术,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审美的根基上,以现代人的审美眼光与想象来重现古代舞蹈风格姿态的“新”古典舞蹈艺术。在“新文科”建设的内涵追求中,中国古典舞的建设之路有着与其相似的价值取向,都主张在多元共存、相互融合中构建新的文化机理,从而实现“新知识”的生产。
(一)中国古典舞的学科机理
中国古典舞学科的建设是我国立足于中华传统舞蹈的基础之上,以现代性文化建设为其核心,而建立起来的反映我国传统舞蹈文化核心的学科体系,故而其核心就是立足于传统舞蹈基础与新文化建设的核心。其观念的本质上即立足于多学科相互借鉴交融的文化建构。
于平在《“身韵”的价值与中国古典舞的学科建构》中发文提出:“中国古典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类概念’,而是一个专属名词”,即作为一个专属名词的中国古典舞是狭义的概念,主要所指的是在解放后以戏曲舞蹈为基础,由我国艺术家借鉴芭蕾的训练体系,吸收戏曲、武术、民间舞蹈中的养分,以当代审美和舞蹈特性为出发点,创造出来的具有古典韵味与典范意义的舞蹈形式;广义上的中国古典舞应该包括中华历史上各个时期具有不同风格的古代舞蹈,从此角度出发,汉唐舞、敦煌舞都可作为某一历史时期特定的古典舞,在多元视域下反观中国古典舞的学科建设,其本身就有着历时性与共时性相互交融的本质特点,即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文化的精华汇聚于一身的特征。中国古典舞极具东方审美韵味,能够体现出中国传统舞蹈的神思妙意,对于传承并发展中华优秀的传统舞蹈、找寻中国传统舞蹈本体属性、深挖中国传统舞蹈内在深蕴都有着深刻意义。
(二)身韵课程的内涵建构
在上世纪80 年代,在欧阳予倩先生主张的领导下,中国古典舞“身韵”这一教材横空出世,成功为我国古典舞学科建设指明了确实的实践道路。此时的身韵课程着重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创建符合我国特色的古典舞教材,于是吸收戏曲、武术等的养分成为了发展中国古典舞的整理发展方式。而后伴随于民族意识的不断觉醒,从“前身韵”时代跃进到“身韵”的不断发力,作为基础教材的“身韵”所着力解决的问题便成为了发展属于本民族独特审美的运动方式,构建基于中华传统舞蹈上的训练教材。
可见“身韵”训练课程的出现基于两个方面:“继承戏曲、武术、民间舞蹈文化的精粹;提炼中华文化的审美特性。”在半个世纪多历经几代舞蹈人的艰辛努力,中国古典舞的课堂教学已经初步构建成以基训——身韵——技术技巧——剧目为一体的学科教学体系,身韵课程作为掌握凝练舞蹈风格属性的关键要素,在教学体系中一直居于重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身韵”课程是对于中华文化审美特性的提炼与升华,但中华文化审美特性的提炼并不局限于戏曲与武术之中,于绘画、诗词、建筑等其他艺术中也能是中华审美文化特性的优秀体现,这就决定了“身韵”课程的未来发展,并不局限于从戏曲、武术中吸取养分,而是能够从各类艺术门类中广采博收,不断扩展其外延成分,丰富内在涵养,这就与“新文科”提倡的各学科协同发展、共享资源促进文化深度发展的要求不谋而合。
二、身韵的课程定位与“新”发展转向
对于身韵而言,其最初的课程体系定位便是培养具有我国特色的舞蹈表演人才。1954 年“舞蹈教练员训练班”的启甸,便是着力于编写教材,培养民族舞蹈表演人才——“身韵”课程的出现便是世纪洪流中的一大“创举”。但关注于当下的民族文化审美,作为“新创”的中国古典舞更有着贴近于眼下的时代特色。以“新”文化的诉求来呼唤中国古典舞的发展,这就更需相同的理念与价值取向来丈量未来之路。
(一)身韵课程的定位与目的
新时期以来,“身韵”课程由以戏曲动作为内核的艺术逐渐转变为以把握本体含义作为内在要素的艺术,在逐渐地探索过程中,形成了由“身段”到“身韵”的转变,而这恰恰是古典舞艺术自觉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精粹的直接体现——即由“传神”到“气韵生动”。“身韵”基础课程的建设展开了中国古典舞从“以形写形”到“以形写意”的探索,由此逐渐构建起中国古典舞的文化意味与审美风尚。
从新文科注重学科交融,以不同学科知识应用于解决重点问题的角度来看,“身韵”课程建设的模式已然从传统舞蹈传承的角度向着新知识体系生产的角度所转化,即将传统舞蹈的形式要素与文化内涵加以提炼,创造新时代符合新思想内容的中国传统舞蹈的古典精粹。《易经》有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身韵”课程的建构是独属于东方神韵的表达方式,正所谓“行未到而神先到”“行止而神未止”,便是“身韵”课程对于追求自身之道的体现。在长期的求索中,“身韵”课程体系建立起了自身的“八字口诀元素训练法”,“三圆”动作运动路线,“离合反始”运动规律等一系列标准,并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取得了极为出色的效果。如果说“基训”解决的是“能够”跳舞,那么“身韵”课程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跳舞,并在后续的作品中“会”跳舞,可见“身韵”课程在整个的人才培养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新文科理念与身韵课程之耦合
早在20 世纪初期,由吴晓邦先生提出的构建中国舞蹈学科的设想也伴随着实践不断细分下去,从而完成了“中国舞蹈学”学科体系框架的搭建。分科式的舞蹈学科体系设置,其效果是极为显著的。但于此同时,过度细化的学科体系建设所存在问题也逐渐的浮出水面,面临着人才培养类型单向深入、知识架构单一等诸多问题。
纵观当下,各个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定位目标仍局限于自身专业领域以内,会编不会跳,会跳不会理论……拥有优秀能力的舞者不少,但真正“会”跳舞的舞者却屈指可数。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吕艺生先生率先提出了培养“H型”舞蹈人才的理念主张,即舞蹈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应兼具表演、编导或其他能力,这是一个双向人才甚至是多维度人才的概念。新文科建设是一个没有边界局限的概念,它应该是多维共存,向外扩展的,而这样的不断扩展也正符合于信息时代、互联网时代对于多元型人才的需求。反观于中国古典舞课堂训练建设来说,“身韵”课程更应该致力于“H 型”人才培养的基础环节。通过“身韵”课程的纵深发展,增强学生思辨性、思想性能力;通过向外、延展式交融,扩充学生知识体系与创新性能力。且在当下新文科建设的总体趋势下,社会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能够跳舞的演员,而是真正会跳舞的人才,高校舞蹈教育则更应该整合资源,着力发展多元交互共融的“身韵”新课程体系,来完成新文科建设理念的实践落地。
三、“新”理念下“身韵”课程的探索建构路径
在新时代不断强调文化自信的时代诉求下,将新文科建设与“文化自信”相结合成为许多学者聚焦的落脚点,也是中国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时代要求。但是如何将新文科建设的目标与发展逻辑落实于舞蹈学科的建设之中,还需要根据舞蹈自身发展的优势与特点去不断地深化实践进程。关于现当下“身韵”课程的建设中,许多高校已经在课程体系搭建、人才培养模式上做出了许多成果,如北京舞蹈学院的《身韵巡礼》、山东艺术学院的《诗境嵌入式课堂教学》、四川音乐学院的中国古典舞身韵组合课程中川剧元素的融合探究——以旦角的人物形象塑造融合为例等等,此类课程的建设都是高校对于身韵课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这不仅仅是符合身韵课程提炼中华文化审美特征的本质特色,更与新文科建设的构思向度相吻合,诸如此间课程的不同探索,已然证明了身韵课程与新文科建设在本质上的相融性。
(一)植根传统架构内涵扩展
在“身韵”课程之中,应该继续扩展传统舞蹈的形式外延,将戏曲舞蹈、民族舞蹈、民间武术的内容加以提炼加工并解构,以“身韵”审美标准为内核进行重构,从而完成“形”的创造,在继承传统文化审美的基础上,建构“神”的风范。在“身韵”课程的建设中,“形神”作为实践层面的内外准则,理应得到充分的关注,但理论性的课堂内容也不可忽视,应该在教学过程探索古典舞审美领域的核心问题。中华文化的审美意象作为一种标准,其所存在的领域并不局限欲于舞蹈之中,我国古典诗词绘画、庭院建筑中,身心、意象作为传统审美上的规范范畴是共通的,故“身韵”课程的建设也应该深入挖掘古典美学意象,注重提炼素材内容背后的历史遗存,将道德观念、人文哲思加以整理,形成理论基础,在课堂中加以推行。
(二)汇源聚本整合多元体系
中国古典舞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汉唐派”“戏曲派(身韵)”“敦煌派”“昆舞派”并立的局面,但追究其实质,四者都是依托于传统文化的沃土中而形成的“当代”中国古典舞,这就决定了三者有共同的文化内核基础。“身韵”讲求“形神劲律,以气导形”,“汉唐”讲究“质朴敦厚、韵律天成”,“敦煌”讲究“飞舞流动,洒脱劲健”……而在不同的形态律动中,却都讲究“韵味”与“动势”。将古典舞体系加以整合,并不是说以“身韵”课程为主导,其余流派服务于“身韵”课程,而是建立起体系相合的概念,以“一体多元”的理念思路丰富“古典舞”课程的多元探索,这一点可以从西方芭蕾舞的风格之辨来吸取一定的经验。古典芭蕾时期作为芭蕾史上的顶峰,确立了古典芭蕾的审美规范,古典芭蕾虽以俄罗斯芭蕾为典型代表,却并未对其余五大流派的芭蕾艺术产生阻碍。相反他们彼此之间是相互成就的关系,而流派之间的不同是受到了不同训练体系的影响。俄罗斯芭蕾从本土特色出发构建起属于斯拉夫民族的训练方式,注重高大飘逸气质的凝练,而丹麦芭蕾则是立足于本土海洋文化的根基上,构建起属于自身飘逸抒情审美的训练方式,但他们却又都统一于古典芭蕾的的审美标准下,并在彼此的借鉴中吸收对于自身有益的养分以促进其自身特色的定式。我国千年历史积淀,文化体量极为庞大,历朝各代不同的意识形态必然也会塑造出不同形态的传统舞蹈艺术,尽管其所偏向的审美特征有所不同,但其总体基调是立足于文化的根脉之上的。于是,身韵课程的建设有必要开启新的历史原点,以不同的训练体系建立起课程建设的多元探索,整合体系,冲破风格程式的束缚,建立起整体韵律的规范,从而为“身韵”课程的发展变化找到新的养分,在中华历史的长河中将中国古典舞的面貌逐渐的明晰起来,建立起中国古典舞的当代神韵。
(三)交叉建构促进系统完善
“身韵”课程体系的架构具有着鲜明的实用意义,即创建具有民族特色的、适用于我国传统舞蹈教学体系的课程素材,其本身就富有着多元交叉的内涵:我国人民在长久的历史中创造了极为丰富的传统舞蹈,风格多样,体系多元,是一个十分丰馈的舞蹈宝库;自古以来的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决定着我国舞蹈有着向其他艺术门类靠拢的潜力;民族舞蹈中极为特色的技巧存在有着杂技技艺的身影。但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中,学科交融就不仅仅在于诗乐舞之间的相互融合,而是可以构建更为多元的学科交叉模式。将舞蹈与图像学相结合便是一种确实可行的方式,以此来构建舞蹈图像学的基础理念:将静态的雕塑图画变为活的动态舞姿并不是无稽之谈,从而身韵课程的建设增添更为多元的文化基础,构建属于本民族自身的传统舞蹈文化特征。当梅兰芳从古代仕女图中寻到舞姿,孙颖依托于文物古籍建立“汉唐古典舞”,高金荣从敦煌壁画雕塑中找到了“敦煌舞”的姿态神韵,刘凤学从古籍记载中复排出了“仿唐乐舞”时,便可见从姊妹艺术中找寻舞蹈创作的契机并不是不可能,且在当下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下,我国出土的各类文物中拥有着大量的乐舞资料,至今尚未进行体系、系统的整理,若进行深入的挖掘整理,将静态的动作编创成为活的舞姿,无疑能够丰富“身韵”课程的内在深度与文化价值。
四、结语
传统的分科式教育一直以来术业有专攻的学科思维模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自洽的学科体系模式,在学科划分中促进了具有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深入,这是老文科思维对于舞蹈学科建设的积极影响;在新时代社会的转型以及对多元人才的需求,促使着对于舞蹈人才的培养也从单一的专业人才转向重视多元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因而,新文科建设的思维模式,对于新时代舞蹈艺术向前的更进一步发展、舞蹈人才的培养、舞蹈特色课程的设置都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身韵课程的建设,一直以来都是在追根溯源的历程中不断前行,在新文化建设的诉求中,“身韵”一方面要反映新文化建设的内涵,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反思自身症结所在。长达三十余年的体系之争,正如引路之灯吸引着中国古典舞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呈现出理论先行而实践随后的发展趋势,这与我国古典舞复杂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语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其所归根的是在于实践中能够赋予教育的实际含义。思想多元的碰撞演变成为丰富我国舞蹈艺术的实践动力,从而构建符合我国传统舞蹈美学特征的典范舞蹈。处于新文科建设的时代背景下的“身韵”课程建设,更是要明确其内在深度与外延广度,打破专业壁垒,建立自身审美标注,在继承创新的交织融合中,保持自身特色,深化文化内涵,发挥自身优势,更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课程体系的充实,为“新文科建设”与“文化自信”的确切实施迈出坚实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