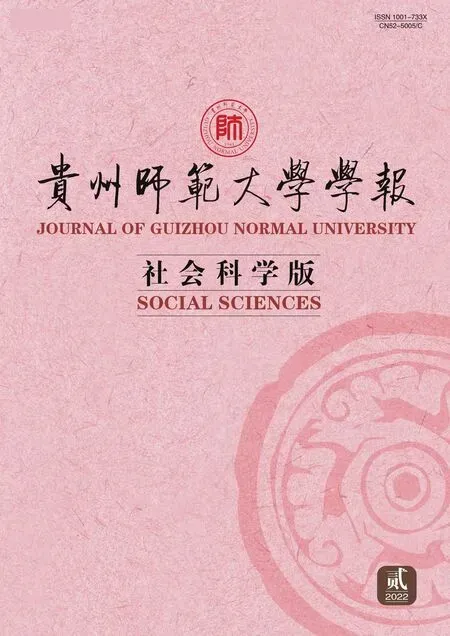舞蹈作品侵权认定的误区与匡正
——兼评我国首例“静态手段侵犯舞蹈作品版权”案
2022-02-26吴梓茗
何 敏,吴梓茗
(1.2.华东政法大学 知识产权学院,上海 200042)
2020年11月30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就备受舞蹈界与法律界人士关注的“杨丽萍诉云海肴公司餐厅装潢案”(以下简称“月光舞蹈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云海肴(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海肴公司”)等三被告将杨丽萍本人创作的舞蹈作品《月光》通过图案形式复制在屏风、墙画、隔断上并作为餐厅主体装潢的一部分置于餐厅显眼位置,同时在“云海肴·云南菜”的官方网站以及微博首页擅自使用涉案作品进行信息网络传播的行为,侵犯了杨丽萍公司就舞蹈作品所享有的复制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
该案是我国首例因将舞蹈作品制作成静态图案而被官方认定构成版权侵权的民事案件[1],其对舞蹈作品保护范围的界定以及侵权认定规则的适用逻辑或对后续其他法院处理类似纠纷的裁决思路产生持续影响。但在笔者看来,该案判决所持观点以及相应的论证理由尚存可商榷之处,亟需理论界作出合理回应。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月光舞蹈案”判决入手,逐一分析并澄清其中所存在的认识误区,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以静态手段侵犯舞蹈作品版权”的具体认定标准,以期为日后舞蹈作品侵权纠纷的处置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1)本案原告主张应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包括《月光剪影》图画、《月光》舞蹈,以及拍摄《月光》舞蹈的视频。由于原告未能提交其对美术作品《月光剪影》图画享有著作权的有力证据,且美术作品并非本文的讨论重点,故本文仅就法院在《月光》舞蹈以及拍摄《月光》舞蹈的视频这两个问题的说理展开分析。。
一、单个舞蹈动作是否具备可版权性
在版权侵权案件中,只有诉争客体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原告才有继续主张权利保护的可能,“月光舞蹈案”的审理同样遵照这一逻辑。该案判决开篇便明确指出,“《月光》舞蹈……通过其手臂、腰肢、臀、腿、膝等部位作出展现女子身体曲线之美的舞蹈动作,上述连续的舞蹈动作转化为抽象、多变的肢体语言,在灯光、舞美、服装、音乐等元素的配合下,艺术化地表现了月光的圣洁以及月光下女人的柔美。上述极具个人特点和表现力的《月光》舞蹈……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舞蹈作品”(2)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32020号民事判决书,第23页。。
但是,在明确《月光》的作品属性之前,判决书在界定舞蹈作品的保护范围时,认为“舞蹈作品的独创性不仅可以体现为静态的舞蹈姿势,亦体现在动态的舞蹈动作的连接、编排、组合中,当然,已属公有领域的传统舞蹈动作不应为个人所独占”(3)同上注。。在反驳被告“被诉装饰图案为静态呈现,不具有连续性,不存在侵害舞蹈作品著作权的可能”的观点时,法院指出,“舞蹈作品的独创性在于每个静态舞蹈动作的连接设计和集合,故每个静态的舞蹈动作亦是舞蹈作品独创性体现的重要组成部分”(4)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32020号民事判决书,第26页。。可见在法院看来,单个舞蹈动作存在公有领域与非公有领域之界分,未落入公有领域的单个舞蹈动作应当是著作权法的保护对象。其所谓“静态的舞蹈姿势本身具有独创性,因此可以单独受到保护”的观点,不但在先前的司法裁判中有所体现(5)如在“王晓玲诉北京市朝阳区残疾人综合活动中心著作权纠纷案”中,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作为舞蹈作品而言,其独创性体现在动作本身具有的独创性,以及动作与动作之间的连接上”。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06)朝民初字第18906号民事判决书。,在学界也同样存在部分支持的声音[2][3]。
本文认为,就单个舞蹈动作而言,不存在所谓公有领域与非公有领域的区分一说。事实是,单个舞蹈动作哪怕从外观上看起来再为新颖,技术难度再高,也是决不可能从公有领域控制范围内逃逸出来而获得版权保护的。原因有三:
首先,与书面文字、动态连续影像等人类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智力成果不同,人类自诞生之日起,身体的各种动作便已如影随形。受制于外部构造和内在机能,人体实际能够做出的动作从数量上看仍是较为有限的。对此美国学者Evie Whiting早就指出,“动作不是凭空被创造出来的,而是不断被人类发现的。可见在版权领域,(单个)动作应当属于某种静待他人察觉而事先早已存在的客观事实”[4]。虽然与日常的某些动作(如跑、跳等)相比,舞蹈动作的产生还需一定的艺术加工,但后者不能脱离前者而单独存在却早已是不争的事实[5]。若将单个舞蹈动作当作作品保护起来,不但会使公众的日常之举动辄得咎,从长远角度来看,还有可能不当限制宪法所规定的公民依法享有的人身自由和权利(6)比如,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相信这绝非立法者的本意。
其次,与计算机程序等晚近才出现的智力成果不同,舞蹈在人类历史上可谓是源远流长。据文献介绍,最早有关舞蹈的文字记录甚至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的古埃及时期[6]。并且,抛开日常生活中人体在不自觉的状态下做出的动作不谈,人类喜爱模仿其他生命体动作的天性同样不容忽视。正因如此,在漫长的岁月变迁以及人类参与社会交往的过程当中,很难说舞蹈家“创造”出的某一看似新颖的动作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如果将单个舞蹈动作当作作品保护起来,不但会出现我国立法者担忧的“舞蹈作品数量过多”的尴尬局面[7],情况严重的话甚至还会像美国著名学者型法官波斯纳在谈及对思想的不予保护时所预测的那样,为了保护舞蹈动作,“法院将不得不界定每一个动作,划定其边界,确定它与其他动作的重叠之处,而且全部当中最为困难的是,确认被控侵权作品中的原创性动作”[8]。如此高昂的确权耗费,相信无论哪一国的司法机关都是极难承受,并且不愿负担的。为维护他人本不应享有的私权利而付出如此昂贵的公共成本,此种做法无疑与现代著作权法所追求的利益平衡的立法目标背道而驰。
再者,正如美国联邦版权局在其主编的《版权局实践规则概要》中所言,单个动作不能受到版权法的保护,与单个文字、数字、标记、颜色、形状不被保护的原因一样,并无本质上的区别(7)See U.S. Copyright Office, Compendium Of U.S. Copyright Office Practices § 805.4(D) (3d ed. 2014).。对舞蹈创作者来说,单个舞蹈动作就像是建造高楼大厦时必须用到的一砖一瓦(building blocks)。如果有人能将这些各自独立的动作垄断起来,这势必会不当抬高舞蹈从业者为了继续从事创作而不得不另行花费的搜寻与确权成本,最终可能彻底扼杀舞蹈作品的繁荣与长足发展。
另外,就像组成文字作品的每个字符一样,单个舞蹈动作并不能完整地展现作者内心的创作意图。抛开音乐、布景等其他创作元素的配合协调不谈,仅从混同原则的角度来看,单个舞蹈动作背后所能表达的思想感情也是极为有限的,对其施以版权保护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思想的垄断。
综上,无论是从舞蹈作品著作权保护的内在法理出发,还是出于推动舞蹈创作的繁荣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以及基于实用主义立场考虑保护效果的必要,对单个舞蹈动作提供版权保护都是不甚合乎时宜的。
二、动作之外的其他元素能否纳入舞蹈作品的范畴
或许是出于对“单个舞蹈动作可受版权保护”的观点根基不稳的担忧,“月光舞蹈案”判决书后续从法律层面对被告的行为性质予以界定时特意指出,“上述《月光》舞蹈中结合了人物造型、月光背景、灯光明暗对比等元素的特定舞蹈动作,并非进入公有领域的舞蹈表达,系《月光》舞蹈作品具有独创性表达的组成部分”,“根据被诉装饰图案与《月光》舞蹈作品的比对结果,被诉装饰图案展现的每个舞蹈动作均在《月光》舞蹈中有相同舞蹈动作可对应……故被诉装饰图案与《月光》舞蹈作品的独创性内容构成实质性相似”(8)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32020号民事判决书,第25页。。在后续否决被告提交的反驳证据的证明力时,法院再次强调,“本案确认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月光》舞蹈作品,保护的是将人物造型、月光背景、灯光等元素融合到人体连续的舞蹈动作中予以表达的整体”(9)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32020号民事判决书,第26页。。可见在法院看来,对于原告享有版权的舞蹈作品《月光》,即便其中单个舞蹈动作不能获得保护,这些孤立的动作与月光背景、灯光等其他元素的结合所形成的“独创性表达”作为舞蹈作品的组成部分,也应当纳入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笔者揣测,该案判决对舞蹈作品保护范围的此种界定,可能是对以往司法实践有关论述的直接借鉴(10)如在“杨波、李佳雯与淮阴师范学院、吕寅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涉案作品《碇步桥水清悠悠》“以碇步桥作为背景,从舞蹈的编排、舞蹈所用服装及道具,通过连续的舞蹈动作在灯光、舞美、服装、音乐等元素的配合下,整体呈现出一群着舞服的女子跨过小巧的碇步桥,展现江南特色文化,表达温润婉约情感的社会生活,体现出较高的独创性和艺术价值,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舞蹈作品”。参见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8民初145号民事判决书。,抑或是采纳了部分舞蹈界人士对舞蹈的学理定义(11)如舞蹈学学者隆荫培、徐尔充先生认为,舞蹈“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内,通过连续的舞蹈动作过程、凝练的姿态表情和不断流动的地位图形(不断变化的画面),结合音乐、舞台美术(服装、布景、灯光、道具) 等艺术手段来塑造舞蹈的艺术形象”。参见隆荫培、徐尔充:《舞蹈艺术概论》(修订版),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页。。但不论最终出于何种可能,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法院都是不宜将动作之外的其他元素纳入舞蹈作品的保护范围的。
(一)著作权法语境下的舞蹈作品≠日常生活中的“舞蹈”
首先要明确,不能简单地将我国《著作权法》中“舞蹈作品”的概念同舞蹈界人士乃至普通民众内心所理解的“舞蹈”一语的含义等同视之。
从立法层面来看,在提交给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我国《著作权法》的官方英文文本中,舞蹈作品的同义翻译是“choreographic works”,而非英语口语中经常使用的“dance”(12)资料来源:https://wipolex.wipo.int/zh/text/186569,2021年7月23日访问。。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主编、我国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对“dance”一词的定义是“伴随音乐节奏而挥动的一系列动作与步伐”(13)参见《牛津英汉高阶英汉词典》(第七版·大字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02页。原文表述为“a series of movements and steps that are usually performed to music”。;而该词典对“choreographic”的名词形式“choreography”的定义则是“在舞蹈(dance)尤其是在(in)芭蕾舞中设计、编排步伐与动作”(14)参见《牛津英汉高阶英汉词典》(第七版·大字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38页。原文表述为“the art of designing and arranging the steps and movements in dances, especially in ballet”。。可见从语言学视角来看,“choreographic work”的范围明显要小于“dance”,其专指在舞蹈中对具体动作的编排,也即编舞。倘若再进一步细究起来还会发现,“choreography”一词实际上是由希腊词汇“choreia”与“graphikos”组合发展而来,前者指代舞蹈(dance)而后者指代编排(write)[9]。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何国际邻接权条约将舞蹈表演者称为“dancer”而非“choreographer”(15)以《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为例,该条约第2条第(a)项将表演者定义为“actors, singers, musicians, dancers, and other persons……”。。
以上结论同样可以从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解读文件中得到证明。《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以下简称《伯尔尼公约》)及其官方指南虽然没有对“choreographic works”下正式定义,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帮助各成员国理解公约有关术语内涵所编写的《著作权与邻接权法律术语汇编》一书中,明确将其定义为“(常与音乐相辅的)舞台舞蹈动作或其他模仿性连续姿态的组合物”(16)See WIPO, WIPO Glossary Of Terms Of The Law Of Copyright And Neighboring Rights, Geneva: WIPO Publication No.816 (E), 1980, p.30. 原文表述为“A composition of movements for stage dancing or any other patterned succession of gestures mostly created to accompany music”。,无疑再次强调和说明了动作(姿态)的独立地位。研究《伯尔尼公约》的权威学者同样认为,公约语境下“choreographic works”的本质是“动作作品”[10]。鉴于我国已经加入《伯尔尼公约》,且基本仿照公约第二条第(1)项的诸项列举在《著作权法》中逐一规定了各种作品类型,故对我国立法中舞蹈作品内涵的理解,也应当与国际公约保持一致,以免出现歧义。就此来看,著作权法语境下的舞蹈作品只能覆盖到具体的动作设计,并不涉及对动作之外其他创造性元素的保护。
(二)通过动作比对判断是否侵犯舞蹈作品版权为各国司法通例
现实生活中,舞蹈作品大多以舞台演出的方式向观众呈现。必须承认,除却动作编排之外,合适的服装、顺时变换的灯光以及彰显意境的舞台背景等巧妙设计,对于一场优秀的舞蹈表演来说同样不可或缺。但需要澄清的是,就舞蹈作品而言,动作设计是否相同或相似才是判断不同舞蹈之间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某一在先的舞蹈动作本身并不符合舞蹈作品的构成条件进而不能得到版权保护,即便他人在后续的舞蹈表演中使用了与在先的舞蹈相同的配乐、服装以及灯光设计等元素,法院也不能径直认定舞蹈作品侵权成立。这与服装、舞美以及背景音乐等辅助性要素在符合相应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可单独作为美术作品、音乐作品等其他作品类型获得著作权法保护的基本规则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如果强行将这些非动作类元素纳入舞蹈作品的保护范围,可能会过度扩张权利人的私有领域,破坏著作权法与之相匹配的利益平衡机制(17)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对于用已发表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以及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已出版的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由于舞蹈表演往往与音乐相伴,为避免创作人借助舞蹈作品而对音乐著作权的法定许可绕道,扩大自身著作权范围的考量,应对音乐作品与舞蹈作品作出明确区分,明确各作品的独立地位,防止著作权的冲突。参见蓝纯杰:《“一台子戏”的著作权法保护秩序重构》,载《政法学刊》2020年第3期,第57页。。
从比较法层面看,各国司法机关对于上述原理已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例如,美国伊利诺斯州北部联邦地区法院在审理Myers v. Harold案时便认为,虽然被告未经许可组织人员在舞台上表演原告的舞蹈作品时,并未使用原告向联邦版权局登记作品提交的视频中出现的同款道具与服装,但这丝毫不影响法院就此得出被告侵犯了原告舞蹈作品版权的结论,因为仅仅是改换服装并没有改变(transform)舞蹈作品本身(18)See Myers v. Harold, 279 F. Supp. 3d 778, 800.。再如,德国慕尼黑地区法院在审理Godspell案时同样指出,虽然被告拍摄的照片将作为原告的乐队组合在舞台上跳舞的姿态拍了下来,照片上也的确出现了舞台设计、布景和原告佩戴的面具等其他元素,但法律对舞蹈作品的保护并不延及动作编排之外的事物,舞台设计、背景布置等辅助性元素并非舞蹈作品所要保护的对象(19)See GRUR 1979, 852.。
但在我国,目前法院的认识和做法则是略显混乱的。比如,“月光舞蹈案”的审理法院曾在审理《千手观音》舞蹈作品著作权归属一案时肯定地指出,“鉴于舞蹈作品《千手观音》系在音乐的伴奏下由聋哑演员表演并由四位手语老师分别站在四个方向进行辅助性指导,因此确认该作品的作者不能仅凭舞蹈的音乐、服装、灯光、舞美等元素的设计,而在于动作与音乐的结合,能够使特定的演员表演特定的动作形成特定的组合达到可确定的艺术效果”(20)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5)海民初字第17304号民事判决书。。而在“月光舞蹈案”中,在单个舞蹈动作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前提下,该法院仍以单个舞蹈动作同所谓的“人物造型、月光背景、灯光明暗对比”等元素的组合与被诉图案进行对比以判断二者之间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此种判断径路不但与国际上共识性的实践做法不符,同时也与本案法院以往所奉行的裁判规则相悖,是值得商榷的。
(三)不应混淆舞蹈作品与其他作品类型各自的保护范围
回到“月光舞蹈案”来看,即便如判决书中所言,“舞蹈作品保护的是将人物造型、月光背景、灯光等元素融合到人体连续的舞蹈动作中予以表达的整体”,但在后续审理过程中,法院实际上却是将拍摄《月光》舞蹈的视频截图与被诉装饰图案放入同一对照组,并在认定“被诉装饰图案展现的每个舞蹈动作均在《月光》舞蹈中有相同舞蹈动作可对应”的前提下,得出“被诉装饰图案与《月光》舞蹈作品的独创性内容构成实质性相似”的结论(21)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32020号民事判决书,第36-41页。。由此不禁会引发新的疑问,即法院此时希望保护的独创性表达到底为何?
首先,如果保护的是每幅图案里特定的舞蹈动作,在被告选择将呈现一定动作姿态的图案分散印在餐厅不同位置,而并未以某种特定的逻辑顺序进行编排的情况下,仅以“十余幅被诉装饰图案所体现的舞蹈动作均能够与《月光》舞蹈作品的相应动作一一对应”作为依据认定被告侵权是否合理?抛开双方孤立比对的单个舞蹈动作均不具备最低限度的独创性,无法直接作为比对对象的结论不谈,事实上,该案法院曾在审理“茅迪芳诉张继钢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时就已明确指出,“动作的比较应是两个舞蹈连续性的可表达一定思想情感的完整动作的比较”,并认为“茅迪芳对《吉祥天女》与《千手观音》舞蹈部分动作的比较不是完整的舞蹈结构和舞蹈画面的对比,而是选择画面的片断进行对比,如同选择两部小说中的字、词甚至笔画进行对比,不能据此判断作品的思想表达相同或相近似”(22)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6)海民初字第26765号民事判决书。。前后两案同一受理法院裁判思路转变缘何如此之大,实在是耐人寻味。
其次,如果保护的是“人物造型、月光背景、灯光等元素融合到人体连续的舞蹈动作中予以表达的整体”,那么这里就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将未被录影机固定的人物造型、月光背景、灯光以及舞蹈动作等元素视作一个整体进行保护。这种解读看似符合文义解释的要求,但细察起来却难言合理。
从该案原告提供的证据情况来看,《月光》表演中使用的月亮背景更多是对现实世界中月亮样态的真实还原,并无多少独创性可言。即便如原告所称,“在月光背景下以人物剪影的形式进行舞蹈的创意由杨丽萍首创”(23)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32020号民事判决书,第7页。,但这一创意仍然属于思想的范畴,而非具体的表达。对于舞蹈表演时所投射的灯光,法院也已查明,“在不足五分钟的连续画面中,前四分钟内并无任何镜头切换、光线、音效等方面的变化,仅在临近尾声处出现一次全景、近景的调整”(24)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32020号民事判决书,第29页。。尽管2020年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已从“作品类型封闭”的立法模式转变为“作品类型开放”,但如此单调乏味的灯光投影只怕也很难视作“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25)参见2020年《著作权法》第三条第(九)项。。
既然上述辅助性元素无法单独获得保护,那么这一结论自然也不会因为其与舞蹈动作的简单结合而发生转变。虽然一整套舞蹈的精彩呈现是灯光师、动作设计师以及舞者等不同工种人员共同合作的结果,但这并不是说每个个体的劳动付出都可以成为作品并受到著作权法保护。法院必须在著作权法的框架下,区分不同人、不同性质的劳动来决定哪些劳动成果构成作品,以及归入哪一类别的作品加以保护(26)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0)京73民终5号民事判决书。。
第二种解释则恰好相反,是指将通过录影机固定下来的、承载“人物造型、月光背景、灯光、动作等”要素的连续画面视作一个整体,而法院则通过阻止被告对这些画面的非法利用来实现对原告权益的维护。
此种解读能够经受住著作权法基本原理的检验。虽然月光背景、灯光投影等元素无法单独获得版权保护,但在舞蹈表演被录影机录制下来后,这些元素便已成为连续影像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而可能以视听作品等途径获得法律保护。以与录影技术成果表现形式相近的摄影技术为例(27)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73民终797号民事判决书。,摄影作品的独创性既可以体现在摄影师对拍摄角度、距离、光线和明暗等因素进行的个性化选择,也可以是对被拍摄的场景和人物作出的具有独创性的可以体现独特表现力的安排[11]。即便被拍摄的对象并非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客体,但拍摄者在摄制画面时所作出的个性化安排完全可以独立于被拍摄的对象而单独获得保护(28)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9)京73民终3812号民事判决书。[12],这是摄影、视听作品之所以能从早期被认为是“单纯对事实的记录”发展成为独立作品类型的根源所在。
以上结论的证成表明,在“月光舞蹈案”中,原告要想保护“人物造型、月光背景、灯光、动作等”众多元素通过有机组合形成的整体性成果,此时妥适的选择应该是以视听作品(29)为表述简便,本文不再考察该案中的视频是否因独创性不足构成录像制品,统称为“视听作品”。由于单帧画面是否属于摄影作品至今仍有争议,且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故不再赘述。权利人的身份向法院寻求救济,以画面拍摄所蕴含的独创性贡献为依据主张权利。这也从侧面再次证明,该案审理法院认为这一整体性成果应纳入舞蹈作品获得保护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易言之,对舞蹈作品保护范围的解释不能使其他法定作品类型的存在失去价值。
事实上,确立舞蹈作品与视听类作品版权保护之间的合理界限,同样是各国的共识性做法。在立法层面,以印度《版权法》为例,该法虽然将舞蹈作品作为戏剧作品的一项子类予以保护,但也同时规定,“戏剧作品包括以书面或者其他方式固定下来的朗诵片段、舞蹈作品或哑剧表演,但以电影画面的方式加以固定的不在此列”(30)See Indian Copyright Act, Article 2 (h). 原文为“dramatic work includes any piece for recitation, choreographic work or entertainment in dumb show, the scenic arrangement or acting, form of which is fixed in writing or otherwise but does not include a cinematograph film”。。与印度相似,澳大利亚(31)Australian Copyright Act, Section 10 (1).、新西兰(32)New Zealand Copyright Act, Article 2 (1).、新加坡(33)Singapore Copyright Act, Article 7 (1).等国家立法也有类似的规定。从实践层面来看,以美国为例,联邦版权局在其工作手册中明确说明,如果登记申请人向版权部门提交登记的舞蹈作品是以戏剧作品或者视听作品的组成部分的形式出现的,那么将来能被保护的只限于(only extends to)其中的舞蹈作品(34)See U.S. Copyright Office, Compendium Of U.S. Copyright Office Practices § 805.8(A) (3d ed. 2014).”。在理论界,学者Leslie Erin Wallis曾明确指出,“舞蹈作品并非……是用电影胶片记录下来的事物(which is filmed),而是通过舞者的姿态和动作来对外呈现的具体表达”[13]。而学者Patricia Solan Gennerich在评价有关舞蹈作品侵权纠纷著名的Horgan案时(下文将详述)更是认为,在分析两张拍摄舞蹈的图片中的舞蹈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时,事实认定者(trier of fact)需要将图片中出现的无关(extraneous)因素统统排除出去,如服装、灯光效果、舞台布景等[14]。一言以蔽之,视听作品可以是对连续舞蹈动作的固定与呈现,但在著作权法上,舞蹈作品的权利人只能阻止他人对动作的非法利用,不能将视频拍摄者为拍摄画面而单独作出的独创性贡献据为己有。
关于舞蹈作品与视听作品的区别保护,支持“月光舞蹈案”审理逻辑的学者在反驳“对舞蹈作品而言,静态使用难以构成对动态作品的侵权”的观点时,其所持立场为,“在判断著作权侵权时,应判断被控侵权作品与权利作品之间的相似性部分是否构成来源于权利作品的独创性表达,而无需考虑实质性相似部分是否构成权利作品的作品类型”[15]。然而,该案的真正症结在于,面对原告同时提出的保护舞蹈和录制视频连续画面的诉讼请求时,法院并未准确界定舞蹈作品的保护范围,甚至将本应由视听类作品保护的独创性表达强行视作舞蹈作品予以保护,这才造成法律适用上“四不像”的窘境。换言之,该案审理法院错在对权利作品的性质认定不清,而前述学者之观点考虑的却是被诉侵权图案性质的界定不明,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联。阐明被侵权人享有权利的具体作品类型,不但是判断其是否能获得保护的基础,同时也严格限定了该作品类型能够获得保护的表达范围,这也为后续实质性相似的判断留足必要铺垫。将著作权客体认定同著作权侵权认定割裂开来、孤立看待的做法,显然与著作权法基本原理不符。
三、以静态手段利用舞蹈作品何时构成版权侵权
在厘清了前述两方面的争议问题后,回到“月光舞蹈案”来看,被告仿照原告视频中的数幅静止画面将相应图案随意分散印在屏风、墙画和隔断上的行为,之所以不构成对原告舞蹈作品的侵权,源于舞蹈作品只保护“连续”的“动作设计”而不覆盖动作设计之外的其他元素。其中关键,一在连续,二在动作。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以上结论在司法机关面对被告以动态方式利用舞蹈作品的行为(如未经许可在公开场合表演舞蹈,或者不经允许在网上传播权利人舞蹈表演的视频)时,并不存在任何法律适用上的障碍。因为不管是现场表演,还是传播舞蹈视频,这些利用方式本身就能完整呈现舞蹈动作转换时天然便具有的连续性。然而,如何在以静态方式利用舞蹈作品的情形之下认定被控侵权者的法律责任,并未因为上述两方面争议问题的厘清而告终结。在现有的立论基础之上,该案还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当所有的舞蹈动作均以静止状态向公众呈现时,何种使用方式才会构成对舞蹈作品的完整(实质性)利用从而落入作品版权人的控制范围?这里不妨对涉案情形作如下改动:如果被告并未将图案分散印于餐厅各处,而是按照视频播放的顺序随机进行截图,并在某本向顾客展示的印刷手册上按照动作出现的时间顺序将这些截图照页码依次排列。遵循这一假设,被告此时利用的便不再是杂乱无章的一堆动作,而这些动作从表面上看也满足“动作的比较应是两个舞蹈连续性的可表达一定思想情感的完整动作的比较”的要求。但与观看现场表演以及重播视频不同,普通公众似乎无法通过这一系列静态的照片集合直接感知到舞蹈作品的动态美感。在该种情形下,如何判断被控侵权人是否连续、完整地利用了权利人的舞蹈设计,便成为司法机关不得不面对并需要单独作出解释的一道难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将直接决定舞蹈作品权利人在著作权法下所能获得的保护水平。
由于以静态方式复制舞蹈动作引发版权侵权纠纷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尚属首次,未能引发广泛关注,因此在我国,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务运用,当前并未出现能对上述问题进行正面回应的代表性观点。而从比较法的视角来看,在全球主要国家中,当前能够公开查询到的也只有发生在美国的Horgan v. Macmillan Inc.案(35)该案是目前能够公开查询到的美国涉及舞蹈作品侵权认定的唯一一案。,与通过静态手段固定舞蹈动作的情形有关,其案情内核与前述假定情形基本一致,并且该案初审与上诉两级法院还就如何认定舞蹈作品侵权给出了两套截然相反且值得深入探析的判断标准。在此现状之下,梳理回顾该案两级法院认定舞蹈作品侵权的不同判断标准,或能对本部分所提出的问题作出合理解释,从而推动有关裁判规则的完善。
(一)Horgan案:“流动感标准”与“动作意涵标准”之争
该案的基本案情为,享誉全球的芭蕾舞《胡桃夹子》早期版本失传后,美国著名舞蹈家乔治·巴兰钦于1954年对该作品的舞蹈动作进行再度编排,并在1981年成功向联邦版权局就改编版《胡桃夹子》的编舞部分以视频格式提交登记申请(36)在初审判决中,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将芭蕾舞《胡桃夹子》拆分为三部分,分别为乔治.巴兰钦设计舞步、鲁本·特阿图尼亚设计背景和灯光、卡林斯卡设计服装,并且明确指出在芭蕾舞中乔治.巴兰钦只能就其中动作的设计获得保护(原文为“The New York City Ballet features the ballet The Nutcracker, with music by Tschaikovsky, choreography by George Balanchine, scenery and lighting by Rouben Ter-Arutunian, and costumes by Karinska. The choreography is copyrighted with the rights held by Balanchine's estate”)。这一结论并未被上诉法院推翻,可以作为先前认定舞蹈作品只保护动作设计的佐证。See Horgan v. Macmillan Inc., 621 F. Supp. 1169 (S.D.N.Y. 1985).。1983年乔治·巴兰钦去世,其私人助理巴巴拉·霍根(Barbara Horgan)被指定为巴兰钦的遗产管理人。1985年,霍根得知被告麦克米伦公司(Macmillan Inc.)打算出版一本名为《胡桃夹子:叙事与芭蕾的完美结合》(The Nutcracker: A Story & A Ballet)的儿童读物,该书作者艾伦·斯维泽经纽约芭蕾舞团许可,在书中第三部分将60张由舞团专用摄影师拍摄的《胡桃夹子》在纽约芭蕾舞团现场表演的彩色照片按照表演时的顺序依次放出,并且每张照片周围都会附有该书作者对动作背后呈现故事内容的说明(包括并未以照片形式直观呈现的内容)。霍根曾多次以巴兰钦遗产管理人的身份告知被告其应获得舞蹈作品的使用授权,但麦克米伦公司坚持认为其无需取得授权并继续准备后续的出版事宜。双方数番协商未果后,霍根便以巴兰钦舞蹈作品版权人的身份,向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寻求宣告性救济,以及初步的和永久的禁止出版该书的命令。
初审法院欧文法官坚持适用“流动感标准”来审理该案。申言之,舞蹈作品与舞步的不断移动(the flow of the steps)之间有着密切关联。被告书中这些静态(still)的照片无论数量有多少,也只能在特定的时间点捕捉到舞者的不同姿态。不论是出于现实还是潜在的可能,它们都没有对舞蹈作品进行实质性的利用。这些照片无法重现(recreated)舞蹈动作的原貌,就像贝多芬的交响曲不能从一份只包含25个和弦的文件中重现一样。据此,初审法院驳回了霍根的诉讼请求(37)See Horgan v. Macmillan Inc., 621 F. Supp. 1169, 1170. (S.D.N.Y. 1985).。
霍根不服初审判决,向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主审法官费恩伯格推翻了初审法院提出的“流动感标准”,认为本案应当以“动作意涵标准”作为指导裁判的基本规则。其首先指出,初审法院在判断版权侵权的问题时并未适用正确的法律规则,当侵权作品出现在不同于固定原作的介质上时,从中还原原作的样貌的确不可能,但这绝非被告能够主张的抗辩理由,正如未经许可将小说《飘》拍成电影的人不能因为观众无法从电影画面中还原小说原貌而主张其并未涉嫌侵权一样(38)See Horgan v. Macmillan Inc., 789 F.2d 157, 162. (2d Cir. 1986).。紧接着,费恩伯格认为,初审法院对一张静态的照片所能传递的信息量理解太过狭隘(limited),它可以捕捉到某种手势、舞者身体某处的姿态或舞者在舞台上的某个位置,而这样的照片在书中有很多。另外,通过欣赏一张照片,读者就可以猜测这张照片记录下来的动作之前和之后的样态,比如根据万有引力定律,就能从一张舞者离地数尺的照片中判断出他是跳起来的,最终也必然会落在地面上。并且,对于那些刚刚看完一场《胡桃夹子》现场表演的观众来说,当他们看到这些照片时,所能获得的信息量将会更加丰富,而这远非初审法院所举的贝多芬交响乐的例子中某一和弦可比(39)See Horgan v. Macmillan Inc., 789 F.2d 157, 163. (2d Cir. 1986).。
当然,费恩伯格也承认,涉案的这些照片或许会因为数量不足或者排列不够连贯而不构成侵权。即便存在侵权的可能,被告或许也会因为合理使用制度的庇护最终逃过追责。但这与初审法院拒绝颁布禁令的理由没有丝毫关系。因此,上诉法院决定推翻初审法院的判决,并将案件发回初审法院要求其重审。由于该案最终以庭外和解告结,判决并未生效,因此这两套法律标准在官方层面并未决出胜负,其合理性有待深入探究。
(二)“动作意涵标准”与舞蹈作品的特点不符
通过对“动作意涵标准”及其背后论证理由的详细考察,笔者认为,至少从以下两个角度来看,该标准及其论证理由无法自圆其说,因此不宜作为我国法院审理以静态手段侵犯舞蹈作品版权类案件时的参考判断标准。
首先,在确定Horgan案仍应运用实质性相似原则判断是否构成侵权的基础上,持“动作意涵标准”论者同时采纳了美国著名的汉德法官在审理彼得·潘案时所确立的“整体感觉标准”,即对一名普通观众而言,除非他尝试去分辨原告作品与被诉侵权作品之间的差异,否则他是否会倾向于忽视它们,并认定二者能够给其带来相似的美学感受(40)See Peter Pan Fabrics, Inc. v. Martin Weiner Corp., 274 F.2d 487,489. (2d Cir. 1960)。应当承认,“整体感觉标准”在法律上的确有其合理之处。但在舞蹈作品侵权判断中,该标准的机械运用却会引发很多问题。
第一,这一标准忽视了客观环境对观众内心感觉的直接影响。如果被告将原告舞蹈与动作无关的其他元素(如音乐、服装、布景等)尽数替换掉并再度进行公演,替换这些元素后的舞蹈所呈现的效果明显会与原舞蹈之间产生显著区别,自然也会给观众带来另类的审美体验。但在动作本身并没有丝毫变动的情况下,被告显然要承担侵犯舞蹈作品版权的法律责任,而借助“整体感觉标准”则很有可能无法直接得出这一结论[16]。
第二,舞蹈作品是否被剽窃有时往往超出普通公众的认知范围,在公众看来两部舞蹈作品之间可能极小的不至于影响整体观感的差别或许正是二者不构成实质性相似的决定性因素,反之亦然[17]。故在认定他人舞蹈是否属于侵权作品时,法院往往需要专家证言的佐助以避免出现错误的判断[18]。由此来看,运用“整体感觉标准”判断舞蹈作品之间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恐非最佳选项。
其次,“动作意涵标准”对于照片与舞蹈关系的理解同样值得商榷。
对于单张照片呈现的舞蹈动作、姿态、舞者位置能否受到保护的问题,本文第一部分已细致阐明,此处不再赘述。
对于该标准所称“读者能够从单张照片中猜测出该照片记录动作之前和动作之后的样态”,笔者认为这一说法有违常理。仍以从舞者离地数尺就能断言其必然是先跳起来而后定然会落地为例,即便此判断为真,试问:这名舞者到底是单脚跳起还是双脚跳起?是转圈后再跳还是原地起跳?跳完之后是停止不动还是继续再跳?问题可以一直这样持续追问下去,而这背后隐藏的可能性更是数不胜数,绝非一张照片所能回答[19]。对此,摄影界人士早已笃定,当舞者的动作在拍摄的那一瞬间被凝固时,整个舞蹈便因与前后被切掉的时间流分离而缺少了某种对照[20]。作者乔治·巴兰钦本人生前同样认为,“当大家对舞蹈的关注点都集中在动作变换上的时候,这其中的美感绝非一张静态的照片所能传达”。由此可知,单张照片至少从外观上看,是无法脱离图像本身去传递图像之外的信息的。既然立法者选择将舞蹈作品的内涵交由社会公众去定义(41)美国《版权法》第101条并未对舞蹈作品作出正式定义,对此美国国会指出此举是有意为之,因为舞蹈作品在社会公众之间已经具备“相对稳定的内涵”(fairly settled meanings)。See H.R. Rep. No 1476, 94th Cong., 2d Sess. 53 (1976).,那么法院在进行个案裁决时,同样应当照顾到公众的普遍认知,不能违背基本的科学常识。
至于说,刚刚看过舞蹈表演的人能够从照片中迅速回想起动作前后的姿态:第一,判断作品之间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需要紧依客观事实,主观感觉可以作为辅助的判断因素但绝非决定性的衡量条件。第二,主观感觉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以此作为判断两部作品之间是否实质性相似的必要条件,极有可能得出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以音乐作品为例,如果有人刚听完歌曲《千年等一回》,对歌词“是谁在耳边~说”印象很深,而后在外散步时听到有人清唱“是谁”二字,可能第一反应便会认为对方也在演唱这首歌曲,但现实情况完全可能是对方唱的是歌曲《天竺少女》的第一句“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可见仅靠主观感觉判断作品是否相似绝非最优解。
通过对“动作意涵标准”及其论证理由的重新审视,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首先,判断舞蹈作品之间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不能仅凭观者的整体感觉作为法官自由心证的基础,对创作要素进行客观层面的比对才是裁判人员的优先选择。其次,单幅图像只能固定舞者瞬间的动作,无法披露图像之外的其他事实性细节,因此单纯的一张照片决不可能侵犯舞蹈作品的版权。深而论之,即便在不同时间点对瞬时的舞蹈动作进行连续拍摄,如果这些影像背后的动作按照出现顺序排布之后根本无法看出不同动作之间进行自然切换的痕迹,那么哪怕照片数量再多,其也只能被视作是一堆静止动作的无规律合集,难以说其构成对他人创作的具有独创性的连续动作设计的侵权。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在舞蹈作品侵权判断问题上,“动作意涵标准”的参考价值是比较有限的,不宜当作首选的判断依据。
(三)“流动感标准”契合舞蹈作品的内在规律,较宜借鉴
既然“动作意涵标准”与舞蹈作品版权保护的内在机理不合,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流动感标准”便可自动证立其合理性呢?答案应该是不言自明的。在笔者看来,正是“流动感标准”对舞蹈作品本质——流动性(flow)的认识,真正实现了法律原理与艺术创作规律的有效结合,并确保司法机关在面对他人以静态方式利用舞蹈作品的情形时,能够作出符合逻辑推演与实践经验的判断。
具言之,与文字组合及音符搭配不同,两个或多个静止的动作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构成舞蹈的不同动作之间必须要通过人体移动实现较为流畅的切换,正如舞者不可能从A动作无间隔地变成B动作一样。由于从A动作切换到B动作(如从跑步的姿态变成射击的姿态)永远不止一种选择方案,如何在不同动作之间完成切换并进行有效衔接,便给舞蹈作品的创作者留下了足够发挥其才智巧思的个性空间。因此,对舞蹈作品所抱以的正确态度,应当是将各个动作视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动作与动作间的连接”作为判断作品独创性与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实质要件,而非简单拆分各个动作,从单纯的动作或者动作顺序入手来争较长短。从这一点来看,“流动感标准”显然更具合理性。
至于说Horgan案的初审法院所提出的“书中的60张照片无法重现舞蹈作品原貌”的观点,持“动作意涵标准”论者在这一点上明显是会错了“流动感标准”的真正意指。此处所指的“无法重现”是指60张照片无法完整或实质性再现舞蹈动作之间的变化,意即对照片单纯的摆列未能再现原告作品的实质部分, 这依旧没有脱离传统意义上实质性相似判断方法的基本范畴。持“动作意涵标准”论者为否定“流动感标准”所举的他人不能从观看电影的过程中还原剧本小说原貌的例子是从读者视角出发作单纯的事实判断,并不涉及对作品样态的法律定性,二者风马牛不相及,自然也无法等量齐观。
借助“流动感标准”所引出的“舞蹈作品要体现流动感”这一结论,我国司法机关今后在审理舞蹈作品侵权案件时,除了要判断两部作品动作设计的顺序是否相同或相似之外(42)即便是相同的动作,动作顺序的不同也会使舞蹈作品发生实质上的变化。这一点我国司法机关已经形成共识。如在“王晓玲诉北京市朝阳区残疾人综合活动中心著作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虽然被告编排的舞蹈《祖国你好》部分动作与原告的《祖国你好》相同,但这些相同的舞蹈动作在双方舞蹈作品中出现的时间不同,出现的顺序不同,出现时的表现形式也不同,因此被告并不构成对原告的侵权。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06)朝民初字第18906号民事判决书。,还需要进一步关注被告的利用方式是否完整或实质性再现了原告作品中不同动作之间所蕴含的流动感。在舞蹈作品的诸般利用行为中,现场表演与视频录制等动态手段自不待言,而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静态动作的照片集合是否侵犯舞蹈作品版权,则要看以上照片按照顺序排布之后是否有如视频一样能够完整或实质性地呈现出舞蹈作品动作之间的流动感,即不同动作之间如何进行衔接和切换(例如舞者是如何从腾空的姿态逐步变为站立的姿态的)[19]。
这一点可以从舞谱的创作过程中得到启示。以著名的拉班舞谱为例,在编谱者笔下,通过对一系列特殊符号的组合运用,舞者手指的移动、节奏的划分以及每个动作的内心意图都能在舞谱上完整地展现出来,每个独立的动作以及动作之间的变化自然也跃然纸上[21]。因此,以静态形式展现舞蹈作品的全貌完全是有可能的,这或许也是美国联邦版权局之所以在2021年3月修正的第52号巡回令中,认可舞谱或者照片可以作为登记作品时保存舞蹈作品的物质载体,并同时要求只要被固定的舞蹈作品具体到能使他人以较为统一的方式按此进行表演即可的原因所在了(43)See U.S. Copyright Office, Copyright Registration of Choreography and Pantomime, Circular 52 (revised March 2021), https://www.copyright.gov/circs/circ52.pdf.。
(四)“以静态手段侵犯舞蹈作品版权”的具体认定标准
通过以上各部分的细致分析与重新归纳,本文认为,我国法院今后在审理“以静态手段侵犯舞蹈作品版权”类案件时,宜按照如下认定标准依次做出判断:
首先,不论是否新颖或者有多高的技术难度,单个舞蹈动作永远不能脱离公有领域而单独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由于其既非人类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智力成果,同时又不能有效厘定其保护范围,因此将之留在公有领域,更有利于后续创作者进行充分利用,促进舞蹈作品的发展与繁荣。
其次,判断舞蹈作品之间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应将目光集中于相同或相似动作的客观比对上。倘若在具体动作层面双方作品并不存有冲突,则在舞蹈作品的问题上无需深究,否则便会不当扩张舞蹈作品的保护范围。至于动作之外的其他元素(如配乐、服装、布景、灯光等),可以参照电子地图类案件审理中的“同错”机制,将其作为判断被告是否构成侵权的辅助性条件(44)由于电子地图多是对客观地形地貌及道路交通的描绘,为求指向精准,留给电子地图测绘者的发挥个性的空间往往相对有限。为了日后能够举证他人侵犯版权的便利,电子地图的制作者往往会在地图上的不同位置设置一些不存在的地点或者画出一些本不存在的道路,如果他人未经许可将这些有意错绘的点线图形移植到侵权作品中去,法院往往会判定被控侵权作品与原权利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而在舞蹈作品中也是同理,即便他人并未照抄原告舞蹈的具体动作,但如果舞蹈的配乐、服装、背景等元素几乎不存在差别的话,认定侵权的可能性也是极大的。。
最后,除了审视具体动作是否相同或相似之外,法院还需考察被告对原告作品的利用方式,是否能够完整或实质性还原舞蹈作品动作之间所呈现的流动感。特别是在“以静态手段利用舞蹈作品”类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原告不但要证明被告是按照权利作品中动作出现的顺序对作品进行利用,而且还要向法院表明,被告对原告作品的使用能够使观众感知到不同动作之间的变换方法。单纯的、毫无关联的静态动作的集合,原则上不可能侵犯舞蹈作品的版权。
四、结语
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对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做了“两步走”的战略规划,即“到2025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到2035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竞争力跻身世界前列”。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打造“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知识产权强国的关键时期,因此有必要适当提升对包括舞蹈作品等在内的著作权保护水准。但要合理实现对舞蹈作品著作权的“强保护”,法院在个案审理的过程当中,还需全面考察单个舞蹈动作的可版权性、舞蹈作品的保护对象以及被告的利用方式是否能完整或实质性呈现舞蹈作品内在流动感等一系列技术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判断。这样方能确保舞蹈作品版权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全面保护,同时又可避免对社会公众原本可以充分施展创作天赋之合理空间的不当削减。
就“杨丽萍诉云海肴公司餐厅装潢案”而言,在被告云海肴餐厅仅仅仿照视频截图制作装饰图案、并未完整使用舞蹈作品的独创性表达,且原告同时主张舞蹈与视频版权侵权的情况下,法院应当沿着视听类作品的审理思路继续判断被告是否侵犯了原告对其视频画面所享有的版权。该案法院也的确对这一问题做了裁量,认定原告拍摄的视频因独创性不足而属于录像制品。但是法院拒绝认定被告侵犯原告所拍视频的版权,理由是“被诉装饰图案与拍摄《月光》舞蹈的视频相比,人物与月亮大小的比例不同,虽展现的动作存在相似之处,但相应画面并不完全一致”(45)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32020号民事判决书,第28-29页。。笔者认为,仅因“人物与月亮大小的比例不同”便由此否定被诉装饰图案与原告视频画面构成实质性相似的可能性,该观点同样也是值得商榷的。期待该案在后续审理过程中能够就此问题作出更有说服力的回应(46)截至本文撰写完成时,该案原告已经正式提出上诉。参见李杨芳:《云海肴“动中取静”,杨丽萍维权胜诉》,载《中国知识产权报》2020年12月18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