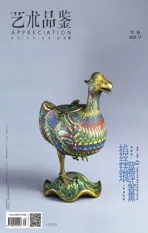由理性“取舍”到音乐形式的“向上力量”
——以舒伯特《C 大调钢琴奏鸣曲》(D.840)为例
2022-02-11张思博山东大学
张思博(山东大学)
音乐只有理性是不够的,还需要“道德”。只有通过道德,才能反思理性的走向,寻求审美的提升。本文以舒伯特《C大调钢琴奏鸣曲》(D.840)为例,从形式关照入手,分析作品中的“取舍”行为,揭示其中的理性思维,并探讨理性的音乐形式如何通过审美拥有“向上力量”、走向“道德”。
一、音乐形式的智性审美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标题音乐盛行的土壤中,诞生了纯音乐与标题音乐之争,在美学上体现为“情感论”和“形式论”。在黑格尔的音乐美学中就可见音乐形式与情感之双重内部品质,并且预示了形式主义、理性主义对音乐元素的解释。直至19 世纪50 年代,汉斯利克《论音乐的美》直指音乐作为独立艺术形式所具有的特殊技术,强调其形式价值,直击浪漫主义“音乐与其他艺术形式结合”的理想的构造,正式将音乐形式价值推到“聚光灯”下。
音乐形式自律与他律美学的讨论,即制约音乐的法则和规律是来自音乐自身还是音乐之外。在他律美学中,音乐本身体现某种外于音乐的客观实在(主要是人类的感情),但事实上,音乐与外界“沟通”的方式只能通过音响,音乐也不具有举例、解释等具体描绘手段。故,将音乐形式的内容和意义归结至外界略显牵强。但是,将音乐作品与精神世界、历史文明割裂也是不合理的,而此种“割裂”也成为后世对自律美学的“诟病”之处。
形式的智性审美和通往道德的路径,也应在此种“诟病”中讨论。实际上,所谓精神、社会历史状况是不能直接影响音乐作品的,它们能影响的只是作曲家,作曲家再通过对音响形式的关照进行创作。也即精神与历史影响的是创作中对构建完美形式的人的“取舍”行为,并不能视作形式的内容和审美对象,汉斯利克对此也有说明,“诗歌、标题、生活经历等没有更多的作用”。
更进一步,当我们作为音乐作品的欣赏者、分析者时,面对的也只是音乐形式上的诸因素,至于了解历史背景、作曲家生平,只能帮助我们了解作曲家在构建音乐形式时可能做的“取舍”,以及“取舍”背后的原因,而并不能越过人的行为动机,直接将感情、精神或历史这些“原因”视为音乐形式的“内容”。
那么如此一来,对汉斯利克形式——自律论的“诟病”则不免地存在着“不公平”。汉斯利克的本意应该是历史、精神和情感等并未和音乐形式割裂,而只是不能和形式共同成为审美的对象。而割裂的点,正处于“取舍”这一行为之上。从分析者的角度看,“取舍”是我们能从形式中解读出的音乐家符合或“不符合”音响规律的处理,而所谓“规律”,是历史上无数次为构建完美形式时的“取舍”行为形成的一般法则,即“传统”。此类法则由大多数人共同认可、赞扬,具有普适性价值。而好的形式一定具有“独创性”和“经典性”的双重意义,成为经典的也永远都是形式。
二、以舒伯特《C大调钢琴奏鸣曲》(D.840)为例
作品840 第一乐章采用奏鸣曲式结构,呈示部主部主题和副部主题为主属调性关系,保持了古典传统。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呈示部两个副部虽于G 大调结束,但没有于此开始,连接部也随之没有属的倾向。第二,再现部处理与典型的奏鸣曲式不同:主部主题于B 大调上再现,又经D 大调和F 大调,直到连接部才转回C 大调。是调性布局的“别出心裁”,更是精心设计主题与和声音响效果的必然结果,体现了“取舍”与“考量”之后的传统与创新的高度协调,是真正的形式的进步。
(一)呈示部概况
主部主题为8 小节乐段,由两个单核异质的动机分别重复或变化重复构成。第一个动机由分解和弦和柱式和弦构成,第二动机为音阶型,呈单核异质的叠置形态。呈示部即是在C 大调和降A 大调上对上述主题的两次陈述。第二次陈述中,第二个动机将部分材料融解,变为副动机,同时在降D 大调的属功能上进行了四小节的悬置,与原有材料的前半部分形成对比,增加了发展的潜力。
连接部为衔接主部的半开放终止,采取了主部的首个单核异质动机为材料,并引入第二个动机的降七级特色音,进行进一步发展,形成主部的递进结构,并利用降七级造成的和声结构不稳定,故技重施,在主部首个单核异质动机催生出副动机,推动调性变化,来到呈示部的小高潮;并以上述主部第二动机部分溶解后的副动机,为副部主题做铺垫。
第一副部主题于b 小调上陈述,与主部主题的第一动机类似,为b 小调主和弦的分解,伴奏部分的材料与连接部主题副动机保持了联系。第二副部主题调性则非常不稳定,材料也较新,但仍可以看到主部主题第二个动机的形态。
结束部主题材料仍旧是分解和弦,于G 大调上陈述,并加入连续的三连音“活跃气氛”,三连音也在主部主题中短暂出现过,因此可视为进一步的首尾呼应,实为精妙。整体上看,作品采用了较统一的主题材料,随着曲式结构的展开,展示真正的主题的不同面貌。
(二)音响效果“取舍”
如上述,乐章呈示部在符合传统奏鸣曲式调性的主属的稳定“框架”的同时,也“舍弃”了一部分稳定性,追求多样的调性变化。但若要牺牲紧凑的调性结构以减弱听觉对主属的期待,就必定需要“获取”额外的具有“识别度”的音响效果,来刺激听觉,从而构建新的依托,保证作品结构的合理性和卓越性。
舒伯特的做法分两步。第一步,构造具有多面性形象的主题动机,保证其在之后的音乐展开中有足够的听觉“识别度”和形态变化潜力,主题的第一动机即是如此。它是由分解和弦与柱式和弦构成的单核异质动机,分解和弦部分由于调性指向不明确性,具有多面性的特点,如谱例1 所示(完整曲谱源于国际乐谱库)。它也为副部b 小调的主和弦分解埋下伏笔,更在展开部大放异彩,因而避免了调性不稳定带来的听觉结构松散。第二步,在主题音阶形态的第二动机中引入降七级变化音,形成向下属方向的离调;并在此单核异质动机融解形成的副动机中,借由降七级形成的下属上的属七和弦突出三全音音程,获取进一步的听觉“辨识度”,支撑结构稳定性。之后,降七级音于连接部加入第一动机,推动了连接部调性变化。

谱例1 《C大调钢琴奏鸣曲》(D.840)第一乐章第1-5小节(图片来源:国际乐谱库)
总之,舒伯特在一定程度舍弃传统调性布局之后,通过主题与动机的精心构造和特色音响的引入构建了新的结构“密码”。以过往大众听觉所广泛认可的习惯、俗成约定为基础,在“取舍”的过程中,对传统形式进行了创新。
(三)整体调性布局“取舍”
有了以上主题精心构造以及特色音及音程带来的强大展开潜力,就很大程度支撑了舒伯特在奏鸣曲式再现部“舍弃”传统的主题重述方式。
即便如此,仍需要加强特色音程带来的听觉影响,才算真正地以再现部的变化取得结构创新,形成新的典范。
舒伯特仍旧用了两步来达到目的。第一步,加强降七级音和由此衍生的三全音音程的听觉的影响。具体情况如下:降七级音除上述提及在连接部加入主题第一动机的柱式和弦部分之外,于展开部的引入部分直接进入该动机的分解和弦中(见第一乐章第108—110 小节)。如此,形成更加紧凑的音响变化结构,从而引发了中心展开更加剧烈的主题形态变化和调性变化——由C 大调降七级音的下属离调(F 大调),在半音化和声中进入升F 大调,与主调形成三全音关系;同时以升F 大调为属准备,主题材料于B 大调上再现,并经由D 大调、F 大调进入再现部的连接部(C 大调),如此,则与升F—C 大调走向共同在调性布局上形成了对三全音听觉结构上的肯定,如笔者绘制的作品840 第一乐章曲式结构图——图1 所示。第二步,扩大尾声的规模。在突出三全音调性布局之后,就必然需要在整体的结构上消除不协和音程,强调C 大调的主调地位。体现在谱面上为第297—300 小节三全音的消失。综上,D.840 第一乐章是以“舍弃”传统主属调性布局、“获取”特色音程为新的结构“支点”的音乐展开过程。舒伯特渴望创新,但在每一步都透露出对传统形式、稳定性和经典的尊重,在谨慎的“取舍”中构建了“独创性”和“典范性”兼具的乐音形式整体。

图1 作品840第一乐章曲式结构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从《C 大调钢琴奏鸣曲》(D.840)的音响、调性布局的取舍中,足见奏鸣曲式在18 世纪末到19 世纪初为调性逻辑和听觉感受所经历的一系列变革——“三调呈示部”与再现部反常规。
舒伯特创作了很多这样具有“三调呈示部”的作品。在《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舒伯特”词条标题为“舒伯特的风格与影响”的一节中就将舒伯特对“三调呈示部”的突出贡献作为他在调性布局方面的重要成就加以陈述。在作品840 中,他统筹调性布局利用的就是多面性形象的主题——主题的多面展开可加强听觉识别,并辅以特色音程和变化音来统筹变化,成就独创性和经典性。除在作品840 中论及的再现部的起始调不在主调之外,舒伯特的《B 大调钢琴奏鸣曲》(D.575)中如此处理,也体现了再现部的调性布局的创新,尤其在于呈示部形成逻辑联系上——再现部的内部调性(E 大调—A 大调—B 大调)也呈现出首尾与呈示部内部调性(B 大调—E 大调—#F 大调)“T—S—D”关系上的呼应,并且再现部与呈示部形成了“向上四度”的整体平行关系。除此之外还有《a 小调钢琴奏鸣曲》(D.845),也有类似别出心裁的调性布局设计。
呈示部和再现部的变革使得原本紧凑的调性结构开始松动,听觉从对属调的期待而被拉伸到色彩化的音响变化中。而舒伯特能在变革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不是由于刻意追求调性的多变,而是他有杰出的天才能力去用音乐形式的其他方面去统筹这样的变化,在19 世纪音乐体裁统一走向膨胀时依旧保有古典精神中对简洁、克制和逻辑的追求,以此形成音乐形式的经典,这才是舒伯特值得推崇的因素。而音乐史的进程中,成为经典的永远只有音乐形式。
三、从“取舍”走向“道德”
(一)“取舍”与音乐形式的道德
从《C 大调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的分析过程中,不难看出着眼“取舍”对于作品本身形式构建上的意义,如何赋予形式“独创性”和“典范性”;体现的是作曲家对完美形式的认知,并致力于其激发的普遍性情感——美。
作为审美对象的音乐形式(或完整的音乐作品),不应仅仅被视作死去的“文献”,它具有永恒性——建立由许多相对真理积累而成的绝对艺术真理的过程,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中都仍然继续进行着。它是“当今”回首过去时,依然可以以其经典性存在并进行,且是具有智性审美意义的对象。
如此一来,“取舍”行为自然成为形式所传达出的直接信息,因此被重点关注和用以引起“美”的感受。
“美”这种情感具有共通性,个体通过审美反思,追问道德的本性和素质。审美连接理性与道德——理性作用于审美,目标指向道德。而“取舍”行为在这条道路上指的就是理性。“取舍”应随个体审美的不断提高,走向更高的道德理想。接触“取舍”时越敏锐,审美体验越细腻,越能接近形式的道德——在历史条件的变化之下谋求音乐形式的“流通性”。
(二)“取舍”与分析者的道德
分析音乐形式上运作的是康德所说的反思判断力的先天原则——“先天地断言——断言人们主观情感(审美)有共通性”,即形式在分析者主体上引起的审美感受是包括作曲家在内的所有人应该共同拥有的,具有普遍性,以此寻求美感上的沟通。
王次炤教授于《论音乐中的精神内涵》中提到,“精神内涵是建立在理性思维和理解认识基础上的审美内容”;并且在2022 年山东大学艺术学院的“致广讲坛”再次提及音乐的审美话题时强调了从音乐形式入手的重要审美接受过程。也即从分析者的角度来讲,把握审美内容时同样也是靠理性判断其风格特征(和声、旋律、曲式结构等),来与作曲家进行审美沟通。康德说“审美沟通是有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在审美过程中接近道德,并反思理性的本质”。
分析者作为感性的人,就是在情不自禁地审美“断言”中意识到自身的道德的——“理解自身的道德本性和素质”,并在作品经过的漫长发展历史中剖析其所遵循的契约、制度以及约定俗成,判断音乐文明形成的过程,和其在形成过程中至今仍然残存的理性思维,抓住智性审美,以接近审美的全面沟通。
当然,审美“断言”是存在“例外”的,且对于作曲家和分析者都是如此。所以,分析者更像是从另一个角度,提供多一种的“断言”。如此,无数的“断言”在文明、人类主体的进步的过程中,会引发趋向道德的动力,由道德对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取舍”)进行自上而下的统一。
(三)“取舍”与音乐史的道德
“一切历史都可看作‘道德史’”,因为从道德反思的角度,可以读出人理性的起源和发展形态;在道德实践“应当”产生的后果中,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被统一,反之,再从两种理性中,道德会触及更高标准。在音乐史中,以“作品”为研究对象,形式的美为道德,“取舍”为理性,最终再以道德为终极趋向。达尔豪斯在《音乐史学原理》中指出——“作品”是音乐史的核心概念。如前文所述,艺术作品是具有永恒性的,我们关注的也正是其作为形式而“残留”至今的意义——“我们对过去的兴趣并非由于它曾经是过,而是因为它现仍起效应,某种意义上现在仍然存在”。
而目前所见的以作品为主体的音乐史研究似乎缺少一种趋向道德的力量,原因部分源自追求“独创性”,影响了审美沟通。甚至从作曲家传记上看,编纂者更强调从音乐的“独创性”的新意入手,以此强调音乐家在音乐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进而将音乐的发展历史重述为无数“特立独行”的阶段的轮番“上演”,将音乐的进步大部分归结在了“不可重复”之上,从而形成音乐的所谓“逻辑”的历史。而这与历史的“道德”进程以及进程中“理性”为大多数认可方具有道德意义是截然相悖的。作品中的“取舍”行为也应如此具有广泛认可,才真正体现形式智性美上的审美沟通价值。
四、结语
音乐形式,也即动机、主题、和声和曲式结构,其在演绎中会随着和声的方向性(终止式),向终点逝去;如同生命一样,不可避免地会面对终结。生命与音乐一样,要面对无数次的“取舍”。
音乐被称为“最高哲学”,也是出自形式上的原因——形式在演绎中必将走向终止;且音乐要在“不具有具体描绘手段”的情况下,实现形式上的完整性、独创性,并以典范性为理想做出尽可能合理的“取舍”行为。
从古希腊对“好” “正义”的讨论,再到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提到的“理性的狡计”,无一不在探求“取舍”的行为如何可以达到“好”的结果,并勾画出人类文明向道德靠拢的曲折路线。音乐形式也是如此——乐音的运动如同一次以泛音列为基本原则的“向死而生”;聆听者们则不断加强对形式的关照,通过审美沟通与作曲家一同在美的体验中趋向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