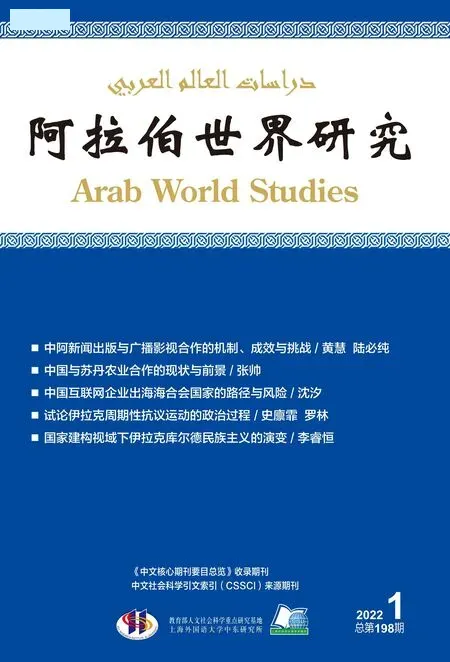试论伊拉克周期性抗议运动的政治过程*
2022-02-05史廪霏
史廪霏 罗 林
2019年10月,伊拉克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运动,在月余时间内席卷全国,300余人在抗议运动中死亡,近1.5万人受伤①“Iraq Protests Death to 319 with Nearly 15,000 Injured,” CNN, November 10, 2019,https://www.cnn.com/2019/11/09/middleeast/iraq-protest-death-toll-intl/index.html, 上网时间:2021年1月15日。。2019年11月,抗议者纵火焚烧了伊朗驻卡尔巴拉领事馆,并将伊朗国旗换成伊拉克国旗。②“Iraq Unrest: Protesters Attack Iranian Consulate in Karbala,” BBC, November 4, 2019,https://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50287644, 上网时间:2021年1月15日.2020年1月,约有20至25万人在巴格达进行游行,抗议者打出反美标语,要求美国从伊拉克撤军。③“Protesters Mass in Baghdad, Demanding U.S. Leave Iraq,”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4,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1/24/world/middleeast/protests-iraq-baghdad.html, 上网时间:2021年15日。兴起于2019年的一系列抗议运动是萨达姆政权倒台以来伊拉克最为严重的一轮民众抗议,导致时任总理阿卜杜勒·迈赫迪(Abdul Mahdi)辞职,连续两位候任总理组阁失败,造成近半年时间的政府权力真空。抗议活动延续不断,各种游行、示威仍在各地出现,在全球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和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背景下,伊拉克国内民众抗议运动的发展仍旧充满变数。本轮抗议运动并非孤立现象,2011年以来,伊拉克已经爆发了五轮规模较大的抗议运动,陷入周期性抗议的泥潭。伊拉克周期性抗议运动提供了极具特点的社会运动研究样本,本文将以五轮抗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政治过程理论对伊拉克抗议运动爆发、发展和衰落的过程进行分析,进而提出伊拉克抗议运动周期性爆发和平息的深层次原因。
一、政治过程理论的研究视角
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在1982年出版的《政治过程与黑人运动的发展(1930~1970年)》一书中正式提出政治过程理论。他认为,社会运动的产生源自于扩张的政治机会、内生组织强度和认知解放三个要素的共同作用。“政治机会结构”用来描述不同群体在权力和政体运行中的地位,掌握制度化权力的政治精英被称为“局内人”,在决策权力中处于优势地位;在权力运行中处于劣势地位的群体被称为“局外人”,是社会运动的潜在发起者,两者在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地位下进行互动。“任何改变既有政治结构或破坏既有结构基础的事件或社会发展进程”,④Doug McAdam,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 41.都会改变既有政治机会结构,增加反对者群体发动社会运动的政治机会,如战争、经济衰退、人口结构变化等。内生组织指被排斥的社会群体中存在的或潜在的政治组织,可以将有利的政治机会转化成为有组织的抗争活动。①Doug McAdam,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 44.认知解放指人们充分认识到政治机会的变化,才有可能挑战现行政治秩序。在运动产生之后,社会运动本身作为一个变量参与广义的政治进程,与政治机会结构、组织强度、集体属性、社会控制强度四组变量的互动决定了社会运动的发展与衰落。其中,集体属性由“认知解放”这一概念发展而来,是连接政治机会、组织强度和社会运动之间的桥梁。社会控制指政府、精英等其他外部组织对社会运动发展做出的反应。
国内外有关社会运动理论的研究大多关注政治功能运转正常的国家,较少关注像伊拉克这样一个处在高暴力环境,社会高度分化状态下的国家。②Irene Costantini, “The Iraqi Protest Movement Social Mobilization Amidst Violence and Instability,”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8, No. 5, 2021, p. 834.本文将每轮抗议视为独立事件,运用社会运动产生模型分析运动兴起的原因;运用社会运动发展和衰亡模型分析运动产生后的发展过程,本文将政治机会结构具体分为经济社会、政府、精英集团、外部势力和突发事件五个次级因素,使之更符合伊拉克抗议运动实际。
二、伊拉克周期性抗议运动
美国主导伊拉克战后重建,希望将伊拉克树立为中东民主国家典范。从临时管理委员会到临时政府,从临时宪法到议会选举,政治制度建设与经济重建、安全重建和国家社会认同构建同时开展。伊拉克复兴党政权倒台后,许多散居海外的伊拉克人重返国家参与到新的政治进程中。2005年伊拉克举行首次议会选举,有7,785名政治候选人自荐,111个政党和联盟登记在册,③Toby Dodge, Iraq's Future: The Aftermath of Regime Chang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5, p.26.反映出政治精英和民众对重建国家的乐观和积极心态。然而,美国基于反恐和反独裁策略,有意将权力从伊拉克现有中央国家机构中分散出去,在联盟临时权力机构(CPA)接管政权时建立了一套基于民族和教派配额的治理结构,随后由伊拉克管理委员会(IGC)将民族—宗派结构制度化,④Oula Kadhum, “Ethno-sectarianism in Iraq, Diaspora Positionality and Political Transnationalism,” Global Networks, Vol. 19, No. 2, 2018, p.165.议会民主制度演变成了根据民族宗派和政党分配政治权力与行政职位的制度。
从政治机会结构角度看,上述转变造成了三方面的影响。第一,新成立的政党尚未扎根伊拉克社会,活跃的政治家长期在国外而远离伊拉克内部社会①Dai Yamao, “Iraqi Islamist Part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Impact of Historic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n Political Conflict in Post-war Iraq,”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Iraqi Studies, Vol. 6, No. 1, 2012, p.27.,无法开展基于国家公民的动员方式,基于民族、宗派、部落和亲属关系的认同被重新唤醒,各政治派别不得不依赖这种动员体系。第二,民族宗派配额制度塑造了伊拉克高度分割和精英依赖的社会政治结构,世俗的公民社会处于体系外围,无法渗透到政治领域。②Ben Robin, “Social Brokers and Leftist-sadrist Cooperation in Iraq's Reform Protest Movement: Beyond Instrumental A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51, No.2, 2019, p.260.宗教和民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1,000余个地方议会机构只是在为选举准备,而不是为当地居民服务。③Mehiyar Kathem, “New Imperialism in Iraq: How the US Occupation Helped Establish but Then Cannibalised the Sadr City District Council,” Peacebuilding, Vol. 8, No. 3, 2020, p. 369.第三,民族宗派配额制度加剧了阿拉伯与库尔德、什叶派与逊尼派、政治精英与国外势力的矛盾,导致了2006~2008年暴力对抗和教派冲突的高峰,④Keiko Sakai, “De-sectarianizing Patterns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the Post-conflict Iraq,”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Iraqi Studies, Vol. 6, No. 2, 2012, p.205.民众对宗派动员导致暴力冲突形成更恶劣生存环境的模式感到失望和恐惧,分裂的伊拉克人民对建立统一有效的政府的期望,为日后爆发的抗议运动奠定了基础。
三大因素叠加影响下的伊拉克社会危机重重,民众通过抗议运动参与到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博弈之中,导致了2011年以来的五轮大规模抗议。第一轮抗议兴起于2011年2月,受“阿拉伯之春”带来的地区性普遍抗议运动影响,抗议者走上街头,抗议恶劣的生活条件、普遍的腐败和裙带关系,呼吁确保更好的就业机会、基本的公众服务和社会福利。⑤“Tensions Flare in Iraq Rallies,” Al Jazeera, February 25, 2011,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1/2/25/tensions-flare-in-iraq-rallies, 上网时间:2021年1月15日。这是战后伊拉克民众首次通过抗议的形式表达对政府的不满,但相较于“阿拉伯之春”的其他国家,伊拉克的抗议表现得较为平和,规模和强度都有所不及。第二轮抗议出现在2012年12月,因逊尼派财政部长拉菲·埃萨维(Rafi al- Issawi)的警卫人员被捕,引发安巴尔省、尼尼微省和萨拉赫丁省等逊尼派占多数的省份爆发抗议运动。民众抗议时任总理努里·马利基(Nuri al-Maliki)的宗派主义、逊尼派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以及政府权力分配不均。⑥“IraqProtestsSignalGrowingTensionbetweenSunniandShiaCommunities,”The Guardian, December 26, 2012,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2/dec/26/iraq-proteststension-sunni-shia, 上网时间:2021年1月15日。抗议运动于2013年底在政府的暴力镇压下结束。此轮抗议的暴力程度加大,凸显出伊拉克教派冲突升级的危险信号。2015~2016年的第三轮抗议正值伊拉克与“伊斯兰国”交战期间,恶劣的公共服务再次引发伊拉克民众抗议,抗议者对酷热天气下的断电和水源质量差进行抗议,要求政府打击广泛存在的腐败。①“Iraqis Protest over Power Outages and Poor Services,” Al Jazeera, August 3, 2015,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5/8/3/iraqis-protest-over-power-outages-and-poor-services,上网时间:2021年1月15日。此轮抗议规模更大,并提出了更为明确的政治诉求,要求结束民族宗派配额制度。2018年7月,巴士拉省及其周边地区因严重水污染事件和电力供应不足问题引发第四轮抗议,抗议者对政府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态度,暴力程度也进一步升级。②“The Violent Protests in Iraq, Explained,” Vox, September 8, 2018, https://www.vox.com/world/2018/9/7/17831526/iraq-protests-basra-burning-government-buildings-iran-consulate-water,上网时间:2021年1月15日。此次抗议在伊拉克慢慢转向和平期时突然爆发,水电等公共服务长期缺乏得不到解决,民众与政府间的矛盾再次升级。2019年10月爆发的第五轮抗议运动在历次抗议中规模最大,抗议者要求结束战后建立的政治制度,对政府的不信任程度进一步升级,政府的反应也十分强烈,抗议过程伤亡惨重,不明袭击和暗杀活动频繁,死伤人数为五轮抗议中最多。除抗议政府外,此轮抗议运动还出现强烈的反伊朗和反美色彩,甚至出现伊拉克国内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泛起。前总理迈赫迪辞职后,抗议运动随着新总理的人选变更轮番上演。直至2020年5月,新任总理穆斯塔法·卡迪米(Mustafa al-Kadhimi)上任后采取系列新政,抗议运动势头有所减弱,但仍未完全平息。
三、周期性抗议运动兴起的原因分析
根据社会运动产生模型,分析五次抗议运动产生过程可以看出,抗议群体不断扩张的政治机会、有效的基层组织动员、民众的认知情感共识是周期性抗议运动能够不断兴起的原因所在。
(一)不断扩张的政治机会
抗议活动是政治机会结构变得脆弱的标志。③Peter K. Eisinger, “The Conditions of Protest Behavior in American Ci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7, No. 1, 1973, p. 41.2011年之后阿拉伯地区的政治动荡,使民生问题回到了中心阶段④Carmen Geha, “Understanding Arab Civil Society: Functional Validity as the Missing Link,”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6, No. 3, p.502.。这一时期抗议运动的特点是抗议者明确的目标以及承诺采用和平的手段①Miguel Larramendi, “A Decade of Demonstrations and Protest Movements in the Arab World,” in IEMed, Mediterranean Yearbook 2020, 2020, p.20.。以政治过程理论视角分析,抗议群体的政治机会在十余年间不断扩张,来源于经济重建失败、政府执政能力低下、政治精英与大众分裂、外部政治势力竞争、突发事件刺激等方面。
第一,战后经济重建失败。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伊拉克国内生产总值1990年已达到1,804亿美元,而2020年却仅为1,672亿美元。考虑到美元贬值因素,实际伊拉克国内生产总值大幅缩水。击退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后伊拉克国内经济也未有起色,2018~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负2.4%,2020年更是加剧到负10.4%,②《GDP-Iraq》(1962-2020),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end=2020&locations=IQ&start=1962&view=chart,上网时间:2021年2月2日。五分之一的伊拉克人生活在贫困线下。经济重建的失败造成的民生问题、高失业率和政府控制能力减弱,扩张了抗议群体的政治机会。
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有意识地轰炸、摧毁了伊拉克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设施,如自来水和能源供给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农业灌溉系统,以及工业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③田文林:《中东去除病根才能摆脱困境》,环球网,2019年11月1日,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9CaKrnKnxxC,上网时间:2020年3月1日。战争、多年的制裁以及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破坏给战后重建带来巨大的资金压力。据估计,重建费用在1,000亿美元至5,000亿美元之间,基础设施的修理和升级预计需要160亿美元至300亿美元,而国际社会给予的援助远远低于有关方面预计的560亿美元水平。④赵国忠:《伊拉克战后重建及面临的困难》,载《和平与发展》2004年第1期,第21页。伊拉克大部分损坏的基础设施至今仍未得到重建,供电能力只有需求的一半,20%的地方未通自来水,⑤《伊拉克国家概况》,中国外交部网站,2021年8月,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148/1206x0_677150/,上网时间:2021年11月2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缺失导致大量难民无法得到有效安置,民众的生活窘迫。与之同期,伊拉克保持高人口增长率,尤其在2011年后持续维持在3%以上,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数的70%,失业率也一直在10%以上。⑥《世界发展指标(伊拉克)》,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iraq?view=chart,上网时间:2021年2月2日。青年人中超过40%未接受教育、就业或培训⑦同上。,贫困无业人员成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大量青年无事可做,成为抗议的主力军,而城镇成为潜在的社会运动萌发地。
第二,政府腐败严重、执政能力低下。据估计,自2003年以来,伊拉克国库中已有3,000亿到3,500亿美元被贪污,①Loveday Morris, “Beyond Terrorism, Iraq's Leader is Struggling to Fight Corruption,”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1, 20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middle_east/beyondterrorism-iraqs-leader-is-struggling-to-fight-corruption/2015/08/20/d84c87b2-45f6-11e5-9f53-d1e3ddfd0cda_story.html, 上网时间:2019年12月10日。国际社会投入伊拉克的巨额资金几乎没有受到监管。政府通过的反腐败的《责任法案》形同虚设,少有腐败官员受到应有惩罚,并且政治领导人也受益于各种有利可图的赞助网络。根据伊拉克议会财务控制委员会的文件显示,政府各部签署了建造6,000个项目的合同,但其中虚假或未被执行的项目有5,000多项,总价值达2,200亿美元。②Faleh A. Jabar, The Iraqi Protest Movement: From Identity Politics to Issue Politics, LSE Middle East Centre Paper Series, No. 25, London, June 2018, p. 16.根据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布的《腐败认知指数》显示,2016年至今伊拉克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一直排名160位之后。民调显示,有83%的伊拉克人认为腐败在加剧。③TobyDodge,“CorruptionContinuestoDestabilizeIraq,”ChathamHouse,October1,2019, https://www.chathamhouse.org/expert/comment/corruption-continues-destabilize-iraq, 上网时间:2020年2月26日。
与腐败现象并存的是政府冗员过多、行政效率低下。伊拉克政府每月需要支付的工资和养老金超过30亿美元,而2016年公共部门员工的休假天数多达184天,经济学家估算这导致一年30亿美元的生产力损失。战后美国遣散了大批官员和职员,解散了军队和安全部队,④赵国忠:《伊拉克战后重建及面临的困难》,第21页。此举动摇了社会基础,给民兵的崛起和教派暴力冲突提供了空间。在防务重建过程中腐败问题同样严重,据估计伊拉克国家安全部队有大约3万名实际并不存在的“幽灵士兵”在吃空饷,他们的薪水被腐败官员侵吞。⑤Ranj Alaaldin, Fragility and Resilience in Iraq, Roma, Istituto Affari Internazionali, 2017,p. 5.政府腐败和行政能力低下导致经济恢复和防务重建效果极差,引发公众信任危机以及安全担忧,而经济和防务水平又反过来限制政府进一步开展变革的能力,财政紧缩以及对公共部门服务的削减显示出政府在政治领域动员能力和控制能力的下降,刺激着其他政治群体挑战的可能。
第三,政治精英和大众的分裂。前期几次选举中,伊拉克民众实际上冒着生命危险,投票给承诺寻求解决伊拉克内部问题的政治力量。但宗派政治造成大众和政治精英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分裂,公众对政治精英无法超越自身或政党利益,无视人民利益和福祉感到愤怒。⑥Gareth Stansfield, “The Political Parameters of Post-withdrawal Iraq,”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 86, No. 6, 2010, p.1262.民众政治参与热情不断下降,大选中的民众参选率从2010年的62%降至2018年的44.5%,①Anthony H. Cordesman, The Uncertain Iraqi Election: The Need for a New U.S. Strategy,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8, p. 8.政治精英利用民众期盼作为政治宣传的口号,利用民众不满进行党派动员,而没有实现更大范围的国家和身份认同。无论是打击复兴党、削弱逊尼派,还是什叶派之间政治精英的统合与纷争,再加上库尔德地区两大政治精英集团关于独立方式的不同追求,伊拉克民众切实经历了残酷的战争、不断的混乱和流离失所,他们很难相信这些政治精英能够从实际问题出发,通过党派的力量解决深层次问题。伊拉克民众期待一个诚实、统一、有效,能够降低腐败、建立法治、弥合教派和族裔分歧、大规模改革经济的政府。这种期待启发并促使2011年后以公民诉求为出发点和以民族主义形式的抗议行为,运动方式也向无党派支持的方向转化。
第四,外部政治势力竞争。美国主导的战后重建与伊拉克国家利益的不一致性被认为是伊拉克重建失败、国家陷入混乱和动荡的根源所在。②王丽影、王林聪:《伊拉克国家重建困境的根源及出路》,载《西亚非洲》2019年第3期,第107页。虽然美国在2010年后逐步撤军,但美军仍以反恐为名从事军事活动,同时美国私人安全承包商的兵力在不断增加。2019年12月29日,美国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真主党旅”目标进行报复性空袭后,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遭到亲伊朗抗议者的包围。2020年1月5日,美国在伊拉克暗杀伊朗“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马尼(Qasem Soleimani)和伊拉克“人民动员部队”(PMF)领导人阿布·迈赫迪·穆罕迪斯(Abu Mahdi al-Muhandis),引发伊拉克反美情绪高涨。美国在伊拉克发动的数次军事行动,不但是对伊拉克主权的粗暴侵犯,还将伊拉克卷入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
伊拉克各邻国也有意削弱美国与伊拉克联系,巩固自身与伊拉克政府间关系。邻国希望存在一个统一稳定的伊拉克,但是一个强大且装备美国武器的伊拉克的崛起,也将被视作威胁。③[伊拉克] 海德:《2010年大选伊拉克前途命运转折点》,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1期,第59页。伊拉克战后国内主要政治集团都与国际势力有正式外交接触,伊拉克的政治生活已经被追求各自利益而又相互竞争的地区大国所渗透。夹在伊朗、沙特、土耳其、叙利亚和美国之间的伊拉克政客们不得不平衡他们与这些国际行动者的关系。④Gareth Stansfield, “The Political Parameters of Post-withdrawal Iraq,” p.1264.在这一局势中,在外部大国利益影响下的伊拉克战略可能与伊拉克人民的期望相抵触。
萨达姆倒台后,伊朗凭借宗教和地缘优势迅速介入伊拉克。政治上与伊拉克什叶派保持密切联系,其亲密盟友哈迪·阿米里(Hadi al-Ameri)组建的巴德尔(Badr)组织在2018年议会大选后成为什叶派重要政治力量。军事上大力扶持以“巴德尔旅”为代表的什叶派民兵组织。什叶派民兵倚重伊朗军事顾问,桀骜不驯,其领导人甚至公然违背伊拉克政府的命令。①唐恬波、马成文:《伊拉克国情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34页。在经贸领域,伊朗在与伊拉克贸易中获得了大量贸易顺差,伊朗廉价食品和商品打击了伊拉克本土农业和制造业,激发了伊拉克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在2019年抗议中,多地示威者冲击伊朗领事馆并纵火,巴格达爆发要求美军从伊拉克撤军的大规模游行,民众越来越将对政府失职的失望转化为对外部势力过度干涉的愤怒。
第五,突发事件的直接刺激。2011年抗议运动受到中东北非地区局势动荡的影响,由“阿拉伯之春”这一地区事件引发。2012~2013年抗议运动起因于逊尼派财政部长埃萨维的警卫人员因恐怖主义指控被逮捕,引发了伊拉克战争后遭受不平等待遇的逊尼派民众的抗议。2015~2016年抗议运动起因于巴士拉地区夏季酷暑期间频繁停电,当地民众不满于在附近石油资源丰富的情况下政府仍不能保证供电。2018年抗议运动同样是由于夏季多起严重的水污染事件引发,同时伊朗切断电力供应加剧了本已严峻的形势。2019年抗议的直接导火索则是时任总理迈赫迪将在对伊斯兰国作战中战功累累、广受好评的反恐部队副司令萨阿迪(Al-Saedi)解职,许多伊拉克人认为此举是受到伊朗势力的影响,②“Iraq's Removal of Counterterrorism Chief Sparks Controversy,” Military Times, September 29, 2019, https://www.militarytimes.com/flashpoints/2019/09/29/iraqs-removal-of-counterterrorism-chief-sparks-controversy/, 上网时间:2019年12月28日。也有人认为是因为萨阿迪坚持与腐败势力斗争。③“Iraq Protests: What's Behind the Anger?” BBC, October 7, 2019, https://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49960677, 上网时间:2019年12月28日。
从五轮抗议运动的起因可知,民众既对政府执政能力不满,又对政治精英在制度框架内解决问题失去信任,在强大的外部势力渗透和影响下,作为“局外人”的群体更可能抓住机遇挑战制度,在政治机会不断扩张背景下,突发性事件的刺激极易引发抗议行为的出现。
(二)有效的基层组织动员
抗议运动频发显示出伊拉克抗议群体具备有效的本地组织、沟通网络和动员能力。从社会运动实践来看,参与者可能参与不止一种诉求的社会运动,周期性运动使得本地组织在不断地运动中强化了组织能力,客观上还培训了更多实际参加过抗议的成员,给抗议运动周期性发生提供了条件。
政治过程理论认为,大范围的运动并非是专门组织起来的,而发源于街头、社区等基层小组织之中,通常弱势群体中的整体性融合性越高,人们越容易被动员成为抗议者。与政治精英依赖宗派性质动员不同,社会基层组织、小规模新兴利益阶层,为抗议发起提供了最初的组织体系。从妇女署和开发计划署等联合国机构到美国政府、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组织为推动中东“民主化”和建立民间社会的努力起到了很大作用。尤其是在伊拉克战争后,由联合国、国际和欧洲捐助者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成倍增加,围绕民主、建设和妇女权利等问题投入资金和项目,被新的专业精英群体所接受。例如,中东地区多个国家的地方协调委员会(Tansiqiyat),成为普通市民提供交流和解决问题的基层组织;希望组织(Al-Amal)和伊拉克妇女自由组织(OWFI)依靠国际女权主义者和妇女权利网络的资助,组织伊拉克妇女参加抗议,其中2015年运动中妇女占抗议者的14%。①Zahra Ali, “From Recognition to Redistribution Protest Movements in Iraq in the Age of New Civil Society,” Journal of Intervention and State-building, Vol.15, No. 4, 2021, p. 534.经历抗议活动后,受过教育的伊拉克中下层民众和中产阶级开始觉醒,对“萨德尔运动”、伊拉克共产党等组织运动方式转变看法,开始尝试新的组织形式。例如由中产阶级领导的贫民窟居民“再安置”计划,以及由伊拉克作家联盟发起的“我是伊拉克人,我读书”运动。伊拉克抗议经历了从宗派动员到市民社会动员的转变,新兴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开始探索世俗的跨越阶级和宗派的抗议组织新形式。
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互联网和新媒体在世界范围抗议活动发起过程中都扮演了重要的组织沟通角色。调查显示,2015~2016年抗议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是运动的骨干(约占60%),而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占总人口的67%。②FalehA.Jabar,TheIraqiProtestMovement:FromIdentityPoliticstoIssuePolitics,p.12.与老一辈伊拉克人不同,青年一代熟悉社交媒体的使用,以年轻人为主体的自发抗议运动最初也是在社交网络上进行动员。一些潜在的运动发起者认为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可以迅速转变,存在利用来自多个国家的社交网站进行广泛动员的潜力。③Killian Clarke, “Unexpected Brokers of Mobilization: Contingency and Networks in the 2011 Egyptian Uprising,”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46, No.4, 2014, p.379.例如,在2011年抗议运动中,一群伊拉克年轻人,包括知识分子、记者、学生、政府雇员和失业青年公布了他们利用社交媒体组织示威反对政府的计划。由“脸书”(Facebook)和“优兔”(YouTube)创造的网络公共领域,在组织抗议运动和团结公众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④Ahmed K. Al-Rawi, “The Arab Spring and Online Protests in Iraq,”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8, No.1, p. 935.网络动员与网络情感构建也开始成为周期性抗议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
(三)民众的认知情感共识
根据政治过程理论,政治机会和本地组织为社会运动提供了客观的结构潜力,中介这种潜力和实际行动的是人们之间形成的认知情感共识。个体的主观想法通过复杂的社会心理作用方式,完成集体属性和社会建构“框架建构过程”①David A. Snow, E. Burke Rochford, Jr., Steven K. Worden and Robert D. Benford,“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1, No. 4, 1986, p. 464.,最终形成运动潜在参与者的认知和情感共识,这时发生集体行动的机会就变得极大。
第一,从抗议运动在多地不断发生可知,伊拉克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已经充分被各界人士所认同,抗议者表达的诉求包括反对腐败、提高公共服务和生活水平、解决就业等经济问题,教派平等、结束民族宗教配额制度等国内政治问题以及反对国外势力干涉。逊尼派在2015年和2019年两轮大规模抗议运动中参与不足,但一项针对逊尼派人士的调查显示,43%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参加抗议运动是害怕因恐怖主义指控而被捕,79%的人表示支持抗议者的诉求。可以推断,逊尼派民众较少参与抗议运动是害怕因逊尼派身份遭到迫害,而不是与抗议运动产生分歧。②Faleh A. Jabar, The Iraqi Protest Movement: From Identity Politics to Issue Politics, p. 20.库尔德地区在2015~2018年间也多次爆发抗议运动,抗议诉求也与伊拉克其他地区的抗议运动类似,要求立即对腐败采取行动,提供更好的经济机会,改善治理和基本服务。2019年抗议运动并未波及库尔德地区,主要原因是抗议运动提出的政治去宗派化呼吁让库尔德民众担忧,参加抗议可能被联邦政府当作修改宪法和限制地区权利的借口,进而影响到库尔德地区的自治局面,不参与并非是对抗议运动反应的问题缺乏认同。③“Why are Iraqi Kurds Not Taking Part in Protests?”Al Jazeera, November 11, 2019,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9/11/11/why-are-iraqi-kurds-not-taking-part-in-protests. 上网时间:2020年12月25日。
第二,抗议者采用条幅、旗帜、标语、口号和海报等形式,在话语构建中体现出对政治体制的不信任和浓厚的民族主义倾向。抗议者打出的标语有:“我是逊尼派,但反对宗派主义;我是什叶派,但反对宗派主义;我是雅兹迪人,但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宗派配额分配,支持公民身份”④Faleh A. Jabar, The Iraqi Protest Movement: From Identity Politics to Issue Politics, p. 18.,“这个国家不需要布雷默⑤布雷默(Bremer)指美国驻伊拉克前最高文职行政长官。的宪法,不需要布雷默的政党,希望修改选举法,修改政党法”。⑥Toby Dodge & Renad Mansour, “Sectarianization and De-sectarianization in the Struggle for Iraq's Political Field,” The Review of Faith &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8, No. 1, 2020, p. 66.上述标语和口号有效地凝聚了抗议者的抗议理念,反映出民众对于战后政治制度的不满、反对配额制度的核心诉求。在2019年抗议运动中,抗议者高喊“没有家园”“我们想要一个国家”的口号,体现了民众对政府的愤怒以及对正常生活的渴望。①“In Iraq, Demonstrators Demand Change — And the Government Fights Back,”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0, 201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19/10/10/iraqprotestors-demand-change-government-is-fighting-back/,上网时间:2020年12月25日。国旗是国家身份的象征,伊拉克国旗广泛出现在抗议运动中,体现了抗议者对于伊拉克国家身份的认同。
第三,五轮抗议运动反映出抗议者普遍对于政府和“局内人”极度缺乏信任。根据2019年底对抗议者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除了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Ali al-Sistani)得到60%抗议者的信任以外,其他所有国家机构(包括立法机构、行政部门、司法部门)得到的信任都不到5%。超过90%的抗议者欢迎提前举行选举,但由于他们不信任政府机构,很少有人同意在目前的选举委员会主持下举行选举,即使在法官的监督下举行选举也不被认可。抗议者对于国外力量的信任度也很低,1%的受访者信任伊朗,7%信任美国,25%信任欧盟,30%信任联合国。②Anthony H. Cordesman and Grace Hwang, Strategic Dialogue: Shaping a U.S. Strategy for the “Ghosts” of Iraq,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April 22, 2020, p. 8.这种对任何体制内角色缺乏信任、反对一切的抗议心态使得抗议运动无法转变为一股协调的、结构性的社会力量,使得抗议运动不能提出明确可行的政治纲领,只能停留在空有口号的阶段。
四、周期性抗议运动发展衰落的原因分析
根据运动发展与衰亡模型,运动兴起之后各因素之间的作用机制变得更加复杂,首先是社会控制程度因素的加入,即政府和精英集团对运动的反应和应对措施。其次,运动兴起后同样也会改变政治机会结构,从而使运动的发展环境更加动态化。最后,导致运动兴起的内生组织强度、认知革命因素也有不同的变化路径,是否能够持续保持组织强度,不断获得运动发展所需的资源,是否能建构参与者集体属性,让更多参与者保持初始目标和共同利益认同,决定着运动迈向成功或走向衰亡。通过观察五轮抗议运动从发展到衰落过程,政府恩威并施的策略和精英集团的分化利用体现出具有伊拉克特点的社会控制。民族宗派配额制度造成了任何“局内人”组建的政府都难以真正解决经济社会问题,从而使“局外人”发起运动后再难以扩张政治机会。配额制度导致的利益认同宗派化、国家认同缺失等原因,使运动兴起后难以保持组织强度,无法进行抗议者集体属性建构。抗议运动陷入兴起易、成功难的循环困境。
(一)难以对抗的社会控制反应
社会控制是外部环境针对社会运动的反应,根据运动发展的阶段和强度,由抗议运动产生的政治条件改变在给政治系统带来变革压力的同时,其他政治集团会做出符合集团利益的回应。从抗议运动周期性经历兴衰的过程来看,政府和精英集团的应对手段表现得极具特色。
第一,在五轮抗议运动中,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总体来说是恩威并施,一方面回应抗议者的诉求,宣称将进行改革改善问题;另一方面出动安全部队进行镇压,阻止抗议扩大。政府有时还会采用分化抗议群体、转移抗议矛盾策略来寻找镇压抗议运动的正当理由。
在2011年抗议中,时任总理马利基承诺要解决电力问题,创造就业机会,提供食品补贴,削减自己的工资,指责地方部门并提出撤换官员。但当这些举措没有减轻抗议势头时,他以复兴党和“基地”组织渗透抗议队伍为由出动安全部队进行镇压。马利基还指控2012~2013年逊尼派抗议运动受到土耳其、卡塔尔等外国势力的操纵,进而出动军队进行镇压。2015~2016年抗议中,政府一方面支持宪法保障的集会自由,寻求与示威组织者的谅解;另一方面采取大规模军事和安全防范措施。政府的暴力手段较前两轮抗议有所下降,使得抗议规模迅速扩大。2018年抗议运动出现抗议者攻击政党办公室和政府机关、纵火伊朗领事馆的行为,政府再次采取让步和镇压的双重举措。时任总理海德尔·阿巴迪(Haider al-Abadi)一方面承诺在南部进行投资,另一方面又支持民兵组织参与镇压,示威者和安全部队的冲突造成至少15人死亡,约190人受伤,社会活动人士因参与示威活动而被捕。①“Water Uprising in Basra: 15 Protestors Lose Their Lives and Political Alliances are Redrawn,” Iraqi Civil Society Solidarity Initiative (ICSSI), September 18, 2018, http://www.iraqicivilsociety.org/archives/9176, 上网时间:2019年12月28日。在势头更大的2019年抗议运动中,政府采取断网、宵禁、出动安全部队等高压措施,造成了五轮抗议运动中最高的伤亡数字。据伊拉克国家电视台2020年2月3日报道,抗议运动导致556人死亡,其中包括13名为安全部队成员。②“Who is Cracking Down on Iraq's Anti-government Protesters?” Post of Asia, February 3,2020, https://postofasia.com/who-is-cracking-down-on-iraqs-anti-government-protesters/, 上网时间:2020年3月2日。与此同时,政府宣布的应对方案也更加优厚,包括为低收入群体建造数千套补贴住房、为失业者提供津贴、为青年提供培训和贷款等①孙华:《已致104人死亡的伊拉克大规模示威游行起因蹊跷,疑似有外国势力在背后插手》,文汇报,2019年10月9日,http://www.whb.cn/zhuzhan/huanqiu/20191009/293683.html,上网时间:2020年3月2日。。2020年5月卡迪米上台后,迅速下令释放自10月份以来被拘留的所有抗议者,向受伤或死亡人员的家属提供赔偿,任命萨阿迪为伊拉克反恐部队司令,②Sajad Jiyad, “Time for a Reset: Iraq's New Prime Minister and the US-Iran Rivalry,” 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y11, 2020, https://ecfr.eu/article/commentary_time_for_a_reset_iraqs_new_prime_minister_and_the_us_iran_rivalr/,上网时间:2021年2月5日。并承诺尽快举行新大选。在一系列新政下,运动势头暂时得以缓和。
第二,精英集团对运动采取了分化利用的策略。大部分社会运动会造成精英集团分裂,精英集团通过判断运动是威胁还是机会采取对抗、合作或不参与等行为。伊拉克抗议运动始终没有形成更大范围内统一的内生组织,抗议者也没有和其他政党形成稳固的联盟,这其中部分原因来自抗议者内部,但精英集团利用抗议的动员能力,达成自身政治利益诉求表现得更为明显。
从五轮抗议活动来看,抗议群体目标诉求是改革式的非极端革命。改革性诉求一般不会遭到精英团体的一致抵抗,某些政治和宗教领袖也会为抗议者提供人员支持和宣传资源。例如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对除2012~2013年逊尼派抗议运动外的四轮抗议都表示了支持和同情。兴起的抗议运动同时也成为精英集团争取政治地位的有效工具,在2011年抗议运动中,抗议者起初只是对腐败、基本公共服务不足提出抗议,随后逐步转变为联合抵制时任总理马利基,从经济目标到政治目标的转换随即赢得了宗教领袖的联合支持。2015~2016年抗议运动最初由巴格达左翼世俗主义者发起并领导,随后什叶派教士、“萨德尔运动”领导人穆克塔达·萨德尔(Muqtada al-Sadr)号召其追随者加入,使抗议规模迅速扩大。随后,萨德尔派、伊拉克共产党和著名民间社会活动家将这场自发的青年运动转变为一个选举联盟,运动也从社会青年主导的单纯变革运动转变为一个复杂的政治利益群体。③Zahra Ali, “From Recognition to Redistribution Protest Movements in Iraq in the Age of New Civil Society,” p. 531.在2018年5月的大选中,萨德尔与伊拉克共产党组成的竞选联盟“沙戎联盟”(Sairoon Coalition)获得议会最多席位。一些学者认为这是精英操纵的典型案例,萨德尔提出的是“假民粹主义”,同时利用民众抗议和左派资源来追求政治利益,因此产生的联盟只是一个“工具性联盟”,“该联盟成员既不依赖,也不产生更大的影响”。①Ben Robin, “Social Brokers and Leftist-sadrist Cooperation in Iraq's Reform Protest Movement: Beyond Instrumental A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51, No. 2,2019, p. 258.
政治精英的加入并非真正认同抗议者,也不是为了解决抗议诉求,更未能基于抗议群体进行文化或意识形态建构,运动只是精英寻求自身政治利益的机会和工具。因此,政治精英加入而扩大的抗议不能表明抗议运动的内生组织增强。在2019年抗议运动中,萨德尔的政党因为没有解决社会问题而被新的抗议者抗议,抗议者与政治精英之间的关系变得互不信任。
(二)难以解决的经济社会问题
关于经济民生的抗议诉求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任何一方或联盟组成的政府都无力完成对抗议者的承诺。基于配额制度组织起来的权力分享体系意味着对政府职位任命的分配就是资源的分配,执政的政党联盟可在政府中获得最有权力和最多的职位组合,掌握部长等高级行政职位,从副部长、顾问到普通公务员的任命也都遵循这一原则进行分配,甚至政府合同也按此分配。配额制度导致制度化、系统化的腐败,某些职位总是出于同一政党或党派联盟,政府内裙带关系盛行。在伊拉克这样一个主要依靠石油租金的食利国家,各政党都希望能掌管资金充足的部门。经济的发展与改善不再重要,如何掌握现有资源分配比例才是首要考虑,这种基于现实经济利益的选择使各党派之间内耗严重,政府不仅无法满足公民的生活需求,也无法做出实质性改变。
在2018年抗议中,一位抗议者表示:“萨德尔派有100多名局长,超过5位大使和部长,还有40名国会议员,其中许多人自身和腐败有关,他们怎么能抗议腐败?”②Ibid., p. 272.据调查,2011年中东乱局之后,政治机构信任度在埃及、突尼斯、约旦和摩洛哥都发生了下降,其中埃及和突尼斯发生了民主转型,尤其是突尼斯进行了相当稳定的民主化,但信任度同样下降,原因在于两国政府都无法短期内解决起初抗议群体所要求的社会经济问题。③Niels Spierings, “Trust and Tolerance Cross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Impact of the Arab Uprisings,”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Vol. 5,No. 2, 2017, p. 10.通过对伊拉克和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观察,抗议者对通过运动解决现实问题,利用政治机会提升组织地位很难有乐观估计,对于教派冲突和战争的恐惧又让抗议难以突破现有局面,抗议运动在两难的尴尬中不断重复。
(三)难以保持的抗议组织强度
如果说有效的基层组织为抗议的兴起提供了基础条件,在运动发起之后难以增强组织强度则是抗议运动周期性衰退的原因之一。运动兴起所依赖的小型本地组织有着坚实的共同利益基础。随着时间发展,运动需要在小组织利益的基础上形成更大范围的新的集体利益,从而避免“搭便车效应”,①[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将组织的远景利益转化为实际中组织强度的增加。从抗议运动发展进程看来,抗议群体始终没有明确的政治层面领导,亦没有形成稳固的政治同盟,抗议运动成为因突发事件引发的反应性事件。
第一,配额制度下的伊拉克宗派主义盛行,给民众设置了明确的政治立场边界,对腐败或公共服务不满的小群体内一致的利益取向难以跨过宗派主义政治边界,形成更高层次的政治利益共识,从而使运动组织难以获得持续进行的资源。伊拉克教派和腐败政治精英掌握的武装团体和民兵在对伊斯兰国战争后已经制度化。②Renad Mansour, “More Than Militias: Iraq's 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s are Here to Stay,” War on the Rocks, April 3, 2018, https://warontherocks.com/2018/04/more-than-militias-iraqs-popular-mobilization-forces-are-here-to-stay/,上网时间:2021年3月1日。通过参加议会大选,准军事部队和民兵的领导人现在已是议会成员,他们对在摩苏尔和伊拉克其他地方威胁、绑架和杀害民间社会活动分子以及许多侵犯人权的行为负有责任。各武装派别和部落领导人任人唯亲,这一制度支配着公共行政和工作,并分配资源以交换效忠。③Zahra Ali, “From Recognition to Redistribution Protest Movements in Iraq in the Age of New Civil Society,” p. 531.
第二,伊拉克政坛由具有政治资本的政治精英领导下的政党或联盟把持,这些政治精英大都出身名门望族,且有父子传承的传统。如“萨德尔运动”的领导人穆克塔达·萨德尔出身于著名的萨德尔家族,其家族是伊拉克政治宗教界两大最有名望的家族之一,出过多名政治和宗教领袖,达瓦党(Dawa Party)创始人即来自该家族。而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领导人阿马尔·哈基姆(Ammar al-Hakim),则出自两大家族中的另一家族——哈基姆家族,由他组建的“全国智慧运动”(Hikma)是2018年议会大选的重要什叶派政党。家族式的精英政治传统给抗议运动发展带来了极大困难,已有的政治团体占据大量组织空间和常规组织实体,运动很难在保持初始利益取向的前提下获得足够的资源。从2015年运动可以明显看出,抗议群体领袖为了获得支持进行的联盟行为很容易产生内部分化,抗议群体领袖在现实政治环境下很难形成领袖权威。
第三,在现有配额制度下,抗议运动自身产生新的政治力量,或者完全颠覆现有规则形成一种强烈威胁,会导致精英集团共同抵制。抗议运动经历了获得精英支持到被精英集团利用的过程,抗议组织形式也逐渐发生改变,五轮抗议运动中的后两次显现出不发展政治组织、不进行政治合作的明显转变,抗议由普通公民领导,不再主动联合任何有组织的民间社会团体和政党。这种单纯性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小范围抗议群体目标一致,但缺点也很明显,松散的公民领导无法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体系,使得政府镇压工作变得更为容易。①Zahra Ali and Safaa Khalaf, “Southern Discontent Spurs an Iraqi Protest Movement,”Current History, Vol. 117, No. 803, 2018, p. 343.
(四)难以推动的集体建构进程
持续的意义塑造和集体建构过程对运动发展非常重要,需要参与者拒绝对现有世界的解释,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和新的相互作用准则。在五轮抗议运动发展进程中,集体属性的归因和建构极为艰难,配额制度作为一个缩影,反映出本土文化、外来政体的共同作用对这一进程的强烈约束,体现着多种族和信仰多元化对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挑战,也反映出国家吸收和控制的失败。②Irene Costantini, “Practices of Exclusion, Narratives of Inclusion: Violence, Population Movements and Identity Politics in Post-2014 Northern Iraq,” Ethnicities, Vol. 20, No. 3, 2019. p. 2.
2003年,美国占领当局和伊拉克联盟临时权力机构成立了由25名成员组成的临时管理委员会,该组织是伊战后首个政府雏形,成员由13名什叶派、5名库尔德人、5名逊尼派、1名土库曼人和1名亚述人组成,代表了伊拉克复杂的社会结构。③Toby Dodge and Renad Mansour, “Sectarianization and De-sectarianization in the Struggle for Iraq's Political Field,” The Review of Faith &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8, No. 1, 2020, p. 61.此举将民族宗教身份政治化,奠定了伊拉克战后新政治体系基调,个人政治立场首先由其家族、部落、教派和民族决定,而不是公民身份。这种基调延续到随后大选中,获得了什叶派和库尔德人支持,逊尼派在被排除在政治制度之外的威胁下,由最开始抵制投票转而参与到宗派主义进程中。此后,宗派主义成为伊拉克选举中各政党进行动员的有利工具。例如前总理马利基在选举中强调什叶派身份,试图将逊尼派和库尔德人放到什叶派的对立面,以建立一个泛什叶派联盟,同时将逊尼派抗议与恐怖主义组织联系在一起,以此为镇压披上合法的外衣。
宗派主义和外来政体结合出的配额制度,将本就缺乏国家认同的伊拉克社会进一步撕裂,使民族国家的概念让位于不断上升的次国家身份认同。随着配额制度不断发展,更大的民族—宗教联盟内部斗争日趋激烈,分裂成更小的利益集团,进一步破坏民众集体意义塑造的基础。这种撕裂现象在2014年大选中达到了顶峰,共有36个竞选集团争夺议会的328个席位。其中,代表什叶派的有8个团体,库尔德人也分裂为4个集团,逊尼派则分裂为10余个参选团体。此外,还有一些代表少数民族的团体。①Faleh A. Jabar, The Iraqi Protest Movement: From Identity Politics to Issue Politics, p. 12.深刻的社会撕裂和认同缺失,让运动参与者在意识上很难形成一种共同归属。
抗议群体往往通过口号、标语等基本宣传形式进行集体建构。2018年,正义联盟(AAH)试图加入抗议运动,而部分抗议群体领袖拒绝正义联盟的加入,抗议群体因此产生分裂。在约定只使用伊拉克国旗,采用相同衣着、口号和标语进行抗议后,正义联盟在巴格达解放广场中依然打出了自己的旗帜,引发宣传平台之争,导致民间抗议分子大规模撤离,伊斯兰主义者控制了广场中央平台。②Ben Robin, “Social Brokers and Leftist-sadrist Cooperation in Iraq's Reform Protest Movement: Beyond Instrumental Action,” p.261.在2019抗议运动中,抗议者最初提出“我们想要一个国家”的口号,③“In Iraq, Demonstrators Demand Change — and the Government Fights Back,”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0, 201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19/10/10/iraqprotestors-demand-change-government-is-fighting-back/, 上网时间:2019年10月12日。继而开始反抗伊朗并喊出“伊朗滚出去”的口号,美国暗杀伊朗“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后,抗议者从单纯抗议伊朗又转而同时抗议伊朗和美国,在新总理提名问题上抗议者内部再次出现分裂。不停变换的抗议口号导致无法形成坚实的共同愿景和可行的改革诉求。④“Iraqi Protesters Face off Against Cleric's Followers,” Al Arabiya, February 4, 2020,https://english.alarabiya.net/en/News/middle-east/2020/02/04/Iraqi-protesters-face-off-against-cleric-s-followers.html, 上网时间:2021年2月15日。抗议团体因为抗议目标、宣传方式、抗议手段、联盟伙伴等问题而产生分裂和争斗,背后是难以跨越的民族宗教隔阂,民族国家基础已被宗派利益摧毁殆尽。集体建构的失败与抗议的式微过程相伴,让抗议参与者对成功的期望逐步转为对前景的悲观。
五、结语
纵观伊拉克战后发展历程,战争、教派冲突和恐怖袭击对民众和政治精英都造成深刻影响,抗议运动中的民众惧怕走向利比亚和也门式的混乱结局。精英集团在现有政体下保留参与权,同样不能接受对“局内人”革命性运动或颠覆政府行为。伴随对双方都存在的威胁,历次抗议运动都表现出改革性而非革命性。或许在伊拉克的政治结构中,无论制度内精英还是受压迫的民众,都认为一个充满问题的政治制度要好于一个未知的政治制度。
脆弱的经济社会基础、较低的政府执政能力、外部势力的干涉和各种突发事件的刺激为伊拉克抗议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政治机会,社会基层组织为运动兴起搭建了初期的组织架构,大量不满的年轻人和新兴社交网络则为抗议运动的扩大提供了可能。由于政府恩威并施的应对策略,精英集团的分化利用,组织强度难以增强,以及集体属性建构进程受阻等原因,抗议运动逐渐进入低潮,形成了因公众利益发起运动,精英群体支持运动,抗议目标和利益诉求转向精英群体偏好,侧重点转变为抗议政治体制,运动组织分化,运动逐渐式微的循环。由于政治体制并未真正进行改革,经济恢复和重建仍然看不到明显好转的可能,配额制度限制了政府治理能力提升,民众对政府信任感丧失,外部势力仍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角力。以上因素造成引发抗议运动的政治机会一直存在,突发性事件可能引爆新的抗议运动。从五轮抗议的衰落过程看,政府控制、拖延、分化的策略行之有效,2020年突发的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也让运动形势迅速衰减。弱小的运动会鼓励政府做出镇压行为,①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8,p. 4.在经历了多次运动失败后,抗议者更倾向于通过提升运动力强度来增加与政府谈判的砝码,让政府选择镇压策略时面临更大的成本和风险,从而做出让步与合作。从五轮抗议运动的实际表现看来,运动强度显示出不断提升的趋势。
周期性抗议运动可能成为推动伊拉克政治体制被迫改革的关键因素。美国不顾伊拉克国情和历史文化现实,将美国式联邦模式和民主制度移植到伊拉克,导致伊拉克的多党制成为披上民主外衣的宗派主义,由此产生的利益交换根深蒂固,因此政治改革很难来自伊拉克政治体系内部。对于抗议者来说,政治精英之间因为宗派和意识形态差别裂痕明显,任一派别都无法完成广泛的政治动员。此种情境下,抗议运动所表达的民族主义和问题导向特征,成为政治精英十分需要的跨越宗派和意识形态的动员手段,蕴含着未来国家认同建构基础。对分裂和对不确定政体等担忧共识下,来自民众的抗议运动成为国家政治权力非正义运行时唯一可能的纠偏方式,亦是推动精英阶层进行政治改革的关键性因素。虽然新任总理卡迪米已被国内和国际各方所接受,但他更像是各方势力妥协后的折衷选择。卡迪米在政坛资历不深,且在议会中没有可依靠的政党,这使他很难进行根本性改革,抗议运动所表达的诉求基本不可能实现,抗议者随时可能重回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