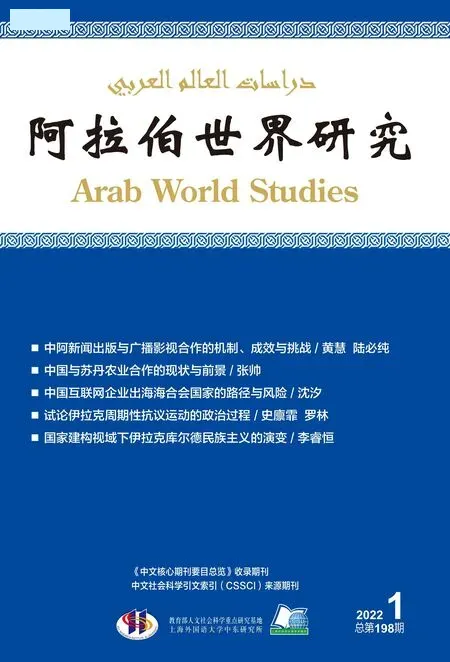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海合会国家的路径与风险*
2022-04-22沈汐
沈 汐
互联网技术的全球商业传播与应用深刻地改变了全球化的内容、形式和发展方向。基于其生成性(generative)的技术特征,互联网与经济产业实体广泛融合,通过“互联网+创新”的形式创造和发现新的价值和市场。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已经成为全球新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不仅如此,互联网“无界”(borderless)和“瞬时”(time-less)的媒介特征使得横亘于传统民族国家之间的地理—政治隔阂变得越来越不明显。随着诸如电子商务、社交媒体开始成为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互联网产品也已经成为连接民众、企业和国家的重要媒介。
尽管互联网出海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文化现象,但西方主流学界依然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资本—权力的框架下来把握互联网产生的全球化政治意涵。他们认为,互联网作为新兴传播技术极大促进了资本全球流动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对政治经济权力格局、资本流动、社会交往和认同的重塑有着重要作用,数字技术的运用和控制已经成为当代全球体系和全球化进程背后的重要逻辑和机制,推动全球化进入“数字转向”①Manuel Castells, Communication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50-53; Jan van Dijk, The NetworkSociety: Social Aspects of New Media,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2001, pp. 103-113; Shen Hong, “Building a Digital Silk Road? Situating the Internet in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12, 2018, pp. 2683-2701.时代。如此一来,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常常被置于一种想象的“自由市场”和“威权国家”的二元对立之中,西方学界普遍抽象地和脱离历史语境地强调互联网自由、中立的规范性价值。因此,主流互联网治理话语奉行的是资本主导的自由市场和国家“不介入”的最小化角色。②Laura DeNardis, Derrick Cogburn, Nannete Levinson and Francesca Musiani, eds.,Researching Internet Governance: Method, Framework and Future, Cambridge: MIT Press, 2020,pp. 33-39; Milton Mueller, Networks and States: The Global Politics of Internet Governance,Cambridge: MIT Press, 2010, pp. 253-271.
综上,西方主流学界着眼于西方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格局,其话语背后的意图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政经发展的单向度趋势中理解把握数字时代的全球互联网治理,并且惯常地把来自中国的创新实践标签化为“反常”,“例外”甚至是“威胁”,中国等其他新兴经济体对全球数字新秩序的主动和创造性的发展建构过程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③Daya Thussu, “A New Global Communication Order for a Multipolar World,”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Vol.4, No.1, 2018, pp. 52-66.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全球交往活动都包含有数字成分,新一轮全球化的底层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鉴于此,有学术研究开始从具体的物质生产、国家产业战略和企业创新等共同作用的综合互动视角出发,思考中国互联网如何在主权政府战略的影响下主动创新,开发新的技术运用场景并拓展新的市场。①参见Hong Yu, Networking China: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Economy,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7, pp. 147-154; Jia Lianrui, Winseck Dwayn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Internet Companies: Financialization, Concentration, and Capitaliza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Vol. 80, No.1, 2018, pp. 30-59; Gianluigi Negro,“Chinese Internet Companies Go Global: Online Traffic, Framing and Open Issues,” in M. Kent, K.Ellis and J. Xu, eds, Chinese Social Media: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New York:Routledge, 2017, pp. 175-190.这种力量为形成更为开放的、基于社会发展的和共同参与治理的新全球数字发展格局提供了可能。
互联网全球化这一复杂的政经现象跨越较大的学科背景。本文认为,对这一现象进行具体的和立体的个案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如何在新技术条件下参与和重构新一轮以数字往来为特征的全球化进程。基于此,本文聚焦于中东地区的海湾地区,选取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合会)国家②本文所指海合会国家特指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成员国。其他海湾地区国家如伊朗、伊拉克和也门等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作为研究个案。海合会国家是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的重要节点区域,该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动能和海合会国家的数字发展战略形成了互补的合作基础。本文通过分析海合会国家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的历史因素和经济社会语境,结合中国互联网企业在海合会国家的业务布局和经营实践,阐述和分析中国互联网企业在海合会国家开拓市场的特点和路径,以及中国跨境数字企业在塑造竞争力过程中面临的监管风险和治理挑战。当前,全球互联网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国家、社会和商业资本等不同行为主体的利益复杂交织其中。观察和剖析中国互联网所催生的技术、平台和模式的出海实践样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在新一轮全球化中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和理想使命。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互联网集体出海
自1994年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在政府战略、市场规模和繁荣的产业发展环境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中国开始从一个拥有10亿网民的互联网大国走向互联网发展强国。以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为代表的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已经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社交新媒体、视频娱乐、电子商务以及在线支付等领域积累了技术和商业实践优势。①Ming Tang, “From ‘Bringing-in’ to ‘Going-out’: Transnationalizing China's Internet Capacity through State Policie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13, No.1, 2019, pp. 27-46.截至2019年,全球有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互联网独角兽企业②互联网创投市场一般把成立时间小于10年且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创业公司称为“独角兽(Unicorn)”。来自中国。根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调研显示,大约40%的中国互联网企业有来自海外的业务收入,60%的互联网企业高管认为海外市场与国内市场同等重要。③“Are China's Digital Company Ready to Go Global?” BCG Consultant, May 22, 2019,https://www.bcg.com/publications/2019/china-digital-companies-ready-go-global,上网时间:2020年11月30日。技术优势和规模市场带来的产品优势已经为中国互联网产品和服务走向海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已经开始拓展全球业务,走到了数字全球化的前台。
(一)技术资本优势加持的互联网企业将目光瞄准海外
近年来,中国出口总量中的新兴服务贸易发展较快,它正在成为全球跨境贸易中增长最为显著、表现最为活跃的部分,尤其表现为个人文化娱乐活动方面的信息通讯技术产品(ICTs)和互联网产品(主要是Apps)。④2021年1月至10月,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总额为18,566亿元,同比增长13.3%,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44.2%,同比提升0.2个百分点。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10,060.4亿元,同比增长16.9%,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50.4%。参见《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网站,2021年12月2日,http://www.mofcom.gov.cn/xwfbh/20211202.shtml,上网时间:2021年12月22日。跨境数据流、信息流和贸易流正在传统贸易的基础上释放出市场潜能和价值。从国家层面看,国务院在《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提出鼓励企业抱团出海,配合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支持和鼓励具有竞争优势的互联网企业联合制造、金融、信息通信等领域企业率先走出去,通过海外并购、联合经营、设立分支机构等方式,相互借力,共同开拓国际市场。⑤《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国政府网,2015年7月14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7/04/content_10002.html, 上网时间:2020年10月5日。2020年8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开展新一轮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进一步推进服务贸易发展试点,支持重点新兴服务出口,通过数字化手段驱动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在国家顶层设计的引导下,中国互联网企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拥抱全球化,从工具类产品到信息分发、社交游戏、在线教育等内容类产品。①《2019年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发展报告》,中国互联网协会,2019年8月14日,https://www.isc.org.cn/editor/attached/file/20190814/20190814172235_29273.pdf, 上网时间:2020年11月6日。位于“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南亚、中东、非洲和东欧等国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较弱,数字经济水平偏低,数字化程度不高,中国互联网企业提供数字贸易服务和产品的能力恰好与这些市场需求形成互补。在中东北非地区,尤其是海合会国家在短短几年内迅速成为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创业圈子中的“蓝海市场”。
(二)海合会国家的石油经济和政府数字战略为跨境互联网业务的繁荣提供了基础
海合会国家普遍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和繁荣的石油经济。然而,全球油气资源的枯竭问题、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已经敲响了石油经济的警钟。从全球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整个中东北非地区互联网产业起步相对较晚。不过,海合会国家在信息技术投资和数字经济发展领域却展现出了不一样的图景。根据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 GSMA)的年度统计数据显示,海合会国家智能手机的接受度为75%,②“GSMA The Mobile Economy Middle East & North Africa 2019,” GESMA Intelligence,November 10, 2020, https://www.gsma.com/mobileeconomy/wp-content/uploads/2020/11/GSMA_MobileEconomy2020_MENA.pdf, 上网时间2020年12月30日。远高于整个中东北非地区的平均水平(见表1)。

表1 2009~2019年中东地区互联网渗透率与全球平均值比较
凭借前期石油经济积累的财富,海合会国家在互联网发展方面呈现出一种非对称的形态:一方面,政府热情拥抱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未来科技;另一方面,海合会国家相对保守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并没有随着技术的进步发生根本性的变化。①Ilhem Allagui, “Internet in the Middle East: An Asymmetrical Model of Development,”Internet Histories, Vol.1, No.1-2, 2017, pp. 97-105.在国际原油价格波动风险和全球能源结构历史性变局的背景下,海合会国家纷纷意识到依赖单一收入来源的风险,国际组织(例如OECD和IMF)也频频警告海合会国家需要注意其严重依赖于化石燃料的国家财政的可持续性问题。因此,经济多元化一直是海合会国家近年来持续投入和努力的方向(见表2)。目前,几乎所有海合会国家都把数字转型和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多元化中的重要一环。例如,阿联酋在2021愿景中提出建设知识经济和知识型社会,沙特在2030愿景中也提出了向数字经济的转型目标,阿曼、巴林、卡塔尔和科威特等都提出类似的数字政府战略。阿联酋在整个海合会国家中走在了前列,2014年迪拜就提出了“智慧迪拜”计划,完成了迪拜互联网城和数字政府的建设。2017年阿联酋提出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计划,其中提到要重点利用数字经济和区块链技术来支撑阿联酋的创新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至2019年,阿联酋已经实现了数字经济对GDP的贡献率达到4.3%,成为整个中东地区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沙特也提出了雄心勃勃的“2030愿景”计划,其中,数字化转型是其经济多元化和社会转型的重要一环。②EnricoBenni,TarekElmasry,JigarPatelandJanPeterausdemMoore,“DigitalMiddle East: Transforming the Region into a Leading Digital Economy,” McKinsey & Company, October 17,2016,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middle-east-and-africa/digital-middle-east-transforming-the-region-into-a-leading-digital-economy, 上网时间2020年11月30日。

表2 海合会国家数字战略摘要
(三)海合会国家的数字消费需求日趋增强
与政治上的保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合会国家在数字战略上普遍呈现出来的进取和雄心。即使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海合会国家目前的互联网渗透率都属于较高水平。从政治文化环境来看,海合会国家均为逊尼派占主导的君主制国家,国内人均GDP普遍在两万美元以上,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基本进入了发达国家水平,居民整体收入水平较高,消费的意愿和能力较强。海合会国家总体人口规模不大。其中沙特人口为3,481万,紧随其后的阿联酋人口为989万,排在第三的阿曼人口为510万,其余几个国家人口均不到500万。从人口结构上看,海合会国家保持较高的出生率,整体人口处于较为年轻的阶段。以沙特为例,截至2020年,沙特常住人口已经超过3,400万,其中38.3%为外来人口,小于24岁的人口占比达到41%,生育率为千分之14.56,远高于全球主要发达工业国家。①“The World Factbook: Saudi Arabia,”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November 18, 2021,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countries/saudi-arabia/, 上网时间:2020年1月31日。由于对下一代教育的重视,绝大多数海合会国家的青年接受了比他们父母辈更好的教育。整体识字率基本都在90%以上,高度教育入学率保持在60%以上。②除了卡塔尔为20%之外,其余海合会国家的高等教育入学率都在60%以上。“World Tertiary School Enrollment,” The World Bank, September 1, 2021,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E.TER.ENRR?view=chart, 上网时间:2021年12月16日。
上述因素使得当地年轻人在思想观念上更为开放和活跃,对于全球流行文化以及互联网产品的接受度更高。他们普遍拥有智能手机,熟练掌握数字技能,乐于接受各种新潮的数字产品和数字生活方式,这和全球“Z世代”年轻人体现出来的特征是一致的。③“Z世代”指1995年至2009年之间出生的一代。他们从小就生活在移动互联网,动漫和手游组成的电子虚拟环境和现实环境结合的原生环境中。与“X世代”和“Y世代”相比,“Z世代”人群在充裕的物质环境下成长他们喜爱新鲜奇酷事物,更注重体验,通常展现出多样的价值观,创新冲动和消费意愿较强。自2010年以来,海合会国家在互联网用户的增长和渗透率上出现了强劲的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整个区域的互联网发展:2010年,中东北非地区与全球平均水平相当;而到了2019年,中东北非地区的互联网渗透率已经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中东北非地区的互联网用户的增长率达到了11%,大幅领先于西欧,北美和东亚等发达区域。其中,海合会国家的互联网渗透率甚至高居全球榜首,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和巴林占据了全球前十。阿曼和沙特则在互联网新用户增长上排名全球前二十。①“Digital 2020: Global Digital Overview,” We Are Social, January 30, 2020,” https://datareportal.com/reports/digital-2020-global-digital-overview,上网时间:2020年10月2日。2000年,沙特国内每百人拥有手机的数量仅为6.8部,而到2016年,这一数字已高达148.5部。截至2000年,海合会国家的互联网渗透率,除了阿曼为95%以外,其他几个国家均接近或达到100%。②“Individuals Using the Internet,” The World Bank, July 1, 2021,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IT.NET.USER.ZS, 上网时间:2021年12月1日。
二、中国互联网企业跨境海合会国家的商业化路径
海合会国家在政治文化上的保守严格和数字产业上的进取宽松为互联网创业的“野蛮生长”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蓝海”市场。一方面,海合会市场释放出的独特需求还未被西方互联网巨头企业重视和捕捉;另一方面,海湾地区互联网创业投资在近几年呈现出一个爆发增长阶段,互联网产业发展环境日趋成熟。根据中东创投平台MAGNiTT发布的报告显示,中东北非的创业并购市场交易笔数从2015年的全年204笔上升到了2019年的全年564笔,仅2016年就有9.6亿美金流入创投市场。其中,电子商务、金融科技和物流是风险投资追逐的热门标的。③“MAGNiTT 2020 MENA Venture Report,” MAGNITT, October 1, 2020, https://magnitt.com/research/q3-2020-mena-venture-investment-report-50731, 上网时间:2020年11月1日。海湾地区作为整个中东北非最为发达的区域,在吸引外资和创业融资方面远远领先于其他中东国家。尽管从人口规模上看,海合会国家的人口总量少于埃及、伊朗等传统中东人口大国,然而,强劲的市场需求和繁荣的创业投资环境等因素共同促使外国互联网公司把海合会国家作为开拓新市场的第一站。
(一)互联网敏锐的市场嗅觉
尽管海湾地区移动互联网渗透率增长显著,但海湾地区本地的人均域名拥有量却不高。从互联网信息服务供给的角度看,海湾国家本地的互联网企业偏少偏弱,用户能够使用的互联网服务多由国际互联网巨头提供。而从互联网内容上看,海湾地区的用户主要面对的是以英语的互联网内容。这意味着该地区用户基于文化偏好的需求未能得到充分满足。在移动互联网普及率快速提升的背景下,蓬勃发展的市场和井喷的需求为互联网跨境业务提供了巨大的增长空间。
就互联网产业化和商用化而言,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整体实力在“一带一路”沿线国中的比较优势明显。①马述忠:《“一带一路”,互联网企业重大机遇》,载《浙江日报》2017年9月12日,第5版。以中国已经发展成熟的电子商务市场为例,到2019年,中国的电商渗透率已超过25%,处于全球绝对领先地位;而在海湾地区,即便电商是最为发达的阿联酋和沙特等国,电商渗透率也不到4%,从国际比较水平看,这个水平甚至低于新兴市场和金砖国家。鉴于海湾国家相对富足的购买力需求,这样的差距为中国互联网跨境电商企业进入海湾地区提供了巨大的机遇。②“E-Commerce in MENA: Opportunity Beyond the Hype,” Bain & Company,February 19,2019, https://www.bain.com/insights/ecommerce-in-MENA-opportunity-beyond-the-hype/,上网时间:2020年9月7日。
中国互联网企业敢于进入西方垄断巨头不愿意或者没有动力进入的市场。早在十余年前,中东市场已经在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脸书和推特的影响下成为全球互联网业务的新增长点。据估算,中东北非地区有1.37亿活跃在线社交和娱乐用户,人均花费在社交上的时间远超全球其他区域。③“Social Networking in Emerging Markets,” Frost & Sullivan, April 1, 2021, http://www.frostchina.com/wp-content/uploads/2021/04/1-4.pdf, 上网时间:2021年12月16日。然而,阿拉伯语的在线社交和娱乐应用的选择范围比较有限。中国互联网企业的社交产品敏锐地瞄准增长迅猛的当地年轻Z世代人群,以本地用户习惯和偏好的形式提供基于阿拉伯语的产品和服务,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挖掘出极具潜能的新的增长空间。根据Sensor Tower的在线用户分析数据显示,2018年中东地区短视频和直播应用前二十名榜单中,来自中国的互联网产品占了十五个。海外版抖音TikTok,欢聚时代的Bigo Live等来自中国的应用以绝对优势力压推特的短视频应用Periscope Live。上述榜单中的20款应用在中东地区的苹果商店和谷歌在线商店的总收入达到1.07亿美元,其中,中国APP的应用内收入为1.02亿美元,占比高达95%。④Sensor Tower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是全球领先的互联网应用、市场调研公司,主要提供广告收益和APP运营数据分析,其产品数据被全球主流媒体、互联网企业和调研机构广泛运用。与西方巨头倾向于在全球推行标准化的产品和带有文化价值观输出倾向的服务不同,中国互联网企业善于研究本地用户的生活特征和实际需求。尤其是在社交娱乐产品上善于针对不同国家市场的需求差异进行个性化定制和开发,推出针对不同国家本土化的产品,并选用懂得本地用户习惯的本地化运营团队负责日常运营。
在电子商务领域,海湾地区本地制造供应链业相对匮乏。中国中小跨境企业凭借完整的产业供应链,在相对不成熟的市场条件下引入中国互联网运营优势,采取不同于西方巨头企业的独特方法,把中国电子商务较为成熟的运营理念和管理模式输出到海湾地区。依托国内制造业完整的供应链优势,借助低廉的商品采购成本和丰富的品类,结合互联网营销的高转化优势,通过日益便捷的跨境物流方案直接触达海湾地区的用户。在短时间内,位于中国沿海省份出口供应链发达区域的互联网创业公司,就能够通过撬动单一国家地区市场从电商小卖家成为独角兽企业。
在投资和经营全球化方面,海合会国家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企业全球扩张的主要目的地。2015年,阿里巴巴集团就和迪拜房地产巨头米拉斯(Meraas)成立合伙公司,开始筹备建立阿里云的中东数据服务中心;2017年,阿里巴巴宣布实施6亿美元的投资计划,计划与迪拜米拉斯集团在杰贝阿里自贸区(Jabel Ali Free Zone)区域建造一个可以容纳3,000家创业公司的数据人工智能创新产业园区。①“Why China Wants to Lead Middle East's Tech Revolution,” Arabian Business, November 16, 2017, https://www.arabianbusiness.com/industries/technology/383751-why-china-wants-to-leadthe-middle-easts-tech-revolution, 上网时间:2020年2月1日。同年,中国互联网出行头部企业滴滴出行参与了中东地区最大在线出行公司卡里姆(Careem)的融资。②卡里姆公司总部位于阿联酋迪拜,于2019年被全球移动出行巨头Uber收购,价格达3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互联网企业也获得了海湾本地风险资本的青睐,比如跨境电商浙江执御(Jollychic)和泛娱乐平台米纳科技(MENA Mobile)分别于2019年获得阿联酋人工智能科技公司G42集团的融资,规模均达到千万美金级别③G42是总部位于阿布扎比的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科技集团,在云计算方面与中国阿里巴巴集团的阿里云合作紧密,是阿联酋政府多个人工智能项目的承接方。G42集团在2020年获得了由阿联酋国家主权投资机构MUBADALA的融资。。
在移动支付领域,阿联酋马士礼格(Mashreq)银行与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合作,为越来越多前往阿联酋的中国游客提供移动支付服务。通过在海外为中国游客提供支付业务,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利用中国出境旅行这一特殊商机在海外布局新业务。①“Chinese Tech Investors Are Turning Towards MENA,” World Economic Forum, April 5,2019,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9/04/chinese-tech-investors-are-turning-towards-menaheres-why/,上网时间:2020年11月14日。同样依靠中国用户海外需求的案例还有在线旅行预订平台携程网,通过为海外中国商旅游客提供在线预订服务,成功于2016年和2017年收购了国际著名在线商旅平台天巡网(Skyscanner.com),从中国走向全球。跨境电商的繁荣为跨境支付产业的兴起提供了可能。在短时期内,中国涌现出了数家服务跨境卖家的收单支付平台,完善了以电商为核心的跨境数字贸易生态。
在“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鼓舞下,互联网企业成为中国提高国际通信互联水平,畅通信息丝绸之路的主要建设参与主体。在国家顶层战略制度设计上,“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互联网企业突破海外市场瓶颈,建设国际化的高水平互联网企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极为有利的条件。②肖蓉:《中国互联网企业与“一带一路”建设》,载《中国信息安全》2016年第2期,第57页。中国互联网企业依靠信息技术互联互通的有利条件,根据本地特有的需求开发具有创新性的产品,依托国内的研发和供应链优势重点突破。据移动互联网行业研究数据显示,在中东地区苹果在线商店(APP Store)和谷歌在线商店(Google Play)中上架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已经超过200家,上线的互联网产品超过500个,社交娱乐类和电子商务类应用占了主流。③《2019中国—中东互联网峰会》,白鲸出海网,2019年8月8 日,http://www.baijingapp.com/article/24238,上网时间:2020年11月27日。
(二)从碎片化的单一功能产品到矩阵化的平台服务生态
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的热潮开始于2010年。最初,跨境企业在海湾地区只是小规模的试水,以手机工具类应用产品为主。相比信息投资基建类的大规模投资,互联网企业出海的规模和成本要小得多,其产品灵活,开发周期短,市场准入门槛低,试错成本低为跨境创业提供了便利。互联网公司主要以小型初创公司为主,科学技术含量较低,主要以在全球互联网巨头平台(比如谷歌、Youtube、脸书)购买流量获得客户为主。2015年以来,在国内“双创”和“一带一路”大环境影响下,中国互联网企业开始大规模出海,从移动手机工具类产品到电子商务、社交软件、手机游戏以及短视频应用,传统上被认为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互联网产品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已经被中国互联网企业内化吸收,在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快速迭代的技术环境中生存下来的企业普遍采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数字手段向海外用户提供具有显著竞争优势的产品(见表3)。

表3 中国互联网企业在海湾地区的产品矩阵
以字节跳动集团旗下的海外版抖音为例,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加持下,字节跳动公司凭借技术的优势迅速打开全球主要市场,通过算法和模型提高用户的粘性和体验,为全球用户提供了内容创作和分享平台。①张志安等:《抖音“出海”与中国互联网平台的逆向扩散》,载《现代出版》2020年第3期,第22页。海外版抖音输出国内成功运营经验,在平台孵化网红达人直播、电商带货等业务。雅乐科技公司开发的娱乐休闲工具抓住了海湾地区用户日常生活休闲娱乐和社交的巨大需求,以贴近本地文化的运营手段,选择语音社交作为突破口,产品设计尊重本地用户的文化生活习惯,以聊天室辅以文字、图片等内容抓住了本地用户的需求和痛点。仅在2020年第二季度,500余万付费用户就在雅乐科技的社交游戏平台上使用达3.095亿小时,累计玩了4.072亿小时游戏,被誉为“中东腾讯”②《社交平台YALLA成功登陆纽交所》,中证网,2020年10月1日,http://www.cs.com.cn/ssgs/gsxw/202010/t20201001_6099511.html, 上网时间:2020年12月5日。。跨境电商浙江执御在提供一站式跨境自营电商购物的基础上,还开发了本地配送,在线支付等业务场景。在电商业务的基础上,融合其他创新业务,打造平台化的APP使用场景,为用户提供一站式的数字服务,成为中东跨境电商独角兽企业。以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云服务为例,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阿里云于2016年11月在迪拜开出第一家区域数据中心,其计算能力能够承载海湾地区所有的商业数据信息流。2020年2月阿里巴巴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WTP)基金会与沙特政府达成协议,在利雅得设立总部,加速跨境电商的发展。这种平台化的数字服务事实上扮演了孵化中小企业和创业公司的生态构建者角色,是深度参与本地数字化进程的体现。
从内容分发到社交娱乐再到电子商务,传统商业领域的业务分割逻辑已经难以涵盖互联网业务的平台化现象,互联网创新的能力也得以依靠平台上的海量用户和数据而进一步释放。在短短几年内,中国互联网企业在海湾国家已经从早期的单一的小产品垂直业务向大平台多产品的生态构筑阶段发展,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事实上正在成为海湾当地数字生活的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三)知识密集型驱动的本地化运营模式
互联网企业与传统的大宗贸易和基础设施承包建设面向大商户端和政府机构客户端不同,其产品面向的主要是个人用户端,在商业模式上具有传统零售贸易的特点。资产轻、业务灵活、产品周转速度快是互联网产品业务的主要核心特征,凭借在国内市场积累的实战经验,出海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开拓新市场方面具有周期快,成本低的特点,能够在短时间内以成本较低的方式反复试错和验证商业模式。
与传统大中型国有企为主要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合作项目相比,在海湾地区经营的中国互联网企业绝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除了少部分“头部大厂”之外,95%以上的互联网企业属于小规模企业,虽然整体业务盘子较小,但是增长快、灵活性高。这些企业普遍创业时间短,业务模式新颖灵活,容易嗅探到被市场忽视的机遇。在国内互联网出海创业浪潮和全球风险资本市场的助推下,来自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在海外经常“低调和鲜为人知”地迅速坐大。与此同时,初获成功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创立之初就具有国际化的基因和视野,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借鉴了美国硅谷的创业模型,在吸引全球风险投资资本和股权融资方面大胆创新;中国国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刺激了科技技术向商业化、货币化加速的进程;在出海过程中频繁采用海外收购和并购等操作,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用户渠道资源和本地人才资源。①Jia Lianrui, “Going Public and Going Global: Chinese Internet Company and Global Finance Networks,”WestminsterPaper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Vol.13, No.1, 2018, pp. 17-36.总体上看,中国互联网企业在跨境并购中体现出生态构建,市场进入、风险规避和文化适应等特征,能够为快速进入全新市场提供技术资源和人才智力支撑。②方旖旎:《互联网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路径与风险研究》,载《湘湖论坛》2018年第1期,第141-148页。
跨境互联网企业普遍采取了本地化策略,引入本地人才组成在地运营团队。国内研发团队加上本地运营团队的组合几乎是所有成功出海互联网企业的标准配置。互联网本身具有“生成性”的技术特点使得其产品能够在用户的使用过程中不断积累数据并迭代创新。数据驱动的互联网公司越来越平台化,提供的服务从单一走向多元,而在平台化的过程中,互联网用户的粘性和价值也越来越高。大数据算法为中小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拓展产品丰富性提供了可能,复制国内成功的商业模式并结合本地化的运营手段已经成为主流互联网创业者的黄金准则,并持续被全球风险投资市场看好。从提供单一产品服务到构建平台化的创新生态,互联网的这种“生成性”特征使得企业在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进化过程中迸发的市场潜力远超传统企业。①Jonathan Zittrain, “The Generative Internet,”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19, No.13,2005, pp. 1974-2040.
三、高速增长风口背后的风险和暗流
在全球科技创投社区里,海湾地区已经成为跨境创业者眼中的“蓝海市场”。不过,2014年夏天爆发的石油价格跳水为海合会国家经济发展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的全球大爆发更是让依赖国际商旅贸易的这些国家进入了停滞期。随着越来越多境外互联网企业的快速涌入,本地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在监管缺失的背景下,跨境互联网企业已经引起了当地政府和监管部门的关注,不断升级和趋严的监管环境将会成为新常态。
(一)长期低油价和新冠疫情双重打击下的低迷经济
国际油价的持续低位从总体上影响了海湾国家政府的支出能力。2016年沙特财政收入急剧萎缩至1,330亿美元,不足2013年的一半。2016年沙特国家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为17.2%,2018年曾降至5.9%,至2020年又上升到11.3%②“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ctober 1, 2021,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1/October, 上网时间:2021年12月15日。。经济不景气对用户的日常支出造成了直接影响。由于对本国公民的就业保护(海湾国家普遍施行就业本地化政策)以及新冠疫情导致的失业,在不少国家(比如科威特、巴林、沙特和阿曼)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外籍劳工流出迹象,直接导致市场容量萎缩。鉴于海合会国家本地人口依赖政府提供公共部门就业以及日常生活补助,国家财政支出紧缩带来的负面影响必然会通过压缩公共部门开支逐级传导至本地人口的日常消费能力。①海合会国家中人口最多的沙特在2030愿景中提出要将失业率从2018年的13%降到10%以下。尽管沙特总体失业率不算很高,但从人口结构看,20岁至24岁青年人口的失业率接近40%,其中女性失业率几乎是男性的两倍。参见“Labor Force Survey,” General Authority for Statistics, March 1, 2019, https://www.stats.gov.sa/en/34, 上网时间:2020年11月15日。作为互联网使用主体的年轻人群更是就业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海湾部分国家青年失业率已经达到了30%,青年人的经济困难将直接影响互联网市场的商业前景。此外,新冠疫情的持续恶化和海湾本地科技公司的裁员导致海合会国家的科技人才流失严重,这对知识人才密集型的互联网创业生态也是一个打击。②“How the Gulf's Expat Exodus is Draining Tech,” WIRED Middle East, January 1, 2021,https://wired.me/technology/gulf-expat-exodus-tech/,上网时间:2021年1月14日。
(二)新冠疫情蔓延背景下的国家数据监管升级
新冠疫情全球大爆发以来,全球各国对互联网工具的需求出现了井喷。在海合会国家,远程电子工作和非接触式电子商务成为新的主流生活方式。经济生活的全方位数字化也使得各国政府意识到了数据和互联网主权的现实意义。疫情期间,尽管阿联酋、阿曼等国临时取消了互联网语音软件的使用限制,不过社交通讯和电子商务软件的高频使用和由此产生的海量数据的存储、加工和使用问题已经逐渐成为海湾各国监管者关注的焦点。阿联酋于2020年颁布的第15号联邦法律(最新的消费者保护法)将电子商务的提供商正式纳入联邦法律监管范围,对大数据价格杀熟、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和广告营销等都作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大幅提升了违反法律的处罚。在数据和隐私安全方面,迪拜政府旗下的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ubai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DIFC)的《数据保护法》于2020年7月1日生效,在借鉴欧洲立法创新的基础上,旨在加强对金融数据的管控,对跨境金融支付类的业务提出了高标准的要求。新冠疫情期间产生的海量公共健康数据已经成为各国疫情治理的关键工具和政策抓手,阿联酋政府已经要求与本地居民健康相关的数据必须存放在阿联酋境内。同年6月,沙特通信与信息技术委员会颁布的《个人数据隐私管理规定》要求通信IT服务提供商应当在沙特境内处理个人数据。由此可见,对互联网的依赖实际上也进一步加深了政府监管部门对数据安全和隐私的忧虑。如上文分析,中国互联网海外平台化运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也意味着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在运营中天然地“掌握”了海量的用户数据,因此能够“有效地”掌握用户的隐私并进行针对性的商业活动。①Daniel Kiliman and Abigail Grace, “Power Play: Address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Strategy,”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September20, 2018,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power-play, 上网时间:2020年12月20日。而东道国监管水平的升级事实上已经改变了初期互联网产品“野蛮生长”商业模式的大环境。
(三)APP带来的社会政治影响力不容忽视
网络规模效应客观上赋予了互联网产品与日俱增的社会影响能力。以平台化为发展方向的互联网产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运行的“基础设施”。社交媒体应用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②Miriyam Aouragh and Paula Chakravartty, “Infrastructure of Empire: Towards a Geopolitical of Media and Information Stud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Vol.38, No.4, 2016, pp. 559-575.以脸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点燃了个别阿拉伯国家聚集的社会矛盾情绪,触发了部分国家的社会动荡。“阿拉伯之春”之后,海合会国家普遍加强了对在线社交媒体的管控。③尤其是出于对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政治安全、社会舆论等带来的不良影响的考虑,海合会国家普遍对互联网内容实施较为严格的管制,这也是西方媒体和人权组织长期攻击海合会国家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中国企业开发的社交娱乐类互联网产品在海合会国家的用户中(尤其是年轻用户)有很高的人气。如何有效地防止用户沉迷,不当使用产品功能为其他目的服务,相关企业还没有认真的思考和设计;另一方面,从企业经营内部合规来看,不同于传统和的大型工程承包合作项目,在海合会国家经营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多为小微型私营企业,由于互联网行业特性的原因,这些企业呈现出“野蛮生长”和无序竞争的特点。在风险投资基金的支撑下,公司经营目标追求“短平快”,没有形成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因此,在业务运营的合法合规、商品服务质量、内容审核、用户数据资料安全和社会舆论风气引导等方面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资源技术投入。这些业务发展中的“副作用”日积月累到一定程度有可能会诱发更大范围的社会影响,触发当地舆论和政府监管部门的责难和惩罚,极易造成企业自身和中国的国际形象的损失。
(四)经济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打压迹象显现
从全球看,针对互联网企业经营内容和行为展开制裁和打压已经成为部分主权国家实施政治打压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有效借口和手段。印度政府从2019年开始就有针对性地对中国的互联网产品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主权为由进行一刀切的封禁和极限打压。①2020年6月29日,印度政府以“有损印度主权和完整,国防,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为由宣布59个中国APP为非法。美国政府将华为及其他70家企业列入技术出口实体限制清单。2020年7月开始,美国特朗普政府开始威胁封杀来自中国的互联网产品海外版抖音。②特朗普政府要求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完整出售TikTok,否则将暂停其在美国的业务。2020年9月,甲骨文公司宣布将成为TikTok海外版的技术供应商。2021年6月,拜登政府宣布撤销对TikTok的禁令,随后又要求美国商务部设计一套新的针对中国等“竞争对手”的软件的应对方案。中国互联网企业可能会在海湾地区遇到打着以民族主义、国家安全等旗号的抹黑和打压。此外,应当注意到从政商界到民间,民族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的潮流仍在涌动,阿联酋电子商务平台Noon的创始人穆罕默德·阿拉巴尔(Mohamed Alabbar)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商人”。2016年他携手沙特公共投资基金(Public Investment Fund, PIF)斥资10亿美金创建了电子商务平台Noon。阿拉巴尔在接受《连线》杂志采访时表示,“我们应该向4亿阿拉伯人提供数字经济服务,这是我们的职责。否则,中东要么落伍于世界,要么将被外国势力占领。这些外国势力以数字银行、数字公司、数字媒体等形式出现,不需要一兵一卒就能将我们的生活占领”③“Inside Mohamed Alabbar's Heavy Weight Slugfest Against Amazon,” WIRED Middle East, December 19, 2020, https://wired.me/business/big-tech/mohamed-alabbar-dubai-noon/, 上网时间:2021年1月5日。。可见,外国互联网公司的入侵已经被部分阿拉伯的商业精英认为是一种新的经济文化“入侵”,无论是出于国家政治安全,还是来自商界的呼吁,要求主权国家作为监管者回归的呼声越来越强烈。④Winseck Dwayne, “The Geo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Journal of Information Policy, Vol. 7, 2017, pp. 228-267.
四、以可持续发展策略应对不确定性和政治风险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面前,跨境互联网企业在确保业务创新和高速发展的同时,应当在公司战略思维上转向更为长远和可持续的发展目标,跳出创业早期“短平快”和无序竞争的粗放模式,转向在产品质量,合法合规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加大投入,与本地用户、社区和政府形成良性互动。
(一)弱化地缘政治因素
尽管从总体上看,目前中国高科技互联网企业在海合会国家的业务没有直接受到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互联网科技企业在海湾地区的总体形象是受欢迎的外国投资者,是海合会国家政府战略的紧密合作者。但考虑到海合会国家与美国在政治经济上的紧密关系,中国互联网企业需要提高警惕,为可能随时出现的因地缘政治和大国关系而产生的营商风险做好准备。①在美国将中国华为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后,华为公关部门副总裁乔凯利在接受《阿拉伯商业周刊》采访时表示,“我知道,美国政府一直在试图说服中东国家,阻止他们使用华为设备,这和美国对欧洲的做法如出一辙”。近年来,“中国科技巨头(China Tech Giant)”这样具有警惕性的词语已经开始频繁见诸于海湾国家主流媒体②参见主流海湾媒体报道,例如Gulf News, Arabian Business, Al Jazeera等。“科技巨头”首先被西方媒体用来指代互联网企业取代传统行业的巨头,其中,“FAAMG”最早由投资公司高盛启用,用于指代“Big Tech Company”,它包括Facebook, Apple, Amazon, Microsoft和Google这五家公司。它们被认为统治了除中国之外的世界信息互联网产业。。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网络安全”“数字主权”这样的概念将会变得越来越有市场,来自美国的政治威胁也可能被海合会国家政府效仿。中国互联网企业应当在日常商业活动中弱化跨境主体的敏感性,积极参与本地行业规范的制定和治理。中小型企业尤其需要考虑抱团出海,充分借助公共外交资源和本地公关关系,对东道国监管部门开展合法的正面宣传和游说。
(二)以企业社会责任赋能可持续竞争力
互联网企业作为技术创新赋能商业模式变革的新物种,拥有成千上万的普通个人用户,手握关乎用户隐私的海量数据,具有深刻改变社会局势的潜在能力。互联网公司应当深刻认识到技术带来的复杂社会影响以及诱发的不良社会后果,承担与自身能力和影响力相匹配的责任,坚持“科技向善”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按照透明、公平和公开的原则向本地用户和东道国社会公众做好日常解释和知识普及工作。把更多的财力和精力投入到构建用户信任和塑造良好的影响力当中去,尽可能消除潜在的误会和敌意。除了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之外,把经营活动和当地社区文化发展结合起来是在海外经营的跨国企业普遍采取的战略。互联网企业应考虑积极履行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可以结合东道国本地的国情社情,对标“最佳实践”,投入更多的精力开展实施有针对性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在用户、社区和监管共同形成的多利益攸关方格局中构建信任和正向能量。
(三)合法合规经营加强对监管动向的重视和研判
全球数字经济的兴起客观上加速了各国政府对管理监督互联网的进程。2018年欧洲正式颁布《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在“欧洲标准”的影响下,海湾地区的监管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严格。2019年以来,沙特、阿联酋和巴林等国出台的一系列网络领域的立法都将目标瞄准数据驱动的互联网跨境企业。随着各国对数据价值的认识的加深,数据本地化作为战略理念日益受到国家重视。①黄道丽、胡文华:《全球数据本地化与跨境流动立法规制的基本格局》,载《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9年第9期,第53页。个人隐私、数据安全和国家主权等已经成为今后互联网行业监管合规的基础价值观念。跨境互联网企业在公司合规体系设计和日常业务经营中必须重新建立新的价值体系已适应来自政府的监管压力。
自2019年以来,欧洲多国开始向跨境互联网企业征收数字税②全球范围内,法国和英国率先开征数字税。2019年7月11日,法国参议院表决通过“数字税”征收法案。2020年3月11日,英国政府也宣布对科技巨头征收数字服务税。此后,意大利、土耳其、捷克等国家在制定“数字税”上也动作频频。参见范春强:《全球数字税立法时代的来临?》,半月谈,2020年5月13日, http://www.banyuetan.org/gj/detail/20200513/100020003313-6201589334864736368746_1.html,上网时间:2020月11月8日。,尽管目前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海合会国家会在短时间内对跨国互联网企业征收“数字税”,不过近年来,阿联酋、沙特和巴林等国已先后开始征收增值税,阿曼宣布于2021年春季开征增值税,卡塔尔和科威特预计也将在不久的将来跟进实施③在新冠疫情期间,沙特更是将增值税从5%临时提升至15%以缓解国内财政紧张的问题。。互联网跨境经营和离岸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东道国的税基和财政资源。在经济多元化和石油收入下降的变革压力下,海合会国家政府显然有更大的动力拓展新的税源,监管政策逐一落地意味着来自东道国政府的关注和处罚将会在未来变得更为频繁。
五、结语
互联网技术的跨境传播和商业应用带来的不仅是生活方式的变革,更为重要的是其分散和去中心化的特征削弱了传统主权国家的权威,给后者的监管方式和治理理念带来了新的挑战。④Saskia Sassen, “Digital Networks and the State: Some Governance Questions,” Theory,Culture & Society, Vol. 17, No. 4, 2000, pp. 19-33.一方面,海合会国家政府在数字战略发展方面的雄心壮志及其年轻用户对数字服务的迫切需求为中国互联网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创新空间,互联网出海的初步成功预示着中国的数字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将对全球数字经济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背后的社会政治影响比如个人隐私、信息安全和国家主权等问题也将逐渐成为跨境监管和全球网络治理的焦点,互联网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以及对东道国国家政治主权的潜在威胁也将会频繁成为东道国制裁和打击境外互联网企业的理由。如何在东道国用户和政府中构建信任和影响力,与东道国政府和用户形成良性互动是接下来中国出海互联网企业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重要问题。
从国际治理层面看,互联网驱动的数字全球化已经对传统的政治经济格局造成了剧烈扰动。大国政治、全球领导力和国际话语权已经成为影响科技发展和跨境贸易的重要因素。在数字时代,网络对国家主权的挑战和侵蚀是全球化时代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①鲁传颖:《主权概念的演进及其在网络时代面临的挑战》,载《国际关系研究》2014年第1期,第77-81页。以1995年互联网开始全球商业化为标志,过去二十多年来以美国为核心的互联网治理模式已经遇到了全球多边机构和新兴国家的质疑,中国在全球多边主义进程和互联网多利益攸关方治理进程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作用,是未来全球数字秩序的重要倡导方和建设主体。②洪宇:《全球互联网变局:危机、转机和未来趋势》,载《学术前沿》2020年第15期,第45页。中国互联网企业作为具体情境下的行动者既要承担外贸产业升级转型的角色,同时也是新一轮全球发展和治理中的主要建设者和活动者。一方面,作为市场活动主体的中国互联网企业要进一步做好合规经营平等互利,持续须防范来自东道国的数字贸易壁垒和陷阱;另一方面,顶层设计和主管部门也须进一步加强全球数字治理的政策研究储备和投入,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为全球互联网和数字发展提供中国经验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