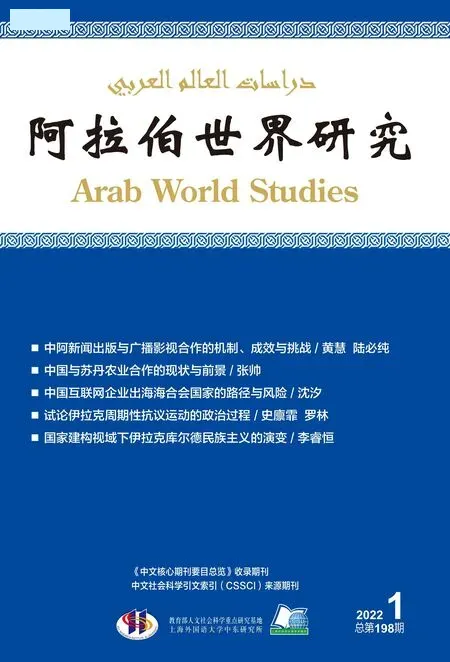国家建构视域下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演变*
2022-04-22李睿恒
李睿恒
1991年海湾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带来的局势变动,赋予了伊拉克库尔德人不断上升的自治地位和权利,其民族意识也随之强化,一度演变成2017年9月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独立公投。从公投92.73%的赞成结果来看①“92.73% ‘Yes’ for Independence: Preliminary Official Results,” Rudaw, September 27,2017, http://www.rudaw.net/english/kurdistan/270920174, 上网时间:2021年1月21日。,具有独立倾向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已然成为当前伊拉克库尔德社会内部一股影响力巨大的政治思潮。库区前主席马苏德·巴尔扎尼(Mas‘ūd al-Barzānī)甚至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我们并非伊拉克的一部分”②“Barzani on the Kurdish Referendum: ‘We Refuse to Be Subordinates’,” The Guardian,September 27,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sep/22/masoud-barzani-on-the-kurdish-referendum-iraq-we-refuse-to-be-subordinates, 上网时间:2021年1月21日。。诚然,伊拉克现代国家自1921年成立以来,一直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对其中央政府权威的挑战。长期以来,国际学界对库尔德人历史遭遇的同情,1991年海湾战争后西方遏制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的政治议程设置,以及伊拉克库尔德人合法自治后的国际形象建构,使得学界和媒体在表述该问题时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了一种库尔德政治精英长期致力于对外塑造的视角,即库尔德民族主义被伊拉克库尔德社会内部所集体共享,并贯穿该问题发展的始终。
按照迈克尔·赫克托的论述,当多民族国家政府建构国家民族主义的尝试失败时,国家边界之内则可能产生拒绝被同化的“外围民族主义”。③Michael Hechter, Containing Nation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pp. 70-83.换言之,一国之内少数族群民族主义化的政治倾向并非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其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建构的进程密切相关。本文据此认为,无论是出于理念认同,还是对政治现实的妥协,并非所有库尔德人乃至民族运动都将独立建国作为其诉诸的最终目标。因此,学界对库尔德问题“无国民族说”④学界对如何准确界定库尔德问题一直未达成共识,总体来看有三类界定方式:第一,“无国民族说”,即库尔德问题是指库尔德人作为一个人数众多的可识别民族未能独立建国的问题;第二,“内政问题说”,由于一战后库尔德人被划分到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四个国家,库尔德问题从法理上看首先是相关四国共有的一个内政问题,它指库尔德人的自治和独立诉求对四国政治稳定和领土完整构成的威胁与挑战;第三,“地区问题说”,即在第二类界定方式的基础上,学界对库尔德问题的含义做出进一步扩展,将其视作挑战中东民族国家秩序的一个地区性问题,库尔德人的独立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中东地区的动荡,其外溢效应也激化着其他民族问题的爆发。上述三种界定方式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将库尔德人的独立诉求作为问题的核心。相关论述参见Mohammed M. A. Ahmed and Michael M. Gunter, eds., 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the 2003 Iraqi War, Costa Mesa: Mazda Publishers, 2005, p. 12; 李秉忠:《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3-14页。的界定,实际上内化了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的视角,不完全具备现实客观性;“内政问题说”更为贴近现实,但又过于突出库尔德问题的冲突性特点。而在特定时期内,库尔德人不必然会对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形成挑战。相反,国家结构会对库尔德人的政治理念带来重大改变。“地区问题说”的界定方式,更多是“内政问题说”的延展,不具备清晰的划分边界。在“内政问题说”的基础上,本文将库尔德问题定义为在相关国家的现代历史进程中,因国家和中央政府未能处理好现代国家建构与国内库尔德人政治、社会与文化诉求的关系而产生的政治认同与社会秩序问题。基于此,库尔德人的诉求也不应仅以最具破坏性的独立建国诉求所单独代言,而需分阶段和主体来辨析其性质与特点。
此外,一战后库尔德人被划分到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四国的现实决定了在共享一种泛化的库尔德民族情结的同时,四国库尔德人分别受到各自所在国特殊国情的影响,衍生出四种不同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发展路径。因此,只有引入伊拉克国家建构进程这一宏观结构性因素,才能更加客观准确地认识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的发展限度。基于此,本文运用西方学界的英文文献和中东学界的阿拉伯文文献,并部分依托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公开的《伊拉克复兴社会党档案》(Hiz·bal-Ba‘thal-‘Arabīal-Ishtirākīin Iraq Archives)①《伊拉克复兴社会党档案》是伊拉克复兴社会党在1968年至2003年间统治伊拉克的档案。该档案使用阿拉伯语书写,含1,100万份文件,包括复兴党统治期间的通信往来、内部报告、备忘录、复兴党成员和人事档案、司法和调查档案,以及与伊拉克政治状况及其治理相关的行政档案等。其中,《伊拉克北部数据集》于1991年伊拉克起义期间被库尔德武装所截获,其余档案是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被美军所截获。目前,这套档案由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2010年起对外界开放,允许研究者赴档案馆在馆阅读和抄录。中的《伊拉克北部数据集》(NorthIraqDataset)②本文研究所依托的《伊拉克北部数据集》集中记录了1968年至1991年间复兴党在伊拉克北部的执政情况,内容涉及伊拉克北部政治、安全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档案体量多达400万至500万份文件。关于《伊拉克北部数据集》的更多细节,参见Joseph Sassoon and Michael Brill,“The North Iraq Dataset (NIDS) Files: Northern Iraq under Ba‘thist Rule, 1968-91,”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Iraq & the Arab World, Vol. 14, Nos. 1 & 2, 2020, pp. 105-126。,尝试从国家建构的角度对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演变进行梳理分析。
一、帝国遗产: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起源
在探讨民族的缘起及其与国家的关系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有关民族主义的讨论。现代主义派学者认为,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出现是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兴起的结果,民族因此是晚近由民族主义观念所建构的产物,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③[英]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页。原生主义派学者则认为,民族主义固然是近现代的政治现象,但民族却早就以“族裔”(ethnie)的形式长期存在于历史中。①[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调和地看,有伊拉克历史研究者认为,两大学派实际上分别强调了民族生成的两张面孔,即“自生性”(natural)和“人造性”(artificial)两个过程。在“自生性”过程中,共同的历史文化要素和逐渐兴起的资本主义商业系统,使民族得以自下而上地自发生成;在“人造性”过程中,与前述“自生性”民族相匹配的政治系统亟待被组织起来,自上而下强制推动该民族的形成,以实现资本市场的扩张。②Faleh A. Jabar and Renad Mansour, eds., The Kurds in a Changing Middle East: History,Politics and Representation, London: I.B. Tauris, 2019, pp. 19-21.欧洲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商业系统衔接了两个过程,但同时期的中东地区却并未形成类似的资本主义贸易体系,其民族和民族国家的生成路径更多呈现出“人造性”特点。作为中东第四大民族的库尔德人自然也不外乎于此。
按照安东尼·史密斯的定义,库尔德人符合一个“族裔”的基本特点。他们长久居住于库尔德斯坦的土地上,因与外隔绝的山区地理特点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和语言体系,17世纪至19世纪库尔德公国的自治经验进一步强化了库尔德人的这些既有属性。16世纪末,库尔德王子夏拉夫汗(Sharafkhān)就在其著作《夏拉夫书》(Sharafnāma)中强调库尔德人与土耳其人的不同,描绘了后者对前者的压迫。17世纪中叶,库尔德诗人艾哈迈迪·哈尼(Ah·madi Khānī)开始以库尔德语进行创作,在其史诗中号召库尔德人团结起来,反对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的统治。③MahirA.Aziz,TheKurdsofIraq:NationalismandIdentityinIraqiKurdistan,London:I.B.Tauris, 2015, p. 55.基于这些著述,有库尔德学者认为,1514年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帝国间爆发的查尔迪兰战役对库尔德斯坦造成的破坏,以及两大帝国1639年签订的《席林堡条约》对库尔德斯坦进行的瓜分,事实上在17世纪就已催生出封建形态的库尔德民族主义。④Amir Hassanpour, 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in Kurdistan 1918-1985, San Francisco:Mellen Research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55-56.尽管如此,奥斯曼帝国通过减免库尔德公国赋税、给予其内部自治权及强调共同的穆斯林宗教身份,使库尔德人承认帝国中央政府的权威,双方由此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因此,以民族意识或民族思想萌芽而非民族主义本身来定义该时期部分库尔德精英的思想,更具合理性。
19世纪后,为应对自身同西方国家之间不断加剧的力量对比失衡,奥斯曼帝国开始推行“坦齐马特”改革,随后形成了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一方面,帝国政府的集权行为极大地折损了库尔德公国原本享有的内部自治权,现代化改革也削弱着帝国统治的宗教合法性根基,而这些公国本质上只是建立在部落和苏非教团基础上松散的政治联盟,后于19世纪后期逐渐瓦解,裂变为规模不等的库尔德部落叛乱。这反过来强化了奥斯曼帝国镇压和直接统治库尔德人的力度,库尔德人的屈辱感和民族意识在此过程中也有所提升。①[伊拉克]萨阿德·巴希尔·伊斯坎达尔:《库尔德斯坦酋长国制度的建立与衰亡:从10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阿拉伯文),巴格达:公共文化事务出版社2005年版,第378-398页。另一方面,部分库尔德知识分子等精英群体在接受西方教育时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开始创办相关报刊和文化组织,宣传库尔德民族自治或独立的权利。由此可见,尽管库尔德人可能早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个潜在的“民族”,但无论是17世纪处于萌芽状态的民族意识,或是19世纪末期开始出现的民族主义思想,库尔德人的民族身份更多是对外界形势变化的反应,且局限于少数精英内部。这既是库尔德民族主义演变的历史基础,同时也是其历史发展所面临的局限。
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的失败为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进一步扩宽了空间。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成为战胜国处理奥斯曼帝国治下各民族问题的基础。1919年3月22日,库尔德领导人谢里夫帕夏将军带领代表团出席和会,提交了库尔德斯坦独立建国的议案,得到和会的原则性同意。1920年《色佛尔条约》的第62条、第63条和第64条规定,在当地居民愿意的前提下,库尔德人有权在“幼发拉底河东岸、土耳其西北部以及同叙利亚和伊拉克接壤的土耳其边境以北”地区建立自己的国家;此外,只要当地居民愿意,战胜国不反对将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并入其中。②[伊拉克]萨拉赫·胡尔桑:《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政治运动:对伊拉克库尔德运动和政党的文献解读(1946~2001)》(阿拉伯文),贝鲁特:巴拉格出版发行公司2001年版,第17-18页。巴黎和会和《色佛尔条约》的规定自此成为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宣称其独立建国权利的国际法理来源。
但是,该方案遭到土耳其凯末尔政府的强烈反对。1923年,土耳其将在希腊土耳其战争(1919~1922年)中获得的战场优势转化为谈判资本,以《洛桑条约》代替《色佛尔条约》,删去了库尔德人独立建国的内容。当然,这并非是土耳其单方面所决定的。从英国的角度来看,它之所以愿意在前述文件中承认库尔德人的民族权利,一方面是为了广泛回应巴黎和会“民族自决”的原则,另一方面则是迫于英法秘密制定的《赛克斯—皮科协定》被苏联公之于众后的国际压力,英国希望借此来淡化事件的负面影响。③同上,第18页。事实上,当时的英国政府并没有就库尔德人建国问题达成清晰统一的政策:支持派官员更多是基于对库尔德人的同情,反对建国派则认为“限制性的种族和地理困难”并不能让库尔德人建立有效的国家,且摩苏尔地区丰富的农场区和石油资源,对新生的伊拉克国家意义重大。④Mahir A. Aziz, The Kurds of Iraq: 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in Iraqi Kurdistan, pp. 60-62.英国在政策上的暧昧很大程度上造成《色佛尔条约》中对库尔德人的承诺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执行。
随着反对建国派官员逐渐占据上风,英国决定将摩苏尔省纳入现代伊拉克的版图,并于1925年宣布反对成立“任何自治或独立的库尔德国家”。①Mahir A. Aziz, The Kurds of Iraq: 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in Iraqi Kurdistan, p. 60.同年,英国借助土耳其政府镇压谢赫赛义德叛乱事件,逼迫土耳其放弃对摩苏尔省的领土诉求。12月,国联裁决将摩苏尔省划入伊拉克。1926年6月,英国、伊拉克和土耳其三方签署《安卡拉条约》,同意摩苏尔省成为现代伊拉克的一部分,接受英国的国际托管。至此,库尔德人建国的可能性正式覆灭,沦为大国政治的牺牲品。从库尔德人自身来看,两个层面的因素也导致了这一结果。
第一,库尔德人长期居住的山区环境与外隔绝,这令他们不敏感于周边局势的演变,较晚才接触到民族主义思想,未能深刻意识到国际体系出现的本质性变化并及时采取相关行动。此外,一战期间奥斯曼帝国为应对俄国扶植亚美尼亚人的政策,强调与库尔德人之间的伊斯兰纽带,以及战后土耳其政府为动员库尔德人共同对抗希腊,没有迅速废除哈里发制度,这也进一步阻缓了库尔德人对战后民族建国潮流的把握。阿卜杜·拉赫曼·卡塞姆鲁援引当时一位英国官员的话称:“当我们告诉库尔德人建国时,他们没有为此去努力尝试。而当他们1922年突然要求14点(原则)时,一切都太晚了。”②[伊朗]阿卜杜·拉赫曼·卡塞姆鲁:《库尔德斯坦与库尔德人:一项政治与经济研究》(阿拉伯文),贝鲁特:黎巴嫩出版公司1970年版,第92页。
第二,内部多样分化的社会政治局面,使库尔德人难以形成合力,共同追求建国目标。诚然,库尔德人独特的历史文化体系足以使其区别于“他者”,但却无法塑造均质统一的“自我”。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库尔德斯坦当时还为部落社会结构所主导,部落是有效进行政治动员与资源整合的社会组织形态,政治精英的行动出发点是维护狭隘的部落利益,而不是服务于一个宽泛的“库尔德民族”。这使得库尔德民族主义者无力动员社会落实其政治理念,外部力量则很容易提供利益收买、介入和分化部落间短暂形成的联盟,无法拱卫既有的政治优势。在文化方面,不同地区的方言、尚未规范的书面语、落后的出版业和有限的识字率,都阻碍着民族主义思想在社会底层的传播,③Mahir A. Aziz, The Kurds of Iraq: 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in Iraqi Kurdistan, pp. 49-53.更遑论社会自下而上产生诉诸于建国的政治运动。
虽然从历史经验上看,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比库尔德人组织化程度更高,有着长期且丰富的帝国统治实践,但中东民族国家体系的建立,是奥斯曼帝国覆灭和西方殖民政策的产物,本质上是一个外输型的政治体系,其内部在不同程度上都有着多元分化的社会文化子系统,缺少现代工业化等推动民族形成的要素,因此具有内在的脆弱性。不同的是,库尔德人并不像阿拉伯人或土耳其人那样,在战后拥有正式的国家系统来整合这些分散的要素,从而逆向塑造自身的民族。因此,如果按巴黎和会与《色佛尔条约》的规定赋予库尔德人建国的权利,上述库尔德内部因素的消极程度或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弱,而库尔德人的历史会是另一幅景象。从当时库尔德人自身的条件预计,如果库尔德人的建国方案得以实践,意味着库尔德社会内部各派力量对建国主导权的争夺和随之引发的局势动乱,①Mahir A. Aziz, The Kurds of Iraq: 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in Iraqi Kurdistan, p. 61.或意味着需要大国意志来推动该进程,两者都会导致英国在中东的成本负担过重,不符合其进行间接殖民统治的初衷。从这个意义上看,英国更愿意依靠内部整合度更高的阿拉伯人,而非支持一个库尔德人国家。
自此,库尔德人不仅失去进行自我整合的建国机会,他们还开始受到各自所在国国情的结构性影响,衍生出四种不同的民族运动发展路径。伊拉克的现代国家框架则决定了伊拉克境内库尔德民族主义发展的特殊轨迹。
二、现代国家: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框架
要理解伊拉克国家框架对库尔德民族主义发展的独特影响,就须对伊拉克现代国家生成方式进行考察。现代伊拉克成立于1921年,是一战后英法殖民者人为构建的产物,由前奥斯曼帝国行省巴士拉省、巴格达省和摩苏尔省组成。三省在历史上行政相互独立,人口构成各异,分别由什叶派阿拉伯人、逊尼派阿拉伯人和逊尼派库尔德人主导,各行省内部还存在多元的文化与社会子系统。将异质的三省合并为一个国家意味着伊拉克通往现代国家的途径很难和平融入,中央政府从而诉诸于强制的军事手段或软性的政治妥协。②Faleh A. Jabar and Renad Mansour, eds., The Kurds in a Changing Middle East: History,Politics and Representation, p. 22.
伊拉克现代国家的这种先天性的内在缺陷,为其境内的库尔德人带来了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除借武力手段镇压部落叛乱外,英国为在摩苏尔省归属问题上制衡土耳其,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扶植亲己的伊拉克库尔德部落,打压土耳其支持的库尔德部落。与此同时,初抵伊拉克进行统治的费萨尔国王缺乏本土执政基础,也积极拉拢库尔德部落,以图推动将摩苏尔省并入伊拉克,增加逊尼派人口,制衡人口占主体的什叶派力量。③Aram Rafaat, The Kurds in Post Invasion Iraq: The Myth of Rebuilding the Iraqi State,Saarbrücken: Lap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2012, p. 16.这让伊拉克库尔德人一开始就获得较为宽松的政治与文化环境。1926年摩苏尔省正式并入伊拉克后,伊拉克政府还根据国联要求颁布《地方语言法》,允许苏莱曼尼亚和埃尔比勒部分地区使用库尔德语开展小学教育和出版工作,同时任命库尔德人出任部分部长职位。这种对库尔德人文化身份乃至政治权利的认可,也被随后的历届伊拉克政府所继承(至少在理论或法律层面),伊拉克库尔德人由此走上了与其他三国库尔德人截然不同的演变轨迹。
但是,伊拉克库尔德人享有的这些优势并不足以克服其本身既有的历史缺陷。早在1919年5月,伊拉克苏莱曼尼亚地区的库尔德部落与苏非领袖谢赫马哈茂德·巴尔金吉(Shaykh Mah·mūd al-Barzinjī)就发动了一次反英起义,当时他打出“吉哈德”(Jihād)而非民族主义的旗号,他希望库尔德人摆脱英国的统治,但非摆脱他个人的统治。①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London: I.B. Tauris, 1996, p. 158.起义很快被英国军队镇压下去,谢赫马哈茂德随后接受英国的招安,被任命为苏莱曼尼亚总督。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在重构其民族叙事时,往往把谢赫马哈茂德叛乱定性为民族主义运动。②[伊朗]阿卜杜·拉赫曼·卡塞姆鲁:《库尔德斯坦与库尔德人:一项政治与经济研究》(阿拉伯文),第65-66页。但他妥协的政治行为表明,作为库尔德社会主导力量的部落精英,在当时并没有清晰的民族主义诉求,叛乱或起义更多受部落、宗教乃至个人利益的驱动。
事实上,伊拉克建国初期库尔德人的民族意识非常薄弱,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库尔德民族主义。以1921年8月是否同意费萨尔担任伊拉克国王的公投为例,除苏莱曼尼亚地区反对外,摩苏尔和埃尔比勒的库尔德人都表示支持。基尔库克一开始暂缓表态,最终于1923年也予以支持,但条件是基尔库克单独成为一个库尔德省,并拒绝与苏莱曼尼亚地区的库尔德人整合。③David McDowall, The Kurds: A Nation Denied, London: Minority Rights Publication,1992, p. 82.这充分表明,库尔德人并非不能接受异族统治。同时,库尔德人内部分化严重,部落与地域意识主导下的政治思维使其难以为一个抽象的“民族”概念而团结协作,基尔库克地区库尔德人的立场就是谢赫马哈茂德影响力有限的明证。诚然,在同一时期的库尔德城镇中,少数受教育群体和逐渐兴起的职业阶层,开始对民族主义产生兴趣,但其规模有限且缺乏组织性。
摩苏尔省问题解决后,谢赫马哈茂德意识到建国无望。1926年底,他再次发动起义,但最终失败,于1927年被捕和软禁。英国和费萨尔国王随后运用利益收买、分而治之和武力镇压的策略,基本维护住伊拉克库区的秩序稳定。1928年,伊拉克政府甚至评估认为,本国的库尔德问题已得到基本解决。④唐志超:《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版,第128页。但需要指出的是,伊拉克国家基于短期统治利益所赋予库尔德人的发展空间,也是其将库尔德社会整合进伊拉克国家认同的长远进程中面临的问题,部落等历史问题在被中央政府工具化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得以存续乃至固化。
1930年,伊拉克和英国签订新的《英伊条约》,英国结束对伊拉克的国际托管,伊拉克将于1932年获得独立。相应地,中央政府加紧对地方权力的控制,这引发了库尔德人的担忧,导致双边关系再度恶化。一方面,费萨尔国王试图树立中央权威,在库尔德偏远地区建立警察系统并征收赋税,对当地库尔德部落的既得利益构成威胁;另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风靡伊拉克政军两界。①Charles Tripp, A History of Iraq,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91-97.伊拉克库尔德人担心英国托管结束后,伊拉克会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合并,加剧其少数派地位,因此倾向于认为任何泛阿拉伯化的政策都“有必要产生一个分化的库尔德实体,无论是在这个阿拉伯上层建筑的框架内,还是框架外”。②Majid Khaddurri, Republican Iraq: A Study in Iraqi Politics Since the Revolution of 1958,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3.例如,马吉德·穆斯塔法、道斯·海达里等库尔德政治家和诸多库尔德部落领袖就曾主张,库尔德人应该选择同伊拉克中央政府合作,共同建构“伊拉克优先”的国家民族主义,但碍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与非阿拉伯民族分享权力时的排他性原则,他们认为有必要继续维持英国对伊拉克的托管,以保护库尔德人的少数派利益。③Denise Natali, The Kurds and the State: E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 Turkey and Iran,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32, 34-35.从这个意义上看,伊拉克国家方案对于伊拉克库尔德精英而言并非是最差或最不可接受的选项,这也表明,他们已经开始在伊拉克的国家框架中思考自身的地位问题。
1930年9月,谢赫马哈茂德逃离软禁,联合利益受损的部落再次诉诸武力,苏莱曼尼亚的工人、学生和商人也举行罢工、罢课和游行示威。起义遭到强力镇压,谢赫马哈茂德最终投降,接受软禁直至1956年去世。很多库尔德历史学家认为,1930年起义是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城市群体的加入扩大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外延与内涵。④[伊朗]阿卜杜·拉赫曼·卡塞姆鲁:《库尔德斯坦与库尔德人:一项政治与经济研究》(阿拉伯文),第95页。贾拉勒·塔拉巴尼(Jalāl al-Tālabānī)进一步认为,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基础已由乡村转向城市,领导层从宗教和部落首领向城市小资产阶级转移。⑤[伊拉克]贾拉勒·塔拉巴尼:《库尔德斯坦与库尔德民族运动》(阿拉伯文),贝鲁特:先锋出版社1971年版,第112-114页。诚然,知识分子与城市居民确已开始发挥作用,但却没有颠覆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所依托的社会基础,只是改变和丰富了它的发展图景。基于伊拉克库区当时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部落依旧是有效进行政治动员与资源整合的社会组织形态,因此该时期的库尔德反抗运动“表面上看是民族主义的,但本质上却是部落和宗教性质的”。⑥Edmund Ghareeb, The Kurdish Question in Iraq,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81, p. 31.
谢赫马哈茂德陨落后,来自库区巴尔赞地区的巴尔扎尼部落逐渐崛起,由谢赫艾哈迈德·巴尔扎尼(Shaykh Ah·mad al-Barzānī)和他的弟弟毛拉穆斯塔法·巴尔扎尼(Mulla Must·afa al-Barzānī,以下简称“毛拉穆斯塔法”)所领导。1932年,伊拉克政府和英国扶植沙尔瓦尼部落的谢赫拉希德打击巴尔扎尼部落,试图推动对巴尔赞地区的控制,引发巴尔扎尼部落的武装反抗。巴尔扎尼部落并没有逃脱与谢赫马哈茂德相同的下场,谢赫艾哈迈德和毛拉穆斯塔法都遭到软禁。直至二战期间,毛拉穆斯塔法借形势动荡出逃,于1943年6月和1945年8月两度起义。
与以往不同的是,1943年起义被认为是库尔德部落领导人第一次鲜明地打出民族主义口号的起义。①[美]埃德蒙·加里卜:《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阿拉伯文),贝鲁特:白昼出版社1973年版,第10页。这主要缘于毛拉穆斯塔法软禁期间与“伐木工人”(Darkār)和“希望”(Hīwā)等库尔德早期政治组织建立了联系。这些组织主要由城市军官、政府官员和教师组成,信奉共产主义,与伊拉克共产党联系密切,并参与了两次起义。起义失败后,1945年10月,毛拉穆斯塔法流亡至伊朗库区。受马哈巴德共和国(1946年1月至12月)及伊朗库尔德民主党的影响,毛拉穆斯塔法意识到起义的成功需要部落与受教育的城市政党结盟。②Gareth R. V. Stansfield, Iraqi Kurdist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Emergent Democracy,London: Routledge, 2003, p. 65.1946年8月16日,他 联 合 多 个 政 治 组 织 成 立 库 尔 德 斯 坦 民 主 党(al-H·izbal-Dīmqurāt·īal-Kurdistānī,以下简称“库民党”)。根据党纲,库民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政治意识形态,强调联合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共同推翻伊拉克的王朝统治,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③[埃及]哈米德·马哈茂德·尔撒:《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从英国占领到美国入侵(1914-2004)》(阿拉伯文),开罗:马德布里书局2005年版,第149页。
库民党的建立首次为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设立了政党化的框架,更重要的是,这也是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第一次明确提出按国别独立建党的原则,进一步表明伊拉克现代国家体系对本国库尔德人发挥的作用,即库尔德人只有首先满足自己所在国的政治现实需求,才有可能追求所谓的泛库尔德民族利益。有必要明确的是,库民党本质上只是占少数的城市左翼力量与农村部落力量的权宜联姻。④Edmund Ghareeb, The Kurdish Question in Iraq, p. 39.巴尔扎尼部落扮演着主导性角色,左翼力量提供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行动框架,二者缺乏互信,相互利用,毛拉穆斯塔法在其中发挥着关键性的纽带作用。两股力量间的合作与竞争,构成了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重要动力。
随着马哈巴德共和国覆灭后毛拉穆斯塔法流亡苏联,独自留在伊拉克国内的左翼力量难以产生实质性的政治与社会影响,且20世纪50年代库民党与伊拉克共产党联系紧密,在意识形态上更多强调阶级斗争和反帝反封建,淡化了民族主义思想的成分。在意识到大国无意变革中东国家体系后,库民党开始逐步将民族诉求从独立建国缩小为获得区域自治的权利。①Alex Danilovich, ed., Iraqi Kurdistan in Middle Eastern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2017, p.17.此时的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总体保持平静,直到1958年“七月革命”爆发,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变。
1958年“七月革命”推翻了哈希姆王朝,伊拉克政体转变为共和制。阿卜杜·凯里姆·卡塞姆(Abd al-Karīm Qāsim)政府为抗衡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选择联合库尔德人。同年7月26日颁布的《临时宪法》声明:“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是这个国家的伙伴。宪法保障他们在伊拉克共和国框架内的权利。”②Edmund Ghareeb, The Kurdish Question in Iraq, p. 38.这是伊拉克宪法首次承认库尔德人的民族权利,前提是维护伊拉克共和国的统一与完整。卡塞姆予以很多库尔德人高职,并邀请流亡中的毛拉穆斯塔法回国参政。相应地,毛拉穆斯塔法也配合卡塞姆政府打压政治对手,并借助宽松的政治环境,大力拓展自身势力。③Marianna Charountaki, The Kurds and US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since 1945, London: Routledge, 2010, p. 132.
然而,随着卡塞姆权力根基渐稳,毛拉穆斯塔法力量逐渐复苏与壮大,这引发了卡塞姆的担忧。1961年7月,毛拉穆斯塔法要求伊拉克中央政府给予库尔德人实质性的自治权,遭到拒绝。9月,双方关系破裂,毛拉穆斯塔法起事,“第一次伊拉克库尔德战争”(1961年9月至1970年3月)爆发。在此期间,伊拉克库尔德人经历了复兴党首次执政、阿里夫兄弟执政和复兴党二次执政等多次政局变动,双方一直处于持续的军事对抗,并断断续续就自治问题进行谈判。伊拉克政局的易变性和反复性,使库尔德人认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存在转圜的空间。
1968年7月伊拉克复兴党在二次执政后对库尔德人进行大赦,承认其民族文化权利,1970年双方达成《三月声明》(BayānĀdhār),库尔德人被承诺享有自治权,库尔德问题得到大幅缓解,双方持续近10年的战争就此结束。诚然,《三月声明》对库尔德人自治权利的认可促使库尔德人民族意识高涨,毛拉穆斯塔法领导的库民党广泛吸引库尔德民众,但与之平行发展的还包括库尔德社会对伊拉克的国家认同。
美国政治学学者丽萨·布蕾兹指出,国家的物质分配和奖励通常以两种方式影响公民的政治行为。首先,公民个人因享受到国家高福利的政策而减少对政府的不满;其次,这同时会使公民个人在心理和未来预期上积极评估现有体制,加大对其“投资”力度,以期获得更多物质回报。①Lisa Blaydes, State of Repression: Iraq under Saddam Hussei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 2018, p. 40.1972年伊拉克石油国有化后不断增长的公职就业机会、城市薪资待遇,与持续完善的居住、教育和医疗设施,吸引库区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移居。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复兴党政府的高福利政策已经对库尔德的社会经济结构产生影响,库尔德平民开始放弃自身对传统部落结构的依附,转而融入伊拉克国家推动的城市化进程当中。这进一步表明,他们或许已经向着萨达姆·侯赛因所号召的方向转变,不再把自己视作库尔德人,而是拥有库尔德民族身份的伊拉克人。②Denise Natali, The Kurds and the State: E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 p. 57.
无论复兴党政府在库区推动的城市化进程是否改变了库尔德人的身份内核,石油财富带来的高福利政策的确提升了库尔德人对复兴党政权的“投资”与认可程度。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的复兴党档案大量记录了库尔德人与复兴党政府之间的合作,同时也记录了库尔德平民在很多时候受到库尔德运动的困扰乃至伤害。例如,1977年的一份文件指出,库尔德村长(mukhtārūn)是伊拉克中央政府了解北部基层事务的一个重要来源。这些村长会定期向政府提交报告,内容主要涉及库尔德运动的武器装备、财政来源和通讯设备等状况。③North Iraq Dataset (NIDS) Doc. No. 02477-101-12, November 29, 1977.再如,1976年的一份复兴党纪要讨论了当库尔德运动武装进入库区村庄索要钱财、偷盗牲畜和威胁村民引发的当地对库尔德运动的不满情绪。④NIDS Doc. Nos. 00843-85-7 and 8, November 13, 1976.即便在两伊战争期间,依旧有许多报告显示,库尔德平民被库尔德“破坏分子”(即库尔德运动)的活动所困扰,认为他们破坏了自己安定的生活,并建议政府切实解决这些问题,这样才“不会打击库尔德人民自愿对抗伊朗的积极性”。⑤NIDS Doc. No. 11358-101-95, August 22, 1983.
库尔德公民对复兴党政权“投资”行为的上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被看作是他们对伊拉克国家身份认同的佐证,尚且存疑。但至少可以认为,在民间社会层面,库尔德人对自己民族身份的理解并未被完全政治化,上升至民族自决或是与伊拉克国家相对立的程度。⑥Lisa Blaydes, State of Repression: Iraq under Saddam Hussein, p. 141.1974年至1975年第二次库尔德战争期间,库尔德人内部的反战立场与库民党向外求援,以及外部支持停止导致库尔德人战场溃败,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薄弱的民间基础。而与战败后在库尔德运动中弥漫的绝望气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75年4月伊拉克军队收复多地城市受到了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⑦Ofra Bengio, The Kurds of Iraq: Building a State Within a State,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12, p. 147.当然,这或许是他们迫于现实的无奈之举。但可以确定的是,发展至此的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在库尔德人中并未达成贯穿精英和底层的共识。对政治运动而言,这意味着库尔德人的自治乃至最终的独立;但对部落势力和民间大众来说,这可能仅意味着富足有效的物质生活,和随历史情景浮动的民族意识与观念。
三、集体惩罚与自治实践: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历史转折
1975年库民党遭遇溃败后,伊拉克中央政府继续在库区推进土地改革和阿拉伯化政策,通过巩固前述庇护网络实现对库尔德社会底层的控制,由此在库区成立了亲中央政府的自治政府,维持着名义上的库尔德自治。由于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都流亡海外,伊拉克库区的反抗活动基本停止,只有部分库尔德游击队制造零星的小规模袭击。
学界研究指出,两伊战争(1980~1988年)的爆发为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开辟出新的空间,战争带来的破坏使得民族主义情感在伊拉克库尔德普通民众中得到普及。①John Bulloch and Harvey Morris, No Friends but the Mountains: The Tragic History of the Kurds, London: Viking, p. 6.《伊拉克北部数据集》的档案表明,贯通精英和底层的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身份认同,实际发端于两伊战争末期伊拉克中央政府发动的“安法尔行动”(Amaliyatal-Anfāl),在1991年伊拉克北部禁飞区设立后的库尔德人自治实践中得到确立和固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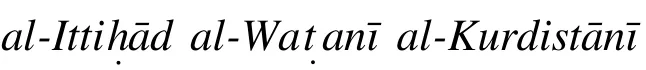
第一,对库尔德人采取细分性政策。根据复兴党档案,库民党和库爱盟被分别称为“背叛之子的队伍”(zumratsalīlīal-khiyānah)和“伊朗代理人之伍”(zumrat‘umalā'Īrān)②受意识形态和与库民党争夺领导权等多种因素影响,库爱盟曾于战争中期(1983年3月~1985年1月)与伊拉克复兴党政府有过合作,当时库爱盟被复兴党称为“塔拉巴尼之伍”(zumrat al-T.ālabānī),这同样是复兴党细分性政策的表现之一。受篇幅所限,笔者在此不展开详细论述。细节可参见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pp. 349-350; [伊拉克]萨拉赫·胡尔桑:《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政治运动:对伊拉克库尔德运动和政党的文献解读(1946~2001)》(阿拉伯文),第411-412页。,并被统一称为“破坏分子”(zumratal-takhrīb);两党不同于“我们的库尔德人民”(sha‘bunāal-kurdī),无法真正代表库区。根据1980年6月埃尔比勒省安全局的一份内部报告,复兴党还进一步区分了库区中的亲政府政党和反对派政党,要求北部地区的安全人员将这些信息牢记于心,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打击“破坏分子”,保护“库尔德人民”,并称未来要对他们的信息掌握情况进行考核。①NIDS Doc. Nos. 06265-13-8 to 13, June 1, 1980.
随着局势的演变,复兴党政府还在反对派人员内部做出政策细分。例如,在如何处理苏莱曼尼亚省叛逃伊朗人员的问题上,1983年6月伊拉克军事情报总局颁布的条例规定,对出逃者全部家属实施拘留或软禁,直至出逃者回国被捕。但苏莱曼尼亚省安全局发现,这不仅无法有效促使叛逃者回国认罪,反而会加剧其他家庭成员的叛逃现象。1985年3月,伊拉克军事情报总局对条例做出调整,其中包括:只对1979年后的叛逃者家属进行惩治;只拘留叛逃者家属中的重要人物,如父亲、兄弟或儿子等人;对叛逃者家属拘留期不得超过1年;拘留对象不包括女性、未成年和作为国家军事与安全人员的成年男性;被拘留人员如若有病情等特殊状况可停止拘留;家中有参战烈士或获得“勇气勋章”者,可酌情豁免,等等。②NIDS Doc. Nos. 00089-28-11 to 15, March 28, 1985.

第二,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在库区既有的庇护网络。1983年开始,复兴党政府在加剧阿拉伯化政策的同时,也放松了对经济的控制,通过推行私有化向私企和个人租赁和买卖土地,解决巨额战争开支。大量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库尔德部落首领重新获得土地并进入商业领域,成为土地主与城建合同商,跻身城市暴富阶层,苏尔齐(Surchī)和兹巴里(Zibārī)部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⑤Faleh A. Jabar and Hosham Dawod, eds., The Kurds: Nationalism and Politics, London:Saqi, p. 8.这在本质上延续了复兴党政府原有的政策,通过石油财富进一步打造库尔德民众的政治忠诚,限制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使其难以获得社会底层的支持。

三项措施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库尔德部落和民众与复兴党政府间的广泛合作。1983年7月至8月,萨达姆派出一个高级政府代表团赴苏莱曼尼亚省进行调研,在数十场与库尔德民众进行会谈的纪要中,虽然很多参会代表表达了对阿拉伯化政策的不满,但其论述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强调“破坏分子”不能代表库尔德人民,希望政府尽快打击“破坏分子”并与其和谈,以期有效解决问题,使被迁移的库尔德人民尽快回归故土。其余论述则主要集中于改善民生方面。①NIDS Doc. Nos. 11358-101, July, 1983; NIDS Doc. Nos. 11359-82, August, 1983.这都证明了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在伊拉克国内所获支持的局限性。即使到“安法尔行动”开展的早期,这种合作依旧显得较为普遍,库尔德民兵数量尚能维持在15万左右。②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p. 354.
必须指出,复兴党政府维系上述三项措施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其高成本的财政投入。例如,参加国防军团的库尔德人,每个士兵每月可以拿到85伊拉克第纳尔的报酬,军官每月则能拿到200伊拉克第纳尔。③Lisa Blaydes, State of Repression: Iraq under Saddam Hussein, p. 149。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第纳尔兑美元的汇率介于1个伊拉克第纳尔兑1.6~3.2美元不等。但受1986年国际油价暴跌的影响,伊拉克财政状况恶化,政府大幅缩减公共支出。④NIDS Doc. Nos. 16409-101, 1989.原有的庇护纽带因此变得松散或自然断裂,极大限制了复兴党政府在库区既有的行动和策略。
以情报验证为例,1987年4月2日,苏莱曼尼亚省安全局收到的一份可靠情报显示,在第79国防军团中有8人与库爱盟有秘密合作,复兴党总部要求核验该情报的真实性。同日,苏莱曼尼亚省安全局向第79国防军团所属的苏莱曼尼亚市安全分局下达核验命令。⑤NIDS Doc. No. 00459-101-53, April 4, 1987.但因迟迟未获取有效信息,⑥NIDS Doc. Nos. 00459-101-48 to 50, April, 1987.苏莱曼尼亚市分局并未及时对省局作出答复。4月28日,苏莱曼尼亚省安全局再次发电要求分局48小时内回复情报核验状况。⑦NIDS Doc. No. 00459-101-47, April 28, 1987.经过新一轮盘查后,苏莱曼尼亚市分局直到5月31日才正式回复省局称,在8名被核验人员中,2人确认与库爱盟有秘密合作,2人只能确定家庭住址,其余4人则无法查到相关信息。⑧NIDS Doc. No. 00459-101-44, May 31, 1987.
情报核验缓慢的效率和地方信息不足,直接印证了复兴党政府对库区统治的有限性和油价暴跌对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从深层次看,整体上这是伊拉克复兴党政权单一依托于石油经济确立其政治合法性的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以及由此造成的国家能力低下的现实困境。事实上,只有极少数复兴党官员可以流利地运用库尔德语,且很少有人愿意赴库区就职,复兴党只有采取薪资高、任期短和升迁快等激励性政策,才能促使其成功赴任。①Aaron Faust, The Ba‘thification of Iraq: Saddam Hussein's Totalitarianis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5, p. 162.1986年复兴党中央组织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显示,1980年至1986年间仅有1,694名复兴党干部在北部地区任职,其中503人都“牺牲在了破坏分子的手下”。②Ba’th Regional Command Collection (BRCC) Doc. No. 029-2-3-0209, July 16, 1986。需要指出的是,被该报告纳入统计的北部地区,除苏莱曼尼亚、埃尔比勒和杜胡克省外,还包括尼尼微省和泰米姆省(即基尔库克省)。统计赴任的1,694名党员中不包括尼尼微省和泰米姆省,两省该项数据缺失,但牺牲人数包括了5个省份的统计,因此实际总赴任人数应多于1,694人。根据《伊拉克北部数据集》档案,库区地方安全部门虽然搜集到大量与库尔德运动相关的库尔德语文件,但只有其中极少一部分被翻译为阿拉伯语。③相关事例参见NIDS Doc. Nos. 00459-101-34 to 36, May 26, 1987。这进一步增加了复兴党政府正确研判局势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合理化政策的难度。在此背景下,财政收缩直接导致库尔德合作者和官僚队伍的萎缩,削弱了复兴党对库区本已有限的掌控力。
正是两伊战争后期复兴党对库区形势认识不足和统治的局限性,使其无力继续维护既有的策略,尤其是细分对待库尔德人的措施。如前所述,由于20世纪80年代的私有化政策使许多部落重新获得土地,复兴党怀疑这些兴起的村落为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后勤补给,但却无力对这些偏远地区进行识别和区分。1987年至1988年,萨达姆下令发动“安法尔行动”,对库尔德人施加无差别的集体性惩罚,连很多与复兴党政府合作的库尔德顾问也未能幸免。④Joost Hilterman, A Poisonous Affair: America, Iraq and the Gassing of Halabj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95.3,000~5,000座库尔德村庄连同农田遭到化武袭击,150万库尔德平民流离失所或被强制迁入城市,受政府的集中控制与管理。⑤Kerim Yildiz, The Kurds in Iraq: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Pluto Press,2004, p. 25.“安法尔行动”给库尔德人的经济造成致命性打击,伊拉克库区“变成一块破碎的土地,社会发展快速地失去经济基础,政党力量弱化,士气低落,库尔德人疲惫涣散”⑥Gareth R. V. Stansfield, Iraqi Kurdist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Emergent Democracy,p. 47.。多份复兴党安全部门情报显示,库尔德两党不堪经济重负,劝说出逃的难民同胞接受政治大赦,回归伊拉克。⑦NIDS Doc. No. 38909-97, 1988-1990; NIDS Doc. No. 38909-97-63, December 16,1988.
诚然,伊拉克库尔德运动因“安法尔行动”遭受了不亚于1975年战败的打击,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伊拉克国家认同、爱国主义或是复兴党政治理念的胜利。相反,“安法尔行动”无差别的集体惩罚思路,让库尔德社会同样对伊拉克国家失去信念,库尔德运动和伊拉克国家实际上在库区面临“双输”的局面。
例如,20世纪80年代库民党入党登记表的变化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状况。1982年至1985年间登记表的表头都写有“我们奋发完成我们伊拉克祖国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建设,依照光荣的7月17日至30日革命①此处的“七月革命”并非指1958年推翻伊拉克哈希姆王朝的“七月革命”,而是指1968年7月17日复兴党二次执政时发动的政变。加强伊拉克国家统一,发展库尔德斯坦的自治”。②NIDS. Nos. 16601-59, 1982-1985.一方面,这反映了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对伊拉克国家前提的承认;另一方面,这或许是出于动员手段的需要。对库尔德普通民众来说,超出伊拉克框架的民族主义在当时还不是他们所能认同和接受的问题解决方案。直到1988年,登记表的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首先“依照光荣的7月17日至30日革命”的表述被删去,③NIDS. Nos. 16587-6, 1988.至1990年表头的整句话被彻底删去。④NIDS. Nos. 16588-34, 1990.
值得注意的是,库尔德运动的衰弱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内部力量的联合。1988年5月,在伊朗的支持下,库民党和库爱盟决定放弃对抗,强调民族团结,联合其他政党宣布成立伊拉克库尔德斯坦阵线(al-Jabhatal-Kurdistānīyyat al-Irāqīyyah),宣布一致对抗复兴党政权。虽然这种联合在“强大”的伊拉克国家面前显得微不足道,复兴党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的库尔德斯坦阵线不过只是一块宣传招牌而已”,⑤NIDS. No. 38909-97-20, November 6, 1989.但讽刺的是,恰是这种虚弱在未来塑造了库尔德人力量的壮大。配合后期局势变动,“安法尔行动”造成的历史创伤开始发挥作用,成为伊拉克库尔德人构建一个想象共同体的宝贵历史素材。⑥John Bulloch and Harvey Morris, No Friends but the Mountains: The Tragic History of the Kurds,p.142.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1991年1月美国发动“沙漠风暴”行动,海湾战争爆发。时任美国总统布什于同年2月呼吁伊拉克人民推翻萨达姆政权。在随后的三周内,库尔德武装控制了库区近四分之三的领土。但从3月中旬起,伊拉克军队开始转入反攻。3月27日,萨达姆派出共和国卫队中的精锐部队向伊拉克北部发动空袭和地面推进,短时间内夺回相关领土,成功镇压了起义。由于担心伊拉克政府会进一步采取报复行为,大量库尔德难民涌向伊朗和土耳其边境。迫于巨大的人道主义压力,同年4月,以美国为首的11个国家以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形式向伊拉克库区派出2万名士兵,开展“提供舒适行动”(Operation Provide Comfort),在伊拉克北纬36度以北建立禁飞区。禁飞区包括埃尔比勒、苏莱曼尼亚、扎胡和杜胡克等地区,任何飞入其中的伊拉克飞机都将成为多国部队打击的目标。①Ofra Bengio, The Kurds of Iraq: Building a State Within a State, p. 200; Gareth R. V.Stansfield, Iraqi Kurdist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Emergent Democracy, pp. 95-96.
作为惩罚,复兴党政府从库区撤出所有的党政军人员,并对库区施加经济制裁,这使得库尔德人承受了国际与国内的双重制裁。30万库尔德公务员工资被停发,库区遭到断电停水,当地公共卫生和基础服务状况急剧恶化。②Ofra Bengio, The Kurds of Iraq: Building a State Within a State, p. 201.由于担心复兴党政府会加大报复力度,20万库尔德难民再次涌向边境。萨达姆希望以此引发库区局势混乱,使库尔德两党面临统治困境,逼迫库尔德公务员和平民尽快转移到政府控制区内,并使他们意识到,至少伊拉克中央政府能够提供比库尔德运动更好的物质生活。
然而,大部分库尔德公务员和平民都抵挡住了萨达姆的威胁,拒绝转移至政府控制区。奥夫拉·本吉欧对此评价称:“(库尔德)公务员和民众作为一个整体准备好经受如此的艰难,确实是(观察)库尔德民族主义成形的一个晴雨表。”③Ibid., p. 201.可以说,“安法尔行动”背后无差别的集体性惩罚思路,实际上激化了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民族身份意识,使对一个“库尔德民族”政治身份的共同想象,开始贯穿于库尔德政治精英和社会底层。谢尔库·克尔曼支就此指出,库尔德人的起义不仅是伊拉克在科威特军事失败的结果,更是复兴党政权多年来压迫库尔德人政策的结果。④Sherko Kirmanj, Identity and Nation in Iraq,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13,p. 160.马苏德·巴尔扎尼在一次采访中也坦言:“起义源自于人民本身。这是我们未曾预料到的。”⑤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p. 371.
但是,复兴党在库区统治的失败,不必然意味着库尔德运动的胜利。事实上,复兴党政府以退为进的倒逼施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效果,杜胡克、苏莱曼尼亚、潘杰温等地区接连爆发民众抗议游行,指责库尔德阵线无法有效维护库尔德平民的民生利益。示威者甚至打出“我们要面包和黄油,不要萨达姆也不要库尔德阵线”的标语。⑥Ibid., p. 379.伊拉克国家与库尔德运动的“双输”局面再次上演,难民的生存问题亟待解决,库尔德阵线急需填补复兴党撤出后留下的权力与秩序真空。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地位显著提高。2004年3月,伊拉克颁布《过渡行政法》,规定库尔德语为伊拉克的两门官方语言之一,承认库尔德人的自治权利和库区政府作为库区三省合法政府的地位,库尔德武装得到保留。该法还规定,如果伊拉克有任何三个省三分之二的人口反对,可否决宪法,这实际上赋予了库尔德人否决宪法的权利。①Alex Danilovich, Iraqi Federalism and the Kurds: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Surrey:Ashgate Publishing, 2014, p. 52.库尔德人的这些权利,最终在2005年10月通过的《伊拉克永久宪法》中得到正式确立。此外,中央预算每年给库区17%的固定比例拨款,和伊拉克总统一职由库尔德人担任等非正式政治安排,都是伊拉克库尔德人2003年后政治地位上升的表现。经济上,国际制裁的解除和丰富的石油资源,推动了库区经济的飞速增长;安全上,相对稳定的局势与伊拉克其他地区形成巨大反差,使其在国际社会上收获“另一个伊拉克”的赞誉;相应地,在文化和思想层面,库区政府的成功对周边国家库尔德人形成示范效应,使伊拉克库尔德人相信库尔德民族独立事业将由自己领导完成。②Henri J. Barkey, “The Kurdish Awakening: Unity, Betrayal, and the Future of the Middle East,” Foreign Affairs, Vol. 98, No. 2, March/April, 2019, p. 112.这些为2017年9月的库尔德独立公投的举行埋下了伏笔。③有关2003年后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倾向与分离情节形成的细节,参见汪波:《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90-112页。事实上,早在2005年库尔德民间运动发起的一次非正式独立公投中,200万的参投人数和98%的独立支持率,就已充分说明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性质的嬗变。④Aram Rafaat, The Kurds in Post Invasion Iraq: The Myth of Rebuilding the Iraqi State,p. 197.
四、结语
当前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所表现出来的独立倾向并非一个既定结果,其本质上是伊拉克现代国家建构失败的产物。换言之,伊拉克库尔德人所面临的国家环境和民族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民族主义发展的限度。
第一,库尔德人的民族意识或民族主义思想萌芽,实际上是对历史上帝国间战争和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覆灭的一种回应,且仅局限于库尔德少数精英层面。库尔德人内部多元分化的文化系统和部落社会结构,没有使其衍生出一个泛化的“民族”概念,并无法在短期内及时主动把握局势变化的潮流,进而成为大国政治的牺牲品。
第二,长期以来,伊拉克国家框架构成了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发展的基本前提。基于现代伊拉克特殊的生成形式,库尔德人被划入伊拉克后,享有较为宽松的发展空间。这一方面使有主导力的库尔德部落很容易为眼前的利益所妥协,限制了它对民族主义的追求;另一方面,这也使左翼化的新一代库尔德城市精英得以缓慢发展,为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但各自的历史缺陷,导致了二者间复杂的竞合关系,无法形成合力一致对外。在社会层面,强势的部落传统认同和现代国家高福利经济政策的驱动,导致库尔德民众的民族意识淡薄,不愿意向精英化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实际的支持。经过长期互动,在伊拉克国家的框架内寻求民族自治成为库尔德精英政治成熟的表现,而伊拉克国家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库尔德普通民众所接受。
第三,贯通政治精英和社会底层的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是晚近才发生的政治现象。如前所述,库尔德民族主义思想从其萌芽起,就长期局限于精英阶层,极大限制了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两伊战争后期复兴党政府推行无差别的集体性惩罚政策,从侧面激化了伊拉克库尔德民众对“库尔德民族”的共同想象,扩大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外延。随着后期伊拉克和地区局势的演化,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因自治实践在制度层面得到进一步确立与深化。
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历史演变进程表明,伊拉克库尔德人显著的民族意识和独立倾向的出现,并非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它本质上是伊拉克国家能力的失效,以及随之带来的畸形的伊拉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的结果。但是,基于长期以来伊拉克国家结构对库尔德问题的深刻影响,以及地区与国际环境的根本性限制,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解决并非没有转圜的空间。因此,20世纪80年代伊拉克复兴党政府在处理库尔德问题上的实践经验与历史教训表明,如何打造强大稳定的国家能力,建构对多族群—教派社会特征具有包容性的伊拉克国家话语与制度安排,是伊拉克有效解决其国家认同困境和库尔德问题的关键。同时,在激烈的大国博弈和中东地缘战略竞争中,伊拉克还应找到利益平衡点,避免作为本国内政问题的库尔德问题被外部利用,进而演化为地区或国际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