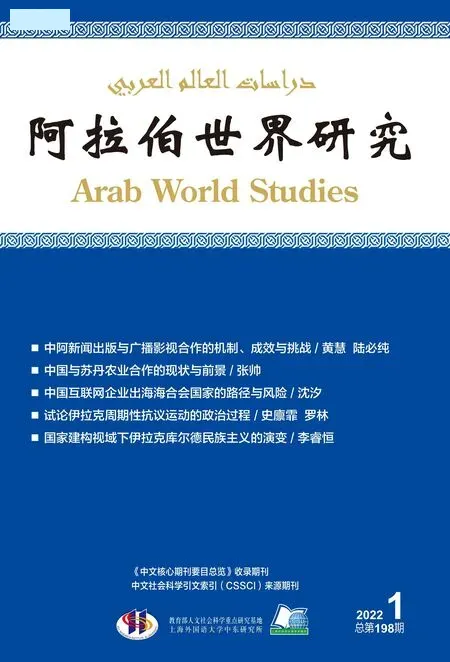古叙利亚埃勃拉城邦的文化与族群归属*
2022-04-22梅华龙
梅华龙

那么,公元前三千纪的埃勃拉人又是什么人?他们和亚摩利人之间存在何种联系?由于亚摩利人被视为早期西北闪米特人的代表,加之埃勃拉地处叙利亚西北部,人们很容易将叙利亚以及埃勃拉周边视为西北闪米特文化的传统势力范围。然而,公元前三千纪的历史现实显然没有几百年后的亚摩利时代清晰。即便在东部两河流域叱咤风云的亚摩利人真的来自西部,我们也无法断定公元前三千纪的埃勃拉人就是亚摩利人或西北闪米特人。因此,公元前三千纪埃勃拉文化缔造者的族群归属便成为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
对古代西亚族群属性的分析往往离不开陶器风格、艺术特征、聚落和丧葬习俗、社会结构和文化、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人名等线索。⑤Govert van Driel, “Ethnicity, How to Cope with the Subject,” in Wilfred van Soldt, ed.,Ethnicity inAncient Mesopotamia: Papers Read at the 48thRencontre Assyriologique Internationale,Leiden, 1-4 July 2002, Leiden: Nederlands Instituut voor het Nabije Oosten, 2005, pp. 4-6.与许多早期西亚地区的族群相比,公元前三千纪中期埃勃拉留下了丰富的文字资料,给了学界相对于物质文化更加直接和相对确凿的族群分析元素。学界从人名学⑥Alfonso Archi, “The Personal Names in the Individual Cities,” in Pelio Fronzaroli, ed.,Studies on the Language of Ebla, Firenze: Istituto di Linguistica e di Lingue Orientali, Università di Firenze, 1984, pp. 225-251; Marco Bonechi, “Onomastica dei Testi di Ebla,” Studi Epigrafici e Linguistici sul Vicino Oriente Antico, Vol. 8, 1991, pp. 59-79; Amalia Catagnoti, “L'onomastica dei testi di Ebla nel contesto siriano del III millennio a.C,” in Amalia Catagnoti,ed., Atti del XXII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onomastiche (Pisa, 28 agosto-4 settembre 2005), Nominatio: Collana di studi onomastici, 2011, pp. 459-72.、埃勃拉语言系属①MichaelAstour,“ToponymyofEblaandEthnohistoryofNorthernSyria:APreliminary Survey,”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08, No. 4, 1988, pp. 545-555.、地名学②Richard Caplice, “Eblaite and Akkadian,” in Luigi Cagni, ed., La lingua di Ebla: Atti del ConvegnoInternazionale (Napoli, 21-23 Aprile 1980), Napol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Seminariodi Studi Asiatici, 1981, pp. 161-164; Michael Streck, “Eblaite and Old Akkadian,” in Stefan Weninger, ed., Semitic Languages: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Berlin and 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2011, pp. 341-352; John Huehnergard and Christopher Woods, “Akkadian and Eblaite,” in R. Woodward, ed., The Ancient Languages of Syria-Palestine and Arab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2008, pp. 83-152.等角度的研究,而争论主要围绕埃勃拉文化属于东闪米特传统还是西边闪米特传统。其中,布切拉蒂(G. Buccellati)提出应从城乡而非东、西闪米特二元对立的角度理解埃勃拉与亚摩利人的关系。③Giorgio Buccellati, “Ebla and the Amorites,” in Cyrus H. Gordon and Gary Rendsburg,eds., Eblaitica: Essays on the Ebla Archives and Eblaite Language,Vol. 3, Winona Lake:Eisenbrauns, 1992, pp. 83-104.本文以文字资料为主,考古发现为辅,从语言、宗教信仰和艺术特征三个最能体现族群特质的方面分析公元前三千纪埃勃拉的族群归属特征及其在不同时代的发展变化。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对布切拉蒂的假设作出评议,进而探讨埃勃拉人的族群归属问题及其与后来西北闪米特亚摩利人的关联。
一、语言与早期埃勃拉的族群归属
我们了解埃勃拉语言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写于公元前24世纪的埃勃拉档案。埃勃拉出土的楔形文字泥板资料多为行政和经济文献,也有国际条约、咒语、占卜,或具有文学、神话性质(如ARET V.6, 7)的文献。从文字和书写传统来看,埃勃拉的楔形文字传统兼具外部和本土特征:其早期的书写和拼读方式可能受东部两河流域和马里的影响;自国王伊尔卡卜·达穆(Irkab-dāmu)时期开始,埃勃拉楔形文字传统逐步在文字细节上也呈现出自身特点。④德国学者扎拉贝尔格(Walther Sallaberger)认为,埃勃拉本地书写传统建立于这一时期,与其在政治上逐步摆脱马里的阴影有关,文化方面的独立发展很可能源于埃勃拉政治地位的日益提高。参见Walther Sallaberger, “Die Entwicklung der Keilschrift von Ebla,” in Jan-Waalke Meyer,Mirko Novák, Alexander Pruss, eds., Beiträge zur Vorderasiatischen Archäologie Winfried Orthmann Gewidmet, Frankfurt: Johann Wolfgang Goethe-Universität, Archäologisches Institut, 2001, pp. 439-441, 444。
我们关注的焦点则是语言本身,特别是埃勃拉语在闪米特语言中的位置以及它是否是一门独立语言。严格地说,后者并不仅是一个语言学问题,也是一个术语和命名问题。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社会,语言的划分受到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有些完全可以互通的语言,随着政治的分化而被视为不同的语言。①如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波斯尼亚语以及最新产生的“黑山语”。Srđan Jovanovic',“The Discursive Creation of the ‘Montenegrin Language’ and Montenegrin Linguistic Nation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Acta Universitatis Sapientiae: European and Regional Studies, Vol. 13, 2018,pp. 67-86.而在讨论一门古代语言应被看作“独立”语言时,我们往往很难了解其背后的政治动因,因此应更多关注这门语言的整体特征及与其他语言的共性,并据此探讨语言的系属问题。在关注语言整体特点的同时,也应关注其独特性,特别是与同系属的语言相比具有何种明显的独创性差异,以及哪些特征受到了其他语言的影响。
(一)埃勃拉语的整体特征
埃勃拉语在整体上体现了东闪米特语的特征,并与叙利亚地区不同时期的西北闪米特语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在词汇方面,埃勃拉语与其他阿卡德语方言共有的词汇较多。②Michael Streck, “Eblaite and Old Akkadian,” p. 349.在动词变位方面,埃勃拉语中的动词和阿卡德语各类方言一样,使用前缀变位形式来描述过去发生的动作即“过去式”(preterite),这一点有别于使用后缀变位即“完成体”(perfect tense)的大多数西北闪米特语。③至迟在公元前三千纪中后期就流行于叙利亚部分地区的亚摩利语(Amorite),一般被认为是西北闪米特语,但也有前缀过去式(prefixed preterite),我们不了解其现在时的形态。部分人名中的状态式或许可以被解读为变位动词。其实,西北闪米特语中一开始也是存在前缀型变位的,特别是出现在叙述当中(乌加里特语)。但后来“过去”这一概念被后缀型变位取代,或仅保留少数固定形式里面(如古典希伯来语中的wayyiqtol型)。比如:
da-si-ig[tassiq]=你亲吻了(ARET XIII 1 r. XII 12)

i-sa-gur[yiskur]=他说了(ARET XVI 1 r. VIII 23)④Amalia Catagnoti, La Grammatica della Lingua di Ebla, Firenze: Dipartimento di Scienze dell′Antichità, Medioevo e Rinascimento e Linguistica, Università di Firenze, p. 130.
其次,埃勃拉语中表示现在或将来的动词形式也采用前缀变位法,且与阿卡德语一样,在词根第一和第二辅音之间有一“a”:

ne-sa-bar[nisappar]=我们(将)送、寄(ARET XIII 13 v. III 7)⑤Ibid., p. 131.
再次,埃勃拉语动词的后缀变位与在阿卡德语中一样表示一种状态(Stative),有时有被动含义。而在很多西北闪米特中,后缀变位是完成体,可以带直接宾语。
最后,埃勃拉语和阿卡德语一样,动词完成体带有-ta-中缀,而这种变位方式基本不见于西北闪米特语:
ig-da-ra-ab[yiktarab]=他已祝福过(ARET XI 1 v. VIII 15)①卡塔尼奥蒂(Amalia Catagnoti)指出,虽然这一形式容易与阿卡德语的Gtn(表示反复、经常性动作)相混,但此处上下文似乎指的是一次性已完成的动作。参见Amalia Catagnoti, La Grammatica della Lingua di Ebla, p. 132, n. 500.
ne-da-ma-ru12[nītamar]=我们已看到(ARET XVI 10 v. II 3)②Amalia Catagnoti, La Grammatica della Lingua di Ebla, p. 132.
上述特征表明埃勃拉语与阿卡德语在动词变位方面高度一致。
此外,从词干③词干(Stem)指辅音词根字母的固定组合方式;同一词干的动词往往在语义、语态上有相似性。的分布和特征来看,埃勃拉语中的使役词干(Causative Stem)与阿卡德语一样使用-š-来表示。当然,尽管许多西北闪米特中使役词干的符号是-h-或-Ɂ-,但单凭-š-本身无法断定埃勃拉语属于东闪米特语。在作为西北闪米特语的乌加里特语中,使役词干也用-š-表示。④关于亚摩利语中的使役词干,参见Michael Streck, “Amorite,” in Stefan Weninger, ed.,Semitic Languages: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p. 456; Ebbe Knudson, “Amorite Grammar: A Comparative Statement,” in Alan S. Kaye, ed., Semitic Studies in Honor of Wolf Leslau on the Occasionof His Eighty-fifth Birthday,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1, pp. 866-885。后者指出亚摩利语中也许存在H使役词干。
除动词外,埃勃拉语中也有若干名词变化与阿卡德语一致而基本不见于西北闪米特语,如表示地点的名词尾缀[-ūm]和表示趋向的名词尾缀[-iš](如gatum-maga-ti-iš[qātūmma qāti's],“从一只手到另一只手”)。⑤Michael Streck, “Eblaite and Old Akkadian,” p. 345。须注意,乌加里特语中可能有-ūm的同源尾缀-u,表示地点。参见John Huehnergard, An Introduction to Ugaritic, Peabody:Hendrickson Publishers Marketing, 2012, p. 40。埃勃拉语中形容词的阳性复数形式也与阿卡德语相同(-ūtum)。需要注意的是,埃勃拉语形容词阳性复数的词尾形式与阳性名词复数并不一致。而在西北闪米特语中,名词和形容词的词尾一致。其中,形容词阳性复数一般以-ū/īm(乌加里特语、希伯来语、腓尼基语等)或-īn(阿拉姆语、摩押语等)结尾。
在语序方面,埃勃拉语和阿卡德语一样以主宾谓为主流,但也有谓主宾和主谓宾这两种语序。其中,谓主宾体现了西北闪米特特征,但也可能是原始闪米特语的遗存。因此,可以说埃勃拉语的语序在整体上也体现了东闪米特语的特点。⑥Michael Streck, “Eblaite and Old Akkadian,” p. 349.
(二)埃勃拉语与其他东闪米特语的差异

在词汇方面,埃勃拉语的介词sin(si-in,有时也拼写成si-ma,意为“向着……”)不见于阿卡德语或西北闪米特语。除埃勃拉语外,这个介词仅存于埃勃拉语和古南阿拉比亚诸方言(Old South Arabian)中的赛博伊语中(Sabaean/Sabaic)。赛博伊语中存在一个介词s1wn(“向着……”)。②Joan Biella, Dictionary of Old South Arabic, Sabaean Dialect, Chico: Scholars Press,1982, p. 330.赛博伊语中的s1对应原始闪米特语中的š,而这一辅音在埃勃拉语中发成[s],③Amalia Catagnoti, La Grammatica della Lingua di Ebla, p. 63.因而这两个词的对应关系是可能的。这个介词有可能是原始闪米特语在两门相距较远的分支语言中的偶然遗留。
埃勃拉语还有两个疑似语音方面的特征颇具特色:一是有时辅音r会被写成l;二是辅音l偶尔可以脱落。


l脱落的情况如下:


i-da-kam4[yihtalk-am](ARET XIII5v.X 12)
ne-mi-ga-am6[nimlik-am](ARET XVI 5 r. V 9)
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一点:这些特征体现的是书写或正字法问题,还是真正的语音问题?r写成l这种拼法,现有证据似乎难以判断。而l的脱落似可由上述最后一个例子(ne-mi-ga-am6=[nimlik-am])明确为语音问题,因为专门用一个符号来表示[mli]这种复辅音开头的音节并不符合楔形文字的书写习惯。与此同时,l的脱落并不是一定的——很多l得以保留。上述几个例子表明,l在不同的环境下均可脱落,包括元音之间、词末、辅音开头音节之前的音节末尾、紧随上一音节末尾辅音的音节开头。不过,这些例子并不能反映重音与l脱落的关系。埃勃拉语中的r写成l和l脱落这两个现象或许来自于底层语言的影响,但也有学者指出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和后来古巴比伦时期马里的文献中也偶有类似现象出现。①Michael Streck, “Eblaite and Old Akkadian,” p. 343.

关于上述差异是否足以让我们认定埃勃拉语是一门独立的东闪米特语而非阿卡德语的一种方言,学者们的看法见仁见智。⑤一些学者认为埃勃拉语独立于阿卡德语,是东闪米特语的另一个分支。其他学者则认为埃勃拉语是一种阿卡德语方言。施特雷克对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参见Michael Streck, “Eblaite and Old Akkadian,” pp. 350-351。埃勃拉语虽然在语音和形态变化方面的细节上与众不同之处,但整体上与其他阿卡德语方言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差异。用施特雷克(Michael Streck)的话说,埃勃拉语与后来的亚述、巴比伦方言之间的区别并不比亚述、巴比伦方言之间的区别更大,而自己独特的创新特征也不多。①一些学者认为埃勃拉语独立于阿卡德语,是东闪米特语的另一个分支。其他学者则认为埃勃拉语是一种阿卡德语方言。施特雷克对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参见Michael Streck, “Eblaite and Old Akkadian,” pp. 351-352.在词汇方面,埃勃拉语与阿卡德语方言之间共有的基础词汇很多,但同时明显受到西北闪米特语影响。因材料所限,语言特征之外的判定因素(如政治主权、民族主义等)在此案例中难以探究。若以语音、词法、句法和基础词汇为判断标准,似乎应该将埃勃拉语视为一种受西北闪米特语影响颇深的古阿卡德语方言(属亚非语系闪米特语族东闪米特语支)。②Ibid.
二、宗教传统与早期埃勃拉的族群归属
(一)埃勃拉的本土神祇

库拉(dKu-ra)毫无疑问是埃勃拉文献中最重要的神祇。埃勃拉的档案至少有200多次提到库拉。这些资料大多记录了献给库拉神的贡品(nindaba=“祭品”;níg.ba=“礼物”),包括金银锭、金银饰品(如gú-gi-lum=“手链”)、羊、面包和衣物等。在这些文献中还提到了库拉神乘坐的战车(giš-gígir-sumša-tiu5dKura...,如ARET XI 2 23)以及供奉库拉的庙宇(édKu-ra,如ARET III 800 I)。目前还无法将库拉的庙宇与考古发现中的神庙对应起来,但其位置大概在宫殿(sa.zaxki)中或宫殿附近。④参见Francesco Pomponio and Paolo Xella, Les dieux d'Ebla: Étude analytique des divinités éblaïtes,Münster: Ugarit, 1997, p. 246; Walther Sallaberger, “Kura, Youthful Ruler and Martial City-Godof Ebla,” in Paolo Matthiae, ed., Ebla and Beyond: Ancient Near Eastern Studies after Fifty Years of Discoveries at Tell Mardikh: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Held in Rome, 15th-17th December 2014,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8, p. 120.。而且,与同时期某些其他神祇(如阿勒颇的哈达)不同,库拉只在埃勃拉一地被供奉,因此可以视之为埃勃拉独有的保护神。⑤库拉在一些地方有“分身”,如阿尔米的库拉(dKu-ra ar-miki)、马努提乌姆的库拉(dKu-ra ma-nu-ti-umki)、西拉哈的库拉(dKu-ra si-lă ki)等。作为保护神,库拉及其配偶巴拉玛(Barama)与埃勃拉的国王、王后和王权概念本身关系密切。每年一月的库拉节来临之时,国王会参加一个洁净仪式,在仪式上王权会被更新。由于库拉、巴拉玛与象征母亲的女神宁杜尔(Nindur)关系密切,宁杜尔在这个仪式上也会象征性地给予库拉新生。学者扎拉贝尔格由此认为,库拉应该被视为所谓“年轻一代”战神。①Walther Sallaberger, “Kura, Youthful Ruler and Martial City-God of Ebla,” p. 127.“年轻一代”指神祇多为诸神之主的儿子或下级。在两河流域,具有战神特征的城邦保护神可能被看作两河流域主神恩利尔(Enlil)的儿子。②如基尔苏(Girsu)的主神宁基尔苏(Ningirsu),参见Jeremy Black, Anthony Green and Tessa Rickards, Gods, Demons, and Symbol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2, p. 138。而在公元前二千纪后期的乌加里特,则有兼具风暴神和战神特点的年轻一代神祇巴力(Baal)晋升为众神之王的神话。不过,库拉并无风暴神的特征。因此,我们并不能根据两河流域或西北闪米特的神话传统推测库拉的特质及其与其他神祇的关系。此外,扎拉贝尔格的研究表明,虽然在名字上类似,但很难确定库拉与胡里(Hurrians)文化圈中的诸如库尔维/库拉(Kurwe/Kura)、库里(Kurri)等神祇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关系。毕竟埃勃拉的“库拉”是否应该这样释读尚无定论。③Ibid., p. 114.除贡品记录外,库拉也出现在人名中(如ku-ra-damu;šu-ma-dKu-ra),共24次。④Francesco Pomponio and Paolo Xella, Les dieux d'Ebla: Étude analytique des divinités éblaïtes,p. 245.总之,库拉并不是常见于西亚地区的闪米特神祇,是埃勃拉宗教信仰本土特征的体现。
另一位重要的本土神祇是伊施哈拉,一位在叙利亚北部颇具影响力的女神。在埃勃拉,伊施哈拉(dAMA-ra/dBARA7/dSIG7.AMA/dBARA7-ra/dBARA7-iš)被提及40次以上。这些文献还偶尔提及多个伊施哈拉的分身,特别是出现了近20次的dBARA7-iš/ramá-NEki和出现了13次的dBARA7/dGÁxSIG7-iš/-išzu/sura-am/muki。⑤Ibid., pp. 208-209, 216.伊施哈拉与埃勃拉的主神库拉之间关系也很紧密。虽然巴拉玛是库拉的官方配偶,但是伊施哈拉被视为城邦及其统治者的守护女神。献祭财物记录中多次提及“国王的伊施哈拉圣所”(dagxdAMA-raen),体现了伊施哈拉女神与国王的特殊关系。伊施哈拉和埃勃拉的关联在公元前三千纪末期赫梯语和胡里语的《解放史诗》(EpicofEmancipation)中亦有体现。伊施哈拉在这部史诗中被描述为埃勃拉的守护神,这表明她在埃勃拉的特殊地位延续到了公元前三千纪末期。
这位女神的起源不明。意大利学者阿尔奇(A. Archi)认为伊施哈拉历史悠久,代表了埃勃拉的底层文化。①Alfonso Archi, “Divinités sémitiques et divinités de substrat: Le cas d'Išara et d'Ištar à Ébla,” in Alfonso Archi, Ebla and Its Archives: Texts, History, and Society, pp. 685-86而这个名字也许和西闪米特的有关。②Francesco Pomponio and Paolo Xella, Les dieux d'Ebla: Étude analytique des divinités éblaïtes, p. 216.伊施哈拉也曾被看作是西北闪米特神达干(Dagan)的配偶。而最终伊施哈拉的影响延伸到了安纳托利亚和两河流域,与女神伊施塔(Ištar)融合,最终成为胡里诸神之一。③Jeremy Black, Anthony Green and Tessa Rickards, Gods, Demons, and Symbols of Ancient Mesopotamia,p.110;AlfonsoArchi,“FormationoftheWestHurrianPantheon:TheCaseofIš̆ ara,”inK.AslihanYenerandHarryA.HoffnerJr.,eds.,RecentDevelopmentsinHittiteArchaeology and History, Papers in Memory of Hans G. Güterbock,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2002, p. 31.无论如何,伊施哈拉和埃勃拉的特殊关系使其可被归类为具有鲜明叙利亚北部特色的埃勃拉本土神祇。
尼达巴尔是埃勃拉的另一个重要神祇,在埃勃拉献祭记录中出现了40次。而尼达巴尔在各地的分身多见于祭品记录。比如,“卢班的尼达巴尔”(NI-da-bal lu-ba-anki)被提及逾110次,“阿鲁加杜的尼达巴尔”(dNI-da-bala-ru12-ga-duki)则被提及66次之多,“阿基鲁的尼达巴尔”(dNI-da-balɁa-gi-luki)也出现了近40次。此外还有“哈马的尼达巴尔”(dNI-da-balɁa-ma-duki),此处的哈马就是如今叙利亚的同名城市。其中,尼达巴尔与卢班和阿鲁加杜这两处属于埃勃拉附庸国阿拉拉赫的城市④TM.75.G.1462中提到阿拉拉赫和卢班向埃勃拉进贡;TM.75.G.1527记录阿拉拉赫单独向埃勃拉进贡。关于阿拉拉赫在青铜时代早期与埃勃拉的关系,参见Alfonso Archi, “Alalah al tempo del regno di Ebla,” in Alfonso Archi, Ebla and Its Archives: Texts, History, and Society,pp. 360-362。关系尤为紧密。两位埃勃拉公主曾在卢班担任“神的配偶”(dam.dingir),即女祭司。⑤Alfonso Archi, “The High Priestess ‘dam-dingir’ at Ebla,” in Alfonso Archi, Ebla and Its Archives: Texts, History, and Society, p. 699。尼达巴尔神的这个分身每年十一月都会在不同的城镇之间巡游(šu-mu-nígin)。⑥关于对TM.75.G.2377和TM.75.G.2379的解读,参见Alfonso Archi, “The Cultic Journey of the God Hadabal,” in Alfonso Archi, Ebla and Its Archives: Texts, History, and Society,pp. 615-621。埃勃拉档案中还提及了“宫殿的尼达巴尔”(dNIda-balsa-zaki),这或许与埃勃拉宫殿中的尼达巴尔祭坛存在关联。与其他神祇一样,大量贡品被分配给尼达巴尔。不过,在人名中这个神名较为罕见。总之,尼达巴尔可能是埃勃拉诸神中仅次于库拉的核心神祇之一。⑦Francesco Pomponio and Paolo Xella, Les dieux d'Ebla: Étude analytique des divinités éblaïtes, pp. 245-246.
以上提及的三位神祇只是埃勃拉本土神的代表。它们体现了公元前三千纪叙利亚北部的宗教传统,有的或许与后来的胡里传统有关。但是,这并不代表它们的来源就是胡里文化。此外,虽然伊施哈拉的名字可能有西北闪米特背景,但在整体上埃勃拉的主要神祇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有别于后代西北闪米特诸神传统。
(二)具有西北闪米特特征的埃勃拉神祇
叙利亚北部历史上一直是不同文化交融的地区,除这些具有鲜明埃勃拉特色的神之外,西北闪米特神祇在埃勃拉献祭文献中的地位也较高。有些西北闪米特神和前述几个埃勃拉主要神祇一样,在该地区拥有祭祀中心并接受大量贡品。其中,最重要的是被提及超过80次的阿达(dɁà-da)。阿达在阿勒颇的分身被提及达57次,而阿勒颇在此时期是埃勃拉的附庸国,也是阿达神的崇拜中心。埃勃拉的阿达即后世西北闪米特文化中地位最高的风神哈达(Hadad/Haddu,两河流域的Adad),在公元前一千纪是阿拉姆人(Arameans)最重要的神。①Francesco Pomponio and Paolo Xella, Les dieux d'Ebla. Étude analytique des divinités éblaïtes, p. 52.另一个在后世极为重要的西北闪米特神祇是拉萨普(dra-sa-ap)。这位与冥界关系紧密的神在马里亦有发现,后来也出现在乌加里特、腓尼基、阿拉姆乃至希伯来圣经中(如《申命记》32:24中的“”)。②Ibid., pp. 313-315; Paolo Xella, “Resheph,” in Karel van der Toorn, Bob Becking and Pieter van der Horst, eds., Dictionary of Deities and Demons in the Bible: DDD, second extensively revised edition, Leiden and Boston: Grand Rapids, MI: Brill; Eerdmans, 1999, pp. 700-703.
有些相当重要的西北闪米特神名则仅出现在人名中。比如,伊勒(il/ilum)在闪米特语中既是泛指“神”的普通名词,也特指某一个神。在乌加里特和其他迦南文化以及希伯来圣经中,伊勒(El,即,伊勒在希伯来语中的形式)被视为众神之主。不过,由于埃勃拉文献并未提及伊勒的祭祀中心,此处“il或ilum”可能是“神”的泛称。阿尔奇认为,早期叙利亚人群有部落乃至游牧背景,所以明确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神祇祭拜并不成熟。在早期人名中的神名部分并不一定是指某确定的城市主神。因此,“伊勒”可以指某家族所信赖、倚仗的任何神祇。在阿尔奇看来,这也体现了古代近东所常见的个人和家庭宗教传统。③Alfonso Archi, “Il in Ebla Documentation,” in Alfonso Archi, Ebla and Its Archives:Texts, History, and Society, pp. 648-655.阿尔奇的观点基本上是可信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另一位西北闪米特主要神祇达干在埃勃拉也只出现在人名中(16次),但献祭记录超过30次提及“图图尔的主”(dBE du-du-lu/la-laki)④达干的崇拜中心就在图图尔城。,接受不同类型的祭品或礼物(nindaba/níg.badbedu-du-lu/lalaki;ARET I 10 3; II 12 4)。换言之,达干在埃勃拉拥有自己的祭祀中心并接受金银等祭品。鉴于“El”在人名中如此常见,如果此处它指专有名词“伊勒神”,则它不应该出现在人名中却不见于埃勃拉献祭文献(即没有属于自己的祭坛、圣所)。所以,伊勒在埃勃拉可能并不特指某一个的神祇。
(三)两河流域诸神对埃勃拉的影响

(四)埃勃拉宗教传统的其他特征
从埃勃拉的人名来看,有些人名中的元素虽然出现在神名的位置,但本身有其他寓意,并不是拥有祭祀中心的神祇。如埃勃拉国王人名中常见的-līm(部落)和-dāmu(血缘),②此二者也见于亚摩利时代叙利亚地区埃勃拉、马里、亚姆哈德等地的王名之中。表示“名字”或“后代”③“名字”在闪米特语中多有“后代”之意。的-šum和-zikir。也有“国王”(-malik-)、“正义”(-išar-)等元素出现在人名中,充当“神名”元素。有些地名可能被神化并出现在人名中,如公元前三千纪叙利亚地区得到强国马里和纳加尔以及附属于埃勃拉的名称阿勒颇,都可充当人名中的神名元素。④Francesco Pomponio and Paolo Xella, Les dieux d'Ebla: Étude analytique des divinités éblaïtes, pp. 466, 473.纳加尔对应的神祇配偶形式“宁-纳加尔”(nin-nagar)出现在马里的资料中。⑤Ibid.,p.473.
除献祭之外,埃勃拉人也会通过咒语、占卜等方式争取神对现实生活的干预。而这些活动也可能反映出埃勃拉与两河流域宗教传统的关系。以占卜为例,埃勃拉的占卜活动与和两河流域一样,围绕着作为祭品的羊展开。占卜师将羊肝取出,并根据羊肝的形状、纹理、脂肪分布等情况预测战争胜负和经济状况。埃勃拉的占卜术语也与两河流域接近,如“观察”羊肝的动作写作ba-la-um(barûm),同阿卡德语;“占卜师”写作lúmáš(-máš),而máš在苏美尔语中指用于占卜的羊。①关于其他占卜相关的术语,参见Alfonso Archi, “Divination at Ebla,” in Alfonso Archi,Ebla and Its Archives: Texts, History, and Society, pp. 687-698。
从整体上看,埃勃拉在宗教和信仰体现了叙利亚北部本土、两河流域以及西北闪米特等三种文化的结合。首先,所谓“古代叙利亚”本土文化的具体特征很难定义。在这一时期,后来在此地区活跃的胡里人及其文化尚未完全成型,但从神名等方面可以看出埃勃拉的宗教文化带有明显的非闪米特、非两河元素,譬如“库拉”这种用闪米特语或苏美尔语无法解释的神名。其次,见于埃勃拉资料的西北闪米特神祇则体现了埃勃拉所处的大环境,也反映了西北闪米特文化的亚摩利人影响力上升之前就已经流行于叙利亚地区。最后,两河流域的神明及宗教活动范式(如献祭、巡游、羊肝占卜)给埃勃拉本土传统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平台。尽管无法断定埃勃拉宗教文化的源头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和阿卡德文化,但两河文明本身特别是其宗教习俗和思想无疑使埃勃拉的本土习俗、信仰和价值观得以整合、发展并形成体系。
三、艺术特征与早期埃勃拉的族群归属
与早期叙利亚文明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埃勃拉在陶器制造及以陶器和金属制品为载体的形象艺术及其他手工艺术品等方面,也展现出本土传统与外来影响特别是两河流域文明的交融。
首先,埃勃拉在制陶工艺方面体现了早期叙利亚地区陶器制造的普遍特征。我们目前对埃勃拉及其周边地区陶器样式、陶器生产及使用的了解,主要来源于若干地区的集中出土发现。在埃勃拉城市内部,大量不同类型的陶器发现于G宫殿。而在宫外,位于埃勃拉遗址下城西北部P区南部的一座房屋(P4号建筑)内,也发现了功能性的陶器集合。在埃勃拉城市之外的小型遗址中也有大量陶器出土,例如位于阿勒颇东南45公里处建于埃勃拉城市被毁后的小型地区中心图坎遗址丘(Tell Tuqan)。研究显示,埃勃拉城内(取样为G宫殿内的陶器遗存)与城外(图坎)的本地产陶器在原材料以及工艺方面并没有明显的差异。①关于G宫殿内陶器遗存与图坎地区陶器遗存原料、质地和烧制技巧的比较研究,见M.L. Santarelli, “Archaeometrical Analysis of Pottery Production at EB III-IVA Ebla and Tell Tuqan,”in Paolo Matthiae and Nicoló Marchetti, eds., Ebla and Its Landscape: Early State Formation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pp. 357-366。从整体生产技术上看,埃勃拉G宫殿的陶器与同时期包含图坎、阿菲斯遗址丘(Tell Afis)等地在内的埃勃拉地区陶器生产技术和风格类似。其中城市地区的陶器生产更倾向于生产标准化高的制品,如高脚酒杯、卵形罐等。而这一时期叙利亚地区整体的陶器生产中心化和标准化仍不明显,具有多中心的特征。②S. Mazzoni, “Centraliz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The Pottery Assemblage of Royal Palace G.” in Paolo Matthiae and Nicoló Marchetti, eds., Ebla and Its Landscape: Early State Formation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pp. 89-96.
与制陶工艺方面的叙利亚本土特征不同,埃勃拉在图像艺术中方面则在以两河流域为源头——如对滚印(cylinder seal)的使用——的同时,兼具本地特色。其中,带有不同图案主题的滚印印记是我们了解埃勃拉图像艺术的重要途径。在埃勃拉,用于封印的泥块(bullae)和陶器表面是滚印印章出现的主要媒介。在封泥上的滚印往往与早王朝时期两河流域的艺术风格类似,但以争斗场面为主,宴会场面则基本不见于埃勃拉滚印之上。埃勃拉的滚印一般只有一幅条状图案(不分上下两幅),有一些在顶部和底部有由几何图案构成的条带,有的在顶部还有一条由人和动物头部图案组成的饰带。③Frances Pinnock, “Palace vs. Common Glyptic in Early Syrian Ebla and Its Territory,” in Paolo Matthiae and Nicoló Marchetti, eds., Ebla and Its Landscape: Early State Formation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p. 72, Figure 3.7.争斗图案一般涉及动物(如狮子、牛和鹿等较为温顺的动物)人、牛头人和神祇。在一枚印章上,一位牛头人还举起了一个看起来似乎由四颗人头图案组成的盘状物。④Ibid., Figure 3.9.在其他印章上还有手持鹿后腿的男性和与牛形人物相拥的女性形象。⑤Ibid., Figure 3.8.陶器上带有的印章图案,在埃勃拉地区目前共发现约50例。根据意大利学者马佐尼(Stefania Mazzoni)的研究,大部分印章图案集中于球形波纹罐和球形三足罐两类陶器。同时,陶器上的印章图案主要分为几何和植物主题与丰产女性图案两种。其中,前者主要出现在波纹罐上,后者主要出现在三足罐上。⑥Stefania Mazzoni, “Seal Impressions on Jars from Ebla in the Late Early Bronze Age,”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 88, No. 4. 1984, p. 488; Stefania Mazzoni, Le impronte su giara eblaite e siriane nel Bronzo Antico, MSAE 1. Roma: Missione Archeologica Italiana in Siria,1992.目前还很难判定陶器上的滚印图像起到的是装饰、象征作用,还是在行政上分门别类的作用。马佐尼指出,这些印章可能标示了器皿的功能或里面所装的物品。而有关丰产和放牧的图像,则可能是为了求吉兆。①Stefania Mazzoni, “Centraliz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The Pottery Assemblage of Royal Palace G.,” in Paolo Matthiae and Nicoló Marchetti, eds., Ebla and Its Landscape: Early State Formation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p. 93.
除了滚印图像外,在埃勃拉还出土了丰富的艺术品,体现了埃勃拉文化和政治精英对权力话语的理解、构建和表达。考古学家在G宫殿发现了国王和一位女性(或许是王后)的木制雕像,以及带有国王及其随从雕像的雪花石饰板。宫殿内还出土了滑石制的男性和女性头饰,也可能是国王和王后的物品。②Frances Pinnock, “Artistic Genres in Early Syria: Image and Ideology of Power in a Great Pre-Classical Urban Civilisation in its Formative Phases.” in Joaquín Ma. Córdoba et al., eds.,Proceedings of the 5th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Madrid:UAM Ediciones, 2008, pp. 25-29, Figure 1-3, 5, 9, 11.学者皮诺克(Frances Pinnock)认为,国王的形象在埃勃拉乃至公元前三千纪的叙利亚地区整体的图像艺术传统里都占有关键位置。与强调国王与神祇密切关系的同时期两河流域传统相比,③当然,整体上埃勃拉乃至早期叙利亚整体与两河流域在艺术风格上的相似之处是广泛存在的。埃勃拉出土的石碗、青金石锁、沥青和青金石制狮子雕像等与乌尔(Ur)地区的艺术风格有一定相似性。参见Frances Pinnock, “Ebla and Ur: Relations, Exchanges and Contacts Between Two Great Capital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Iraq, Vol. 68, 2006, pp. 85-97。埃勃拉地区权力的展现主要围绕着国王及其家庭(特别是王后和大臣)本身,而王宫就是呈现这些形象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的核心区域。在G宫殿内出土的军旗上甚至没有神祇的形象。此外,真人大小的国王塑像就矗立在王座所在的大殿入口两侧。而在王宫其他房间内也装饰有带有国王形象的嵌板。在埃勃拉的特产雕刻并嵌有饰物的木质家具上,国王和其他王室人物形象也时常出现。埃勃拉和早期叙利亚其他政治中心以展现国王形象为核心的艺术风格,可能也影响了后世叙利亚乃至两河流域新亚述帝国的王权思想及其艺术呈现。最后,尽管埃勃拉艺术品中国王形象居重要位置,但在埃勃拉尚未发现两河流域常见的国王碑铭。④Frances Pinnock, “Artistic Genres in Early Syria: Image and Ideology of Power in a Great Pre-Classical Urban Civilisation in Its Formative Phases,” in Joaquín Córdoba et al., eds., Proceedings of the 5th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pp. 19-20, 24。在公元前2000年第二埃勃拉被毁后,新的人群(或许是亚摩利人)在保存部分早期埃勃拉文化的基础上,带来了新的宗教和文化元素。例如,闪米特女神伊施塔的地位代替了过去埃勃拉的主神库拉;而国王在宗教和仪式当中的角色也比过去更加明显。参见Frances Pinnock, “Change and Continuity of Art in Syria: Viewed from Ebla,” in Jan-Waalke Meyer und Walter Sommerfeld, eds.,2000 v. Chr.-Politische, wirtschaftliche und kulturelle Entwicklung im Zeichen einer Jahrtausenwende: 3. Internationales Colloquium der Deutschen Orient-Gesellschaft, 4-7 April 2000 in Frankfurt/Main und Marburg/Lahn, Saarbrücken: In Kommission bei SDV, Saarbrücker Druckerei und Verlag, pp. 87-118。
需要指出的是,除两河流域的持续影响外,地处两河文明与埃及文明交汇之处的叙利亚自然也与后者建立了文化上的联系。例如,埃勃拉G宫殿内曾出土一个刻有埃及第六王朝法老裴皮一世(Pepi I)头衔的雪花石膏制容器盖。①PaoloMatthiae,“ALongJourney.FiftyYearsofResearchontheBronzeAgeatTell Mardikh/Ebla,” in Paolo Matthiae and Nicoló Marchetti, eds., Ebla and Its Landscape: Early State Formation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p. 45.
总之,作为商贸重镇的埃勃拉,在文化上体现了不同地区特色的交融。其中,滚印的使用使埃勃拉的艺术呈现出明显的两河流域特征。作为早期叙利亚地区城市文明的代表,埃勃拉在以艺术表达的权力概念体系与意识形态上颇具自身特色。
四、埃勃拉人与亚摩利人:族群归属差异还是城乡差异?
上述讨论为我们明确回答“埃勃拉人属于什么族群归属”这一问题奠定了一定基础。严格地说,由于无法确认埃勃拉地区的统治者和平民是否属于同一个族群,而绝大多数文献及考古资料仅提供有关统治阶层的信息,因此我们的推论也存在局限性。假如埃勃拉统治阶层在语言、宗教上的特征反映了埃勃拉文化创立者的来源,则这种文化在早期就已具有明显的混合特征。首先,埃勃拉语是一种具有本地特征东闪米特语。其次,尽管埃勃拉最具影响力的神祇如库拉或许有非闪米特背景,有些后来还曾被纳入胡里诸神,但许多埃勃拉的重要神祇在后世的西北闪米特宗教中地位至关重要。最后,在艺术上埃勃拉兼具两河流域和叙利亚本土特征。除这三点之外,还需注意埃勃拉本土的人名主要是闪米特人名且大多带有西北闪米特语特征。②从人名的类型来看,卡塔尼奥蒂将其归类为“叙利亚型”。与之相对应的是“两河流域型”,主要发现于同一时期的马里。她指出,叙利亚型人名的主要特征是亲族关系术语在名字总充当神名元素的情况较多(-līm,“部落”;-dāmu,“血”,或许指祖先;此外还有“父”、“兄”等词),且这些亲缘术语在此处也反映了埃勃拉的政治思想,比如“兄弟”一词也可能指代国与国之间的联盟关系。参见Amalia Catagnoti, “L'onomastica dei testi di Ebla nel contesto siriano del III millennio a.C.,” pp. 466-69。-dāmu,-lim,-malik(国王),-zikir和 -šumu(名字)充当人名总神名元素的情况也见于其他早期叙利亚城市,如艾马尔国王的名字中也常出现-dāmu。参见Alfonso Archi, “The Personal Names in Individual Cities,” p. 238。埃勃拉人名中的“部落”、“血缘”等元素不禁让我们联想起公元前二千纪前半期马里等地亚摩利人人名中的“-līm”这个成分。“līm”这个词虽然可能与阿卡德语的līmu(一千、千人队伍)有关,但更可能来自西北闪米特语(如乌加里特语中的līm;希伯来语中的,“民族”、“族群”)。总之,不管从词源角度考虑,还是从其背后所反映的政治、社会意识形态(部落政治背景)角度考虑,似乎埃勃拉命名传统中存在不可忽视的西北闪米特元素。在这一时期的叙利亚北部边缘也存在族群归属不明的人名,用闪米特语或苏美尔语都完全无法解释。至少其中一小部分可能与后来在此地区十分重要的胡里人有关。①如bù-gú-e。此外,埃勃拉文献中提及了阿尔米(Armi)和杜鲁(DU-lu)这两座城市若干以-wa-du结尾的非闪米特人名。参见Amalia Catagnoti, La Grammatica della Lingua di Ebla,pp. 462-63, 464。总之,早期埃勃拉文化具有东、西闪米特及非闪米特的混合特征。
由此可见,早期埃勃拉文化所体现的特征难以归于任何一个特定族群。值得注意的是,在语言文字和宗教(特别是人名中的神名元素)这两方面,起到主流作用的传统来源分别是东、西闪米特传统。那么,埃勃拉文化的创造者应被归为东闪米特人,还是西闪米特人?是东闪米特人采用了西北闪米特的某些信仰和文化元素,还是叙利亚本土业已存在的西北闪米特人学习了东闪米特语言和楔形文字?
意大利学者布切拉蒂(Giorgio Buccellati)另辟蹊径,认为在公元前三千纪,作为一个文化—语言—族群概念的“西北闪米特”可能尚未出现,因此“东、西之别”并不存在。他认为,后来被看作“西北闪米特”文化早期代表的亚摩利人在公元前三千纪并不应被看作是一个与“西”这个方位有特殊关联且在语言、民族上已完全区分于其他闪米特人的族群。在自然条件与相应的经济模式的影响下,在乡村生活的闪米特居民可能因为降水不足而在叙利亚南部、东部的某些地区走向半游牧化。同时,乡村生活使他们既从属于某一以城市为核心的政治实体,又与城市的居民和文化逐渐区分开来。甚至他们的语言也逐渐有别于城市居民的语言,从而形成某种“社会方言”(sociolect)而非传统语言上由地域决定影响的方言(dialect)。所谓亚摩利人,就是乡村人,与他们相对应的是埃勃拉、阿卡德等城市中心人口。这两类语言当时并未完全分开,但乡村话更存古。②Giorgio Buccellati, “Ebla and the Amorites,” pp. 98-102.如果布切拉蒂的说法成立,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埃勃拉语里面的所谓“西北闪米特”元素只是尚未分化的北部闪米特(如以阿拉伯半岛为闪米特诸语的“南部”区域)语言的共有特征。这些元素因乡村语言存古而得以保存,而在阿卡德语这种城市语言中则已经消失。如此一来,埃勃拉文化的族群归属背景便应该被归为某种夹杂着乡村语言特征的北部闪米特文化,与“东”、“西”分野并无关联。
然而,尽管布切拉蒂的理论不乏新意,但有一些问题仍无法解释。首先,如果公元前三千纪北部闪米特语言的内部分化不以东、西为界线,而是城乡二元对立,那么不同城市中心之间的方言何以存在较大差距?如上所述,埃勃拉语在词汇方面(介词、动词)以及部分形态学、语音特征上与萨尔贡时期的阿卡德语(也是城市方言)差距颇大。这种差别恰恰属于地域差异而非城乡差异。其次,按照布切拉蒂的逻辑,或许可以推论,既然乡村语言即亚摩利语存古,那么埃勃拉语的“西北闪米特”特征也是因为存古,而存古的原因则是他们受乡村人口(即他眼中的亚摩利人)影响很大。然而,根据埃勃拉文献记载,亚摩利人(在埃勃拉文献中依苏美尔语称为Mardu)在埃勃拉似乎被看作一个位于当今叙利亚中、东部从帕尔米拉向东北延伸到幼发拉底河的政治实体,埃勃拉文献还提到过亚摩利的“国王”。因此,亚摩利人和埃勃拉似乎是分开的两个群体。①Alfonso Archi, “Mardu in the Ebla Texts,” in Alfonso Archi, Ebla and Its Archives: Texts,History, and Society, pp. 353-354.布切拉蒂自己也认为,在埃勃拉内部似乎没有亚摩利人。②Giorgio Buccellati, “Ebla and the Amorites,” p. 85.若亚摩利人在埃勃拉文化中的直接影响不大,那么埃勃拉语究竟为何“存古”而有别于东部的阿卡德语?布切拉蒂的理论未能解答此问题。再次,亚摩利语是否真的存古?实际上,我们对公元前三千纪的亚摩利语知之甚少,大多只能依靠人名来了解。而判断一个人名是亚摩利语还是阿卡德语,有时只能看动词前缀是ya-还是yi-。现存亚摩利人名中缺少前缀加双写第二词根字母的未完成体和明确的、能带宾语后缀变位(人名中的后缀变位区分于动词状态型)。而恰恰是这两种特征的有无,影响着我们对一种闪米特语是否存古的判断。因此,布切拉蒂关于亚摩利语存古的结论,实际上很难证明。③前者被语言学家构拟于原始闪米特语中,可视为存古特征;后者为西闪米特语新起的特征。亚摩利语是否具有此二特征不得而知,因此无法判断其存古程度。见John Huehnergard,“Proto-Semitic,” in John Huehnergard and Naʕama Pat-El, eds., The Semitic Languag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pp. 62-63。感谢芝加哥大学张泓玮博士关于此问题的建议。
综合前文对埃勃拉某些文化特征的归纳,我们不妨可以提出一种更为简明的观点:即埃勃拉等叙利亚城邦和附近的乡镇甚至部分村落的居民就是东闪米特移民,本身就讲与两河流域阿卡德语同源的语言。与此同时,以亚摩利人为代表的西北闪米特人在那一时期已经形成在语言、宗教上别具特色的另一种族群,而叙利亚的乡村地区恰恰就是他们的聚居地。④一般认为,亚摩利人会采用季节性游牧的生活方式。在公元前三千纪末期,随着环境变化,亚摩利人可能涌入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传统城邦(如马里、埃勃拉、乌加里特/Ugarit、比布罗斯/Byblos)并更广泛地接受了定居生活。这一点也得到了考古和文本资料的印证。参见Minna Lönnqvist, “Were Nomadic Amorites on the Move?: Migration, Invasion and Gradual Infiltration as Mechanisms for Cultural Transitions,” in Hartmut Kühne, Rainer M. Czichon and Florian Janoscha Kreppner, eds., Proceedings of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Archaeolog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29 March-3 April 2004,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8, pp. 203-206.经过一段时间的共存和交流,埃勃拉的东闪米特人群在语言、宗教、人名乃至艺术各方面吸收了业已存在的西北闪米特元素。在语言方面,形态变化、句法基本与萨尔贡时期的阿卡德语类似,但词汇层面则有西北闪米特特征,这说明埃勃拉语的本质上是一种东闪米特语。语法和形态变化方面保守,而词汇上广受西北闪米特语影响,这也符合语言接触中借用现象发生的规律。①例如,中古英语接受了大量来自法语的借词,但形态变化则较少受到法语影响。这一点在汉语、日语及汉语、朝鲜语之间的关系上也有类似体现。在语序方面,埃勃拉语和阿卡德语一样以主宾谓为主流(可能受苏美尔语影响)。西北闪米特语(材料多来自公元前二千纪和前一千纪)常用的谓主宾仅偶然出现。参见Michael Streck, “Eblaite and Old Akkadian,” p. 349。这表明西北闪米特语对埃勃拉语的影响并不深入,仅以词汇(名词、动词和部分介词)为主。关于形态和词汇在语言接触中被借用的不同可能性,见Donald Winford, “Contact and Borrowing,” in Raymond Hickey, ed.,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Contact, Malden: Wiley Blackwell, 2010,pp. 175-177。在宗教、人名等方面,非闪米特和西北闪米特元素的影响则更大。②埃勃拉人在语言上保留了祖先的东闪米特语言并吸收了定居地的词汇,而在人名和宗教上则受到本土非闪米特和西北闪米特元素更为深远的影响。这一情形在古代社会的族群迁徙过程中比较常见。比如,公元1000年前后马扎尔人定居于当今匈牙利。至今,匈牙利语言属于芬-乌戈尔语系(Finno-Ugric),被周围的印欧语包围。而在宗教方面,匈牙利早已成为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并随之采用了大量有希腊、罗马、日耳曼、斯拉夫及带有圣经背景的人名。关于马扎尔人的早期定居史,参见Miklós Molnár, A Concise History of Hunga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8-40。这一时期北叙利亚的西北闪米特文化和非闪米特文化,或许是底层文化,或许和东闪米特文化一样属于外来移入的文化,但它们都为埃勃拉等东闪米特文化增添了新的色彩。
五、结语
以埃勃拉城邦为代表的公元前三千纪叙利亚文化为我们展示了地中海东岸地区早期文明的特征。这一时期的叙利亚在文明的基础属性上(语言及部分宗教特征)明显具有两河流域东闪米特文化的特点。与此同时,西北闪米特的特征已经渗透到语言、人名、宗教和艺术等方面,在某些方面甚至起主流作用。本文认为,东闪米特是其族群文化的主体,主要是因为其语言属于东闪米特语。东闪米特语在叙利亚这一后世西北闪米特语通行区的出现,或许因为早期叙利亚城邦曾普遍使用东闪米特语,而后被西北闪米特人群逐步吞没;也可能因为西北闪米特人群早已生活于此,而埃勃拉等城市是外来东闪米特人形成的“语言孤岛”。无论哪种情况,都说明公元前三千纪的埃勃拉居民及其文化源头是和阿卡德居民一样的东闪米特人群。
这一结论并不令人意外。事实上,早在公元前四千纪末,西亚早期文明的发展就与两河流域文明核心区的向外扩张关系密切。在这一时期,两河流域南部苏美尔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同时,为更好地控制远离苏美尔城邦的资源和贸易通路,以乌鲁克(Uruk)为代表的苏美尔政治力量开始向外扩张,在伊朗、两河流域北部、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北部哈布尔河(Habur River)和拜利赫河流域(Balikh River)等地区建立了殖民地和据点。这一波城市化在叙利亚北部持续到公元前三千纪初期结束。①关于叙利亚的乌鲁克殖民地,参见Guillermo Algaze, “The Uruk Expansion: Cross-cultural Exchange in Early 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30, 1989, p. 577。当然,由于在埃勃拉地区并未发现乌鲁克类型的陶器,它应该并非乌鲁克扩张的直接产物。有些学者认为,埃勃拉的初期发展可能源于乌鲁克扩张结束之后叙利亚北部地区于公元前三千纪中期开始的第二波城市化。②Lucio Milano, “Ebla: A Third-Millennium City State in Ancient Syria,” in Jake M.Sasson, ed., Civilization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New York: Scribner, 1995, p. 1220.而促成第二波城市化的因素也可能包括来自两河流域文明核心区的第二波移民。在公元前三千纪中期,操东闪米特语的人群和苏美尔人一样也是两河流域文化元素的传播者,很可能曾经向西迁徙并在叙利亚地区建立了城邦文明。操东闪米特语的埃勃拉就是其代表之一。当然,截至埃勃拉文献所记载的公元前二十四世纪,叙利亚的西北闪米特和非闪米特元素也已成为了埃勃拉文化特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总之,埃勃拉在语言、文字、宗教、人名、艺术等各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考察早期文明传播、政权建立与族群迁移之间关系的经典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