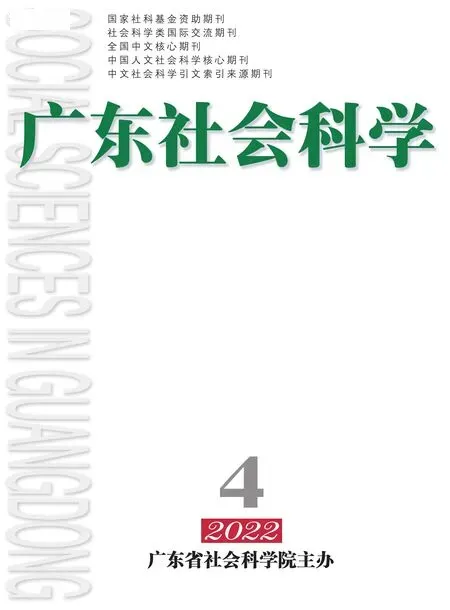清律名例律与六律关系再探析*
2022-02-04雷明波
李 栋 雷明波
《大清律例》(以下称“清律”)作为中华传统法典的集大成者具有完善的结构体系。“它的总体框架是由‘名例律’和‘六律’构成。”①张晋藩主编:《中国古代监察法制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30页。六律即吏、户、礼、兵、刑、工六律。这种体系结构沿袭自明律。明代之前的唐宋律典共分十二律,明朝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刑部请编类颁行,始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律,而以‘名例’冠于篇首。”②《四库全书总目·唐律疏义提要》,司马朝军编撰:《〈四库全书总目〉精华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72页。即明代按照六部官制将唐宋律典中名例律之外的其他十一律改成六律,而篇首则和唐宋律典一样为名例律。
对于名例律与六律之间的关系,长久以来学界将其界定为总则与分则关系,即将名例律与总则进行类比,六律与分则进行类比。这一论断几乎成为通说。①代表性的作品参见张生:《中华法系的现代意义:以律典统编体系的演进为中心》,《东方法学》2022年第1期,第26—37页;曾宪义、赵晓耕主编:《中国法律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42页;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律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97页;郑秦:《清代法律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6—217页。据笔者考证,这种类比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清末沈家本指出“总则之义,略与名例相似。”②沈家本:《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进呈刑律草案折》,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一卷),李秀清等点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62页。清末陕派律学的代表人物吉同钧认为名例律与总则之间虽然名称不同但意思是一样的,其指出“名例者,本刑名、法例之约词……东西各国谓之总则,名异而义则同。”③吉同钧:《大清律讲义》,闫晓君整理,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第1页。可见,这一论断是在变法修律,西法东渐的大背景下形成的,体现着特定时代的历史风貌。
总则与分则的法典编纂体例产生于西方,清末变法修律以来被我国所采纳并延续至今。④有学者认为1751年德国《巴伐利亚刑法典》开始有类似当代总则与分则的体例,这与唐律体例有非常大的相似性,但却跟同时代德国其他刑法典体例非常不同,故而提出一个有待进一步了解的问题:是否有可能,这样的相似性可能来自于当时这个法典的订定者受到传统中国法律包括唐律与《大清律例》的影响?参见陈惠馨:《1751年德国〈巴伐利亚刑法典〉——德国当代刑法的起源》,《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1期,第2—4页。从比较法功能主义上讲,学界长久以来将名例律比作总则,六律比作分则,实际上是在求同,是在努力探求中西方法律文化中的暗合之处,是在努力搜寻古今法律之间的相同之处,以此彰显中国传统法中的优秀之处。这种类比极大地拉进了中国与西方、传统法与现代法之间的距离,揭示出传统法具有某些“现代性”的价值,然而这种直接以现代法类比传统法的研究方法是否能够全面阐释传统法的内容值得我们深思。
因此,将清律中的名例律和六律关系类比为总则分则关系这一近乎“公理”式的论断,我们有必要重新对其进行认真的审思。我们需要审思的是:清律名例律与六律关系与现代法总则与分则关系,是否具有同一性?如果不具有同一性,那么名例律和六律之间的关系又该怎么理解?清代在司法实践中是如何具体处理名例律与六律关系的?哪些是符合现代法总则和分则要求的,哪些是不符合的?对于那些符合的,我们当如何理解?对于那些不符合的,我们又当如何解释?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助于我们全面挖掘传统法的丰富内涵,甚至可以就其中的合理部分通过创造性转化融入当下中国法典之构建。因此,本文将对清律名例律与六律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和全面的审视。
一、名例律六律关系与总则分则关系的相同之处
无可否认的是名例律与六律关系具有类似于总则与分则关系的一面,两对关系之间具有许多相同之处。
首先,按照现代刑法理论,“总则与分则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关系。总则指导分则,分则是总则某些原理、原则的具体体现,二者相辅相成。”⑤《刑法学》编写组编:《刑法学》(上册·总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49页。换言之,总则中的法条是一般规则,分则中的法条是特殊规则;总则中的法条是抽象规则,分则中的法条是具体规则。
从现代法学来看,名例律中有些律条具有总则之义,含有总则性质,发挥着统帅六律的作用。换言之,名例律中的律条具有总则所具有的一般性规则特征。
比如,名例律“加减罪例”条明显是一般规则。六律律条规定了各种类型的“加”“减”,名例律“加减罪例”条就是解释六律律条所言及的“加”或者“减”是什么以及如何进行“加”和“减”的问题。清人王明德指出“律有加减各例,备载正律各条。其类甚夥”,因此名例律“特将加减罪例共分一条,明著律首。”①参见王明德:《读律佩觿》,何勤华、程维荣、张伯元、洪丕谟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217—218页。换言之,名例律“加减罪例”条对六律律条中分散的“加”“减”规则进行集中统一规定,并做了一定的概括抽象。相对于六律律条,名例律“加减罪例”条是一般规则、抽象规则,正所谓“此条系总括各律言加言减之通例也。”②马建石、杨育棠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97页。六律中的“加”“减”规则是该条的具体体现,属于具体规则、特殊规则。
再如,名例律“犯罪得累减”条就是一个一般规则。该条规定了行为人犯罪之后,根据六律规定,有多个可以“减等”的情形时,对犯罪行为人可以“累减”定罪。六律中“减等”情形包括“为从减”“自首减”“故失减”“公罪递减”以及“有因物之多寡而累减者,有因情之轻重而累减者,亦有因名分服制之尊卑亲疏而累减者”③吉同钧:《大清律讲义》,第11页。等。在此,名例律“犯罪得累减”条相对于六律是一般规则,具有普遍性和概括性,抽象提炼出了犯罪行为人如果触犯六律之罪,又有多个可以“减等”的情形时,如何定罪处罚的问题。该条普遍适用于六律中涉及需要“减等”的犯罪。
又如,名例律“称日者以百刻”条规定了“日”“一年”“人年”的计算方法,解释了“众”“谋”的含义。该条普遍适用于六律中涉及上述概念的律条,换言之,凡六律律条中涉及上述概念都需要遵循名例律“称日者以百刻”条规定。因此,名例律“称日者以百刻”条规定的是六律中的共通性问题,该条所关注的是一般性问题,属于一般规则,而六律中的相关律条则是特殊规则。
其次,按照现代刑法理论,“只有把总则和分则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地认定犯罪、确定刑事责任和适用刑罚。”④《刑法学》编写组编:《刑法学》(上册·总论),第49页。在清律的司法实践中,有些案件同样需要将名例律与六律紧密结合才能正确地认定犯罪、确定刑事责任和适用刑罚,即名例律与六律存在着联合适用关系。对此,沈之奇在《大清律辑注》中指出“名例者,诸律之凡例;本条(六律律条——笔者注)者,断罪之正法。律文简要,不欲重述,凡本条有缺而不载者,皆统于名例也。”⑤沈之奇:《大清律辑注》(上),怀效锋、李俊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03页。薛允升在《唐明律合编》中也曾指出“名例为众律之纲领,本律(六律律条——笔者注)赅载不尽者,均统括于名例之内矣。”⑥薛允升:《唐明律合编》,怀效锋、李鸣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761页。通过这两段话可以看出,在有些案件中,因六律缺乏相关规定而不足以完全涵摄案件事实,所以单靠六律的规定不能定罪处罚。此时需要依靠名例律规定弥补六律未涵摄的案件事实。换言之,在有些案件中,六律中的律条与名例律中的律条必须结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律条规范体系,才能涵摄案件事实。因此,司法者需要将名例律与六律联合起来进行适用。
例如,在“金谿县贼犯潘友南等挖窃黄邱氏尸棺衣服、闻拿投首一案”①参见全士潮、张道源等纂辑:《驳案汇编》,何勤华、张伯元、陈重业等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758—760页。中,江西巡抚首先依据刑律“发冢”条将潘友南拟绞,同时又因为潘友南具有“闻拿投首”的事实,然后又依据名例律“犯罪自首”条将潘友南减等拟流。然而,刑部提出不同的审理意见。刑部认为,潘友南“将黄邱氏已埋尸棺挖掘,开棺见尸,暴露尸身,剥取尸衣,系属损伤于人不可赔偿,并不在自首之律。”因此,刑部将该案予以驳回。驳回之后,江西巡抚遵照刑部的意见将该案予以改判,对“潘友南依律改拟绞监候”。对这个裁判结果刑部表示同意。
在清代,判语中时常引照法律,其最明确的方式是将“律载”“例载”作为前置,或者引用条文的一部分,或者引用全部原文。②参见[日]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日)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24页。本案刑部在最终的裁判案件适用法律过程中同样也是引用了清律条文,其指出“查律载‘发掘他人坟冢,开棺见尸者,绞监候。’又《名例》载‘损伤于人不可赔偿者,不在自首之律’各等语,此案潘友南……应依‘发掘他人坟冢,开棺见尸者,绞监候’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由此可见,刑部明确指出了该案所适用的法律包括名例律“犯罪自首”条、刑律“发冢”条。换言之,刑部是将名例律中的相关律条和六律中的相关律条联合起来联合适用,以此来确定行为人的罪与罚。
实际上,江西巡抚的初判同样是将名例律与六律结合起来适用。因为本案案件事实当中行为人有“闻拿投首”的情节,而关于该情节的规定位于名例律中,所以相关规范需要在名例律中寻找。只不过江西巡抚的初判适用的是名例律“犯罪自首”条“至死者,听减一等”③《大清律例》,田涛、郑秦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12—113页。的律文规定,而经过刑部题驳之后,该案最终适用的是名例律“犯罪自首”条“其损伤于人……不可赔偿……并不在自首之律”④《大清律例》,第113页。的律文规定。
综上,针对本案行为人具有“闻拿投首”的案件事实,司法者在适用刑律基础上还需要补充适用名例律“犯罪自首”条,以便能够涵摄所有的案件事实。于是,本案司法者将名例律中的律条和六律中的律条联合起来适用之后,确定了行为人的罪和罚,体现了在清代司法实践中,某些案件需要将名例律与六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能正确地定罪处罚。
最后,现代法总则与分则之间所具有的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使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刑法典总则指导刑法典分则的适用。”⑤曲新久主编:《刑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页。同样清律名例律有些律条具有指导六律律条适用的功能。
比如,在清代“霍邱县民王引割伤继弟王三等一案”⑥参见全士潮、张道源等纂辑:《驳案汇编》,何勤华、张伯元、陈重业等点校,第458—459页。中,刑部指出“查律载‘毒药迷人而未死者,绞监候’;又例载‘雇工人殴家长期亲折伤者,绞监候’,又《名例》内开‘二罪俱发,从一科断’等语,今该抚既讯明王引并未归宗,应照例以雇工人论,应将王引依‘雇工人殴家长期亲折伤者,绞监候’律应拟绞监候,秋后处决等因。”由此可见,刑部就该案如何裁判,首先引用了刑律“造畜蛊毒杀人”条,其次引用了刑律“奴婢殴家长”条,再次引用了名例律“二罪俱发以重论”条。
那么本案中名例律“二罪俱发以重论”条、刑律“造畜蛊毒杀人”条以及刑律“奴婢殴家长”条三者之间适用关系是什么呢?名例律“二罪俱发以重论”条“乃二罪以上一时俱发及先后发拟断之通例。”①沈之奇:《大清律辑注》(上),第84页。即用来指引司法者如何应对“二罪以上一时俱发及先后发”的情形。本案中王引的行为正好属于二罪俱发情形,其罪名涉及刑律“造畜蛊毒杀人”条与刑律“奴婢殴家长”条,到底如何适用这两条?司法者借助名例律“二罪俱发以重论”条“凡二罪以上俱发,……罪各等者,从一科断”②《大清律例》,第115页。律文规定的指引,便能够准确选择适用刑律“造畜蛊毒杀人”条还是适用刑律“奴婢殴家长”条。本案最终选择的结果是对王引适用刑律“奴婢殴家长”条,即对其按照刑律“奴婢殴家长”条“雇工人殴家长期亲折伤者,绞监候”律判处绞监候。本案体现了名例律中有些律条与六律律条之间具有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即名例律指导六律的适用。
二、名例律六律关系与总则分则关系的不同之处
尽管清律中的名例律六律关系存在着与现代法总则分则关系相同的一面;然而,通过对清律立法与司法实践的考察还可以得出,名例律六律关系具有不同于总则分则关系的另外一面。
第一,名例律中某些律条并非一般规则,而是特殊规则。比如名例律“亲属相为容隐”条属于特殊规则,该条规定了亲属之间隐匿罪行减免处罚。按照现代刑法理论,该条是刑律“知情藏匿罪人”条的“但书”。刑律“知情藏匿罪人”条规定的是“犯罪之人,非亲属不得相为容隐。”③沈之奇:《大清律辑注》(下),第977页。对于刑律“知情藏匿罪人”条与名例律“亲属相为容隐”条之间的关系,吉同钧指出“此律与《名例》亲属容隐一条正相对照。”④吉同钧:《大清律讲义》,第251页。沈之奇指出刑律“知情藏匿罪人”条“专言凡人。若系亲属及奴婢、雇工人,则有勿论及减三等、减一等之法,当照名例亲属相为容隐条,不用此律。”⑤沈之奇:《大清律辑注》(下),第978页。从现代法学理论上来看,名例律“亲属相为容隐”条可以说是“知情藏匿罪人”条的除外规定,作用在于排除刑律“知情藏匿罪人”条的适用。因此,名例律“亲属相为容隐”条属于就特别事项作出的特殊规定,解决的是一个具体性问题,并不是总则性规定。
清末在进行变法修律的过程中,改变了传统法典分名例律与六律的编纂体例,采取了西方法典分总则与分则的编纂体例。对此,沈家本在进呈《刑律草案》时曾指出“是编(《刑律草案》第一编总则——笔者注)以刑名、法例之外,凡一切通则,悉宜赅载。若仍用名例,其义过狭。故仿欧美及日本各国刑法之例,定名曰总则。”⑥沈家本:《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进呈刑律草案折》,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一卷),第463页。由这段话可以看出,《刑律草案》总则编既是对欧美和日本刑法的仿效,又是对中国传统法典名例律的沿袭。也就是说清末立法者将《刑律草案》总则编与传统法典名例律进行了类比,既意识到了两者之间所具有的关联性,又认识到了两者之间的不同。这个不同表现在《刑律草案》总则编比传统法典名例律涵盖性更大,总则包含一切通则性规定,要将一切通则性规定都囊括进来,当然也包括名例律所规定的所有通则性规定。因此,总则比名例律包含的通则性规定更多,《刑律草案》采用总则体例也更加合理。为此,清末立法者在仿效欧美、日本刑法的基础上,弃名例而改用总则,并将清律名例律中所有类似于总则性质的规定,通过转化变通规定在了《刑律草案》总则中。
但是,《刑律草案》并没有将名例律“亲属相为容隐”条直接规定或者将该条予以转化规定在总则编中,而是将该条予以变通后规定在了分则编。具体来看,名例律“亲属相为容隐”条转化为《刑律草案》第十一章第177条“犯罪人或脱逃者之亲族为犯罪人或脱逃者利益计而犯本章之罪者,免除其刑。”①沈家本:《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进呈刑律分则草案折并清单》,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一卷),第559—560页。本章从第174条至第177条共有4条。其中第174条规定是由刑律“知情藏匿罪人”条沿革而来。②参见沈家本:《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进呈刑律分则草案折并清单》,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一卷),第558—559页。由此可以看出,刑律“知情藏匿罪人”条与名例律“亲属相为容隐”条都是关于藏匿罪人的特殊规则。因此,若依照现代法典总分则关系,清律名例律“亲属相为容隐”条应该规定在刑律“知情藏匿罪人”条之后。
第二,清律名例律形成机制与现代法总则形成机制不一样。现代刑法总则是在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一些资产阶级刑法学家将刑法分则条文中的共同性或共同点从分则条文中提炼出来,放在刑法条文的最前面,从而形成了现代刑法的总则。”③李晓明:《刑法学总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8页。“所谓总分结构(lex generalis/lex specialis),就是指按照提取公因式的方法(von die Klammer ziehen或von die Klammer setzen),区分共通性规则与特殊规则,将共通性规则集中起来作为总则或一般规定,将特殊规则集中起来编为分则或作为特别规则加以规定。”④王利明:《民法典体系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5页。由此可见,总则的形成机制在于将规则中的共同之处通过归纳总结抽象提炼出一般规则,然后将这些一般规则以总则的形式全部框进来,最后将总则放置在法典之首,也就是说总则法条的形成在于对分则法条共同之处的自觉提炼。实际上,萨维尼在建构当代罗马法体系中“总则”部分,非常详细地展示了这一点。⑤李栋:《萨维尼法学方法论的内容及其展示》,《法治现代化研究》2020年第1期,第168页。
然而清律名例律形成的原因之一是犯罪对象的特殊性,即清律中有些律条之所以会放在名例律,是因为该律条所规定的犯罪对象具有特殊性。比如名例律“十恶”条,该条之所以位列名例律,原因在于“律重纲常,首严十恶。十恶之犯,皆无君无亲,罪大恶极,为天地间所不可容之罪,故特列篇首以昭炯戒。”⑥吉同钧:《大清律讲义》,第4页。因此,清末草拟《刑律草案》时,名例律“十恶”条没有直接规定或者通过转化变通规定在总则中,而是将名例律“十恶”条转化变通规定在了分则中,如将“十恶”条大不敬规定转化变通后分别规定在了分则第一章关于帝室之罪、第十八章关于伪造文书及印文之罪、第三十二章关于窃盗及强盗之罪。⑦参见沈家本:《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进呈刑律分则草案折并清单》,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一卷),第526页。
第三,六律中也有可以适用于全律的一般规则,但并未列入名例律。比如,刑律“妇人犯罪”条规定了关于妇人犯罪后收管问题、孕妇拷决问题、孕妇产后行刑问题的法律规则。“此条是收问之事。”①薛允升:《唐明律合编》,第814页。“乃收问犯罪妇人之通例也。”②沈之奇:《大清律辑注》(下),第1048页。按照现代法学理论,“妇人犯罪”条所规定的这些规则有不少属于一般规则,需要规定在总则中,然而在清律中,“妇人犯罪”条属于刑律之下的一个律条。与刑律“妇人犯罪”条具有高度关联性的是名例律“工乐户及妇人犯罪”条,吉同钧指出两个律条之间“须合参之。”③吉同钧:《大清律讲义》,第282页。名例律“工乐户及妇人犯罪”条包含有“妇人断罪之通例。”④沈之奇:《大清律辑注》(上),第52页。该条“是发落之事。”⑤薛允升:《唐明律合编》,第814页。刑律“妇人犯罪”条与名例律“工乐户及妇人犯罪”条调整对象同为妇人,都属于具有总则性质的一般规则,却一个规定在了名例律中,一个规定在了刑律中。因此,清末草拟的《刑律草案》将刑律“妇人犯罪”条中的孕妇产后行刑规则经过稍微改造后规定在了总则编第40条。⑥参见沈家本:《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进呈刑律草案折》,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一卷),第499—500页。
第四,从近现代刑法总则的规定来看,名例律对散见于六律各种规则之中的总则性规定并没有进行抽象概括而加以规定。比如,《刑律草案》在阐述总则编第17条未遂犯的沿革时指出“现行律所载,有谋杀已行、未伤及伤而未死,强、窃盗未得财、强奸未成等,皆属未遂罪之规定。惟散见各门,并不列诸名例……然此固不应仅属二三种犯罪,实系通乎全体之规则。本案故列于总则之中,欧美各国及日本之法,殆莫不然也。”⑦沈家本:《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进呈刑律草案折》,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一卷),第481页。也就是说,未遂犯规则应该是总则中的一般规则,需要规定在总则中。在清律中,六律规定有谋杀已行、未伤及伤而未死,强、窃盗未得财、强奸未成等各种未遂犯的具体规则,这些规则具有高度关联性,本可以总结出一般规则,进而规定在名例律中,但是清律名例律却没有关于未遂犯的一般规则。究其原因在于名例律并不等同于总则,传统法典的立法者不会自觉的像现代立法者那样以提取公因式的方式将散见于六律中的一般规则都提炼出来,这也是名例律六律关系与总则分则关系的不同之处。
三、经权关系视角下的名例律与六律
由上可知,清律名例律六律之间的关系与现代法总则分则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不同之处,也就是说现代法总则分则关系并不能完全解释清律名例律六律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清律名例律与六律之间是一种经权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圣人之道,有经有权,经者法之常,而权者法之变。”⑧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4页。在传统法领域,“经”即“常”,“权”即“变”,常行法属于“经”,权变法属于“权”。⑨参见高明士:《〈尚书〉的刑制规范及其影响》,《荆楚法学》2021年第2期,第148页。对此,《刑统赋疏》解释道:“先王造律,有正有权。正者,常也,常行之正法。权者,变也,权宜之变法”;“先王之法,有常有变”;“先王立法,有正有变”。①沈仲纬:《刑统赋疏》,沈家本编:《枕碧楼丛书》,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标点,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第184、193、197页。《粗解刑统赋》解释道“一定不移者谓之常。”②傅霖撰:《粗解刑统赋》,孟奎解,沈家本编:《枕碧楼丛书》,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标点,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第145页。由此,经强调的是常行,正法;权强调的是一时,权宜,变法。正如明太祖朱元璋所言:“法令者,防民之具,辅治之术耳,有经有权。律者,常经也。条例者,一时之权宜也。”③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480页。在此,朱元璋指明了明代律与例这两种不同的法律形式之间具有经权关系。清律名例律与六律之间同样也存在着经权关系。
清人王明德在《读律八法》中指出“贼盗、人命、斗殴三篇所著,动关生死,固为律中要领。而名例一篇,更为吃紧纲维,乃所以运用全律之枢纽,轻重诸法之权衡,愈为要中至要。”④王明德:《读律佩觿》,第2页。贼盗、人命、斗殴三篇在清律中属于六律中的刑律。这三篇固然重要,但是名例篇更加重要,具有六律枢纽地位,而名例律之所以具有枢纽地位,原因在于名例律是“轻重诸法之权衡。”申言之,名例律与六律之间是一种“权衡”关系,对此如何理解?王明德进一步阐发了名例之义,其指出:
名例之义何居乎?……故为之简其名,核其实,撮其要,尽其变,分其类,著为四十八条,冠于律首以统贯夫全律。而于正律各条所未备,则采故明历朝令行之可因者,别之为条例,并列于正律各条之后,以辅正律之穷而尽其变……乃律中,采疏议所注,于名例二字,止注曰:名者,五刑之正名,例者,五刑之体例,未免有举一遗百之谬。而愚则以名者,五刑正体变体,及律例中,人所犯该,以及致罪各别之统名。而例,则律例中,运行之活法,于至一中,寓至不一之妙,更于至不一处,复返至一之体。举凡宽猛竞絿,权变经常,无不备为该载。所谓权而不离乎经,变而不失于正,是盖轻重诸法之权衡,一定不移之矩矱也。⑤王明德:《读律佩觿》,第19—20页。
从王明德所阐发的名例之义中可以看出,清律以小注的形式对名例注释为“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体例也。”⑥《大清律例》,第80页。然而王明德明确地指出清律对名例的这个注释并不全面,有挂一漏万的错误。其认为名例律是“轻重诸法之权衡”,因为名例律是律例之统名,律例之活法,包括宽猛竞絿,权变经常。宽猛竞絿说的是名例律律条的轻重,权变经常说的是名例律律条的分类,其中一类是权变法,另一类是经常法或者说是常行法。申言之,相对于六律而言,名例律既是经常又是权变。换言之,针对不同的六律律条,名例律律条或是六律律条的经常,或是六律律条的权变,名例律与六律之间具有经权关系,而且两者之间互为经权。同时根据王明德的阐述,名例律与六律之间的经权关系可以说是“权而不离乎经,变而不失于正”,也就是说,六律之权变法并没有背离名例律之常行法,当然名例律之权变法也不会背离六律之常行法。
名例律与六律之间的经权关系首先是指名例律为经,六律为权,即名例律律条为常行法,相应的六律律条为权变法。
比如,名例律“五刑”条所规定的刑罚与六律律条所规定的刑罚之间构成经权关系。清律名例律“五刑”条并未囊括六律所规定的所有刑罚。名例律“五刑”条只规定了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除此之外,并没有规定其他种类的刑罚。然而清律六律中又有很多律条规定有除五刑之外的其他刑罚,如刑律“谋反大逆”条、刑律“杀死奸夫”条、刑律“奴婢殴家长”条等规定有凌迟,户律“盐法”条、兵律“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条、刑律“强盗”条等规定有枭示,刑律“谋杀祖父母父母”条规定有戮尸。按照《读律佩觿》的解释,六律刑罚规定与名例律五刑规定产生不一致的原因在于名例律与六律之间的经权关系。对此,《读律佩觿》阐述到:“按五刑正目,自汉景以后惟止笞、杖、徒、流、死而已,是以名例特冠其例于首,以明刑之为法各有其正。虽云五者之外,仍有凌迟、枭示、戮尸等类,初非国之常刑,要皆因时或为一用者,终不可以五刑之正名。故止散见于律例各条中,或备著乎律例各条外,卒不得与五刑正目同俦而并列。”①王明德:《读律佩觿》,第135页。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名例律五刑由来已久,属于国之常刑,是常行之正法,所以要置于律首,名例律五刑之外六律中的凌迟、枭示、戮尸属于一时之法,是权变法,不能与五刑并列于名例律,只能散见于六律各条。也就是说名例律“五刑”条属于经,六律相关律条是权,名例律与六律构成经权关系。
名例律与六律之间的经权关系其次是指名例律为权,六律为经,即六律律条为常行法,相应的名例律律条为权变法。
在传统法中,常行法往往会因“情”而变通为权变法。比如,“凡以物大小论罪者,法之常也;以情之轻重为罪者,法之变也。”②沈仲纬:《刑统赋疏》,沈家本编:《枕碧楼丛书》,第202页。又如,“流宥鞭扑因罪之轻重而定之,法之经也;眚灾怙终因情之轻重而酌之,法之权也。经者,立乎常法之中,权者,行乎常法之外。”③奕䜣:《乐道堂文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1页。
对于“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宫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这五句,朱熹认为“宽猛轻重各有条理,法之正也。”对于“眚灾肆赦”“怙终贼刑”这两句,朱熹认为“或由重而即轻,或由轻而即重,犹今之律有名例,又用法之权衡,所谓法外意也。”④朱熹:《朱子全书》(第23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167页。在此,朱熹将“眚灾肆赦”“怙终贼刑”比作名例律,而“眚灾怙终因情之轻重而酌之,法之权也。”即“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属于权变。申言之,名例律为法之权,即权变法,这是相对于六律而言。因此,六律律条相对于名例律律条来说也有可能是常行法,属于经,这也导致了名例律不全是一般规则,存在着特殊规则。因为以现代法为视角,常行法多属于一般原则、一般规则,权变法多属于具体原则、特殊规则。当然,常行法和权变法也有可能同属于一般原则、一般规则,或者同属于具体原则,特殊规则。
比如,名例律“亲属相为容隐”条以现代法学理论来看,应该属于特殊规则。从传统律学理论来看的话,“亲属相为容隐”条就是权变法,相应的刑律“知情藏匿罪人”条为常行法。刑律“知情藏匿罪人”条主要是禁止容隐藏匿罪人,这是常行法,但是亲属之间如果还是按照刑律“知情藏匿罪人”条规定的那样,要求知情亲属相互揭露、抓捕犯罪亲属,就会违背亲属之间的“恩义”之情,可以想象的是亲属之间的“恩义”将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知情揭露犯罪的法律规定“当随情而通变,使轻重得宜而已矣。”①佚名:《别本刑统赋解》,沈家本编:《枕碧楼丛书》,第160页。因此,清律以“本乎人情,原乎天理”②沈之奇:《大清律辑注》(上),第99页。的法律精神,权衡“恩义”轻重,在名例律中专设亲属之间可以相互容隐罪行的律条,即“亲属相为容隐”条。对于该条的权衡之义,吉同钧给予了高度评价,其指出“本律之义是寓情于法,使恩义不相妨也……此皆权恩义之中而教人以亲睦之道。”③吉同钧:《大清律讲义》,第35页。如此立法,刑律“知情藏匿罪人”条与名例律“亲属相为容隐”条被适用于不同身份之人。刑律“知情藏匿罪人”条“专言凡人”,④沈之奇:《大清律辑注》(下),第978页。适用于一般身份之人,属于常行法、正法,名例律“亲属相为容隐”则适用于“亲属之间”的特殊身份之人,属于权变法。
结 论
在近代西方法律科学的影响下,通过“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将法典在结构上分法典为总则编和分则编,成为一种潮流与趋势。相信不久的将来,行政法、环境法等领域可能会有更多坚持“总则分则结构”的法典陆续出台。在此背景之下,冷静地反思一下我国传统法典如清律分名例律与六律的编纂体例实有必要。
从类型学上讲,清律名例律与六律之间的关系复杂,与现代法典总则分则关系并非完全一致。现代法典总则在本质上是一种法律科学意义上、通过体系化建构而编纂的,其侧重于“自下而上”的抽象和提炼;而传统中国法典中的名例律侧重“自上而下”司法的适用,关注于如何具体地实现“罚当其罪”。尽管如此,清律名例律与六律之间的关系还是可以与现代法典总则分则之间的关系进行类比。但是对这种类比需持谨慎态度,既要看到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更要清楚地认识到两者之间所具有的不同。
如此可以通过古今比较的方式准确把握清律名例律与六律之间的复杂关系,挖掘出名例律与六律关系背后所折射出的固有法文化的特殊意义。一方面,清律名例律与六律之间的关系确实可以借助总则分则关系理论来把握理解,进而帮助当下研究者理解清律的规则体系和清代司法实践活动。另一方面,如果看不到两者之间的不同,直接用总则分则关系理论来解释清律的规则构成、体系以及清律的适用,就会发现清律中的很多规则以及有些司法实践活动无法得到解释,甚至出现对清律的解读错误。因此,清律名例律与六律之间具有一种区别于现代法的独特性关系,即经权关系,而且两者之间互为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