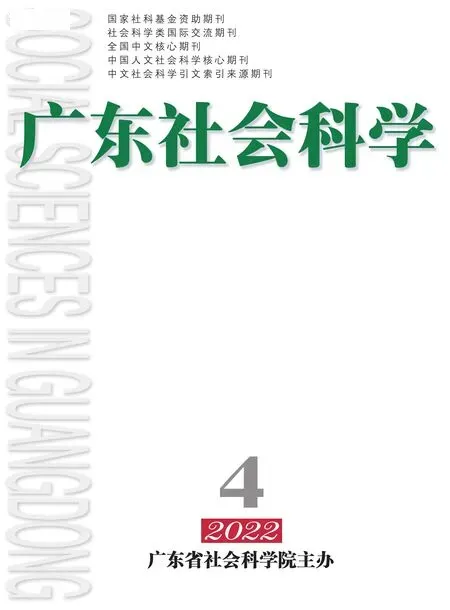甲午前晚清官绅“商务”观的嬗变
——以晚清域外日记为中心*
2022-02-04杨汤琛
杨汤琛
前 言
农耕文明源远流长的古典中国,重农抑商可谓根深蒂固的主流意识形态,早在先秦时期,孟子、商鞅及韩非等重要思想家均主张抑商,孟子有义利之辨,商鞅认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①《商君书》,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77页。;韩非将工商业者列为“五蠹”之一;战国晚期,荀子总结诸国求强的措施即为重农抑商,“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民时,如是则国富矣。”②《荀子》,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41页。西汉尊崇儒术,以商为贱,如《史记·平准书》所载:“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③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182页。“重农抑商”自此成为一以贯之的基本国策。至甲午之战后,上述观念才得以根本扭转,重商思想方才超越抑商观,并在制度层面得以确认。专攻近代经济史的学者朱英即撰文指出,甲午后,中国商人地位得到实质性改变,中国第一次真正出现了重商思潮①朱英:《甲午战后清政府经济政策的变化与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新政”期间,清朝廷专门设立商部,大力支持商会的建立,1903年,光绪帝下旨将商务定位为经国之要政:
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总期扫除官习,联络一气,不得有丝毫隔阂,致启弊端,保护维持,尤应不遗余力,庶几商务振兴,蒸蒸日上,阜民财而培邦本,有厚望焉。②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013页。
由此,晚清重商观念在制度上得以保证,成为基本国策之一。
晚清近代商务观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事实上,思潮的变迁自道光时期就已汹涌,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所构成的压倒性挑战以及利权的丧失,让不少有识之士痛定思痛,魏源、冯桂芬及王韬等纷纷著书立说以探索富强之道,如冯桂芬即撰《校邠庐抗议》,指出“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③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57页。然而,西方诸国如何富强,其富强的实施途径与操作方式究竟如何?其言说承续的仍是传统经世、事功之固有思路,有关西方商业的论述仍是雾里看花;而自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遣使西洋考政问学,晚清官绅得以远涉异国,实地体察西方商务制度、感受西方经济生活,由此,有关西方诸国的富强认知不再是纸上得来的辗转言说,转而化为切实的商务观念与商业意识,他们出使日记中的商务书写亦清晰地展现了晚清官绅如何从蒙昧走向开明,如何更新商务观念、接纳近代商业意识的思想线索。
从最初奉命出洋的斌椿、志刚及孙家榖,到稍后出洋的郭嵩焘、薛福成等,这批晚清官绅获得了中西比较的视野,随着时代的推进与洋务运动的兴起,他们的商务观发生了鲜明的变化,并不断自我突破,生成了相对先进的近代商务思想,为甲午后的重商思潮奠定了有力的基础。第一阶段当为19世纪60年代,以斌椿、志刚为代表的首批持节海外的使者,虽然见识了西方现代商业文明,但是仍然持传统抑商观念,他们的商务书写呈现了清王朝庸常官僚保守的心理图式;第二阶段为洋务运动大兴的19世纪70年代至甲午之战前,以郭嵩焘、薛福成等开明官绅为代表,他们亲沐欧风美雨、怀持变革之意,其观念形态、思想意识在以往经世思想之外,对传统商务思想框架有所突破,主要呈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强调以商务为本,深化了国内的重商思想;二是在比较视域下对洋务运动的商务机制加以反思,引发了一系列的观念变革;上述突破加速改变了权力阶层对于商务的再认知,他们与国内维新人士的商战说相应和,有力地促使了晚清整体商务观的近代转型。
一、传统意识拘囿下的商务观
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自1866年始,清政府络绎遣使出洋探其利弊,斌椿(1866)、志刚(1868)、张德彝(1866、1868)、孙家糓(1868)作为遣使初期的出洋官僚,自东往西,历经香港、新加坡而至西欧,遭逢了异域风物,也遭逢了迥异于农业文明的资本主义工商文明的新图景,不仅香港、新加坡等昔日荒蛮之地已摇身变为商舶云集的贸易巨埠,英、美等国更是处在资本工商业欣欣向荣的扩张之途中。然而,这批早期出洋的官员目睹西方商务之扩张及其利害,虽然有所触动与提及,但拘囿于个体见识、传统意识的牵绊以及国内尚未形成气候的商战论,他们对于近代商务的认识与理解仍徘徊于浓厚的传统阴影之下,由此,较之浓墨重笔所书写的西方器物文明、民俗风情等,商务事宜往往被一笔带过,或被置于批判的位置。
开洋之初,对于乘槎远行的使臣而言,首要之务是为朝廷探察虚实,源于个体见识以及开洋之初的茫昧意识,这批出洋官员大多走马观花,域外凡有所见,多揽入文中“以资印证”,热衷于对异域风俗、近代工业器物(奇技)等巨细无遗的描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图景下的商务运作逻辑以及商务观则尚未被有效纳入书写范畴。斌椿的《乘槎笔记》除了于寥寥两处一笔带过荷兰国“贸易之盛”外,基本没有留意西方诸国的商务现状;张德彝于1866年、1868年两次随使出访欧美列国,津津乐道于各国风俗人情,精雕细琢于火轮车等工业器物,对欧美经济的关注却只局限于技术方面的钱币浇铸之法,显然,西方的商务理念与运作方式还没有进入他的关注视野,换而言之,较之火车、机器等被视为亟待师法的“夷技”,商务的战略地位与重要性还没有被斌椿、张德彝一类普通官僚所认知。
一旦涉及对西方商务的价值性认知,这批出洋官员则浮现出抑商轻利的顽固的心理图式。斌椿在回应西人有关中西比较问题时,以冠冕堂皇的语言对义利与中西之别进行了一番高下比较:
答以我圣教,所重在书礼;纲常天地经,五伦首孝悌;义利辨最严,贪残众所鄙。①斌椿:《天外归帆草》,《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202页。
中国文明体系中的纲常、五伦成为预设的唯一标准,它承续了千载而下的孔孟之道,可谓不可动摇的真理,其中,斌椿特别指出“义利辨最严”,从义利层面对文明高下进行辨别定位,所谓义利之辨也是儒家的经典言说,如孔子所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②《论语》,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43页。将利与道德匮乏的小人进行意义对接,利相对于义而言,沦为违反了伦理道德的末端,逐利之人则为丧失了道德性的小人;延续孔子思路,孟子亦强调,“何必曰利,惟有仁义而已矣。”③《孟子》,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页。直接将利排斥于儒教伦理规范之外。孔孟两位圣人的义利之辨为中国士人的“崇本抑末”说定下了固定的伦理基调,承续这一价值标准,斌椿指出“所重在书礼;纲常天地经,五伦首孝悌”,④斌椿:《天外归帆草》,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203页。纲常成为至高无上的“圣教”,而与“义”相对应的“利”(诗中暗指西方发达的工商业)则是中土文明所排斥的“贪残众所鄙”之类,西方由此被定义为尚奇贪利之地,在国运黯淡、强邻交迫之际重申传统伦理,并据此将西方归于道德范畴内被歧视的类型,这自然为国人制造了可以依傍的强大的精神幻觉。
较之斌椿、张德彝走马观花的游历,志刚作为首位正式出访的使臣,不得不卷入与有关西方商务的外交实践活动之中,英国访问期间,有洋人来与他商议山东开矿事宜,志刚却婉言谢绝,在他看来开矿谋利招致社会动乱,与其谋利不如谋求安定,“诚以无业游民易聚难散,中国人烟稠密,始见为利者,不旋踵而大乱随之。…………乃又告以中国断不能希小利而开大乱之端也。”⑤志刚:《初使泰西记》,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296页。可见,对于商务之利,志刚是保守乃至抵制的,指认逐利为大乱之端,这一思路可谓与传统抑商思想一脉相承,西汉名士晁错曾向汉文帝进言,商人的社会流动性对国家稳固而言存在极大隐患,因为商人“不农则地不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①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31页。显然,以农为本的传统社会结构依赖于官民之间稳定的二元结构,附着于地的农民是兵役与徭役稳固的提供者,而商贩游离于这一稳定结构之外,是可能带来离心力的异己分子,因此,逐利的商业与商人始终是大一统社会的统治者排斥的力量。正因怀揣保守的商务观,志刚于域外游历期间,不仅忽略西方商务实况,还孜孜不忘以朝廷大臣的身份向海外华商反复强调纲常五伦:“尚望尔等虽属寄迹遐方,尤当希作贤良,且存中国之体面,无忘中国历代圣贤流传之教。五伦不可紊,五常不可离。”②志刚:《初使泰西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页。在这里,志刚将圣贤之教与中国的“体面”尊严牢牢联系在一起,五伦、五常等伦理规范成为绝不可偏离的文化准则。
由19世纪60年代的官绅域外书写可知,普遍官僚仍拘囿于传统意识藩篱之内,并没有因为西方经验的进入而幡然醒悟,这一凝滞的书写形态离不开彼时社会的总体意识,即鸦片战争虽然导致清王朝“利权”丧失、民生凋敝,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刺激了一批敏锐的官僚与士大夫倡导商务,面对岿然庞大的传统惯性,魏源、冯桂芬等开明官绅有关重商的言论仍然势单力薄,他们的呼吁尚未在社会形成声势,近代商务的观念形态以及价值尚未被普遍官绅阶层所理解与接纳。
二、“以商为本”与商务观的深化
19世纪70年代正是洋务运动大兴之时,洋务派在追求“强兵”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求富”的重要性,如王尔敏所论,“就图强一念出发,深入进展,加以西方列强现势之导向,工商竞争之压力,中国思想理论与行动,终必自然循行求富一途。”③王尔敏:《中国近代之自强与求富》,《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01页。源于上述思路,商务逐渐引起朝野重视,洋务派率先开始了官督商办的经济变革;与此同时,“商战”作为一种强国策略开始为一批先进官僚与士人所宣扬,曾国藩、李蟠提出了“以商敌商”的对策,郑观应于《盛世危言》宣扬“商战”,重商主义思潮逐渐弥漫于朝野,这一背景下,19世纪70年代出洋的使臣不仅浓墨重笔书写西方商务,更因西方商务的考察而发生了“以商为本”的观念深化。其中,郭嵩焘、薛福成作为有影响力的开明士大夫可谓这一阶段的代表。目前,学界对郭嵩焘、薛福成的商务观的研究,多有探讨,并渐成规模。近代史专家蒋廷黻于《中国近代史》指出“他(郭嵩焘)努力研究西洋的政治经济社会”④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年,第41页。,虽然限于史论的篇幅没有详细展开论述,但强调了郭嵩焘与西洋经济的关联;随后,张良俊、吴义雄等学者均探讨了郭嵩焘的“富强观”,指出其重商主义思想在价值观念层面的革新意义;但是,相关探讨较少结合郭嵩焘的域外经验进行剖析。薛福成的商务思想则是薛福成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诸多学者对其重商富国论都展开过详细论述,强调其作为洋务改革派在近代工商业的贡献与影响;其中,钟叔河先生于其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之《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的前言,就薛福成出使期间对西洋经济的认知作了详尽的介绍,并强调“当然,薛福成洋务思想的核心始终是重商。他出国以后,在考察商务、了解商情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认识也较过去大有提高”①钟叔河:《从洋务到变法的薛福成》,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35—36页。。钟叔河的洞见有力启发了后来者的研究。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域外经验引发观念变迁的角度,来综合分析郭嵩焘、薛福成这类具有变革意识的士大夫在走出国门、体验西方近代经济文明之后,所发生的商务观的深化,以期在经验变迁与观念嬗变的关联点上寻绎其思想演变的线索。
郭嵩焘出洋之前便以“精熟洋务”而闻名,出使英法期间,其近代商务观更趋成熟,于广泛考察各国工商机构与商贸活动后,郭氏明确指出商务意义重大,为西洋立国的根本,“西洋以行商为制国之本,其经理商政,整齐严密,条理秩然,即在中国,往来内江船主皆能举其职,而权亦重,优于内地官人远矣,宜其富强莫与京也。”②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56页。在郭嵩焘看来,西方成熟的商务制度奠定了强国的基础,指认西洋立国之本为商务,而不为“道”或者“农”,这是源于现实考察所得的结论,更重要的是,郭嵩焘将之与中国现状进行对照,商务优劣与富强与否昭然可见,商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见,郭嵩焘急欲对照西洋商务来改变国内的商务现状,为“商务”位置打造上升空间。
稍后出使的薛福成作为曾门弟子,承祧曾国藩的商战思路,出洋前即作《筹洋刍议》阐释“商政”思想,积极主张“筹洋”“变法”,只是薛福成此时尚未亲睹西洋商业之利害,这类破格之论仍不离“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物周孔之道”的传统意涵,不脱儒家之经世思想,而其“商务”观的真正转变与深化则离不开域外经验的刺激,经过一系列西洋商务考察,他形成了“以商务为本”的观念,于出使日记内指出:“欧洲立国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借于商,而尤推英国为巨擘。列国虽欲与之颉颃争衡,而终不及其心计之工规模之远也。英与法最近,其通商亦与法最先。”③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第210页。途径香港、新加坡等地,薛福成见“洋人借经营商务,辟荒岛为巨埠”,返身将笔锋指向中国现状,从中西比较的视域下对中国“重农抑商”的传统迷思进行重新检讨:
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此其理为从前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而外洋创此规模,实有可操之券,不能执中国“崇本抑末”之旧说以难之。……若居今日地球万国相通之世,虽圣人复生,岂能不以讲求商务为汲汲哉!④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第82页。
薛福成指认“商”足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带活了士农工,是掌控四民之纲要,这一论调与传统经济思想大相径庭,农耕文明源远流长的传统下,农业向来被视为国家根基之所在,如郑板桥所叹“农夫上者种地百亩,其次七八十亩,其次五六十亩,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⑤郑燮:《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郑板桥集》,太原: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177页。。薛福成因域外之所见闻,大胆冲破了“农本”观,鼓吹商务为国之命脉、民之纲要,积极转向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薛福成在鼓吹“商务”的同时,还着意破除“义利之辩”的成说,为提升“商人”的社会地位摇旗呐喊:
中国用人以富者为嫌,西俗用人以富者为贤,其道有相反者。夫登垄断以“左右望而罔利市”者,谓之“贱丈夫”,中国数千年来,无愚智皆知贱之……贬之曰铜臭,斥之曰守财奴,中国之习俗然也。泰西各国最重议绅。议绅之被推选者,必在殷富之家。……至其选为各部大臣及宰相者,非殷实之世爵,即富厚之名人,其意意味彼皆不忧衣食,专顾体面,未有不竭诚谋国者。……非极富则不能为上等之学问,非极富则不能交上等之朋友;况复囿于见闻,牵于衣食,其不能开拓胸襟也,审矣。若夫豪杰之士,非以财助之,不兴也。盖“有恒产即有恒心”者,吾于泰西风俗见之。①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第772页。
薛福成于字里行间力图破除轻商、嫌富的老观念,并大力介绍西方“以富者为贤”的社会风俗,对西方富人治国详加描述、津津乐道,此番述评显然针对“义利”观辖制下晚清社会现实,虽然洋务运动时期出现了商业鼎盛的局面,各类官方工厂纷纷开设,商业获得了一个相对繁荣的空间,但是在思维意识及其政策层面,“商”的地位并未发生明显改变,重臣李鸿章力推洋务,却认为,“与其病农,莫如病商,犹得古人重本抑末之义。”②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第6卷,影印本。商务以及从商之人一直在社会空间难以获得尊重,钱穆感慨,“汉代有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之事,此种限制,直到清代,还是时时变相出现。”③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31页。因此,才会有清末士人叹商人地位频遭轻贱的愤懑,“外国之富商大贾,皆为议员,执政权,而中国则贬之曰末务,贱之曰市井,不得与士大夫伍。然一旦偿兵费赔教案,甚至供玩好养国蠹者,皆莫不取资于商人。……然则中国之商人,不过一供给财用之奴隶而已。”④佚名:《说国民》,《国民报》1901年6月10日。在彼时轻商、贱商的社会总体意识下,薛福成强调商务为立国之本,着力描述商人治国的诸多好处,由中西比较而引发对“义利之辩”思想的批判,对贱商习俗的反驳,上述种种溢出传统之外的论述不仅带来了现代重商思想的发展,更意欲从政治层面肯定商人的地位与价值。
针对商业以及商人的不平之鸣自明清以来就不绝如缕,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财计》篇曾反驳世儒的抑商论,顾炎武、王夫之均力倡“富民”,他们貌似激进的论调主要从“不平”的消极层面展开,如余英时所论“这时的儒者已不再寄望于朝廷积极地有所作为,而是要求政府不对民间致富的活动加以干扰。”⑤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1页。薛福成、郭嵩焘等官绅的“商本”思想已逾越了明清以来隐约流布的“富民”思潮,而从积极的层面肯定商务对于国体的根本作用,将商务提升至国之纲要的位置,津津乐道于视商人为国家要臣的西方制度,这可谓商务思想的一大跃进,它与国内波澜初起的商务运动以及商人的权利要求相促进,有效促进了晚清近代商务观的深度发展。
三、商务反思与观念变革
西方内部经济、文化的编码方式与清王朝内部迥然不同,特别进入19世纪之后,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形成了成熟的运作模式,“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6页。与之相对,晚清洋务运动时期,虽然“商战”的呼吁日益高涨,官督商办企业成为一时的富国强兵之计,如1872年上海轮船招商局成立,1877年滦州开平矿务局建立,1882年又设上海机器织布局,“到甲午战争之前,民用企业总数已达40个以上。”①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21页。但是,上述商务事宜由于处于草创阶段而罅隙多多,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工商体系与制度千疮百孔,产生了种种弊端,如颇具规模的官办工厂不脱官督商办的腐朽习气,清政府对民间商务设置了种种限制,甚至与民争利等。对商务素有研究并亲历西洋资本社会的郭嵩焘、薛福成等,于游历期间详细考察了西方税收、招商局及私人公司等商务运作模式,由此及彼,在中西比较视野下,针对国内具体的商务政策、商务制度展开反思,由此触及了勾连商务体制背后的一系列的意识形态结构(如自由竞争思想、民主理念),引发了富于挑战性的、更深层次的观念变革。
纵观洋洋百万字的《伦敦与巴黎日记》,郭嵩焘数十次讨论了西洋各国的税制,并进行了抽丝剥茧式的剖析,如详尽分析了关税税则、关税种类乃至酒税、房租税等;他路过殖民地锡兰,又具体比较了英国、荷兰两国经济殖民政策,对英国与民同利的政策大力褒扬,“惟务通商贾之利,营立埔头,使其人民有居积之资,交易数万里,损益盈虚,皆与国家同其利病,是以其气常固。”②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52页。相形之下,荷兰“专事苛敛”,对附属国征以重税,所以属国不服,常有争端。郭嵩焘藉此表达了对重税的反对,提出还商于民的思想,他于出使日记特意谈及商与民之间的有机联系,将商务扩张与“养民”“民利”进行对接,“中国要务在生财,宜以开采制造等事委之于民,而官征其税。”③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561页。这一主张委利于民的商务观,自然脱离了洋务运动时期普遍存在的官督商办理念,隐然指向西方民主制度下自由主义经济观。郭嵩焘为此专门在日记中引录英人对中国招商局的讥讽,对官督商办的批评之意溢于言表:“连日《代模斯》新报讥刺中国,深中腠理,直谓相沿制度及各衙门所办时间及官人德行,相习为欺诈已数百年。所以招商局半官半商,无所主名,未见其利,先受其累,终无能求有益处也。阅之叹息而已。”④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823页。主张官商分离、还商于民,其背后已然是亚当斯密所崇尚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思想,代表了新兴经济力量的精神诉求。
西游经历下,郭嵩焘对英国税制屡有激赏,他于光绪三年九月廿九日的日记以几千字的篇幅详尽介绍了英国税制,“约分四款:一曰食用项下之税,二曰过印项下之税,三曰产业项下之税,四曰入息项下之税。”⑤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350页。其中,郭对印花税与息税又进行了阐释,其篇幅之详尽可堪为国内税制的镜鉴。郭嵩焘还追溯英国税制成功的原因,指出宽松的税收为商业发展带来了广阔的空间,“英国课税惟茶、烟、酒三事,馀则听商人营运,无税则,而岁计各家所入,每金洋一磅纳佩宜八(约八十分之一)”,并借刘云生之口道出英国政治制度与税制的内在关系,“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固也。”⑥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156页。这一出位之识将商务问题的症结指向政治体制,它对于当时仍处于云遮雾绕下的晚清税务筹划而言不但新鲜且更具现实挑战性。
随后出洋的薛福成则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公司制度的运作力量“西洋各国之所以致富强者,以工商诸务之振兴也。工商诸务之无阻,以各项公司之易集也。”⑦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第575页。并以上海商业公司为例,检讨中国商业制度的缺陷,“无如任事者既未深知此种利病,措注不能中窍,甚者恣其挥霍,亏负累累,未一二年而入股者之资悉化为乌有。…………余谓中国公司之不举,半由人事,半由气运。虽小端而实系全局。呜呼,时事之岌岌如此,安得有大力者出而一转移之力也!”①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第575页。上述尖锐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薛福成源于对西方现代技术与现代运作制度的认知,更容易从外部看清中国商务的弊端,他不再满足于旁观者与阐释者的身份,而怀揣变革意图,开始以“介入”的姿态来指正百弊丛生的中国商务。
郭嵩焘、薛福成等晚清官绅所关注的西方各类商务活动以及运作模式,自然会涉及一系列西方现代商业实践中的核心思想,比如资本主义自由经济观、近代管理理念等,无可避免地会促使一系列针对国内商务的反思如商人的边缘化位置、官商督办的弊端等,无疑,这不仅只是“用”的层面对中国商务进行具体指摘,同时,也是“体”的层面的动摇与削弱,它会撼动惯性的传统意识,并藉此引入一系列近代观念,正如列文森所分析的“已为士大夫所接受的西‘用’,腐蚀着士大夫的思想,并最终将使他们失去对儒学之不可或缺的完整性的信仰。被西方人所使用的西‘用’,通过鼓励一种新的社会选择,即选择商业-工业生活方式,对中国士大夫的生活方式提出了挑战。这种生活方式不仅使儒学越来越变得不合时宜,并且使儒家的约束力(像家族背后的那些约束力)也越来越受到削弱。”②[美]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1页。
结 语
从文化比较视野来看,对西方的商务考察促使晚清官绅于中西比较的维度下对商务的意义及其作用展开深入思考,重审中国的商务观与商业运作方式,从借鉴与反思的角度有力推动了近代商务观在晚清的发生、发展。甲午之后,近代资本主义形态的商业观凸显为社会的主流思潮,商人的社会地位亦随之迅速提升,时人曾感叹:“中兴名臣曾国藩仅赏侯爵,李鸿章不过伯爵,其余百战功臣,竟有望男爵而不可得者,今以子男等爵,奖创办实业之工商,一扫数千年贱商之陋习,斯诚稀世之创举。”③杨诠:《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东方杂志》1911年第8卷第7期。同时,商部的设立、商律的颁布意味着商务在清朝廷得到了制度性保障,这均意味着近代商务观在中国的确立。以晚清官绅的域外日记为途径对这一观念变迁史进行观察,使我们认识到,中国近代商务观的确立是经过了一段曲折的酝酿过程才臻于成熟的。
近代商务观的成熟不仅意味着包涵了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因子的经济方式在清末普遍生成,它还成为导致传统伦理秩序解体的主要力量,陈寅恪即将清末以来三纲六纪的崩散归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致变迁;纲纪致说,无所凭依……”④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6—7页。经济的变化从根本上导致伦理纲常等意识形态的变化,晚清商务观的变化亦可谓近代一系列变化的基本动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