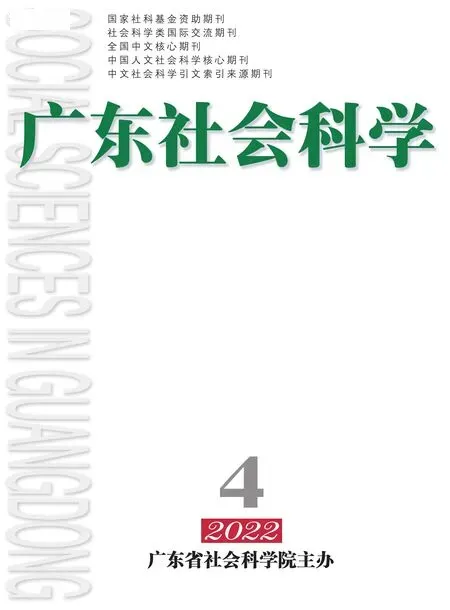中国近现代教育中的“白话文运动”及意义*
2022-02-04张卫中
张卫中
在中国近现代语言变革史上,文白之变是实现言文合一的主要选项,也成了解决文字学习难的主要路径。“五四”前后,因为文学在中国文化中占有突出重要的位置,同时胡适、陈独秀在文学中发起的白话文运动一呼百应,产生了很大反响,因而文学中的文白之变受到了更多关注;以至于很多人以部分代整体,将文学中的白话文运动等同于此期整体的白话文运动,认为只有文学中出现了白话文运动,其他领域的文白之变都附属于文学,是在它的影响下产生,没有独立的意义。而实际上,变文言为白话是当时社会的一个总体要求,它是在多个领域同时发生。在中国近现代教育中,因为文言与近现代教育的宗旨、体制存在根本矛盾,它很早就产生了使用白话文的要求,教育领域中的文白之变有自己独立的动机和谱系,是一场独立的白话文运动,它与文学中的白话文运动互相促进,并不存在谁依附谁的问题。从这个角度上说,“五四”白话文运动是多源的,它是复数的而非单数的;多领域的文白之变互相促进,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潮流,最终推动中国语言文字完成了一场关键性变革。
一、文白之变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知识者最早意识到文言是中国现代性转型中的一个问题并非始自文学,而是始自教育。1877年黄遵宪以参赞身份出使日本,得以从另一种文化视角审视文言,他就意识到:“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发现了中国人学习文字存在困难的原因,于是提出:“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①〔清〕黄遵宪:《日本国志》(下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10—811页。梁启超在《论幼学》中指出:“古人文字与语言合,今人文字与语言离,其利病既缕言之矣。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②《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页。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论文言之弊、白话之利也多从教育出发,他谈到白话的“便幼学”时指出:“一切学堂功课书,皆用白话编辑,逐日讲解,积三四年之力,必能通知中外古今及环球各种学问之崖略,视今日魁儒耆宿,殆将过之。”③徐中玉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第1集),上海:上海书店,1994年,第85页。
当然,文言与白话是汉语的两种语体,它们各有优缺点,如果说文言有学习难问题,也主要是相对于现代教育而言,因此,文言的问题也只有在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开始以后,才会逐渐显现出来。
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一般认为始于20世纪初由清廷主导的学制改革。1902年当时的管学大臣张百熙向清廷进呈《学堂章程折》,经批准后,以《钦定学堂章程》颁布,史称“壬寅学制”。但这个章程不够完善,颁布后并未施行。其后,这个章程经过修改,张百熙联名荣庆、张之洞再次进呈,以《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并实施,史称“癸卯学制”。1903年在维新思潮中出台的“癸卯学制”是一个新旧教育妥协的产物,虽然这个学制的指导思想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立学宗旨”就是“以忠孝为本”;④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98页。但是为了救亡图存,清廷对教育改革的力度还是很大的;事实上,壬寅、癸卯两个学制基本上都是照抄日本,“虽修改七次,终缺少独立精神。”⑤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1074页。它们还是较多体现了现代教育的特点。癸卯学制是中国第一个颁布施行的带有现代特点的学制,它的出现意味着中国教育现代性转型的开始,而这个学制的实施也让现代教育与文言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
与传统教育相比,癸卯学制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它开始从人才教育转向国民教育,两者的主要不同是,前者是精英教育,宗旨是培养官员士大夫,也只有少数人能享有这种教育;后者是大众教育、国民教育,至少在理论上,它的宗旨是让全体国民享受教育。《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在“立学总义章第一”中就明确规定:“外国通例,初等小学堂,全国人民均应入学,名为强迫教育;除废疾,有事故外,不入学者罪其家长。”“初等小学堂为教成全国人民之所,本应随地广设,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童,始无负国民教育之实义。⑥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300—301页。癸卯学制以国民教育为宗旨,当然是一个很大进步,但是伴随学制改革,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文言难学难用;当教育为少数精英所垄断时,教育与文言的矛盾尚不突出,而当教育要普及到大众时,这个矛盾就暴露出来。旧中国的民众为生计所迫,很难有机会接受教育,即便有幸得到这个机会,年限也必定十分短暂,而这个时间如果都用来学习文言,很可能一事无成。蔡元培说过:“从前的人,除了国文,可算是没有别的功课。从6岁起到20岁,读的写的,都是古人的话,所以学得很象。现在应学的科学很多了,要不是把学国文的时间腾出来,怎么来得及呢?而且从前学国文的人是少数的,他的境遇,就多费一点时间,还不要紧。现在要全国的人都能写能读,那能叫人人都费这许多时间呢?”①高平叔编:《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6页。胡适在这个问题上说得更清楚:“至于教育一层,这20年的教育经验更可以证明文言的绝对不够用了。20年前,教育是极少数人的特殊权利,故文言的缺点还不大觉得。20年来,教育变成了人人的权利,变成了人人的义务,故文言的不够用,渐渐成为全国教育界公认的常识。”②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09—310页。
新学制受到西方与日本教育的影响,还有一个面向实用的转变。1902年张之洞在致张百熙的电文中就谈到:“日本学制,尤切实用。”他说:“外国文武官,下至农工商,无不习普通学者,但普通有深浅耳。普通门目,除伦理必应切讲力行外,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算学、卫生、体操皆要。”③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141页。张之洞、张百熙在拟定新学制时一直关注教育面向实用的问题。《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的首条就是:“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为宗旨;以童年皆知作人之正理,皆有谋生之计虑为成效。”④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315页。“尚实”是癸卯学制的宗旨之一,所谓尚实就是学以致用。如后来荣庆在《奏陈教育宗旨折》中所说:“所谓尚实者何也?夫学所以可贵者,惟其能见诸实用也。……方今环球各国,实利竞尚,尤以求实业为要政,必人人有可农可工可商之才,斯下益民生,上裨国计,此尤富强之要图,而教育中最有实益者也。”⑤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546页。新学制与传统教育一个明显不同就是教育内容增加了。传统教育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经典和中国文字,古代儒生大部分精力是用在学习使用语言文字上。如张志公所说:“传统语文教学的头绪很简单,一点都不复杂。一共干两件事:一是花大力气对付汉字,一是花大力气对付文章。”⑥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50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既要求学生学习古老、艰深的文言,同时又要求学习诸多实学课程,就有一个时间、精力不敷分配的问题。现代人并不比古人多一个脑袋,在古代如果很多人毕其一生学习语言,现代人不可能用同样的时间既学习文言,又学习外语、数学、物理和化学等实学知识。
癸卯学制是一个具有现代特点的学制,但制定时缺少充足准备,其自身就有许多矛盾:其教学宗旨带有现代特点,但要求使用的还是文言。在实施过程中,这个矛盾也明显暴露出来。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语言文字学习占用了太多时间。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初等小学堂每周有30小时,其中与语言文字有关的“读经讲经”占12小时,“中国文字”4小时,合起来超过总学时的一半,占总学时的53.33%。⑦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308页。高等小学堂每周36小时,其中“读经讲经”12小时,“中国文学”8小时,合起来还是超过一半,占总学时的55.55%。①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320页。当时的教育者面临的问题是,文言难学,要保证基本的教育质量,就必须保证有充足的时间,而现代教育其他学科有更多的内容需要学习,它们同样也需要增加教学时间。1909年江苏教育总会拟定了一份《呈学部请变通初小学堂章程文》,文中拿日本、美国和意大利的小学年限与癸卯学制的年限做了比较,认为后者年限偏长。其中的原因就是语言的学习所占时间过多,导致小学阶段学习期限过长。而另一方面,国民又无力承担这种过长的教育年限。该文指出:“以江南号称财富之区,凡小学生徒能毕初等五年之业而不为家族之生计所迫以致中辍者,尚寥寥焉;其他贫瘠之省,更复何望?”其后,呈文特别讲到“读经讲经”一科文字难的问题。该文指出:“而古人浅近之语言,自今人讲习之,无一非深邃之文义,童年索解尤苦其难;故小学教员惟此科成绩较少。……明知经籍即中国文字之菁华,而义随时代为变迁,体因传写而殊异;粗达其旨,已类翻译,将责效于讲解,则师生俱困。”呈文因而请求“将初等小学年限科目,比照《女学堂章程》酌量更定。”②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555—557页。
癸卯学制较多借鉴了日本及欧美的学制,让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有了一个基本依据,但是,语言文字既是教育的内容,也是一个载体,如果学制改变,而没有语言文字的改变,它仍然使用难学难用的文言,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新学制与语言文字的冲突,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甚至在与私塾的竞争中也处于劣势。因而文白之变就成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一个关键问题。
二、教育改革中的文白之争
中国近现代教育中的文白之变一直面临着比较复杂的情况:一方面这个变革的理据是适应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文言在中国社会的影响根深蒂固,它的传承主要依靠文言教育,教育是文言最后的堡垒,教育中的语言变革不可能在不触动社会整体语言格局的情况下进行。清末民初,在文言传统仍然十分强大的情况下,要在教育中实现文白之变,必然面临很大困难,它会遭遇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阻遏;在这个转变中也必然有一些观念的冲突。因而自甲午战后,特别是癸卯学制实施以后,有关中国教育是否应当使用白话,如何使用白话就一直有人关注,也不断引发讨论。
早在癸卯学制刚刚发布的1904年,有人在《时报》上就撰文谈到变革语言的必要问题。该文訾文言之艰深,建议应“毅然删去讲经读经一科,将经籍要义归并诸修身科中,复纂读本,以授普通知识与普通文字。”作者给出的理由是:“所以不慊于古籍者,为其文字既难,而发扬复少也。呜呼!中国教育既无国语一科,势不得不以国文代之。”③李桂林、戚名琇、钱曼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31页。该文作者虽然没有直接发出以国语代国文的要求,但至少表达了不用国语的遗憾。
从民元开始,教育界对文言白话的问题越来越重视,相关讨论也越来越多。在当时,重视应用成了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那么什么样的语言更适宜应用,就成了十分重要的问题。1912年,潘树声在《教育杂志》发表的《论教授国文当以语言为标准》一文就深入讨论了这个问题,也说明了何种文章更适宜于应用。作者分析了以往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各种模糊认识,然后指出:“夫吾谓应用文当以语言为标准。”“应用”的标准应当是“顺乎语言之自然”。在语文教学中,教读本,应当“化文字为语言”,教作文,则“化语言为文字”。①顾黄初、李杏保主编:《20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9—24页。这里“语言”的所指是口语,变成文字则是语体文。1916年,陈懋治在《中华教育界》上发表《国民学校改设国语科意见书》,文章指出:“近来毕业于高等小学之儿童,其所学国文不能达意者颇占多数,……欲捄斯弊,窃谓宜改初小国文科为国语科。取今日通行之语,所谓官话者择其尤近于文者,而编定之为国语。小学之国文科,即改用此种国语。其各种教科书,亦用此种国语编辑之。庶几声入心通,易知易解,不特教育易于普及,且可为他日语言统一之基础。是诚急不容缓之举矣。”②陈懋治:《国民学校改设国语科意见书》,《中华教育界》1916年第5卷第8期。
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一次最重要的、有关文白之变的大讨论发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1934年5月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育学主任的汪懋祖发表了《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稍后教育家吴研因发表《辟小学参用文言与初中毕读孟子及指斥语体文诸说》,批评汪懋祖的观点;汪懋祖则撰《中小学文言运动》予以反驳。在这场论争中,汪懋祖得到柳诒徵、任鸿隽、余景陶及许梦因等人支持,但也遭到吴研因、胡适及鲁迅等人批评。
汪懋祖的《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在教育领域复兴文言的主要观点,该文虽然分别讨论了教育中的5个问题:思想问题、教材问题、教学问题、社会需要问题及学制课程问题,但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文言多优点,白话多缺点,中小学教育应当更多地使用文言。他说:“窃谓初级小学,自以全用白话教材为宜,而五六年级,应参教文言,不特为升学及社会应用所需,即对于不升学者,亦不当绝其研习文言之机会也。初级中学国文科文言教材,以限于课程标准,分量至薄,青年因长久诵习语体,潜移默化,而躭好所谓时代作品,即平易之古文,涵正当之思想,每屏弃不观,……。”他批评教育部“一再令禁小学讲习文言,……而两次修订标准,文言文分量愈削愈少,势将驱除文言于中学课程之外,而尽代之以白话。使十数年后,文言绝迹,移风易俗,莫善于此矣。”他认为文言在教育中应当占更多的份额。他对文言教育提出的要求是:小学高年级“应参教文言”,“初中能读毕孟子,高中能读论语,学庸以及左传,史记,诗经,国策,庄子,荀子,韩非子等选本,作为正课,而辅以各家文选及现代文艺,作为课外读物。”这在当时对增加文言是一个较高的要求。汪懋祖提出多用文言,理由自然是文言有很多优点,白话有很多不足。他认为白话的不足是,首先,文言经过时间的选择,所以沉稳且有价值;白话没有经过历练,因而浮泛。他指出:“惟文字一道,其可保存流传,堪为模范者,必经长久之选择,有公认的价值,而不为时间性所拘束。”他认为“现代语体文,乃新文化运动之产品,”这种语言“毁灭礼教,暗示斗争,”学了有害无益。其次,白话文有欧化之弊。他说:“近来文字,往往以欧化为时髦,佶屈不可理解,须假想为英文而意会之,始能得其趣味,使学生童而习之,其困难几同读经,而语调奇变,几非中国人矣。”另外,汪懋祖认为学习白话看似简单,其实更难。他说:“学习文言与学习语体,孰难孰易?必经心理专家之长于文字者,作长期的测验研究,殊未可一语武断。”但在这个话题下,他并未给出文言、白话孰难孰易的结论。然后他举“如之何”与“怎么样”为例,指出前者快写简于后者。在他看来,学习文言比较难,但使用起来更有优势。他说:“或谓学习文言,当较白话费力。曰然,但略加努力,以后之受用,必且倍蓰。”③汪懋祖:《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时代公论》1934年5月4日,第3卷第6号,总110号。汪懋祖的这篇文章篇幅不长,却代表了教育领域反白话者的主要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
汪文刊出后,吴研因撰《辟小学参用文言与初中毕读孟子及指斥语体文诸说》予以批评。针对汪文“在小学高级参用文言”的主张,吴研因认为“小学高级如参教少许古人不用典故的写景叙事诗歌,如范石湖的田园杂兴及木兰辞等,以助儿童读书趣味,原也无所不可,……如必参教‘之乎也者’的叙事说理等文,实在是治丝益紊(棼)而不得益的办法。”对汪文“初中能毕读孟子”的主张,吴研因认为:“可选读孟子的菁华,但是决不可从头至尾毕读。”其中的差异是应当“选”读,而非“毕”读。另外,吴研因还反驳了汪文在文白之变上的一些偏见,包括“禁习文言乃少数人之私见”,“现代白话文上苴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之说,青年读之,信为洪水猛兽。”“初中因限读文言文,故教材‘斯穷且滥’。”“今人以儿童中心为白话童话之护符,实不知儿童心理。”以及文言学习不难于白话、文言较白话更简洁等。①吴研因:《辟小学参用文言与初中毕读孟子及指斥语体文诸说》,《申报》1934年5月16日。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的语言变革中,很多人的心态是:他们意识到现代教育需要白话,文白之变是大势所趋;但对文言又有很深的眷恋,短时间内无法改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旧两派的交锋通常并不十分激烈,双方观点的差异不是是否使用白话,而是白话在现代教育中应占多大比例;他们的对立也有更多情感因素。汪懋祖等在理智上也认识到现代教育使用白话的必要性,但情感上却难以接受,说到白话自然有很多愤激之词。在30年代中期,胡适也参加了与文言复兴者的论争,他在《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一文中,就专门提到了汪懋祖的这个特点。胡适指出:“他的主张不过如此。这样的主张,不过是一个教育家的个人见解,本来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他的文字所以引起读者的反感,全因为他在每一段里总有几句痛骂白话拥护文言的感情话,使人不能不感觉这几条简单的主张背后是充满着一股热烈的迷恋古文的感情。感情在那儿说话,所以理智往往失掉了作用。”②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93—394页。
三、白话在教科书中的使用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的语言变革中,教科书的改变是一个关键,学界关于语言变革方面的所有设想都必须在教科书中体现出来。因为近现代语言变革有着复杂的矛盾纠结,文言、白话各自都有在近现代教育中占据一方天地的理由,因而教科书就成了文言、白话进行激烈角逐的场域。在教科书中使用白话虽然有充足的理由,但这个改革在实践中还是遭遇了很多困难。
在清末民初,很多教育界人士一方面对白话文尚有偏见,认为白话文过于俚俗不登大雅之堂;另外,他们还可以通过使用浅文言缓解文言学习的难度,所以,当时教科书编纂者更愿意在文言的浅化上下功夫,而不使用白话。事实上,在癸卯学制制定之前,早期的教科书也都不约而同地使用这个策略。中国最早被认为具有现代特点的教科书是1897年朱树人所编、南洋公学出版的三本《蒙学课本》,这部教科书实开中国人自编现代教科书的先河,出版后被其他学堂效法,产生了很大影响。这部教科书使用的是文言,但追求的是文字浅显。该教本在《编辑大意》中就指出:“是编专取习见习闻之事物演以通俗文字,要使童子由已知达于未知而已。”“我国文字语言离为二物,识字之所以难也。其文序与语次相歧者,童子尤难领悟,是编专取文语同次者。凡倒装句法及文中所有语中所无之字概不阑入。”①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0、86—87页。到了1903年,清廷制定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在语言上所取也是这个策略,要求初等小学使用文言,但又要力求浅显。其后的小学教科书则基本遵循这个策略。商务印书馆1904年发行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是清季流行最广的教科书,“从1904年一直发行到1911年,发行量占全国课本份额的80%。”其“编辑大意”中就谈到:“虽纯用文言,而语义必极浅明,且皆儿童之所习知者。”②毕苑:《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98—100页。
当然,关于文言究竟能否浅显到白话的程度,在阅读上做到完全没有障碍,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议的,当时也有人持不同看法。吴研因就指出:“但是文言无论如何浅显,儿童总不能直接了解。小学教科,把五分之四的功夫,用在读书上面,结果也只造成了少数勉强能文的高材生,跟所谓国民教育相差太远。”③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442页。他认为,说到底,文言还是存在一个言文分离的问题,文言的深浅只有程度的不同,并不能做到真正的言文一致。因而清季最后十多年在教科书编纂的主流之外,还是一直有人在尝试使用白话编纂教科书,以实现真正的言文一致。
中国最早的白话教科书应当为钟天纬在1895年(光绪21年)所编;民国学者陈翊林在30年代撰著的《最近30年中国教育史》中就提到:“21年华亭钟天纬在上海办三等学堂,而以语体文编教本为国语教科书的先河。”④陈翊林:《最近30年中国教育史》,上海: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第46页。这个时期钱塘人施崇恩创办的彪蒙书室也编印了很多小学白话教科书,如《绘图中国白话史》《绘图外国白话史》《绘图蒙学识字实在易》《中国地理实在易》等。这套教材最大的特点,一是使用白话,二是有大量绘图。例如《绘图中国白话史》刊登的广告就提到:“中史浩繁,编纂非易,新辑历史课本类皆文义稍深,初学未能领会。是书将五千年大事纯用白话演说,略通文义者即可读,此小学之佳本也。”⑤石鸥:《我国最早的白话教科书——彪蒙书室出版的教科书》,《书屋》2008年第3期。这个时期尝试编纂白话文教科书的还有陈子褒。陈子褒是晚清白话文运动一个重要的参与者,他的《俗语说》《论报章宜改用浅说》《论训蒙宜用浅白读本》在当时都有广泛影响。他认为:“大抵今日变法,以开民智为先。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不改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居于黑暗世界中,是谓陆沉。”“然余试取浅近者以譬之。文言譬如古玩店,浅说譬如卖米店。一国之中,可以人人不买古玩,不可以一人不买米。”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2期,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25—126页。陈子褒终生从事小学教育,他也是近代以白话编纂教科书的探索者。他“主张小学教材一定要用浅近白话编写。”⑦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657页。从1895年起他编写了大量白话文课本,如《妇孺三字书》、《七级字课》五种和《小学词料教科书》等,在当时有很大影响。
民初几年,教育界语言改革的势头有所回落,但是到了1915年前后,新的改革浪潮再次兴起。因为在初等教育领域,白话代替文言毕竟是大势所趋,因而民国兴起的这个语言变革势头更加强劲,另外,文言白话化毕竟还给文言留了个尾巴,要彻底实现语言通俗化,最好的办法还是完全使用白话,因而白话文还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教科书中。在民初几年一个明显的变化是,苏南教育发达地区的一些学校开始自编白话文教材。据吴研因回忆:“民国成立后的1915年左右,由俞子夷发起我们在江苏苏州的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才私自实行了真用白话文自编教材,油印了教学初级小学的低年级生。”他谈到,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也有不少人主张初等小学用白话文,教育部总长张一麐“也是主张用白话文教小学生的。他是苏州人,曾写了一封长信给苏州教育界,要求苏州教育界向一师附小学习。”虽然,张一麐的信并没有得到很多的响应,但一师附小却得到了鼓舞。“后来索性连中年级也用白话了。”其后,到了吴研因主持一师附小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更彻底的改革:“除了高小语文仍用文言教学以外,高小其他科目和初小各科,凡是要用文字教学的,一律改用了白话文。”①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446—447页。
谈到改革的理由,吴研因说:“我们觉得文字是一种工具,文言、白话功用差不多,但是白话文是用语言写出来的,读时容易明了,不必花去翻译讲解的工夫,作文也容易,要说甚么就写甚么。因此,主张小学用白话文编教科书。就在所办的小学里,自编白话教材,教授儿童。”②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第442—443页。通过自编白话文教材尝试语言改革的还有北京的孔德学校。孔德学校创办于1917年,“这个学校的国文科教授,改革最早:授语体文和注音字母,创办成立后即已实行。……所用的读本,也不是购自商务印书馆也不是购自中华书局,乃是自行编选的。”③李桂林、戚名琇、钱曼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31页。
因为社会上出现了对白话教科书的需要,这个时期一些出版社也在尝试语言改革。中华书局1916年出版的《新式国文教科书》,在每册后面都附有四篇白话课文,作为“副课”。这种尝试还得到了教育部的肯定:“查该书最新颖处,在每册后各附四课,其附课系用官话演成,间有与本册各课相对者,将来学校添设国语,此可为其先导,开通风气,于教育前途殊有裨益。至各册所用文句,其次序大致均与口语相同。尤令教员易于讲授,儿童易于领悟。在最近教科书中洵推善本。”④“中华书局广告栏”,《中华教育界》1916年第5卷第1期。
随着讨论的深入,教育界在国民学校使用语体文的意见渐趋统一,这种认识也开始在各种官方或半官方会议的文件中出现。早在1913年,“读音统一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议决的问题之一就是:“请教育部将初等小学‘国文’一科改作‘国语’,或另添‘国语’一门。”⑤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9页。1917年,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决了《推行国语以期言文一致案》,其中的一个要求就是“莫如改国民学校之国文科为国语科,将国文程度改浅,国语程度提高,仿语录及说部书之形式,俾文与语之距离渐相接近,成一种普通国语。”1919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召开,刘半农、周作人、胡适和钱玄同等提出了《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其中“第三件事”就是“改编小学课本”。该议案提出:“如今打算把‘国文读本’改作‘国语读本’,国民学校全用国语,不杂文言;高等小学酌加文言,仍以国语为主体,‘国语’科以外,别种科目的课本,也该一致改用国语编辑。”⑥李杏保、顾黄初著:《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86—87页。
鉴于教育界在国民学校改国文为国语的意见渐趋统一,1920年教育部下令各省改国文为语体文,文告中指出:“本部年来对于筹备统一国语一事,既积极进行,现在全国教育界舆论趋向,又咸以国民学校国文科宜改授国语为言;体察情形,提倡国语教育实难再缓。兹定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①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60页。胡适后来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他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20年。”②胡适:《〈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新教育》第3卷第1册,1921年2月。
1920年教育部下令国民学校一二年级改国文为语体文,实是语文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当时的教育界已认识到白话文在建构现代教育中的重要意义,也意味着白话文在现代教育中已取得了合法地位,占有了一席之地。但是,其后白话在与文言的角逐中,虽然也在继续扩大影响;不仅在小学,在初高中语文教学中也占有了一定份额,但这个进展总起来说是缓慢的,在教育领域并未像在文学中,出现白话战胜文言一边倒的情况。
进入20年代,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白话文的合法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1922年,教育部综合各方意见颁布了一个新的学制系统,即壬戌学制。其后为了适应学制的变化,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制定了《中小学各科课程纲要》,并于次年六月颁布。这个《课程纲要》包含了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部分,分别由吴研因、叶圣陶和胡适起草。1923年施行的这个《课程纲要》,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语言变革的最新进展,确定了白话文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同时在初高中语文教学中也给白话留出了一定的位置。在小学阶段,由吴研因制定的《小学国语课程纲要》注重基本的听说和阅读训练,要求学生“练习运用通常的语言文字,引起读书趣味,养成发表能力。”关于作文,该纲要要求低年级“能作语体的简单记叙文,实用文(包含书信日记等)而令人了解大意。”高年级“能作语体的实用文,记叙文,说明文,而令人了解大意。”③吴研因:《小学国语课程纲要》,《小学教育界》1922年第2卷第3期。在中学阶段,文言也给白话让出了很大空间。在1923年由叶圣陶制定的《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中就明确要求:“与小学国语课程衔接,藉以较充分的练习运用文字的能力,并涵养文学趣味;由了解语体文,进而了解文体文,由浅及深,自成一圆周,并为高级中学国语课程的基础。”在这个纲要中,阅读和作文都体现了一个由语体向文言的过渡。第一年,阅读方面,“语体约占四分之三”,“作文以语体为主,兼习文体文。”第二年,阅读方面,“语体约占四分之二”,“作文语体文体约各半。”第三年,阅读方面,“语体占四分之一”,“作文以文体为主,兼及语体。”④叶绍钧:《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山西省教育会杂志》1923年第9卷第4—5期,第19—24页。就高中阶段来说,由胡适制定的《高级中学公共必修课的国语课程纲要》在坚持以文言训练为主的情况下,也给白话留出了一方天地。该纲要的“教学目的”设置的培养目标主要都是关于文言的:“培养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能力。”“增加使用古书的能力。”“继续练习用文言作文。”其中只有一条是关于白话的:“继续发展语体文的技术。”纲要列出的阅读书目中,有少量的白话小说,多数则是历代文言文本。胡适给出的“毕业最低限度的标准”是:“曾精读指定的中国文学名著八种以上。”“曾略读指定的中国文学名著八种以上。”“能标点与唐宋八家古文程度相等的古书。”“能自由运用语体文体发表思想。”⑤胡适:《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国语课程纲要》,《广东省教育会杂志》1925年第2卷第6期,第82—84页。总体上说,壬戌学制主导下《课程纲要》的特点是,小学基本使用国语教学;初中平分秋色;高中则是文言教学居于主体地位,语体文只占很小一部分。
语文教学改革的下一个节点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1928年国民党控制政权后在教育政策方面也做了一些调整。1929年教育部中小学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公布了《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初级中学暂行课程标准》《高级中学普通科暂行课程标准》,要求各学校试验研究。这个新课程标准后来经过试验修订到了1932年,才去掉“暂行”,由教育部正式颁布。如果说与此前相比,“新课程标准”对文言、白话使用尺度的把握在小学与高中阶段没有很大变化,但在中学阶段还是有一些改变。这个改变可以从教科书的编排要求看出来。它的要求是:“语体文与文言文并选,语体文渐减,文言文渐增,各学年分量的比例递次为七与三,六与四,五与五。”①《初级中学暂行课程标准》,《河南教育》1930年第2卷第16期,第3—6页。与新学制时期相比,语体文的份额整体上有所增加。
结 语
在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中,教育是一个最复杂、与社会方方面面联系最密切、也直接关系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领域。如果说,文学的功能主要还是审美、娱乐,对大众来说,它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奢侈品,而教育则不同。一个人能否接受教育,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很大程度上能改变他的一生;一个国家能否普及教育,普及什么样的教育,则能决定一个国家能否富强、振兴,能否自立于民族之林。与文学相比,教育是一种制度化的学习方式,它可以通过学制与课程标准的制定、教科书的编纂等一系列制度化的方法强迫学习者接受某种语言。现代教育用制度化的程式,要求学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学习某种语言,它在很大程度上会整体塑造学生的语言形态,进而影响一代人的语言选择;教育中的“白话文运动”会对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虽然,中国的教育改革主要是由政府推动(从新学制、课程纲要的制定,到教育部下令国民小学改国文为国语都是由政府主导),新旧双方的论争不是十分激烈,但文言教育是文言传统的支柱,教育中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它的任何一点小的变革都会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应,阻力也特别大。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教育领域中的“文白之变”举步维艰,白话文最终也是满足于与文言平分秋色,而不是像文学取得一边倒的胜利。
在中国近现代语言变革史上,不仅文学中有一个白话文运动,教育之同样也有一个白话文运动;这样说来,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就是多源的,是复数的而非单数的,以往那种将文学中的白话文运动等同于全体的白话文运动与历史多有不合。在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中,文学、教育都产生了对白话的需要,也都发生了一场从文言到白话的变革。白话文运动的多源性一方面说明这个运动发生的必然性;近代以来不是一个领域需要白话文,而是多个领域都需要白话文。另外,正因为这场变革是多源的,白话文运动才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成功,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