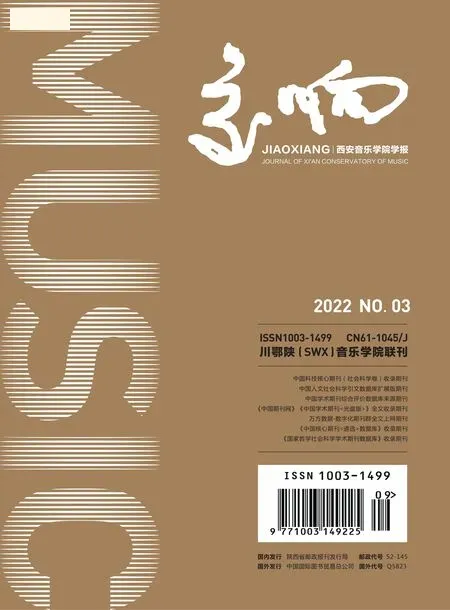古琴艺术的符号化审美特征探究
2022-02-02葛雅琳黄汉华
●葛雅琳 黄汉华
(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广东·广州,510000)
在夏商时期,中国已出现礼乐文明的雏形。周朝建立后,为了巩固周朝的统治,辅佐年幼成王的周公“制礼作乐”,通过礼乐制度区分并规范人们所处的阶层及相应的尊卑贵贱的秩序,将礼乐文化符号化,以此维系周朝的宗法统治。[1]虽然到了西周后期,伴随着周王朝王权陨落,西周传统礼乐文化符号系统逐渐被破坏,形成“礼崩乐坏”的政治局面,但礼乐思想仍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古琴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国古代音乐史、文化史中,古琴不仅是一种造型优美、音色悦耳的乐器,更是一种独特的象征符号,深受中国统治阶层的尊崇。虽然,谈及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应是儒、道、释并举,但从符号学角度看,古琴艺术的符号化进程主要受儒家思想影响,古琴的重要地位与儒家倡导的礼乐文化符号系统有密切的联系。当然,道家的“薄名黜礼”“道法自然”等思想,佛家禅宗的“明心见性”“顿悟”等观念也在不同程度影响了古琴艺术的发展,这是我们不可忽视的。
一、古琴文化地位的符号化
我国第一部记载了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尚书·益稷》有载:“戛击鸣球,搏附琴瑟以咏,祖考来格。”由此可见,早在商周以前,古琴就被用于人们祭祀祖先的仪式中了。但古琴的重要地位并不仅是缘于祭祀,因为同被祭祀礼仪所使用的乐器八音皆具,而古琴在其中无疑是非常特殊的存在。当代著名古琴家李祥霆就认为,古琴能拥有尊贵崇高的地位,还与其自身拥有较高的音乐表现力密切相关。①也就是说,古琴不仅是一种祭祀祖先、促进人与天地神明沟通的工具,其更是一种在人们日常音乐生活中扮演着重要地位的、具有较丰富音乐表现力的常用乐器。这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多有反映。如“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周南·关雎》)“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郑风·女曰鸡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小雅·鹿鸣》)“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小雅·常棣》)等等。可见早在周朝,古琴已广受欢迎和重视,人们爱琴、敬琴,开始了将其符号化的进程。
如果说祭祀祖先与神明的仪式是将古琴艺术孕育成一种特殊的文化象征符号的摇篮,那么为古琴设想一个完美的“出身”,则是将古琴艺术符号化的第一步。按现有文献推断,古琴至少有三千年的历史,其创制者的真实身份实际已无从考证。但我们可以看到,仍然有多篇文献“记载”了古琴的创制者,并且主要认为创制者出自于在古代中国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三皇五帝”中。如战国的《吕氏春秋·古乐》有载:“昔古朱襄氏(炎帝)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琴),以来阴气,以定群生。”[2](P212)东汉蔡邕所作的《琴操》有云:“首昔伏羲氏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3](P227)同是东汉时期的桓谭《新论》曰:“昔神农氏继宓羲而王天下,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4](P92)宋代《太古遗音·琴议篇》(佚名)曰:琴者禁也,禁邪归正,以和人心。始乎伏羲,成于文武,形象天地,气包阴阳。神思幽深,声韵清越。雅而能畅,乐而不淫。[5](P108)等等。此类记载或论述,在历朝历代的琴论或琴谱广泛存在。通过这些文献,古琴尊贵的出身被反复强调,其尊崇地位被合法化,实现了“名实相符”。
从文献上看,描述古琴的起源与琴制的文献,主要集中于汉代,后世文献涉及内容多为复述而并无新意。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从古琴形制的发展看,目前较为公认的观点是古琴的形制在东汉末年应已基本定型。②也就是说,古琴的形制很可能在汉代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化并逐步定型的阶段,这引起了人们对其起源的想象与讨论。二是从社会历史背景看,汉代历经刘邦立国、“文景之治”等阶段后,统治阶层认识到儒家学说对维护社会安定、巩固统治的优势,董仲舒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并被汉武帝接纳采用。西汉年间,先秦儒学的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具有比较完整体系的音乐理论著作——《乐记》的完成,体现了该时期统治阶层重塑儒家礼乐文化符号思想的努力与成就。与此同时,古琴由于其优越的音乐表现力和便携性深受文人阶层欢迎,又被认为具有通天地、格鬼神、去淫邪、明道德、序尊卑、美风俗等功能,其作为礼乐思想象征之一的符号性被进一步强化。
二、古琴造型及结构的符号化
古代琴人认为,古琴作为沟通天地宇宙与人之间的乐器,其既要与天地和合,又要与人相应。因此,古琴的外观造型一方面与宇宙及天地之“象”(形象与运行之道)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还呈现、阐释了中国传统社会规范——“礼”。基于这样的审美追求,历代琴人对古琴的造型和结构的命名和阐释具有强烈的暗示性和象征性,古琴的外观造型及内在结构所蕴含的符号群可谓蔚然可观。这些符号承载的信息反映了琴人对自然的敬爱、对社会规约的遵循以及对真、善、美的追求。
古琴由面板和底板上下相合而成,从侧面看,琴面隆起呈弧形,琴底则为平整的平面。此造型被在历代琴论中多被阐述,观点较为一致,均是将古琴此造型与“天圆地方”观③联系起来。关于“天圆地方”观有多种阐释,包括形状说、动静说、时空说、天地之道说、阴阳说等等。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这些观念与说法并非是非此即彼、互相对立的,多种对“天圆地方”观的阐释,实际是对由感性思维而得的形状说的理性化。即历代学者通过抽象、引申及补充,与形状说形成了互补、互渗、互阐、互释的“天圆地方”说体系。
在古代琴论中,古琴造型与“天圆地方”联系的方式有几种。一曰“象”,如宋代朱长文《琴史》的“圣人之制器也,必有象。观其象,则意存乎中矣。琴之为器,隆其上以象天也;方其下以象地也。”[6](P133)即认为,古琴上下面板的形状源于对天地圆方形状的模仿。一曰“观法”“取法”,如桓谭《新论》中的:“……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焉。”其可被理解为古琴上下面板的形状是对天地形状的观察、模仿与效仿,更可被理解为是在模仿天地形状的同时,还效法天地之道。又有“象”“法”同用,如清代《五知斋琴谱》中的:“前广而狭,象尊卑有差也。上圆象天,下方法地。”[7](P385)根据上下文语境,此处的“象”“法”可理解为古琴上下面板的造型是对天地之道的模仿与隐喻。古琴面板的上隆下方,有明显的实用功能,其符合乐器的发声学及演奏便利的要求。古代文人视人为天地自然的一份子,敬畏天地、热爱自然,并将这种情感移情至他们最为尊崇的乐器——古琴中。正因如此,他们不断将古琴与天地自然联系在一起,不断地将古琴符号化,最终将这些符号固定下来。从上述文献可见,在历代琴人心里,古琴上下面板的造型并不仅仅是对天地形状的简单模仿,更含有“礼”的深刻意蕴。进一步看,天圆地方说中的时空说、阴阳说等在古琴面板外观上还有可对应之处。
在无垠的天地空间中,时间静静流淌。如果说古琴上下面板的立体造型形成了一个对空间的隐喻,那么古琴的平面造型则隐含了许多关于时间的象征符号。东汉桓谭在《新论》有云:“琴长三尺六寸有六分,象期之数。……”[4](P92)蔡邕在《琴操》中曰:“琴长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也;……”[3](P22)这种观点到明清的琴论中仍被反复提及,如《五知斋琴谱》中的《上古琴论》中仍显示出对前人观念的恪守与传承:“琴制长三尺六寸五分,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年岁之三百六十五日也;……”[7](P385)这些琴论反复强调古琴的长度是“三尺六寸有六分”或“三尺六寸五分”,但实际上,历代古琴的尺度并非如琴论所述一般严苛及固定。虽然要考虑历代同时期或不同时期的度量衡制度不统一的因素,我们仍可发现古琴的实际尺度根据时代审美风格的偏好及不同琴式的实际需要产生了变化,未必能完全符合“三尺六寸五分”的要求。可见,古琴的长度为“三尺六寸五分”这一说法用以象征“一年有三百六十日或三百六十五日”的内涵多于现实意义。
古代琴人对通过古琴表达时空隐喻的步伐并未止步于琴长对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的象征,而是层次鲜明,具有系统性。这其中琴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琴徽是镶嵌在古琴面板上,呈直线不均匀分布的十三个圆点,所谓“一徽”“二徽”至“十三徽”是由琴头往琴尾方向顺数而得。右手拨弦左手轻点琴徽所标识之处,可取象征天籁的泛音色。虽然有无琴徽并不影响古琴的演奏效果,但其方便了琴人对古琴音准的把握,并对古琴的调律与记谱有重要意义。琴徽组合的外观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大小一致,一种是大小有变化。后者更为常见,体现为居中的七徽圆点最大,然后往古琴两端逐渐缩小。琴徽多选色泽富于光彩的螺钿即螺壳或海贝为材,名贵之琴亦有用金或玉石镶嵌。琴徽所选之材均为反光材料,这主要是由于古琴面板一般为深色,选取善反光之物是为了与琴面区分便于识别,此实用功能在古代采光条件较为局限的情况下非常重要,多有文献记载,如欧阳修的《三琴记》中有云:“世人多用金玉蚌琴徽,此数物者,夜置之烛下炫耀有光,老人目昏,视微难准,惟石无光,置之烛下黑白分明,故为老者之所宜也。”[5](P100)除了实用性,琴徽在琴面实现的造型还有婉转的隐喻。嵌在深色的、隆形琴面的琴徽,在月色或灯火下闪烁着灵动的光彩,整个面板表现出夜空中星月闪耀之形象。星月是古人观察时间变化的重要参照,肖似星月的十三个琴徽的大小如上文所说常被设为有规律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十三个琴徽的整体形象带有一种流动感,这些细节正是琴徽成为时间象征符号的基础。传世或当代的古琴多用螺钿徽,这或许不是仅仅因为螺钿易得和具有反光特性。螺钿徽色泽生动,其光芒内敛而流转、气质典雅而质朴。螺钿徽此般外观气质一方面符合古代文人的审美追求,另一方面其与生俱来的动感也是与其作为时间符号的身份暗相呼应的。
宋代朱长文的《琴史·莹律》论曰:“琴——所以考天地之声也。天地之声出于气,气应于月,故有十二气,十二气分于四时,非土不生。土,王于四季之中,合为十三,故琴徽十有三焉,其中徽者土也,月令中央。……凡天地五行十二气、阳律阴吕、清浊高下,皆在乎十三徽之间,尽十三徽之声,惟三尺六寸六分之材可备,故度而制之,亦以象期之日也。当宓羲之时,未有律吕之器,而圣人已逆其数矣,未有历象之书,而圣人已明其时矣。”[5](P102)通过阐释古琴“三尺六寸五分”的琴长被琴面十三个琴徽划分这一现象,朱长文将古琴与天地、气节、五行、阴阳,尤其是十二月的划分密切地联系起来。
而清代琴家、占卜学家潘士权所著的《大乐元音·形上篇·徽义》云:“琴之徽,一十有三者何也?一年之气二十四,首尾两徽,当冬至之分;首之后为小寒,尾之前为大雪。二徽当大寒之中而立春始;三徽当雨水之终而惊盐始;四徽当春分之终而清明始;五徽当谷雨之终而立夏始;六徽当小满之终而芒种始;七徽则正当夏至之中;八徽则小暑终而大暑始;九徽则立秋终而处暑始;十徽则白露终而秋分始;十一徽则寒露终而霜降始;十二徽则立冬终而小雪始;至十三徽乃以大雪终焉。……”[5](P509)文中除了强调十三个琴徽与二十四气节对应,又以琴徽为中介,将属于人对自然认识范畴的气节与属于对社会认识范畴的定徽、音律联系起来。
此外,更有将四时即四季与古琴联系起来,如明代胡文焕所编《文会堂琴谱·琴制尚象论》中的:“……琴末承弦曰龙龈,其折势四分,以准四时。”[8](P133)于是,在上下面板所隐喻的天地之间,“三十六寸五分”的琴长所象征的三百六十五天被十三个琴徽分为十二个月或二十四气节,再由龙蘸(或曰龙龈)体现四季分明。期间五行与四时互相配合运转,春夏秋冬四季分别为木火金水,而土被放在夏秋之交,居中央,这又体现在面积最大的第七琴徽上。由此,古琴的外观造型构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年、月、四季运转自如的时间符号体系。而上述古代琴论中的论述,也恰恰从琴学的侧面,证实了笔者认为各天圆地方说是一个由形状说、动静说、时空说、天地之道说、阴阳说等各说互补、互渗、互阐、互释的学说体系之观点。
古代琴人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将他们钟爱的古琴设想为一个微观宇宙、天地之缩景。在完美架设时空符号的基础上,古琴的一些局部构造的造型与命名,更是进一步隐喻了古代文人心中理想的生存环境。古琴架弦的部件“岳山”为全琴琴弦与琴面距离最远的部位(琴尾则反之),岳山架七弦,七弦经过“龙龈”到琴背面路过“凤沼”被固定于“雁足”(或曰“凤足”)上。古琴有赖于琴人振弦而发声,由于古琴槽腹特有的结构,能引导演奏者通过振弦而所发之声,在琴腹回响,因此拥有蜿蜒悠长的余韵是古琴音色的一大特点。琴声与水均有无具体形状及具有流动性的特点,琴声在琴腹的回荡,如同水入深潭而有暗流(通过“足池”沟通“龙池”“凤沼”)。如此以琴弦、琴声喻水,构成了天地间高山流水的形象,其意象逻辑更是符合了人们对山是水之源,水顺流而下汇聚于池或潭中这一自然现象及流水运动规律的认识,亦体现了古代文人对“山水精神”的向往以及“上善若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等审美趣味。
正如《新论》中所云:“神农氏继庖牺而王天下,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焉。”若上文所说的古琴的立体轮廓是通过“远取诸物”来“以通神明之德”,那么古琴“天人之和”的符号化,则依赖于古琴平面造型的“近取诸身”——对人体的模仿。这里的讨论需注意两个前提:一是已出土的魏晋以前的琴或我们说的古琴雏形,如曾侯乙墓出土的素漆十弦琴,其平面(尤其是音箱部分)类似于一个长方形,线条相对简约,还难以与人体线条对应。因此“琴身如人身”很可能并不是在古琴起源之始就有的。二是在一定尺寸内的古琴造型变化,对古琴音响效果尤其是音色、音量有一定影响,但在正常的制琴工艺下这种影响往往不会是颠覆性的。古琴不同形状的琴式众多,有史料可查的超过百种,流传下来常见的也有十余种。在十余种常见琴式中,有不少琴式的平面造型与人体线条并无直接对应的可能。比如呈类扁长鹅卵石形的混沌琴式、两侧线条为单一微弧形(无转弯无棱角)的太和式、线条极似芭蕉之叶轮廓的蕉叶式。与人体形状线条接近的古琴往往多以古之圣贤为名,如流传最广的仲尼式,以及神农式、伏羲式、列子式、师旷式。因此仅简单说“古琴看上去就是一个人体”之类的观点显然并不全面。当然,不可否认取圣贤之名的琴式,尤其是仲尼式流传面相对更广,在此暂不展开讨论。
以上两个前提,说明虽然琴人惯常以头、额、眼、颈、项、肩、腰等词描述琴身各部位,但古琴线条与人体线条的关系并非一定是完全对应的,因此一些学者以此作为琴体如人体的证据则必然会显得不够充分。正如《文会堂琴谱·琴制尚象论》所云:肩曰仙人肩,取其正齐也。腰曰玉女腰,取其纤细也;又曰龙腰,取其屈折如龙之形也。自肩至腰曰凤翅,象凤翅耸然而张。……[8](P132-133)此文在将古琴平面线条与人体线条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阐述了另外一种可能——与龙凤图腾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当然,这并不妨碍琴人以“近取诸身”为路径,将古琴人格化,因为龙凤图腾本身也是被人格化的。如《乐书·琴制》(宋·陈旸)中所论:“琴之为器,有龙池者,以龙潜于此、其出则兴云以泽物,而人君之仁如之;有凤池者,以南方之禽,其浴则归洁其身,而人君之德如之。”[5](P140)
此外,除了琴身线条及其结构名词的拟人化,众多以古之圣贤为名的琴式、琴人在古琴身上留下的琴铭,以及泛、按、散三种音色所分别代表的“天籁”“人籁”与“地籁”中,均含有的“人”的因素,这些因素对“人”在琴器中的符号化显现起到了支撑作用。
在琴人长时间的艺术实践活动中,古琴造型意象所隐含的“天人合一”“礼乐”等观念被积淀、逐渐凝聚及固定下来,其意象便走向了符号。古琴外观构造的设计制作也因此实现了对乐器实用性的超越。古琴上下面板的立体造型形成了一个有意味的广袤空间的隐喻——“天圆地方”,平面造型则隐含了一个层次分明的年、月、四季等运转自如的时间符号体系。加上“人”的要素后,古琴的外观及构造符号群营造了一个人在宇宙天地之间生存,在山水之间行走,吸收天地之灵气,修习人间之礼、乐,近有鸟兽陪伴、远有神灵护佑,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和谐运转的符号景观。由此,在古琴外形的符号系统中,天、地、阴、阳、五行所代表的自然与人、琴器、音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完美地呈现了古人习琴观中的天、礼、琴、人合一的思想。
三、琴人身份及其艺术实践活动的符号化
在古琴艺术发展的过程中,历代琴人有意通过对古琴艺术实践④活动的描述,将懂琴、抚琴之人与非懂琴、非抚琴之人区别开来。这意味着,琴人通过抚琴、听琴、授琴等与古琴相关的艺术活动,实现了“琴人-君子”身份的符号化。正如上文所说,古琴原本不仅在祭祀仪式中占有一席之地,还广泛活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延续下去,随着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的崛起,古琴和士的关系逐渐紧密。[9](P56-61)如战国至秦汉年间的典章制度书籍《礼记·曲礼》有载:“君无故玉不去身,大夫无故不彻县,士无故不彻琴瑟。”[5](P13)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琴谱》中曰:“雅琴者,乐之统也。与八音并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亲密,不离于身,非必陈设于宗庙乡党。……故琴之为言禁也,雅之为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5](P19)宋代陈旸《乐书》云:“琴者,士君子常御之乐也,朴散而为器,理觉而为道。惟士君子乐得其道而因心以会之。盖将终身焉。虽无故斯须不撤也,故能出乎朴散之器,入乎觉理之道。卒乎载道而与之俱矣。”[5](P107)类似的观点在《梧冈琴谱》(明·黄献)、《程一堂琴谱》(清·程允基)、《琴学》(清·曹庭栋)等文献中反复出现或被反复引用。
此外,除了直接将琴与士、君子联系起来,还有一些文献阐述了对学琴、抚琴之人的规定。如《太古遗音》(宋·佚名)⑤就直言:“黄门士、隐士、儒士、羽士、德士,此五者,雅称圣人之乐,故宜于琴。……骚人逐客、游子怨女,皆寄情于琴,以伸快其意,古人皆尚之。凡学琴,必须要有文章,能吟脉者。……武士之家不宜鼓琴……商贾不可鼓琴。……优伶不敢鼓琴。……非中土有乡谈番语者,以其自音之不正,安能合圣人之正音,故不宜也。……百工技艺之人,皆谓之俗夫,以俗夫之材而鼓圣人之琴,是玷辱圣人之器,故忌之。有腋气口气者不宜鼓琴,是丧慢圣人之气,故忌之。”[5](P112)文中对琴人的要求之苛刻,令人咂舌,显示出强烈的排他性。正是通过这种排他的规定,琴人逐步培养出专属于古琴的艺术品味并愈发明晰地界定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角色。这些规定在后世琴谱中仍经常出现,如《风宣玄品》(明·朱厚爝)中提及的“……其人须是读书”[5](P246)。《琴学正声》(清·沈琯)引述“臞仙”(明·朱权)曰:“……口上要有髯,肚里要有墨。”[5](P318)还有《指法汇参确解》(清·王仲舒)中对古琴的传承对象有所规定:“……不抚郑声、不传俗子、有宜弹,有不宜弹,□遵先贤遗词而于学琴之准绳规矩,不差毫厘,则品立矣。”[5](P367)记载了类似观点的还有《成玉磵琴论》(北宋·成玉磵)、《卾宫祠说琴》(清·朱启连)等。
如此看,孔子以后,琴人群体在实际上逐渐被缩小,参与抚琴活动的门槛升高了。汉代以后,古琴更是主要与贵族或文人阶层“捆绑”在了一起,成为了这类人群在音乐文化方面的象征符号之一。反过来,通过古琴艺术的一系列实践活动,琴人也将自己与非抚琴之人区别开来,实现了其身份与文化品味的符号化。
除了通过各种约束与规定将琴人群体符号化,反复强调抚琴礼仪与抚琴环境的严格要求也将古琴与其它乐器区别开来。如《蔡中郎文集补·女诫》中要求:“舅姑若命之鼓琴,必正坐操琴而奏曲;若问曲名;则舍琴兴;对曰某曲;坐若近,则琴声必闻;若远,左右,必有赞其言者;……琴必常调,尊者之前不更调。张私室,若近舅姑,则不敢鼓独;若绝远,声音不闻,鼓之可也。鼓琴之夜,有姊妹之宴,则可也。”[5](P35)宋代《太古遗音》(佚名)中的《弹琴有十戒》中曰:“头不可不正;坐不可不端;容不可不肃;足不可不齐;耳不可乱听;目不可邪视;手不可不洁;指不可不坚;调不可不知;曲不可不终。”[5](P111)此外《事林广记》
(南宋·陈元靓)、《玉梧琴谱》(明·张进朝)、《风宣玄品·古琴训论》、《遵生八笺》(明·高濂)、《指法会参确解》(清·王仲舒)等历代琴学文献也对琴事礼仪亦多有论述。
明代《永乐琴书集成》收录的宋代琴人成玉磵琴学论著《成玉磵琴论》中对“露下弹琴”“弹琴盥手”“焚香弹琴”“对月弹琴”“弹琴舞鹤”“临水弹琴”“膝上横琴”“道人弹琴”等抚琴场景标注了细致的规定。明代朱厚爝所著的《风宣玄品·琴室》详细记载了琴室的建设、布局及装饰,其中描述的环境可谓是风雅至极。著名才子屠隆在其《考槃馀事·琴笺》中对抚琴的抚琴佳境做了归纳:“对月——春秋二侯天气澄和,人亦中夜多醒,万籁咸寂,月色当空,横琴膝上,时作小调,亦可畅怀。对花——宜共岩桂,江梅,詹卜匍,建兰,夜合,玉兰等花,清香而色不艳者为雅。临水——鼓琴偏宜于松风涧响之间,三者皆自然之声,正合类聚。或对轩窗池沼,荷香扑人,或水边莲下,清漪芳芷,微风洒然,游鱼出听,此乐何极。”[10](P184-185)这些文献中描述的抚琴环境幽静清雅、格高意远,其中透露出权威感也使得古琴艺术实践的环境具有了某种规约性。
上述琴学文献中对琴事礼仪的规定和古琴艺术活动场所的选择有实用合理的一面,端正的抚琴姿态和洁净的手指状态符合古琴演奏的技术要求,对环境的要求也充分考虑古琴音量小而音色丰富的特点。但其中不少规定对于当代琴人来说过于繁缛且迂腐,甚至不利于古琴艺术传承与发展的要求,完全盲从对古琴艺术的发展无益。琴论中对琴人演奏礼仪的要求充满着仪式感,处处体现出高雅的君子格调。而其中提及的奇石流水、松竹梅林、亭台楼阁、净室高堂、游鱼白鹤这些人们在抚琴听琴时常择选的景观场所,随着千百年的琴景交织、物我相融,早已超越了其功能性、实用性,而成为了古琴艺术实践中的景观符号。这些符号在深深影响着古琴艺术实践活动的同时,也使古琴艺术与其他器乐彻底区别开来并获得其独有的品格与文化地位。
四、古琴音乐的符号化审美
从乐器本身的音响效果看,古琴是一种音色非常丰富的乐器。古琴外观造型如此多样,与其追求个性化的音色品质有密切的的关系。如《斫匠秘诀》中所记载:“古琴之音,或如雷震,或如水激;或如敲金戛玉,或如撞钟击磬;或含和温润,或高明敦厚。”(《琴苑要录》)[11](P22)说的便是不同的古琴所拥有的音色具有不同的表现力和“性格”,因此为了追求最好的艺术表现效果,琴家有时甚至会根据具体作品和演奏场所的需要而选择某种音色的琴进行演奏。琴人运用不同的演奏法则可以使古琴产生三种基本音色,分别是散音、泛音及按音,庄臻凤编《琴学心声谐谱》中述云:“凡散声,虚明嘹亮,如天地之宽广、风水之淡(澹)荡,此散弹也。泛音,脆美轻清,如蝶蜂之采花、蜻蜓之点水。按声,简静坚实,如钟鼓之巍巍、山崖之磊磊也。”[5](P305)其说的就是三种基础音色各自不同的艺术表现效果。绝大部分古琴曲是散、按、泛音交互使用,且旋律与和声融为一体,时起时伏、互相呼应。古之琴人普遍将泛、散、按三种音色与天、地、人联系起来,使得古琴的音色具有了象征符号的意味。
《太古遗音·三声论》中的相关论述非常经典:“夫泛声应徽不假抑按,自然之声,天声清也。律应气于地弦,象律管入地之浅深而为散声之次第,是为地声,地声浊也。……天声出于地声之上,人声出于地声之下,是谓天地人此言其分也。人声虽在弦下,而指按弦上。是谓天地人(之合也)。此言其势也。夫琴受成中天而为地声,上有天统焉,下有人声焉,而皆有徽节之应合,是各具一后天也。……近世曲操,天声少,而人声地声多,人与地相近,声类亦进,故也。天声径洁平易,人心好奇,用之者少。人者有余,天者不足,所谓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故善琴之君子,每不取乎按声之繁碎、巧急、淫艳良有以也。苟能以三才之道求之。斯得古音之正统欤。”[5](P109)
文中阐释了将泛、散、按三种基础音色与天、地、人联系起来原因,强调其中的秩序及彼此之间的应合之道,并将这些看似“虚”的道理,具体实现在琴的具体艺术表达中。其要求合理运用泛、散、按三声,尤其要求不可过度追逐演奏技巧(主要体现在人为因素较多的“按声”中)而失“古音之正统”。此外,古琴有七弦五音(散音),在中国传统乐论中,宫、商、角、徵、羽五音分别象征着古代社会的“君、臣、民、事、物”。这些论述体现了古之琴人对古琴音色运用的重视,也体现了古琴美学一如既往地将天地之道、人间之礼及艺术追求融为一体的传统。
古琴艺术的符号化审美方式在其音乐实践中还有多方位体现。比如在古琴传承中,为了便于教学,琴人创作了独有的指法手势图,这些手势图一方面再现了抚琴指法的具体且精确的手势动作;另一方面又通过鸟兽、龙凤、景观等绘画形象模拟出这些手势动作在姿态、动态和精神气质等方面的艺术形象。如明朝袁均哲编撰的《新刊太音大全》中,指示右手指法的“风惊鹤舞势”“孤鹜顾群势”“幽谷流泉势”,指示左手指法的“蜻蜓点水势”“文豹抱物势”“号猿升木势”等等。学者杨芬精辟地将手势图之特点归纳为“状其形,传其势”和“喻其声,达其境”。杨芬认为,结合了名称的手势图不仅可以模仿古琴演奏手势的模样和形状,更可以通达其内在的运动之势。有些手势图在说明手势的同时描摹音响效果,并进一步为习琴者引入空间想象以传递其中的审美意境。[12](P100-106+6)古琴指法手势图这种贯通于传统书论画论及琴学的表达方式,也从侧面体现了古琴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互文与互动。
此外,古琴曲所涉及的母题⑥,也常常具有象征性,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在各种自然、理想、情感、家国等琴曲母题中,自然母题的符号内涵是最丰富的。自然母题往往与“天人合一”的思想相联系,而其中的“月”“花鸟”“山水”等艺术形象又各自有其象征性并常常形成多重隐喻,内涵唯美而富含哲理。例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月是女性、安宁、美好事物及和谐的象征。相关的古琴名曲有很多,如表现了豪迈而孤寂边关情的《关山月》、闲适优雅的《良宵引》、超逸洒脱的《秋宵步月》等等。又如,大雁是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的象征。同时,又因为大雁有远避人群,择水草而栖的生活特点,古代文人也有以大雁比喻隐逸的高洁之士的传统。相关的琴曲亦有不少,如表现自然意趣的《平沙落雁》、表达怀才不遇怅然心情的《秋鸿》、抒发怀想忧国之情的《塞上鸿》等等。有关山水母题的琴曲更是多不胜数,诸如《高山》《流水》《潇湘水云》《山居吟》《碧涧流泉》等都是千古流传的名曲,它们承载了琴人对自然的热爱和山水情趣,甚至是中国山水精神的代表之一。
由于古琴的母题是人们在漫长的审美活动中通过创作、演奏和琴学讨论逐渐成型而来,又与其它中国传统艺术如诗歌、绘画、园林紧密互文。一方面,琴曲的母题是琴人共同的精神追求、文化品味、艺术格调的集中体现,具有某种约定性。这种约定性对琴人的演绎产生了艺术风格意义上的指引性甚至是约束性。另一方面,通过母题对琴曲背后的内涵进行深入解读与阐释,有助于人们在复杂的互文网络的支撑下,借助特定的艺术形象理解琴人的内在情感世界与精神追求。从这一角度看,琴曲母题也是一种内涵深刻而层次丰富的艺术符号。
结 语
由上述梳理可见,古琴艺术的符号化具有整体化和系统化的特点。整体化是指古琴艺术的符号学特征使其整体与其它中国民族器乐区别开来,独特性强、识别度高。系统化是指古琴艺术的符号化覆盖了选材、起源、形制、命名、琴人群体、作品、音响效果及相关艺术实践等各个方面,有机地形成了一个较完善的符号体系。我们知道,古琴艺术的符号化与中国文人阶层有密切关系,历代文人对古琴艺术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他们对古琴艺术的传承与创新、理论研究(包括琴学与演奏)、艺术创作(包括音乐、文学、绘画、建筑等)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这使得古琴成为一种少见的兼具哲思与美感的极高雅艺术。中国传统琴论对古琴艺术中的符号现象做了许多归纳、总结和阐释,但总体来说侧重于从古琴艺术中的肖似符号出发,论证其象征性。历代琴人力图通过他们的古琴理论建设将古琴象征符号的能指与所指规定起来,这其中有热爱古琴的缘由,也有出于建设儒家礼乐的需要。但过度符号化也限制了古琴的发展,重道轻器、重德轻艺,过于强调古琴那些被僵化的符号特征使得古琴的传承范围越来越窄,以至于到了民国时期古琴经历了失传的风险,这种情况应引发当代琴人的反思与警惕。⑦[9](P56-61)中国近现代的琴学研究围绕着琴史、古琴美学、演奏、打谱、琴曲分析等主题不断深入,并广泛吸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现已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趋势,可谓是硕果累累。但从符号学角度对古琴艺术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少,古琴艺术的符号学研究空间巨大,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
注释:
①我国当代著名古琴演奏家李祥霆认为:从《尚书》《诗经》等文献中可知,古琴在商周时期就已经成为很有表现力的乐器,而且受到社会的重视,其虽然在当时参与了敬神和祭祖的重要活动,但古琴首先是作为诸乐器中的一种而存在,并广泛地为人们进行情感交流、艺术交流和社会交往服务。其中具体讨论可参见李祥霆《古琴综议》第21-2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②早期的古琴的形制与发声机制与现存的唐宋以后的传世琴的形制差距较大。其弦数不定,有一弦、五弦、九弦、十弦、七弦等。目前可见的早期琴器实物有战国初曾侯乙墓出土的五弦琴和十弦琴、战国中期楚墓七弦琴、西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七弦琴。它们的形制与相应的音乐表现力与现今人们熟悉的古琴有很大差距,但也有非常重要的相同点,比如有面板和底板、弦下无柱等。详参刘承华《古琴艺术论》第4-11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③“天圆地方”主要指我国古代对天地结构的一种认识,这种认识对中国古代文化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祭祀使用的礼器如玉琮;生活用品如规矩铜镜;建筑如祭坛(故宫的天坛、地坛是经典例子)、客家围屋,甚至墓穴;乐器构造如古琴、阮等等都带有“天圆地方”的影子。
④本文中的“古琴艺术实践”包括琴器形制创新、斫琴、古琴曲创作、古琴演奏、琴曲欣赏、琴曲传承、古琴雅集等一系列与古琴有关的艺术活动。
⑤范煜梅编的《历代琴学资料选》中收录了宋代《太古遗音》(署名为“佚名”)的琴学资料,该版本中的琴学内容与笔者手上的杨抡在田芝翁原版上重辑的《太古遗音》略有不同但格调相近,后者关于儒士、道士、德士、隐士、黄门五士的言论收在其《五士操论》中,其中只阐明了五者的优点而并没有其它严格的规定。
⑥刘承华在《古琴艺术论》中介绍:“古琴音乐的‘母题’是指在音乐行为(包括创作、演奏、演唱等)中经常出现的主题或题材。……音乐母题的这种独特性是由文化赋予的。一种音乐选择以什么样的母题作为表内容,从根本上说,是由这音乐主体的生存状况和文化形态决定的。所以,要像深入了解一种音乐,就必须了解这种音乐所经常表现的母题;而想要了解一种音乐的母题,又必须了解形成这种母题的文化,把握这种母题所暗含着的深层文化意蕴。”详参刘承华《古琴艺术论》第143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⑦有关于文人对古琴艺术发展影响的利弊,苗建华在《古琴美学思想研究》中有较为深入的探讨。详参苗建华《古琴美学思想研究》第56-61页,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