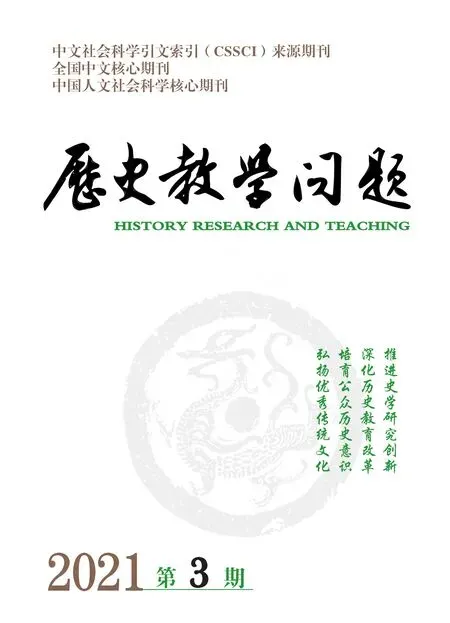论吕思勉的古书考辨成就与反思
2021-12-29陈冬冬
陈 冬 冬
辨伪学是古文献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包括辨伪书、辨伪说二方面的内容。20 世纪是中国辨伪学由学科创建走向多元发展的时代。特别是20 世纪上半叶,中国辨伪学在辨伪理论的构建、近代辨伪方法的产生、辨伪思潮的兴起、辨伪成果的激增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果,构建了学科发展的基础。[1]刘重来:《中国二十世纪文献辨伪学述略》,《历史研究》1999 年第6 期。吕思勉作为“现代史学四大家之一”,[2]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215 页。不仅著有二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史,在历史学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成就;而且亲身参与了20 世纪中国辨伪学的构建与探索,在考辨伪书、伪说方面均取得了卓有特色的成果,但现有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十分充分。[3]学术界关于吕思勉的辨伪学成就研究,主要有李波:《吕思勉与古史辨》(《史学史研究》2011 年第2 期),认为吕思勉与顾颉刚、童书业建立了长期学术交往,亲身参与了《古史辨》的编著,但在辨伪方面有独到见解,不能简单看作“古史辨派”的一员;何周、张子侠:《吕思勉的文献辨伪实践》(《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 年第5 期),考察了吕氏对《孝经》《竹书记年》等29 种文献的辨伪成果;何周:《吕思勉的辨伪思想》(《淮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 年第6 期),将吕氏辨伪思想归纳为古书不容轻信、不容过疑,书无全伪、伪书各有其用,古史“层累地造成”、又“逐渐地剥落”,古书中未见记载者未必不存,儒家经传史料价值接近,实物未必皆可信。本文拟以吕思勉的古书考辨为中心,考查其学术来源,对其取得的成就、进行的反思作进一步研究,以期发掘出其辨伪学的特色。
一、吕思勉古书考辨的学术渊源
吕思勉的古书考辨工作自成体系、成果众多。通过梳理,不难发现其思想及方法有以下学术渊源:
其一,中国古代辨伪学成果的影响。中国辨伪学的学科体系虽然构建于近代,但古代学者已经取得丰富的辨伪成果。例如,对于《古文尚书》的辨伪,就是宋代吴棫、朱熹,直至清代阎若璩、丁晏等拾级而上、不断完善的过程。吕思勉在《经子解题》中对此类古代辨伪学成果有较多梳理与吸收。他认为《伪古文尚书》出现后,“至宋之胡棫、朱熹,始疑古文《尚书》为伪书,数十篇中,文体之难易相差甚大,决不能无疑也”,从文体难易入手,揭开了怀疑《伪古文尚书》的序幕。接下来,明代“梅鷟致疑《伪古文尚书》,从客观方面考证之,虽不甚精密,实开此案之先河”,开始收集证据考辨伪古文。最后,“清之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而证据乃大备……阎若璩之《古文尚书疏证》只证明《古文尚书》为伪造,尚未证明出于何人手笔,丁晏之《尚书余论》出,《伪古文尚书》之作者,乃属于晋之王肃矣”,最后确认了伪古文的伪书性质及其作者。由于充分吸收了古代学者的考辨成果,吕氏对《尚书》的考辨结论,“其经说固有问题,即经之文本,亦有真伪之别,伪者称之为伪古文可也”,[1]吕思勉:《群经概要》,《吕思勉全集》第16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第71—72 页。就显得有较强的说服力。
其二,清代常州今文学的影响。清代常州今文学者从分辨今古文入手,取得了丰富的辨伪成果,是近代辨伪学最突出的代表。吕思勉家族自明代永乐年间之后世居常州,吕氏在读书治学过程中也受到常州今文学派影响。他回忆称:“稍长,遍读近世经师之书,得吾乡刘申受先生之作……然后知圣门微言大义之所在。……盖自我武进庄氏、刘氏始绍《春秋》治学于既绝,再传至仁和龚氏、邵阳魏氏,而其说益昌。近世巨儒乃推其说以见之于行事,乃有晚近数十年之变。”[2]吕思勉:《西营刘氏清芬录序》,收入《论学丛稿(上)》,《吕思勉全集》第11 册,第319 页。盛赞以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乡贤开晚清今文学风气之先。吕思勉又受到今文学派后学康有为的影响。吕氏回忆称:“至于学问宗旨,则反以受漠不相识的康南海先生的影响为最深,而梁任公先生次之。”[3]吕思勉:《从我学习历史的经历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收入《论学丛稿(下)》,《吕思勉全集》第12 册,第748 页。又称:“成童时,最信康梁之说。”[4]吕思勉:《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收入《论学丛稿(下)》,第1221 页。认为康有为是对其思想影响最大的学者。
吕思勉的辨伪学观点,直到上世纪20 年代初期,仍与晚清今文学者保持高度一致。例如,吕氏在1921 年所作《答程鹭于书》中称“今儒多知古文经为刘歆所伪造”,又称“今古文在考古上之价值如此,吾人从事于考古之时,不能不将二者分别清楚,自无待言,盖今文家源出孔子,古文家祖述莽、歆。则考见孔子之学说真相者,固不容不剔除莽、歆之言;欲考见莽、歆之学术真相者,亦不容不剔除孔子之语”。完全认同今文学者刘歆伪造古文说。他还认为:“今后学者之任务,则在就今文家言,判决其孰为古代之真事实,孰为孔子之所托,如此,则孔子之学说与古代之事实,皆可焕然大明,此则今之学者之任务也。”[5]吕思勉:《答程鹭于书》,收入《论学丛稿(上)》,第266—269 页。认为今后辨伪学的任务,只是沿着今文家的道路,剔除古文伪经,便可恢复孔子学说的原貌。吕氏早年弟子钱穆称:“惟忆诚之师谨守其乡前辈常州派今文经学家之绪论。”[6]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2005 年,第59 页。仅就吕氏这一阶段的观点来看,并非虚言。
其三,“古史辨”派的影响。上世纪初,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兴起,怀疑、考辨古书、古史真伪在学术界蔚然成风,廓清了有关中国古史的可疑史料与谬说,奠定了中国现代辨伪学的基础。吕思勉是“古史辨”运动的直接参与者。1934 年,《古史辨》第5 册选入了吕思勉《辨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1941 年,吕思勉更与童书业等完成了分量最大、内容最充实的《古史辨》第7 册的编纂。《古史辨》第7 册题为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具体分工如童书业所言:“但这册《古史辨》在上海出版,也得到了许多意外的助力,如史学界前辈吕诚之(思勉)先生帮助我们的地方实在不少,使我们的工作大为增光。……这册《古史辨》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吕先生独立校阅的,其他三分之二,是我和吕、杨二先生合校的。”[7]童书业:《自序二》,《古史辨》第7 册(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第7 页。认为吕思勉完成了第7册绝大多数编校工作。
吕思勉不仅亲身参与了“古史辨”派的活动,在考辨思想上也受到顾颉刚等人影响。他提出:“疑古之说初出,世人大共非訾,然讫于今日,其理卒有不可诬者。……古史之传于今者,探其源,盖有神话焉,有十口相传之辞焉,有方策之遗文焉,有学者所拟议焉,且有寓言无实者焉。其物本樊然淆乱,而由今观之,抑若略有条贯者,皆节经损益润饰而成。其人不必相谋,而其事一若相续,此顾君颉刚所由谓古史为层累造成。”认为流传到今日的古史来源多途,经过由混乱到有条理的加工过程。疑古学派及顾颉刚“层累造成的古史”说自有其合理性。他又提出:“宋儒病之……其所立说,则亦不足信也。清世儒者又病之……今之所谓疑古者,特更进一步,辨析及于先秦而已。溯流者必穷其原,理固宜然,亦抑势所必至,几亦循前人之途辙而更进而已,又奚足怪?”[1]吕思勉:《古史辨第七册自序》,收入《论学丛稿(下)》,第787—788 页。肯定疑古思潮有继承自宋代、清代学者的历史渊源,并非向壁虚造。
吕思勉的古书考辨虽受到以上学术渊源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并未简单照搬。对于古代学者古书考辨的成就,他并不盲从。例如,唐代学者刘知几的《史通》、清代学者崔述《考信录》的辨伪成就,均曾受到胡适、顾颉刚等人推崇。吕氏却提出:“子玄疑古,颇据《汲冢书》及《山海经》,此皆伪物不足据,亦其所以不见信于世也。”[2]吕思勉:《史通评》,《吕思勉全集》第17 册,第275 页。认为刘氏疑古以伪书作为材料,影响其考辨成果的可信度。吕氏又提出:“《崔东壁遗书》,近人盛称其有疑古之功,此特门径偶然相合,其实崔氏考据治学,并无足称……虽能多发古书之误,实未能见古事之真。”[3]吕思勉:《读崔东壁遗书》,收入《论学丛稿(下)》,第742 页。对崔氏的疑古、考据成就评价有限。对于晚清今文学者的观点,吕思勉也逐步进行扬弃。吕氏1923 年所著《群经概要》中认为:“《春秋董氏学》系根据《春秋繁露》而编纂者,《春秋复始》内谓《左传》《穀梁》皆刘歆所伪造。以余观之亦未必然也。”[4]吕思勉:《群经概要》,《吕思勉全集》第16 册,第81 页。不再盲从今文学者的刘歆伪造《左传》说。对于“古史辨”派的考辨,吕思勉亦有不同意见。他认为:“胡适之摘其‘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等语,谓为反对东周后之横征暴敛,引《硕鼠》等诗为证,皆非也。……《老子》一书,皆发挥玄理之语,非对一时政治立言;又观其问题之古,即知其书非出周代,亦不得引风诗为证也。”[5]吕思勉:《经子解题》,《吕思勉全集》第16 册,第148 页,第162 页,第183 页。不认同胡适、顾颉刚等人《老子》晚出说。
二、吕思勉古书考辨的成果与方法
吕思勉的古书考辨,在古代辨伪学、晚清今文学派及“古史辨”派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他的古书考辨,集中在《先秦学术概论》《群经概要》《经子解题》三部著作中,还有部分成果散见于《论学丛稿》等著作与论文中。仅以《概论》《概要》《解题》三书而言,共考辨经部著作14 种、史部著作3种、子部著作31 种,[6]经部含《诗经》《书经》《仪礼》《礼记》《大戴礼记》《周礼》《周易》《左传》《公羊传》《 梁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史部含《逸周书》《战国策》《山海经》,子部含《老子》《庄子》《列子》《荀子》《晏子春秋》《墨子》《公孙龙子》《管子》《韩非子》《商君书》《尹文子》《慎子》《邓析子》《吕氏春秋》《尸子》《鹖冠子》《淮南子》《关尹子》《鬻子》《文子》《李子》《公孙龙子》《吴孙子》《吴起》《军礼司马法》《尉缭子》《六韬》《素问》《灵枢》《难经》《神农本草经》。尤其致力于对先秦经部、子部古籍真伪的判别。在考辨过程中,主要利用了以下四种考辨方法:
其一,从目录文献入手,考察古籍文献的远流以辨其真伪。例如,吕思勉考辨《晏子春秋》时,即使用此法:“此书《汉志》八篇。《史记正义》引《七略》及《隋》《唐志》皆七卷,盖后人以篇为卷,又合杂上下为一篇。《崇文总目》作十四卷,则每卷又析为二也。其书与经子文辞互异,足资参订处极多;历来传注,亦多称引;绝非伪书。”[7]吕思勉:《经子解题》,《吕思勉全集》第16 册,第148 页,第162 页,第183 页。认为此书在古代目录中卷数分合有绪,又可与其他文献相互证明,并非伪书。
其二,从文风语体入手,考查其出现的特定文风、语词、文体等以辨其真伪。例如,吕思勉考辨今本《邓析子》时,主要使用了该法:“愚案此书有采掇先秦古书处,又有后人以己意窜入处。核其词意,似系南北朝人所为。如‘在己为哀,在他为悲’‘患生于宦成,病始于少,祸生于懈慢,孝衰于妻子’等,皆决非周、秦人语也。”[8]吕思勉:《经子解题》,《吕思勉全集》第16 册,第148 页,第162 页,第183 页。通过考察其中多数文句文风语体有南北朝风格,断定该书虽采辑少量古书文句,整体上仍并非先秦古书。
其三,从征引文献入手,考查其传本的异同、时代的先后等以辨其真伪。例如,吕思勉曾用此法考辨传世本《文子》:“今本《文子》,多袭《淮南》,亦取《庄子》《吕览》,多浅鄙之言。引《老子》处,尤多误解,决为后世伪书。”[9]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吕思勉全集》第3 册,第391 页。认为通过分析今本《文子》多袭用《庄子》《淮南子》《吕氏春秋》等文献之言,引用《老子》处尚有误读,判断其为伪书。
其四,从思想内容入手,考查其体现的学术观点、语词文风等以辨其真伪。例如,吕思勉在考辨今本《关尹子》时,曾应用此法:“今之《关尹子》,多阐佛理,又杂以阴阳之说。并有龙虎、婴儿、蕊女、金楼、绛宫、宝鼎、红炉等名,盖融合后世之道家言及佛说而成者。其文亦似佛经,全不类先秦古书。”[1]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吕思勉全集》第3 册,第390 页,第391 页。通过考察今本中含有后世道教、佛教产生后才出现的思想内容,判定其并非先秦古书。
吕思勉在考辨古书时,还能注意综合运用多种考辨方法,使结论平实可靠。例如,在考辨《鬻子》时,吕氏就采用了综合考辨:“道家伪书,又有《鬻子》。案《汉志》,道家有《鬻子》二十二篇,注曰:‘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小说家又有《鬻子》说十九篇,注曰:‘后世所加。’《隋志》道家,《鬻子》一卷,小说家无。《旧唐志》,小说家有,道家无。《新唐志》同《隋志》。今本凡十四篇,卷首载唐永徽四年华州县尉逢行珪进表。各篇标题,皆冗赘不可解。又每篇皆寥寥数语,绝无精义。《列子》之《天瑞》《黄帝》《力命》三篇,各载《鬻子》之言一条。《贾子·修政下》,亦载等问于鬻子事七章,此书皆未采及,伪书之极劣者也。”[2]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吕思勉全集》第3 册,第390 页,第391 页。考察了《汉书·艺文志》以下多种等目录文献记载,对比了《列子》《贾子》等书的征引,并判定其思想浅薄,综合应用三种考辨方法断定今本《鬻子》属于层次较低的伪书。
吕思勉认为:“书籍在今日,仍为史料之大宗。”[3]吕思勉:《先秦史》,《吕思勉全集》第2 册,第11 页,第11 页。在考辨古书时,多利用传世文献作为主要材料。除了对从历史事件、作者生平入手的方法使用不多外,善于利用不同考辨方法进行综合研究,达到了上世纪下半叶出土文献大量涌现前古书考辨的最高成就。由于功力深厚,其考辨成果能接受时间检验。例如,《鹖冠子》一书,自唐柳宗元判定为伪书之后,陈振孙、晁公武、王应麟、胡应麟、姚际恒多据此立说。近代张心澂集辨伪之大成的《伪书通考》,亦将此书定为伪书。《鹖冠子》伪书说几成定论。吕思勉考辨认为:“按《汉志》仅一篇,韩愈时增至十六,陆佃注时,又增至十九,则后人时有增加,已绝非《汉志》之旧,然今所传十九篇,皆古词茂义,绝非汉以后人所能为。”认为今本《鹖冠子》篇目虽与目录记载不合,但其语言风格当为先秦以前,绝非伪造,肯定该书“实为子部瑰宝”。[4]吕思勉:《经子解题》,《吕思勉全集》第16 册,第194 页,第144—145 页。直到上世纪70 年代马王堆帛书出土后,学者发现今本《鹖冠子》语句多与帛书相合,才推翻了这一伪书公案。[5]李学勤:《马王堆帛书与鹖冠子》,《江汉考古》1983 年第2 期。吕思勉对《鹖冠子》的考辨,虽仅利用了传世文献,却能为出土文献所证实,体现了其辨伪学的卓识。
三、归纳古书“通例”,反思古书考辨方法
吕思勉不满足于仅仅依赖传世文献资料,应用近现代通行辨伪学方法讨论古书真伪,而能够从先秦古书独有的性质与特点出发,总结古书“通例”,对近代“疑古”思潮及考辨方法进行反思。他认为:“近二十年,所谓‘疑古’之风大盛,学者每訾古书之不可信,其实古书自有其读法,今之疑古者,每援后世书籍之体例,訾议古书,适见其鲁莽灭裂耳。”[6]吕思勉:《先秦史》,《吕思勉全集》第2 册,第11 页,第11 页。指出疑古派以后世书籍体例,考辨先秦古书真伪,存在不小的局限性。吕氏对古书通例的反思与总结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其一,先秦诸子大抵不自著书。吕思勉认为,先秦古书多非题名作者本人所著。他指出:“先秦诸子,大抵不自著书。今其书之存者,大抵治其学者所为;而其纂辑,则更出于后之人。书之亡佚既多,辑其书者,又未必通其学;不过见讲此类学术之书共有若干,即合而编之,而取此种学派中最有名之人,题之曰某子云耳。然则某子之标题,本不过表明学派之词,不谓书即其人所著;与集部书之标题为某某集者,大不相同。集中记及其人身后之事,及其文词之古近错出,固不足怪。”[7]吕思勉:《经子解题》,《吕思勉全集》第16 册,第194 页,第144—145 页。即先秦古书的题名作者、记录者、整理者常常并非一人。书籍往往先由某派先师口头传授,接下来为其门人记录成文,最后由后学将学派、性质相近的若干篇章汇编成一书,取此派最著名的学者题名为“某子”。其中记录相传作者之后的事迹,或混杂不同时代语言,都是常见现象。
其二,古书多“寓言”。吕氏认为:“至于诸子书所记事实,多有讹误,此似诚有可疑;然古人学术,多由口耳相传,无有书籍,本易讹误。而其传之也,又重其义而轻其事;如胡适之所摘庄子见鲁哀公,自为必无之事,然古人传此,则但取其足以名义;往见者果为庄子与否,所见者果为鲁哀公与否,皆在所不问。岂惟不问,盖有因往见及所见之人,不如庄子及鲁哀公之著名,而易为庄子与鲁哀公者矣。然此尚实有其事。至如孔子见盗跖等,则可断并其事而无之,不过作者胸中有此一段议论,乃托之孔子、盗跖耳。此则所谓‘寓言’也。此等处若据之以谈事实,自易谬误;然在当时,固人人知为‘寓言’。故诸子书中所记事实,乖谬者十有七八,而后人于其书,仍皆信而传之。胡适之概断为当时之人,为求利而伪造;又讥购求者不能别白,亦未必然也。”[1]吕思勉:《经子解题》,《吕思勉全集》第16 册,第145 页,第145 页,第144—145 页。即先秦古书所记事件多有错误,或由口耳相传而致误,或由借事说理而致误。特别是如庄子见鲁哀公、孔子见盗跖等,虽明显与史实不符,却是古人借事说理的例证,其性质属于寓言而非史实。此类记事讹误,不能认为系古人牟利伪造,或购求之人不能辨别,作为判定古书真伪的依据。
其三,古书多荟萃众说而成。吕氏认为:“则古本有一家之学,而无一人之言,凡书皆荟萃众说而成,而取一著名之人以为标题耳;而辗转流传,又不免有异家之书羼入。此古书之所以多错乱。然编次之错乱是一事,书之真伪又是一事,二者不容相混也。”[2]吕思勉:《先秦史》,《吕思勉全集》第2 册,第22 页。古书既非一人手著,而是某一学派文献的汇编,则不免混杂一派之中多名学者学说。而流传久远,又不免有其他学派书籍混入。故而古书时常出现编排混乱的现象,却并不能简单据此认定为伪书。
其四,古书有但传其意者、有兼传其词者。吕氏认为:“又古人之传一书,有但传其意者,有兼传其词者。兼传其词者,则其学本有口诀可诵,师以是传之徒,徒又以是传之其徒;如今瞽人业算命者,以命理之书口授其徒然。此等可传之千百年,词句仍无大变。但传其意者,则如今教师之讲授,听者但求明其意即止;迨其传之其徒,则出以自己之言;如是三四传后,其说虽古,其词则新矣。故文字气体之古近,亦不能以别其书之古近也,而况于判其真伪乎?”[3]吕思勉:《经子解题》,《吕思勉全集》第16 册,第145 页,第145 页,第144—145 页。即古人传授一书,有“兼传其词”者,即师徒之间如传诵口诀不改易字句,即使流传千百年之久,语言文字仍变化有限;又有“但传其意”者,则师徒传授只求学说大意,弟子可以重新表述,则数代之后文意虽变化不大,而语词早已更新。故而不能简单以语体风格的早晚辨别文献真伪。
吕思勉在归纳古书通例的基础上,一方面坚持考辨古书真伪,“读古书固宜严别真伪,诸子尤甚”;另一方面又对近代人的考辨方法有所反思,“然近人辨诸子真伪之术,吾实有不甚敢信者”。对于近代学者习以为常的“(一)据书中事实立论,事有非本人所能言者,即断为伪”,“(二)就文字立论……又或以文字体制之古近,而辨其书之真伪是”二种方法,吕氏皆有所保留,“予谓二法皆有可采,而亦皆不可专恃”。他指出“胡适之摘《管子·小称篇》记管仲之死”“胡适之所摘庄子见鲁哀公,自为必无之事”,均为“据书中事实立论”之法,实为不明“先秦诸子大抵不自著书”“古书多寓言”通例之误;“梁任公以《老子》中有偏将军、上将军之名,谓为战国人语”,使用“就文字立论”之法,实为不明“古书多荟萃众说而成”“古书有但传其意者、有兼传其词者”通例之误。[4]吕思勉:《经子解题》,《吕思勉全集》第16 册,第145 页,第145 页,第144—145 页。由前述吕思勉古书考辨的成果与方法部分可知,吕氏对于从历史事件等入手考辨古书真伪的方法(即据书中事实立论之法)完全没有使用,对从文风语体入手考辨古书真伪的方法(即就文字立论之法)有所使用但较为谨慎,正是其基于对古书通例的认识,反思古书考辨方法的体现。
吕思勉对古书通例的总结与思考,是其针对近现代今文学派、“古史辨”派等疑古思潮兴盛一时,但相关古书考辨方法仍不完备进行的反思,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吕氏同时代的余嘉锡在《古书通例》一书中,曾做过性质相似的工作。将吕思勉、余嘉锡归纳古书通例的工作进行比较可知:
其一,从写作与出版时间上看,吕思勉早于余嘉锡。吕思勉在成书于20 世纪20 年代中期、出版于1926 年的《经子解题》中对该问题已有成型论述,又于出版于20、30 年代的《先秦学术概论》《先秦史》诸书中多次阐发。余嘉锡于上世纪30 年代年间在北京各大学讲授校读古籍课程时,编写了《古书通例》(一名《古籍校读法》)作为授课讲义。该书长期只有临时印本,未曾公开出版,直到余氏去世多年后的1983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印行。
其二,从内容上看,余嘉锡较吕思勉更为详尽。吕氏归纳的“先秦诸子大抵不自著书”“古书多寓言”二条通例,与余氏归纳的“古书多造作故事”“古书不皆手著”二条通例标题与内容基本等同。吕氏多出“古书多荟萃众说而成”“古书有但传其意者、有兼传其词者”二条通例,余氏多出“诸史经籍志皆有不著录之书”“古书不题撰人”“古书书名之研究”“汉志著录之书名异同及别本单行”“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汉魏以后诸子”“古书单篇别行之例”“叙刘向之校雠编次”“古书之分内外篇”九条通例。总体而言,余氏归纳的通例数目多于吕氏。以内容相近的吕氏“先秦诸子大抵不自著书”,与余氏“古书多寓言”“古书多造作故事”“古书不皆手著”通例相比,吕氏的论述较为精炼,仅提出核心观点,并略举一、二条实例进行论证;余氏则将前者细分为“托之古人,以自尊其道也”“造为古史,以自饰其非也”等七种类型,后者细分为“编书之人记其平生行事附入本书”“古书……并载同时人之辩驳”等五种类型,各种类型下又详细举例,论述较吕氏完备不少。
其三,从系统性上看,余嘉锡较吕思勉更胜一筹。吕氏学说散见于《经子解题》《先秦学术概论》《先秦史》诸书,每一书中相关论述多局限于数千字的一、二章节之中;余氏学说集中于七万字的《古书通例》一书之中。
余嘉锡古书通例学说虽更加详尽、系统,但内容上有部分相近之处,时间上又明显晚于吕思勉。余氏总结古书“通例”,反思辨伪方法的工作,无论是否受到过吕氏直接影响,仍可视作在其基础上的补充与完善。[1]据笔者所见,余嘉锡《古书通例》对吕思勉相关著作无直接引用,亦未见二人交游记载及论学信札。二人对“古书通例”的归纳,可能是各自相对独立的发明。《古书通例》获得了学界高度评价,甚至有学者认为余氏根据传世文献对古书通例的推断,与20 世纪下半期出土文献相契合,显示了其深厚的传统学术功底。[2]李零指出:“余先生读书多广,善于提炼,能由博返约,直探古人心曲,故验之以出土文献,若合符契。”(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收入《李零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27 页)相比余氏所获得的盛誉,吕思勉对上世纪初总结古书通例、反思近代古书考辨相关工作有发轫之功,其贡献不容忽视。
四、“疑古”“考古”“释古”三者不容偏废
20 世纪10、20 年代“古史辨派”,“在古书真伪和年代问题上,一方面廓清了传统古典学的不少错误观点,一方面又对古书搞了不少冤假错案”。[3]裘锡圭:《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收入《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5 页。总体而言,存在破坏过度,建设不足的倾向。针对这些问题,吕思勉对古书考辨的任务进行了反思。
其一,古书之伪者并不多,伪书仍有其用。“古史辨”派对古书总体上持怀疑态度。顾颉刚认为:“古物出土愈多,时常透露一点古代文化的真相,反映出书籍中所写的幻想,更使人对于古书增高不信任的意念。”[4]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1 册,第78 页。吕思勉与此相反,认为“古书之伪者并不多”,[5]吕思勉:《先秦史》,《吕思勉全集》第2 册,第22 页。对古书总体上持信任态度。对于所谓“伪书”,吕氏认为“凡书无全伪者”,是真伪材料的混合物。例如,他认为《孔子家语》中,“王肃以己意羼入处固伪,其余仍自古书中采辑;又其将己意羼入处,以为孔子之言则伪,以考肃说则真矣”。即《家语》是王肃之说与古书材料的混合物,王肃之说虽非孔子之说,但研究王氏学说仍有其价值。故而,吕氏提出“故伪书仍有其用,惟视用之之法何如也”,[6]吕思勉:《史学与史籍》,《吕思勉全集》第18 册,第30 页。肯定伪书材料如能正确使用,仍存在史料价值。
吕思勉认对伪书或古书中有伪的部分进行考辨,确定其真实年代,仍能发挥其史料价值。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将辨伪学的任务由拘泥于古书是否作伪,去伪存真,调整为考证古书形成的真实年代,各安其位。20 世纪70 年代以后,由于出土战国、秦汉文献大量涌现,李零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用古书年代学替代辨伪学”,[7]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 年,第215 页。印证了吕氏的观点的预见性。
其二,古书要在分别观之,逐一加以审核也。吕思勉认为:“故知古书不容轻信,又不容过疑;要在分别观之,逐一加以审核也。”[8]吕思勉:《读史札记(上)》,《吕思勉全集》第9 册,第603 页。既然古籍真伪夹杂,那么对其既不可过于相信,又不可过度怀疑,关键在于考辨。如何进行考辨?吕氏认为途径在于:“(一)后人伪造品,窜入其中者。(二)异家之言,误合为一书者。盖诸子既不自著书;而其后学之著书者,又未尝自立条例,成一首尾完具之作;而其书亡佚又多;故其学术之真相,甚难窥见。学术之真相难见,则伪品之窜入自易,异家之误会亦多。夫真伪混淆,则学说湮晦;异家错处,则流别不明;此诚为治诸子学之累;故皆急宜拣剔。拣剔之法,仍宜就其学术求之,即观其同,复观其异;即观其同异,更求其说之所自来;而求其所以分合之由。”[9]吕思勉:《经子解题》,《吕思勉全集》第16 册,第144—146 页。即通过考察古书中的学术观点,剔除其中伪造的部分,分别其中混杂的部分,则所剩部分仍属真实可信的史料。
吕思勉曾提出疑古、考古、释古三义:“今人与古人所见自不能同,听见异,于古说安能无疑。而古书之训诂名物,又与后世不同,今人之所欲知者,或非古人之所知;或则古人以为不必知;又或为其时人人之所知,而无待于言;而其所言者又多不传,幸而传矣,又或不免于伪误。如是求知古事者,安能废考释之功。……故疑古考古释古三者必不容偏废。”[1]吕思勉:《论疑古考古释古——为徐永清作》,《论学丛稿(下)》,第876 页。认为时人所见与古人不同所产生的怀疑即为疑古;但由于古书文字训诂与后世不同,所记内容又与后世偏重不同,所以想要了解古代事件,不能脱离对古书、古史的考证与阐释。对古代文献保持合理怀疑,是产生问题的起点;在此基础上进行考古、释古,挖掘古代文献的正面价值,才是学术研究的目的。
20 世纪30 年代,冯友兰提出当时中国史学界存在信古、疑古及释古三大流派,认为信古一派“大概不久即要消灭”,疑古“即是审查史料”,释古“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2]冯友兰:《冯序》,《古史辨》第6 册,第1 页。冯氏所谓疑古概念,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古史辨”派对古书的怀疑与批判,与吕思勉的考古较为接近;冯氏的释古说,与吕氏基本相同。上世纪下半叶,在一批先秦简帛文献出土,大量在近现代被判定为“伪书”的古书获得平反的背景下,李学勤曾接着冯友兰的释古说展开,提出要将文献研究与考古研究结合起来,走出疑古时代的著名论述。[3]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19 页。
吕思勉在主要利用传世文献的条件下,即已提出古书考辨不能停留于疑古,更要致力于考古、释古,显示出其学术观点的前瞻性。吕氏提出“考古”“释古”学说,酝酿于20 世纪30 年代撰写、1940 年出版的《先秦史》等书,系统表述于1944 年撰写的《论疑古考古释古》一文,与冯友兰1937 年撰写的《古史辨》第6 册序言提出释古说基本同时;其学说又与冯氏大同小异,应得到与冯氏同样的重视。他肯定“疑古”“考古”“释古”并重,既不止步于怀疑,提出要对先秦古书进行考证与阐释;又不盲目相信,提出要对其保持适当警惕,经过考核、拣剔才能使用。这一态度,可能较一味“疑古”或“走出疑古”的观点更为符合实际。
余 论
有学者认为,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疑古思潮,是近代以来中国古典学的第一次重建;20 世纪70年代以来,受赐于大批宝贵的出土简帛,学术界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开始了古典学的第二次重建。[4]裘锡圭:《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第2—4 页。吕思勉学习、继承了大量古代及近代今文学派的辨伪成果与方法,又亲身参与了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现代辨伪学工作,熟练地利用近现代辨伪方法考辨了近50 种古书,其中不少结论扎实可靠,可谓是第一次古典学重建的杰出代表。但他没有局限于被动参与近现代“疑古”思潮,而是在“古史辨”派的基础上自觉地继续推进。他先于余嘉锡总结归纳古书“通例”,对近现代辨伪方法进行反思;与冯友兰同时提出重视“考古”“释古”,对辨伪学的任务提出转换。这些观点被20 世纪下半期第二次古典学重建的结论所印证,预见了当代辨伪学的发展趋势。无论是总结近现代辨伪学的历史经验,还是找寻当代辨伪学的思想源头,吕思勉的古书考辨成就,都是一座不可忽视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