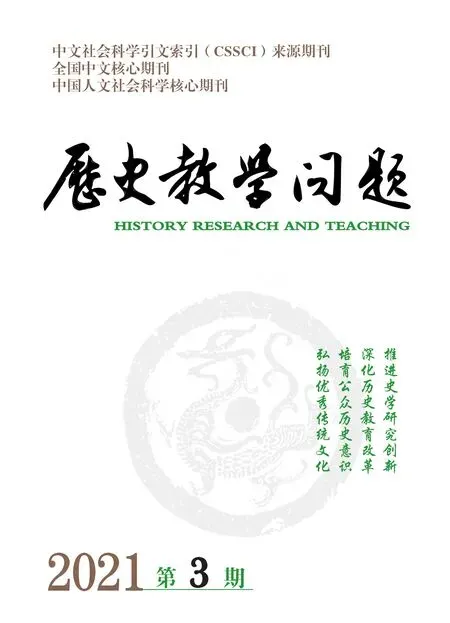论刘邦的“内防外制”之策略及得失
2021-12-29王振兴
王 振 兴
前人时贤对于刘、吕夫妇的集权措施多有论及,但一来学界对刘邦与吕后朝的内防与外制措施缺少系统性解读,多集中于对异姓诸王的防范,亦不曾论及刘邦屡屡亲征之缘由;二来仅从肯定角度评述汉初集权措施,鲜有论及其负面作用。笔者不揣谫陋,试图多角度探究和评价刘邦时期的“内防外制”策略,以求教于方家。
一、“内防”之策略
元勋宿将在“打天下”时代是君主仰仗的股肱,却也是“坐天下”时代的首要防范对象。汉初中央较之地方尚无压倒性优势,而亲贵宗室较之军功集团亦暴露出孤弱的不足。为强基固本,刘邦联手吕后祭出一套“内防”组合拳。
(一)扶植外戚,抑制重臣
外戚在中国传统史学语境中形象不佳,素与宦官群体同被视作祸乱朝政的两大源头。此乃权力继承愈发突出正统,官僚体制愈发成熟严密而排他,皇权专制体制愈发强化之必然。外戚与宦官干政不一定比皇帝乾纲独断更好,但绝不会比后者更坏。因为权力集中程度与为恶程度正相关。在帝国早期,外戚形象并不难堪。史公尝言:“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1]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九《外戚世家》,中华书局,2013 年,第2387 页。亦即外戚为皇室之重要辅弼。吕后之于刘邦亦然,不单是打天下的好帮手,亦是贯彻夫君遗志的守业者。
起兵之前,吕氏与刘邦密切配合,编织各种异象神迹,营造声势;起兵之后,吕氏倾其所有,“佐高祖定天下,父兄及高祖而侯者三人”。[2]班固撰,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卷三《高后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141 页。特别是在诛韩信、屠彭越过程中,吕后扮演了较之刘邦更加凶恶的角色,做了刘邦想做却不便做的事情,令诸大臣战栗。若非刘邦默许,妇人安敢如此?刘邦深知太子仁弱,诸刘势孤,根本无力独自应对军功集团之挑战,联合诸吕实乃必然。病危之际,他既未托孤于大臣,亦未交待于太子,独将政事托付于吕后,足见其借助外戚,匡扶刘氏,刘吕一体以抑制外臣之意图。故而,吕后作为刘邦的政治继承人,亦如刘邦之化身。吕后当权,一面扶植诸吕,一面构建二代刘吕联盟,矛头所指皆为文武大臣。故而,吕氏之兴实乃是刘邦有意而为之。正如吕思勉所论:“内任外戚,外封建宗室,此汉初之治法也。知此,则可与言吕氏之事矣。”[1]吕思勉《秦汉史》,中华书局,2020 年,第65 页。
再者,放弃废储,维持原状也是刘邦防内意识的体现。刘邦晚年因废长立幼曾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经多次拉锯,他在权衡得失利弊之后最终放弃废储之念,维持原状。时人论及此事,多以为是刘邦摄于支持太子一方势力庞大,难以撼动,故知难而退,即所谓“羽翼已成,难动矣”。[2]司马迁:《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2486 页,第2483 页。例如,臧知非教授以为:“刘盈的太子之位完全是大臣们保下来的,也就意味着功臣已经自觉地承认了这个仁弱的太子就是他们未来的主人,他们自然会尽心竭力地扶持刘盈,否则他们没有必要去得罪刘邦,反对改立太子。”[3]臧知非:《吕后》,现代出版社,2017 年,第186 页。此说固然有理,但恐不全面。首先,帝王权力独操,若刘邦一意孤行,臣子定难扭转局面。刘之所以放弃主张,乃自身权衡利弊之结果,而非慑于臣子反对。同时,功臣集团深知废立之事的敏感与利害,并不愿过多涉入。这才出现了“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的局面。[4]司马迁:《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2486 页,第2483 页。事实上,真正强谏者不过周昌与叔孙通而已,且未说动刘邦。直至“见留侯所招客从太子入见,上乃遂无易太子志矣”。[5]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3299 页。但张良参与此事乃是吕后集团胁迫所致,非其本意。至于策略是否有效则更无把握。既如此,又怎可说刘盈之位完全出自功臣力保呢?至于“羽翼已成,难动矣”,应视作刘邦对于辜负戚姬母子的借口与安慰之词。故而,所谓功臣集团成功保全刘盈储君之位的说法值得商榷。
那么,刘邦放弃废储之念的深层次考虑是什么呢?视皇权稳定为头等大事的刘邦自当所虑深远,即刘如意和戚姬方面势力过于单薄,倘若上位必然为大臣所制,江山易色亦有可能。反观刘盈与吕后显然更具优势。刘盈为嫡长子身份;吕后则坚毅果敢,与刘邦共定天下,对军功集团拥有仅次于刘邦的威慑力。亲贵如卢绾者亦对其畏惧三分。再者,作为刘邦的最佳拍档,吕后通过自身权谋并仰仗父兄、妹婿之力在朝中积累了一定实力,此更是戚姬方面无法比拟的,亦即刘邦清楚地意识到唯有吕氏方能在自己百年之后团结和制衡实力强劲的军功集团。团结和制衡貌似冲突,实则不然。所谓团结只是权力实现均势后的表象,而能否实现权力的制衡才是团结局面出现与否的根本。
吕后在掌权的15 年间贯彻刘邦遗志,凭借自身权谋与威慑力,左右开弓,恩威并施,内防功臣集团,外制强宗大藩,能够基本维持政局之稳定,殊为不易。虽计穷力竭,顾此失彼,难保身后之事,致使诸吕倾覆,但对于巩固刘汉天下而言,吕后可谓功莫大焉。
(二)敲打萧、曹,震慑百官
猜忌是专制权力的本性,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君臣有义”不过是美好的政治想象。即便是对于恭谨勤勉,居功至伟的萧何,尚算豁达的刘邦也未曾放松戒备。《汉书·萧何曹参列传》共记载四则刘邦与萧何的“交锋”。在前三次考察中,鲍生、召平和门客(甲)分别助萧何勘破刘邦意图,成功避祸。但公忠体国的萧相国难改职业习惯,终因为民请上林苑空地而横遭下狱,蒙受不白之冤。若非王卫尉仗义执言,萧何免不了遭受更多牢狱之苦。出狱后,萧何愈发如履薄冰,甚至不得不刻意霸占民田以自污,足见其隐忍。遭受敲打的不仅是萧何,作为刘邦在军方的首席代表——曹参亦受到贬黜和外放齐国的处置。
曹参在武人集团中威望甚高,军功卓著,仅次于韩、彭、英等王。自汉二年(前205 年)八月起,他以假左丞相身份追随左丞相韩信渡河开辟第二战场,擒魏豹,斩陈馀,降燕、代,下齐国,二人精诚合作,立下不世之功,韩信先升相国,后封齐王,期间曹参升任右丞相之职。汉五年(前202 年),韩信徙为楚王。曹参归汉相印,随后改任齐相国,“孝惠帝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6]司马迁:《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第2464 页,第2464 页。无论是齐相国,或是齐丞相,较之汉丞相而言,毕竟属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左迁”,缘何如此呢?曹参虽为沛县旧人,但自渡河击魏始,“长期追随韩信,为其第一助手……所获军功也多与韩信有关,而韩信又是刘邦最为猜疑和忌惮的对象”。[7]王振兴:《汉初君臣博弈背景下的刘吕联盟探析》,《社会科学论坛》2019 年第3 期,第67 页。若再联系封侯排次之时,刘邦不取众望所归的曹参,而是强推萧何为首功,足见外放曹参乃是防范和敲打朝中武人的重要举措。当然,曹参经受住了考察,“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8]司马迁:《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第2464 页,第2464 页。萧相国病逝,曹相国接班。
(三)崇文抑武,重建朝仪
病危之际,刘邦尚且嫚骂医者:“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1]班固撰,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卷一《高帝纪》,第119 页。夺取天下的现实令编户民刘邦忘乎所以,自感天命所归。但恐怕“天命论”惟在陆贾为代表的知识阶层较有市场,对于依仗拳头,推崇事功的武人集团而言,所谓天命,玄而又玄。樊哙问陆贾:“自古人君皆云受命于天,云有瑞应,岂有是乎?”[2]刘歆:《西京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28 页。马上取天下的汉初武人不信天命,后世武人亦不信天命。布衣天子的景象揭示了天命思想的虚伪性,对皇权理论产生了不小的冲击,更使得皇帝群体陷入某种自相矛盾的困境之中。打天下时,祭出兵强马壮者为之的幌子,坐天下时,搬出一套天意民心的谎言。而武人集团的亲身经历,较为憨直的职业性格使得其难以信服这套骗人的把戏。既如此,武人集团自然成为坐天下时代的首要防范对象。所谓兔死狗烹成为皇权时代越发普遍的政治现实,远较封建时代为甚。汉初武人则不单功高,更有不少与刘邦关系匪浅者,斗鸡走马的过往使得天命思想在汉初武人面前非常苍白。雷戈曾对秦汉之际,天命式微的现象有过精彩总结:“承继战国人力成功、人气上升之余势,后战国时代天对于人的意义确实已经大为降低。……即便伐无道也只是一个单纯的人间行为,而无需借助天的权威。……混杂于人事、事功中的‘天’虽然可能有多重含义,但我们很难直觉到天的超越性和独立性。”[3]雷戈:《道术为天子合——后战国思想史论》,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80 页。
受命于天的瑞应可以应验于“布衣天子”,为何不能显现于“布衣将相”呢?刘邦无奈成为首度面对此难题的君主。他主要从封侯排序和重建朝仪方面对武人集团加以贬抑。
汉初布衣将相,征战沙场数年,所图不过功名利禄。故对爵位高低,封户多寡与职务之轻重,无不极为看重。论功行封之际,“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4]司马迁:《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第2448 页。刘邦则心属文臣萧何“功最盛”,武人自然愤愤难平。刘邦遂发表了著名的“功人功狗说”,终使“群臣后皆莫敢言”。但武人实未心服,不过是慑于皇帝的权势罢了。论及何人应居班首,武人推举曹参为第一。而刘邦仍然心属萧何第一,但由于此前先封萧何已经拂了武人之意,不好再次强行拍板。这时,体察圣心的鄂千秋站出来发表了一通议论,认为“萧何第一,曹参次之”,刘邦大悦,鄂千秋也因举萧何之功,封安平侯,食二千户。鄂千秋封侯,恐令武人更加气馁,三寸之舌此刻远胜大刀长矛。这也揭示了封侯与否的最高准则,即是否能为君分忧,解君之难。中牟侯单右车仅因“始高祖微时有急,给高祖马,故得侯”,[5]司马迁:《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1136 页。也是此原则之体现。刘邦置文臣萧何于武人之上,也许有嘉奖和慰劳之念,但核心在于借封侯排序而刻意敲打天下甫定,威望臻于鼎盛的武人集团。考虑到萧何与曹参有隙,刘邦的平衡之术也就越发明了。吕思勉评论道:“论功时以何为第一,正所以风示武臣耳。”[6]吕思勉:《秦汉史》,中华书局,2020 年,第72 页。
刘邦帐下诸将多起自草莽,布衣多而衣冠少,其中不乏从事贱业者。既如此,世家之礼乐教化与军旅之令行禁止,对其来说都显得有些陌生。虽经数年战火洗礼,但起事前业已成型的观念和习性绝难轻易改变,加之他们与刘邦浪荡于中阳里,游走于丰沛一带的的特殊经历,竟使得汉初朝堂呈现出“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神奇景象。[7]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3296 页。秦末乱局之下,公卿将相与贩夫走卒同台竞技,身份贵贱让位于能力大小,此所谓“天下豪杰并起,能者先立”。[8]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九《张耳陈余列传》,第3133 页。加之刘邦与诸将同为编户民的过往,故而显得重建朝仪,定格君臣身份尤为迫切。而重建朝仪绝不仅是形式问题,它是皇权主义的仪式化体现,对于激发和强化臣民意识,凸显皇权之至高无上具有重要意义。甘怀真以为:汉初“君、臣、民间的身份等差不是那样理所当然,更具有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故更需要藉由礼仪与语言文字加以确认并强化”,其中“君臣关系间的身份认同是官员身份认同的核心部分”。[9]甘怀真:《中国古代君臣间的敬礼及其经典诠释》,《台大历史学报》2003 年第31 期。而这种认同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常态化加以保证和强化,“一种频繁的仪式化过程也足以使皇帝和官僚双方都能够有效确证自己的自我意识和身份”,[10]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415 页。非此不能达到尊君的终极目的。
二、“外制”之策略
刘邦乍得天下,子弟孤弱而又难以消化,不得不顺势而为,且走且看,无论是封异姓诸王,亦或是令同姓取而代之,均为填补地方权力空虚的权宜之计。然刘邦绝非一味迁就,而是积极布局,防患于未然。
(一)调整封地,预作防范
刘邦对大臣之防范非起自称帝,而是早在楚汉争霸期间就开始了。文臣主防萧何,前已有论述,武人则主防韩信。刘邦对韩信既爱又恨,这是独裁者面对人材的常见心态。“修武夺兵”的冒犯行径无疑体现其对前线将领的猜忌。垓下大战之后,刘邦迅即故伎重施,“驰入齐王壁,夺其军”。[1]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477 页。
夺军只是第一步。紧接着,刘邦借口齐王韩信为楚人,习楚风俗,徙为楚王,都下邳。齐、楚虽同为大国,楚之地域更为辽阔,但楚地自秦末以来所受战火之荼毒远胜齐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语足见楚人受害之酷烈。反秦怒火首燃于楚地,楚人为抗秦之主力,绝非偶然,楚地之残破凋敝可想而知。齐地则不然,受害相对较轻。且韩信身为平齐统帅,在当地享有独一无二的震慑力,招揽故齐文武以为己用,极易坐大。刘邦随即徙其为楚王,以削弱其实力。韩信之楚国虽残破却地大,辖五郡之地,假以时日不难恢复为大国,遂继有二分楚国之事。
刘邦调整封地,先发制人的另一举措为更换韩王信之封地。韩王信之封地初在颍川,为韩国故地,可谓名副其实。但此地十分要害,“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2]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三《韩信卢绾列传》,第3192 页,第3192 页。可谓是天下之中,又横亘在关中与齐地中间。倘若有变,出关要道函谷关与武关皆有可能为敌所阻,刘邦断然不会将此地握于他人之手。而韩王信非懦弱之辈,史称其“材武”,又曾在荥阳有过变节行为,实难令刘邦心安,遂在汉六年(前201 年)春,“诏徙韩王信王太原以北,备御胡,都晋阳”。[3]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三《韩信卢绾列传》,第3192 页,第3192 页。刘邦终于搬掉了眼前的一块绊脚石,保障秦齐通道之畅通。更将东方诸国分割为南北两半,取得了战略优势。至于韩王信后因见疑而归降匈奴,多次寇边,在素来秉持重内乱而轻边患的中国君主看来,终不过癣疥之疾尔。
(二)充实关中,构筑关塞
刘邦与群臣皆为关东之人,故初欲定都洛阳,但齐人娄敬却不以为然,他指出刘汉天下之建立全赖武力,致使生灵涂炭,如此则不得不防备变乱再起。但娄敬毕竟为布衣,初见刘邦许多话不便说透,仅含蓄强调“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刘邦迟疑未决之时,张良一锤定音,认为关中是无可争议的上上之选,尤其是它“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4]司马迁:《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2483 页。以张良之地位自可直言不讳,定都关中之首要目的即“东制诸侯”。刘邦闻此,即日起程,西都关中。
汉初,天下凋敝,作为汉军后方基地的关中,经历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后民力已然枯竭,恢复、充实和巩固其地位迫在眉睫。刘邦自称帝即颁布《罢兵赐复诏》,通过一系列措施,填充和巩固关中地区。关中本为四塞之地,有山川之险可资凭借,汉廷又“充分利用鄂西山地和豫西山地的自然阻隔及其间的扜关、郧关、武关等关隘”,[5]梁万斌:《从长安到洛阳:汉代的关中本位政治地理》,复旦大学2013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3 页。打造出以函谷关为中心,以黄河为屏障,北抵阴山,南达三峡的大关中防御体系,从而使得刘邦在肃清异姓诸侯王的一系列战事中进退自如。
中央与东方诸侯国之关系势若敌国亦可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中看出:“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一要(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其坐谋反者,能偏(徧)捕,若先告吏,皆除坐者罪。”[6]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88 页。此外,作为京畿的关中地区,享受到较多轻徭薄赋的优惠政策,汉廷亦不遗余力地移民充塞之。关中遂得以较快恢复元气,进而凭借“地势便利”,实现“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7]班固撰,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卷一《高帝纪》,第90 页。
(三)扶植刘齐,威慑东方
齐素为东方大国,膏壤千里。早在战国后期,奉行绥靖政策的齐国就已脱离战场,虽致使政权倾覆,但却侥幸保全了民力。秦汉之际齐地所受兵祸相对较小。汉初,天下凋敝,齐国则属人烟较为稠密之地。齐地战略地位重要,位于函谷关东方大道的东端,与秦地相望对峙,号称“东秦”。如此形胜要地,刘邦怎能交与他人呢?故而,韩信欲王齐而终不得。刘邦在击败项羽之后再夺其兵权,改封楚王。时楚地卑湿,深受战火荼毒,自然难以媲美齐地。齐地暂时归属中央。汉六年(前201 年),刘肥封齐王,王齐地70余城,成为东方第一大国。更命曹参为齐相国辅助刘肥。刘邦所为自然说明齐地要紧,而令“民能齐言者皆属齐”,显然有壮大之意图,恐非纯粹出于“偏爱”。考察此后齐国在攻灭陈豨与英布等集团过程中的突出表现,实乃刘邦监制赵、梁、楚与淮南诸国,经略东方的重要举措,一如周初武王封吕尚。足见刘邦外放曹参实收一举两得之功效,既可敲打此人,又可利用其平齐时所树立之威望稳定局面。齐国遂成刘邦东方之奥援,与关中遥相呼应。
(四)安插亲信,构陷诸王
早在楚汉争霸之际,刘邦就十分看重用间,特别是任用陈平行反间之策,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刘邦对于异姓诸王之防范从未稍歇,诸王之阴事,多为其所探得。韩非尝言:“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1]韩非:《韩非子》,中华书局,2010 年,第106 页。刘邦显然就属于这类“智术之士”。
韩信将好友兼钦犯钟离眛(故项羽将)藏匿府中,此等密事刘邦缘何得知?为何随即“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2]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第3184 页。刘邦声称“人告公反”,何以至洛阳不见任何审讯调查即废信为淮阴侯?倘若果真谋反定当夷灭三族,贬为列侯则说明查无实据,甚至不曾启动调查。既如此,所谓“人有上书”当为预先布置无疑。彭越与英布均与臣下发生矛盾后被对方揭发检举。“梁王怒其太仆,欲斩之。太仆亡走汉,告梁王与扈辄谋反。”[3]司马迁:《史记》卷九十《魏豹彭越列传》,第3146 页。英布怀疑姬妾与中大夫贲赫有私,“赫恐,称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变事,乘传诣长安”。[4]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一《黥布列传》,第3158 页,第3158 页。对于这种违反规则,公报私仇的告密和构陷行径,常人自是极为厌恶和忌讳,但却为专制者所喜。萧何是唯一对构陷诸王之事提出异议的大臣:“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诬之。请击赫,使人微验淮南王。”[5]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一《黥布列传》,第3158 页,第3158 页。但刘邦不会错失良机,更不会诛杀“用功之臣”。结果,英布不得不反。
由此可知,将异姓诸王置换为刘姓诸王已是路人皆知的公开秘密。卢绾在描述自己的险境之时曾说:“非刘氏而王,独我与长沙耳。……今上病,属任吕后。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6]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三《韩信卢绾列传》,第3199 页。亦即,非刘氏而王则“其罪当诛”。但卢绾不便,不愿也不敢怨恨与己有“竹马之交”的皇帝,故只能归咎于吕后,但如此军国大事,吕后何以自专呢?臧荼见诛之时,因其本非刘邦阵营,关系疏远,尚不曾引起大臣警恐,但功高如韩、彭者惨遭灭族,亲贵如张敖者亦无端被废,政坛众人不难发现这样的事实,即揭发攻击异姓诸王就是政治正确。既如此,如欲邀功请赏,公报私仇,或避祸自保,则构陷诸王成为上佳手段。[7]温疥“为燕相,告燕王臧荼反,侯,……千九百户”;(《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1109 页)栾说因“告淮阴侯信反,侯,二千户”;(《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1125 页)贲赫“上书告布反,侯,二千户”。(《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1140 页)倘若刘邦最初还需安插暗探以构陷的话,那么经过几轮演练,或与诸王有隙,或意图邀宠之人将自觉充当刘邦的“特使”角色,刻意安插已然不必。因为借告密以求上位之徒,绝对远多于特务,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五)屡屡亲征,力求全胜
“御驾亲征”之事起源甚早,但若论及频繁程度,绝少有胜过刘邦者。自汉五年(前202 年)称帝至汉十二年(前195 年)伤势加重而殁,刘邦几乎是鞍不离马甲不离身,常年在外征伐。而汉初军功侯百四十三人,其中多为刘邦嫡系,他却不遣大将为主持,竟以皇帝之尊,每每亲征,主抓关键性战役,帐下诸将仅是负责追剿残部和打扫战场。前人从未论及此现象之异常,似觉得理所当然,窃以为不然。反刘者固然有高居王位且勇猛善战如英布、韩王信者,刘邦不得不亲往击之,但也有如利幾、陈豨这般仅为侯爵的部下,朝中不乏善战之辈,为何刘邦却从不假手他人,强要御驾亲征呢?[8]汉十二年(前195 年),卢绾反时,刘邦病重,不得不遣樊哙和周勃将兵击之。主因有三:
首先,皇帝亲征,以图威势。汉初七大异姓诸侯王南面称孤实为局势发展之必然,但起自布衣的刘邦毕竟与诸王曾经“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1]班固撰,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卷一《高帝纪》,第81 页。故而,当刘邦试图打压昔日同侪之时,不得不借助皇帝之尊、中央之威取得政治上的正当性与气势上的压倒性,营造皇帝亲临,兴师问罪之态势。倘若遣军功侯挂帅,从身份上就要低对方一等。所以,刘邦以皇帝之尊亲征诸王,从地位上占据优势,易于鼓舞己方士气,震慑敌方。异姓诸王也的确比较服膺或畏惧刘邦。无论是韩信的不忍背汉,彭越的张皇失措,还是英布的误判局势,均说明作为开国之君的刘邦的确具备较强的震慑力,以韩、彭、英三人之能尚且如此,遑论其余。
其次,诸将力有不逮,难保全胜。刘汉天下之建立,主要在于韩、彭、英为首的异姓诸王。此间,刘邦嫡系部属所扮演的角色,或是随军听候调遣,或是配合诸王作战,亦即缺少独当一面的统御能力,自然难以在日后对诸王产生震慑作用。诈擒韩信之前,刘邦问计陈平;亲征英布之前,刘邦讨教薛公。根本未将诸将的狼烟大话放在心上,足见绛、灌之流在关键时刻难入刘邦法眼。而作为同僚的韩信和英布也素来轻视汉廷诸将,信尝言“羞与绛、灌等列”,[2]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第3185。英布则强调“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余不足畏也”。[3]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一《黥布列传》,第3160 页。概言之,若非刘邦屡次亲征,凭借皇帝之威,调集各方势力对敌形成政治、军事和心理的压倒性优势,在天下未稳,人心未服的情形下,稍有不慎,极有可能落得满盘皆输。更何况北方诸王侯多有勾连强敌匈奴犯边者,从韩王信,到陈豨,再到卢绾皆是如此,内外交织使得问题更显棘手。楚汉争霸历时四年,除异姓王费时六年,两场较量的综合难度与风险,实难分伯仲。
再次,骄兵悍将,他人难以驾驭。除了麾下诸将能力不济,难以独挡一面之外,刘邦屡次亲征还因诸将多为骄兵悍将,旁人难以驾驭。为免出现同僚抵牾,前线倒戈等意外,刘邦不得不亲征以求万全。“六年……上在洛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4]司马迁:《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2481 页,第2485 页。汉初历史较之历经整肃和装裱的后世历史更显底色,时人言语颇有“直抒胸臆”的风采,给人“憨直”之感,这当然也与史公的传神妙笔有关,但汉初政治毕竟尚未完全受到皇权专制体制的禁锢,确有不少鲜活案例呈现出当时社会生态的活力。无论是英布的“欲为帝耳”,贯高的“能者先立”,还是田横君臣的守义不辱,皆有汉初风采。此处张良的“此谋反耳”,显然也是此类特质的体现。汉初武人,抛家舍业,刀口舔血,皆为功名利禄,此亦不难理解。但仅因封赏不称己意便萌生反心,其骄悍和难以驾驭是十分显然的,大异于后世维诺恭谨和口称戴罪的“忠臣良将”。为平息怨气,稳定局势,刘邦只得扩大封赏范围,前后封侯143 人,超越秦代所封列侯的总和。
诸将的难以驾驭亦可从刘邦诛樊哙一事看出。樊哙因他人进谗而见疑于刘邦,刘邦命“陈平亟驰传载勃代哙将,平至军中即斩哙头”,[5]司马迁:《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第2501 页。但陈平、周勃二人领旨却不奉旨,担心刘邦息怒之后反悔,故仅是将樊哙押解入京。陈平在刘邦在世之际竟然伙同周勃玩弄两面手法,一切围绕自身利弊得失行事,对待刘邦尚且如此,倘若是吕后和刘盈呢?
此前,刘邦意图命刘盈代己亲征,商山四皓力劝吕释之阻挠此事,因为他们认为诸将乃“天下枭将”,若是刘盈带兵,无异于“使羊将狼”,诸将必然“不肯为尽力”,则“无功必矣”。[6]司马迁:《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2481 页,第2485 页。惟有刘邦亲征,诸将才不敢不尽力。两相对比,无不道出诸将舍刘邦皆难驾驭的事实。在此局势之下,遂有刘邦去世四日而不发丧,吕后与审食其图谋尽诛诸将的重大危局。臧知非教授以为,此乃吕后集团借机除掉功臣,试图大权独揽的明证。[7]臧知非:《吕后》,现代出版社,2017 年,第186 页。吕后意图发难,自然有揽权之意,但也是极度畏惧和恐慌之下以图自保的条件反射,也许有些过激,但这实在是权力角斗场上的寻常之事。吕后毒辣不假,功臣集团亦绝非善类。得知吕后意图诛杀大将,郦商警告:“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大臣内叛,诸侯外反,亡可翘足而待也。”[8]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492 页。足见双方不过权力争斗,无所谓正邪善恶之分。至于诸将展露实力,咄咄逼人的态势也足以说明吕后之忧惧理所当然。
再者,在地方诸王大臣眼中,朝中诸将亦非善类。代国君臣在商讨是否受邀入继大统之时,郎中令张武等以为“汉大臣”属于“实不可信”的谋诈之辈。宋昌虽然反对张武的保守性建议,但却并未否定高帝大将多谋诈的判断,而是认为民心向刘,宗藩制衡,诸将难以为乱。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袁盎亦对周勃等人的忠诚持怀疑态度,视其为投机分子,仅可称之为功臣,而非社稷臣。综上,汉初诸将对于政局的诸多隐患足见其形象绝不仅仅是所谓匡扶社稷那么简单,骄兵悍将恐是更接近底色的一面。
三、刘邦策略之得失
经刘邦的连番压服,异姓诸王被削平殆尽,所余不过吴芮。汉廷仰仗关中财力,聚敛天下精兵,强干弱枝之局面已成,形成中央对地方的压倒优势,为此后的进一步削藩集权奠定基础。同时,置换诸刘为王,植根地方,对于树立正统意义重大。“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强”,[1]司马迁:《史记》卷十《文帝本纪》,第526 页。可见大封子弟的确对朝中的军功贵族集团构成了制衡与威慑,这在剿灭诸吕之后表现得极为突出。时陈平、周勃为首之军功集团咄咄逼人,左右朝政,但亦不得不从宗室中选择接班人。故而,确保刘姓江山不变色的主要目的基本达到,但若具体分析,也埋下了危机。
(一)滥杀之嫌
汉初,陆贾常以儒术进言,刘邦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2]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第3296 页。虽然此观点遭陆生批评,刘邦也虚心纳谏,但无疑昭示了得天下者的嚣张与霸道。一时的收敛并不代表刘邦真要铸剑为犁,偃武修文。武力夺取天下的成功经验必然根植于刘邦的意识之中,认为武力才是克敌制胜的不二法门。而若要长保武力优势则唯有集权之路。集中权力与掌控军队乃是专制统治者的命根子。但权力如豺狼,若走向极端则将反噬。集权之路也必然伴随着绵延的杀戮与动荡。刘邦在位期间征伐不休,临死之前北方战事仍在进行。而权势愈大,猜忌之心愈重。敌人不是越杀越少,反而是越杀越多,临死前尚在叫嚣:“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3]班固撰,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卷一《高帝纪》,第117 页,第112 页,第89 页。在告密日盛的情形下,刘邦的滥杀迹象越发明显,且渐由外向内转移,轻信谗言而意图诛杀樊哙就是明证。而这种滥杀,无疑会激化政权内部的矛盾。
(二)民众疲敝
刘邦晚年,民力已然不堪重负,突出表现在征讨英布一役。战前,“上乃发上郡、北地、陇西车骑,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万人为皇太子卫,军霸上”。上郡、北地、陇西为防备匈奴之前哨阵地,刘邦为了平定内乱,不惜抽调边兵置边防安全于次要。出征之际,“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从军;征诸侯兵,上自将以击布”,[4]班固撰,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卷一《高帝纪》,第117 页,第112 页,第89 页。如此倾巢出动前所未有,反倒是在穷兵黩武的汉武帝时期较为常见。汉初,“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5]司马迁:《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1050 页。刘邦称帝时,曾诏令“兵皆罢归家”,民“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实际情况则是与民休息不过两月。“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将征之”,[6]班固撰,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卷一《高帝纪》,第117 页,第112 页,第89 页。新一轮战争大幕就此拉开,至死不休。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惠帝和吕后时期对内萧规曹随,奉行“不折腾主义”,对外则绝不轻启战端,即便是吕后受到冒顿单于的调戏和侮慢也只能隐忍不发,遂有史公对二人当政时期民生政绩的大加赞誉。
(三)后续危机
刘邦去世之后,吕后与军功集团的矛盾一触即发,险些喋血京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显然更应从刘邦执政后期的诸多做法寻找原因。过度防范与制衡,屡行大狱致使人心浮动,无不在刘邦与诸大臣之间埋下了不信任的种子。这种不信任势必为后续执政的吕后所承袭,遂有后来的收权之举。而汉初军功集团起自民间,多桀骜少文之辈,绝非后世职业官僚可比。强悍如吕后者,也不过采取架空手法而避免与其爆发直接冲突。饶是如此,军功集团对于权力重组所导致的大权旁落也是愤愤难平,在吕后晚年即已开始串联,意图夺回大权,此乃诛吕政变的伏笔。追本溯源,皆与刘邦执政后期的猜忌与滥杀有关联。
结 语
楚亡汉兴,皇权专制体制得以再次确立,排他性愈发彰显。正如徐复观所论:(诬杀诸王)“并没有其他的政治理由,只因刘邦既以天下为他一人之产业,则凡有夺其产业的可能性的人,便都是罪大恶极之人,这是专制者最基本的心理状态。”[1]Rosalind Thoma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10.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一),九州出版社,2014 年,第150 页。权力成为皇帝之禁脔,猜忌日甚一日。原本较为豁达的刘邦越发变得狭隘、敏感而残忍。法家反复强调“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2]韩非:《韩非子》,中华书局,2010 年,第159 页。既如此,纵然汉初文臣武将皆为一时之选,刘邦仍将每每亲征。因为如韩、彭、英这般当世名将全部成了刘邦的仇雠,必欲除之而后快,就连萧、曹这样的沛县班底也成为他猜忌的对象而受到敲打,如履薄冰;亲贵如卢绾和樊哙者亦是朝不保夕,命悬一线。孤家寡人又怎能不发出“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感慨呢?归根结底,刘邦鞍马劳顿也好,中箭身亡也罢,皆是身处皇权专制体制旋涡中心者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