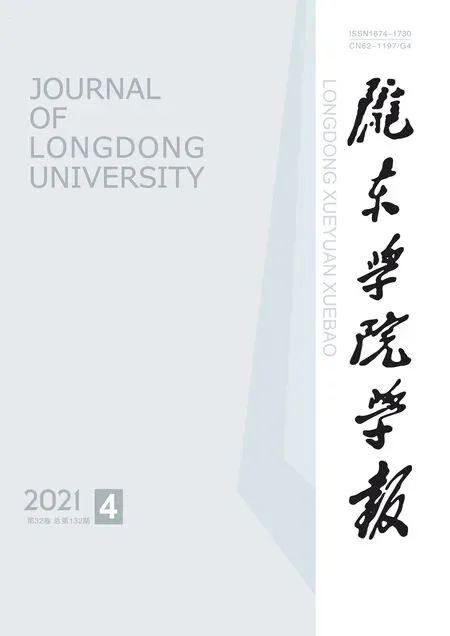交往行为视域中的亲子冲突及其化解
2021-12-28陈思梦
陈 思 梦
(安徽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几乎每个家庭都发生过亲子冲突,它不仅是一个家庭亟待解决的问题,也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时刻威胁着孩子身心的健康发展、亲子关系的和谐构建以及美好家庭的幸福建设。亲子冲突可以理解为父母与孩子之间发生对立并不能以良好的方式解决对立的行为和表现,主要有言语、情绪、身体冲突三种类型。研究者们从教育、心理、文化和社会的角度进行分析并提出应对策略,却始终无法根本解决。因此,本文从人类交往行为出发,以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为主线,详细介绍理论内容并尝试分析亲子冲突作为一种交往行为所形成的原因,并提出化解对策。
一、交往行为理论的学术演变及主要内容
(一)交往行为理论的学术演变
交往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可以说有了人类之后就有了交往活动,从学者对交往概念的注意到理论范畴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持续拓展与深化的过程。最早对交往行为进行探讨的人当属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1-1704),他在《人类理解论》一书中谈及著名的“白板”理论时顺便发表自己对于交往行为的理解;他认为人们相互沟通的过程就是交往过程,人类是群居动物无法独立于社会,唯有通过交往才能彼此理解互相扶持[1]。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首次把交往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将其理论化,他从人性视角看待人类交往行为,认为“共同感”和同情是交往的人性基础,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共同感,这是人类能够换位思考、沟通理解的前提条件,否则人们将不能进行有效交往[2]。然而到了18世纪,学者对于交往行为的研究开始转向政治方向以满足政治上的需求。法国著名思想家查理·路易·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表示每个人都有社会性,每个人都需要与他人保持良好的交往关系,这样可以确保自己能够在社会上生存下去[3]。克洛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etiu,1715-1771)的交往观具有十分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他指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目的都是出于利益需要,功利主义是人们现实中交往的原则[4]。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吸收和发展了费希特“相互承认”的交往思想,认为人们之间的“相互承认”是在劳动的过程中实现,人们在劳动中接触、交流、思想碰撞进而建立起正常的交往关系[5]。黑格尔的观点对之后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的交往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和启迪作用。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对交往问题做出了十分深刻的诠释,他认为“事物质生产的人,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同他人一起。……人通过与他人的交往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在交往需求的支配下,持续改变现实关系同时也能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6]从哈贝马斯在批评继承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基础上,结合当下社会现实问题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
(二)交往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
哈贝马斯看到现代社会中的科学技术扩大人们自由空间的同时也看到由此引发的工具理性在现实生活中的泛滥,人们的交往活动逐渐由此支配和统治,造成生活世界的危机与冲突。据此,哈贝马斯希望通过重建交往合理性来打破交往异化的困境。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是指至少两个以上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互动,这些主体使用手段,建立一种人际关系;行为者通过行为语境寻求沟通,以便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把他们的行为计划和行为协调起来[7]。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主体间性是交往行为的基础。哈贝马斯表示理性构成了哲学的基本论题,他提出以主体间性为中心的交往理性成为他整个理论的基础。哈贝马斯发现在资本主义的进程中,理性越来越被局限于目的—手段关系而萎缩为工具理性,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固守“主体-客体”分析范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被物化。因此哈氏主张用“主体-主体”,即主体间性的分析范式取而代之。交往的目的在于达成共识,交往有效性不是个体的独角戏,而是交往主体之间意识形态的协调和理解关系。哈氏认为“交往行为的目标是导向某种认同。认同归于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两相符合的主观际相互依存。”[8]交往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相互理解、求同存异的主体间性关系,他们可以平等地进行交流和对话,唯有此才能实现交往的合理性。
2.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的背景。生活世界既来源于主体的交往关系,又为交往行为提供活动场所,为参与者交往的实现提供了需要的背景知识,是交往者之间互相理解、达成共识的前提,也是交往活动顺利进行的基础。哈贝马斯继承和丰富了胡塞尔生活世界的内涵,将生活世界概括为交往行为者所处的先验领域,指出它是人们通过语言将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内容抽象出来所形成的知识背景,在交往行为发生前就已经存在。“在一定方式下,生活世界,即交往参与者所属的生活世界,始终是现实的;但是只是这种生活世界构成了一种现实的活动的背景。”[9]同时,生活世界也是交往行为的“信心储存库”,在他看来,生活世界中储存着前人传承的经验总结、文化知识和资源,是社会成员间达成相互理解所需的必要背景知识。该背景知识作为人们开展交往活动以及形成共识必不可少的要素为人们所共享,并且借助语言表现出来。
3.理解共识是交往行为的目的。人们每一次的交往行为其目的都是为了彼此之间形成理解、达成共识,促使交往活动的顺利有效完成。相互理解是交往行为有效性的基础,也是达成共识的前提。每个人都会经历无数次交往活动,在此期间如果大家不能理解彼此的想法,各自为政,就会导致矛盾的发生,即使拥有血缘关系的亲子之间也不例外。达成共识是交往行为有效性的目标以及相互理解的结果。人们能够就某一观点达成共识意味着可以在多元社会背景下构建起一套可被大多数人所认可并共同遵守的普遍道德规范。这一规范象征着大部分社会成员的一致认可,能够被社会成员普遍接受并遵守。因此,我们交往行为的目的就在于主体之间是否达成了一致,相互理解的程度有多深。
4.对话沟通是交往行为的媒介。在哈贝马斯的对话理论中,对话是指交互主体通过语言达成沟通、理解的方式。在哈贝马斯看来,人与动物的最本质区别在于人类能够使用语言进行交流沟通,在日常生产、生活过程中,对话可以有效促进交往活动的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主要依靠语言的方式,把语言作为媒介进行对话,通过对话与交流来达到彼此间心灵的互相认可和理解。每个主体要想别人认同和接受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或者理解别人的思想看法,这一切都需要对话实现。同理,有效交往同样需要对话作为中介来互相获得一致意见,得出一致结论,进而形成共识。
二、交往行为理论视角下的亲子冲突
(一)亲子冲突问题现状
学界对于亲子冲突的概念至今未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学者对亲子冲突的研究最初从人际冲突的视角进行探究,认为亲子冲突是家长与孩子之间的一种人际冲突,这种观点忽视了亲子之间特殊的亲缘关系。接着学者从家庭教育角度出发指出亲子冲突是孩子对于父母管教的不顺从和违抗行为。Yan和Smetana给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亲子冲突不仅体现在行为层面,它应该是亲子之间表现出来的不一致[10]。这种表现既可以是外部可观察的行为也可以是观念或情绪的对立,冲突程度可深可浅。概而言之,亲子冲突包括行为、语言和心理三个方面的冲突;亲子冲突的内容纷繁复杂,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具体包括日常生活安排、穿衣打扮、行为习惯、家务、外表、看书写作业、考试、交朋友、钱、隐私等。总地来说,子女与父母冲突最多的就是日常生活安排和学业。
亲子冲突是家庭中常见的现象,可以说每个家庭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亲子冲突,它成为孩子身心健康成长、亲子关系和谐建立以及美好家庭建设的障碍。有研究指出与父母存在冲突的孩子更容易抑郁且问题行为更多,亲子冲突对孩子的认知发展、心理发展以及社会性发展均有一定的消极影响。据此,研究者试图从个体的生理和心理方面、家庭环境方面以及社会文化方面探寻亲子冲突的原因,尝试揭开亲子冲突的面纱。然而,亲子冲突问题依然困扰着无数个家庭,始终无法从根源上彻底解决。实际上,亲子冲突归根结底是一种在家庭场所中发生的亲子之间的互动行为,确切地说是一种无效的互动行为,它是亲子互动失败的结果。首先,哈贝马斯认为有效交往必须保证交往主体之间的平等性,而父母很难用平等的姿态对待孩子,这会导致亲子交往过程的异化。其次,父母与孩子拥有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和生活背景,他们遵守不同生活世界中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亲子之间理解的困难。再次,亲子之间的不理解和不一致也是交往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父母与孩子往往因不能理解对方的做法而致使冲突产生。最后,亲子缺乏必要和正确的对话沟通,真诚、真实、正当的对话是交往合理性的前提和基础,而父母不善表达对孩子的爱是中国父母的基本特色。
(二)亲子冲突的原因分析
1.交往地位不平等:你的事,我做主。封建社会时期,封建宗法等级关系是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必要手段,其体现在家庭中就是家长制的宗法统治。长久以来中国人民恪守尊卑等级的传统观念,父尊子卑成为支配传统中国家长教育子女的信条,孩子是父母的私有财产或者附属品,父母与子女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家长拥有绝对的权威地位,正如如威廉·J·古德所说,“传统的规范和压力给予父母更多的权威和特权来管教孩子”[11]。即使在现代社会,依然有很多家长固守错误的亲子观、教育观,认为自己是孩子的父母有权支配和主宰他们的生活。事实上,父母理所当然地具有较高的家庭影响力,处于支配和统治地位。与子代相比,父母无论是身体力量还是财产资源都有绝对优势,柯林斯认为财富、权力与声望是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三个基本因素,这同样符合家庭地位的衡量标准。子女与家长之间因资源、权力和地位的不同形成鲜明对比,导致自己时刻受到父母管控,亲子交往自始至终由父母主导。家庭中亲子这种交往方式很容易导致亲子之间缺乏沟通与交流,不能相互理解,从而引发家长与孩子之间的冲突。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行为有效的前提条件便是交往主体之间的地位平等,这样可以使得交往主体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观点,吐露真实心声,传递完整信息。然而在很多中国家庭中,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并非平等、民主的亲子关系,孩子不能与家长平起平坐,亲子之间无法达成主体间性的交往关系和地位,因而造成父母与孩子很容易因为生活琐事发生冲突的问题。
2.交往生活背景不同:我和你,不一样。主体之间的接触、沟通与交往不是发生在真空中,而是以一定的生活世界为依托和背景,生活世界先验的存在,即先于我们存在,我们不可能走出生活世界不受其影响。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作为“惟一现实的、在感知中被现实地给予的、总能被经验到并且也能够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12]。生活世界能够为交往活动参与主体提供用语言结构组成的,并且能够在交往活动参与主体中进行相互沟通与交流所必需的信念或知识。交往主体依据生活世界的信念知识作为处理事物的行为活动的指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世界,我们的言行举止都会受到生活世界的影响却意识不到它的存在。由于生活世界的多种多样致使不同交往者的价值观、思想认识、心理状态、生活态度、行为方式以及兴趣爱好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家长和孩子拥有不同的生活世界,他们遵守各自生活世界的行为方式,很多家长认为自己和孩子生活在共同的时空之中,却意识不到他们所属的生活世界的不同,它不仅体现在空间区别还包括文化、社会、个性等方面的差异。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速度在加快,家长却始终坚守自己生活世界的行为规则并且以此看待和评判子女的言行举止,可子女要通过自己的瞳孔看世界,于是两代人之间产生了新与旧两种生活方式的矛盾和冲突,从而酿就了最终的代际冲突。
3.交往缺乏理解与共识:我的爱,你不懂。对哈贝马斯来说,交往参与者能够理解对方的想法或就某个观点达成共识,这是交往行为成功的标志也是交往有效性的目标和结果。理解与共识说明交往主体具有表达的能力和资格、处于平等的交往地位,并且他们能够信守彼此间约定好的道德准则,就某件事形成观念合力共同推进事件的发展和前进。亲子之间的冲突恰恰源于父母与孩子交往的过程中未能达成理解和共识。父母对子女的爱毋庸置疑,中国家长对子女付出了毕生心血,从孩子出生到上学,再到结婚买车买房娶妻生子,他们把一辈子的精力和时光都花在了子女身上。父母对子女的关心和照顾无微不至、事无巨细,而父母的所作所为在孩子眼里却成了全面的控制和压迫,他们只看到父母外显的日常生活的管控却看不到父母对他们内隐的爱。外显与内隐的失衡,规训与教化的矛盾直接导致子女对父母行为的不理解,他们不明白父母为什么非要自己上各种枯燥的辅导班、非要自己考试一百分、非要自己遵守各种行为规范。父母与子女是经常交往的两个群体,他们的交往内容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父母对子女的管教也弥漫着生活的各个角落,而子女很难在这些繁多的生活小事上件件理解父母,因此亲子之间的冲突必然时常爆发。如果子女对父母多些理解,父母对子女多些宽容,心平气和进行沟通制定双方皆认可的家庭交往规则,这样不仅可以促进亲子交往的顺利进行在此基础上还能够构建良好的亲子关系,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
4.交往工具缺失:你爱我,却不说。在交往活动中,语言是重要的沟通媒介,交往主体通过语言进行互动,然而在家庭中,亲子交往的语言却发生了异化,使得以往通过沟通从而达成协调的目的不复存在。语言没有成为表达观点和思想的工具反而成为父母命令、使唤孩子的工具,同时也成为孩子欺骗、对抗家长的策略性手段。只有话语满足了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有效性要求时,话语顺利呈现事实、正确表达自我意向和建立合理人际关系的功能才能全面实现,交往行为才得以顺利进行。因此,交往活动既要有对话作为互动桥梁也要求话语满足有效性条件,这样才能达到交往主体的相互理解。中国家长与孩子的交往中从不直白地表达自己的爱,他们倾向于间接侧面的表露心扉,这样就导致亲子交往的话语缺失真实性和正确表达。而孩子与父母存在的代际差异使得他们不愿向父母吐露内心的真实想法,对父母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时刻隐藏和包裹自己,这样就会导致亲子交往的话语缺乏真诚性。因此,尽管亲子之间交往互动的次数和频率相对其他人际交往来说更多,但是由于双方并未理解交往语言的核心要义从而使得很多交往行为成为无效交往。父母与孩子没有正确使用对话的交往工具,彼此无法理解对方的言行和思想观念,致使家庭中亲子冲突的爆发已成为家常便饭。
三、交往行为理论视角下的亲子冲突化解策略
(一)建立亲子交往的主体间性关系
很多家庭中亲子冲突的产生是由于亲子之间的交往不是双向的、平等的、民主的互动,而是父母支配孩子听从的单向不平等关系。亲子之间的交往不应该只是父母单一主体的独白,相反应该是父母与子女共同作为主体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交往。孩子虽然是由父母生育抚养,但他们是独立的主体有自己的人格、尊严、个性和思想,正如诗人纪伯伦在《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中写到的,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他们通过你来到这个世界,……却不属于你。因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思想。哈贝马斯认为只有主体间的关系才能算得上相互关系,因为主体间的关系是互动的、双向的,而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是有被动和主动之分的,是单向的,因而不能称之为相互关系。马丁·布伯(Martin Buver)指出“在这种对立而不是交融的关系中,‘我’不能发现自身的意义;而‘我和你’关系则是人类应有的真正的基本关系。”[13]因此,在交往活动中父母和孩子都要认识到自己是主体性的存在,应该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能够按照自我意愿进行活动,并且还要学会尊重别人的主动性,给予对方以自由表达、自由行动的机会。
(二)创设亲子交往的理想话语环境
家长与孩子生活在不同的环境背景下,由此形成各不相同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这种区别客观的、先验地存在着,这些差异无法从根本上弥合和消除,在日常生活中不经意制造了亲子交往的诸多障碍。此时,人为地创设亲子交往的话语环境显得尤为重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亲子交往的认知、心理和空间的差异。通过生活世界“信念存储库”的作用,主体之间就可以达成理解并形成共识,从而排除对峙,解决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哈贝马斯提倡构建一种全新的“理想的沟通语境”,让全部参与主体可以在无外在压迫的状态下畅所欲言,交换心中的想法。在亲子交往中,首先,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要有机会表达自己心中真实的想法,而不是相互隐瞒和敷衍了事,在家庭营造可以自由表达的话语环境。其次,亲子之间要经常沟通和交流,及时了解各自思想的动态变化,充分发挥话语的正向功能,用对话促进亲子交往的顺利进行。
(三)构建亲子平等交往的规则规范
亲子冲突的发生大多是因为交往中的主体无法理性支配自己的行为和意识,只能任由交往活动的负面走向,亲子交往处于无序的状态,这时就需要交往参与者共同制定一套平等的交往规则让规则主导交往互动的发生发展。哈贝马斯认为在主体相互间的交往过程中,要想实施合理化的交往,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就是建立共同的交往规范和行为准则,并且交往的主体必须要尊重和遵守这些规范和准则,他认为主体之间进行交往活动时,遵守由他们一起协商并达成一致,共同认可的交往规则,彼此相互尊重、相互制约、相互协同,才能实现交往过程的合理性。当然,实际交往过程中,参与交往的行为主体应该普遍都能接受,并自愿遵守这一规则,这就需要所有交往主体共同参与规则制定的过程,进行多次协商讨论,使大多数同意某项规定。在这个过程中,交往参与者要能够换位思考,反思自己的行为。只有这样形成的规则才能具有最有效的约束力,让大家自愿遵守和维护。亲子之间的交往互动同样需要制定一些规则,亲子共同参与制定过程,每个人都要抒发自己的想法,并且能够自觉地严格遵守。只有用规则化解冲突,这样才能保证亲子之间的关系处于和谐平等的状态。
(四)转变亲子和谐交往的方式方法
不同的交往方式会得到不同的交往结果,化解亲子冲突促进亲子关系和谐发展需要在方式方法上做出改进和创新。首先,变单向交往为双向互动。在很多家庭中亲子关系以父母为中心,父母主导全部家庭生活和亲子交往活动,亲子交往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互动关系。这种情况下,父母要自觉主动摒弃家长权威地位,不能一味采取使子女服从的压力方式,而应当积极了解、尊重接纳子女的想法,鼓励孩子主动与父母沟通互动,努力使亲子间消极的单向交往转化为积极的双向互动。其次,变单一的说教为平等的对话。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观中,交往的本质就是对话,当然这种对话不是单一的说教而是交往主体之间平等的对话交流。因为只有在对话中交往参与者才能更加了解彼此,平等对待彼此的差异和矛盾,促进情感的交流和行为的协调,交往的意义和价值在对话中得到诠释和深化。因此父母不能总是用说教的方式与孩子交往,这样会加重与子女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尝试蹲下来与孩子心平气和地沟通交流,亲子之间就会建立更加全面和谐的关系,亲子冲突自然而然地得到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