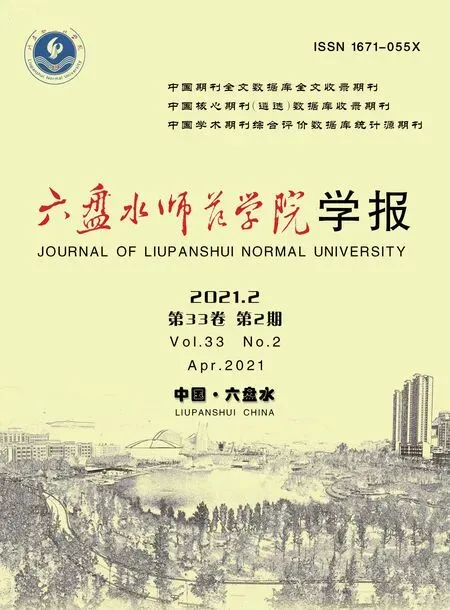汉赋 “ 铺写叙物 ” 的文学思理与文化精神
2021-12-28支媛
支媛
(1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2六盘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贵州 六盘水 553001)
对自然万物的强烈观照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显著特征,从文学创作的过程来观测, “ 文 ” 如何选择和表现作为审美对象之 “ 物 ” ,主要循思于文体体制风格和创作主体才思两个层面,前者体现文体的定性规范与表现风格的关系,后者显示创作者个性创造与创作整体风貌的连接。一方面,不同的文体类型必然 “ 有一些规定风格的力量 ”①,作家在创作时首先要受到不同文体选择的规定性支配。《文章辨体序说·凡例》谓 “ 文辞以体制为先 ”[1],所谓诗有诗之法式,赋有赋之规程,不可混淆,换言之,文体的体制风格牵引着创作者对外物的表现方式。从体性意义分别各体,并以文体规范对 “ 物 ” 的取舍运造,文章体式风格也因客观事物千姿百态、创作个性的差异以及不同表现的需要而随常变迁,如陆机《文赋》言 “ 体有万殊,物无一量 ” , “ 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 ”[2]。另一方面,在创作活动中,创作主体如何进行艺术构思和语言修炼从而达到以文载物、物以适文,需要天资,亦需要学养积备。
就赋一体而言,汉大赋最为代表,其文本赋作在体制上别开一体,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 “ 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 ”[3]270指明赋体与其他文体的差异,纪昀评述以为 “ 铺采摛文,尽赋之体;体物写志,尽赋之旨 ”[4]。赋之为体, “ 敷陈 ” 的本质要义最为显要,挚虞《文章流别论》言 “ 赋者 ” 以 “ 敷陈之称 ”[5]《全晋文》卷七十七,1905明其体,特别是汉大赋寡于情志,主物摛写,明示通过对 “ 物 ” 的铺写集叙之法来彰显赋体本色,赋体以 “ 铺写叙物 ” 为表征,体现为博观包容的审美视域及繁辞巧构的技艺蓄积。
一、大赋体制与博观包容
文章辨类定体,风格态势便随之形成,《文心雕龙·定势》言:
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3]1113-1115。
以此阐明文章体裁与风格的关系,依不同的表达内容来确定文体,同时,体裁形式也规约着文体表现手法和审美特征的形成,根据文体的规定形成风格,这是创作的自然之势。于赋而言, “ 鸿裁之寰域,雅文之枢辖也 ”[3]283与 “ 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 ”[3]288亦有区分,可见对审美客体 “ 容量 ” 的宏大或狭小首先受制于文体本身的体制要求。从体制上看,大赋极富盛览,其直接继承了楚辞恢弘阔大的空间意识, “ 赋家闳衍钜丽之体,楚《骚》《远游》等作已然,司马、班、杨尤尚此 ”[6]卷七,7。汉大赋在描绘宇宙的广度和深度上追求极致的 “ 闳侈巨衍 ” ,对 “ 物 ” 的容纳显示了相当的文体优势,以文辞的视觉观感将东南西北、天地上下的物类汇聚,多角度、全方位描写展现包罗万象的宇宙图景。大赋体制构筑的特殊性具有得天独厚的穷极 “ 写物 ” 功能,用 “ 苞括 ” 的铺陈手法,从都邑之雄阔,到宫殿之奇美,从经济之繁茂,到民俗之杂彩, “ 取天地百神之奇怪,使其词夸;取风云山川之形态,使其词媚;取鸟兽草木之名物,使其词赡;取金碧彩缯之容色,使其词藻;取宫室城阙之制度,使其词壮 ”[6]卷三,8,容纳万有,连类繁举,实为 “ 物 ” 之府库,故 “ 京殿苑猎 ” 最适宜大赋的笔法和心胸。刘熙载论及文体篇幅与表现手法的对应关系说: “ 作短篇之法,不外婉而成章;作长篇之法,不外尽而不污。 ”[7]40“ 长篇宜横铺,不然则力单;短篇宜纡折,不然则味薄。 ”[7]77此语深得作文之理路,汉大赋往往长篇巨制,汗漫数千言,其容量自然比短制的诗词更具 “ 总揽万物 ” 的文体特质。
胡应麟《诗薮》言: “ 文章自有体裁,凡为某体,务须寻其本色,庶几当行。 ”[8]不同的文体必然固有与其相应的艺术表现方式和由此形成的特定艺术规范,即为文体的 “ 本色 ” ,学文写文都应依据各体的 “ 本色 ” ,把握不同文体的艺术标准与风格,创作运文才能不离文体轨制。明陈洪谟云: “ 文莫先于辩体,体正而后意以经之,气以贯之,辞以饰之。 ”[9]也就是要求创作首先要辨别文体,遵循文体独特的审美特性和表现手法,即使在文体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打破文体严格界限的情况,但也要仍 “ 本采 ” ,即以适宜于文体的体制寻求相对稳定的表达规制,方才不失其文之 “ 大体 ” 。大赋一体截然不同于其他文体的本质要义在于 “ 铺陈 ” 的体制规范,其审美对象为外向万物,其蕴含的精神结构为 “ 假托虚夸 ” “ 铺排名物 ” , “ 大题巨篇,苞涵广博,假设陈辞,凭虚构象,多致异物,不为征实,四言一顺,铺陈名物,堆砌形容 ”[10],揭示了汉赋文本的形式特征,正是这样宏大的审美对象和炫示的审美精神,决定了汉大赋表现 “ 物 ” 的方式以铺排充实、罗列名物、盛览炫博为旨要,以写物图貌之工笔,蔚似雕画之匠心凸显博观包容的文体特色。刘熙载《艺概·赋概》云: “ 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 ”[7]86近人刘咸炘《文学述林卷一·文变论》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 “ 铺陈物色固有宜赋不宜诗者矣 ”[11],可明赋之体性特征比诗更适合 “ 铺写叙物 ” ,大赋因巨制长篇而预设了苞括总揽的铺陈空间,博阔宏制使得物类丰满,林林总总,杂陈而出。清王芑孙《读赋卮言·小赋》谓 “ 赋者用居光大,亦不可以小言……极赋能事在于长篇 ”[12],易闻晓先生言 “ 其题包涵,至大无外,遂自由铺陈,尽情敷写。……笼天地于形内,措万物于笔端,非有大题包涵、巨制容纳,不克为之,可见赋体本质,必以铺陈效功 ”[10],以张扬物色为基本法式的文学体制非大赋而不可。
挚虞《文章流别论》曰: “ 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当而辞无常矣。 ”[5]《全晋文》卷七十七,1905“ 事形为本 ” 则文繁物丰,大赋一体将京都宫苑、山川湖海、地形物产、歌舞乐音、鱼虫兽禽等统通包纳其中,必然要求以丰盈的语词与精巧的构思为基础。汉大赋将前所未有的初创国家想象转化成 “ 直观的物化包综方式 ” 来总揽世界,并总是表现为一定的空间方位关系。以《上林赋》为例,程大昌《演繁露》言:
亡是公赋上林,盖该四海而言之。其叙分界,则 “ 左苍梧,右西极 ” ;其举四方,则曰: “ 日出东沼,入乎西陂 ” , “ 南则隆冬生长,涌水跃波 ” , “ 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水揭河。 ” 至论猎之所及,则曰: “ 江河为阹,泰山为橹。 ” 此言环四海皆天子园圃,使齐楚所夸,俱在包笼中[13]。
汉赋空间方位的书写,超越了现实的广阔无边,在汉赋的描写中,其本身并不是完全真实存在的现实世界的再现,而是一个想象中的国家疆域版图的精心虚构,但其构筑亦有其审美基础,冯小禄认为汉大赋作家生活在两汉 “ 声威无限远播、文化无限发达的大统一、大缤纷时代,有着相当现实的社会政治、疆域、制度、思想、文化基础和感受基础,其看来的夸张失实之处,正是真切感受所膨胀出来的艺术审美结果 ”[14]177。这种极尽辞汇陈述众多的事物、炫目的景象,东西南北、左右上下观览世界的书写方式,使得夸张繁缛、闳侈巨衍成为汉代逞辞大赋的普遍风格,也正是如此,赋体因其篇幅巨制、容量弘博,才能为包纳万物提供尽情铺写更丰富广阔的书写空间。
二、赋兼才学与繁辞巧构
虽然大赋的体制规定性有着 “ 铺写叙物 ” 的文体优势,但要广取名物、摛写丽藻,没有赋家深厚的积养和广博的学识,定然难为 “ 闳衍钜丽 ” 之文,汉大赋铺写之繁、运辞之巧、构思之妙,赋家才思丰蕴、覃精研思的技艺蓄积是必然的基础。清王修玉《历朝赋楷》言: “ 赋之体裁,自宜奥博渊丽,方称大家。 ”[15]赋家往往博通经籍,精于辞章,于创作便体现为囊括名物之富余,运造辞藻之丰赡,征材聚事、铺陈辞藻都基于赋家广博闻识和深厚学养。毛琅《师竹斋赋钞叙》论赋云: “ 风归丽则,辞翦美稗,其运意尚巧,其骋词贵妍,其选韵必新,其构局宜警,非学力者不能工,非有天资者愈不能工。 ”[16]此为刘熙载《艺概》所言 “ 赋兼才学 ”[7]101之谓。
赋体与中国古代其他文体相较而言,具有显著的语言艺术特征,汉赋作家着意为文的自觉心态、锻炼造文的书写路径,也使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文人群体。 “ 辞赋尤其是大赋最资学问。 ”[17]说明赋体创作对学识才力的要求甚高,并主要体现于辞章的修养、博物的取用、字词的繁难等方面。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云: “ 作赋之法,已尽长卿数语。大抵须包蓄千古之材,牢笼宇宙之态。其变幻之极,如沧溟开晦;绚烂之至,如霞锦照灼,然后徐而约之,使指有所在。 ”[18]31极力说明赋家创作本于学养积备,其所谓 “ 法 ” ,是以 “ 才学 ” 为前提。《汉书·艺文志》云: “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列为大夫。 ”[19]1755可明 “ 大夫 ” 的职能素养在于 “ 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 ” ,这也是 “ 能赋 ” 的基本内容和要求。作赋的前提是赋家笃厚的积学储备, “ 博极群书,方得选材豪富;拓开万古,方得标旨空旷 ”[20],如此,驱遣万象莫不包容博观,遣词造语莫不藻饰扬辞,唯有多识多闻才能发为伟赡钜丽之辞,在创作实践中沉淀于胸,融汇于心,贯通于思,运笔于言。明代谢榛对赋家积养有非常精到的论述:
汉人作赋,必读万卷书,以养胸次。《离骚》为主,《山海经》《舆地志》《尔雅》诸书为辅。又必精于六书,识所从来,自能作用。若扬袘、戌削、飞襳、垂髾之类,命意宏博,措辞富丽,千汇万状,出有入无,气贯一篇,意归数语,此长卿所以大过人者也[21]。
大赋铺写靡极、名物充实都基于 “ 养胸次 ” “ 精六书 ” 的广博积学。汉赋大家皆擅侈丽,尚罗列繁难奇异的字词,又因表达需要多新铸造字,炫示文采,这须有深厚的字学功底,清阮元《四六丛话序》云: “ 综两京文赋诸家,莫不洞穴经史,钻研六书,耀采腾文,骈音丽字。 ”[22]如 “ 隆崇嵂崒 ” “ 巃嵸崔巍 ” “ 噏呷萃蔡 ” “ 铿鎗闛鞈 ” “ 驞駍駖磕 ” 等等。另外,铺写的取资需要从浩繁海博的各类书籍中广泛搜罗, “ 赋家铺陈,正以搜罗异物,广致难僻,乃见取资之广,博识多方 ”[23]。如《子虚赋》连类铺排各种植物: “ 衡兰芷若 ” “ 芎藭昌蒲 ” “ 茳蓠麋芜 ” “ 诸柘巴苴 ” “ 葴菥苞荔 ” “ 薛莎青薠 ” “ 藏莨蒹葭 ” “ 东蔷雕胡 ” “ 莲藕觚卢 ” “ 菴闾轩于 ” 等等,赋家举凡各类名物纳于笔端本立足于多识博闻,非博学蓄势而不能为。《文心雕龙·才略》专以赋体创作为中心阐释赋家积养与创作风格的关系:
汉室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其辩之富矣。贾谊才颖,陵轶飞兔,议惬而赋清,岂虚至哉!枚乘之《七发》,邹阳之上书,膏润于笔,气形于言矣。仲舒专儒,子长纯史,而丽缛成文,亦诗人之告哀焉。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然覆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 “ 文丽用寡者长卿 ” ,诚哉是言也!王褒构采,以密巧为致,附声测貌,泠然可观。子云属意,辞义最深,观其涯度幽远,搜选诡丽,而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矣[3]1773-1779。
对于大赋体制而言,由于长篇巨制的形制要求,征材聚事的构篇布局,要达到汇集名物,堆砌辞藻,绝非简单的艺术思维活动。细究汉大赋之天文地理、人事典制、山川河泽、草木虫鱼、宫殿苑囿、声乐歌舞,无所不包,其 “ 苞括宇宙,总览人物 ” 并非敷陈无方, “ 赋览之,初如张乐洞庭,褰帷锦宫……如文锦千尺,丝理秩然;歌乱甫毕,肃然敛容 ”[18]31。如此宏大篇制,物象事类浩博繁复,若无一定思理规范,胡乱堆砌,必然杂乱无章,无论是从空间的架构、物类的晓通,还是从词汇之宏博、列罗之绚烂,其思维理路皆能 “ 秩然 ” ,让人感叹其构思的密缜而周备,必是赋家经过了一番倾尽心血的营心构造。《文心雕龙·神思》所谓 “ 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 ”[3]989,可见赋家写赋必殚精竭虑、倾心造作,否则不成。赋用以铺陈事物,要条理清晰,语言清朗,又必潜心为文,据《西京杂记》载: “ 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 ”[24]12桓谭《新论·祛弊》载: “ 子云亦言,成帝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诏令作赋,为之卒暴,思精苦,始成,遂困倦小卧,梦五脏出在地,以手收而内之。及觉,病端悸,大小气,病一岁,由此言之,尽思虑,伤精神也。 ”[25]30将作赋的运思和凝虑以神魂颠倒、如痴如醉、劳神劳思的形象作如此记录,班固《两都赋序》说: “ 朝夕论思,日月献纳。 ”[26]23也正是描绘了赋家作赋运思之艰苦,造文之不易。
《西京杂记》引司马相如言作赋之法: “ 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 ”[24]12此谈及赋家创作时的刻意构思,精雕细琢,思虑缓成,只有对物性博通、知类融汇、洗练辞藻方可为文, “ 赋欲纵横自在,系乎知类 ”[7]99。如枚乘《七发》写音乐一节,先从乐器选材写起, “ 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中郁结之轮菌,根扶疏以分离。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 ” 。经过 “ 背秋涉东 ” 的沉炼后成为上佳的制器之材,后铺叙乐器制作的精细和加工的高超技艺, “ 使琴挚斫斩以为琴,野茧之丝以为弦,孤子之钩以为隐,九寡之珥以为约 ” 。最后经过顶尖乐师对乐曲出神入化的演奏,达到音乐的至高境界, “ 使师堂操《畅》,伯子牙为之歌。歌曰:‘麦秀蔪兮雉朝飞,向虚壑兮背槁槐,依绝区兮临回溪。飞鸟闻之,翕翼而不能去,野兽闻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蟜蝼蚁闻之,柱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 ”[26]634-642若非作者对琴器物性、乐音知识的晓通,绝写不出此言语。汉赋往往通过语言文字的状物描绘功能来调动各种感官,达成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多重感受在字里行间的游艺,全显赋家驱遣辞藻和锻字造语的功力。
赋家运才的精思巧构还表现在铺写秩然有序,叙物紊而不乱,刘熙载《艺概·赋概》分别从铺写物类事类的空间性和时间性上来概括赋体书写形构的方式: “ 赋兼叙列二法:列者,一左一右,横义也;叙者,一先一后,竖义也。 ”[7]98描摹地理空间的经典文例莫过于《子虚赋》 “ 其东 ” 至 “ 其下 ” 一节,其所列 “ 众物居之,不可胜图 ” ,却不乏清晰列序,构思巧妙。 “ 由此足见司马相如在处理空间叙写时,非常用心地建构了一道井然有序,而又为大家所熟悉的骨架。在‘东南西北’的平面圆形空间叙事中,又穿插了‘其高’‘其卑’‘其中’‘其上’‘其下’的布置而构成立体、三维的空间。有了这个严整的立体骨架,即使容纳更多的景观、物象,也不致失其空间的严整性、有序性。而且,方位的骨架下,各类景物和物象按其性质、种属得到了最充分和尽乎穷尽的展示。 ”[27]可见赋家赡详且具巧思是大赋创制的主体要求。陈绎曾《文筌·汉赋法》极为全面地剖析了辞赋技法的锤炼:
汉赋之法,以事物为实,以理辅之。先将题目中合说事物,一一依次铺陈,时默在心,便立间架,构意绪,收材料,措文辞,布置得所,则间架明朗;思索巧妙,则意绪深稳;博览慎择,则材料详备;锻炼圆洁,则文辞典雅。……事事物物,必须造极[28]。
明王世贞云: “ 赋家不患无意,患在无蓄,不患无蓄,患在无以运之。 ”[18]31赋体的整体风貌源于赋家集 “ 学 ” 与聚 “ 材 ” 的修养与学识,赋家以其博辞巧构的才学与功力成就了大赋 “ 连篇累牍,博辩纵横;抽密骋妍,飞腾绮丽 ”[29]的艺术景观。
三、 “ 体国经野 ” 与文化精神
汉赋 “ 体国经野 ” 首先表现在政治文化图式的精神呈现。两汉极度彰显宏阔豪迈的时代精神,歌颂汉代盛世和勋业的文学要求是当时从统治者到大臣文士的一种共识。王褒《四子讲德论》明言大汉 “ 盛德巍巍荡荡 ” “ 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 ”[26]958,桓谭认为 “ 开辟以来,惟汉家为最盛 ”[25]40,理应有颂盛之文,王充《须颂篇》亦言 “ 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记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 ”[30],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声明了炽烈浓郁的 “ 宣汉 ” 意识: “ 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 ”[31]4005赫然可见武、宣之世因开疆拓土之功,货裕物丰之治,极大地刺激了统治者 “ 内多欲而外施仁义 ”[31]3774的统治思维, “ 更由于儒学的尊隆、文学与思想的泛政治化,而进一步主要表现为儒士广大的胸襟和抱负,于是借助宏阔的意境和铺陈排比手法,对自然和人生展开壮丽的畅想 ”[32]。汉赋所描写的对象往往宏大而繁缛,《西京杂记》言 “ 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 ” ,追求 “ 控引天地,错综古今 ”[24]12的大题包容格局,总体呈现出侈丽宏衍、靡丽多夸、穷形尽相的风格, “ 物之赋显,事以颂宣 ” 是汉代大赋作家共同的审美旨趣。汉赋所构建的巨大时空意识,将山川河泽、宫殿苑囿、林木鸟兽、土地物产、音乐歌舞、骑射酒宴,一一包举在内,炫示德兴国治、物博地大的意识正折射了汉人将物质享受再造为精神享受的文学自觉。
汉代统治者物质上日渐丰裕的同时,也通过精神浸润的方式逐步实现中央集权的一统化,从叔孙通定礼仪,到董仲舒尊儒术,使汉家政治合理性认同和巩固思想文化的途径有了坚实的基点,在文学上如何顺势和承载汉家政治集权的思想指归,显然是汉代文人需开辟的文学道路, “ 三代之后,以西汉为文章之盛,而尤盛于武帝时。其时文似有三种,枚、邹、庄、司马、吾邱之流,皆以词赋倡和,供奉乘輿,此其一。太史公包罗诸史,成一家言,又其一。至淮南宾客,撮合诸家之旨,发明道术,又其一 ”[33],正是阐述了赋体文学在新的政治环境下的发展态势。时代催生了规模宏大、包罗万象的文学形态,其必定是政治话语所选择的书写模式,其也必须着力为两汉政治统治承担文化使命。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篇》说: “ 赋家者流,犹有诸子之遗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 ”[34]颇有见解地指出赋家作赋的初衷正如同诸子孜孜寻求天下统一之道一般,诸子的主导思想是通过建构一种学术思想和学术思维方式来掌握统治话语权,而 “ 汉赋最典型的就是从诸子‘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分裂的学术汇总到汉武帝崇礼官、兴太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并为中国文学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典雅模式 ”[35]。许结先生认为这个模式就是中国文学最偏重的统一的帝制文学,汉代的政治文化图式通过 “ 京都苑猎 ” 大赋以 “ 体国经野 ” 的气象得以呈示。
再次表现为政治地理空间的文化视域。对于雄视寰宇的强大王朝而言,首先必须强调的是地理版图的认同和昭告,在这一点上,汉赋 “ 铺写叙物 ” 的文化精神有其实在的政治功用。《隋书·地理志》载: “ 自古圣王之受命也,莫不体国经野,以为人极。上应躔次,下裂山河,分疆画界,建都锡社。 ”[36]806近代学者柳怡徵亦云: “ 分析土壤,剖辨物种,而民生国政于是乎定。 ”[37]《尚书·禹贡》就记录了天下划野分州,畿服贡赋,过常宝以为这 “ 表达了建立在大禹整治山水的神圣史迹上的地理政治理念,是一种初步的地缘国家意识 ”[38]。据《隋书·经籍志》载: “ 《书》录禹别九州,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条其物产,辨其贡赋。 ”[36]987对国图之区画 “ 依江、河、湖、海为线界划分‘九州’,从政区到农业、物产、贡赋、山川、交通铺述全国地理概貌,构成综合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整体图式 ”[39]141。从汉赋所作东南西北中的地理方位叙述模式来看,其 “ 物 ” 的范畴首先是依地理空间意识而展开铺写的,以文学的形态宣示地界国图予以附和。汉武帝时,用兵边陲,开疆拓土,平东夷,扫北狄,灭西戎,服南蛮,版图空前扩大,四夷俯首听命,纳贡称臣。扬雄《长杨赋》就对汉家领土辖管进行了颂扬:
于是圣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骠卫,汾沄沸渭,云合电发,猋腾波流,机骇蠭轶,疾如奔星,击如震霆。碎轒辒,破穹庐,脑沙幕,髓余吾。遂躐乎王庭,驱橐驼,烧熐蠡,分剓单于,磔裂属国。夷阬谷,拔卤莽,刋山石,蹂尸舆厮,係累老弱,兖铤瘢耆,金镞淫夷者数十万人。皆稽颡树颌,扶服蛾伏,二十余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临,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节西征,羌僰东驰。是以遐方䟽俗,殊邻绝党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绥,莫不蹻足抗首,请献厥珍。使海内澹然,永亡边城之灾,金革之患[26]175-176。
司马相如《上林赋》也描绘出一个包罗万象、震撼心魄的广大空间:
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灞浐,出入泾渭;酆镐潦潏,纡馀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洲淤之浦,经乎桂林之中,过乎泱漭之壄[26]157。
此描绘的虽不是完全征实的地理版图,但仍然可以从赋家对世界万物的浓厚兴趣,夸诞虚饰的醉心构结,典型地反映出汉人心目中浓缩了的宇宙天地。相如之后,大赋的空间地理思维始终延存不废,继而出现了大量以京都为中心对政治图域的书写,可见,对于汉王朝历史版图空前扩大的自信和自矜,赋家当以 “ 巨丽 ” 的大赋进行应和,初创政权时期的新鲜感和好奇心使得文学将目光集中投射到外部世界,形成上下左右、东西南北打量的文化心理,汉大赋可当是一个强大文学想象的精神构建。据《汉书·地理志》载:
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壄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是故《易》称: “ 先王建万国,亲诸侯。 ” 《书》云 “ 协和万国 ” ,此之谓也。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19]1523。
政治首重实惟治地,之要在于地域观念和行政管理的结合,《周礼·天官冢宰》载: “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 ” 郑玄注: “ 体犹分也。经谓为之里数。 ”[40]639故观汉赋 “ 写物 ” 空间地理意识的凸显,与《周官》所记版图、测量、土壤、民物一一经画无异,均为政治之助益。《文心雕龙·诠赋》也集中表达了汉赋在 “ 体国经野 ” 上的功用: “ 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 ”[3]283“ 体国经野 ” 首先体现在国都和郊野的规划,内涵画野分州的政治文化主旨,彰显以京都为中心的统一文化,虽然汉大赋并非一一征实记录国家地理与方志,但其关于国家政治的文学隐喻和想象确是一种自觉的创作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汉大赋的宏大体制和规模,铺张扬厉的体格特征,更多体现的是国家意志而非个人意志,是初创帝制时代的产物和象征。
在政权交替的正统认同上,汉赋发挥了极强大的精神舆论功能,特别是在思想上强调汉代帝王取代前朝的合法性。如 “ 天命有圣,托之大汉 ” (杜笃《论都赋》), “ 上帝受命,将昭其烈,潜龙初九,真人乃法 ” (崔骃《反都赋》), “ 于是圣皇乃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赫然发愤,应若云兴 ” (班固《东都赋》),都极力表明汉得天下是受天之命,取代前朝是代天而革其命。 “ 秦汉之前周代天子礼仅是一种理想图式,其政治结构是宗法分封,至汉代以‘郊祀’为代表的天子礼出现,方完成这一历史的转换,而汉大赋中有关天子礼之描写,既是应运而生的新气象,更是汉天子礼的真实记载。 ”[39]143有如杜笃《论都赋》: “ 方躬劳圣思,以率海内,厉抚名将,略地疆外,信威於征伐,展武乎荒裔。若夫文身鼻饮绥(严可均校:绥,当作缓)耳之主,椎结左衽鐻鍝之君,东南殊俗不羁之国,西北绝域难制之邻,靡不重译纳贡,请为藩臣。 ”[5]《全后汉文》卷二十八,626张衡《西京赋》: “ 方今圣上,同天号于帝皇,掩四海而为家。富有之业,莫我大也。 ”[26]61其形成的以京都为中心辖制全国的政治理念,典型反映大汉盛世的宏阔气象。
四、结语
“ 文 ” 如何择选和表现 “ 物 ” 既形成了一定的话语秩序建构的文本体式,同时也因不同文体体制和规范的确立而受其约束和规定,展现出不同的结构模式和艺术风格。体正为先,至于文之精神、结构、布局、辞藻还须仰仗作家的个体创造。 “ 赋以铺陈为正格。 ”[41]赋有别于其他文体的本质要义全在 “ 铺写叙物 ” 的文体规制,其文制的基点与博阔宏衍的体制风格、精研覃思的作者学识密切系合。
同时,汉赋的体制风格也与整个大汉时代 “ 宣汉 ” 的意识相应和,追求空前绝后的文化心理造就了汉赋的造作意图, “ 引发淋漓书写的欲望 ”[14]161,两汉的兴盛赋予汉赋作家明确的宣颂意识,鼓动着尚大、尚多、尚繁、尚丽的文学欲求。汉赋的闳侈衍制承继楚辞空间包容的余绪,在与大汉时代精神结合后,便催生了最能体现盛世的新兴赋体文学,既是强大政权文化心理折射出的宣汉图式,也是政治地理空间思维的文学附会。 “ 汉赋虽然很少有作者个人情绪的表现,然而它的华美、庄严和壮丽,却正是大汉全盛时代之雄伟的呼声。 ”[42]汉赋兴盛的情理尽在其中。
注释:
①[瑞士]沃尔夫冈·凯赛尔著,陈铨译:《语言的艺术作品:文艺学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二部分第九章 “ 风格 ” A之五,第373页指出 “ 风格对作家创作的规律性影响 ” : “ 盛行的风格规律、公共的嗜好、代表性的模范、世代、时代等等,它们统通对创造作品的作家发生影响,正如选择的类别本身已经对它们发生影响一样。它们抓住了作家,把他带到这里来,对他施加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