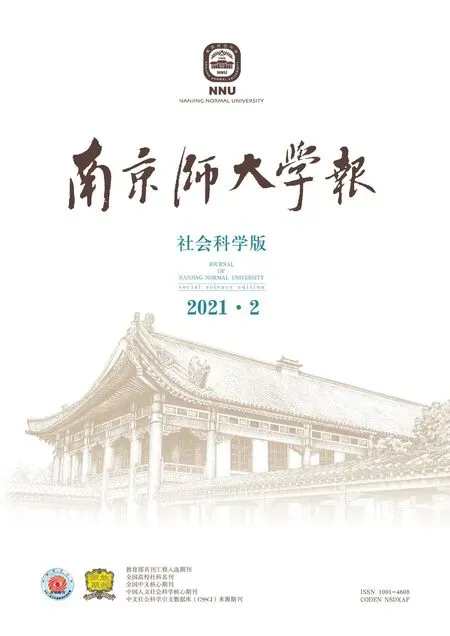如何倾听来自“伦理”的文化天籁
2021-12-26樊浩
樊 浩
一、 倾听爱因斯坦引力波的“大耳朵”
每个民族都有一些携带自身生命密码的基本话语,因其缔造生命的基因意义,它们常常作为“心灵的惯习”而以文化本能的方式被表达演绎,日用而不知;因其基因复制逻辑的残酷式强大,在文明史的漫长演进中,青春期的文化勃兴每每以某种决然的方式试图告别母体,以宣示自己的独立,然而不可逃脱的宿命却总是以一次次终极觉悟而认同回归。
通达这些基本概念,人类必须进化出一只探测爱因斯坦引力波的“大耳朵”,[注]1916年,爱因斯坦根据广义相对论预言了引力波的存在。近十多年来,各国科学家建造诸多引力波探测器,成功捕捉到来自遥远时代遥远星体的“声音”,这些探测器被比喻为“大耳朵”。藉此倾听来自本土与世界、传统与现代诸文明维度的文化天籁。倾听来自文明根脉、文化深处民族精神原初的生命气息;倾听这些生命气息在穿越时空的漫漫文明旅程中于当下承载它们的主体生命中的心脉搏动;诸多异质文化之间相互倾听,倾听异域风情的天籁及其与本土文化生命气息相通的文化交响,从而倾听现代文明的共同心音。当然,拥有这只“大耳朵”必须有一种开放而自信的情怀与慧心,洞察希夷之境中相似概念的毫厘之差所可能导致的千里之谬。在文明对话和文明冲突的双重背景下,也许没有任何学术努力比对这些基本话语的相互倾听和彼此理解更重要而急迫,其意义决不局限于本土话语的重建。在文明内部,它具有“知道你自己”即回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终极追问的本原意义;在文明对话中,它是达成真正的文化理解和文明和解的哲学前提。
“伦理”,就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基本话语之一。人们很难否认它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基因意义,其文明史的地位已经为中国五千年文化传统以及古今中外的杰出研究所揭示,新的挑战在于:到底如何倾听来自“伦理”的文化天籁?
显然,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对于通达“伦理”这类基本话语已经捉襟见肘,无论“原意”还是“意义”、“解释”还是“理解”,都难以显现“伦理”在中国文化中幽远而不息的生命基因意义,也难以在文明对话中把握中国文化体系中“伦理”的染色体地位。倾听“伦理”,大而言之,倾听来自任何文化体系中的那些元概念或元理念的生命气息,必须借助老子在《道德经》开篇所说的那种彻底的哲学大智慧:“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因其是民族生命的文化基因,这些概念“可道”,但一旦被“道”便已经非其所“道”;“可名”,但一旦被“名”已经非其所“名”。“非常”之处在于它们的根脉意义或“元”地位。“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德经》)“伦理”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染色体,在质朴“无名”的原初状态,它已经参与了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的历史性创造;在“有名”即中国文化的伦理觉悟和世界对中国的文化认知中,它开启并绵延了伦理型文化的五千年文明史历程。在中国文化中,“伦理”“可道”却非一般意义上“伦理”之“常道”;“伦理”“可名”并且已经获得伦理之“名”,但也非日常意义更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伦理”之“常名”。
“可道”而“非常道”,“可名”而“非常名”,倾听来自“伦理”的文化气息,必须在本土文化传统、跨文化对话、人类文明史的有机体系中进行三大哲学辩证,由此既“听”其“中国心音”,又“见”其文明史的普遍意义。
二、 中国文化“最崇高的概念”是什么
这是来自本土文化根脉的哲学辩证,其结论是:“伦”,是中国文化“最崇高的概念”;“伦”与“道”,是中国文化基因的一对染色体。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提出“轴心时代”的概念,金岳霖先生“接着讲”,指出轴心时代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一些“最崇高的概念”。然而无论“轴心时代”还是“最崇高的概念”,都遭遇严峻的逻辑和历史挑战。雅斯贝斯发现:“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所发生的精神过程,似乎建立了这样一个轴心。在这时候,我们今日生活中的人开始出现。让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的时代’。”(1)田汝康、金重远:《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9页。轴心时代是人类精神奠基的时代,在中国、希腊、希伯来、印度等不同地域差不多同时产生了共同的觉悟,相信人类可以在精神上将自己提升到与宇宙同一的高度,诞生了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释迦牟尼等思想先知。金岳霖先生进一步指出,这种精神奠基的标志就是产生一些“最崇高的概念”。轴心时代的觉悟具有根源性文明史地位。“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2)[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4页。当今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的“复兴”话语相当意义上指向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的概念具有很强的表达力与影响力,一经提出便处于激烈的学术争讼之中。很多学者认为,它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倾向,将整个文明史“砍掉一半”“打对折”。(3)正如许倬云先生所说,“轴心时代”理论有突出古希腊而回避文明源头之嫌:“古代的几个主要文化——两河、埃及、中国及印度河流域——都已有文字。然而雅斯贝斯却不承认两河、埃及有过轴枢文化。雅斯贝斯的疑难,在于他未能认清两河古代文化与埃及文化实为波斯文化、希腊文化以及以色列文化的源头。”许倬云:《论雅斯贝斯枢轴时代的背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余国良:《轴心文明讨论述评》,《二十一世纪》2000年第2期。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按照“轴心时代”的理论,中国文明史只有从老子、孔子开始的两千多年,作为根源的三千多年便没有意义,于是五千年文明史只剩下两千年。正如有的学者所批评的那样,雅氏轴心时代的理念出自黑格尔,认为“所有历史都走向基督,而且来自基督。上帝之子的出现是历史的轴心”。(4)田汝康、金重远:《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38页。张京华《中国何来“轴心时代”?(下)》,《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轴心时代只是西方思想家的理论假设,而非真实性的概念;只是解释性的概念,而非事实性的概念。(5)张汝伦:《“轴心时代”的概念与中国哲学的诞生》,《哲学动态》2017年第5期。
不过,无论关于“轴心时代”的争讼多大多深刻,不可否认它是一个已经产生很大影响的概念。悬置这一跨文化争讼,需要追问另一个问题:假设真的存在的一个轴心时代,那么中国文明在这个时代所提出的“最崇高的概念”是否就是金岳霖先生所说的“道”?
金岳霖在《论道》中发现,每个文化区有它的中坚思想,每一中坚思想都有它最崇高的概念,是基本的原动力。中国即儒道墨兼有的“道”,印度即“梵”或涅磐,希腊的逻各斯,希伯来的上帝。然而精神史的事实表明,中国文明在“轴心时代”最重大的觉悟不仅是“道”,而且还有“伦”,“道”与“伦”构成所谓“轴心时代”中国文化互补互动的两个“最崇高的概念”,它们是中国文明的一对染色体。“道”作为轴心时代为中国文化所贡献的“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没有太多争议,然而“道”并不足以解释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关于“道”表述最系统的是老子的《道德经》,然而《道德经》中的“道”与“德”都不是所谓“常道”和“常德”,或者说不是道德形而上学,而且是关于宇宙人生的哲学形而上学。“道”揭示形上世界的本体性,在形上本体性之外还有生活世界的总体性,这个总体性的概念就是所谓“伦”。
以下三方面可以提供佐证。
其一,表面看,作为道家、儒家经典的《道德经》和《论语》的核心话语都是“道德”。在《道德经》中,“道”出现77次,“德”出现45次,“伦”和“理”都未出现。在《论语》中,“道”出现89次,“德”出现40次,“伦”只出现2次,“理”字未出现。然而并不能由此证明道德高于伦理,事实上,无论《道德经》还是《论语》,关于“道”和道德的讨论,都基于并指向世俗生活的人伦。而且,关于伦理和道德,还有另一种概念表述,这就是“礼”和“仁”。《道德经》中“礼”出现5次,“仁”出现8次。《论语》中“礼”出现75次,“仁”出现110次。《道德经》分《德经》和《道经》,其主题和体系是由天道而人道,推天道以明人事,所谓人道和人事就是人伦。《论语》的核心命题是“克己复礼为仁”,“礼”的伦理高于“仁”的道德。“伦”字虽未出现或很少出现,但没有足够的根据由此望文生义断言其文化地位逊于“道”。
其二,在中国文化中,“伦”和“伦理”的概念可能比“道”和“道德”的概念出现更早,至少差不多同时诞生。“道”和“伦”在《诗经》和《尚书》中都已经出现。潘光旦先生在《说伦》中借用汉代刘熙在《释名》中的考证,指出“伦”与“沦”“论”“纶”“抡”等带“仑”的字都可以相互通借。“论,伦也;有伦理也”;“沦”“伦也;水文相次有伦理也”;“纶”即“伦也;作之有伦理也”。以“伦”或“伦理”说明其他带“仑”的字,表明“伦”“伦理”的出现比它们更早。
其三,关于“道”和“伦”的关系,最经典的表述是孟子《孟子·滕雯公上》中那个著名论断:“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道”是人之为人之根本,但“道”的坚守和拯救都在于“伦”。“人之有道——教以人伦”,是中国文化的根本逻辑和根本觉悟,其文化逻辑与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命题一以贯之,它表明,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孔孟之道”中,“道”与“伦”,是具有染色体意义的一对“最崇高的觉悟”。
无论轴心时代的建构还是后人对“最崇高概念”的认同,中西方都具有不同的哲学传统。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寻找唯一的“始基”或“造物主”,于是有“逻各斯”或“上帝”;中国文化依循《周易》所揭示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规律,以阴阳辩证互动为世界的根源,“一阴一阳之谓道”,认为世界的生命、文化的生命像人的生命基因一样有阴阳两个辩证互动的染色体。伦与道,或伦理与道德就是中国文化生命,中国人精神世界,也是轴心时代的“中国觉悟”的一对文化染色体。
遗憾的是人们在对此做出理解和解释时,往往接受西方式“始基思维”或“本体思维”的方式,只将“道”认同为“最崇高的概念”,于是最多只追究了形上世界的本体性,冷落和解构了生活世界的总体性。按照同样的逻辑,在理解“道德”时只抓住“道”而失落了“德”,理解“伦理”时只抓住“伦”而失落了“理”,从而对文明史的解释和对世界的把握都不可避免的碎片化,难以理解和诠释文明史和文化史的生命本真。
三、 “伦理”=“ethic”?
这是来自跨文化对话的哲学辩证,结论是:伦理≠ethic。
现代中国学术对“伦理”概念的文化诠释,从博士论文到教授讲课,一种认知与表达几成范式:“伦理”就是英文中的“ethic”。通常的推进是由此找到这一英文概念的古希腊源头,于是二者之间似乎便既“同”且“和”。无疑,在全球化和文明对话时代,任何一个基本概念的诠释都需要在异质文化中寻找相对应的参照,以使对话成为可能,这种状况犹如高铁车厢中乘客总是以窗外静止的参照物感知火车运动的状态和速度一样,而在不挂一丝云彩的天空,人们常常很难直观地感受到飞机的驰行。
然而,这种诠释方式的最大局限也许只能寻觅异域风情的参照,却很难在异域中邂逅真正的“知音”。因为任何概念尤其那些“最崇高的概念”总是在“本乡”故土的母体中从单细胞成长为灵长类,在文化的“异乡”最多只能找到某些外表的相似性,难以发现真正的孪生兄弟。简单的话语互释很可能导致潜在信息流失、意义歪曲甚至价值异化的重大风险。可以说,以“ethic”简单比附甚至直接等同“伦理”,是关于“伦理”概念的理解和对话中最常见也是最深刻的误区。
第一,按照人文社会科学的移植理论,人文社会科学遵循与自然科学完全不同的对话规律。(6)杜祖贻:《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移植与应用》,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4页。自然科学具有世界性,所谓“中国数学”“中国物理”意味着数学和物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而“中国伦理”“中国哲学”一定是“中国人”的伦理和中国人的哲学,是在中国文化中生长出来的伦理理念和哲学理论,“中国伦理”和“中国数学”的区分,如果用英文表述,那就是“Chinese Ethic”和“Mathematics in China”。人文社会科学遵循“移植”的规律,同乡与异乡的差异,很可能使同一概念有“橘子”和“枳子”的天壤之别(7)这是出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的一个故事。“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战国时代的齐国宰相晏子出使楚国,楚王设计羞辱齐国,指着被捕的盗贼问:“这是哪国人?”回答:“齐国人。”楚王感叹:“盗贼怎么尽出于齐国啊!”晏子讲了这个故事,说有一种水果,在淮河以南是甘甜的橘子,然而一旦到淮河以北便成为苦涩的枳子,品种相同,只因环境殊异。暗指齐国人在楚为盗完全是因为楚国伦理风尚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南橘北枳”的故事。。
第二,在人类文明的广阔视野中考察,中国文化中“伦”和“伦理”的概念或早于古希腊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古希腊“ethic”的概念到亚里士多德才正式出场并建构系统理论,经典即《尼各马科伦理学》;而在中国的《诗经》《尚书》中就已经有“伦”字或者“伦理”的话语,《周礼·冬官考工记》有所谓“析干必伦”。孔子《论语》可以被当作系统论述人伦或“伦理”的著作,甚至可以说《论语》即《伦语》。即便将《论语》与《尼各马科伦理学》做比较,孔子也先于亚里士多德两百多年,以一个出现较晚的概念诠释更早形态的文化理念,显然有历史错位之失。
第三,“伦理”与“ethic”在各自文明体系中的地位和文明史上的命运迥然不同。“ethic”生成于古希腊,但在日后古罗马的拉丁化过程中经西塞罗的拉丁文转换而成英文的“moral”即道德,此后一直到康德时代,西方文明史上“ethic”便总体上缺场,正如黑格尔所说,康德只有道德,完全没有伦理的概念,甚至对它公然凌辱,(8)“康德多半喜欢使用道德一词。其实在他的哲学中,各项实践原则完全限于道德这一概念,致使伦理的观点完全不能成立,并且甚至把它公然取消,加以凌辱。”[德]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2页。直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诞生,才恢复了伦理在精神哲学体系中的地位。而在中国,不仅伦理与道德几乎同时诞生,而且“人伦”往往比“人道”更具体也更优先,孟子“人之有道——教以人伦”的范式已经清晰澄明“伦”与“道”之间的精神哲学关系,在近现代的中国更是诞生了作为独立学科的“伦理学”。“伦理学”虽然像有些教科书粗枝大叶的所说的那样,是研究道德问题的学问(9)我并不认同这一说法,因为研究道德问题的学问应该直接被称为“道德学”,“伦理学”是研究“伦”及其“理”的学问。,而在近现代西方,“伦理学”往往被称为“道德哲学”或“道德科学”。可见,不仅在中西方文明体系中“伦理”与“ethic”的文化地位不对等,二者的历史命运也相当不对称,以后者诠释前者,解释力与表达力十分有限。
第四,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伦理”携带“ethic”所不具有的诸多文化信息,最核心的信息是人伦与天伦、人伦与人道总是贯通并且同一。“伦理”是中国入世文化所具有的终极性和根本意义的概念,可以说如果没有“伦理”,中国的入世文化就不能建构和延绵,因为“道”的形上本体性并不具有“伦”的总体性那样为生活世界提供家园和终极归宿的意义,道家后来流为道教可以证明;而在西方文化中“ethic”则以上帝或神的存在为前提,是终极实体预设前提下的一种价值体系。更具文明史意义的事实是,“伦理”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文明路径下的“最崇高概念”,或“国——家”文明背景下的文化理念,其根本伦理规律是人伦本于天伦而立,社会关系的人的规律根源于家族血缘关系的“神”的规律。
鉴于以上四个方面,当用“ethic”诠释“伦理”,或将“伦理”当作“ethic”时,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信息流失,价值异化。无疑,文化需要对话,对话必须在跨文化中找到相对应的概念话语,然而必须牢记的事实是:它们只具有相似性,因而只可作为异域风情参照,不可直接嫁接。
四、 “伦理”是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一种文化形态或文明形态
这是来自人类文明史的哲学辩证。
当今讨论和理解“伦理”的概念,一般只是在与“道德”相对应的意义上言说,将它当作意识的一种形态或精神的一种形态,也许这一定位对西方“ethic”的概念诠释来说有合理性,但在中国文化中却严重窄化甚至扭曲了“伦理”的概念内涵及其文明意义。在历史上,中国文化被称之为伦理型文化,不仅表明“伦理”是意识的一种形态,而且表明它具有文化范型意义,其地位如此重要乃至创造了一种文化类型即伦理型文化,也创造了一种文明类型即伦理文明。
梁漱溟先生曾以几个著名命题揭示伦理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有宗教之用”;中国“以伦理组织社会”。(10)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77、85、113页。梁先生发现,西方社会以团体与个体为两极,以家庭为虚位,“中国人却从中间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而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团体这两端”。他认为说中国文明“家庭本位”不恰当,缺乏解释力,因为伦理自家庭始,家庭是伦理的自然基础,故伦理首重家庭,“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1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78、79页。但家庭在中国文化中确实不仅具有根源地位,而且具有范型意义。所谓“伦理有宗教之用”“意谓中国缺乏宗教,以家庭伦理生活来填补它。但我们如果说中国亦有宗教的话,那就祭祖祀天之类”。他将这种宗教称为“伦理教”。(1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87页。梁先生发现自孔子提出“正名”,中国文化便开始“春秋定轨”,自觉地进行以伦理组织社会的文化设计和文化历程。孔子的正名思想,既是一种人格理想,也是一套组织秩序,孔子对后世的最大贻赠,就是提供了一套伦理秩序的大轮廓。(1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121页。
不少西方学者也发现中国文化的伦理气质。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东方世界·中国”部分曾断言,中国完全建筑在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就是客观的家庭孝敬。对黑格尔这一论断的翻译可能有所偏差,根据其《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的理论,将其翻译为中国完全建筑在“伦理的结合上”可能更准确。英国哲学家罗素也发现,“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1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19页。当今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演讲中也多次断言,所谓“中国”,其实是一种文明。这些论断隐含了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但将中国当作一种文明形态有其合理因素,这种文明形态的内核就是伦理,所谓“伦理型文化”。
也许人们会说“伦理型文化”只对传统社会有解释力,现代中国早已天翻地覆。然而,一方面,关于“伦理”的概念和理念不仅要从中国文化的深处梳理,寻找其基因意义,它在相当程度上不仅根源于传统,而且必须对漫长的传统社会以及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发展有解释力和表达力;另一方面,事实表明,现代中国文化依然是伦理型文化。
根据我们自2007年以后所进行的持续十年的三轮全国性大调查的信息,虽然现代中国社会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发生根本变化,但伦理型文化的基因没有变,这就是变中之不变。具体表现有二:一是宗教并未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主流,信教人数不到10%;二是伦理路径依然是调节人际关系的首选。它说明,“有伦理,不宗教”依然是中国文化气质和中国文化气派。中国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都是在有宗教选项的背景下而没有走上宗教的道路,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有伦理”,“不宗教”的底蕴和底气是“有伦理”,在“有伦理”与“不宗教”之间具有必然的因果关联。(15)关于现代中国文化依然是伦理型文化、以及“有伦理”与“不宗教”之间关系的论证,参见樊浩:《中国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共识——基于改革开放40年持续调查的数据》,《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
要之,中国文化中的“伦理”概念具有非常广泛而丰富的内涵,它不只是意识的一种形态,而且是具有范型意义的一种文化形态,创造了一种文化类型和文明类型,具有深刻的文明史意义。因而对“伦理”概念的把握,既不能简单进行抽象的概念分析,更不能进行语言学的粗暴配对,而必须在世界文明史和中国文明史的整个进程中进行生态把握和生命理解。西方式的诠释方法、现代主义的解析方式,都会导致对“伦理”的肢解和曲解。
通过以上来自中国文化深处、与西方文化的跨文化对话、回归文明史的全景及其生命进程的哲学追问,可以确立关于“伦理”理解的三大哲学理念:“伦”是中国文化“最崇高的概念”,“伦”与“道”,是中国文化的一对染色体;“伦理”≠“ethic”;“伦理”不只是意识的一种形态,而且是文化的一种形态、文明的一种形态。藉此,才可以倾听到来自“伦理”的生命气息和文化天籁。
五、 “伦理”的文化天籁
如何倾听来自“伦理”的文化天籁?老子、黑格尔、伽德默尔的方法论对话,可以提供一个倾听“伦理”引力波的“大耳朵”。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提供形上指引;伽德默尔的“解释”与“理解”、“含义”与“意义”提供解释学意义上的信息处理器;而黑格尔的“概念”与“定在”、“灵魂”与“肉身”则为倾听伦理的文化天生天籁提供一个坐标系。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的开篇曾宣示,哲学所研究的是理念而不是概念。理念是概念和它的定在即实存的统一,其中概念是灵魂,它所表征的那个实存或所谓定在是肉身。“概念和它的实存是两个方面,像灵魂和肉体那样,有区别而又合一的。”“定在和概念、肉体和灵魂的统一便是理念。”(16)[德]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页。其实,任何文明体系中的基本话语都不只是概念,而是理念,它们不仅是信息符号,而且表达和传递对世界的态度。中国的“伦理”话语是理念,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它不是抽象的话语工具,而是鲜活的民族精神和伦理生活,因而不能局限于抽象的概念分析,必须在民族伦理精神、民族伦理生活的全景及其历史进程中,进行生命倾听和生态理解。
黑格尔的“理念”给予重要的哲学启示:“伦理”的文化倾听包含不可分割两个维度,一是所谓“灵魂”,即“伦理”的话语结构;二是“肉身”,即它所表达和建构的民族精神和伦理生活。话语结构的“灵魂”是“含义”,它所建构的民族精神和伦理生活是“意义”。(17)根据伽德默尔的解释学理论,人们在解释中并不能真正把握文本原初的“含义”,而只是把握“意义”,“意义”在解释主体与文本的关系中建构。“含义”携带它的创造者的生命信息,在解读中难以触摸;“意义”是负载和继承它的主体的生命体征,在不断建构延绵中演奏余音绕梁的乐章。不过,由于它是基本话语,具有可以解释而不被解释、但又必须被解释的特质,因而归根到底,还是老子所说的那种哲学意境:“道可道,非常道”,无论“灵魂”还是“肉体”,话语结构还是民族精神,都必须“道”,但又必须洞察和把握其“非常”之“道”。
根据“概念”与“定在”、“灵魂”与“肉体”的理念,倾听“伦理”天籁的“大耳朵”,位于以下由两个结构、四个要素所构成的坐标系:知识考古与义理分析,文化选择与文化演绎;重大文化事件,重大民族节日。前二者是所谓概念或灵魂,后二者则是所谓定在或肉身。
知识考古和义理分析是概念把握的传统方法,相当意义上也是基本方法。知识考古的意义在于揭示和发现那些基本概念的生命基因、文化初心和文明本色,但很难呈现在文明进展中的生命成长和基因的同化异化。知识考古只是概念把握的一种方法,决不能过度依赖。义理分析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伽德默尔的所谓“含义”与“意义”的辨析,但需要特别注意也是可能存在的最大误区,是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概念尤其那些基本概念有不同的呈现方式。在语义哲学意义上,中西方传统就有不同的话语方式,中国是伦理句,西方是哲理句,二者体现伦理型文化和形而上学传统的不同取向。西方传统偏好并擅长概念规定及其分析,中国传统哲学倾向于义理把握。中国传统哲学对“仁”的把握,表述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18)《论语·颜渊》。“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19)《孟子·尽心下》。以西方哲学的标准,似乎孔孟对“仁”的定义不明确不严格,然而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其义理十分清晰,一旦与西方哲学对话,便体现出很高的哲学与伦理意境。樊迟问什么是人,如何做到人,孔子一言概之,“爱人”,“爱人”不仅是“仁”的概念内核,而且也是达到“仁”的康庄大道。在这个意义上,“仁”就是“人”即成为“人”并达到“人”的终极实体的根本,“人”与“仁”的合一,就是所谓“道”即“人道”。因此,对包括“伦理”在内的那些中国文化的基本概念的理解,不仅需要哲学的悟性,而且需要伦理的灵性。纵观中西方文化,有四大哲学传统,中国哲学的义理传统,德国哲学的思辨传统,英国哲学的分析传统,美国哲学的实用主义传统。必须在文明对话、文化对话的基础上,打通诸文明的基本概念,才能既把握“含义”,又理解“意义”。
难题在于,基本概念在文化史上往往由某些哲学家提出或阐发,即便成为民族传统的共同话语,不同学派对它们也有不同侧重或取向,因而必须在文明史的全景中透过文化选择和文化演绎把握,于是对重要历史典故的分析,就是义理把握的重要路径。“伦理”与“道德”是中国文化的一对基本概念,儒家与道家、《论语》与《道德经》在春秋时代同时诞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对孪生胎,就说明它们的文明染色体意义。然而在“伦理”与“道德”之间,中国文化的取向到底是什么?也许局限于经典的分析难以全面至少难以鲜活地把握,因为它只是流连于理论的象牙塔中,“相濡以沫”的历史典故,就是对伦理理念及其与道德关系的最恰当的诠释。在《庄子·大宗师》中,庄子哲学地虚拟了一个场景:“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在这个典故中,庄子所批评的是“相濡以沫”的伦理守望,提倡的是“相忘于江湖”的道德自由,认为它才是真正的“道”。然而,千百年来,中国文化一如继往称颂的却是“相濡以沫”,而庄子竭力启蒙的“相忘于江湖”早就被“相忘”。“相濡以沫”被守望,“相忘于江湖”被“相忘”,这就是中国文明的文化选择,也是中国伦理型文化的历史演绎。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中国传统中伦理处于比道德更优先的文化地位,这就是“伦理型文化”而不是“道德型文化”的逻辑与规律。同时,“相濡以沫”与“相忘于江湖”也以典故的话语形态,诠释和演绎了伦理与道德两个概念,以及现代西方哲学所讨论的伦理认同和道德自由的哲学矛盾。
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民族节日,分别从文化精英和普罗大众、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两个维度演绎和展开“伦理”,大而言之,那些基本话语的概念及其义理。重大历史事件之所以“重大”,不仅因为它们发生于历史的重大关头,而且因为它们承载了文明史的基因信息,由此不仅是重大历史事件,而且是具有生命意义的重大文化事件和重大文明事件。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文化解码,可以发现与之相关的那些基本概念中所隐藏的基因密码。对“伦理”话语来说,中西方文明史的源头发生的四个重大事件,即古希腊文明的“苏格拉底之死”,希伯来文明的“上帝之怒”,中国春秋时代的“孔子周游”“老子出关”,生动演绎了“伦理”的普遍意义及其在中西方文明中的不同风情。“苏格拉底之死”被当作古希腊文明转型的标志,然而苏格拉底为什么死?死于什么?对它的文化解码就有助于发现“伦理”的真谛。文明史的还原表明,它成为重大文明事件的根本原因,不是像一般研究中所说的那样出于对雅典城邦法律的尊重,树立了道德的基型,如果这样,它只是一个历史事件,而不是文明事件。苏格拉底之死的意义,不仅在于他因“慢神”和“教唆青年”而被判处死刑,而在于苏格拉底为什么慷慨赴死。苏格拉底反复辩护,自己没有慢神,也不是教师,由此说以这两个问题而判断苏格拉底死刑开启了一个人文的转向和人文时代,根据并不充分。苏格拉底慷慨赴死的根本原因,是他对雅典城邦的伦理认同。他解构了一种文明,又对这个文明深深认同,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伦理世界的“悲怆情愫”。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必须死,苏格拉底只能死。苏格拉底因伦理而死,为伦理而死,苏格拉底之死是人类的伦理世界的重大文明事件。希伯来文明童年的“上帝之怒”同样如此。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只是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即偷吃智慧果,就被上帝逐出伊甸园。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假设只有两种,一是上帝不仁慈,这个假设不能成立,它是亵渎神圣;于是只有第二个假设,这就是人类祖先在伊甸园犯的错实在太大了,乃至是“原罪”。何种原罪?偷吃智慧果之前的世界,是上帝、亚当、夏娃直接同一的实体性伦理世界,亚当、夏娃是上帝的创造物,亚当和夏娃之间的关系,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你是我的肉中之肉,骨中之骨”。然而一旦偷吃智慧果,启蒙了,也就沉沦了,原初的伦理实体分裂了,产生了第一次也是人类文明中最重要的“别”,即男人与女人的性之“别”,也产生了第一个“他者”,这就是作为造物主和终极实体的上帝。于是上帝发雷霆之怒,将人类的祖先逐出伊甸园,走上赎罪得救的文化长征。在这个意义上,上帝之怒,是一个重大文明事件。上帝因具有终极意义的伦理实体的被解构而怒,为伦理而怒,伦理实体的复归,也是获得拯救的终极之路。中国文化童年的“孔子周游”“老子出关”具有同样的伦理意义。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其文明镜象的要义,同样是伦理实体的解构。不同的是中国文化在童年上演的是“游”与“出”的喜剧,而西方文化上演的是“死”与“怒”的悲剧。喜剧与悲剧,演绎的都是人类童年的伦理正剧。重大文明事件,以历史正剧的方式诠释与演绎了“伦理”的概念与理念。
重大民族节日的意义,不只是所谓“民俗”。民俗是伦理的集体记忆和集体演练,是民族的自在形态,是民族精神的生活化和艺术化的表达方式,在伦理型的中国文化中,它在相当意义上就是伦理的肉身,是民族的伦理生活和伦理世界,也是“伦理”理念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形态。中国的四大民族节日,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相当意义上都是伦理的节日,它们所上演、重温和传承的都是一种伦理的集体记忆和民族精神。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民族节日,它是家国一体文明路径下独特的民族节日。春节期间,遍布世界各地的人们,不辞辛劳,不计成本,回归于自己的家庭和家乡,这是任何理性所难以诠释和理解的文化现象。有人说,中国的春节是这个星球上最为壮观的“动物大迁移”,数亿人回归家庭的人流,形成浩浩荡荡的伦理大军,年复一年地上演中国人的伦理正剧。事实上,一年一度的春节,是家庭血缘纽带、家庭伦理关系的一次检阅、重温、巩固和扩展,表达人们对家园的根深蒂固的伦理情结。可以说,中国文化之为伦理型文化、中国之为中华民族,春节以及其他重大民族节日,提供了最基本的伦理供给和伦理凝聚力。理解中国的“伦理”理念,需要读懂中国的春节,以及其他重大民族节日。当然,市场时代和全球化背景下,这些重大节日也难免被文化殖民,但正因为如此,对其伦理内核的守护,才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和文化安全意义。
由此,知识考古和义理分析,文化选择、重大文明史事件、重大民族节日,赋予“伦理”话语以“灵魂”和“肉身”,也提供倾听“伦理”的文化天籁的立体坐标。当然,倾听“伦理”天籁还有另一课题,即如何进行中国与西方的互镜对话。文明对话、文化对话是达到“伦理”理解的必由之路。基本话语是文化传统和文化生命的基因细胞,对话必须具有生命全景的意义,对于学术史上纷呈理论的任何信手拈来都可能将对话陷于偶然并导致严重误读。一种可行的策略是将黑格尔哲学尤其是其《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作为与中国“伦理”话语的对话文本。因为,其一,《精神现象学》以整个西方文明史和精神史为宏大叙事背景,是西方文明史的“精神现象”;《法哲学原理》以西方经验及其文化精神为对象,是他的“精神哲学”中“客观精神”即精神现实化自身的体系性构造。其二,这两本著作也是以伦理道德为重要研究对象的哲学经典。由此展开的与中国“伦理”话语之间的跨文化对话,相当意义上可以说是中西方两种文化传统、文化生命之间的相互诠释和相互倾听。无疑,这只是一个理论假设,关涉一些复杂的理论问题,当另文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