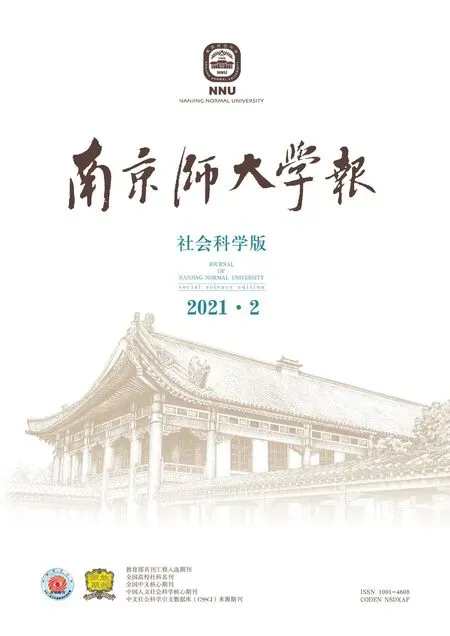制造留学神话:制度、资本与面子
2021-12-26程平源
程平源
近年来中学生到海外留学在我国已经成为潮流并引发社会关注。2014年《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显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注]人民网:《中国留学发展报告发布:我国仍是世界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2014年12月18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218/c70731-26234813.html,2019年5月8日。2019年《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显示中国高中生赴美留学热潮涌动,在赴美留学大军中数量激增,留学发展已呈现出明显的“低龄化”趋势。目前,中国高中及以下低龄留学的学生,已占出国留学生总数的35%。2007—2019年,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集中了90%以上的中国高中留学生。其中,美国是最受中国高中留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国,42%的中国留学生选择在美国就读高中,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则紧随其后。从2009年起,在美就读高中的中国留学生人数直线上升,并于2011年超过韩国成为美国高中留学生第一大生源国。[注]搜狐网:《高中及以下学生占出国留学生总数的35%》,2019年3月23日,https://www.sohu.com/a/315184002_10029775,2019年5月20日。
尽管各项数据不断揭示“海外留学成功”更多是神话而非事实,但“学渣华丽逆袭上TOP50美国名校”“牛娃考不上清华北大上世界顶尖大学”“学霸上哈耶普”式的成功案例仍然是中国家庭和学生的梦想。低龄留学潮基本是被“海外留学成功神话”所笼罩,致使多数中国家庭和学生对留学充满了乐观的想象。本文从神话理论出发,力图探究支配学生与家长选择留学行为的动力机制。
一、 留学神话:一个分析思路
低龄留学潮如何被留学神话的意识形态所驱动?英国作家毛姆说制造神话是人类的天性。……这是对平凡生活的浪漫抗议。(1)毛姆:《月亮和六便士》,徐淳刚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5页。人们乐于制造神话,把不抗重负的现实寄托在想象的美好事物之中,对近在眼前的事物则采取一种抗拒和逃避的态度。罗兰·巴特指出,神话不隐匿什么,也不炫示什么,神话只是扭曲;神话不是谎言,也不是坦承实情;它是一种改变。神话,……它借助于折衷方式来摆脱困境。(2)[法]罗兰·巴特:《神话修辞术》,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0页。法国结构主义神话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神话模拟了人类生存的结构,在模拟同时,把现实呈现为一系列的二元对立。(3)M.弗雷里奇,《列维-斯特劳斯方法的神话》,叶舒宪编选:《结构主义神话学(增订版)》,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2页。“神话以二分的方式,展示了世界和社会不断演变的组织形态,……神话中隐含的结论是,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涉及的两级:天与地、火与水、高与低、近与远、印第安人与非印第安人、同胞与外国人等等,……正是这一连串的差异推动了整个宇宙的运转”,(4)[法]列维-斯特劳斯:《猞猁的故事》,庄成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7页。松村一男认为神话的意图在于消除人类的基本困境,目的在于为解决矛盾而提供逻辑模式,这种逻辑模式在他看来就是神话思维中的二元对立结构。(5)[日]松村一男:《现代神话学与列维-斯特劳斯》,叶舒宪编选:《结构主义神话学(增订版)》,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2页。在中国留学市场上流行的留学神话同样如此,以二分的方式将中国应试教育与西方教育对立起来,塑造了一个完美的他者形象,似乎使一切陷入中国应试教育困厄的家长和学生都得到了拯救,从而化解了现实的教育困境。
从消费的立场来看,目前中国因为西方教育神话主导的留学潮其实是教育资本的冲动。教育资本在消费市场创造了关于留学的神话。卡西尔认为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符号活动,神话思维也不外乎创造符号,并在符号的基础上制造意义之网。(6)[德]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黄龙宝、周振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2页。这种符号性消费令我们产生安全感、安慰感。……事实是,我们却无法摆脱幻影重重的传媒。原因在于,我们只有个人的日常生活,而无法拥有整个世界的日常生活,换言之,我们总是不那么了解世界;(7)何林军:《波德里亚消费文化理论管窥》,《夹缝中的文化与美学》,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4页。在鲍德里亚看来,这种神话建立在个人或集体的消费心态上。这种心态最重要的体现就是人们在消费中隐藏着一种对于奇迹的期待,借以超越日常生活的平庸。“在日常生活中,消费的益处不是作为工作或生产过程的结合来体验的,而是作为奇迹。”(8)[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福、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页。罗兰·巴特揭示了广告、电影等合力共谋的现代神话,认为神话是一种集体行为、意指形式、言说方式,是将文化之物逆转为自然。(9)[法]罗兰巴特:《神话修辞术》,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布鲁斯·林肯指出神话是特定社会之中被各种力量共同创造的话语体系,“它是一种不可移易的集体产物,是经过了叙述者和听众长期的切磋琢磨而形成的。”(10)[美]布鲁斯·林肯:《死亡、战争与献祭》,晏可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中译本序言第7页。
每个神话的形成与传播都有其心理基础与文化根源,留学神话的心理基础与文化根源是中国传统的面子心理。鲁迅说“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11)鲁迅:《说“面子”》,《朝花夕拾》,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第171页。面子如何支配中国人的日常行为和选择,社会学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理论积累,自从中国人类学家胡先缙1944年将这一概念引入社会科学领域之后,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根据胡先缙传播到西方的“面子观”提出了“脸面工程”概念。戈夫曼认为,“面子”是指在特定社会交往中一个人为自己有效争取同时他人也认为其应该获得的积极性社会评价。在日常人际交往互动中,个体都在为积极性社会评价这一理想化的“自我形象”即面子而努力,戈夫曼将人们的互动比喻成“戏剧”。每个人的表演目的是给其他人制造“我们是谁”的印象,最好呈现一个理想化的自我,即称为面子的自我形象。(12)E.Goffman,Interaction Ritual: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New York:Pantheon Books,1967,p.5.这些理论视角解释了调研中观察到的现象。
二、 摆脱制度困境
随着教育资本化进程的加剧,今天中国中小学生的教育竞争和投入已经处于白炽化状态,面对当下的教育体制,大多数中国家长正无可奈何地忍受着“被压迫者的命运”。(13)程平源:《中国教育问题调查》,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1页。甘愿或不甘愿地在分数至上的指挥棒下推进着孩子的教育,为了孩子能追逐到有限的名校资源,在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家长们背负了极大的压力,焦虑、紧张抓住了他们的心,中国家长无可避免地患上了“教育恐慌症”:从没有一个时代的家长这么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也没有一个时代,几乎所有家长都开始对孩子有这么高的期待。教育的家庭投入已盛世空前,学生的学习压力、升学压力、考试淘汰制度、身心健康都成了家长在现有的教育制度内难以摆脱的困境。
《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显示,自2008年开始,我国出国留学生人数保持在20%左右的年增长速度。目前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已占全球总数的14%,位居世界第一。(14)教育中国—中国网:《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生数全球第一占14%》,2012年10月9日,http://edu.china.com.cn/liuxue/2012-10/09/content_26731337.htm,2019年5月9日。逃离中国教育,摆脱中国教育给家庭带来的一系列困扰是人们选择留学的一个重要动力。留学之所以迅速成为中国家庭摆脱教育困境的一个选项,留学神话功不可没,因为对事物的神话可以帮助人们摆脱暂时的困境。陷入教育困境的家长们在乐此不疲制造留学神话的过程中完成了对中国应试教育的反判,同时又实现了对自身家庭教育状况的救赎。于是,一系列的留学神话被制造出来。
(一) “点石成金”的神话
神话可以帮助人们摆脱现实的困境,制造“点石成金”的神话就可以宽慰陷在制度困境中的家长和孩子。一位妈妈告诉我们:
留学是我孩子的唯一出路。我的孩子成绩还行,不过有点淘,一开始我孩子跟同学关系挺好的,当时他们班主任说:“差生啊,你跟他玩,死路一条啊”我孩子怎么是差生呢?只是不擅长考试,数学难题做对了,简单的没有做对,有一次物理考了59分,有一道题目的标准答案是“量杯”,儿子的答案是“有刻度的量杯”,一个大叉……我原来是打算让他出国读本科,现在孩子初二,照现在这个样子肯定考不上什么好高中,我们决定放弃中考出去都美高,有什么办法,只有这一条路。
中国精英学生为了更强的竞争力纷纷向海外名校奋斗时,一些在应试战场中失利的学生也开始涌向海外。前途在远方,希望在远方。远方的教育能“点石成金”,“在中国战场处于劣势的孩子到了国外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他们适应了,他们开朗了,他们优秀了,他们成功上名校了”,这个神话因为很多完美例证而显得无比真实。远方的教育能让“金子”更加闪亮,一位妈妈说:
在国内我儿子班主任对我说:我儿子有点封闭没有什么朋友。结果到了加拿大,天哪,不要太能干喔,……现在他租了一个房子,分租给国内去读研的学生,大家轮流做饭。朋友也多,他交了一个国际物理竞赛得奖的朋友,两个人常常聊得可以不吃饭。他和老师也成了朋友,上课常常是老师和他探讨问题,……现在他上了名校,才进大学不久就参与一个物理课题,我儿子现在目标明确: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中国应试教育学生压力大,很多孩子小学成绩很优秀,随着竞争的加剧到初中以后成绩不理想了,家长就将原因归咎为应试教育体制,认为分数不能评定一个人优秀与否。对于那些学习习惯良好,充满创造力,在应试教育中因为偏科等原因成绩下滑的孩子来说,西式教育有可能帮助他一飞冲天。但是这只是极少数的个例,对于大多数缺少父母正确指导、溺爱、没有建立良好学习和生活习惯的学生要想通过留学就变得优秀,不啻是一个神话。
根据我们在美国调研期间对小留学生的观察,很多陷入学习困境的孩子会采取逃学、打游戏、结交朋辈、早恋等途径来释放压力。“这些都是中介教育机构刻意制造的教育神话,只专注于好的结果,而忽略了所有生活、学习的过程和细节。以为在国内有很多升学的压力,到国外这种压力就没有了,这是对国外教育的一种误识。”(15)腾讯新闻:《中国小孩没童年没快乐没自由,留学就能有吗?》,2016年8月18日,https://cul.qq.com/a/20160828/003686.htm,2019年5月10日。
(二) “至少阳光”的神话
今天的家长很在意老师对学生的态度,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他们常常会拿西方学校老师对学生的宽松、肯定和赞扬来对比,老师粗暴的批评和羞辱学生常常令家长不能接受又无法摆脱。这也成为逃离应试教育,出国留学的一个原因。一位已经把孩子送到美国读9年级的家长回忆说:
女儿和同学反复演示各种各样考验我们家长心理承受力的事情:体育课是老师带孩子们到校外锻炼,在回校的路上,老师对不听话的孩子拎起来狠狠地往地上掼,或者干脆就把那个孩子一个人丢在外面,让他自己回来。还有老师经常让大家集体羞辱某个同学,骂他是坏孩子、差生、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或者要大家去扔那个同学的文具、课本,把那个同学撵出教室……。
有些家长很欣喜地告诉我们,孩子出去以后“至少变得阳光了”。一位妈妈说:
我儿子动手能力强,但记忆力不太好,在中国很吃亏,我给他又是上辅导班,又是团课,他吃苦我也吃苦,效果还不大,家里为了儿子纠结啊,焦虑啊,吵啊,打啊,我实在觉得这日子没法过,初三就让孩子休学,一年不去学校,只上各种各样的英语班,然后送他去美国读书,儿子在那阳光得不得了,上个美国名校没问题,现在我整个放松了,我和孩子爸爸的关系也和谐多了,以前为了孩子教育,吵得都想离婚,国内的教育害死人。
根据在美国期间对小留学的观察和访谈,我们发现寄宿家庭问题、语言与文化融入问题、人际交往、情感生活、学校选课、升学等方面的问题是小留学生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和关口。处理不好这些问题,留学生就会出现难以适应美国的学习、厌学、游戏成瘾、社交缺乏、华人抱团、无法融入、抑郁等心理问题。(16)程平源:《小留学生海外生存状况调查报告》,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主编:《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80页。
不同的教育制度和学校体制不能完全二元对立。中国学生在高考面前有沉重的学习压力,并不表明海外的西式精英教育就是轻松愉快。为了逃避中国应试教育带来的问题,人们普遍有一种制造神话、维系神话的心理倾向,这种倾向具体表现在人们乐于制造一种对立的生活来满足自己的幻想,贵远贱近,把遥远、未知的事物想象得格外的神奇和美好;对熟悉的,近距离的事物则容易采取一种轻视和不屑的态度。
三、 售卖一个灿烂的前程
对于身陷制度困境的家长和学生来说,留学给人们打开了一线生机。多数中国家庭和学生对留学充满了乐观的想象,每年“学渣华丽逆袭上TOP50美国名校”的案例鼓动着留学的浪朝。具有强烈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意愿的中国家长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黎明,似乎是沉浮在汪洋大海中的孤筏有了着陆的生机。家长为孩子选择留学主要是出于“国外教育质量好不唯分数,重视孩子的全面发展。自己的孩子仅仅成绩不好,但是各方面潜质很好”“西方教育不只重视成绩,同时会考察孩子的综合素质,升学压力小,更容易上到理想的学校”“低龄出国孩子更独立,年龄越小语言接受能力越强,更能融入国外文化”的愿望。教育资本竭力完成了一个消费神话的演绎过程,像舞台剧一样,消费取代了教育的艰辛劳动,彷佛童话故事里讲述的一个乡下的穷小子魔术般地变成了王子。把教育当成一个消费领域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来理解留学神话的推动机制,自1997年以来的中国教育市场化改革,使教育行为受到市场规律行为影响,同时,资本创造了一个教育市场,从而使教育本身变成了商品,教育等同于商业,教育活动嵌入于资本运作之中。
教育资本化的后果是教育成了一种可以购买的商品,目前中国因为西方教育神话主导的留学潮其实是教育资本的冲动。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文化是符号的形式,“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教育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17)[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5页。神话思维在于创造符号并赋予符号以意义。留学是一个教育消费市场,教育资本就需要制造“留学”神话符号,以驱动中国家庭的消费。每年全美国际教育协会都会发布一份权威的留学生现状报告——《开放门户报告》(open doors reports),根据《开放门户报告》,2016—2017年国际学生通过支付学费、食宿费、生活费,对美国经济的贡献超过390亿美元。其中,中国学生贡献近三分之一,达125.5亿美元,并支持了美国超过45万个就业岗位。2017至2018年间,中国大陆学生留学美国总人数为363341人,占国际学生总数的33.2%。中国留学生给美国的贡献高达138.89亿美元。最新的美国《开放门户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学生给美国带来的经济影响高达149.13亿美元。(18)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Open Doors Reports,https://eca.state.gov/impact/open-doors-reports.
2018年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公布一组留学生对英国经济影响的数据报告,留学生对英国GDP的贡献量达到200多亿英镑。除此之外,留学生还直接支持了英国43万的工作岗位,并创造了接近83.4万个工作机会。占英国所有工作的2.8%,其中中国是最大的生源国,占国际学生总数的15%左右。(19)搜狐网:《数据:留学生为英国GDP贡献近200多亿镑,留英前景再次看涨》,https://www.sohu.com/a/216769329_125528,2018年1月15日。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美、英、加、澳大利亚开始倾销他们的教育,留学经济不只让主要留学目的国受益匪浅,留学潮带来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语言培训机构、留学中介机构、报纸、杂志纷纷辟出留学专栏,留学专业网站……这些教育资本为留学神话推波助澜,通过传播与暗示将“留学”塑造成一个“消费符号”,通过情绪感染与群体催眠,使追逐“留学”的家长群体陷入集体无意识,并驱动这些无意识的个体通过想象将自己与“留学”这个符号连接在一起。资本推动留学潮,为此创造了一些典型的教育神话。
(一) “留学要趁早”神话
“留学要趁早,早规划,早行动”堪称这个神话的标志口号。为何要趁早?更习惯,越早出去,越习惯国外教育方式;更融入,越早留学就能融入西方文化,适应当地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更独立,现在大部分的中国学生都是独生子女,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弱,早点出国留学能够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更容易进名校;更好的就业前景是市面上的留学中介为制造这个神话给出的理由。这些用词都专注在一种想象的可能,而忽略了所有生活、学习的过程和细节。这些闪闪发光的词汇诱惑着望子成龙、望子成凤的家长。而小留学生一旦孤身在海外求学,常常遭遇的是孤独、寂寞、没有归属感,缺乏慰藉等情感危机。一个小留学生回顾自己的留学生活时告诉我们:
我高中来的美国。高一,那时我才16岁。我的寄宿家庭对我都很好,但是自己要做早饭,生病也没有人照顾。真的,太小出来不是很好,生病也没有人照顾,我很想回家,有几次在超市我差点要哭出来的。有一次,我看见一个美国小女孩,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妈妈问:要不要吃这个要不要吃那个?小女孩说:不要。我想如果我妈妈在,我就要啊。我特别珍惜和爸妈在一起。不是东西好不好吃,是亲情。特别是生病的时候,以前在中国不要吃药,现在一生病就马上吃药,吃水果,吃豆子饭。我的表弟在国内读的高中,申请的都是美国顶尖的大学,我到美国久了,差点忘记其实自己就是中国学生。如果我没来美国,申请的学校会更好些,因为我根本没有了竞争意识。
在美国调研小留学生期间,我们发现文化融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美国是一个多种族跨文化共存的社会,它有一种多元文化的传统,但是对于华裔学生来说,融入这个多元的传统也是相当困难的,或者就干脆不融入。一个在加州读高一的女留学生对我们说:
在我的学校里,我的朋友就是和我一样的人,中国人。在教会学校的时候,我语言也不是很大问题,但我也不是很喜欢和美国人说话,说完了我很累,我觉得很假。你要装得很快乐。但你必须装得兴高采烈。美国人自己是真的兴高采烈,但我兴高采烈我就觉得我是在作假,我没有那样的情绪。我也不太和ABC做朋友,因为她们觉得自己是美国人,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我问过她们,她们说我是美国人。她们是美国人了我和她们说什么?我妈妈总是很奇怪说我为什么不能融入?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融入呢?
根据我们在美国期间的观察,中国留学生虽然和其他学生一起住在寄宿家庭,大学生相互合租在一起,但是很宅,生活局限在上网、打游戏、熟人之间聚会,旅游、去教会。缺少西方社会所要求的社会能力——一种热爱公众事务、集体运动、社会服务的能力。
(二) “未来世界人才”神话
留学资本在制造留学神话时,刻意打造了留学可以成为未来世界精英的神话,“要不要留学?就像有人问要不要爬山,或者问要不要走出家门。面对未来,留学毫无疑问是一种很好的扩展方式。世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整体,光了解中国,不了解世界是不行的。懂得中西方文化、中西方语言、科技、传统的人才,才是未来世界最需要的。只要有机会,年轻人都应该出国留学。”(20)新东方网站:《新东方俞敏洪:留学是中国孩子的好出路》,2014年6月23日,http://goabroad.xdf.cn/201406/10082540.html,2019年5月19日。未来的人才、搭建中美文化桥梁、为学生提供国际视野,这些词汇使“留学”闪耀着神话般的光芒,根据我们在美国对小留学生的调研,小留学生在国外的生活与学习在寄宿家庭、语言与文化融入、人际交往、学校学习等方面都会遭遇到一系列障碍,而这一切又会影响到留学生的升学,因为要申请到美国的名牌大学,除了有出色的功课表现(GPA),良好的SAT成绩外,还要有突出的课外活动,以及老师中肯的推荐信。这样一种开放式的主动性的学习方式是中国学生不熟悉的,一个面临升大学的小留学生告诉我们:
去年最低上UCLA的GPA是3.2,今年是3.1,没有一个固定的线,主要看你的其它地方强不强了。看你的personality。南加大国际生2.6、2.5都收过,本地的2.1都录取过。它是私立学校,有时4.0它也不会收,都会问很多个人的问题:你最想做的实务是什么、你最崇拜的领袖是什么,你最有名的发明是什么……
除此以外,在升学上的亚裔配额制度导致中国留学生的竞争对手仍然是华裔,目前中国学生申请美国大学的SAT分数越来越高,很多留学生甚至回国参加SAT培训班通过刷分申请美国大学,这样一来,中国学生仍然处于应试状态,不过应的是洋高考而已,后遗症就是很多高分学生到了美国大学以后退学、转学到社区大学等等问题。
中国留学生逐年增长的趋势并不是对教育本身的追求,恰恰相反是另一种的反教育,是教育资本推动的留学潮,通过追求洋学历完成更好地向上流动,这种趋势的产生内生于中国教育的制度劣势,外生于中外教育资本,是两者共同催生的产物。正如亚利桑那大学Adele Barker教授所指出,搭建中美文化桥梁、为学生提供国际视野等等不过是美国大学吸引留学生高额学费的冠冕堂皇的说辞。(21)环球网:《美国教授坦白:中国学生需要我们的学位证书》,2015年10月20日,https://lx.huanqiu.com/article/9CaKrnJQIVg?w=280,2019年5月19日。今天在教育资本所营造的媒体上,诸如“发展”“未来需要”“经济桥梁”等等已经成为拉动留学需求、制造西方教育神话的话语工具。
在消费社会中通过符号消费人们才能获得现实生活中的安宁。访谈中我们发现“留学”作为一个神话符号,让消费这一符号的家长得到了精神自慰,他们的心理充满了对奇迹的盼望,仿佛“留学”本身就是“成功”,或者进入了“成功”的大门,无论自己的孩子曾经多么让他们焦虑,多么让他们觉得失败。“留学”这个闪光的消费符号裹挟了中国家长和学生对留学的认知,导致他们没有更深地理解到中学生到海外留学所要遭遇的生活适应性困境、文化与价值冲突、中西教育制度的差异、成本投入与就业收益之间的不平衡等因素,由此导致了一系列中国学生在海外留学期间的生活学习以及未来的就业困境。这是消费社会中人们的普遍状态,正如鲍德里亚所指出的“消费尺度不是对世界认识的尺度,也不是完全无知的尺度,而是缺乏了解的尺度”。(22)[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页。这也是留学神话得以不断延续,留学潮能持续高涨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这些家长身边或多或少有留学失败的案例,但他们选择性忽略,他们依然期待奇迹,这正是符号消费者的心理特点,他们宁愿“在空洞地,大量了解符号的基础上,否定真相。”(23)[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1页。
四、 面子得到满足
美国《世界日报》在质疑中国低龄留学潮时引述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的话:“近30年来,中国的大学没有培养出优秀人才。”(24)中新网:《中国工薪家庭卖房送子女留学美媒质疑:值得吗?》,2012年6月13日,http://www.chinanews.com/lxsh/2012/06-13/3959327.shtml,2019年5月13日。该报认为类似的观点令父母即使牺牲自己,也咬牙栽培子女能在异域学习新知、开创新生活。这样一来,留学就不再是失败者的逃亡,而是迈向成功的必经之路。西方教育神话是受压迫者的自我拯救,参与这种神话的生产也是受压迫者在精神上释放自身义不容辞的责任,大家对制造神话乐此不疲换来的是一种批判的力量和一种逃亡以后胜利者的优越感。
对有些人来说,到美国留学不仅可以追求学业进步,还可以带来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一名高一的时候来的上海女生,原来在国内读国际班,她爸爸不同意她来美国读高中,因为他觉得在国内读高中更加扎实,但她妈妈想让她过来,她就过来了。而她想过来有三个理由,吃西餐方便、美国人爱运动、在上海说英语和夹英语单词的人被认为洋气。一位小留学生家长在行前请朋友吃饭的时候说,我现在虽然是总经理,但是很遗憾也只是一个初中生,虽然管了几百号人,但是还是有缺憾,这次儿子能够出去留学,我觉得特别高兴,留学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在周围人看来很有面子。西方中心论已经内化为很多中国人的崇洋媚外意识,留学在这个意义上也与中国人内在的面子观结合起来,认为留学“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在周围人看来很有面子。”国人的面子心理是留学神话的心理基础与文化根源,主导了很多人的留学选择。
在国人看来,一个人的成功不仅使个人获得成就感与满足感,更重要的是获得他人的认同与羡慕,光宗耀祖,这样才能在他人面前获得自尊感和自豪感,就是有面子。戈夫曼认为面子来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活动,一个人有没有面子,取决于其他人怎样看待他和他觉得其他人会怎样看待自己,面子只有在交往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形成,其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取决于他如何“做面子”给其他人看。(25)E.Goffman,Interaction Ritual: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p.5.项羽也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26)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缩印本,第315页。这表明中国人自身的价值体现在“做面子”给别人看,为他人为面子活着才有意义。在中国,一个人的成功不仅使个人获得成就感与满足感,更意味着整个家族获得荣耀与面子。翟学伟说:“面子在根本上是一种由于个人表现出来的形象类型而导致的能不能被他人看得起的心理和行为。”(27)翟学伟:《中国人的日常权威:关系与权力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70页。这有效地解释了中国家长和学生对留学神话的自愿服从和想象因为面子而得到了加强。
访谈中我们发现很多家长的留学意愿来自于面子,看着周围的朋友送孩子上了国外的高中,觉得自己家孩子也要上,对孩子的学习习惯、学习能力、自律能力这些对未来升学至关重要的因素反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看重的只是出国留学这件事,这件事本身满足了家长的面子和虚荣心。中国家长和孩子对中国教育劣势的切身体会和中国媒体盲目神话西方教育的优势共同助长了家长对西方教育的美好期待,从而不顾一切地在孩子留学上进行投资。与此同时,当期待落空,怕丢失面子中国家长不断掩盖真相,甚至为了挽救面子,继续鼓吹“留学神话”。因此,“留学神话”穿上面子的外衣犹如安徒生童话中皇帝穿上新衣开始在成人的世界游行。
五、 结语
留学神话主导了一场中国低龄留学潮,这种教育神话的编织主要在于西方教育制度的比较优势、中西教育资本的推动以及家长和学生对留学神话的自愿服从和想象,三方面的共同作用加强了这种趋势。留学神话掩盖了小留学生在海外遭遇的语言、文化融入、升学、就业限制等一系列的障碍。(28)程平源:《小留学生海外生存状况调查报告》,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主编:《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6》,第180页。对这个神话的祛魅,关键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回归教育本原,破除留学神话。中国家长普遍的教育恐慌症反映的是中国社会的结构性问题。目前中国社会的资源高度集中,整个社会变得紧张焦虑。压力与逃避恰恰是制造留学神话的温床,当人们对生活不堪重负之时,对现实的批判与对远方的想象就开始主导了人们的选择,然而忽略的恰恰是小留学生在海外真实的适应性问题。神话思维中的二元对立结构,把现实呈现为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在留学市场以二分的方式将中国应试教育与西方教育对立起来,塑造了一个完美的他者形象,似乎使一切陷入中国应试教育困厄的家长和学生都得到了拯救,从而化解了我们现实的教育困境。如果留学只是对中国教育和社会问题的逃避,并不能真正改变中国应试教育的现状。从对小留学生的调查和研究来看,需要改革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尊重教育规律回到教育本原,真正减轻大多数学生沉重的学业负担和竞争压力,让每个学生能各尽所能地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天赋才能,对学生进行多元的教育评价和考核,回归教育本身的目的。教育目标扭曲,就会导致留学神话盛行。
第二,启蒙家长与学生理性,破除留学神话。今日中国留学生逐年增长的趋势内生于中国教育的制度劣势,外生于中外教育资本,是两者共同催生的产物。西方教育神话主导的留学潮实际是屏蔽了对不同教育制度和社会文化的分析,单方面唱衰中国教育以此来鼓励留学,其实是教育资本的冲动。教育资本创造了一个关于留学的消费神话,在消费中人们得到一种精神慰藉。留学市场的营销策略使得大众失去批判和否定意识,在神话符号的迷惑下,人们成了放弃理性思维的“群氓”。这表明整个社会长期的思想统一被教育资本创造的留学神话裹挟,只有普遍的理性觉醒,才能期待一个多元而又充满个性的社会。
第三,唤醒家长教育责任,破除留学神话。教育改革要从家长教育开始。最需要教育的是家长。很多家长舍得在教育上投资,甚至不惜砸锅卖铁供孩子留学,但是却放弃了自己作为家长的教育责任,导致家庭教育缺失。很多家长用“孩子留学”来装点自己的面子。其实大多数留学生都有潜在的“被留学”特征。孩子留学满足了家长的面子心理。所以,破除留学神话首先要破除面子心理,个体需要从群体的承认——“能不能被他人看得起”——中解放出来,同时需要唤醒家长的教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