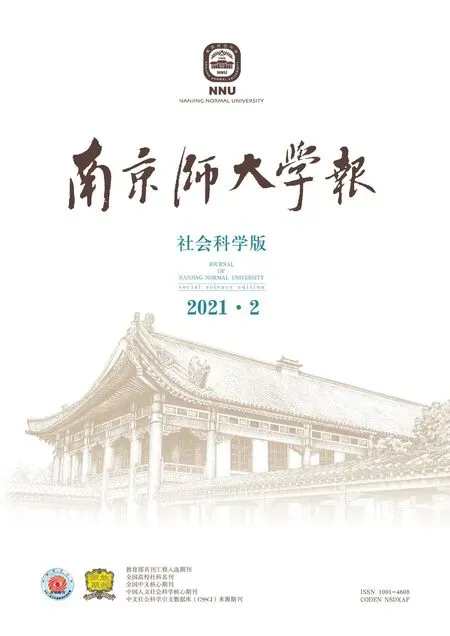异托邦与异质形象:《上海幻梦》中的他者空间
2021-12-26项静姝
项静姝
作为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一名当代本土作家,胡安·马尔塞(Juan Marsé)的作品常着眼于巴塞罗那这座颇具特色的城市,而《上海幻梦》却是他笔下一部带有东方元素的作品。这部小说面世于1993年,故事背景是20世纪40年代西班牙战后的艰苦岁月。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巴塞罗那,马尔塞却以生花妙笔为读者创设了另一座迷人的东方城市——上海。两座城市的空间嵌套,两个并行故事的相互纠缠,使小说拥有一个极为特殊的空间叙事结构。这种叙事结构,赋予这部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让我们能够通过文学的透镜,一窥人类社会生活中那些让人难以忘怀、令人心驰神往的一幕幕人间正剧,参悟社会和人生的无穷奥妙。
一、 “异托邦”的概念与小说中的异托邦空间
在《上海幻梦》中,发生在巴塞罗那和上海的两个故事是完全独立的。随着小说内在节奏的变化,作者安排主叙述者与次级叙述者,分别用娓娓动听的话语为我们呈现一系列交替叙事。镜头在两大都市间来回切换,却又不令人感到眩晕。因为,作为整部作品稳定的主线,两位叙述者在发生于巴塞罗那的故事中互动,使得叙事空间交错而并不突兀。在小说叙事的空间结构中,有一处连接上海和巴塞罗那的特殊空间,是作者巧妙地暗藏于故事之中的一扇通往另一个故事的大门。要清晰地解析小说中这一特殊的叙事空间,需要先引入“异托邦(heterotopía)”这个概念。
“异托邦”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另类空间》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福柯用它来指代一个既与乌托邦相对,又与其有着某种相似性质的空间,即一种存在于想象中,却又处于某个真实场所的,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的乌托邦。这是一种对人的社会存在状态的特殊反思,是一种在哲学和社会学意义上透视人之存在状态的独特理论视角。“很可能在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文明中,都存在着一种真实有效的场所,这些场所在社会的建构过程中逐渐形成,它们是一种反场所,是一种在真实的地点里得以实现的乌托邦。……由于这些场所与它们所反映出的,和所表达的位置都截然不同,所以作为一种与乌托邦相对的概念,我将之称为‘异托邦’”(1)M.Foucault,“Des espaces autres”,dans Empan,54,2004,p.15.。
对于这一抽象的、充满哲理且略显晦涩的阐释,福柯随后又给出了具体的例证。他以镜子为例,指出镜子的两侧恰恰可以构成一对乌托邦与异托邦的空间关系。镜子之中的世界可以被视为乌托邦空间,因为它是“没有场所的场所”(2)M.Foucault,“Des espaces autres”,p.15.。与此同时,“镜子同样是一个异托邦”,镜中的世界,与我们所站立的这一侧,即镜子真实存在的空间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返还的效果”(3)M.Foucault,“Des espaces autres”,p.15.。福柯通过镜子的例证,向我们展现了乌托邦与异托邦两个概念的关系与异同。镜中世界将我们置于一个不存在于真实世界的地点,这是它的乌托邦特性。同时,通过镜子的反射,照镜子的人通过一个虚构的场所观察到他所站立的那个真实的场所,这使得观测者所占据的地点同时成为“绝对真实的场所”与“绝对不真实的场所”(4)M.Foucault,“Des espaces autres”,p.15.。镜子的异托邦可以被视为一种基于真实场所构建的乌托邦,它强调了一种概念上的呼应关系,即通过镜子的表面,真实与非真实、现实与虚幻实现了彼此双向的连接。福柯认为,在当代社会中,存在一种新型异托邦空间——“偏离异托邦”,“人们将那些偏离了社会所要求的规范准则,或是平均标准的个体放置于该异托邦中”。(5)M.Foucault,“Des espaces autres”,pp.15-16.《上海幻梦》正是通过叙事空间的切换,为读者建构了一个具有“偏离异托邦”性质的空间,它在小说叙事的空间结构中发挥着十分奇妙而特殊的作用。小说的空间叙事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分,一是由主人公丹尼尔叙述的巴塞罗那,另一个则是由伏加特叙述的、以“金”为主人公的上海。虽然两个故事彼此独立,但小说建构了一个特殊场所,即结核病小女孩苏珊娜所居住的高塔眺台。由于这座眺台在叙事中的特殊地位,它不能被简单纳入小说刻画的巴塞罗那城市空间,而是一个专属于结核病小女孩的疗养地,一个远离所有其他巴塞罗那人的特殊地点。
正如米克·巴尔(Mieke Bal)对空间叙事的归纳,“一个空间往往成为另一个空间的对立面”(6)M.Bal,Teoría de la narrativa:una introducción a la narratología,trad.Javier Franco,Madrid:Ediciones Cátedra,1987,p.104.。高塔眺台与巴塞罗那外界空间最根本的差异,是一座城市的日常生活与一位失去自由的肺结核病人的世界的对立。在小说中,丹尼尔的朋友们曾数次窥探这间结合病人的卧室,并煞有介事地描述了它的独特和异常之处。那是一处精心挑选过的房间,它是“整座高塔光线最好,最舒适的房间”(7)J.Marsé,El embrujo de Shanghái,Barcelona:Random House Mondadori,2012,p.36.,落地玻璃窗“总是被水汽笼罩”(8)J.Marsé,El embrujo de Shanghái,p.36.J.Marsé,El embrujo de Shanghái,p.36.。此外,“在眺台的一隅,有一架醒目而夸张的大火炉,上面始终煮着一口盛满水和桉树叶的大锅”(9)J.Marsé,El embrujo de Shanghái,p.37.。借由主人公与朋友之口,眺台所有异于正常卧室的部分都被着重叙述。这种叙事,使眺台在文本中具有了异托邦的性质,因为它不再是它的本身,而是一个被异化了的空间,其所有作为偏离异托邦的“非正常性”都得以彰显。
小说对于高塔眺台的叙事,展现了福柯的异托邦空间理论对不同空间关系的阐释。福柯在《另类空间》中写道:“空间的形式表现为位置之间的关系”(10)M.Foucault,“Des espaces autres”,p.13.。爱德华·索佳在评述福柯的空间理论时,更是明确指出:“把地点和地点间的空间关系(也可以叫做地点的‘处境’)作为当代空间性的核心,这是福柯异形地志学的一个鲜明特征。”(11)[美]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01页。异托邦的性质,是由特定的场所与社会中其它所有场所之间的关系决定的。我们通过异托邦,看到它与我们所处的空间的差异性与关联性,进而得以更加清晰地审视我们自身所处的位置,也更加鲜明地意识到另一侧的空间所具有的异化属性。在主人公第一次去高塔见苏珊娜的情节里,可以看到这个空间与主人公所代表的正常世界的隔阂:“随着逐步靠近眺台,我也感受到一股桉树的香气逐渐在四周弥漫,还夹杂有一种温暖而病态的潮湿感。空气变得厚重,充斥着一种我从未在任何屋子里闻过的味道。这一切令我激动不已,却又顾虑重重。我决定要与病人的床铺谨慎地保持一段距离。”(12)J.Marsé,El embrujo de Shanghái,pp.46-47.通过对于空间环境的叙述,小说营造了这一空间的不正常氛围,将眺台这一空间从巴塞罗那的普通生活空间中剥离出来,赋予它一个“他者”的含义,并奠定了眺台这一空间偏离正常生活的异托邦特质。小说关于眺台的空间叙事,使它成为整部小说中最重要的舞台,是整个故事根基性的空间。小说采用双叙述者、双主人公的叙事安排,也使得这一异托邦空间获得了与其它空间并置的多维度的空间关系。
二、 诞生于异托邦空间的城市
在眺台空间的诸般异托邦特征中,最重要的空间存在,是诞生于其中的一个海市蜃楼般的城市,一个东方的幻梦——上海。小说叙事对于这一空间的构建,是通过上海与巴塞罗那两座城市的二元对立完成的。正如福柯所言,“异托邦有权力将众多相互间不能共存的空间和位置并置为一个真实的场所”(13)M.Foucault,“Des espaces autres”,p.17.。在小说中,眺台就具有这样的异托邦特征,上海和巴塞罗那这两个相距甚远且截然不同的世界,在苏珊娜生活的这个小世界中实现了共存,并通过叙事不断转换。眺台空间既属于巴塞罗那城,同时又是一扇通往上海的大门。小说中两个独立的故事交替叙述,作者常常会在没有交代任何叙述者交换过程的情况下,开始讲述和前一章节全然不同的另一则故事。在次级叙述者负责讲述的部分,每一节的结尾又往往会进行场景空间的转换,从上海城回到高塔的眺台,而叙述主体也随之转换到小说主人公身上。
眺台作为一个异托邦空间,让两则故事在这里次第展开。次级叙述者仅在这里讲述关于上海的故事,而此时主人公们所身处的世界,被上海这座遥不可及的城市替代了。巴塞罗那与上海两座城市在作为异托邦的眺台中重叠,其中,巴塞罗那作为真实的场所,而上海则是在这座异托邦空间中被创造出的幻想世界,这恰好符合福柯对异托邦特性所给出的第六种定义:“异托邦具有一种作用,它体现于两个极端之间。……有时正相反,异托邦创造出另一个空间,另一个真实的空间,这个空间是如此的完美,如此的细致而周密,如此的有序,而我们的空间却是无序的、混乱而缺乏管理的;这或许并非幻象型异托邦,而是补偿型异托邦。”(14)M.Foucault,“Des espaces autres”,pp.18-19.在小说中,上海这座东方城市正是这样一个被创造出来的世界,而眺台则是迈入此地的大门。巴塞罗那这个“我们的空间”,在眺台中被置于福柯所说的那面镜子前,当主人公丹尼尔在这里倾听关于金的冒险故事时,他便如站在镜前,观看镜中那个被创造出来的梦幻世界。上海在小说中与巴塞罗那呈现出了一种极端化的二元对立的状态,表现出福柯所说的补偿型异托邦的空间特征。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对于类似结核病、癌症这样的病症在文学作品中的隐喻有如下的论述:“疾病隐喻……时不时地出现在浪漫派把心与脑、冲动与理性、自然与人工、乡村与城市对立起来的奇谈阔论中”(15)[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2003年,第65-66页。。在《上海幻梦》中,结核病所引发的对立出现在巴塞罗那和上海两座城市之间,前者是主人公生活的“我们的空间”;后者则是在异托邦中创造出来的遥远而神秘的异国他乡。在主叙述者丹尼尔的故事中,小说主要以两个场所为空间叙事对象:其一是高塔的眺台,另一个是叙述者所住的街区,叙事以“瓦斯泄漏”为线索,通过主人公陪伴布莱易上尉走访的过程展现巴塞罗那街道的空间特征。故事中,主人公生活的街道常年散发着难闻的恶臭,布莱易上尉认定这源于一间小酒馆的瓦斯泄漏,然而“尽管街坊邻居们不断向加泰罗尼亚天然气公司和市政府反映,却始终无人检修”(16)J.Marsé,El embrujo de Shanghái,p.13.。人们每日不得不提心吊胆,“警惕地从人行道边绕行,以防经过酒馆大门……住户们每日进出都如同一只只受惊的耗子”(17)J.Marsé,El embrujo de Shanghái,pp.13-14.。利用一场旷日持久的瓦斯泄露事件,小说将巴塞罗那街道塑造成一个充满危机的空间。在伏加特的叙述中,身处巴塞罗那的苏珊娜陷于疾病和贫穷的双重困境,“宛如一只受伤的鸽子般卧在床上,被囚禁在一座水晶的牢笼之中,更有张牙舞爪的黑烟穷追不舍。”(18)J.Marsé,El embrujo de Shanghái,pp.74-75.
巴塞罗那城市空间的叙事过程,是以主人公在收集针对空气污染的抗议签名时,作为城市之中的步行者来完成的。米歇尔·塞托(Michel de Certeau)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讨论了这一以“城市之中的步行者”来实现的空间秩序。他将“步行”这个行为定义为一种“陈述的空间”(19)M.de Certeau,La invención de lo cotidiano,vol.1,trad.Alejandro Pescador,México:Universidad Iberoamericana,Departamento de Historia,Centro Francés de Estudios Mexicanos y Centroamericanos,1996—1999,p.110.,认为城市空间秩序是一种由可能性与禁止性所组成的集合,而步行者实现了其中的一部分。在步行者所完成的道路修辞中,城市的一部分被消解,而另一部分被夸大,城市空间被分散化、碎片化,偏离了它原本静止的秩序(20)M.de Certeau,La invención de lo cotidiano,vol.1,p.115.。角色步行的行为是小说叙事对于城市空间以何等形式展现的一种选择方式。通过步行,文本的空间叙事得以聚焦于城市特定的部分,从而组成属于作品本身的独特的城市展现方式。《上海幻梦》中的巴塞罗那城,以主人公的步行过程作为其空间的实现方式,被极其文学化地建构出来。
巴塞罗那,这座苏珊娜生活的城市,被赋予了贫穷、疾病和污染的特征。然而,小说中上海的形象完全处于巴塞罗那的对立面。在伏加特作为叙述者的部分,上海是一个实现梦想的场所。在这里,相爱的亲人得以重逢,女孩的结核病也已康复。“你在黄浦江边郁郁葱葱的林荫下,笑着漫步。你的高烧早已消退。他伸手挽着你。你是那样美丽,一枚玉簪在发间闪闪发光。你和其他优雅的中国姑娘一样,身着一件绿色的丝绸服饰。那件衣服紧贴着身体的线条,在两侧各开了一道口”(21)J.Marsé,El embrujo de Shanghái,p.105.。上海在这里被塑造成一个充满希望的空间,其中的景象与生活在巴塞罗那的苏珊娜所面对的现实一一对应。她渴望见到父亲,而在上海她将得以与父亲重逢;她久病卧床,而在上海,她却是自由的、健康的;她所居住的街区环境恶劣,而上海外滩却是郁郁葱葱。在小说中,上海不是对真实空间的摹仿或重现,而是巴塞罗那负面形象的对立折射。
尽管上海被塑造成一个摆脱了巴塞罗那现实生活中所有苦难的美好世界,然而它却也是孩子们永远无法触及的一个幻梦。小说通过对金这个人物神秘性的塑造,将这座城市置于一个与巴塞罗那相隔绝的无法抵达的场所。直到小说的结尾,苏珊娜也没有见到她的父亲。正因为上海这座城市,金这个人物可以存在于一个神秘而又充满希冀的空间里;也正因为上海,金与小说的主人公们所处的现实世界隔离开来,他只出现在次级叙述者的故事中。
金这个人物是小说的核心所在,他的人物形象与小说中的异托邦空间紧密相关,且贯穿整个故事的始终。小说中所有对金的描述都是异位的,皆出自他人之口,带着描述者的主观色彩。故事以金的神秘与未知作为开头,亦以金形象的谜题作为结尾。小说开篇借主人公和他的朋友们对坊间传闻的捕捉,为金的形象蒙上了神秘而传奇的色彩。这是一个“活在老人们压低了声线,闪烁其词地讨论中的人物”(22)J.Marsé,El embrujo de Shanghái,p.17.,这个人物“被人们随意编排、想象,却说得煞有介事”(23)J.Marsé,El embrujo de Shanghái,p.17.。这样的描述,奠定了这个人物在整部作品中的基调:一个只存在于他人想象之中的人物。在小说随后的章节中,金从未出现在以主人公为叙述者的巴塞罗那,他只作为伏特加口中冒险故事的主人公,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闯荡。随着关于上海的故事逐渐展开,金不畏强敌、勇于冒险的人物形象似乎也逐渐明朗,然而,在小说的最后一章,金的这一形象却兀然间被完全推翻。丹尼斯在眺台的突兀出现,使金的人物形象再次变得扑朔迷离。在丹尼斯的口中,金不再是那个深爱苏珊娜的爸爸,而是一个对爱情不忠的人;他也不是什么英雄,而是一个可耻的叛徒。小说的最后一章,是上海这个梦境终结的过程。丹尼斯所带来的关于金的故事,构成了小说次级叙事者伏加特所述故事的终结。随着苏珊娜的康复,眺台不再作为虚构的上海城所对应的“镜子前的空间”,它失去了异托邦的特性。
在故事的结尾,小说通过一段对主人公内心矛盾冲突的叙述,成功地将两条空间线索合而为一。在这里,主人公虽然认可了丹尼斯故事的真实性,但依旧对伏加特所描绘的那座充满冒险气息的城市抱有幻想和留恋。在主人公的脑海中,金的冒险故事依旧在上海延续:“这就像是金所经历的那个不详的夜晚,他站在码头,看着黄浦江中浑浊而污秽的滚滚江水。”(24)J.Marsé,El embrujo de Shanghái,pp.245-246.上海这座从异托邦中诞生的、幻想的城市,却深深地镌刻在主人公的心底,“比任何掠过视网膜的影像都更加有力量”(25)J.Marsé,El embrujo de Shanghái,p.246.。金与上海的故事不再需要通过眺台中次级叙述者的形式来呈现,主人公自身成为讲述者。于是,小说的两条空间线索最终在此合并。
三、 作为“东方”的上海与其异质形象
要探讨作为“东方”这一他者形象(imagen del otro)的上海,首先需要涉及“异质形象(heteroimagen)”这一形象学概念。自20世纪以来,形象学研究已逐渐被比较文学界普遍接受并得到重视。根据伊夫·谢弗勒(Yves Chevrel)的定义,这是一种对于反映外国的文化形象的研究,是比较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6)[法]伊夫·谢弗勒:《比较文学》,王炳东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6页。。胡戈·狄泽林克(Hugo Dyserinck)在谈及“自我形象(autoimagen)”与“异质形象”这组概念时,作出了以下阐释:“实际上,‘形象’与‘幻象’不仅仅是对于外来者和他们‘有差异’的文学与文化的一种反思,自我形象也可以成为这二者的客体。在这种情况下,自我形象时常通过间接的途径来实现,它需要借助于一种已有的、来自于外部的形象,即异质形象。”(27)H.Dyserinck,“Imagología Comparada”,trad.Rosa Teresa Fries,en Anuario de Literatura Comparada,6 2016,p.290.根据狄泽林克的阐释,“自我形象”与“异质形象”是一对联系紧密的概念,它们彼此对立,却又相互依存。在形象学看来,文学中的“形象”不仅仅是一种对于外来文化和异域风情的文本建构,对于“自我”的反思同样体现在这一过程中,且自我形象的实现,通常是以异质形象为参照的。
意大利文学批评家阿曼多·格尼西(Armando Gnisci)在其《比较文学导论》一书中对于“自我形象”与“异质形象”有这样的论述:“一个社群可以通过对于某一异质形象的占有和消化,将其转化为一种自我形象,或者相反,它会有意识地将自身区别于这种异质形象。”(28)A.Gnisci, Introducción a la literatura comparada,trad.Luigi Giuliani,Barcelona:Editorial Crítica,2002,p.359.巧合的是,在这段文字之后,格尼西同样给出了一则与镜子有关的例证:“对于外来的移民来说,当他们所处的新社群将他们置于一面‘镜子’之前,镜子之中依稀可见一个被扭曲了的他们自身的形象,这一形象反复地在他们内心深处投射,进而变得无法抛弃,这时,他们就可以很轻易地‘发现’他们自身的文化身份。”(29)A.Gnisci,Introducción a la literatura comparada,p.359.在格尼西看来,异质形象像是镜子中投射出的一个扭曲了的“自我形象”,当这一形象被站在镜子前的人们观察并消化,这一过程会使他们更加清楚而鲜明地认知他们自身。这种认知过程可能是对于镜中形象的接受和转化,也可能是对于镜子之中的扭曲形象的排斥,并通过这种排斥,意识到自我与“异质形象”的差异。在《上海幻梦》中,上海城这个虚构空间自始至终都作为基于眺台这个异托邦而存在的“镜子内的世界”,同时也是巴塞罗那这座城市的一个扭曲的镜中形象。
正如萨义德(Edward W.Said)所言:“东方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30)[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2页。巴塞罗那与上海空间形象的对立,是疾病与健康、孤独与团聚、禁锢与自由、无趣与冒险、污浊与清新的对比。这种对立的目的,是用关于上海的美好而充满神秘感的空间想象,来反映主人公们所在现实世界的各种困苦,并带给他们一种遥不可及,却又极富吸引力的希望。这种空间想象是一种文化上的“镜子”,通过“异质形象”(作为“他者”的东方,或者说上海)映衬“自我形象”(作为“自我”的西方,或者说巴塞罗那),而文中巴塞罗那城的故事和上海城的故事之间反复的穿插叙事,使得二者又产生了一种相互作用,即通过对“自我”认知的强化,使“他者”得到进一步的异化。萨义德指出,“东方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在大部分时间里,‘the Orient’(东方)是与‘the Occident’(西方)相对而言的,东方学的思维方式即以二者之间这一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为基础”(31)[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第3-4页。。上海的城市空间,作为一个相对于巴塞罗那(西方)的镜中东方世界,正是诞生于这种“东方学”的思维方式之中。小说中的上海,并非是作为与巴塞罗那进行对比的另一座确实存在的东方都市,而是作为一个与“自我形象”相对立的、远东文化的混合体。
小说有一段对于伏加特穿着的有趣描写:“黄昏时分,当我正准备回家时,伏加特来到了眺台里。他脚穿一双古怪的木制凉鞋,身着一件宽大的黑色袍子,上面印着花朵,和一个中国象形文字。他在背后藏着什么,冲着苏珊娜笑道:‘看,这身丝绸的和服是你的父亲送给我的。’他说着,慢慢走向床边,‘现在,笑一笑,我就把这个东西给你。’那是一张上海城市的明信片,和一把丝绸做的绿色扇子。根据伏加特的解释,明信片上的图案是风景如画的黄浦江和它众多的繁忙而多彩的码头,还有一旁的外滩,那是远东最有名的大道,那里有着无数傲人的摩天大楼和海关的古老建筑。”(32)J.Marsé,El embrujo de Shanghái,p.69.在这里,和服、木屐这些日本文化中的元素,与中国文字、上海、外滩等元素,在叙事中被不加区分地杂糅在一起。这种张冠李戴虽有明显的文化异样感,但这里的和服和木屐,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它们原本象征着日本文化的意义。它与外滩和黄浦江等上海的城市元素浑然一体,使上海成为一种带着远东异域色彩的神秘空间。在这个特殊空间中,同时混合着众多他者的符号,上海不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一座中国城市,它已经成了一个融汇众多代表东方符号的文化载体,一个属于远东的他者空间。
小说的故事发生于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实际上,这一时期的上海,正饱受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战火,经历着与巴塞罗那相似的艰难时世。尤其是1937至1941年间,上海正处在被称为“孤岛”的艰苦岁月之中,经历了粮食物资极度缺乏、货币贬值、物价急速上涨,以及继而引发的社会恐慌(33)熊月之,周武:《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413页。。在中国当代作家的笔下,这一时期的上海往往伴随着战乱与不安。如上海作家王小鹰所著小说《长街行》中,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就有着这样的描述:“盈虚坊有三分之一被炸成了废墟,最惨的是常府西院的难民收容所,除了颂经堂还留了个骨架,‘蛇弄’的耐火砖墙还屹立不倒,其余的尽是一片瓦砾。有难民抚着亲人的尸体哀哭,还有人双手扒拉着断梁碎石,一声声喊叫着亲人的名字,其情其状惨不忍睹。”(34)王小鹰:《长街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58页。同样是上海作家的王安忆在她的小说《长恨歌》中,对于40年代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城则做出了这样的描述:“这些日子,报纸上的新闻格外的多而纷乱:淮海战役拉开帷幕;黄金价格暴涨;股市大落;枪毙王孝和;沪甬线的江亚轮爆炸起火,二千六百八十五人沉冤海底;一架北平至上海的飞机坠毁……”。(35)王安忆:《长恨歌》,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第110页。
作为“我们的世界”,上海在中国作家的笔下弥漫着战争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和生活艰难。这与西班牙作家对西班牙战后时代的描述是相似的。然而,当上海这座城市作为他者的空间被审视和叙述时,它便以一种完全相反的姿态被呈现出来。《上海幻梦》整部小说的核心是巴塞罗那城,它从正经历着战后艰苦年代的巴塞罗那的视角,通过“他者空间”来呈现一个东方都市,一个与自身有着鲜明对比的“异质形象”。在小说的空间结构中,上海和巴塞罗那这两个空间并不是对等的。实际上,真正被再现的只是战后巴塞罗那的城市空间。对于上海的叙述,只是为描述生活在巴塞罗那的主人公服务的。作为巴塞罗那的一面镜子,上海是“巴塞罗那”扭曲的影子。
在这里,虽然上海被制作成一个象征东方世界的符号,但巴塞罗那却并没有笼统地化身为西方的代名词,而是作为“我们的世界”被详尽而充满真实感地叙述,进而反映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苦难和救赎。“东方不是一个思想与行动的自由主体”(36)[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第5页。,小说对两座城市的展现方式,实际上是基于巴塞罗那这个主体的。上海在小说的空间结构中,是作为客体而存在的。上海城被呈现的方式,是依赖于巴塞罗那被呈现的方式的。它自然而然地站在了重现巴塞罗那城市空间各个环节的对立面,只有巴塞罗那城被注视的那些部分,人们才会同样注视上海城中的“异质形象”。这种对于上海空间的审视是经过预设的,而这种预设又是基于对巴塞罗那城市的审视的。
在伏加特作为叙事者的部分,小说塑造了一位名为“陈静芳”的上海女性形象。这一形象被描绘成一位身着旗袍,安静而雅致的上海姑娘,“她身着一件典雅的天蓝色丝绸旗袍,高领无袖,在衣服两侧有两道开口。她一头乌黑的长发收拢在脑后,一枚玉簪从发间穿过……”(37)J.Marsé,El embrujo de Shanghái,p.139.。通过小说叙事可以看出,这位陈静芳,实际上是结核病小女孩苏珊娜这个人物在他者空间所投射出的一个“异质形象”。对陈静芳的描写,与前文伏加特描绘的那个康复后与父亲在上海团聚的苏珊娜,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两个在上海与巴塞罗那两段完全平行的故事中毫无交集的人物,小说将其形象设计和描述得如出一辙,这并不是一种巧合。陈静芳作为一位被金欣赏的女性,拥有美丽而动人的外貌,在金的冒险旅程中常伴在他身侧,这正是苏珊娜梦想中的女性角色,是这位结核病小女孩形象的一种镜中投射。小说中,小女孩苏珊娜曾试图模仿陈静芳的形象,并要求丹尼尔为自己画一幅像寄给她的父亲(38)J.Marsé,El embrujo de Shanghái,p.143.。陈静芳这一“异质形象”,与苏珊娜之间的差异是如此的鲜明,而小说却特地在二者的形象描述中使用了极为相似的文字,形成了一种形象上的隐喻。在眺台异托邦的镜子中,苏珊娜看到了那个完美的自己,尽管带着被扭曲后的异域元素,但她依旧对这一形象产生了认同,并试图模仿这个虚构的形象。“陈静芳”这一异质形象,在眺台的异托邦中,完成了与自我形象之间的转换。
小说对于上海这一他者空间的描绘并非完全虚构,上海并不是巴塞罗那纯粹的镜像。正如萨义德所言,欧洲在审视东方形象时,并非只是简单地全部凭借自身的想象来虚构出一个东方,而是“以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位置而处理、协调东方”(39)[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第2页。。
现在让我们回到小说开篇的那句话:“孩童的梦境总在大人的嘴里渐渐腐败”(40)J.Marsé,El embrujo de Shanghái,p.11.。“梦境”一词,正好点明了上海这个空间在小说中所具有的意义:它并不是一个与巴塞罗那相对等而存在着的另一座实实在在的城市,而是一个被伏加特编织出来的属于主人公丹尼尔和苏珊娜的梦境。梦境与现实相连,并基于现实而展开。上海这个异托邦空间,以经历着战后艰苦岁月的巴塞罗那城为根基,在叙事中展现出与巴塞罗那一一对应的一系列他者特征。“眺台”作为一个具有异托邦特征的特殊空间,成为了连接现实和梦境的众妙之门。小说叙事通过这一空间的过渡,使巴塞罗那的现实被遥远的东方城市所替代,疾病与痛苦被希望与冒险替代,“我们的”被“他者”所替代。眺台是一面镜子,巴塞罗那是照镜子的一方,而上海城则是镜子另一端那个虚幻的空间中映出的“我们”。
掩卷沉思,反观人生,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常常面对各种异托邦空间?文学作为现实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为我们展示出现实生活的异托邦空间,常常迫使我们不得不同时面对现实社会和心中梦想,如同罗丹的思想者那样,坐在处于生活与叙事、真实与想象、现实与希冀之间的文学之门前,陷入关于人生意义的永恒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