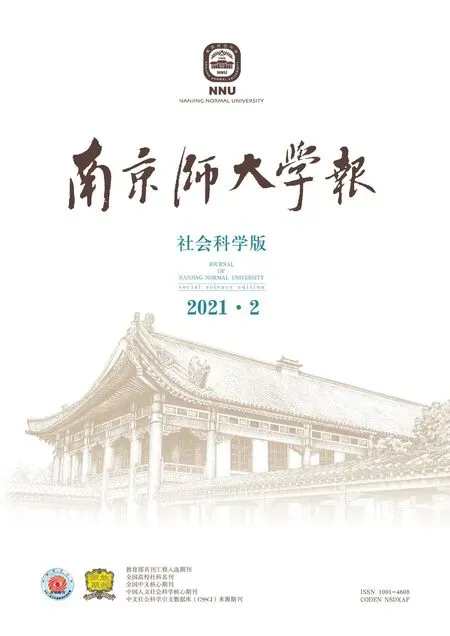中国传统书院的时间管理:制度变迁、结构功能与当代启示
2021-12-26李雨潜
李雨潜
教育时间渗透于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是学校一切教育活动得以开展和延续的基本条件,还客观、真实地制约着学校教育活动的落实与走向,形塑着学校教育的整体形态与基本结构。[注]孙孔懿:《〈教育时间学〉出版十年反思与前瞻》,《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9期。如何管理、组织与分配学校的教育时间已经成为区分传统与现代学校的重要标志,然而“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大多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我们对过去的认识,通常服务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注][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页。,因此当我们从时间视角反思学校的日常管理工作时,不仅要关注学校当前时间管理制度的基本形态,还要重视对学校时间管理制度过往历史的认识。中国传统书院自唐代开始出现,历经一千多年的发展与变革,最终在清末民初剧烈的社会变革浪潮中完成转型,实现了与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重要承接。作为我国古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教育组织形式之一,对其时间管理制度的考察不仅能丰富我们对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认识,也能为解决当代学校在时间管理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提供经验参照。
一、 中国传统书院时间管理的制度变迁
“时间”兼具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自然时间是由日夜交替、四季轮换等自然节律构成的客观存在,结构相对稳定;而社会时间是人们在交往互动过程中人为约定和建构的时间协作系统,其结构会伴随人们交往方式和权力关系的转变而转变,并表征为时间制度的变迁。(1)郑作彧:《社会的时间:形成、变迁与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5页。制度通常由正规成文规则和作为正规成文规则基础与补充的典型非成文行为准则组成。(2)[美]诺斯·道格拉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3页。本研究在挖掘历代书院正式颁布的学规、训规、章程及政府颁发的政策文本中有关书院时间管理制度规定的同时,结合历史人物传记和地方志中对书院时间管理制度的记载与评价,并参考后世学者整理、汇编的书院史资料,对中国传统书院的时间管理制度进行全面考察,主要包括书院的教学、讲会、祭祀活动时间规定,书院的学年、学期、学时设置以及书院的日常作息与假期安排等方面内容。
(一) 书院时间管理秩序形成与制度建立:唐至南宋
书院产生于唐代,由私人读书治学的民间书斋和朝廷收藏整理典籍的官方机构两种形态发展而来。(3)杜洪波:《中国书院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第33页。袁枚在《随园随笔》中指出:“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4)袁枚:《袁枚全集·随园随笔》,王英志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47页。。真正具有学校教育性质的书院是在家族书堂、私人书屋等民间书斋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5)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编:《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5-8页。有学者对全国地方志进行考据,发现在收集的资料中明确记载了教育教学活动的书院在唐代有“松洲”、“桂岩”、“东佳”、“皇寮”4所,五代时增至12所。(6)杜洪波:《中国书院史》,第21-32页。此时的书院处于萌芽阶段,数量和规模十分有限,主要依照家族传统惯例对书院进行时间管理。最具代表的是由当时江州陈氏家族书堂发展而来的“东佳书院”。在陈氏七世掌门人陈崇订立的《陈氏家法三十三条》中有对书院时间管理的明确规定:每年正月择一吉日开学,至冬月散学;童子7岁时入书屋接受启蒙教育,至15岁时择其能者入书堂继续修学。(7)陈月海:《义门陈文史考》,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6页。“书屋”和“书堂”的教学阶段划分、生徒入学和修业的年龄规定、书院开学和散学的日期选择等在“家法”的制度保障下使该书院的时间管理秩序初见雏形。
宋初新生王朝为满足文人士子被战事长期压抑的求学诉求,在增加科举考试录取名额的同时积极提倡民间私人创办书院并予以资助和支持,一批由私人创建的书院由此兴盛。此时的书院对生徒入学资格、入学年龄、修业年限等均不设限;(8)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3页。教学常在游历、用餐中随时进行,教学节奏舒缓从容;学生与师长随时切磋、问学取友、自由论辩,学术氛围自由开放,(9)丁钢、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5页。但这并不表示书院的时间管理松散无度,范仲淹就曾仿照《苏湖学规》于天圣五年(1027)掌管应天府书院时“常宿学中,训监学者,夜课诸生,读书寝食,皆立时刻”(10)脱脱等:《晏殊传》,《宋史》卷三百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60页。。尽管《苏湖学规》原文早已佚失,书院时间管理细则也无从考证,但至少证明此时的书院管理者已具备基本时间管理意识。遗憾的是,当朝廷恢复设办官学的能力后,便开始尝试重新夺回对教育的主导权,先后发动了三次兴办官学的变法运动。失去朝廷的认可与扶持,民间书院发展受阻,初步形成时间管理秩序的书院随即进入短暂停滞期。
进入南宋之后,为重振教育、发扬学术,以朱熹和张栻为首的一批理学大师开始另立书院、讲学授业,并制定章程、学规以保证书院教育实践活动的有序开展。第一个系统、完整的书院学规是南宋朱熹制订的《白鹿洞学规》,后世书院大多在其办学宗旨、教育方针的基础上针对教学、讲会和祭祀活动三方面内容制定各自书院时间管理细则,包括对书院生徒的作息规范、课程设置、考试安排,对讲会开讲日期与步骤程序的设定,以及对祭祀活动举办周期与仪式程序的规定等。如明道书院规定“每月一、六日讲史,三、八日讲经;每月分经疑、史疑、举业各考课一次”(11)吕永辉纂:《明道书院志》卷十,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刊本。;延平书院要求生徒每日“早上文公四书、早饭后类编文字、午后本经论策”(12)邓洪波编:《中国书院章程》,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1页。,并要求“每旬山长入堂会集职事生员讲授、签讲、覆讲如规,三八讲经,一六讲史,每月三课”(13)邓洪波编:《中国书院章程》,第58页。;紫阳书院将讲会分为月会和大会两种,“月会每月初八、二十三举行,巳时开讲、申时散会;大会每年九月十五朱熹生日或三月十五朱熹忌日举行,月会和大会各举行三日”,并于大会开讲前举办对圣贤先师的祭祀仪式,借榜样力量强化生徒对书院所倡学术理念的认同。(14)施璜编:《紫阳书院志》卷十八,清雍正三年(1725)刊本。
浓厚的学术氛围和规范有序的时间管理制度使南宋书院在规模和影响力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形成南宋书院独具特色的自主性与规范性兼具、学术自由与制度规范相容的教育时间结构。在书院章程和学规的保障下,南宋书院的时间管理制度得以正式建立。
(二) 书院时间管理类型分化与制度赓续:元明至清初
元代以降,书院开始被纳入官方教育体系。书院山长由朝廷命官委任,授以官衔并领取官俸,院生可由地方官员荐举,经监察机关考核通过后担任政府官吏。(15)宋濂:《选举一》,《元史》志三十一,上海:中华书局,1977年,第201页。这为书院学子打通了求学与从政的现实通道,也促使书院开始采用与官学几乎无异的时间管理办法。最具代表的如程端礼所著《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规定生徒在24岁后须用二至三年时间专心致力于习作文章,以备科举;明确提出要指导生徒“作科举文字之法”,并制定了详细的“读作举业日程”。(16)邓洪波编:《中国书院学规集成》,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169-182页。这一日程作为书院时间管理的指导方案被刊印于各地官学与书院,不仅对元代书院产生重要影响,也为后世书院承袭沿用。
元末战火弥漫、民生不安,书院多毁于战事。明初政府将教育重心放在兴办官学和提倡科举上,直至明中后期在王守仁、湛若水及其门人的带领下,书院才得以迅速发展。书院的时间管理也继南宋后进入形式更多样、特色更鲜明、制度更为完善的新时期。从形式上看,明代书院大体分为两类:一种是考课式书院,此类书院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安排主要配合科举考试要求,重日课和月考,时间管理模式与官学一致;另一种是讲会式书院,此类书院重讲学和论辩,在规范日常教学授课时间的基础上更重视对讲会活动的时间管理。如嘉靖四年(1525)九月,王守仁为绍兴书院制定讲会日程,定每月朔、望、初八、二十三开讲授业,并将这一开讲日期、具体流程及相关原则书于墙壁,告诫生徒“勿以予之去留为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虽有俗事相妨,亦须破冗一会于此”(17)王守仁撰:《王阳明全集》,吴光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94页。;讲会不仅严格按期举办,还设有十分隆重的开讲仪式。如仁文书院讲会一般于已时开始,“鸣钟五声,院赞二生导引齐入,肃仪澄虑,诣四先生神位前,唱:‘排班,班齐揖,平身’。如是揖者四,礼毕。初入会,谒者另出四拜。复导引出至仁文堂,东西分立,击鼓三声,各就班位,肃揖就坐。……过未,击鼓七声,执事者进茶饼。毕,一揖乃退”(18)岳元声编:《仁文书院志》,《中国历代书院志》卷十一,明万历中刊本。。尽管书院对生徒日常学习、讲会及祭祀活动的时间管理十分严格,但也允许生徒依规告假,如《湖南书院训规》中规定,生徒入院半年后“有父母在堂者许给假归省,若不幸有闻丧应奔,师生同往吊慰,即日放归”,还依据生徒离家远近授以十五至三十日不等的假期。(19)赵子富:《明代学校与科举制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第157页。此外书院向底层民众开放,对与会之人身份不设限制,如仁文书院规定“会讲之日,如或山林布衣,力行好修,但愿听讲,不妨与进”(20)邓洪波:《面向平民:明代书院发展的新动向》,《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其后的虞山书院向民众开放力度更大,“百姓不问远近、不论年龄,有志听讲者皆不拒”(21)邓洪波编:《中国书院学规集成》,第259页。。张弛有度、自由开放与严谨有序的时间管理使讲会式书院不断发展壮大,影响力逐渐扩散至民间各地,成为王、湛之学的宣传中心和中下层读书人讽议朝政和试图干涉政权的基地,也由此招致了朝廷的不满,在遭受三次禁毁后逐渐沉寂。
清初政局稳定后朝野上下要求兴复书院的呼声不断,于是清廷对书院的政策由抑制转变为积极兴办并加强控制,(22)王志民、黄新宪:《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制度考略》,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08页。不仅掌控书院的创办权和人事任命权,规定书院课程内容和考核标准,还制定极为严苛的惩罚制度。为激励院生刻苦读书以备科考,将院生每日学习时间细分为固定模块,如上海龙门书院“分晨起、午前、午后、灯下四节,按时定课大要。逢月之五、十,呈于师前,以请业请益”(23)赵所生、薛正兴编:《江苏书院志初稿》,《中国历代书院志(册一)》卷一,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72页。。要求“凡诸生住院者,间十日始许一出,无事亦可不出。出入必禀师长,立册注准出入晷限,及入不得逾限……违者立即出院”(24)刘兆伟、赵伟:《中国教育法制史》,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3页。,对院生“严立课程,不与以暇,坐止语默,绳以礼法,稍有逾闲,呵责立至”(25)陈尚敏:《清代甘肃进士传记资料辑录》,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1页。。
官民两种力量的博弈使书院分化为以发扬学术思想为目标的讲会式书院和以应对科举考试为目标的考课式书院。讲会式书院的时间管理模式强调学术自由、遵循教育规律,形成宽严相继、松紧有度的书院教育时间结构;而考课式书院的时间管理模式重考试、轻教学,长期的政府控制和官学化改造使书院逐渐沦为科举制度的附庸,极为严苛的时间禁令使文人士子几乎丧失思想和行动的自由,严重脱离社会现实需要,使书院失去了自身的独特性。
(三) 书院时间管理制度变革与形态重塑:清中晚期
两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打开国门,西方传教士纷至沓来,一批教会书院得以迅速建立。(26)邓洪波:《晚清书院改制的新观察》,《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5期。教会书院将西方科学知识纳入课程体系,采用西方24小时钟点时间制,引入“礼拜”“学期”等时间概念以保障其教育实践活动的稳定性与秩序化。如同治二年(1863)由美国狄考文创办的登州书院要求学生每天早八点和晚八点会集礼拜、歌诗祈祷,礼拜日下午三点赴会堂礼拜,假期除清明、端阳、中秋外增设基督圣诞假;(27)陈谷嘉、邓洪波编:《中国书院史资料》,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1998年,第2089—2102页。教会书院的时间管理模式对中国传统书院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也为中国传统书院主动学习和变革自身提供了制度参照。面对日益严峻的列强入侵态势,一些有识之士产生了彻底变革书院旧制,建立新式学堂的迫切愿望,甲午海战败于日本后更是发出“整顿书院刻不容缓”的强烈号召。(28)林增平、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上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9页。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起,朝野上下掀起了变革书院旧制的高潮,并在“经世致用”的旗帜下建立起一批新式书院。不仅在课程内容上广泛引入西学,还在书院传统时间管理制度的基础上积极融入西式学校时间管理方法。如张之洞对两湖书院、经心书院进行改革时“均照学堂办法,严立学规,改定课程”(29)朱有、王献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53页。,在组织制度上一反旧式书院习规,不设山长,仅委派提调一名、监院两名,负责书院日常行政;在学生课程及作息时间上既遵循皇帝历法又引入西方24小时钟点时间制,要求生徒“凡值心、危、毕、张、箕、壁、参、轸、元、牛、娄、鬼诸星日,九点至十点,第一班地理,第二班英文;……凡值房、虚、昂、星诸星日休沐”(30)邓洪波编:《中国书院学规集成》,第317页。,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清廷限令全国大小书院在两个月内全部改制为兼习中西学的新式学校,按省会、郡城、州县为标准将书院划为高等学、中等学和小学三层次,并颁布《京师大学堂章程》进行统一制度管理。(31)陈谷嘉、邓洪波编:《中国书院史资料》,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70页。尽管这一激进的改制政策不到百日即告失败,全国书院再度恢复旧制,但书院改制已是大势所趋。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清廷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被迫施行新政,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再次下达书院改制诏令,宣布改书院为学堂。(32)朱有、王献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第893-894页。三年后又颁发了张百熙、张之洞等拟订的《奏定学堂章程》,以钟点、星期、学期、学年等为标志的新式学校时间管理制度得以正式确立。变革中不断充斥着中西文化的碰撞和新旧思想的冲突,但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学制的颁布与施行,中国传统书院的时间管理形态最终在向新式学堂转型的过程中实现了彻底重塑,严密的新型学校教育时间结构就此建立,并开始对学校教育实践活动的走向和教育中人的行动与思想发挥新的作用。
新式学校的时间管理制度是在民族存亡危机日益深重和实用型人才急剧短缺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对西方学校时间管理制度的借鉴、模仿与融合成为清中晚期书院时间管理制度变革的重要途径。这为中国近代学校时间管理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历史基础,也是中国学校教育迈向近代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
二、 中国传统书院时间管理的结构功能
历代书院管理者、教育思想家和先进知识分子不断尝试对传统书院的时间管理制度进行创新与变革,但纵观中国传统书院时间管理制度的变迁历程能够发现,“政治时间”通过自上而下的权力干预参与了对书院人才培养目标的引导与规划;“测度时间”通过对时间单位的准确测量与精致分割实现了对书院生徒教育惯习的养成;“仪式时间”通过对特定时段的氛围塑造与程式演练完成了对书院生徒的道德教化。以下即从政治时间、测度时间和仪式时间三个方面对中国传统书院时间管理的结构功能展开讨论。
(一) “政治时间”对教育时间的干预及其目标引导功能
“政治时间”是通过对过往的反思为当下赋予正当性和进步意义的一种时间标记,借此实现对社会生活时间秩序的重构,建立连贯性的权力关系和有秩序的共同体伦理。(33)王海洲:《仪式与政治时间的更新》,《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2期。作为宣告皇权正统地位和安排臣民日常生活的重要手段——变帝号或年号、改正朔、颁新历,几乎是历代新王朝确立之初必定会开启的政治时间变革。(34)苏舆:《三代改制质文第二十三》,《春秋繁露》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85页。政治时间对传统书院教育时间结构的干预作用首先就体现在政府对纪年方式和历法体系的制度规定中。纪年和历法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向社会推行的基础性时间制度,规定和制约着社会生活的基本时间结构。(35)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3页。传统帝王纪年和阴阳历法系统将“天人感应”“君权天授”的思想观念与政治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融合,以此树立政治时间的权威,实现对传统书院教育时间结构的干预和对文人士子“忠君”、“崇圣”思想观念的引导与塑造。(36)江湄:《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无论是对帝号、年号的变更还是对岁首、月首日的重新分配,都是在传统阴阳历法体系中进行的,其实质是为宣扬“天命王权”的政治理念服务。直至清中晚期,知识分子开始以变革帝王纪年和传统阴阳历的方式对专制王权提出挑战,试图消解传统帝制时间的政治权威。尽管在变革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了科学观念与历史情感难以调和的矛盾,但在进步知识分子的努力下,更加实用的西式公元纪年法和阳历计时系统在书院改制的过程中逐渐被接受和采纳,(37)江湄:《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最终带来了传统书院教育时间结构的彻底重塑和传统教育观念及人才培养目标的近代化转向。
除直接的纪年和历法制度规定外,政治时间对书院教育时间结构的干预作用还隐藏在科举考试制度的间接引导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素有“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理想,(38)高晶:《中国传统文化通论》,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1—219页。政府通过设立科举考试制度为古代知识分子打通了求学与从政的现实通道,(39)钱建状:《举业无妨于道学——南宋的理学、书院与科举》,《科举学论丛》2017年第2期。因此,尽管中国传统书院崇尚修身养志,反对沉溺举业,却始终无法真正脱离与科举制的关联。隐藏于科举考试制度中的政治时间要素不断嵌入传统书院的教育时间结构中,间接传递了政府的教育价值主张和对人才培养目标的设定。
因此不论是通过纪年、历法的直接规定还是借助科举考试的制度引导,都彰显着政治时间对书院教育时间结构自上而下的权力干涉与制约,传递出政府对书院人才培养目标的设计与定位。
(二) “测度时间”对教育时间的分割及其惯习养成功能
“测度时间”是基于计时工具对时间单位的测量,使人们的日常生活能够依据独立于个人或地区的某种时间单位进行安排,形成可以普遍遵守的、不受物理时空限制的时间参照系统。(40)郑作彧:《社会的时间:形成、变迁与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8页。计时工具本身并不能构筑出时间秩序,而是借计时工具使社会形成广泛而统一的时间参照标准,以此促成规律性集体行动的发生,指向的是一种关系的建构与规约。
中国书院创设之初往往以天体运行和自然节律等物候现象作为安排日常教育生活的时间参照标准(如“日出”、“午后”、“日落”等)。(41)赵所生、薛正兴编:《江苏书院志初稿》,《中国历代书院志(册一)》卷一,第72页。这种时间参照标准与季节、气候、地理环境等自然因素关联紧密,强调对经验的遵守和对自然节律的服从,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稳定性,使早期书院形成简单、粗放的时间管理模式和较为缓慢的教育时间节奏。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各种计时工具(如日晷、水漏、沙漏等)和照明工具(如蜡烛、油灯等)的使用使书院在时间管理上逐渐克服自然条件的制约,获得更加精准度量和细致分割时间的能力。(42)华同旭:《中国漏刻》,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25页。特别是西方机械钟表的传入和普及,对书院教育时间结构的转型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钟表将时间划分为均等而精细的时、分、秒单位,创造出一种抽象而客观的测度时间系统,并且这一抽象、客观的时间标准由特定时间测定机构决定,不受自然节律和政府力量制约,具有跨时空的稳定性与普遍适用性。(43)徐文璘、李文光:《谈清代的鐘表制造》,《文物》,1959年第2期。
以日晷、水漏、沙漏等计时工具为标准的传统测度时间系统体现的是一种为维护当前状态而依靠实践积累和遵循自然规则向“过去”寻求经验的循环时间观。在循环时间观的指导下,一切对书院教育实践活动的时间管理目标最终都指向为维护专制王权统治服务。而以钟点时间为标准的测度时间系统则体现出一种为突破当前状态而依靠理性设计和严密规划向“未来”提出挑战的线性时间观。计划性和目的性成为评判时间管理制度优劣的标准,速度、效率、成果成为衡量学生能力高低的依据。这在很大程度上为书院时间管理制度的变革提供了观念和技术支持,在晚清维新运动的浪潮下,伴随书院的改制和新式学校的建立,时间的钟点化管理逐渐普及开来,学校的一切活动都开始受到钟点时间的规约。可以说新式学校教育时间秩序和权威的获得正是得益于这种对时间的细致分割和精准掌控。
从这一结果来看,尽管不同测度时间系统对教育时间结构的分割方式与划分标准不同,其目的都是为了促成学生规律性集体行动的发生,指向的都是在日常教育实践活动中关系的建构和惯习的养成。
(三) “仪式时间”对教育时间的塑造及其道德教化功能
“仪式时间”是将某些固定时刻从日常生活时间中抽离出来,通过反复的程式演练塑造神圣和令人敬畏的气氛,传递某种符号象征意义的过程。(44)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第206页。符号本身并不能独立传达意义,只有体现于具体的时刻、情景氛围和仪式过程中才会被生动而形象地建构与解读。(45)[美]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4页。
由于抽象的“道”在古代社会占据了核心地位,学校教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传道教育,而中国传统书院作为传道教育的重要场所,如何利用同一时间内的仪式重演和强烈的仪式化氛围实现对书院学子的道德教化是其时间管理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严朔望之仪,谨晨昏之令”是对传统书院学子的基本仪式要求。(46)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第204页。“朔望之仪”是指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日向圣贤先师行祭拜礼仪。祭拜时一般由年长者带领生徒按主次长幼顺序进行排位并依次向圣贤先师行三跪九叩之礼,祭拜过程中喧哗者或迟到者均要受罚。整个仪式程序繁琐、复杂,气氛严肃、庄重,以此向学子传递书院的学术理念和道德追求;(47)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第204页。“晨昏之令”是指书院生徒每日早晚向授课老师行问候礼仪。一般由生徒中的年长者提早抵达书院,间隔固定时间敲击木板,提示全体生徒在三次敲击后必须到齐,如遇特殊情况需禀明缘由,否则罚跪。生徒集体向当日授课老师作揖问安后方能入座读书,每天散学时也需重复同样的仪式程序,以此强化生徒对儒学道统的认可,传递尊师崇贤和尚礼重道的思想观念。
传统书院的仪式时间在晚清时期遭到了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教会书院首次将宗教祈祷仪式引入书院的日常教育实践活动中,要求生徒每日早晚集体歌诗祈祷,每周日还要赴会堂进行礼拜。尽管教会书院对宗教祈祷仪式的程序设计与传统书院的朔望之仪、晨昏之礼不同,其本质依然是通过对固定仪式的反复演练,塑造神圣、庄严的仪式氛围,实现对书院生徒的身体控制和对宗教思想的宣传。
不论是传统书院复杂、严格而庄重的朔望之仪、晨昏之令,还是转型过程中教会书院的宗教祈祷仪式,都是通过营造特殊仪式氛围将仪式时间与庸常生活时间进行区分以维持书院的基本教育秩序,并通过对复杂仪式的重复演练和意义赋予实现对书院生徒的道德教化。
三、 对当代学校时间管理的启示
延绵千年之久的书院办学历史在清末“变书院为学堂”的制度变革中走向终结,书院时间管理制度的变革与重塑也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但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之一,书院留下的时间管理经验和传递的时间管理理念对当代学校的时间管理制度建设仍然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当代学校在时间管理上不仅同样面临来自政治时间、测度时间和仪式时间的干预、分割与塑造,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教育内在需求的转变还在不断被提出新的要求。具体而言,当代学校在时间管理中应回归育人本位,增加学校时间管理的弹性空间;遵循教育规律,加强学校时间管理的制度理性;重视文化建设,丰富学校仪式时间的意义构成。
(一) 回归育人本位,增加学校时间管理的弹性空间
“时间就是权力,谁控制了时间体系、时间象征和对时间的解释,谁就控制了社会生活”(48)王海洲:《仪式与政治时间的更新》,《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2期。,不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学校教育时间的安排与分配总是受到国家和政府的严密控制。中国古代政府通过将政治时间嵌入传统书院的教育时间结构实现对书院人才培养目标的引导与控制,而当前政府部门在学校的时间管理中不仅扮演“顶层设计者”角色,为学校制定纲领性时间规划,如在《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中对学校发展提出宏观时间要求,也深入参与学校时间管理制度的实施过程和最终结果的评价中,身兼学校时间管理制度的制定者、监督者和评价者等多重身份。具体体现在对学制体系的设置和对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安排上,落实于学校的课程表、作息时间表、校历等时间制度规定中。然而学校教育的对象是作为个体的学生,整齐划一的时间要求未必能够兼顾不同学校之间的现实差异,也难以满足不同特质学生的个性需求。此外,与中国传统书院在科举考试制度的间接引导下将政治时间引入书院教育时间的方式十分相似,当代学校在应试考试的压力下也试图建立一种与考试要求相匹配的时间管理制度来实现其培养、甄别和选拔人才的目的,履行国家对学校的基本职能要求。但以考试选拔标准为依据、以结果为导向的时间管理制度容易使学生将增加分数和提高排名视作接受学校教育的唯一目的,违背学校教育的初衷。
学校教育的真正目的在于人性的完善和人的全面发展,“育人”是学校教育的本位。正如黑格尔所说:“社会和国家的目的在于使一切人类的潜能以及一切个人的能力在一切方面和一切方向都可以得到发展和表现”(49)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9页。。只有将学生作为“目的”而非“工具”看待,才能真正体现学校教育的育人价值。这就要求学校不仅要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争取更多时间管理的自主空间,还要尊重学生个体间差异,重视学生的生理时间特性,去除以牺牲学生健康为代价的将学生工具化的时间管理要求,增加学校时间管理的弹性空间,由此才能使学校时间管理制度焕发蓬勃生命力。
(二) 遵循教育规律,加强学校时间管理的制度理性
学校的教育时间与社会及时代发展关系密切。自中国向世界敞开国门,从悠闲的农耕时代跨入快节奏的工业时代以来,学校便不断调整和更新时间管理方案,努力适应工业时代的社会节奏。在科学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不断提高的物质生产效率和不断加快的信息交换速度使学校面临愈加承重的时间压力。于是,更加精细的时间分割和节奏掌控成为当代学校时间管理的关键,学校的一切活动不仅被放置在钟点时间的框架中,还被要求在相同时间内完成比以往更多的任务或延长对学生的教育时间。然而对“速度”的狂热崇拜和对“效率”的盲目追求极易掩盖对学生个体的关注,忽视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使学校沦为与中国古代官学化书院相似的“考试培训基地”,造成学校教育时间节奏的无止尽加速和学校教育目标的异化。
在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的当下,学校更应保持客观冷静态度,加强时间管理的制度理性。不论是政府部门对学校发展制定的宏观时间规划,还是学校为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而制定的具体时间规定,都应遵循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满足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
(三) 重视文化建设,丰富学校仪式时间的意义构成
政治时间和测度时间作为学校组织和安排教育活动的基本时间框架,因其制度合法性和强制性特征对学校的整体教育形态发挥着直接影响。仪式时间则是对学校“日常”生活时间的抽离,通过意义的赋予和氛围的塑造建构出一个有秩序的文化共享时空,在潜移默化中将学校倡导的教育理念和价值追求传递给学生。(50)王海洲:《仪式与政治时间的更新》,《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2期。当代学校的仪式活动形式多样,包括巩固民族国家合法性地位的升国旗仪式,宣传党政思想意识形态的入团、入党仪式,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节日庆典,象征学生阶段性成长意义的入学、毕业典礼,以及彰显不同学校文化特色的各种活动等。这些仪式和活动不仅寄托着社会对学校教育的期待与认可,也承载着人们对国家统一、政通人和、民族兴盛的美好期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新的文化和思想不断创新和丰富着学校仪式时间的结构与内容,也一定程度造成了学生对传统文化和符号意义的理解的缺失,使学校的仪式时间沦为重复、空洞的程式操练时间。学校仪式时间的意义不仅在于传承和怀旧,也在于创新和引领,只有重视学校的文化建设,丰富学校仪式时间的意义构成,将更多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符号行为注入学校的仪式时间中,强化对符号意义的解释,才能提高学生在仪式时间中的感受度与参与度,使学生对仪式时间中传递的教育价值理念产生共鸣和认同,发挥学校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