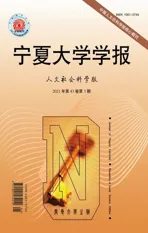庄子的“逍遥空间”与山水画
——宗白华、徐复观对庄子与山水画关系的读解
2021-12-25吴咏絮
吴咏絮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300071)
中国现代美学生发和逐渐形成于西方文化“新源”对传统文化强烈而持续的冲击之下,20世纪中期宗白华、徐复观以保存与发展国族文化、重振国民精神人格为旨要的诸子哲学与文艺研究,借用西方美学理论、使用更为精密的现代语言对所发掘之传统精神资源进行重新阐释,辨明和宣扬了传统文艺中凝结的国族之精魂。他们以敏锐的眼光注意到庄子对中国文艺极重要而特别的作用,并以“逍遥游”为中心,揭示了庄子哲学对作为中国文人艺术代表形式之一的山水画的深远影响。宗白华、徐复观对庄子、山水画及二者关系的读解,皆能深入作为个体生命的“庄子”其人之生存境遇与精神世界,揭示其“道—艺”会通的壮伟心灵所构造的“逍遥空间”与山水画这一空间艺术在精神质素、审美趋向、核心技法等层面千丝万缕的关联,由是凸显了庄子哲学的艺术意味(美)与山水画的深层含蕴(真)。《庄子》文本本身的多义性和宗、徐两位学者在气质学养、研究方法、审美方式等方面的异同,则使他们对庄子逍遥“空间”与山水画之关系的具体读解也互有异同。此间产生的互生互释、互相补充的丰富内容,为具有根本性的“中国艺术精神”之文艺命题的建构和“道—艺”会通之现代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话语体系、可能的诠释思路和精妙的研究范本。
一 “空间”中的逍遥
20世纪中国学者对国族传统精神资源的整理与研究,受时代背景与文化思潮影响,具有保存与发展国族文化、重振国民精神人格的鲜明指向。一方面,在西方文化之“新源”的冲击下,回到作为国族思想之起点与基石、充满活力而含蕴丰厚的先秦哲学研究,在对先秦诸子的重新阐释中确证其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是为国族文化保存与发展的题中之意;另一方面,就国民精神人格之重振而言,又要求研究者从传统精神资源中发掘能够参与全新国民理想人格之塑成、提升国民精神境界的内容。宗白华、徐复观的庄子研究,是在战乱频仍、社会生活急剧变动时期,研究者以强烈的共鸣透过庄子的文辞把握他更本质的艺术心灵,体认一个立体而鲜活的生命在“天下沉浊”的生存世界中,凭借体“道”的人格境界开辟具有超越性、无限性的“逍遥空间”,进而肯认这心灵与“逍遥空间”对现时代国民的精神、生活的影响。这同时标志着研究方法的更新和对庄子认知的深入,也为探索庄子与山水画这一空间艺术的关系、构拟“道—艺”会通的传统文化体系做了准备。
宗白华在《我和诗》中提到,他由青岛转学进上海同济读书后,相继研习过庄子与近代德国康德、叔本华、歌德的哲学思想,这些哲人在他的“精神人格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痕”[1]。由此文和1919年11月12日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的《读伯格森“创化论”杂感》,可以看到宗白华哲学研究、文艺活动和对宇宙自然的游赏、观想间紧密的联系。对他而言,欣赏诗歌能引起“一股宇宙的遥远的相思的哀感”[2],诗歌创作表达着“听到永恒的深秘节奏,静寂的神明体会宇宙静寂的和声”的哲思[3],“图画美术是一种直接表示宇宙意想的器具”[4];庄子等哲学家则需要诗人的天资,哲学也可以是“宇宙诗”“宇宙图画”,是“用文字概念写出宇宙意想”[5]。这种将哲学视为宇宙意识与诗性想象之综合的独特理解,和康德、斯宾格勒等西哲关于时空之探讨的影响,使他在讨论老庄之“道”时,也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方式:并非对文本进行概念性的归纳、分析以层层推演出“道”的内涵,而是运用“时空意识”“空间境界”一类语词和具有直觉、想象意味的“散步”式的美学散文来表述他们对“道”的体认。写于1959年的《道家与古代时空意识》一文中,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宗白华将是否参与生产实践视为宇宙意识之形成的决定因素,以具有“积极性、创造性、现实性”的“时空统一体”和静观冥想、倾向于“空间”意识区别了儒家《周易》与老庄思想[6];认为老庄同是从室内空间的观察中悟到宇宙的“常”,把“虚空”提高到形上之“道”、万物根源的地位;又以思想境界的一“游”一“守”和“虚空”观念的一“大”一“小”作老庄哲学的分野。他说:“《庄子》书里最喜欢拿‘游’字来表达他的思想境界。他的‘内篇’第一篇就名为《逍遥游》。他遨游于‘大而无垠’的空间”[7]。其后宗白华又写有《中国古代的音乐寓言与音乐思想》一文,在引用《庄子》中《天地》《天运》两篇说明庄子的音乐思想时,他部分修正了上文的观点,进一步区分了老庄对“道”的体认及其时空意识:“老庄谈道,意境不同……他(老子)对音乐不感兴趣。庄子却爱逍遥游。他要游于无穷,寓于无境。他的意境是广漠无边的大空间。在这大空间里作逍遥游是空间和时间的合一。而能够传达这个境界的正是他所描写的,在洞庭之野所展开的咸池之乐”[8]。宗白华认为中国特有的“时空统一体”之宇宙意识的发现,源于注重礼乐生活与农事活动的儒家哲学。他在《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哪里去?》《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等文中指出,人于天地间观照万物“生长流动,具有节奏与和谐”,由是感受到空间中时间的推移和动力的因素,体验“宇宙间生生不已的节奏”“天地创造性的旋律”,自己的生活也融化在这节奏与旋律中[9];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周易》说“天地缊,万物化醇”,是这种时空意识最为典型的表现[10]。当他基于这一认知而以儒衡道,便容易发觉老庄哲学对现世生活的“超离”及其导致的对岁时迁次之参与感、融合感的缺乏,故在《道家与古代时空意识》中说,老庄较为倾向“空间”意识与静观冥想。然而老子面对这宇宙的“超离”,乃是“高超严冷”的观照,他由一静闭的空间抽绎出与自然、与美无涉的形而上的宇宙之本;“活泼”的庄子却走出了老子所坐守的安静闭塞、一成不变的狭小屋舍,审视广阔无尽的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把他的精神生命体合于自然的旋律”[11]。他要在深闳而肆、无限广大的空间中作永无止境的遨游;他的空间于是由本身的伸展不止、流动不息和精神生命在其中活跃飞动的虚空之“游”,引入了“动”的质素。他的超越是精神生命“逍遥”于自然空间中,进而如宗白华在《形上学——中西哲学之比较》中所说,“由天地之大美,以达于道!泛神境”!庄子在天地大美中感受到万物有灵的泛神境界,万物在他的虚空中得以显现各自的生命活力,而“空间与生命打通,亦即与时间打通矣”;故其“逍遥游”正表示着《周易》“正位凝命”“革故鼎新”外,使空间“意象化,表情化,结构化,音乐化”的另一种时空合一的宇宙意识[12]。宗白华认为“咸池之乐”能够传达庄子在广漠无边而与时间合一的空间中作“逍遥游”的体道境界,这音乐以壮伟浪漫的精神奏出时间中仿佛永恒流动的变化无方而浑合自然的旋律,而使人同时发生“荡荡默默”的情绪活动与“充满天地,包裹六极”的空间感觉,确足以象征庄子的精神生命在空间中的“逍遥”。
庄子本人对他所体认的“道”,用着一种诗性的图像化的言说方式,他对体道之人及其“逍遥”境界的描述,常伴随着一个个具有鲜明形相乃至色彩的空间的展开;这空间和其中的意象是现实存在与审美想象的交融,表示着他最鲜活的精神世界和最深切的生命体验。此为宗白华之解读方式得以成立的依据。而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中,也明确提出要在《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外采取另一种解读方式以究求前书未尽之意,他说:“当庄子从观念上去描述他之所谓道,而我们也只从观念上去加以把握时,这道便是思辨的形而上的性格。但当庄子把它当作人生的体验而加以陈述,我们应对于这种人生体验而得到了悟时,这便是彻头彻尾的艺术精神”[13]。由“人生体验”以解悟庄子之“道”,实亦为宗白华把握庄子之“道”的方式。不过,宗白华对这种体验的描述,更强调个人精神向外部的宇宙自然之观察、体合、扩展,而能形成供精神生命游赏活动的场域;徐复观则依持以心性之学“为中国之学术文化之核心所在”的理念[14],将不毁万物的“虚空”直指为能“涵容万有”之虚静心体的隐喻。他认为“逍遥游”是由道落实下来的人之精神充量的自由解放的象征,而“无用”与“和”是达成这种自由解放的基本条件,即一方面以无用为用,摆脱个人成见和欲望桎梏,达到“心斋”“坐忘”“无己”“丧我”境界,使主体恢复“虚静”的本性;另一方面是忘我物化,打破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限隔,使人达到“一种圆满具足,而又与宇宙相通感、相调和的状态”[15]。进而借康德、胡塞尔、李普斯等西哲的学说,以说明虚而待物的主体在心物相接时,对此一物所作的乃是“以纯粹意识为其活动之场”的纯知觉活动,这不期然而然的便是美的观照,是“洞察物之内部,而直观其本质,并使其向无限中飞越”[16]。在这种美的观照中,人通过最大想象力的活动由对象的外部形相看出“使其形”的新的、本质的形象,所谓“意味的表象”“美的表象”;体验到天地之大美和与天地万物相通的大情、天乐。徐复观对庄子“体道”人格的把握,实是从主体精神的角度切入而说到人对宇宙的涵摄与审美活动,这显然与宗白华“以大宇宙间自然境界为美感范围”的空间中的“逍遥”是相类相通的[17]。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虚静的自身,是超时空而一无限隔的存在;故当其与物相接,也是超时空而一无限隔的相接”[18],但当庄子将老子从虚空之“无”中悟出的“道”落实于主体精神时,他也采用了“虚室”“天府”等空间词以为比譬;徐复观更顺承此类表示空间的语词,将虚静之心表述为“社会、自然、大往大来”“仁义道德可以自由出入”[19]的“虚灵之地”[20],即一能够涵摄万物的“精神的空间”。而对现实世界之多苦多难的痛切感受,使他在讨论庄子的“逍遥游”时,又特别强调了为道家“精神的空间”所涵容的客观世界“实在只合是自然世界”[21];并引《逍遥游》《山木》等文本指出,庄子面对天下沉浊的生存境遇“实有超越现世而宁愿寄情于‘广漠之野’的倾向,所以作为他的自由神像的‘神人’,只有住在‘藐姑射之山’的上面”;他实际上也“过着与大自然相融合的生活”[22]。徐复观虽未如宗白华一样,直说出庄子的体“道”境界乃精神生命在“空间”中逍遥遨游的活动姿态,然将“逍遥游”寄托于“广漠之野”与“藐姑射之山”,即是说人只有在“广漠之野”与“藐姑射之山”所表象的精神化的“自然空间”或自然化的“精神空间”中,才能体验到精神充量自由解放的逍遥之境。这种精神与自然两相冥合的理想空间,正是他在庄子心灵中体认到的“逍遥空间”。人的生命在此“逍遥空间”中的安顿,乃是精神疲惫不堪者在变动不居、多苦多难的世界中寻求到的一种艺术性的解脱之道;这也成为徐复观为庄子与山水画关系之解读把握到的真正基点。
二 山水画:从“逍遥空间”到空间艺术
宗白华《艺术学》认为欧洲的山水画可以分为客观的山水画(intern Landscape)和人格化的山水画(Heroic Landscape),而“中国山水画即属于人格化的”[23]。徐复观也说:“完全成熟以后的文学艺术,是直接从作者的人格、性情中流露出来的。文艺的纯化与深化的程度,决定于作者人格、性情的纯化与深化的程度”[24]。他们对中国山水画的研究,皆未停留在就艺术而论艺术,而是意图在整个传统文化体系之内,阐明哲学思想、艺术成就、人格心灵乃至文化精神间千丝万缕的关联。即此不仅能使中国的哲学、艺术及其现代意义交相显发于人前;且单在山水画之发展历史、精神内涵、审美质素与艺术技法等方面,其把握也更为精密、准确而深刻。在这种“道—艺”会通之现代研究中,就庄子与山水画之关系的读解而言,宗白华和徐复观正是以庄子的“逍遥空间”为基点,探讨其在画面上的实现,从而勾连出庄子哲学对山水画这一空间艺术所发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如上文所说,宗白华认为哲学和图画皆可以表现人对于宇宙的时空意识和诗性想象,高明的哲学既然可以是“宇宙诗”“宇宙图画”,则伟大的艺术亦可被视为关于宇宙的哲思。他在《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中指出,中国人以宇宙深处为“无形无色的虚空”[25],画家在纸面空间上创造的画境,正是其宇宙意想的具象化。虚空和物象是同时随其笔下点线而呈现的、这画境中二而一的组成要素。画底不仅是空白,而是灵气往来,生命流动的虚灵空间;画中所绘不仅是姿态万千的物形,而更要把捉它们生动的气韵、生命的活力。就纸面空间而言,这是运用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多次提到的“虚实相生”、虚空处传神的审美原则,造成空间与物象一片浑溶、气韵生动之美感。就其中含藏的一层最深的意义、境界而言,则是表示出了那作为万象源泉、万动根本的形而上的“道”。文中宗白华虽同时引老庄的“虚无”与儒家的“天”以说明“画底”所表示的虚空,但这是就中国人共有之宇宙意识而言;当落实到山水画这一层面时,则如他在《徐悲鸿与中国绘画》中所说,“中国古代画家,多为耽嗜老庄思想之高人逸士,彼等忘情世俗,于静中观万物之理趣”[26],“静观”的、作为知识分子的创作者受老庄“空间”意识之影响显较儒家更为深刻。
上所举两篇文章都发表于1932年。在1959年完成的《道家与古代时空意识》一文中,宗白华进一步认识到老庄空间境界一“游”一“守”、一“大”一“小”之别,并说:“中国许多画家的空间意识也表现着这个境界。明朝画家周臣的杰作《北溟图》辉煌地写出了庄生逍遥游里的‘北溟’”,认为中国山水画的精神境界究以庄子之“遨游于‘大而无垠’的空间”为其主源[27]。又不仅是纸面的空间境界,艺术创造者在这空间中典型的精神活动和他们在空间中构造的山水所具之独特美感,也与庄子的“逍遥空间”紧密相关。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宗白华引大画家恽南田及石涛语云:
恽南田《题洁庵图》说:“谛视斯境,一草一树、一丘一壑,皆洁庵(指唐洁庵)灵想之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其意象在六合之表,荣落在四时之外。将以尻轮神马,御泠风以游无穷。真所谓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尘垢秕糠,绰约冰雪。时俗龌龊,又何能知洁庵游心之所在哉!”画家诗人“游心之所在”,就是他独辟的灵境,创造的意象,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中心之中心[28]。
艺术家要在作品里把握到天地境界!德国诗人诺瓦理斯(Novalis)说:“混沌的眼,透过秩序的网幕,闪闪地发光”。石涛也说:“在于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艺术要刊落一切表皮,呈显物的晶莹真境[29]。
画家因心造境,其人多涵泳深味于庄子哲学,故以画中山水表出一片“独辟的灵境”,实是《庄子》中表象着其“逍遥空间”的神人居所。画家游心于其间,乃于画面空间中体验庄子“游心于物之初”,精神在虚空中的逍遥游观。庄子缘天地之美而达于道,其体“道”境界是万物有灵的“泛神境”,画家则要以其笔墨尺幅上有秩序、合规律的艺术创造,使这虚空中的万物焕发晶莹之美。这“晶莹”并非肉眼上的明亮通透,而是在艺术心灵的静观中,万象刊落了纷繁芜杂的外部形象——“光明莹洁,而各得其所,呈现着它们各自的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这自得的、自由的各个生命在静默里吐露光辉”[30]——其生命内部的活泼鲜洁方得以显现。宗白华对这艺术之“真境”的探索,更推进到他所崇尚的晋人之美处;他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指出,这种在中国艺术上具有根本性的美感或美的理想,是在汉末魏晋六朝时期奠定了其根基与趋向:
中国伟大的山水画的意境,已包具于晋人对自然美的发现中了!……晋人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乃能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晋人的美的理想,很可以注意的,是显著的追慕着光明鲜洁,晶莹发亮的意象。……庄子的理想人格“藐姑射神人,绰约若处子,肌肤若冰雪”,不是这晋人的美的意象的源泉么[31]?
《中国古代的音乐寓言与音乐思想》中也说:“庄子的理想人物:藐姑射神人,绰约若处子,肌肤若冰雪,也体现在元朝倪云林的山水竹石里面”[32]。在山水画的起步处,成为其最高、最终之美的理想而对画家审美意识起决定作用的,即是表征着庄子之“逍遥”人格的姑射神人;这精神生命之美的表象,也在山水画艺术发展的顶峰和艺术成就的最高代表之一——倪瓒的山水树石中再度被表现出来。换言之,在宗白华看来,庄子的“逍遥空间”和在此中“逍遥”遨游的精神人格之美,是深而又深地全然化入山水画这一空间艺术的意境之中了。
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也以大量篇幅论述了魏晋六朝时人面向自然的审美活动和山水艺术的发展,及庄子与山水画的关联。相较于宗白华的“散步”方法和将中国与西方、哲学与艺术、不同学说与艺术门类融会贯通的研究路向,徐复观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待艺术的发生和演变,用“追体验”的方法对思想学说与艺术实践在精神意境上的关联加以体会、表诠。他认为中国的山水画是“在长期专制政治的压迫,及一般士大夫的利欲熏心的现实之下,想超越社会,向自然中去,以获得精神的自由,保持精神的纯洁,回复生命的疲困而成立的”[33]。儒、道、禅学虽然都曾对中国文人精神及艺术创造发生极大的影响,但儒学的意境,是超越人欲烦扰夹杂,达到与道为一、“精神‘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大自由、大解放”[34],这是夹带责任感的仁义之乐;由儒家之思想系统所导出的艺术精神,其最高境界是孔门乐教所要求的美与善、美与仁的统一,即“乐和同”之音乐境界与“仁”的道德境界得到自然而然之汇通、统一的无限艺术境界;其目的与结果是个人之道德理性人格的完善和社会风俗的和谐。禅学的意境,则是由庄学的意境再向上一关,不仅要从世俗、成见、私欲中求解脱,还要从生命中求解脱,达到与客观世界相接时“本来无一物”“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虚空”之境;这种精神境界中不能起美的意识,更不能产生绘画,以禅论画的黄庭坚、董其昌等士大夫乃是“禅其名而庄其实”[35]。只有由老庄之思想系统所导出的以“虚静”为内容的“纯艺术精神”,其意境是超越个人的成见私欲,更对道德人生加以摆脱而归向人间以外的自然世界,能够作为中国山水画成立的精神根据。这种精神的开出,又是始于老子而到庄子才发展得十分显著,且庄子在后世文人精神上发生的影响亦较老子更“近于本色”[36],故徐复观直以山水画为“庄学的‘独生子’”[37]“庄子精神不期然而然的产品”[38]。他认为在庄子的思想中初不曾有成就某种人生的念愿,更不曾有艺术的意欲乃至落实为某种艺术创造的追求。然由他显出的典型,实是“中国人的心灵里所潜伏的与生俱来的艺术精神”;故而到经学陵替、老庄思想抬头的魏晋时期,这种“纯艺术精神”便因玄学之盛行而“在文化中有普遍的自觉”,且“赋予很早便已存在的艺术作品以独立的价值,并有意识地推动当时的纯艺术活动”[39]。
具体地说,本由老庄演变而来的魏晋玄学,经过了从正始名士之“思辨的玄学”,到竹林名士之“性情的玄学”,再到元康名士之“生活情调的玄学”三个阶段[40]。自竹林玄学始,《庄子》代替《老子》《周易》成为主要的思想成分,玄学亦逐渐由形上的思辨向生活和艺术上落实;竹林名士即“由玄心而过着旷达的生活,一方面是不拘小节而依然守住人道的大防;一方面,他们寄情于竹林及琴、锻、诗、笛等艺术之中,使其玄心有所寄托”[41]。随玄学思潮的演化,庄子之艺术精神向魏晋人士生活上的渗透,也在人伦识鉴中启发了人对自身形相之美的自觉。这种以发现个人之本质为关键的活动,从政治实用性的道德判断转向艺术欣赏性的审美判断,“在玄学、实际是在庄学精神启发之下,要由一个人的形以把握到人的神;也即是要由人的第一自然的形相,以发现出人的第二自然的形相,因而成就人的艺术形相之美”[42],把握住具有本质意味的“美的表象”。这种美的自觉延展到绘画上,遂使当时的人物画也为表现出这种本质之美,走到通过“形”以传其“神”的方向上去,作为纯艺术活动之绘画因而得以成立。在人与自然融合的活动中,这种艺术精神的渗透则启发人打破与自然间的主客体之对立、限隔,进入“以玄对山水”的“物化”境界,从而发现和主动追寻自然山水之美;并且感到较之具体的人或人间世,在深远、广大、纯净的自然空间中方能完全安顿自己的生命,求得精神的“逍遥”。徐复观指出:“以玄对山水,即是以超越于世俗之上的虚静之心对山水;此时的山水,乃能以其纯净之姿,进入虚静之心的里面,而与人的生命融为一体,因而人与自然,由相化而相忘;这便在第一自然中呈现出第二自然,而成为美的对象”[43]。如上文所说,“藐姑射之山”所表象的精神与自然两相冥合的“逍遥空间”及人的精神生命在此“逍遥空间”中的安顿,乃是徐复观为庄子与山水画关系之读解找到的真正基点;他认为只有在“广漠之野”与“藐姑射之山”所表象的精神与自然两相冥合的理想空间中,才能体验到精神充量的自由解放。由庄子艺术精神启发的玄学名士之艺术生活,实未能完全摆脱与人间世的纠葛;传“神”的人物画,亦不能使主体的整个生命融入和安顿于对象之中。只有“未受人间污染,而其形象深远嵯峨”的山水能怡然理顺地进入心中虚灵之地[44];以虚静之心与山水之姿的两相冥合,成就一与“藐姑射之山”相类通的全新的“逍遥空间”,使人在其中得到精神充量的自由解放,而庄子的艺术精神始得到自然而然的着落。山水画的兴起,则是进一步要求将人所把握到的精神、所洞察到的真山真水呈现于画幅之上,实现由“逍遥空间”到空间艺术的转换。故徐复观对于这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加以解释说:“庄子的逍遥游,只能寄托于可望而不可即的‘藐姑射之山’;而宗炳则将当下寄托于现世的名山胜水,并把它消纳于自己绘画之中,……他们(宗炳、王微)的画,乃是他们所追求的玄学的具象化,所追求的庄学之道的具象化”[45]。魏晋六朝时期的宗炳、王微,在生活实践上真能超越人间世而陶醉于山水之中,乃是与庄学之意境相契会的画者。他们的“澄怀观道”,正是以“玄”的心灵、亦即庄学精神观照和融入自然山水,在其有限形质中发觉通向无限的、超越性的“神”;进而创造性地将其神形相融的“第二自然”用绘画加以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徐复观认为庄子所游心的“物之初”乃是“以自己虚静之心所照射出的物的虚静的本性”[46],人在此处方能得到精神的自由解放。则于其“逍遥空间”中呈现出原有之姿的自然山水亦必以“虚静”为内容,并在向空间艺术转换时随之成为山水画固有的精神内蕴,此即徐复观所说庄子精神反映在艺术作品方面一定会表现出“纯素”的性格之美[47]。这种性格之美,一方面使山水画在审美观念上形成了“逸格”或“平淡天真”之最高标准;另一方面,则要求这一艺术形式在达到“直接从作者的人格、性情中流露出来”的成熟之域时,能通过画幅空间上自然山水之色彩、形相,将这种“纯素”之美作全般的表现;因而对山水画的技法发展与创作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三 “逍遥空间”的艺术创构与“三远”法
前述宗白华和徐复观的庄子美学对其体“道”境界及与山水画关系的读解,揭示了庄子精神与自然相融合的“逍遥空间”和山水画这一表写自然大物的空间艺术在意境上的紧密关联。这种意境上的关联若就艺术品的创作与接受而言,则成为画面上“逍遥空间”的艺术创构问题;宗、徐两位学者对庄子与山水画关系的探讨,遂更具体推进于艺术语言及艺术技法的运用上,并特别注意到郭熙《林泉高致》中提出的“三远”法在“道—艺”汇通之艺术境界的完成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他们由庄子的“逍遥空间”这一基点出发,将他在自然与精神相冥合之理想空间中的“逍遥游”的精神活动与视觉感官在画幅空间上的推移、延伸及由此产生的联想和想象活动相纽结,为山水画的文本解读分别提供了“目推神游”与“形远神见”的审美范式,赋予“三远”法全新的哲学含蕴;也由此进一步肯定了山水画对人的精神的安顿作用及其表征的文化精神,而对西方绘画的空间表现提出了批评。
金浪在《从动静文明论到文化形上学——1930—1940年代宗白华营构中国艺术意境的方法论转移》中,揭示了宗白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写就的一系列有关中西绘画比较的文章背后,对于“中国艺术意境”之营构工作从“对作为‘动静融合’的‘气韵生动’的阐发,再到以时空范畴来置换动静范畴,围绕‘趋向音乐’与‘空间感形’来论说中西画法差异,到最终在中西形上学比较中以‘时间率领空间’来概括中国人的宇宙观特质”的方法论转移[48]。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顺此文从历时性角度梳理这些“看似重复”的工作而发掘出一条“营构艺术意境”之演进线索的思路,重新考察宗白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于中西绘画的阐释,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宗白华对于中国画之空间境界的认知的进展,其背后实以更为具体的艺术文本之考察工作为坚实基础。这一时期他对中国画的独特质性的思考,步步推进而最终完成了“艺术语言—艺术技法—空间表现—艺术境界”的析分与整合。在上文所引写于1932年的《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徐悲鸿与中国绘画》两文中,宗白华对中国古代画家受老庄思想影响至为深刻有所认识、其所绘花鸟山水画之空间意识亦源自老庄之宇宙意想的事实予以揭示,并指出不以科学之透视法刻画三维空间的立体物象,而以笔墨表现出远眺中云烟山景之神态意境为中西画的根本不同。在后文的“附言”处,宗白华还提到了中国画虽无凹凸阴影,然所写之画境仍有深、空、明暗、阴阳、远近之空间感觉,然未及引申和发挥。1934年10月发表于《文艺丛刊》第一卷第二期的《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中,他一是将中国画的艺术语言,由较为抽象的、中国性的笔墨置换为能与西画之色块相对照的世界性的线条,指出中国画是解衣盘礴的画家以飞动的线纹描摹宇宙,形成点线交流的律动的形象,使空间及其中万物浑然一体而“结成全幅流动的虚灵的节奏”。二是提出“三远”法这一山水画的核心技法,以解读为“在时间中移动徘徊”的“游目周览”之透视方法,放到与西画透视法相对照的层面上来。由这种艺术语言及技法形成的山水画,遂能造成画面之趋向音乐、融合时空的“空间感形”。三是把山水画所写之“神态意境”,非立体而有宇宙空间之深远感觉的画境,明确阐发为“一片神游的意境”——这一表述明显地来自庄子的《逍遥游》[49]。在1935年的演讲《中国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中,他一方面引恽南田语将供“神游”之空间表述为“灵”的空间,同时以“空间”置换了“气韵生动”,说“那无穷的空间和充塞这空间的生命(道),是绘画的真正对象和境界”;另一方面由山水审美中的视觉活动与心灵感悟对透视法作更为详尽的阐述,将对待客观世界“纵身大化,与物推移”的态度和盘桓、流连的空间观视、“由远至近,回返自心”的空间感觉勾连起来[50],赋予“以大观小”“三远”等艺术技法浓厚的哲学意味。随着这些艺术文本之考察工作的进展,到20世纪40年代末,宗白华终于在确立艺术意境之营构方法的同时,把山水画的艺术语言、艺术技法、空间表现、艺术境界以层层升进的方式组织、结构起来。于1949年3月写就的《中国诗画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中,提出了完整的解读方法。他引清代画论家华琳对“三远”法的论述,认为“推之法”为“远之神”呈现的关键,山水画这种“力线律动所构的空间境”具有“由动的节奏引起我们跃入空间感觉”的特质[51]。中国书画的笔墨,讲求以指腕力量的灵活运用表现出点线的圆转活脱与飞动之“势”,艺术家调动肌肉的生理节奏,在现实空间中作兔起鹘落的肢体游动;他创造的线纹逐渐显现于纸面空间的俯仰姿态,遂以活跃飞动的节奏,引起人的视觉活动;随着目光在画幅空间上的推移,人的精神亦于不知不觉间“跃入”了由“三远”法所构造之审美空间中。这一审美空间,亦即那“一片神游的意境”,正是庄子所游之“逍遥空间”在画幅空间上的幻现。值得注意的是,宗白华虽在此文中引《周易》及老庄共同说明中国人以之为一“虚灵的时空合一体”的宇宙意想,又糅合《周易》的仰观俯察和庄子的逍遥游观而形成对宇宙自然及画幅空间的观照法,但他始终认为山水画家的空间境界是以庄子为其主源;或者即可说,画家以“三远”法创构于画幅空间上的,正是庄子所游的“逍遥空间”。从上所举《道家与古代时空意识》(1959年)及《中国古代的音乐寓言与音乐思想》(1961年)两文可知,他从以“倾向于‘空间’意识”分判老庄与《周易》,到庄子对“咸池之乐”的描述中确认其“大空间”中的“逍遥游”是既区别于老子,也区别于《周易》的另一种时空合一的空间境界,乃最终完成了对庄子之宇宙观的体认;亦使庄子的空间境界与山水画境达到完全的契合。则宗白华对山水画及其与庄子之关系的思考,亦当反为他解读庄子哲学提供了养分。
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的“自叙”中则明确表示,在对“庄子的再发现”中,他的研究路径是由画史、画论、画作而“追到魏晋玄学,追到庄子上面去”,从山水画的艺术风格与美学境界中体悟到玄学、庄学精神的流演;又以“动的观点”“发展的观点”从大量材料中清理出一条由庄学、玄学到山水画的线索[52]。他以人在精神超越上的不同诉求分判儒释道,认定要由人间世而归向自然的庄学意境是山水画得以成立的精神根据。庄学精神经魏晋玄学的转换即生活化、艺术化地落实于自然山水及山水画幅空间上;而完全成熟后的山水画,乃是与“与庄子的精神相通”的伟大艺术家的人格境界及其独特的美在画幅空间上达到全般的流露、呈现[53]。这样,山水画所使用的特殊艺术语言、艺术技法及空间表现的生成便具有了必然性;“逍遥空间”的艺术创构则成为一个不断突破艺术语言与艺术技法的障壁,以求表现出山水具有本质意味的“美的表象”,使庄子之道、使其艺术精神能落实、具象化于画幅空间之上的演进过程。如果说宗白华对“逍遥空间”之艺术创构,是从共时层面上组织起由语言到意境的解读范式;则徐复观对“逍遥空间”之艺术创构的解读,正要从历时层面上把这一过程和山水画的发展史完全结合起来。在这一解读方式上,山水画走向成熟的唐宋时期的艺术语言与艺术技法的发展和变革,遂成为“逍遥空间”之艺术创构的关键。
自然山水的艺术形象之表出,是基于形体的构造。徐复观引《历代名画记》中“始于吴,成于二李”之说指出,在山水画的艺术语言上,唐代吴道子“如莼菜条”之笔法较以往“匀细如蚕丝的线条”[54],始足以表现山石之量感、力感,乃是对传统技巧上的解放;李思训以青碧金绿入画而开皴染之先河,能表现山水之量块及其阴阳向背。这是山水形体的完成。然而就山水画的发展历程而言,在形体的完成之外,尚有与庄、玄精神相契合的伟大艺术家,要求在画幅空间上将此种精神意境加以表现。宗白华与徐复观在这一处,虽都把握到艺术家乃在画幅空间上表现其游心于庄子的“逍遥空间”,然宗白华所默识深契的乃是庄子虚空之“游”的活跃飞动及所游之宇宙空间的无限深广、虚灵动荡;徐复观却紧扣住“远”之一字,他的关注点着落于人的精神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由所寄情之理想空间对人间世的远离带来的“安放”感觉。“远”于凡近的“虚旷放达之场”,对于庄子而言是他由壮伟的体道精神与诗意灵魂构造出的姑射仙山、广漠之野,在魏晋以来却在人对自然山水的“远望”中落实于那玄远纯净、深远嵯峨的山水空间之上。这种空间上的“远”,遂被徐复观认定为能够表出庄、玄之境的、自然山水具有本质意味的“美的表象”。于是艺术家在画幅上所表示的自然与精神相冥合的审美空间,在山水画的起步处便特以“远”的表出为其最核心的问题。由此“艺术意欲”而发生的艺术技法与空间表现上的重要变革,正是水墨画和“三远”法的出现:前者使山水画至此而能在色彩上真正表出目见的远处山水之色及与庄子“逍遥空间”的纯素玄淡之美的元素契合的“神”;后者使山水画至此而能在形象上真正表出远处山水的“势”及与庄子“逍遥空间”的深远无限之美的元素契合的“神”。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第八章第八节“形与灵的统一——远的自觉”中指出,“三远”法之“远”代替了“灵”的观念;在人的视觉与想象的统一中,山水形质延伸而通向更远处的虚无,形成“与宇宙相通相感的一片化机”,人的心灵于是在这画幅空间上“随视线之远而导向无限之中,在无限中达成了人类所要求于艺术的精神自由解放的最高使命”[55]。这种由山水空间之“远”体认庄学意境的“形远神见”的审美范式,同时也说明了山水画与西方绘画迥异的“留白”之空间表现。遂在宗白华之外,由对庄子哲学的现代阐释而为山水画的读解开出另一种可能的诠释思路。
四 余论
宗白华和徐复观对“道—艺”会通之传统文化体系的重新阐释,同样强调了主客交融的中国哲学与艺术中给予人内心世界之安顿的力量。宗白华在《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中批判了西方以科学“控制无限空间的欲望”[56],及其14世纪以来传统画境由几何学与透视法造成的“可怖的空幻”“苦闷的象征”之空间表现和随之而来的向无边的锥形空间彷徨驰求之空虚感觉[57],而在中国的山水画中发现了使“向往无穷的心”能“有所安顿,归返自我,成一回旋的节奏”的审美空间[58]。徐复观则在《毕加索的时代》《再论毕加索》等文章中,批判了产生于主客对立之文化精神下的西方现代绘画,顺承“两次世界大战及西班牙内战的残酷、混乱、孤危、绝望的精神状态”表现出的主体通过对客体的扭曲、破坏与变态构造审美空间的艺术风格,认为中国的山水画以主客和谐交融构造的空间境界能够解决现代社会中的人“由过度紧张而来的精神病患”[59]。他们对庄子与山水画的读解,既是构建“中国艺术精神”之文化思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同时具有应对由现代文化所引发的精神危机的鲜明现实指向;在对中国哲学与艺术的客观评估、定位及世界文化未来走向的展望中,表现出充分的文化自信,也为以中国文化精神为底色的现代美学建设提供了精妙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