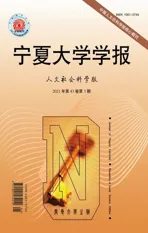论钱锺书“意内言外”诗学批评理念之构建
2021-12-25万明泊
万明泊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100872)
在钱锺书诸多著述中,语言问题一直是他关注的焦点。但此前囿于钱锺书片言只语的批评范式,相关的讨论常常既乏厚度,又少深度,未能从材料本身中梳理出一条理论脉络。比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只是标举出“哲学家文人对语言之不信任”[1]问题,却没有梳理要点;在《管锥编》中,他也对语言问题做过总结,将其分成“粘着欠灵活”和“暧昧不清明”两类,指出存有“曲解而滋误解”[2]的问题。
然而,钱锺书为何会对语言问题有如此多的关注?这同他一贯的批评主张又有什么关系?同时,就“言外之意”本身而言,亦有两种情况值得我们讨论:一种蕴藉深远,需要读者细读文本,反复考虑作品中的语句,挖掘其背后的指涉与暗示;另一种寄托遥深,读者不能单凭文本就妄下判断,须借助其他材料来斟酌比对,才能看出言在于此、意在于彼的意涵,如此交互往复,方使其意义圆足。所以,面对这样的两种情况,钱锺书会作何判断,并形成何种批评理念?
对于上述问题,《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以下简称《札记》)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新的理解路径。《札记》作为钱锺书的读书笔记,带有极强的私人属性。随处勾抹的文字样式,直率随意的语言表达,都印证着这一特质。同时,该书时间跨度较长,包含着不少此前未曾发表的看法,宏富精审,胜义纷披,鲜明地勾勒出钱锺书文学观念上的变与不变。研读分析这一新近出版的著作,能够明显感到它与钱氏其他著作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因为书中的不少内容正是《管锥编》学术思想的重要来源。
本文拟借助《札记》中的相关材料,对前文提及的语言问题进行溯源,探讨钱锺书的诗学批评路径,考辨其方法的构建过程,挖掘他独到的诗学批评理念,并在此基础上,联系陈寅恪的“诗史互证”法,对两位学术大家的治学路径做一对比,以此来观照二人在路径取向上的不同。
一 构建的起点:从“尊本文”处出发的批评主张
纵观整部《札记》,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不少内容是《管锥编》的源头所在,其论述也更为直接细致。我们通过对这些内容的比较分析,恰可以窥见钱锺书独特的批评理念。比如,同样是论述《诗·狡童》的表达意涵,《管锥编》和《札记》就呈现出了不尽相同的风貌。《管锥编》中的钱锺书旁采诸说,分析了汉儒“权臣擅命”说同朱熹“淫女见绝”说的差异,最终采信了朱熹的说法。他给出的理由是:“窃以朱说尊本文而不外骛,谨严似胜汉人旧解”[3]。更进一步说,他认为对文意的理解应建立于对文本的尊重上,而非舍近求远,以某种臆断来评判作品,由此来强行攀附、胡乱影射。苏珊·桑塔格说:“一个人在没有隐喻的情况下是无法思考的,但这并不等同于不存在一些我们宁愿避而不用、试图抛掷的隐喻”[4]。忽视文本内涵,只追求对隐喻的开掘,往往会导致对作品的过度解读。
而在《札记》中,钱锺书的论说则更进一步,对如何防止过度解读问题的产生、如何把握言外之意的内涵,提出了“意内言外”的批评方法。需要指明的是,此处“意内言外”并非常州派论词之说。论词的那一方面,《管锥编》论《诗·关雎》一则下已有考辨[5],是故本文不再赘述。而他在阐释系统内构建“意内言外”的批评方法,则是将“意内”与“言外”两者视作某种递进关系。《札记》中有段详尽的论述:“意内言外者,言外之意即顺言内之意而申之,即谓之‘言内包蕴’可也。非另标名色、自开户牖,取了不相属之事物,附会而强说为影射也。诗者,言之不可代、无所待者,意即寓言,象亦自征,谓之‘象征’(icon,unconsummated symbol)是也。非如说理致用之文,许读者得意忘言、登岸舍筏,且但登彼岸,不泥何筏,外指倘明,他词可易。王辅嗣《易略例·明象篇》所谓‘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则只是符号(sign)而已。前者譬之山水画,自成位置,不必按画检真;各具意匠,不容以此代彼。后者譬之地理图,须得山川道里之实始中,苟能得实,则彼图犹此图也。《说卦》云乾为马,亦为木果;坤为牛,亦为布、釜。盖意在乾者不言马而言木果,意在坤者不言牛而言布、釜,无所不可。然而《车攻》之‘马鸣萧萧’,《无羊》之‘牛耳湿湿’,易之曰‘鸡喈喈’‘狐绥绥’,通篇情景必随以更换焉”[6]。如此细致且周密的论述,在《札记》中实属罕见。因《札记》读书笔记式的特性,文中许多论述往往是不耻支离、点到即止。钱氏能在此洋洋洒洒,挥笔写就如此多的文字,足见他对这个话题的兴趣与看重。并且经笔者查阅后发现,这段论述在钱锺书其他著作中并未得见,此前也没有学者做过讨论,也足见该内容的独特性与讨论价值。
在整段论述的开篇,钱锺书便点出了阐释作品时还是应当从作品本身出发,言外之意也该顺着文本内部的意思去推求,不应过度发挥,以政治化和主观化的解读来统摄一切。这一观点,也映衬出他一贯的批评主张。如他在年少时提出的“当因文以知世,不宜因世以求文”[7],批评那种将文学只当作对时代反映的观点;他在编选《宋诗选注》时,也立场鲜明地提出了“六不选”原则,把那些只可算作押韵文件的诗歌排除在外。我们从这样的一番选择中可以看出,他并不认同将文学作品划归成只是反映历史与社会的文献,文学自有文学性价值在。而钱锺书将《诗经》的读解回归到普遍的文艺鉴赏,从“尊本文”处出发,则是跳出了传统经学批评的框架,把握诗之所以为诗的艺术魅力,将其复归到诗文鉴赏的路数中去。
然而,将《诗经》的读解复归为诗文鉴赏的路数后,则又势必会引发新一轮的问题。因为《诗经》之所以能够占据这样高的地位,绝不仅仅是因为其文学特性,更多的也是来自对其政教伦理性的体认。如果将这一面彻底抛开,《诗经》的经典意味定会失色不少。所以,钱锺书从文学本位的角度剖解《诗经》时,也没有忽视其作为政教经典的历史意义,积极承认历史传统所赋予的读解价值。如他分析《诗·采葛》一篇时,虽不认可毛《传》的解读方式——将情侣慕思曲解为朝士疑惧,然而赏其“于世道人事,犂然有当”[8],故又兼而采之。伽达默尔曾将“理解”归纳成“一种效果历史事件”[9],指出阐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可以说,任何一种文学经典的形成,不只是依托其本身的艺术价值,更是由历史潮流、时代风气等多种因素层累堆积而成,任何一种文本的读解与阐释都逃不掉所谓效果历史的影子。当阐释者在分析作品时,又不应把这一系列背景因素抽成真空。所以钱氏此番行为,粗看之下颇自相矛盾,似在阐发政教的经学传统与以诗解诗的文本分析间骑墙,实则二者内里相连,骑驿相通。其目的在于拆散经典中被后设的光环,以平视的眼光,还其本来面目。在方法上表现为打通中西间的文艺理论,促使经典研究走出宋代以来的经学阐释传统,让经典回归文学之本位。也在这样一种游走与跳脱之间,重塑了“尊本文”的价值与意涵。
反过来,钱锺书也并不认为那些号称赋予重大社会意义的作品就必然具备很高的文学价值。在他眼中,那些打着寄托遥深、关系重大旗号的作品,内里往往不堪,带着些芜词庸响、语意不贯的腔调。若论者只将这类旗号视作精华,则是“不屑眉睫之间而上穷碧落、下及黄泉,以冀弋获”[10]。这是历史的考据,而非谈艺之当务。以钱锺书所处的时代环境看,他能在举世滔滔中坚守这份态度,殊为难能可贵。将作品的文献价值同文学价值区别开来,发掘作品内在之美感,这是钱锺书的谈艺标准之所在。同时,钱锺书也曾对“虚伪”与“诚实”二词做过细腻的考辨。他指出,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常能遭遇虚而非伪、诚而不实的境况,语言的诚伪与虚实常“相连而不相等,一而二焉”[11]。艺术上的造境与物象上的虚实并不等同。故而以钱锺书的评判标准看来,那些寻行数墨、锱铢以求的考据行为,都只能称得上是“以不可执为可稽,又不思之过焉”[12]。这种评判标准的厘定,也塑造了钱锺书独特的阅读关注与批评方法的戛戛独造。
二 内里的形塑:由现象学所主导的阐释路径
钱锺书说:“我一贯的兴趣是所谓‘现象学’”[13]。那么,我们该从何理解他所谓的现象学(Ph·nomenologie)?这又与钱锺书一贯的批评主张有什么关系?
首先,从钱锺书个人表述与治学历程来看,他所谓的现象学概念或更接近于海德格尔的定义。据笔者统计,在《札记》中的第四十三则、第四十六则、第六十四则、第二百五十三则、第二百七十八则、第六百六十八则、第七百零三则、第七百零七则、第七百三十八则和第七百五十六则等多处均对海德格尔理论有所称引。可见,钱锺书对海德格尔关注不少,对其思想观念青眼甚多。而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现象学历经了一个由先验现象学到存在论现象学的转变。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被遗忘了,以致存在及其意义的问题便乏人问津。他的任务就是要将人们从对存在的遗忘中唤醒,从而对存在者的存在加以探寻与关注。所以,在海德格尔眼中的现象学为:“关于这些对象所要讨论的一切都必须以直接展示和直接指示的方式加以描述。‘描述性的现象学’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个用语其实是同语反复……凡是如存在者就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展示存在者,我们都称之为现象学”[14]。也就是说,虽然这种现象背后并没有别的东西,但它可能隐而不显,而现象学正是使存在者的存在得以显示的科学。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观察,钱锺书的做法更着重于此。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是有这样一种声音,他们将现象当作某种过渡,认为在得道之后就该抛掷舍弃,所谓舍象忘言是也。也是受这种影响,古代哲学家、思想家在触碰到相应问题时,往往会忽略了现象本身的价值,钱锺书认为不可。他在分析“象”这一概念时,指出了其在文学研究中的不同之处:“词章之拟象比喻则异乎是。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变象易言,是别为一诗甚且非诗矣。故《易》之拟象不即,指示意义之符(sign)也;《诗》之比喻不离,体示意义之迹(icon)也”[15]。所以,钱锺书强调诗歌之“象”正是值得分析之处,正是诗所以为诗的精髓,片面否定抛弃实不可取。这同样也可以解释钱锺书为何对反映论心怀抵触,因为这违背诗歌的本来价值,无视了对现象特征的把握。在《札记》中钱锺书表示得更加直接:“不解诗之取譬与《易》之取象,理有相通。知谈艺之须辨体矣,而不知谈艺更贵乎达用也”[16]。从中我们也可以品读出钱锺书谈艺的特色,即“贵乎达用”,也就是从直接指示的角度来把握现象。
其次,不同于胡塞尔的感性直观,海德格尔把范畴直观对感性直观的渗透当作重点。海德格尔认为:“对上手用具的任何知觉都已经是有所领会、有所解释的”[17]。所以,他进一步指出:“我们不可因为‘作为’在存在者层次上不曾被道出就误入迷途,就看不到‘作为’结构正是领会所具有的先天的生存论建构”[18]。在谈艺析理时,钱锺书也强调以直接指示的方式加以描述。如《札记》中他对王安石赋物作诗的批评:“锺记室所谓‘即目直寻’、元遗山所谓‘眼处心生’,乃为不征之目验,而求之耳食。借古人语以自解,可谓尽信书不如无书者”[19]。这和海德格尔的理论貌异心同,这也可以算是钱锺书为何排斥体系的原因之一。因为在构建体系的过程中,一切都会系统化、抽象化,但这难免会让人忽略存在者自身的具体情况。当所有的内容皆被纳入体系中时,一些细节与特性难免被遮蔽与遗忘了。所以,钱锺书笔下的文学批评,往往能够跳出理论的桎梏与焦虑,直抵其真正的事实本质。如他评价《离骚》:“虽多有草木鸟兽之名,出非穷理博物之作”[20]。评价《焦氏易林》:“而‘有韵’之向不名‘诗’者,却‘直’可‘为诗’而无害。盖只求正名,浑忘责实,知名镜之器可照,而不察昏镜或青绿斑驳之汉、唐铜镜不复能照,更不思物无镜之名而或具镜之用”[21]。这些例子生动地说明了钱锺书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在反思了前人“忘责实”的方法后,对事实本身进行了一场回归。
从海德格尔现象学定义来看,他将其方法论意义定位为解释,途径则是“整理出一切存在论探索之所以可能的条件”[22]。在阅读钱锺书的著作时,我们明显感到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尝试。在其行文中,我们常能看见“文心”一词。所谓“文心”,即是《文心雕龙》中“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23]。钱锺书在品评作品对传统写法的突破时,也最喜用“文心”二字。如他对贾谊《过秦论》的评论:“按项平父《项氏家说》卷八云:‘贾谊之《过秦》、陆机之《辨亡》,皆赋体也’。此真具文心者之言”[24]。此处是就文之破体而言;还有对杜诗的品鉴,认为:“少陵则自道得力于儒,盖其藻鉴初不遗周公之籍、孔氏之书,文心足继彦和而开退之”[25],此处是对其师法渊源而言。此外,钱氏不只是在古代典籍品评中悬此准绳,评论西方作家时亦复见此语。如:“英国则Milton(弥尔顿)诗中始以taste(味道)作文心诗眼,吾国却无此说”[26]。所以,钱锺书对文心的关注是贯穿其行文理路中去的,恰如其所谓“青史传真,红楼说梦,文心固有相印者在”[27]。在各个学科的游走中,在各处文献的打通中,钱锺书发掘文心,正见其慧眼之独具,思想之独特。
此外,钱锺书之所以对现象学抱有持久的热情,还是因为他相信文学不仅是被分析的素材,也往往是理论观念的先导,是对时代气息的敏锐洞察。所以钱锺书对文学作品的把握往往能从大而无当的理论遮蔽中走出,直视文本的本来面目。钱锺书在给胡乔木的信中就曾指出,文史家有一种通病,即不理解所谓诗人具备时代触须性的特质,所以哲学思想常常先于文艺作品崭露头角,形象思维导夫逻辑思维之先路。“文艺与哲学思想交煽互发,转辗因果,而今之文史家常忽略此一点”[28]。钱锺书指出当前从事文史研究的学者,轻视了文学作品暗含的先导思想,忽视了文学与哲学间的互动。因为理论观念实际上是对社会人心的高度概括,而文学恰恰是社会心态最敏感的神经末梢。如果我们只谈论理论而不谈此前文学所发出的声音,一切就会变得黯淡而无趣。
而在《札记》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钱锺书对所谓触须特质的把握。如其对《老子》分析中,就专门谈到文学作品的现象。钱锺书写道:“一家显学,开宗明义前,故书雅记每有片辞碎旨,隐导其说先者,特引弓不发、散钱无串,未能条贯统纪耳。《老子》尚未成书,《道德》之旨往往遇之。《诗·桧风·匪风》:‘谁能烹鱼,溉之釜鬵’。《毛传》:‘溉,涤也。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知烹鱼则知治民矣’。……亦Bergson(柏格森)所谓‘créer sa préfiguration dans le passé’(创造对过去的预览)”[29]。钱锺书在这里引用了柏格森的言论,可见其打通之妙。因为柏格森生命哲学重点就在于直觉的方法,他说:“实体显得是不息的川流,是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只有直觉以及同情的内省才可掌握它”[30]。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柏格森这样的思考范式则是将哲学转向经验,承认没有超出世界和生活的哲学,否定理智时间断裂式的思考。柏格森一再强调:“理智化的时间其实是空间,理智是在时间的幻影之上工作的,而不是在时间本身上”[31]。另一方面,真正的文学对于世界经验的把握不是来自理性总结,恰恰来自最敏感的直觉。如果我们能理解好这一点,我们就能读懂钱锺书为何如此关注文学作品中先于哲学思想的部分。他实际上是从时间的流动性中,看出了直觉观察的价值与意义。
回归到对现象学的关注,从文本内部对作品进行发掘与考释,彰显了钱锺书一贯的批评眼光,也促使其形成了“史必征实,诗可凿空”[32]的艺术理解。
三 理念的实践:与陈寅恪“诗史互证”方法之分野
每有学者论及钱锺书诗学批评理念时,常会将它同陈寅恪批评理念共置。陈寅恪作为20世纪享有盛名的学者,与钱锺书一样,都善于贯通文史,打通中西。然而钱、陈二人治学趣味、学术方法迥然不同,对文学和历史研究的判断也不尽相同,此前虽有部分学者进行过比较论述,但因材料短缺,未能直截了当地从二人针锋相对处切入,由此来展开讨论,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而《札记》作为钱锺书的读书笔记,带有极强的私人属性,其心绪吐露得更加直白,表达上往往放言无忌、直抒胸臆。在《札记》中就有这样一段话,坦率地道出了他对陈寅恪的批评。钱锺书先是援引历代诗文中的相关内容,指出存有“女貌拟男容”的修辞特征:“按《左传》:‘孔父之妻美而艳’。男女之色,初无差别。李颀《郑樱桃歌》亦迳以‘美人’及‘娥娥’状之。……可参观《天方夜谭》中‘Girls or Boys?’(男孩还是女孩?)一则所谓:‘I have always noticed,too,that you,who love boys and wish to describe them,compare their caresses to those of girls.’(我也总注意到,如果你喜欢男孩并想描绘他们,就将他们的爱抚比作女孩)”[33]。随后他笔锋一转:“柳如是《戊寅草》有《男洛神赋》(‘惟隽郎之莫忘’),亦此类,而陈寅恪谓为赋陈卧子,迂谬可笑”[34]。钱锺书在此直接批评陈寅恪分析《男洛神赋》时无视修辞手法、刻意考据的作风,将其贬为“迂谬”,不满之情,由此可见。
实际上,如果我们回归讨论现场,就会理解陈寅恪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结论——将柳如是《男洛神赋》判为赋陈子龙,这与他的批评理念密不可分。陈寅恪认为当前研究文史的学者,必须对同一性质题目的作品:“考定其作成之年代,于同中求异,异中见同,为一比较分析之研究,而后文学演化之迹象,与夫文人才学之高下,始得明了。否则模糊影响,任意批评,恐终不能有真知灼见也”[35]。这段话中隐含着两点意见:一是对作品历史背景的稽考是评析作品的基础,否则一切无从谈起;二是通过对这种时代、年代的分析比照,我们才能形成一个精细化的评判标准,而不是流于一般的表面印象。解乎此,我们就明白陈寅恪在论及《男洛神赋》时,为什么会率先提出这两个问题:“(一)此赋实为谁而作?(二)此赋作成在何年”[36]?并且他进一步指出此赋命题之所以如此:“当由于与河东君交好之男性名士,先有称誉河东君为‘洛神’及其他水仙之语言篇什,然后河东君始有戏作此赋以相酬报之可能”[37]。顺着这样的逻辑推论,陈寅恪自然就走上了借助历史文献来考释文学作品之路,在赏析作品之时着重稽考史实,力图建立一种可量化的评价体系。
由陈寅恪这样的评价体系推断,如果我们要对作品进行艺术鉴赏时,应该建立一种历史的观念——尤其是面对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更要将其安放在相应的历史背景下去评判,以此“窥见时代之风气,批评作者之技能”[38];而当我们面对同代或时间相近的作品时,又要对其书写特征做历时性考察,“因袭变革之词句及意旨,固历历可睹也”[39]。但这种遍考文献是否信而有征的做法,确实很像钱锺书说的“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40]。将历史眼光过度应用在对文学作品的阐释时,我们常会忽略文学作品的独特魅力。就像钱锺书在分析《男洛神赋》时,指出这种写法不过是中国文学里固有的一个修辞特征。如果一味刻意引申,强行将文学的影子落到历史的实处,最终难免会形成一些经不住推敲的谬见。
此外,在面对历史文献与文学作品的交互关系时,二人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如陈寅恪所写的《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一文,罗列大量史料说明“杂种胡即中亚昭武九姓胡”[41],并借助杜诗中涉及“杂种”“杂虏”四首诗来互相发明,以诗证史。从整篇文章的写作安排来看,此处引用杜诗都是为了补充唐史“杂种胡”之说。然而陈寅恪以诗证史的同时,实际上也在脑海中架设了另一条轨道——把史料当成对杜诗的笺注。为什么这样说?那是因为关于杜诗的“杂种”之义,注者历来争议颇多,如仇兆鳌注“蛮夷杂种错相干”谓:“杂种,指吐蕃、回鹘、党羌言”[42]。浦起龙注“杂种抵京室”谓:“杂种,指回纥,旧注非”[43]。今人谢思炜则认为“杂种”泛指蛮夷,“杂种胡”很有可能是临时的词语组合,“非某一族之特指”[44]。杜诗“杂种”之义本无定论,陈寅恪却将“杂种胡”坐实,认定其特指九姓胡,并将杜甫四首诗中三处“杂种”和一处“杂虏”都当作同义的用语。他对杜诗用词的理解与前人不尽相同,为此处的杜诗做了一个无形的注脚。所以,陈寅恪的做法也是在借历史文献给诗文作笺释,透过历史材料来坐实诗歌的某些含义。
而一如前文所讲的那样,钱锺书的文学批评着重于对文心的开掘,文学批评从“尊本文”处出发。故而在他的批评语境下,历史背景是被虚化的,那些穿透时间与空间河岸的东西常被拿出来讨论,一如人性,一如情绪。钱锺书《札记》中论及杜甫《哀江头》:“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此句中的“望”是否应为“往”或“忘”,且整句诗该作何解,历来争议颇多。钱锺书主张为“望城北”,认为此解殊具诗眼。随后他援引多方例证:“参观《敦煌掇琐》廿一《女人百岁篇》:‘八十眼暗耳偏聋,出门唤北却呼东’。卷十四《过临晋县适调发》云:‘千里馈粮人未返,百丁团甲户无余’”[45]。如前文所谈,钱锺书谈艺向来注重人性和人最深层次的感受。故而他之所以将其解为“望城北”,是因为觉得杜甫心慌体衰方会出现“欲往城南望城北”的情形。当然在《管锥编》中,钱锺书也谈到了另一种说法,即:“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二据《两京新记》谓曲江在都城东南,地最高,灵武行在则在长安之北,‘欲往城南’即潜行曲江,‘望城北’即登高以冀王师之至”[46]。钱锺书关于这点的态度,在文中袒露得非常明确,他称这种说法是“(杜甫)苟非‘忠’而愚,亦同鸱蝠之能暝视矣”[47]!可见,钱锺书本人十分反感学者将诗人行为过度拔高,从而来完成某种政治化和主观化读解的做法。所以他所讨论的场景更加集中在人性的相通处,而非以历史文献来作为注释和考据的所在。在这一点上,钱锺书与陈寅恪可谓截然相反。
对于钱锺书,人们总爱提到他的顽皮与幽默。然而在那顽皮与幽默的背后,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他那冷峻目光与悲凉况味。夏志清回忆他同钱锺书晤面时的情形,钱氏形容自己的处世态度为:“目光放远,万事皆悲;目光放近,则自应乐观”[48]。如此处世态度,也反过来构建起他文学鉴赏的方向。我们翻看钱锺书的著作时,就能明显感到他与其他学者的不同。他在谈艺析理时,更多聚焦的是人性,是人作为无羽毛之两足动物那逃不开、避不掉的根性。因此,无论是多么肃穆庄重的说辞,道貌岸然的腔调,在钱锺书那凌厉目光的剖解下,人性的可怜荒唐在这里裸裎。还比如在《札记》中就有一则,提到他帮同事校改《中国文学史》,忽然忆起他对汉乐府《上山采蘼芜》一诗别有新解,指出“古今说者皆未中肯窾”[49]。有关于此诗的解读,论者多从所谓“人不如故”的角度去把握,以为男性主人公的陈词是在表达他的念旧。而钱锺书却以为:“此诗写喜新厌旧分两层:第一层指故人言,其事易晓;第二层指新人言,则窥见者鲜矣。盖新人入门后,相习而成故;故人出阁后,缘别而如新。是以新渐得人嫌,而故能令公喜。……如谓夫悔心复萌、余情未断,尚是浅看此诗也”[50]。在钱锺书的眼中,诗里面男主人公依然保持着喜新厌旧的根性。只是对他而言,新人见多了便成了“旧”,故人远走了就成了“新”。至于那些什么幡然悔悟、旧情未断的托词,是安不到主人公头上的。当然诗无达诂,但由这样的批评角度,我们可以一窥钱锺书对人性幽微之处的开掘,对世事人心的洞察,而他流露出的态度也是这般坦率与犀利。他从那些空头词句处转身,漫溯进人性暧昧不清的所在。这般品读方式,其实已不只是在读文,而是在去阅读人,去阅读人自己都难指明的情感矛盾。
而这样的谈艺方式,早已遍布于钱锺书的行文中。《札记》载其评王泠然的《与御史高昌宇书》,钱锺书便对其中“贵人多忘,国士难期”[51]一语,援引多条史料进行参证:“上句流传,已为俗谚,钱竹汀《恒言录》卷六即出诊然此《书》。《陈涉世家》云:‘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外戚世家》云:‘薄姬少时与管夫人、赵子儿相爱,约曰:“先贵无相忘”’。此冀其能贵,又冀其贵不忘故旧。然赖治然一语,点破贪痴妄想”[52]。假如只从学术考证的角度来看,钱锺书只需写完上面第一句话便可了结,后面的铺排则显得颇无意义。但恰如笔者之前讲述的那样,钱锺书的品评不只囿于考据,而是把赏析文章视作思考世事的途径,那么后面的叙述愈发凸显钱锺书的研究个性,他是在挖掘这句话背后所蕴藏的人生况味。这同样也是钱锺书作品不同于一般学术著述的原因,他把生命体验与学术考据交织在一起,从而进一步提炼自己的申说与表达。所以这样的写作既可划归学术内,又可以说是跳脱于学术之外。
总的来看,钱锺书“意内言外”诗学批评理念的提出,与他长期以来的治学兴趣和观察角度密不可分。在大的时代浪潮中,钱锺书坚守自我的批评主张,规避开那些大而无当的批评话语,深耕于文本,因文以知世,用不耻支离的方式完成思想上的申说。此种理念,既是对作品本身的看重,也是对文学价值的尊重。而我们通过对它建构过程的勾勒分析,也能够读出一代学人的学术心曲,以及掩映在字里行间的文化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