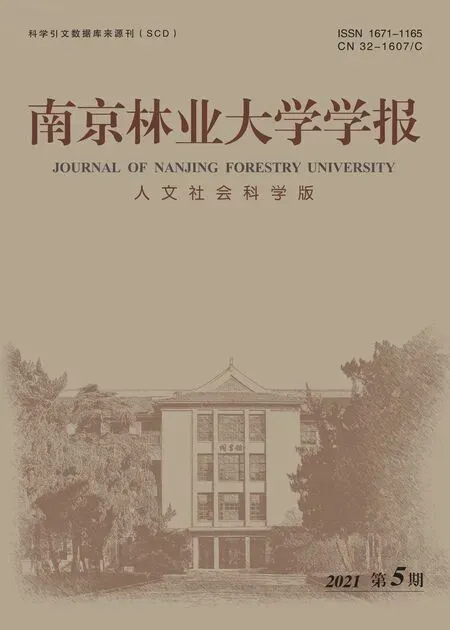爱的原则如何扩展到动物?
——儒家视域下的人与动物关系★
2021-12-24杜永宽
杜永宽
(苏州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建构系统完善、实践性强的生态伦理体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动物伦理作为生态伦理体系建构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渐渐受到重视。国内学者对如何利用本土资源来接洽生态伦理、动物伦理进行了一系列的学术尝试,其中最受重视的是从儒家思想中挖掘相关生态伦理的资源,成果斐然。相比广义的生态伦理,儒家思想与动物伦理关系的研究方兴未艾,因此笔者认为理清和呈现儒家思想所包含的人与动物的关系面向及其特质,可以为我们考察儒家思想与动物伦理之间的联系提供切入点。
一、双重世界中人与动物的关系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人与动物的关系最初不是一个伦理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妥善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既是治国安邦的需要,也是国治民安的体现。《尚书·舜典》记载:“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舜专门设立了管理动植物的官职,与掌管百工和祭祀的职位并列。《伊训》里赞美夏禹的贤明,也说:“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灾。山川鬼神,亦莫不宁,暨鸟兽鱼鳖咸若。”把动物的繁衍生息当做为政之德。《逸周书·大聚解》中说:“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礼记·郊特牲》中阐述周礼时记载:“天子大蜡八。……飨农及邮表畷、禽兽,仁之至,义之尽也。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通过祭祀禽兽之神,特别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猫神和虎神,来表明统治者对国家的治理已尽了最大努力。
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都延续了这一观点。孔子视保护和合理利用动物资源为保证国家繁荣的手段。如《孔子世家》所载:“丘闻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史记·孔子世家》)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舜和周文王时期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因此都出现过凤凰,在此可见孔子也接受了凤凰的出现代表时代兴盛的观点。孔子还将动物与礼联系起来,在子贡建议废除鲁国告祭祖庙用活羊的制度时,孔子却认为羊代表的是礼,去掉活羊,其实就是破坏了礼的完备,所谓“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孔子曾多次告诫弟子为学需以道德修养为主,为政需德治与礼治相结合。出于礼治的需要,一向主张“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的孔子一反在樊迟欲“学稼”和“学为圃”时的斥责态度,要求弟子“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篇》)。可见,孔子认为对动植物的认知是一个人治理国家的必要才能。
孟子、荀子更为重视取之以时、用之以节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在面对梁惠王询问如何治理国家时,孟子有段经典阐述:
不违农时,谷不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在孟子看来,动物不仅是供人食用的,而且动物的繁衍生息与“王道”息息相关。一个好的统治者不仅能够为百姓提供足够的肉食,而且能够避免动物泛滥,以免挤压人类的生存空间,故孟子又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孟子·滕文公上》)“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乱。”(《孟子·滕文公下》)能否将动物控制在合乎人类发展的尺度是衡量君主统治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
荀子在这方面与孟子的看法类似,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这一系列举措都是为百姓生活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鼋、鼍、鱼、鳖、鳅、鳣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荀子·富国》)物种的丰富,为人类生存提供了重要的生活资源。
在这种观念里,动物被视为保证人类生存和繁衍的重要生产、生活资源。人对待动物的态度不掺杂道德情感,纯粹出于尊重自然规律,最大限度地加以合理利用来保证人类社会的繁荣昌盛。因而动物在孔子的思想中不是被直接纳入“仁”这一范畴中的,而是通过礼或者王道才联系起来的。“仁”的基本内涵是“爱人”,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爱作为一种价值观被赋予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类本质”的意义。在马厩发生火灾时,孔子关心的是“‘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孔子对待动物的基本态度是工具性质的。
但孟子则在孔子“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合理地拓展了仁爱的内涵,提高了其普适性。这是否意味着动物成了具备内在价值的道德主体呢?施韦泽在《敬畏生命》一书中就赞扬:“属于孔子学派的中国哲学家孟子,就以感人的语言谈到了对动物的同情。”[1]72这是针对《梁惠王上》的相关记载,但是孟子以“感人的语言”谈到了“对动物的同情”的目的是什么。孟子对齐宣王“以羊易之”的做法持赞同态度,认为:“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这段话常引发的一个议题:以羊易牛、君子远庖厨是否伪善。在这里其实是个伪命题,从孟子的角度来看君子远庖厨不是一个有关善恶的伦理问题。孟子对动物本身并没有特殊感情,这里强调的是极端情况下对不忍人之心的触动。我们结合另一段话来看:“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同样看到生命遭遇危险,这里对待孺子与牛的态度截然不同,不可能用一个仇人的孩子或者一个品行不端的孩子来代替,但对动物却需要考虑到祭祀的重要性、人的口腹之欲。这种差异不是用差等之爱可以解释的。无论是陌生人还是亲人“将入于井”,他的恻隐之心并不会因此而有强弱之别。
因此,孟子的仁爱虽然相较孔子内涵更为丰富,但人与动物的道德关系并没有得到提升。所以孟子说:“理义之悦我心,如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认可人对肉食的喜爱;又说:“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孟子·尽心上》)发自内心具有道德意义的爱与敬,依然是局限在人的范围内,并且严厉批评重视动物、轻视人的行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滕文公下》)。
可见,“仁民而爱物”的思想显然不是指人要平等地爱一切事物,而是要把道德准则拓展到万物上,是四端之心不断拓展的自然呈现。正如“万物皆备于我”是指道德的根据在自己,道德自由不受外在力量的左右,并不是表达一切客观事物都依我而存在的主观唯心思想。在孟子这里“爱物”其实就是个人道德修养的需要和道德境界的呈现。
在先秦儒家思想中爱的原则通过两种路径扩展到动物身上:一是治国安邦的需要,在这一路径中人类对动物的关怀与其自身的繁衍生息密切相连;二是个人道德修养的需要,在这一路径中动物被化约为投射人类道德原则的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种路径下,动物作为自然界的一员,鸟兽鱼虫各有其时、各有其性,仍然保留了内在的独特价值;在第二种路径下,动物本身的特点和价值则趋于同质化,或者说趋于模糊化。因为道德原则并不会因动物的不同而产生变化,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无需区别动物的生理特性或感受性,需要体认的是人伦道德通过动物的呈现方式和途径;而且被视为一种工具意味着动物是外在于人类的他物,在落实道德修养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只要处理好人与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便无视动物,也无碍于提高道德境界的认知。
二、自然世界与道德世界的统一
先秦儒家将动物的价值一分为二,即自然世界的动物价值和道德世界的动物价值。从外在结构上看,两个世界并行不悖,互不干涉;若从内在理路上看,自孔子的“为政以德”至孟子的“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就蕴含了两个世界统一的必然性。宋儒通过以下途径完成了这一任务。
第一,以“仁”释“生生”。对宋明儒者而言,自然的“生”具有重要的意义,如程颢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2]120“生生”与“仁”紧密联系在一起,不仅具有了宇宙论的意义,还成为人类道德原则的根源,自然世界和道德世界具有了统一性,并因此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上也有了新的认识,解决了动物作为一种工具可能受到忽视的缺陷。
包含了“仁”之意义的“生生”不仅是宇宙间的普遍法则,而且是道德上的至善,故宇宙间的一切生命都因体现了“仁”而值得重视。周敦颐在回答为何不除窗前草的时候说:“与自家意思一般”,程颢解释为“观天地生物气象”[2]83。所谓“窗前草不除”就是通过绿草的生长体会人的生命与自然万物生命的相通性,体察到生生不息的自然气象与人的内在道德的紧密联系。程颢在实践“观天地生物气象”中,更进一步,“明道书窗前有茂草覆砌,或劝之芟,曰:‘不可,欲常见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鱼数尾,时时观之,或问其故,曰:‘欲观万物自得意’”[3]。不仅对自然生长的草不加修剪,而且主动饲养小鱼观赏。观鱼这一行为显然不是出于审美或娱乐之心,而是为了通过鱼的生意盎然体验宇宙的生生之意。动物是宇宙生命意义的体现,人生的一切际遇,接触到的一切外物都是进德修业之资,在这种认知上“观物”才有意义。而且人对“仁”的体察也需要经由“观物”达至“万物一体”的境界,如果只从人的视角、人的利益需求来看待自然万物,则是“人只为自私,将自家躯壳上头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佗底”[2]33。因此程颢除了观鱼,还说“观鸡雏可以识仁”。
第二,“民胞物与”的提出。与程颢相似,张载经常“观驴鸣”,其原因就在于“民胞物与”: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4]
这段话中,张载虽然对儒家的博爱作了形而上的论证,但“民胞物与”的思想不是通过认识论意义上的观察自然物、体认自然物独特价值达到的,而是由明而诚、明诚两进的极致,是境界之说。在这一境界中,自然界是一个整体,自然界的万物都是自己家庭成员的一部分,人和自然共同构成了一个家庭,“爱物”也就被纳入“亲亲”的范畴内,超脱了功利之心。既然人对家庭成员应该负有道德义务,那么人对动植物也应该有道德情感和道德义务,由此建立了一种彻底的义务论。在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中,人与动物关系的描述已经呈现出了伦理责任观;但这种伦理性是体现在家庭伦理和道德境界之上的,与立足于权利意识或平等观念的西方动物伦理截然不同。
第三,朱熹通过对《中庸》“赞天地之化育”的解释,将先秦儒家对动物的两种态度进一步融合。从孟子提出以“不忍人之心”导出“不忍人之政”,这两种态度的融合就是题中之意,同时也是对《大学》修齐治平次序的贯彻,“外王”的根基仍在“内圣”。朱熹说:“‘赞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间,虽只是一理,然天人所为,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种必用人;水能润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熯物,而薪爨必用人。裁成辅相,须是人做,非赞助而何?”[5]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圣贤出来抚临万物,各因其性而导之。如昆虫草木,未尝不顺其性,如取之以时,用之有节:当春生时‘不夭夭,不覆巢,不杀胎;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所以能使万物各得其所者,惟是先知得天地本来生生之意。”[6]人与万物虽同为一体,但并不是要消除人与物的区别,抹杀生命个体间的界限,恰恰相反,人与动植物的和谐相处,正在于人能够判明万物之不同,顺物之性来利用物,使其发挥作用,由此人对万物有了一种责任感。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责任感是单向度的,动物并不拥有选择权。只有体会到天地生生之意的圣贤才能做到“因其性而导之”,因而给这种责任感加上了一层道德修养的色彩。
第四,对杀生不仁的驳斥。对于动物生命的重视和珍惜并不代表需要戒除杀生。“儒者有两说。一说天生禽兽,本为人食,此说不是。岂有人为虮虱而生耶?一说禽兽待人而生,杀之则不仁,此说亦不然。大抵力能胜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尔。故曰:‘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2]399二程承认客观世界存在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但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不忍人之心”,人在客观世界之中又塑造了一个道德世界,所以既反对天生万物供人所用的观点,也反对杀生不仁的说法。正因此朱熹赞赏张栻的观点:“然于物也,有祭祀之须,有奉养宾客之用,则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于是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若夫子之不绝流、不射宿,皆仁之至义之尽,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则王政行焉,鸟兽鱼鳖咸若矣。若夫穷口腹以暴天物者,固人欲之私也。而异端之教,遂至禁杀茹蔬,殒身饲兽,而于其天性之亲,人伦之爱,反恝然其无情也,则亦岂得为天理之公哉!”[7]在朱熹构建的人与动物的关系之中,虽然人对动物应该负有道德义务,但其价值内核还是孟子以羊易牛的仁义之心的触发,动物生命本身是否具有价值这一西方哲学家反复讨论的问题被如何达到“仁之至义之尽”的合理利用这一问题所取代。
相比先秦儒家,宋代儒家对生生不息的大自然多了一份特别的关注,虽然本质还是继承和发展了孟子的四端之心,但宋儒不仅发展了人与动物关系的内在心性依据,而且试图通过仁义与天理的结合,使人与动物的关系纳入由道德进路而来的宇宙观中。
三、“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下的人与动物关系
宋儒的理论路径在王阳明思想中被进一步发展和补充了。王阳明通过大力倡导“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将宋儒所强调的人对动物的道德责任感和道德性宇宙观发挥到极致。
万物一体对于王阳明来说,不仅是一种至高的理想境界,也是一种需要落实到现实世界的工夫实践。万物与人一体同在,人与动物之间绝不存在疏离、割裂的状态,只是三代以后孔孟以降,邪说横出,才导致“间形骸”“分尔我”“人己物我”的关系完全割裂,因此有志之士要有重建一体之仁的道德担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8]29人不仅不能凌驾于万物之上,成为万物的主宰,反而要自觉承担起维护万物顺性长养的责任。
因而王阳明哲学中的宇宙是一个人与万物血肉相连、休戚相关的有机性的整体。“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辩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如何与他间隔得?”[8]141人作为个体与其他存在物并不是主客对立的关系,人不仅被包含在自然万物之中,而且必须意识到人及其他存在物之间的一体性。没有人的灵明,天地万物只是物理性的客观存在;反之,没有了物质性的自然事物,个体的价值也无处安放。只有在世间万物的交互感应中人的意义与价值才能得到呈现。
这样一个有机一体性的价值世界或者道德世界,消泯了人与动物的紧张关系和情感隔绝,对于动物苦难的感通是人之本性,是心体之本然,所以王阳明说:“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8]1066从这段话也能看出儒家“万物一体之仁”与西方动物伦理的不同。西方学者往往围绕动物是否具有理性或者感受力来展开论述,但在王阳明的阐述中人对鸟兽的同情并不是因为动物本身具有感情或者感知能力,而是与仁为一体,即便是毫无知觉的草木瓦石同样应得到人性化的对待,因为对其的同情爱护,是人之本心朗现的结果。王阳明为人对动物的道德情感寻找到了本体论方面的依据。这种道德情感具有了普遍性和绝对性,人对动物的关照和爱护成了发自本心、不言自明的道德准则。
若把“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推到极致难免有沦为理想主义之嫌,似乎难以在实际生活中贯彻和实行,程颢面对蝎子就不免困惑,“杀之则伤仁,放之则害义”。王阳明提出的实践原则有二。
一是针对具体实践行为的“爱得是与不是”。在王阳明看来,“万物一体之仁”是建立在正确的是非、善恶价值判断之上的,“然爱之本体固可谓之仁,但亦有爱得是与不是者,须爱得是方是爱之本体,方可谓之仁。若只知博爱而不论是与不是,亦便有差处”[8]217。“万物一体之仁”与“博爱”形式相似,内涵则完全不同,“博爱”是缺乏价值导向的泛爱,“仁爱”则涵盖了一定的价值选择。如何判断“爱得是与不是”,只能依靠“人思而自得,非言语所能喻”[8]217,体现出实践哲学的思想品格。
二是针对道德价值相冲突时的“道理合该如此”。“惟是道理自有厚薄……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心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宴宾客,心又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宁救至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这是道理合该如此。”[8]122-123这就意味着当对动物的爱护与其他道德价值相冲突时,是需要为更能体现“仁”的道德价值服务的。这里的“道理”显然不是一种空泛的道德原理、道德准则,而是每个人在认识外部世界、体悟生活意义中形成的实践智慧。
由这种实践智慧能不能发展出西方动物伦理的知识论原则呢?王阳明面对徐爱提出的“恐天下事理,有不能尽”时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8]2所谓的“道理”还是人伦规范的原则,囿于道德伦理之中。说到底儒家所认为的人与动物的关系不是西方哲学所谓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动物本身并不脱离人的价值世界而具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动物是被纳入人的伦理道德之中才具有意义。儒家所谓的动物有知,强调的不是动物具有智慧和情感,而是把人的道德意识赋予了动物,反过来又用这种具有道德意识的动物作为人伦道德秉自天、本心拓展的依据。如明儒高攀龙所说,“少杀生命,最可养心……省杀一命,于吾心有无限安处”[9]。明代杨豫孙将孔子所讲的“方长不折则恕也”解释为“方长不折,非止爱物,只自养仁”[10]。儒家对于动物的同情和保护追求的不是外在客观世界的和谐和价值,而是内在的人格完善和德行圆满。与西方动物伦理相比,上述明儒的论述反映了儒家关注人之所以为人、重视道德的思想特质。
四、结语
儒家对人与动物关系的论述基本上都蕴含在对“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解读和论证中,从宇宙间生生不息的天道中寻找伦理道德的本体论依据,将天道复归于人道。人与自然的理想关系建立在道德境界的提升之上。动物在先秦儒家中作为保障政治安定的自然资源尚保留的一丝独立价值,随着宋明儒家对孟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最终被消解在以“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道德境界中。在“民胞物与”中所建立起的儒家对于动物的责任感与康德间接义务论也有本质上的区别。在康德哲学中,立论根据在虐待动物会败坏人的心灵,导致对他人残忍;而在儒家哲学中,虽然对动物的爱护怜惜也是人之本心本性的体现,但不是建立在以人为目的的考量之上,而是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动物也是自己的一部分,对于动物的爱护就是对人自身的爱护。动物不是一种工具,对动物的义务也不是一种手段,而是仁义之心呈现的必然要求。与其说儒家思想论证人与动物关系,不如说是论证人如何体现和践行“仁”。
儒家思想中关爱动物的理念和行动依附于道德修养的本体论和工夫论中,一直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这就制约了系统的动物伦理思想的形成。虽然古代也有一些法律条文规定不得随意捕捞、宰杀动物,但都是出于农业生产的考虑。儒家思想中人与动物的关系在表现形式上有近似于现代所谓动物伦理的地方,但现代西方动物权利、动物福利立足在动物具有复杂的意识和自主性上,是现代权利意识的延伸,因此倡导者多建议立法保障动物权利和动物福利;儒家思想中有关动物的关爱则是儒家仁爱思想的呈现,动物本身不具有独立性,因此儒家更强调生生之爱。两者本质上的区别导致单纯从儒家思想中无法自行发展出西方思想界所谓的动物伦理。
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中人与动物关系的论述丧失了现代价值。正如张岱年所说:“西方有一种流行的见解,以为把人和自然界分开,肯定主体与客体的区别是人的自觉。而宋明理学则不然,以为承认天人的合一才是人的自觉。应该承认,这是一个比较深刻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说,原始的物我不分,没有把自己与外在世界区别开来,这是原始的朦胧意识。其次区别了主体与客体,把人与自然界分开,这是原始朦胧意识的否定。再进一步,又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肯定天人的统一,这可以说是否定之否定,这是更高一级的认识。”[11]宋明理学超越了主客对立,构造了一个澄清透彻的道德境界,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体,不以征服自然为目标,对自然万物抱有道德情感和道德责任。著名的人道主义者施韦泽说:“把爱的原则扩展到动物,这对伦理学是一种革命”[1]76。从孔孟到程朱,再到阳明,儒家通过对“仁”的诠释,发展出了不同于西方动物伦理的“爱的扩展”方式,最终在“万物一体之仁”的世界里,关爱动物、保护动物不是某一个团体或某一类群体的事情,而是下贯于每一个生存在现实世界的“愚夫愚妇”身上。同样,救助动物、倡导生命的平等也无需物质条件或心理因素的成熟,而是寓于人性,“当下即是”。无论是生态环境保护还是更具体的动物保护,都具有跨地区、跨行业、见效慢的特点,仅依靠政府的三令五申,难以彻底解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西方的动物伦理思想中人与动物的对立预设,动物权利、动物解放的主张,又容易给普通民众造成“率兽食人”的担忧;而儒家的伦理立场可能会在两者之间提供一种平衡,成为应对生态挑战和建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可供借鉴的一种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