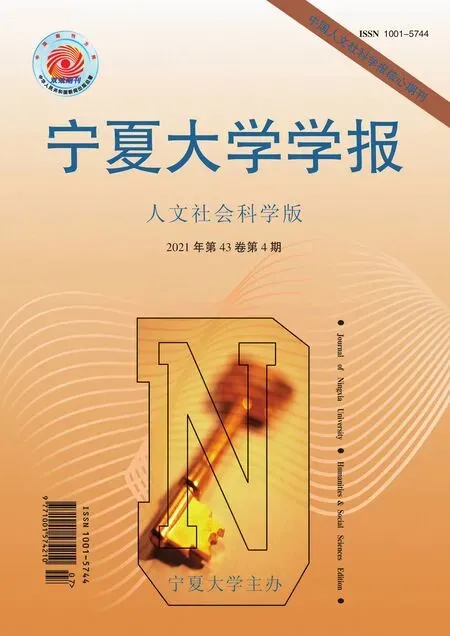当代中国政府垂直管理制度的起源和形成(1931—1954)
2021-12-23黄涛
黄 涛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101)
政府垂直管理制度,简称垂直管理制度或垂直管理,是指上下级对口政府部门之间建立起直接的、排除地方党政机关领导的行政隶属关系,下级政府部门的人事权、财政权、业务权由上一级对口机构直接领导的制度。这种制度强化的是上一级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权力。根据学者李振和鲁宇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实行中央垂直管理的职能部门有海关总署、审计署、烟草专卖局、地震局、邮政局、气象局、财政部、外汇管理局、税务总局、人民银行等29个部门[1]。政府垂直管理制度是特殊的条管制度,构成条块结构极重要的一环,是当代中国政府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管理学者沈荣华指出:垂直管理制度“在保证政令畅通、克服地方保护、平衡中央地方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各国政府广泛采用的一种组织形式”[2]。
那么垂直管理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如何产生和起源的?原因和过程是什么?研究清楚这个问题,不但可以还原一段重要的党史、行政管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可以看到1949年前后中国政府体制形成和国家构建时的历史环境、国际背景、影响因素和内在机理,传统制度对新国家形成的影响,以及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领导人的选择等,是从微观层面剖析当代中国国家构建、政府体制形成的一次重要契机。
一 中国共产党1949年前垂直管理实践的延续
历史学者钱穆指出:“某一制度之创立,绝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渐渐地在创立”[3]。回溯历史发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垂直管理制度的雏形。
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个重要的管辖反革命案件的具有司法性质的政权机关”[4],是为了应对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政治军事打击而设立的。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随着国家政权的建立,苏区保卫工作的重要性,也被提升到新的高度。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肃反工作要集中到政治保卫局的系统去,对付反革命组织的方法与技术,必须改进’。根据这一要求,国家政治保卫局随之成立”[5]。当月,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
关于国家政治保卫局制度,1932年1月27日颁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有详细规定。关于性质定位,《纲要》规定:“国家政治保卫局在苏维埃境内依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之规定,在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管辖之下执行侦查、压制和消灭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反革命的组织活动及侦探盗匪等任务”[6]。关于组织制度,《纲要》规定:“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组织原则是完全集权的,代(其)本身在委员会的管辖之下工作。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即委员会的主席,并得列席人民委员会,有发言权。国家政治保卫局委员任免处分权,属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7]。关于上下级关系,《纲要》规定:“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上下级关系,除特别障碍以外,是一贯的垂直系统。下级对上级的命令须绝对服从。各分局、各特派员在政治上受当地各该级政府或红军中军事政治负责者指导,各分局长并得列席于省苏、县苏的主席团会议,但工作的关系上绝对隶属于国家政治保卫局,地方政府及红军指挥机关无权改变或停止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命令,如有抗议只能提到人民委员会解决”[8]。也就是说,国家政治保卫局及其分局实行完全的垂直管理体制,排除了地方政府和军队的领导和干预。法学学者张晋藩指出:“国家政治保卫局及其分局,名义上是同级地方人民政府的机构,实际上完全不受同级政府领导,完全实行垂直管理,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国家政治保卫局及其分局只在政治上接受同级党和政府的指导,业务上与组织上保持独立,自成体系”[9]。
国家政治保卫局“为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进攻,保卫苏维埃政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0],但也存在脱离地方党委政府监督、权力过大等问题,受到了不少批评。1932年1月7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曾作出《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批评道:“肃反的组织——肃反委员会与地方政治保卫处〔局〕,在一个时期内,竟形成了超党超政权的独裁机关”,“有些地方政治保卫局(如江西)与上级断了关系后,竟不受当地的党和政权的指导,且他的本身又根本无委员会的集体组织”[11]。这个批评指向的就是这种垂直管理体制,但这种管理体制仍旧延续。此后,中央苏区根据地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直到1935年,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政治保卫局的机构才被撤销”[12]。
虽然国家政治保卫局只存在4年多,但这种垂直管理制度却非常严格和完整,表现为两点。第一,政治保卫局实行垂直管理,组织上形成一个单独系统,在业务上完全排除了地方党政机关的领导。第二,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这种组织性法规作为其机构设置和管理体制的依据。此外,肃反委员会、裁判所也实行接近于垂直管理的制度,但以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制度最为典型。这些实践为中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推行垂直管理制度打下了制度和经验基础。
二 学习和借鉴苏联的结果
中共早年受共产国际领导,加上当时自身经验不足,实行“以俄为师”的政策,大力学习和借鉴当时俄国和后来的苏联,包括党的组织制度、政府体制,其中就包括垂直管理制度。美国政治学者李侃如指出:“毛泽东时代的正式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苏联的体制,虽然也参考了中国帝制的历史、国民党及根据地的经验”[13],此言很中肯。具体到垂直管理制度,中共受苏联影响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苏联为中共提供了垂直管理制度样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体制基本上是苏联体制的翻版,大至整个体制,小至政府机构的名称,都与当时的苏联高度相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共最典型的垂直管理制度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制度,该制度名称与体制都来自苏联。有学者认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是我党在革命战争时期‘以俄为师’探索红色政权人民公安保卫工作的历史里程碑”,学习的就是20世纪20年代成立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委员会”[14]。中华苏维埃政权的“苏维埃”,是俄文Cober的音译,意为会议或代表会议[15]。即使在摆脱共产国际领导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仍大力学习、借鉴苏联制度。苏联的垂直管理制度深刻影响了中共对于垂直管理制度的认识与实践。
其次,苏联政府体制中的条管制度(又称部门管理原则或部门管理)也被中共直接学习与使用。政治学者周振超认为:“条条”是指从中央延续到基层的各层级政府中的职能相似或业务内容相同的职能部门,“块块”是指各个层级的地方政府[16]。政治保卫局、肃反委员会、裁判所是特殊部门,实际上,即使在一般性的政府部门,中共也大力学习苏联制度,引入中央政府部门与地方政府共同管理的双重管理体制,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以“条”的管理为主,“块”的管理为辅。这种条管制度某种意义上也是垂直管理制度的前身。以“条”为主的双重管理制度与垂直管理制度只有程度的差异。
当时的苏联体制,在政府部门设置上,高度强调垂直管理。苏联政府部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实行完全的中央垂直管理,地方政府没有领导与干预权;另一类实行双重管理体制,由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双重领导,现实中往往以中央部门领导为主,地方政府领导权很小。苏联试图通过这种制度安排来实现高度的政治经济集权,推行计划体制。在条块问题上,苏联高度强调条条作用,推行部门管理原则。这一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为中共所学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布的法令特别强调各部上下级的统属关系,在“条块关系”上特别侧重于“条”,这在中国历史上属于首次。《中华苏维埃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1933年12月12日通过)第95条规定:“区及县属市的各部、直隶于县的各部、县及省属市的各部、直隶于省的各部、省及中央直属市的各部、直隶于中央的各部,成为直的组织系统,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第96规定:“区、市、县、省各级苏维埃的各部,除隶属于各该部自己的上级各部之外,受同级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的指导和节制”。第97条规定:“主席团没有停止各部执行各该部上级的命令之权。如主席团对于各该部上级的命令有异议时,应提出到上级执行委员会或主席团去解决,未得上级执行委员会或主席团的指示之前,不得停止各部执行上级的命令”。第98条规定:“各级苏维埃非得各部上级的同意,不能随便调动主要的负责工作人员(部长、副部长等)”[17]。这4条规定显示上级部门对于下级对口部门的领导明显优于地方政府的领导。这种非常典型的条管制度,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垂直管理制度的前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这些垂直管理制度和条管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自然地得到延续,比如在海关、铁道、邮电、检察等机构,都实行垂直管理制度。其中,检察系统的垂直管理体制确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要是学习苏联的产物。1922年5月20日,列宁在《论“双重”领导和法制——给约·维·斯大林并转政治局的信》中指出:“我建议中央委员会在目前情况下否决‘双重’领导,规定地方检察机关只受中央机关领导”[18]。列宁主张检察机关实行垂直管理。实际上,后来斯大林推行的正是检察机关垂直管理制度。“苏联总检察长任命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州及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的检察长,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以及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的检察长只服从苏联总检察长,它们的职权不受任何地方机关的干预,而过去联盟的检察机关和各加盟共和国的检察机关之间并非隶属关系”[19]。苏联检察机关管理制度深深影响中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共便确立了检察机关实行垂直管理的思路,并最终把它变成现实。《中共中央批转〈第二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决议〉及高克林〈关于过去检察工作的总结和今后检察工作方针任务的报告〉》(1954年6月12日颁发)规定:“在宪法颁布后,检察机关将实行垂直领导”[20]。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1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在上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下,并一律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第83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地方国家机关的干涉”[21]。检察系统确立了垂直管理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政治和行政制度学习于苏联,这一点是中共领导人的共识。1960年6月,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22]。这里说的前八年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八年,外国指的是苏联。1986年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时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23]。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认为中国对苏联制度的学习与借鉴。因此,中共大规模在政府部门实行条块结合的双重管理制度以及较大规模地实行垂直管理制度,受到苏联的直接影响,是学习苏联的结果。
三 传统中国垂直管理实践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历史悠久,政治经验非常丰富,传统中国已有垂直管理实践,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缔造者毛泽东是一个注重从历史中汲取治国智慧的政治家,古代中国的垂直管理制度与实践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垂直管理制度的起源有着重要影响。
垂直管理在古代中国早就有了实践,主要有两类。
第一类是一些特殊领域、特殊事务,如盐铁、漕运、特务机构等。为了破地方主义和更有效地监控地方、管理国家,保证江山永固,古代皇帝想尽办法,垂直管理制度是他们非常青睐的制度。在历史上,上述领域大都强调中央专属,实行垂直管理。政治学者周振超指出:“汉代,已经出现了全国范围内垂直领导的机构。以后的历代王朝都有垂直管理的机构,只不过垂直内容、数量和程度不同”[24]。历史学者吴宗国指出,西汉时“王朝在产盐之处设置盐官,西汉的盐官遍及28郡国,共35处;产铁之处则设有铁官,西汉铁官遍及40郡国,共48处。与之相似,有国营手工作坊处设工官、服官,有水池及鱼利之处设水官。在西汉它们都属于中央派出机构。盐官、铁官属于大司农,工官或属少府,水官或属水衡都尉”[25]。汉代在局部领域实行的垂直管理制度已经颇为成熟。
第二类是监察系统、军事系统的管理体制,钦差大臣制度等。这些部门、领域实行的制度也带有垂直管理的意味。如监察系统,中国从秦朝开始就在中央层面确立丞相、太尉、御使大夫分立的体制,三人分掌行政、军事和监察。《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御史大夫,秦官,银印青绶,掌副丞相”[26]。御史大夫与低一级的御史构成一个单独的系统,即监察系统,负责监督政府。政治学者林尚立指出:“在中国古代政治系统中,有一个主要负责监督地方官吏的监察系统。该系统中的监官独立于行政、军事系统,直接对皇帝负责”[27]。直接对皇帝负责,实际上就蕴含垂直管理的味道。此外,古代皇帝大多强调自己对于军队的完全掌控,不让地方插手,在制度设计上表现为垂直管理军队事务。
总之,古代中国一直都有垂直管理机构,尽管只在局部范围内。伴随着中央集权思想的强大影响,这种垂直管理的实践和传统也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度设计。
四 中国国情与时代环境的要求
国情和时代环境对于制度选择有着重大影响。历史学者瞿同祖认为:“无疑,所有行为分析必须放到特定的情境中进行,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按照任何行为在具体社会和政治条件中实际显示的情形来思考分析它”[2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有些部门实行垂直管理,或者说在“条块关系”中强调“条”的管理,也是国情和时代环境使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垂直管理制度起源的国情和时代环境,最核心的是争取和巩固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发展生产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先实行垂直管理的是海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都就海关问题发表过看法,他们将海关独立看成是反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要内容。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中指出:“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之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29]。1949年6月,中共中央指定由孔原负责筹建海关总署。周恩来对孔原说:“新中国海关工作性质要求全国统一,要有具有一致对外的统一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人民海关。新中国必须把被帝国主义把持的旧海关加以彻底改造,使它成为为新中国建设事业服务的人民海关”[30]。周恩来谈到海关“独立自主”和“全国统一”。1950年4月29日,刘少奇在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演说中表示:“帝国主义已经从中国赶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许多特权已经被取消。新中国的海关政策与对外贸易政策已经成为保护新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工具。这就是说,我们已把中国大门的钥匙放在自己的袋子里,而不是如过去一样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袋子里。从今以后,中国工业就不致受到帝国主义的廉价商品的竞争,中国的原料将首先供给自己工业的需要。这就扫除了一百年来使中国工业不能发展的一个最大的障碍”[31]。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强调海关不仅要独立于西方列强,而且强调海关必须要高度集中统一,也就是垂直管理。这里,我们看到垂直管理的目的是独立和革命,包含了主权不容侵犯和分割的考虑。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明确海关总署为政务院组成部门[32]。1949年10月25日,中国海关正式成立。1950年3月8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关于海关总署直接领导全国各地海关的通知》,决定“全国各地海关均应立即和海关总署建立上下级的关系,受总署直接领导,一切有关海关的组织、人事、行政、业务等均应向总署报告请示,总署所颁发的一切规章、命令、指示,都应严格地遵照执行。不经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及海关总署批准,各地不得自由变更”[33]。海关上下级间建立行政隶属关系,确立垂直管理体制。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暂行海关法》,进一步巩固海关垂直管理制度。《暂行海关法》第九条规定海关总署“组织并管理全国海关机关及其业务”。第十五条规定:“各关直隶于海关总署,由总署统一领导,与当地对外贸易管理机关保持密切的工作联系,并受其所在地大行政区人民政府的指导”。第十六条规定:“各分关、支关的领导隶属关系,由海关总署规定之”。第十七条规定:“关设关长,必要时得设副关长,均由海关总署署长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免之。分关设分关长,支关设支关长,必要时均得设副职,均由海关总署署长任免之”[34]。这和国家政治保卫局有两点相同。一是海关也作为一个单独的系统,实行严格的上下级垂直管理。二是也通过法律来规范海关设置和管理体制。
中共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初决定海关、铁道、邮电、军事等实行垂直管理,是基于革命、巩固政权和国家建设的需要,这也是当时的特定条件与环境决定的。军事和半军事性质部门必须实行垂直管理,才能适应新生政权的需要,才能巩固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邮电、铁道等部门实行垂直管理体制,有利于打破各地通信交通分割的局面,打下大规模建设的基础。
此外,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较多使用垂直管理制度,除了学习苏联的因素,也是当时残酷的政治经济环境所迫。当时,面对国民党的打压和进攻、日本的侵略和扫荡,这种体制可以有效贯彻上级组织乃至中共中央的决定、命令,提高战斗力,确保中共得以生存和发展。
五 中国基本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需要
一个国家的基本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对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制度选择具有重大影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需要“条块”权力架构,尤其需要通过垂直管理和“条”的管理来强化中央权力和保证计划目标的实现。这是当代中国垂直管理制度起源的一个重要的内生原因。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共中央已经确立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针,这正是中共为之奋斗几十年的重要目标。社会主义道路在当时唯一成功的样本就是苏联模式,即政治经济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曾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有过预言式描绘:“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亿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这就是落在我们肩上的巨大组织任务”[35]。斯大林模式正是试图实现这一目标。斯大林模式在经济上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国家通过部门管理原则来强化中央集权,以确保国家计划目标实现。在对地方政府部门的领导上,中央部门的权限要远远大于地方政府。可以说,斯大林建立了“条”压倒“块”的政府管理体制。正如姜长斌等学者所言,斯大林经济体制的灵魂是“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经济计划,它的运转工具是垂直的部门行政指挥”[36]。计划经济体制与政府部门垂直管理可以说是孪生兄妹。
学者程又中指出:斯大林时期,“在经济上,联共(布)中央和联盟中央政府各部门牢牢控制全联盟经济大权,各加盟共和国已无权独立领导和管理自己的经济和文化建设。联共(布)通过各级党的领导机关设立的与政府机关相对应的机构,领导上至联盟中央政府、下至市和区的经济管理机关;由联盟中央制定并监督执行具有法律效力的全联盟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直接管理银行、财政、物资、进出口贸易及全国绝大部分工农商业企业,从而中央完全控制了全联盟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37]。据学者陆南泉研究,到1946年,联盟预算占全苏联预算的79.5%,加盟共和国预算和地方预算共占20.5%[38],这一切都有赖垂直管理制度。
中国学习苏联模式,在经济上要确立计划经济体制,必然需要学习苏联这种广泛使用的部门垂直管理制度,通过中央部门领导地方对口部门来保障计划目标的实现。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当经济恢复之后,中共中央通过取消大区政府等手段来强化中央以及中央各部门的权力,大致到1954年前后就确立了中央各部门对于下级对口部门的有效领导。学者郭为桂指出,1953年底,“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一大特色,即各综合、专业部门的高度集权的垂直领导体制初步确立,形成了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中的诸多‘条条’。各‘条条’开始在各自的管辖轨道内事无巨细地发号施令,‘一竿子插到底’,对整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39]。1954年,《国务院组织法》颁布,对中央与地方关系和部门管理体制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政府机构继续增多,国务院机构增加到64个,较1953年增加20多个,此后继续增多。学者李振和鲁宇指出:“1949年后的建政初期,中国在许多部门都实行了垂直管理体制。1954年之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中央部门从1953年底的35个增加到1957年的81个,当时几乎所有经济部门都实行了垂直管理”[40]。另一方面,政府管理制度中条的管理以法律形式确立。这意味着以条条管理为基本特点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确立,政府垂直管理制度基本形成。
1956年2月14日,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汇报有关发挥地方积极性问题时表示:“我去年出去了几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也不通知他们;他们的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曾希圣意见最多,对商业部很有意见,对不批准他们办肥料厂很有意见”[41]。这则谈话反映了垂直管理制度、条管制度已经普遍形成。而且,就连地方办肥料厂也需商业部批准,反映了中央部门权力之大,条块矛盾已经开始浮现。
从1957年开始,在毛泽东推动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第一次大规模向地方放权,当时叫“体制下放”,条块关系向“块”一端倾斜。如,已经确立垂直管理的邮电部、铁道部开始“体制下放”。1958年6月1日,《邮电部党组关于改变邮电体制的请示》称:“如果不改变邮电企业的体制,邮电建设还是按目前这样由中央统一规划、集中建设的办法,那么本来就已很落后的邮电通信必将成为国家建设中的狭窄地带……应当改变邮电企业的体制,以地方为主领导并规划建设各地的邮电企业,把直属邮电部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邮电管理局,改归各地的人民委员会领导,作为它们的组成部分之一”[42]。铁道部也一样,1958年,《铁道部党组关于改进铁路管理体制向中央的报告》提出铁路下放的建议,“现有十七个铁路管理局的行政管理一律改为各省(市)、自治区和铁道部双重领导”,“各省、自治区的铁路管理局和工程局即作为各省、自治区的铁路规划、建筑和管理的机构,直接对各省、自治区负责;涉及省、自治区以外的铁路规划、建筑和管理,由铁道部负责综合平衡”[43]。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些请示。这种大规模放权对刚刚形成的垂直管理制度、条管制度是很大的削弱,但也反映垂直管理制度过多使用影响了地方发展。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共已决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决心学习苏联制度,实行计划体制,这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垂直管理的起源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从基本制度面上决定中国必须大力推行垂直管理制度和条管制度。
六 结语:兼论当代中国早期国家构建
作为当代中国政府体制的重要组成,垂直管理制度的起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一个有着两千多年中央集权传统、有着古代最为发达的官僚制、高度注重纵向结构调控的国家,垂直管理制度起源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度构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垂直管理制度的起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体制和国家构建是国内和国际、历史和现实、客观环境和主动选择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建立的,而是在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的国家的基础上构建的,而且这个国家有着长期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和大一统传统,政府管理经验极其丰富。尤为重要的是,古代中国在盐铁、漕运、特务系统等特殊机构早已实行垂直管理,积累了不少垂直管理经验,这些经验直接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其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较长岁月中,中国受到西方国家的持续封锁和敌视,而苏联是当时的强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是中国可以依靠的最重要外部力量,所以中国很自然地采取投向社会主义阵营、与苏联结盟的外交政策。学习和模仿苏联是当时中国进行国家构建和制度建设的主要方式。当时的苏联体制就是斯大林模式:政治上高度集权,党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经济上实行计划体制,国家是生产的管理者、组织者、分配者,市场高度萎缩;整个国家在政治经济上都高度依赖垂直管理制度和部门管理制度。苏联的垂直管理制度是中共垂直管理实践的直接源头。
再次,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中共已经进行了28年的革命和武装斗争,有着管理党和政府的丰富经验,而且早已实践了垂直管理制度,以使得自己能够在危险而残酷的环境中生存和壮大。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中共在应对国民党的政治军事围剿时一种自我保护举动,实行严格的垂直管理制度,地方党政机关无权干预。当国家政治保卫局走到极端,带来权力不受制约乃至于肃反扩大化的弊端时,中共及时废止了它。在普通的政府部门上下级之间,当时中共已经高度强调“条”的管理,这是古代中国所没有的新事物。古代中国上下级政府的普通政府部门虽然也对口设置,但不是垂直管理,而是以地方管理为主,实行分级负责制。
最后,在当代中国政府垂直管理制度形成过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的价值取向和选择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他们把垂直管理制度当作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保障国家独立、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方式,直接领导了垂直管理制度的创设和改革。不过,他们虽然强调中央集权,但高度注重条块之间的平衡,强调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一切服从于巩固国家政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更高的目标。
到1954年,中国已经在海关、邮电、铁道、水利、军队等领域建成了垂直管理制度。此外,在大量其他政府部门(如农业部)也确立了条管制度。这时,古代中国极少见的条块关系、条块网络进入中国政府体系,成中国政府架构的基础性内容,深刻影响中国政府管理、国家治理的全过程,条条块块也成为了中国人经常使用的词汇。这是中国政治史上的新现象、新事物。从此,垂直管理制度始终成为中国党政机构改革、国家构建的重要抓手和路径依赖,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国家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