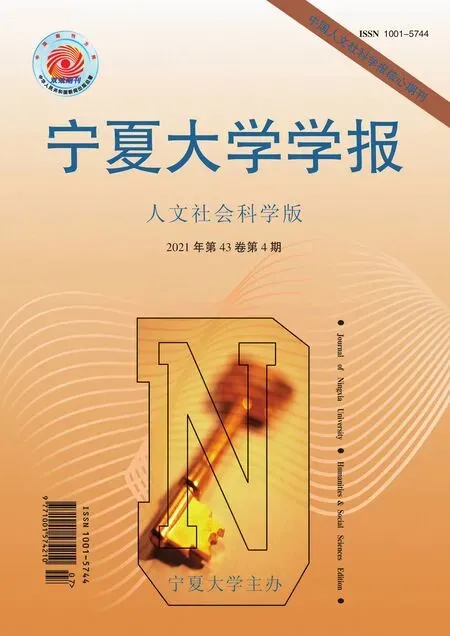危机与新生:中美比较视野下调查记者的生存现状探析
2021-12-23李海波
邱 清,李海波
(华东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上海 200241)
调查记者这一职业群体,向来被视为新闻从业者的角色模范,体现出比一般记者更高的职业素养和更执着的新闻理想。近年来,新闻业的结构性危机弥漫全球[1],调查记者的人才流失与生存困境引发业界和学界的关注。2018年“长生疫苗事件”期间,网文《深度调查行业兴衰史——中国调查记者都去哪了?》获得病毒式传播,关于中国调查记者衰微的讨论——特别是对所谓“黄金时代”的凭吊和乡愁,甚至超过疫苗事件本身,成为当时热门的公共话题。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财新》《南方周末》等媒体的调查报道赢得了较高赞誉,将调查记者群体及其生存现状再次带入大众视野。布罗姆利(Michael Bromley)的研究发现,调查记者的衰落是一种全球性现象,遍及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新闻业发达的国家[2]。在一本梳理和分析美国调查性新闻业历史的著作中,斯塔克曼(Dean Starkman)认为兴起于进步主义时代的“扒粪”式报道,眼下正遭遇市场压力和商业危机而陷入泥潭,进而发出“看门狗不叫了”的慨叹[3]。
美国是调查性报道的发源地,虽然面临重重危机,但目前仍然是国际新闻界最新发展趋势的风向标,调查记者这一职业群体在美国遭遇的生存困境以及他们的突围策略,对于中国新闻业无疑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关于调查记者的研究,国内外迄今已有不少文献,但将中美两国调查记者生存现状进行比较者寥寥无几。中美调查性报道及调查记者角色的变化都由于社会变革的影响而经历着兴替,但又因具体社会文化语境而具有自身的“底色”。因此,本研究引入中美比较的视野,首先阐述两国调查记者生存的总体状况,其次从商业模式与薪酬制度、法律风险与人身危险、从业心理与职业认同等方面进行具体的比较分析,以探究调查记者这一群体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 中美调查记者群体的总体状况
关于中国内地调查记者的行业生态,张志安团队在2010—2011年和2016—2017年做过两次全国性的普查。研究发现,近年来,该行业总体呈现断崖式下滑的趋势:第一次调查样本总数为334人,6年之后骤降至175位,显著下降的从业人数、优秀调查记者的外流、日益萎缩的调查团队似乎意味着调查报道行业的凋零[4]。曾是《中国青年报》记者的叶铁桥说:他当时供职的《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部”曾经在业内颇有声誉,但在2014年12月30日宣告解散;紧随其后,《华商报》《南方都市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相继削减深度调查团队。调查记者这一特殊工种在2015年衰落趋势尤为严峻[5]。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人员锐减的困境主要是针对传统媒体而言,实际上“澎湃”“界面新闻”“腾讯谷雨”等新媒体机构或平台为调查记者开辟了新的职业空间。比如成都传媒集团出资打造的新兴媒体“红星新闻”,2017年以“20万+”的年薪待遇招聘“心怀理想,追求真相”的调查记者[6];“人民网”开出年薪百万的待遇条件招聘拥有5年以上从业经验的“首席调查记者”[7]等举措,在纸媒行业低迷之际引发传媒圈的广泛点赞。
可以说,中国调查记者的总体情况喜忧参半,那么美国的情况如何呢?2003年,“美国调查记者和编辑协会”(Investigative Reporters and Editors Inc,简称“IRE”)的注册会员人数为5391人,2009年为3695人,而到了2014年,IRE仅有2734名成员,降至历史最低点[8]。如此看来,似乎也遭遇了人员锐减的困境。然而,根据IRE官网2021年的数据,该协会的成员目前为5500多名[9],比起2014年翻了将近一倍,甚至超过2003年的历史最高值,且该网站持续不断地发布调查记者的招聘信息(job posting)。可见,新媒介技术的变革和市场竞争的压力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效果——在导致传统媒体调查报道团队成为裁员和人才流失重灾区的同时,又以另一种方式吸纳了更多适应新媒介环境的人才。
中美两国的调查记者在代际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相比而言,中国同行的年龄结构整体偏年轻化。张志安的统计显示,34.8岁为中国调查记者的平均年龄,仅有4人年龄超50岁[10]。王维佳认为,这个现象与商品化新闻生产逻辑有关,即新闻机构出于经济效益的考量而追求高素质、低成本的年轻劳工[11]。在2010年参加全球调查记者大会(The Glob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Conference,简称“GIJC”)时,29岁的记者赵何娟在许多资深调查记者面前颇觉羞愧:“这也是中国新闻业的羞愧,中国记者比西方同行普遍年轻又浮躁,没有经验积累或思想厚度”[12]。由于调查记者是需要长期经验积累的职业,只有在某个问题上有更多的经验,才会有更加深入的理解,进而能够梳理出事件背后的脉络,因而整体来说,调查记者群体的年轻化状况不利于中国调查性报道的长远发展。
二 中美调查记者的生存现状
(一)商业模式与薪酬制度
讨论调查记者的衰微,通常会提及新媒介生态下纸媒的经营困境,传统的商业模式难以为继,因此难以支撑调查报道的生产投入和人力成本,导致调查记者收入下降,从业者规模急剧缩小。既往很多研究以“新闻民工”来描述调查记者群体的处境,认为调查报道制作周期长、难度大,而媒体机构给予的物质保障不足,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再加上信息碎片化和流量至上的追求,挤压了深度调查报道的市场空间。张志安的研究表明,2016—2017年40%的调查记者月收入水平低于10000元,仅有22%的头部记者超过15000元[13]。“薪酬网”的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记者及采编职位平均月薪为8915.56元[14]。而ER(I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旗下的薪酬评估网站SalaryExpert的评估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3月,中国调查记者的平均年薪为125050元,年均奖金为2488元,其中,拥有1~3年工作经验的新入门调查记者年均工资为93868元,拥有8年以上工作经验的资深调查记者的平均年薪为153533元[15]。考虑到通货膨胀和其他行业薪资情况,这样的薪酬待遇对于优秀人才而言,显然不足以提供为之奋斗的持久动力。叶铁桥认为,调查新闻业的存在不能仅仅依靠情怀与理想,还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来支持它,以使梦想成真[16]。
整体收入情况不容乐观,具体的薪酬赚取与分配方式同样不利于调查记者的专业实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媒体开始实行市场化改革,新闻机构普遍采取“计件工资”的绩效薪酬制度,即所谓的“挣工分”,繁重激烈的生存竞争导致许多新闻从业者疲于奔命,使得具有使命感的新闻劳动在一定程度上退化为单纯的谋生活动。对于调查记者这个高投入、慢产出的特殊工种而言,“挣工分”的薪酬体系对其尤为不利。夏倩芳的研究中曾提及一个生动的案例:一家省报的很多记者喜欢把一篇报道拆分为多篇进行发表,这样可以多挣几倍的“工分”,显然比做深度报道更划算[17]。白红义指出,在媒体内部广泛实行的工资计件制将加强新闻工作者的“劳工”特性,从组织运营的逻辑来看,这种方法可以增强效率并降低成本。但是,这对记者个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长远考虑,它还会影响新闻输出内容的质量[18]。迫于绩效考核压力,调查记者开始采取行动规避报道风险、追求稿件数量,这使得撰写移花接木、添油加醋等“注水”稿件成为部分调查记者的实践动力,与客观公正、准确独立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相悖。此外,在我国,女性调查记者的处境更为艰难——尽管媒体单位普遍设有产假制度,但在绩效考核制度下,女性调查记者生育期间产假所得仅为所剩无几的基本工资。在王海燕对我国22位女性调查记者的深度访谈中,许多女性调查记者坦言自己因为休了产假,职业上升尤为艰难——不是从一线岗位被换下来,就是被迫跳槽[19]。
可以说,调查报道以及调查记者的衰落,在过去新闻商品化机制下已经显露端倪,如今在移动互联网和数字人工技术的冲击下,传统的新闻商业模式遭遇严峻的危机,调查记者的生存境况因此愈发艰难,这是理解行业趋势的大前提。不过辩证地看,信息技术和新传播生态给调查报道带来的并非全是冲击,同时也提供了一些新的机遇,比如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平台的直接打赏和间接的流量变现,拓新了内容领域的商业模式,使得优质稿件存在获益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计件工资”制度或许是调动调查记者劳动积极性的一种方式。在考核制度上,“界面新闻”等新媒体机构以“定薪制”代替了“计件制”[20],以使调查记者静下心来专心做深度报道,《财经》周刊至今仍在推进“财经奖学金”项目——每年提供10个让旗下记者以脱产方式系统学习调查性报道及财经新闻相关内容的资助名额,该项目每年的周期为3个月[21],这在行业中做了很好的表率。
相较于中国,美国实行以商营媒介为主的媒介体制,且媒介集团往往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极大的影响力,因而美国媒体过去大多成立专门的调查性报道小组,给予调查记者足够的财力支持。但在新媒体时代,美国传统主流媒体为应对冲击,也在缩减开支,这直接影响到调查报道的生产和调查记者的生存。为了减少媒体支出并扩展新媒体平台业务,自2012年以来,“美国有线电视网”(Cable News Network,简称“CNN”)裁减了耗时且昂贵的调查新闻团队,扩大了数字新闻团队的规模[22];2018年,拥有近百年历史、以追求“深度信源和守在门外的报道”为核心的《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把采编团队缩减至45人,仅为原先的一半规模[23]。IRE和美国AR&D(Audience Research&Develpoment)公司共同发起了一项面向全美的网络调研,数据显示,虽然有76%的媒体管理者表示调查报道是在媒体中起决定作用的业务,仍将在美国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受访者中持有“媒介组织并未给予充分资源来支持调查记者”这一观点者占47%,例如未能支付合理的薪酬和调查活动经费等[24]。在美国调查记者个人薪酬水平上,美国职业资源网站Zippia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该国调查记者的平均年薪为53881美元[25],而2019年美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65850美元[26]。美国调查记者群体中薪酬最低的10%的人员年收入约为35000美元,而最高的10%的人员则为80000美元。在大多数情况下,所属媒体的地理位置对薪酬水平起到关键影响作用,位于纽约、新泽西州、马萨诸塞州、路易斯安那州和阿拉斯加州的调查记者拥有较高的工资[27]。
由此看来,美国调查记者似乎也得不到足够的经济支撑,但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悲观。余坪和余婷研究了“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ProPublica以及“伯克利调查报道中心”(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in Berkeley)等新兴机构的调查报道运作,得出“数字新闻媒体及非营利性新闻机构引领着调查报道迈入新生”的结论[28]。这些机构通常由企业家或慈善机构资助,从传统新闻媒体挖来具有资深调查报道经历并痴迷于产出高品质内容的媒体人以执行特定业务。目前,一些机构已成为新型调查报道的先锋,如ProPublica在2019年和2020年获得多项“普利策新闻奖”。2021年2月,ProPublica发布了一则招聘信息,为全职调查记者开出年薪75000美元外加福利津贴的待遇条件[29],相较于53881美元的美国调查记者群体的平均年薪[30],ProPublica的招聘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该机构创始人施泰格(Paul Steiger)曾透露,ProPublica每篇调查报道的资金花费通常在20万~50万美元,以确保调查工作能够顺利开展,有的调查甚至会耗时3年[31]。除了“桑德勒基金会”(the Sandler Foundation)捐赠的1000万美元外,ProPublica还有多种资金来源:一是网站使用者的自愿捐助;二是通过为《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今日美国》(USA Today)、《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等主流媒体提供调查报道来源或协作进行调查以获取资金;三是提供新闻培训、制作新闻报道电子书及出售数据集等衍生产品。
此外,美国一些调查记者采取了项目制的远程调查方式,有临时调查需求的雇佣者可以在美国招聘网站Upwork上发布项目并与这些调查记者进行合作[32],这些调查记者的薪酬按小时支付,且雇佣者可以看到他们的市场评分及当前所接项目数量等信息以供选择。由此可见,新媒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远程调查合作的开展提供了便利,亦拓宽了调查记者的谋生路径。
(二)法律风险与人身危险
作为新闻业的一个特殊工种,调查记者所面临的职业风险会大于一般记者。概而言之,中国调查记者开展调查报道存在更大的法律风险,而美国同行面临的生命危险更甚。
通过对相关法律条文的爬梳分析,周福志指出,“单纯从法条角度而言,……我国当前保护记者权益的发展进程已有很大进步”[33],不过现有相关法规存在“约束性条款多,保护性条款少”[34]、“打击力度欠缺,救济效果较差”[35]等问题。聂芊芊指出,数字化时代中,调查报道的原创性难以保障[36]。这一问题,近年来在自媒体公众号“呦呦鹿鸣”与记者王和岩的“洗稿”之争等事件中已多有体现[37]。尽管2021年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针对民事主体人格权的抗辩方面为保护记者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譬如记者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第八条、第一百三十二条所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抗辩与“不可滥用民事权利”抗辩开展调查报道,但整体而言仍是约束性条例多于保护性规定[38],且并未对调查稿件被“洗稿”的问题提出有效解决方式。相比而言,美国同行虽然也会在某些时刻面临法律风险,但整体而言相对“安全”,从“曾格案”到“纽约时报诉莎利文案”,美国已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法律来保护记者的报道权与知识产权,譬如《阳光下的政府法》(Government in the Sunshine Act,简称“GSA”)、《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简称“FOIA”)等。
近年来,我国调查记者遭遇口头威胁甚至人身攻击的事件时有发生,例如,2017年陕西广播电视台记者在调查医院“天价停尸费”事件时被打;2020年,多家媒体记者采访“原阳儿童被埋”事件遭殴打等。除了来自调查对象不配合而招致的人身安全威胁,也需要警惕借着“接受贿赂”名义而“抓记者”的类似案件背后所隐含的信息。周泽在对“太原检察官抓记者”“西丰警察抓记者”等案件进行法理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这些案件均将反映问题的爆料人与记者一同抓去,试图在无形中掩盖调查记者原本所采访的社会问题,舆论监督正受到一些黑恶腐败势力的制度化抵制与反击[39]。
受“看门狗”新闻理念的深刻影响,美国记者格外留意社会黑暗现象。再加上受到美国由《纽约时报》、CNN等私营传媒来完成新闻国际传播的体制及文化帝国自我认知的影响,美国调查记者执着于前往存在严重腐败现象、战乱、动荡或专制集权的国家进行报道,这会提高他们发生意外事故的概率。他们面临的安全威胁不仅来自国内,还来自国际报道引发的风险。美国调查记者面临的人身危险,特别是在海外进行调查采访的国际新闻记者及战地记者,近年来引发了广泛关注。例如,2012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简称“CBS”)的调查记者洛根(Lara Logan)在开罗采访时遭到暴徒殴打和性侵;知名战地记者科尔温(Mary Colvin)在报道斯里兰卡内战时失去了一只眼睛,11年后在叙利亚采访时遭炮击身亡等。“全球调查新闻网”(Glob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Network,简称“GIJN”)的数据显示,自1992年以来,全球遇难记者人数超过1370人,其中有800多位被谋杀,而凶手未被绳之以法。杀戮仅是冰山一角,调查记者还面临着来自恐怖袭击、贩毒团伙等方面的威胁[40]。针对调查记者的人身安全问题,一些国际机构积极参与援助,不仅编写了《高危环境记者手册》(A handbook for reporters in high-risk environments)、《女记者安全手册》(Safety Handbook for Women Journalists)、《为记者提供安全报道抗议活动的23条指导方针》(23 guidelines for journalists to safely cover protests)等各类保护这一群体人身安全的指南,还成立了新闻安全小组,譬如纽约“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简称“CPJ”)实行了新闻从业者援助计划,为面临危险的记者提供法律、医疗和安置方面的帮助,并为被杀害和被监禁的新闻记者的家属提供支持。
(三)从业心理与职业认同
对于调查记者这个充满理想主义的群体来说,行业态势、收入水平、职业风险等外部因素固然重要,但专业理念认同感、工作满意度等内在要素同样不容忽视。在当前的行业生态下,调查记者矛盾交织、进退失据的从业心理值得关注。
程赛博将新一代调查记者的择业动机归结为三种:强调监督与启蒙作用的“倡导”驱动、追求名利与尊严的“功利”驱动、出于喜欢与热爱的“兴趣”驱动[41]。这三种择业想象符合“黄金时代”延续至今的专业认同感。曹艳辉的新近调查表明,在坚守理由的言说中,推动社会进步、调查事件真相等“理想情怀”的话语建构最为生动丰富,这反映出调查记者的从业动机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理想主义是职业认同的源头与初衷。曹艳辉发现,愈发密切的信息共享、相互鼓励等同行间的守望相助现象,形成了一种“同行共议合法性”,这有助于加强调查记者的角色认同感[42]。在对自身角色认知的层面上,张志安、曹艳辉基于两次全国性调查数据,开展了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舆论的监督者、环境的监测者这两种定位仍然得到现今我国调查记者的重视,尤其是对因“理想情怀”而入职的调查记者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下一方面愈发强调“党媒姓党”,另一方面,新闻媒体面临营利危机的背景之下,我国调查记者愈发偏向将自身角色定位为政策的解释者,不仅是文人论政与“党的喉舌”传统之延续,亦有努力获取拥有政策支持的话语资源及重申自身合法性之意味[43]。
然而,“理想情怀”和“专业理念认同感”的延续与强化,并不意味着这一群体工作满意度的提升。聂芊芊访谈了12位2010年以后入行的调查记者,结果发现,新一代调查记者职业满意度较于前辈调查记者呈下降趋势[44]。在当前的媒体生态下,调查记者的身份焦虑和职业担忧等心理问题值得关注。张志安团队发现,36.8%的受访者对于能否继续坚守岗位存在疑虑,43.6%的受访者明确表示5年内不再从事调查报道,这个群体职业忠诚度通常较低,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45]。曹艳辉、张志安的最新研究表明,中国调查记者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认同感显著下降,归根到底,既有优秀调查记者前辈转行而新人缺乏扎实的采访突破能力,也有数字时代新闻生产职业边界愈发模糊的因素,致使调查记者群体呈现出对自身职业声望评价降低的变迁趋势[46]。由此,一方面是激昂的理想情怀,另一方面是低迷的职业状态,显示出中国调查记者颇为矛盾的心理结构。
美国调查记者的择业动机同样离不开理想情怀。卡普兰(Andrew Kaplan)访谈了281名美国调查记者,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比起外部的金钱或奖励刺激,从事调查报道能推动社会变革是他们从业的最大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们仍然饱含工作激情,但大多怀念过去那种更易于展开调查的行业生态[47]。在职业现状评价方面,拉诺斯格(Gerry Lanosga)等人开展的对861名以美国调查记者为主的研究,得出相对乐观的结论:虽然有些调查记者流露出悲观的情绪,但是大多数受访者仍然具有较高的工作满意度及工作自主性,其调查报道资源并未显著减少,并且流向非营利新闻机构的调查记者对他们的职业现状有了更积极的评价[48]。
三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从中美比较的视野,描述和分析了两国调查记者的生存现状。总体而言,新兴媒体在导致两国传统媒体调查报道团队成为裁员和人才流失“重灾区”的同时,又以另一种方式吸纳了更多适应新媒介环境的人才。在收入方面,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已是普遍现象,中国调查记者面临机构投入缩减、个体收入水平不容乐观的境况,但新媒体平台的直接打赏和间接的流量变现使得优质调查稿件存在获益的可能性;美国主流媒体也减少了对调查记者的资金支持,但新媒介机构与非营利性新闻机构给这一群体带来了新的机会。在风险方面,中国调查记者面临的法律风险更甚,而美国同行面临的人身危险更大。在从业心理方面,两国调查记者同样矛盾交织,都在承受理想和现实的落差。
由前文可知,中美调查记者的生存现状并不乐观,但也并非灰暗一片,一些新的探索给这个群体的未来发展带来了些许曙光。美国新闻界近年尝试了众筹新闻模式,围绕明确的选题,吸引社会资金支持深度新闻调查和报道,同时对资助额度设限,以保证报道的独立性。一些新兴机构还采取了与各区域本地媒体合作的方式,扩大调查报道网络,实现资源共享。ProPublica的最新年报显示,2020年,该机构为增强本地调查报道网络,宣布了一项长期的杰出研究员计划———本地记者可以通过在家开展调查项目的形式与ProPubclica合作三年以上[49]。
此外,在商业媒体机构效益低迷的情况下,不少美国高校成立了专门的新闻调查中心,依托学校资源开展调查报道,譬如布兰迪斯大学的“舒斯特新闻调查中心”(Schuster Institute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Brandeis University),以及波士顿大学的“新英格兰调查报道中心”(New England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Boston University)。此种以高校为主的培养模式在我国亦有所尝试: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调查性报道国际工作坊;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引入业界调查记者与学界教师共同讲授调查报道相关内容。在中国近几年的社会性公共事件报道中,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的校园媒体亦有不俗表现,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南京大学学生记者的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关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大众化写作浪潮为校园媒体、学生记者带来了一些“出圈”的机遇,对于某些重大新闻题材,学生记者有可能从独特的角度切入,经过不计成本的高强度智识劳动——这是市场化新闻媒体机构所不具备的条件,从而作出高水准的调查和写作,并在内容市场一试身手。
“丁香医生”这样的垂直领域自媒体的蓬勃发展,也给调查记者带来一定启发。例如对真相的追问、对专业领域的积累,以及对证据的把握等职业素养仍然是高质量深度调查的前提,但在新的媒介环境下要想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和经济收益,调查记者应当加强报道形式的创新,提高捕捉热点、制作爆款和议程设置的能力[50]。对于媒体机构而言,应进行薪酬制度、生产流程、运作机制等改革创新,同时加强自身知识产权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