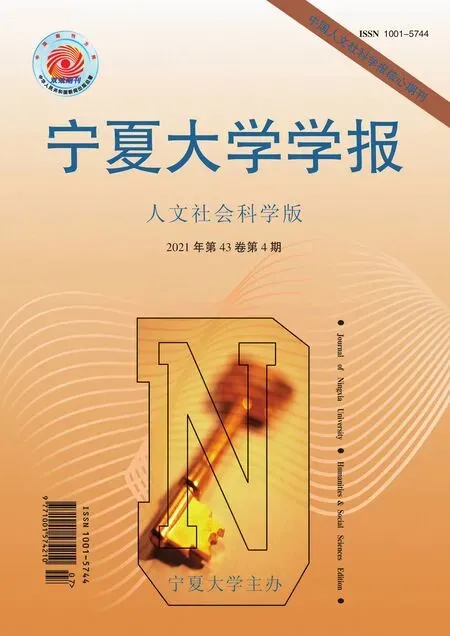河南鹿邑方言的“可”
2021-12-23王战领
王战领
(上海师范大学 语言研究所,上海 200234)
鹿邑县位于河南省东部、豫皖交界处。北靠柘城县与商丘市睢阳区,西接淮阳县,南望郸城县,东临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河南境内的中原官话,按其内部的语音差异可以分为6个片区,其中鹿邑方言属于郑汴片。
汉语方言中的“可”语音形式复杂,语法功能多样,常为学者们关注。不同方言地区其用法虽有交集,但也不乏独特之处。从地域分布来看,中原官话区“可”最显著的用法就是作为疑问副词,和谓词性成分一起组成“可VP”结构,形成所谓的“反复问句”,相关讨论见徐杰、张媛媛(2011)[1]等;晋语区的副词“可”除一般表强调、转折等语义外,还能表示状况的轻量和程度逆转,见张国微(2010)[2]等。
以往学者对某一方言中“可”的句法功能进行全面描写时,多以语音为纲,如赵雪伶、沈力、冯良珍(2018)[3]等。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对鹿邑方言来说并不是好的选择。因为,由于语法化过程中的历史层次差异,以及共时层面的连读变调等原因,鹿邑话中的“可”在韵母和声调上共表现出五种组合情形:(据 《河南省志·方言志》,鹿邑话的四声调值分别为:阴平24、阳平42、上声55、去声31[4])。若以语音为纲对它进行拆分,非但无法使其句法特征更加简明,反而会扰乱其不同用法之间的界限,也不利于通过语义之间的联系来梳理相关语法化过程。
因此,本文准备以用法为线索,详述鹿邑方言“可”的各种句法和表意功能,并在必要时进行跨方言之间的比较,以便突出其在本方言中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文章也尝试探寻其若干语法化路径。
一 “可”的用法和功能
(一)构词语素“可”[kh 55]
“可”在鹿邑话固有词汇中充当构词语素的情况不多,较常见的有“可怜”“可莫”“可莫可”等,然而在这些词中,其表意并不一致。具体如下。
1.可怜[kh55lian0]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可怜”的解释是:(形)值得怜悯[5]。显而易见,“可”就是“值得”的意思。在鹿邑话中“可怜”多作动词用,“可”同样表示“值得”。例如:
(1)她没爹没娘,谁不可怜她你说说。
(2)我也没钱,谁可怜可怜我啊!
(3)这妮儿嘞脸冻嘞可怜人。这姑娘的脸冻得可怜人。
(4)到最后他一啥也没落,怪可怜嘞。到最后他什么都没得到,挺可怜的。
2.可莫[kh55mo0]
“可莫”表示“大概、可能”或“应该”,是对事物数量或空间范围的估测。其中“莫”读轻声,主要义项由“可”来承担。例如:
(5)这袋子面可莫二十斤。这袋儿面粉大概二十斤。
(6)这棵树可莫喽有两米五。这棵树可能有两米五。
(7)我到嘞时候可莫十二点了光。我到的时候应该是十二点的样子。
(8)那个男嘞看喽可莫三十出头。那个男的看着大概三十出头。
古汉语中的“可”就有相关用法,且句法上也是直接修饰数量短语,这表明鹿邑方言的“可莫”与通语同出一源。例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柳宗元·小石潭记)
粲乃驱男女小大仰一大铜钟,可二百石,煮人肉以喂贼。(朝野佥载卷二)
李小平(2020)指出,晋语临县话“有可1[i312-24kh312-21](有可能,也许)“”两可[1li312-24kh312]”等,双音节词中的“可1”是表示“可能”的意思,例如[6]:
我明儿有可 [1i312-24kh312-21]城里去,有捎的咾说甚。我明天有可能去城里去,有捎的话吭声。
去不去还两可[1li312-24kh312]着嘞嚜,看把你乐的。去不去还两可着呢嘛,看把你高兴的!
据上两例,临县话中的“可1”虽然表示“可能”,看似和鹿邑话“可莫”中的“可”表意相近,但差异还比较明显:前者是对事件发生概率的推测,与普通话“可能”接近;而后者只能估算事物的数量范围,更像是对古汉语义的继承。
3.可莫可[kh55mo0kh55]
“可莫可”的意思是“刚刚、正好”,它与“可莫”在形式上是上下位的组合关系,在表意上也是用来修饰限定事物的量,只不过是一种精确的判定。例如:
(9)这袋子面可莫可二十斤。这袋儿面粉刚刚二十斤。
(10)今年打嘞粮食可莫可装两车。今年打的粮食正好装两车。
(11)清早带嘞种子可莫可够使嘞。早上带的种子刚刚好够用。
我们仍然认为,“可莫可”中的“可”跟“可莫”的“可”是同一构词语素,其所构词的词义之所以会出现偏差,显然是由不同的词汇形式造成的。可以推想,就像普通话中“不得不”的双重否定原理一样,如果一个“可”是表示“估测”,那么两个“可”的重复也许就表示“精测”。
(二)动词“可”[kh 42]
鹿邑话中“,可”作谓语动词时表示“与…(大小)相适”义,它对所管辖宾语的语义范围要求较窄,基本上只能是表示身体部位的单音节名词,例如:
(12)你看这衣裳多可身儿。你看这衣裳多合身。
(13)这双鞋穿喽怪可脚嘞。这双鞋穿着很合脚。
(14)衣裳可不可身儿你自己不知道蒙?衣裳合不合身你自己不知道吗?
共通语中的“可”也有“可口”“可人意”“这回倒可了他的心了”等动词用法。和鹿邑话相比,两者在语义上存在细微差别:鹿邑话的“可”仅仅表示具体物品在形状、大小方面的“两两相适”,而不能表示“心意”等抽象概念上的“相符”。这也是能与其搭配的宾语较少的原因。
在很多情况下,语言接触会导致语言改变。也许,鹿邑方言“可”的动词用法在不久之前还比较活跃,只是由于受到普通话的影响才逐渐减弱或消退。另外地域因素的影响也是存在的,宗守云(2013)就指出,张家口处于晋语的边缘地区,和中心地区晋语相比,表逆转否定的轻量程度副词“可”,其用法已经减少了很多[7]。
(三)助动词“可”[kh 55]
按朱德熙(1982),助动词是真谓宾动词里的一类。包括:“能、能够、会、可以、可能、得、要……值得”等[8]。谓宾动词也就是带谓词性宾语。鹿邑话的助动词“可”的确带谓词性宾语,且往往是单音节动词,表示“能”或“值得”的意思。例如:
(15)明个聚会我没啥可穿嘞,你说咋弄?明天聚会我没有什么能穿的,你说怎么办?
(16)他一点都不可说,一说斗哭。他一点都不能被说道,一说就哭。
(17)电影怪多,斗是没啥可看嘞。电影挺多的,就是没有值得看的。
(18)我跟他没啥可说嘞。我跟他没什么值得说的了。
据词典解释,共通语中的助动词“可”还能表示“许可”,比如“可见”。这一用法明显是从古代汉语表“许可”义的动词“可”演变而来的,例如:
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春秋·孙子》)
左右谏曰:夫以一都买一胥靡,可乎?(《资治通鉴》)
对于此义项,鹿邑方言一般用另一助动词“管”来表达。例如:
(19)他现在有传染病,你不管见他。他现在得了传染病,你不可以见他。
(20)我现在腿疼嘞厉害,晃儿可管不去了?我现在腿疼得厉害,下午可以不去了吗?
——管!可以!
朱先生在对其所列助动词的句法特点进行归纳时提到一条:可以单说。比较之后我们发现,鹿邑话的助动词“可”却不能单说,而“管”能。但这并不使我们怀疑“可”作助动词的正当性,只是应当注意,即便是一个数量较小的封闭性词类,其成员间也可能存在细微差异。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助动词“可”常常与否定副词短语“没啥”共现,构成“没啥+可V+嘞”构式,表达与否定相关的评价意义。例如:
(21)我跟他没啥可说嘞。我跟他没什么值得说的。
(22)这块地坑坑洼洼嘞,没啥可种嘞。这块地坑坑洼洼,不值得种。
此构式在鹿邑话中使用频率很高,而且就算没有否定副词,“有啥+可V+嘞”在疑问句中依然表达否定意义。例如:
(23)你还在这儿干嘛?还有啥可说嘞?你别在这儿了,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
“没/有啥可V嘞”构式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我们知道,“主观性”(subjectivity)就是说话人在话语中的“自我”表现成分,即说话人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9]。“没/有啥可V嘞”的主观性是由助动词“可”的主观化导致的。因为它所表达的“值得、能”义,本身就是说话人对某一事物的主观评价。试比较:
(24)a.这一桌子菜没啥可吃嘞。
b.这一桌子菜没啥能吃嘞。
前者是说,这些菜做得没问题,但是我却觉得不好吃,这是我个人原因造成的;后者的意思是,这些菜本身就有问题,可能看上去已经馊了,吃了对人有害,这是一种客观事实。以上就是鹿邑话助动词“可”的基本用法。
(四)介词“可”[kh55]
“可”的介词用法在中原官话区较为常见,如项城方言(韩金广,2015)[10]等。鹿邑方言中的“可”作介词使用时,一般要带上助词“喽”,表达“充分按照……(空间、大小、范围等)来……”的意思;句法功能就是与所辖宾语构成介宾小句,前置于谓语动词,以说明其活动的范围。例如:
(25)这些麦你可喽屋子垛哎,跺满为止。这些麦子你按着屋子大小来跺,跺满为止。
(26)你看他吃饭,可喽嘴填。你看他吃饭,嘴巴能塞多少就塞多少。
(27)这地你可喽一晌午夯,夯多少算多少。这块地你按一上午的时间来夯,夯多少算多少。
(28)这趟去你可喽三千块钱步蹬,步蹬完就没有了。这趟去你就按三千块钱来花,花完就没有了。
据赵雪伶、沈力、冯良珍(2018),霍州方言中“可”表示“满/全(NP[范围])”或在某范围NP内“到处”义,其用法主要是后接名词性成分,为谓语引介活动范围。如:
他可世界哩寻你咧。他满世界地找你呢。
文章还指出,在实际语言表达中,为了强调主要谓语的活动范围,有时表人的主语成分可以省略,由话题化后的处所格作主语。例如:
霍州城里可处都是卖烧饼哩。霍州城里到处都是卖烧饼的。
语言通过比较才能显示自身特点。同属中原官话的两种方言,虽然介词“可”的表意功能十分相近,都是规定谓语动词的活动范围,但在句法上却有差别,跟霍州方言相比,鹿邑话的介词“可”必须跟助词“喽”共现,构成双音节前置词。同时,其所辖宾语的类别相对宽泛,可以是地点名词、时间名词,以及带数量短语限定的不可数名词,但这些名词都必须表示具体空间或数量范围,如屋子、嘴巴、上午、三千块钱等,而不能像霍州方言那样,引介像“世界”“处”等没有限定的抽象名词。
至于必须同“喽”共现,我们认为,这是“可”正从动词语法化为介词的伴随现象。我们说“喽”是助动词,常常跟在动词后面,相当于普通话的“着”,如“吃喽饭嘞吃着饭呢”“干喽活儿嘞干着活呢”;也用在介词后边,如“按喽他说嘞干按照他说的做”“照喽脸打朝着脸打”等,这是因为很多介词都是由动词语法化而来。在鹿邑话里,“按”“照”等词的动词用法依然显著,如“按喽他嘞头按着他的头”“照喽他嘞脸照着他的脸”,只是因为其出现在了前置小句的介词位置,才把它们看作介词,而这“重新分析”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语法化的过程。但由于它们还未演变为纯粹的介词,所以无法摆脱助词“喽”的依附。而语言类推作用使“可”沿用了同样的语法化路径,只不过其动词用法消失得更快罢了。
(五)副词“可”[kh24][/khei24]
在鹿邑方言中,“可”用作副词远比其他词类频率高得多。作为副词,其在句中主要表达“强调”“释然”以及“反诘”“疑问”等语气。
虽然语义上是表达各种语气,但是其性质应该得到进一步明确。张谊生(2014)把“可”划分为评注性副词,认为它们“同典型的副词在句法功能和表意功能上等各方面都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并解释道,评注性副词“主要是表示说话者对事件、命题的主观评价和态度”[11]。我们同意张先生的看法,把表示“强调”“释然”语气的副词“可”当作评注性副词。另一方面,“可”的反诘或疑问功能无论在古汉语还是现代汉语各方言中都有存在,江蓝生(1990)因此把它叫作疑问副词[12]。这里,我们不妨也把鹿邑话中表示“反诘”“疑问”语气的副词“可”看作疑问副词。更何况,两者在语音上的差别正与此相对应。
具体来看,副词“可”的两种不同发音主要表现在韵母上。从音韵角度看,“可”中古是果摄歌韵开口一等上声字。歌韵的字,在现代鹿邑话中共有三个读音,即“-uo(多,拖)/-a(哪,阿)/-(歌,蛾)”,只有疑问副词“可”的韵母是“-ei”,整个果摄也再无类似读音。这使我们无法相信“可”读[khei24]是古音的历史层次问题。汪化云、李倩(2013)指出,河南固始方言的疑问副词“可”,在询问主观意愿的“可1VP”结构中读作[kh35],在询问客观事实的“可2VP”中却读作[khei214],作者认为,后者的语音变化实质上是“可”与“没”合音的结果[13]。鹿邑话的“可VP”疑问结构是用来询问主观意愿的,我们怀疑“可”的[khei24]音是“可”与“不”的合音,过程大概是“khb u t→kh i→khei”(“不”的音值参照王力先生的拟音系统)。毕竟北方方言确实存在“可不VP”用于询问听话人的主观意愿,如山东牟平话(罗福腾,1981)[14]。不过这只是一种猜测,需要更多证据进行论证,这里则不作过多讨论。
1.评注性副词“可”[kh24]
前面说过,评注性副词主要是表示说话者对事件、命题的主观评价和态度。“可”在作评注性副词时,主要表示“强调”“释然”等语气。另外,在特定的语境下还能衍生出“讽刺”语气。具体如下。
表“强调”语气时,说话人出于感叹某事实现的效果,或对某人进行主观评价,有“真的”的意思。例如:
(29)你说嘞可教我笑死了!你说的真的把我笑死了!
(30)这活儿可教我累死了!这活儿真的把我累死了!
(31)他这回可气死我了!他这回真的把我气死了!
(32)你别不信他,他可黏贤了!你别不相信,他真的很有能力。
表“释然”语气时,主要是对事情结果的评价。有“终于”的意思。正如《国语辞典》对“释然”的解释:因疑虑、嫌隙等冰释而放心。例如:
(33)房子可盖好了,再也不怕漏水了。房子终于盖好了,再也不怕漏雨了。
(34)哎呦我嘞老天爷哎,我可找着你了。哎呦我的老天爷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5)你可回来了,小孩都想你想嘞哇哇叫。你终于回来了,小孩都想你想得哇哇叫。
(36)你可算明白我嘞意思了。你终于明白我的意思了。
在“强调”语气的基础上,“可”还能在特定语境中衍生“讽刺”语气,例如:
(37)你可真精,谁也没有你精。你可真精明,谁也没有你精明。
(38)你可真能,能过头了都。你可真有能耐,有能耐过头了。
事实上,以上所列的“可”的三种语气,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比较下面三例:
(39)a.你可白不回来啊!你可别不回来啊!
b.你可回来了,我都不知道该咋弄了!你终于回来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c.你可回来了,不回来家里也没恁些事!你可回来了,不回来家里也没那么多事!
按照我们的归纳,上述三例的“可”分别表示“强调”“释然”和“反讽”语气,但是仔细揣摩就会发现,三句其实都是强调句,只不过强调的方面不同:a句强调的是“说话人的主观意向”;b句强调的是“事件实现的效果”;c句强调的是“说话人对行为结果的不满”。我们认为,后两种语气是由第一种语气在特定语境下“激发”出来的。从形式上也能看出,三例句中前一句为单句,后两例却为复句,而复句的后半句正是激发“可”的“释然”或“讽刺”的语境,若非如此,其各自就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话轮,也不能在语义上相互区分开来。所以,我们应该看清各种语气背后的本质联系,这样才能对“可”表意的多功能性作出合理解释。
齐春红(2006)把现代汉语副词“可”归为语气副词,认为其除了在感叹句或陈述句中表强调、在一定语境中有释然的口气之外,还能够[15]:用在祈使句中,表示祈使语气。
这把子你年纪了,你可别去干歪门邪道!(莫言《师傅越来越幽默》)
当上下文有转折语境时,“可”表转折语气。
我可不是瓜呆儿!(陈忠实《地窖》)
“可”表示转折语气,用在句子开头时就是转折连词。
可我丈夫急也不摔贵重物品,你这是随意发挥。(王朔《顽主》)
从鹿邑方言“可”的用法来看,上述分类似乎有些不妥。我们知道,祈使句是为了要发出命令或请求,上例中,如果把“可”去掉,听话人仍然能够感受到说话人的命令语气。试比较:
(40)a.你可别去干歪门邪道!
b.你别去干歪门邪道!
两句话的祈使语气都是由否定副词“别”和整个句子的句调共同构成的,前句副词“可”的作用只是进一步“强调”其后的整个述题。另外,鹿邑方言中的“可”从来不用在句子开头充当连词,这跟方言口语缺少正式连词的特点有关。
2.疑问副词“可”[khei24]
根据江蓝生(1990),表示反诘的疑问副词“可1”在东汉时期就出现了,而表示推度询问语气的疑问副词“可2”最早见于唐五代的文献中。鹿邑话中的疑问副词“可”既能表示反诘语气,又能表示推度询问。
表“反诘”的例如:
(41)伤天害理嘞事咱可能做?伤天害理的事咱不能做。
(42)我都麻烦他多少回了,可好意思再去了?我都麻烦他多少回了,不好意思再去了。
(43)光吃不干活儿可管你说说。光吃不干是不行的。
表“推度询问”的例如:
(44)饭做好了,你可吃嘞?饭做好了,你现在吃吗?
(45)晃儿教剩下嘞那些活儿干完,可中?下午把剩下的那些活儿干完,行吗?
(46)你可知道谁家小孩今年考上大学了?你知不知道谁家孩子今年考上大学了?
(47)铁蛋儿娶嘞媳妇儿可漂亮哎?铁蛋儿娶的媳妇儿漂亮吗?
一般来说,“可”的“反诘”语气没有表示推度询问的使用频率高。从语用学的角度来讲,我们认为“可”表“反诘”语气属于一种间接语言行为。如例(41)至例(43)显示,说话人本来想表达否定的陈述命题,但是没有使用带否定副词“不”的陈述句,而是用“可VP”的疑问形式来间接地表达,这是语言形式和语言功能之间的不一致所带来的结果。它的使用多出于礼貌原则和修辞上的考虑(比如直接说“不”显得不礼貌,或者用反问表达陈述获得的语境效果更好)。“与直接语言相比较,间接语言既费力气又带有风险……对听话人来说,理解间接语言,脑子要多转一个或几个弯”[16]。也正因此,间接语言在日常口语中的使用频率没有直接语言高。
我们想重点讨论的是鹿邑话中表推度询问的“可”。我们知道,“可VP”一直被认为是汉语方言疑问句的核心结构之一,朱德熙(1999)曾指出,苏州话的“阿”问句、昆明话的“格”问句以及合肥话的“克”问句都是“可”问句的语音变体,它们无论在句法结构还是表意功能上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17]。朱先生把它们叫作反复问句,属于选择问句的一种。两者的区别在于:一般的选择问句要对方在X与Y里选择一项作为回答,反复问句则是让人在X还是非X里选择一项作为回答。
鹿邑方言的“可VP”问句毫无疑问属于此类,例如:
(48)你可是后个去上学?你是不是后天去上学?
(49)这西瓜可甜?这西瓜甜不甜?
(50)恁爸可好吸烟哎?你爸爸爱抽烟吗?
它还有一种变体形式,即“可”+“中/管/粘”置于陈述句之后,对前面整个命题进行确认,并以此承担整个句子的疑问焦点。有学者把这种问句形式叫作附加问。例如:
(51)a.你明天老老实实地给我下地干活,可中?
b.你看你胖成啥了,今个晚上的饭就别吃了,可管?
c.写完作业再玩游戏,可粘?
附加结构的功能和普通话的“好不好?”或“行不行?”一样。同时,“可中”“可管”“可粘”都能分别用“中吧”“管吧”“粘吧”来代替,回答如果是肯定的,用“中/管/粘”来表示,否定的则用“不中/不管/不粘”。
需要说明的是,“可VP”问在鹿邑方言的选择问句中具有显赫地位,是选择问句中的显赫范畴。显赫范畴是库藏类型学的核心概念。作为方言语法调查的两大对象之一,刘丹青(2013)指出,具有充分的语法手段表征其存在或扩展其语义语用用途的范畴就被称为显赫范畴。并解释道,同样作为入库范畴,因为语法手段的语法化程度不同、功能强弱不同,会造成该范畴在特定语种中的使用频度、在语义分布中的扩张度和母语人语言心理中的激活度或可及性的差异[18]。按此定义,“可VP”问句在鹿邑方言选择问句中就是一种显赫范畴,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使用频率和母语人语言心理激活度高。鹿邑方言的选择问句有多种表达方式,除“可”问句外还有其他形式,例如:
(52)a.新娘子可漂亮?
b.新娘子漂亮不漂亮?
c.新娘子是丑还是漂亮?
d.新娘丑美哎?
在询问“新娘子是否漂亮”这一情况时,虽然有以上几种问法,但说话人往往会选择第一种,这就说明“可VP”问句在鹿邑话中的心理激活度高,与之伴随的是使用频率也高。
就算不是询问X和非X的一般选择问时,“可”问句依然有较大的选择倾向。比如某块田地有同等机会种植小麦、大豆、棉花等作物(按照当地种植习惯),说话人在询问时往往还是会选择“可VP”的形式,如“这块地可种小麦?”此时听话人可以回答“嗯,种”,或者直接回答“不种,种大豆/棉花”,而往往不选择“这块地种小麦还是大豆哎?”,或“这块地种大豆棉花哎?”这样的问句形式。
二是语义分布范围的扩张。“可”问句还能够“非疑而问”,即形式上是反复问,语义上却在表达祈使义。发问者认为听话人该做某事了,进而以问句的形式进行提醒。例如:
(53)天都快下雨了,你还钻屋里看电视,场上嘞麦可收了?天要下雨,该收麦子了!
(54)这作恶嘞小偷可有人管管了欸?我嘞老天爷欸!真应该有人管管小偷的偷盗行为!
(55)你可能先别干嘞我嘞个爹啊!你应该先停一下!
这种祈使意义跟上文所提到的“反诘”语气应当分别对待。如文中所说,“反诘”语气的使用多出于礼貌原则和修辞上的考虑,大多情况下是对否定陈述句的替换,而这里的祈使意义则不同,其真实要表达的是说话人的诉求,是说话人要求听话人付诸某种行动。
至此,疑问副词“可”在鹿邑话中的表意特征已经详述完毕。
二 “可”的语法化
(一)一般路径
在早期的一些研究中,语法化被看作具有连续统的结构,也就是常说的语法化链。而多义模式作为语法化链的一个特征,便是语法化的典型产物之一。从目前多功能、多语义的使用情况来看,现代汉语虚词“可”经历了语法化已是不争的事实。
齐春红(2006)用历史文献论证了现代汉语“可”的语法化的一般路径。
可,《说文·可部》:“可,从口丂,丂亦声。”“可,肎(肯)也。”《广韵》:“可,许可也。”“可”的本义为“准许、许可”,作动词。如《史记·李斯列传》:“胡亥可其书。”“可”由许可义动词虚化为助动词,表示“可以、能够”,由许可义又引申为“应该、值得”。“可”的助动词义最早出现于西周金文,其用法在先秦已经非常成熟,一直沿用至今。
齐文进一步指出,表反问的“可”在凸显疑问意义的语境下引申为疑问语气副词,再引申为强调语气副词,再由强调语气副词在转折语境中引申为表转折的连词或带转折语气的副词。
我们同意上述观点,用历史文献资料来证明语法化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然而,方言有方言的特色,共通语中的某一用法在方言中不见得会有,比如“可”的连词用法在鹿邑话中就没有出现;反过来,方言中出现的用法,在共通语中也并不见得保留。比如“可”的介词用法。鹿邑话“可”的介词功能如何语法化而来,需要我们深入讨论。
(二)“可”从动词到介词
类型学和语法化研究显示,介词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常见的源头是动词、名词和副词[19]。我们认为,鹿邑方言的介词“可”正是由动词语法化而来。其语用动因是概念隐喻,机制是重新分析和类推。
海涅等(2018)指出,隐喻(范畴)转移构成语法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也就是说为了表达更“抽象的”功能,就得征用具体项,并给出了范畴抽象度链:人>物体>活动>空间>时间>质量,从左到右越来越抽象。隐喻过程就是用直接接近人类经验的概念,来表达不太接近人类经验的更抽象的概念[20]。
上文提到,鹿邑话的动词“可”表达“与……(大小)相适”义,而充当起宾语的实际只有某些身体部位名词,如“身儿”“脚”,亦即和非常具体的“人”的范畴相关;作介词时表达“充分按照……(空间、大小、范围等)来……”的意思,这显然是动词义的引申。
充当介词宾语的虽然有时还是身体部位名词,比如“嘴”“肚子”等,但实际上它们表示的已经是空间范畴了:“可喽嘴填”“可喽肚子吃”。更多情况下,“可”是和属于更抽象范畴的名词进行搭配,比如表空间的“屋子”、表时间的“晌午”,甚至与质量有关的“三千块钱”等。这就是“可”从具体范畴到抽象范畴的概念隐喻,也是其语法化的重要动力。
当然,语法化过程在形式上的表现就是结构的“重新分析”。先看下边两例:
(56)a.这活儿你想教我干多长时间欸?
——斗可喽一个月吧,到时间就走。
b.这活儿斗可喽一个月干,干完就走。
例(56)a中,后边只有一个NP作宾语的情况下,“可喽”似乎既能被分析成谓语动词,又能被分析成复合介词,这是词类发生语法化时经常出现的“潜在的歧义性”;但是到了例(56)b,其被分析成介词已经没什么问题了,因为功能上是为后边动词引介时间范围的。
另一方面,语言的类推作用使“可”对“朝”“按”“照”等的介词用法进行效仿,例如:
(57)朝喽南边撂。
照喽靶子打。
可喽场子堆。
一旦进入“X喽N地点V”的格式里,“可”也便具备了介词功能。
在本质上,重新分析沿着线性成分结构的“横向组合”轴在起作用,与之相对,类推是沿着在任何一个构成成分的节点上选择的“聚纵合”轴在起作用[21]。它们都涉及语法化过程中的结构创新。关于鹿邑方言介词“可”的语法化过程,我们暂时讨论到这里。
三 结语
副词“可”是现代汉语语法老生常谈的对象,原因不外乎其重要的语法地位:作为常用副词之一,它语义功能多样,能产性强,但在各方言中的表现又不完全一致。据笔者了解,晋语中的“可”不表疑问,只表示强调和轻量;云南富宁方言中存在疑问副词“可”的语音变体“噶”[ka33],却没有像共通语中那样的强调语气功能。
整体来看,鹿邑话中“可”的方言特色表现为:作构词语素时,其在“可莫”“可莫可”等词中的义项,与古汉语中的“大约”义一脉相承;作动词时,它直接支配身体部位名词,表示主宾语的“(大小)相适”;作介词时,它常常同“喽”共现,与空间、时间名词构成前置介宾小句,来说明谓语动词的活动范围;而作为疑问副词,其组成的“可VP”反复问句在鹿邑话的疑问句中处于显赫地位。这些都是研究者值得注意的方面。
无论如何,对某一具体方言语法现象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更多的角度、更宽阔的视野来揭示共通语的演变规律,也为描写人类语言的共性提供有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