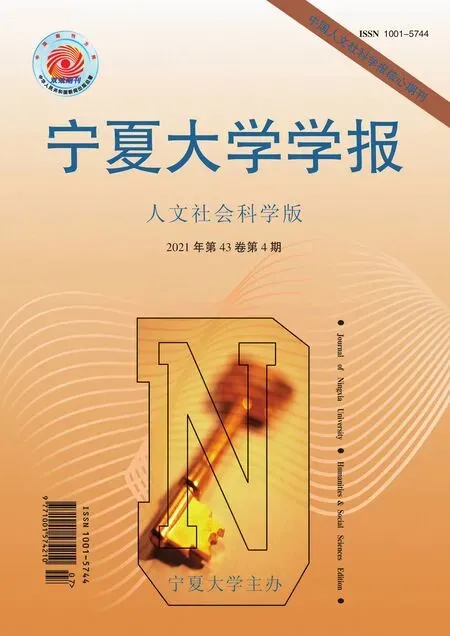自我与他者的伦理关系重构
——帕特·巴克《双重视域》中“为他者”的表征伦理观
2021-12-23霍甜甜
霍甜甜
(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2)
帕特·巴克(Pat Barker,1943—)是当代英国著名小说家,迄今为止已出版14部小说,20世纪90年代她凭借历史小说《重生三部曲》(Regeneration Trilogy,1991—1995)蜚声欧美文坛,并于1995年获得布克奖。《双重视域》(Double V ision,2003)是巴克的第10部小说,既延续了她对世界范围内暴力问题的关注,又在主题上有所突破和偏重。正如巴克在布兰宁甘(John Brannigan)的访谈中所言,《双重视域》的主题是“表征伦理(the ethics of representation)”[1]。那么,什么是表征伦理,小说又传递出对表征/伦理的何种思考?此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利用列维纳斯的他者思想,围绕表征与伦理的关系、伦理表征的两种形式“尊重他者”和“自我承担对他者的责任”进行阐释“为他者”的表征伦理观。
一 表征与伦理
“表征”(representation,另一种译法为“再现”)的概念有多重意涵。《牛津简明英语词典》的释义是“对人或物进行描述的动作或实例;意象、模型,或其他对人或物的描述;针对当局所做的、用以传递某种观点或提出某种抗议的陈述”[2]。作为动词,它的基本意思是“用某种媒介再次呈现事物的形态”[3]。学者周宪指出,“表征的要旨实际上是对实在世界与其符号呈现的某种关系的规定,即以语言、象征或符号来再次呈现经验世界中的实在——人、物或事件等,它是特定语境中的某种‘表意实践’”[4]。由此可见,文学、艺术、视觉表象等均属于表征。
表征作为一种表意实践,对客观现实再现的过程并非是“镜子式”的精准再现,而是充满了创变与重构。换言之,表征的主体再现客体的过程也是一个意义建构的过程,客体被构建成什么样的形象、又以何种形象被展示,在一定程度上与表征主体的主观意愿有关。如此,将不可避免涉及表征主体与被表征客体之间的关系。而当被表征对象是人时,则直接关系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关系。
作为表征主体的“自我”与表征对象的“他者”如何才是一种“伦理的”关系?这正是巴克在《双重视域》中要探讨的主题。一些思想家已经就相关问题有过深刻论述。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权力理论关注到“作为表征体系的话语”[5],认为表征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充斥着权力的运作。稍作引申,可以说表征主体与对象之间处于复杂的权力场域之中。赛义德(Edward Said)在《东方学》(Orientalism)中揭露了西方学者对东方“他者”的“半神话式的建构”[6]。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在《属下可以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中揭示了表征主体对客体的“知识暴力”(epistemic violence),指出作为没有权力的人群和阶级的“属下”(subaltern)只能“被代表”而不能“言说自己”[7]。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在《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Outlaw Culture:Resisting Representation)中批评对黑人社会的“表征权”历来掌握在白人和黑人精英阶层这些特权阶层人士手里,导致底层黑人的形象被歪曲[8]。这几位批评家都关注到表征的主客体间因权力不对等而导致的对他者的(刻意的或出于政治无意识的)扭曲甚至抹除。换言之,“表征的权力”导致了某种可称为“表征暴力”的“非伦理表征”。
表征的主客体不平等关系是否有逆转的可能呢?或者说,是否存在重新想象另外一种“伦理表征”的替代方案呢?法国当代思想家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提出的“他者伦理”(Ethics of the Other)学说对于我们思考这一问题具有借鉴意义。列维纳斯将暴力的根源追究到西方的同一性哲学之中。他认为,西方意识哲学和存在论本质上都是强调同一而排斥差异,以自我否定他者。这种宣扬自我中心的“自我学”内在地包含了自我对他者的暴力。形而上学中的“自我学”落实到社会政治实践中,将必然导致暴力、战争等人类灾难。对此,列维纳斯颠覆性地提出了“他者伦理”,强调自我要承认差异,尊重他者,担负对他者的绝对责任,以重构自我与他者的道德关系。他给伦理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由他人的出场所造成的对我的自发性的质疑,称为伦理”[9],“他者伦理”主张打破主体中心,导向为他者的人道主义。从“他者伦理”重审表征的主客体关系,可以得到的启示是,表征主体若能跳出自我中心的藩篱,从他者立场审视表征的意义,则有助于消解表征暴力,从而达成一种“伦理表征”。
小说《双重视域》对表征伦理的思考暗合了列维纳斯倡导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不是主客体二元对立,而是一种伦理关系”。小说主张的伦理表征不是主体无动于衷地对客体的再现,而是主体尊重他者独立存在,体会他者苦难,临近、倾听和回应他者,承担起对他者的责任的表征。需要提及的是,小说中所讨论的“他者”主要是指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
二 尊重他者
面对受暴力侵害的弱小者,他们脆弱不安的面容应该以何种方式被再现?《双重视域》以19世纪的西班牙画家戈雅(Francisco Goya,1746—1828)与虚构的战地摄影师本及小说家彼得为例,呈现出尊重他者和排斥他者两种对立的表征方式,巴克在对两者的刻画中流露出她的认同与批判。他者伦理始于对主体同一性的批判。列维纳斯批评,主体的自我总是持有“一种普遍综合的企图,力求把所有的经验,所有合理的东西都还原为一个总体”[10]。这种主体同一化具体表现为,“主体通过置入一个对存在的理解进行确保的中间项和中立项而把他者还原为同一”[11]。为对抗主体的霸权、消解主体对他者的同一性暴力,列维纳斯强调他者的绝对异质性、不能被主体整合的他性。他者伦理学要求自我必须以承认、尊重他者的独立存在为基本伦理律令。
小说中多次提及的蚀刻版画《战争的灾难》(The Disaster of War,1863),是戈雅在目睹1808年法军入侵西班牙后,含着对入侵者暴行的控诉,对权贵们昏庸的愤怒,对祖国深沉的爱,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创作的。画作采用隐喻、反讽的创作手法,把他所目击的愚昧、残酷和压迫深刻刻画出来,体现出对生命的理解。比如他在刻画等待被法国军队处决的平民时(第26幅画),着力再现了人们绝望而无助的神情。人们眼神中的哀求呼告和挣扎求生的欲望穿透画直抵观者的心灵,观者很难不被触动,继而对战争的残酷有所反思。再比如他在呈现被欺凌女性时(第11幅画),突出展现了她面对施暴者被置于完全被动无力的处境。人们“目击”一个个生命如同玩偶般被暴力所撕裂和毁灭,“看到”在暴行面前,生命一如草芥,毫无尊严可言。通过这样的表征,戈雅所唤醒的是人们对受苦受难的他者的认同和对战争、暴力和人性的深思。正如桑塔格(Susan Sontag)评价《战争的灾难》所说的那样,“那食尸鬼似的残忍是要惊醒、震撼、刺伤观看者。戈雅在艺术中确立了一种对痛苦作出反应的新标准”[12]。小说中史蒂芬注意到,“戈雅几个世纪前的困境与今天表征的困境如出一辙:展现真相与可能带来的后果处于紧张关系”[13]。而小说卷首语引自戈雅的三句箴言:“这不能看。我看见了。这就是真相”,则充分显示出这位艺术家以对人间疾苦广袤的悲悯之心超越了伦理困境。正如小说中凯特在看到戈雅描绘囚徒的一幅画作时赞叹道,“画上的人们没有希望、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但透过戈雅坚定而同情的眼睛看这些人,却感受不到任何诸如绝望之类简单、琐屑的情感”[14]。戈雅以对受苦者深切的共情与共振,为历史上无足轻重的卑微者画像,从而践行了一种从弱者/他者立场出发的、以服务于弱者/他者为旨归的表征实践。
与戈雅形成对照的是战地记者本的表征。本在阿富汗战争期间所拍摄的照片中有一张也是关于行刑的场面。但与戈雅的画不同,本将自己的形象也包含在照片中。“一个跪着的男子盯着准备杀死他的那个人,但是本把自己的影子也拍了进去。影子在布满灰尘的路上延展,似乎在说‘我在这里,我举起相机,这将决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在下一张照片中,死者躺在路上,而摄像者头部变形了的影子,却靠得更近了”[15]。本刻意将自己的影子放进行刑的画面,或许意在以自己的在场“见证”一个生命被杀死的过程。但是,“我在这里,我举起相机,这将决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形象地印证了桑塔格所说的“摄影/射杀”(shoot)的双重意涵[16]。拍摄者无法从被拍摄者的视角和立场来衡量拍摄的意义,亦无法与对象产生一种情感上的联结,导致摄影机的在场变成对他者的一种冒犯,进而造成伦理与见证的冲突。可以设想观众看到这张照片时,可能并非对被害者感到同情,而是与旁观者产生认同,进而滋生一种对他者苦难的淡漠之感。
本的另一张拍摄一个遭强暴后被杀的年轻女性的照片所暴露的伦理问题更加突出。在波黑战争期间,本和史蒂芬在萨拉热窝一幢被炸毁的楼中发现了一名死因不明的被害者。“有个女孩在垫子上蜷缩着。她没有说话,没有喊叫,也没有试图离开。本在墙上摇晃手电筒的光,直到看见她的脸。她的眼睛大睁着,裙子被掀起,在腰上揉成一团,张开的腿之间被黑色的血污和疼痛填满”[17]。史蒂芬的反应是默默将女孩的裙子拉下来后离开。本却在离开后又独自返回拍摄了那个女孩。为了呈现真实的场景,他将女孩的裙子重新拉了上去。史蒂芬在看到这张照片的第一反应是“震惊。史蒂芬为她被暴露成那个样子而感到极度震惊。虽然从伦理上讲,本并没有做错什么。他并没有设计这张照片,而只是记录了尸体原本的状态。但仍然很难不感到那个女孩腿那样大张开,是被侵犯了两次”[18]。在此,本所持摄像机的“菲勒斯”(phallus)象征意义不言而喻:表征者处于操控者的角色,而被表征者则完全处于被动境地。表征者因而不仅是旁观者,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施暴”的“同谋”。在此意义上,史蒂芬所言的女孩“被侵犯了两次”,一次是身体遭强暴致死,另一次则是被“表征”所“强暴”。总之,在本的表征中,作为表征主体的“自我”与被表征客体的“他者”始终处于不平衡的权力结构和主客体等级秩序之内。“我”将“他者”作为一个“对象”乃至“物体”再现,在这个过程中,“我”始终高于他者,而无法切近体会他者的苦难。这种表征者/被表征者二元思维模式,正是小说所揭示的表征伦理困境。
小说题目“双重视域”有着明确的所指,即表征者需要有“双重视域”:一重是表征主体的“自我视域”,另一重则是被表征对象的“他者视域”。若表征者只从前一重视域看待所表征的人或物,则会导致表征的“唯我论”,从而抹杀他者的意义,使表征陷入非伦理境地。小说中的小说家彼得就是这种“唯我论”的典型。彼得的人格问题在于他缺乏“他者意识”。对他而言,他人仅仅是他操控和利用的对象,而非独立的个体。这种极端的自我主义使他在儿时就犯下谋杀罪,他仅仅因为一位老人发现他行窃,便把老人杀死。这种自我中心主义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则表现为作品没有道德中心。当被问及“如何将真实人物变成虚构的人物”时,他的回答是,“把自己的一部分加入其中。我们都有黑暗的一面”[19]。甚至在他创作的两篇短篇小说中,叙述者对施暴者表示欣赏,而对受害者无动于衷。对彼得而言,表征的对象并不独立存在,而是仅仅作为自我的投射而存在。表征不是望向他人,而是回望自我,不是“他恋”而是“自恋”。正如小说人物贾丝廷指出的,“彼得所做的就是将自己的情感倾注在别人身上,然后同情他自己”[20]。如果说本透露的是表征主体对他者无意识的主导地位的话,彼得则是赤裸裸的对他者的同一化、占有和消灭,是典型的表征主体“唯我独尊”的体现。
《双重视域》区分了伦理表征和非伦理表征。以戈雅为代表的,表征主体兼具自我与他者“双重视域”,尊重他者独立存在、体会他者苦难的表征,可称为伦理表征。相反,以本为代表的主体无视他者/弱者体验,或以彼得为代表的主体固守自我中心主义,从自我出发以“单向视域”对他者表征,将导致他者被吞噬、表征沦为自我独白。这样一种表征根本上是否定他者独立存在的,因而也是非伦理的表征。小说中以“阿斯伯格综合征”(Asperger’s)——一种认知障碍,只能将他人视为物,而不是人,来讽喻非伦理的表征。我们也可以打个比喻:非伦理表征就像是一面镜子,人们从中只能看见自己;而伦理表征则是一扇窗户,让人们看见差异和他者。它召唤人们走出习以为常的思维框架,去体认我们的世界、关照我们当下的现实,去靠近那些遭剥夺、被驱逐的边缘人群。
三 自我承担对他者的责任
在列维纳斯看来,“伦理的先在性决定了责任先于自由,无论我的行动是否有价值,伦理都是我的存在的当然条件”。他在对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进行大尺度批判和颠覆后,提出一种认可和尊重异质性他者绝对先在性的伦理或形而上学言说。“西方哲学本体论忽视他者的绝对先在性,简单粗暴地使他者从属于自我,是一种自私狭隘的‘为自己负责’的论说,从中无法推导出真正的、纯粹的伦理学。只有承认差异,尊重和发现他者的哲学价值,从自我走向他者,主动担负起对他者的伦理责任,才能达至真正意义上的正义与和平”[21]。
他者伦理观认为,“人类的天性和主体性是对他者的责任”[22]。作为主体的“我”对穷人、陌生人、无家可归者、孤儿寡母等“他者”负有绝对的责任,他们的苦难看似遥不可及,但都与我有关。“‘我’不得不担负起责任,不得不作出无条件的应答。正是因为‘我’处于这种人质状态,在这个世界中才会有怜悯、同情、宽恕和亲近,甚至才会有‘先生,你先请’”[23]。伦理主体的存在正是超越同一、走向善良的“为他人而在”[24]。《双重视域》以主人公史蒂芬的亲身经历论述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说明当表征主体遭遇他者苦难的“不可表征性”时,以“自我承担对他者责任”回应他者的必要性。小说是通过一个“鬼故事”来影射这一思想的。
主人公史蒂芬的闹鬼经历源起于他和本在萨拉热窝看到的那个受害女孩。与本坚持曝光女孩不同,史蒂芬被女孩的遭遇强烈地触动,他无法做到客观纪录,而是“屈膝在她旁边,把她的裙子拉下来。他的脑海中有一个声音在说,这是犯罪现场,不要碰她。但另一个声音却说,该死的,这整个城市都是犯罪现场。他想帮她合上那双恐怖的眼睛,却无法触摸她的脸”[25]。面对被摧残致死的女孩的“面容”,史蒂芬所遭遇的正是他者的“不可表征性”。“面容”是列维纳斯的著名概念。面容是“他者越出他者在我之中的观念而呈现自身的样式”[26],它象征着伦理,镌刻着他者和无限的意义,是“我”所不能认知和把握的。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脆弱不安的生命》(Precarious Life)中发展了列维纳斯的面容理论,并提出“不可表征性”(unrepresentability)的概念。她指出,“有一种面容我们无法对其进行直接表征——“这种‘面容’是人类的苦难,是人类苦难的哭泣与要求”[27]。巴特勒认为,面对这样的面容,不是表征,而是相反的“表征的失败”才显现出人性。“在表征的失败中,面容并未遭到‘抹杀’;相反,表征的失败确立了面容的性质”。史蒂芬与本以居高临下俯视的态度拍摄女孩不同,他在与面容相遇的瞬间,领悟到其“不可表征性”。“表征的失败”迫使他质疑自己的主体立场,并直面他者。
在“唯我”视角得以抛弃之际,就是“他者”面容临显之时[28]。面容一方面“抵抗”主体对它的同一化,另一方面也拒绝主体旁观,它向他/她发出强大的伦理召唤,要求他/她面向它、倾听它。小说中女孩的“面容”如同幽灵般萦绕着史蒂芬,“那天晚上,史蒂芬蜷缩在睡袋里难以入睡,他想起那个女孩,以及她看他的眼神,她似乎什么也看不到。她的头在枕头上挨着他,但是当他翻滚试图摆脱她时,却发现她的身体就在他身子下面,像沙子一样干燥、不满足”[29]。她还命令或者恳求史蒂芬去倾听她,“她在等待着他,确切是这种感觉。她有话对他说,但他却没有去聆听,或没有以正确的方式去聆听”。此时,史蒂芬从主动者变为被幽灵缠绕的被动者,而女孩则处于主动的地位,她的“面容”在“高处”不断向史蒂芬“临显”(epiphany),要求他作出回应。
“面容”所召唤出的是“我”生命超越的向度,它开启了“我”对无限的感知,并打开我给予、慷慨、好客的心灵。史蒂芬对“面容”作出回应的过程,也是他不断亲近他者和逐渐担负起对他者责任的过程。小说巧妙地采用“镜像人物”的手法使“人鬼之间”的“对话”得以继续。史蒂芬的年轻女友贾丝廷以萨拉热窝女孩的镜像形象出场。这从二人年龄相仿,史蒂芬初次看见贾丝廷时仿佛时空穿越回到他看见萨拉热窝女孩时的情景,以及贾丝廷的一双“蓝色的大眼睛”总让史蒂芬想到女孩那双“月光中瞪大的双眼”等细节可以看出“萨拉热窝女孩是贾丝廷的幽灵他者”[30]。史蒂芬在倾听贾丝廷的心灵创伤中走近她,而贾丝廷也渐渐向史蒂芬敞开了心扉。二人从陌生人走向情侣的过程由贾丝廷的“面容”标示出来。从最早贾丝廷“掩藏起自己的脸”拒绝让史蒂芬看见[31],到“彼此看着对方的脸。但并非像亲密爱人般凝视对方”[32],再到史蒂芬抚慰贾丝廷时“看见了她,或部分的她”[33]。贾丝廷的“面容”从不可见到可见,也标志着史蒂芬不断向萨拉热窝女孩的“面容”作出回应。小说的高潮是当贾丝廷遭遇入室行窃的盗贼的暴力殴打时,正在山上散步的史蒂芬不顾一切奔赴暴力现场,勇敢地制服了施暴者,救贾丝廷于危难之中。可以说,贾丝廷的经历重演了萨拉热窝女孩的遭遇,而史蒂芬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翻转:他从“旁观者”变为了“行动者”。
“所谓责任,就是担负‘回应’的能力”[34],当“我”回应他者的吁求时,“我”便成为“为他者”的伦理主体(ethical sub j ect)。史蒂芬以伸张正义的行动回应了他者对正义的呼吁。小说中写道,“他从山上一路跑下来,脑海中像闪光灯不停地闪烁。那么多被强暴和遭折磨的女孩们——他无须想象就能描绘出即将发生在贾丝廷身上的事情。他完全可能看到她像一个破碎的玩偶躺在楼梯底端,她的裙子被掀到腰上,她的眼睛大睁着”[35]。“那么多被强暴和遭折磨的女孩们”代表的是所有各种暴力的无辜受害者。史蒂芬最终从女孩的“面容”中体悟到自我与他人血肉之躯的生命交织,于是沉默被打破了、他以介入回应不公正。
而史蒂芬的“介入”唤醒了自己内心深处“爱”的感觉。“那一刻,当他从陡峭的山上冲下来,当他知道无论他多么用力跑也不可能及时到达那儿的那一刻,比数月的内省更加使他明白自己对贾丝廷的感情。他意识到自己生活的中心已经悄然发生转移。你觉得自己在乎这个吗?别傻了,这个女孩,她才是最重要的。”[36]贾丝廷作为受害者的代表,史蒂芬对她的“爱”不仅是狭义上的爱情,更是对受苦的他者之爱,是爱他者。具有隐喻意义的是,当史蒂芬与贾丝廷以爱相连时,萨拉热窝女孩的幽灵被驱散了。“月光下他看得见贾丝廷的眼白。片刻间,他又看见萨拉热窝楼梯间里的这个女孩,但她已经失去了力量。这一刻将她驱散,或许不是永久的,但至少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如此。”[37]——“爱”作为对“面容”的伦理回应,满足了幽灵的恳求。
史蒂芬的转变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作为一名战地记者,他在目击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包括波黑战争、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九一一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众多人类历史暴力后,选择归隐乡间。他试图退守“孤独之自我”以求得心灵之安宁。然而,个人主义的堡垒并不能让他获得自由,他依然备受他者“幽灵”之缠绕。只有当他不再逃避而是采取行动,不再孤立而是寻求联结时,正义、爱、善良这些希望的力量才得以生发。史蒂芬的伦理觉醒代表着一种朝向弱者的道德力量。
阿多诺(Theodor Adorno)曾说,“奥斯威辛以后写诗是野蛮的”[38]。这句话从表征的角度询问当他者的苦难如此之深重,以至于任何形式的表征都成为不可能时,作为旁观者的表征主体还能够做些什么?小说《双重视域》中以一个“幽灵缠绕”的隐喻告知我们:面对他者苦难的不可表征性,接受表征的失败,以自我担负对他者的责任回应他者,可称之为“不表征的表征”。至此,小说所探讨的“表征”,已经大大超出了狭义的文学文化层面的“作为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的表征,而回归到“表征”的原初意义。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关键词》中对“表征”一词的词根(represent)做过辞源考察,表明represent从早期开始就具有代表他者(standing for others)的意涵[39]。可见,“表征”所标示的是主体与他者之间的一种关系,而小说所传递的思想是,“表征”的正义归根结底在于“为他者的人道主义”。
四 结语
巴克以书写暴力题材著称,在《双重视域》中围绕“自我视域”和“他者视域”探讨表征的伦理问题,从戈雅画册写到史蒂芬和贾丁斯的爱,再以幽灵切入分析暴力发生的伦理机制。小说质询了自我中心主义引发的暴力,并重申主体的伦理性,重构自我“为他者”的伦理关系。本文强调两种视域必须同时具备,这对于个体来说,能引导个人走向善良,消弭对他者的暴力;对于人类来说,反抗霸权主义,推进人类和平,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思想可能遭到如下反诘:现实中主客体关系受制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化等差异而处于复杂纠缠的状态,相形之下,“为他者”的伦理不免带有乌托邦和浪漫主义色彩。但其理想主义特质并不会削弱其现实批判及建构意义。在个人主义在西方盛行的时代,它呼唤个人建立与世界上受苦者之间的“联结”,召唤人们从弱者的视域看到社会的不公正,并用“爱”回应苦难者对正义的呼唤。这既是对表征伦理的呼吁,也是对社会正义的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