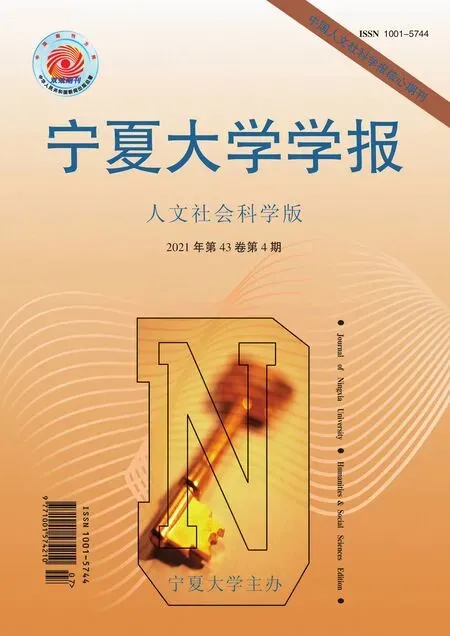从审美构思角度论《文心雕龙》“风骨”之内涵
——兼论现代话语体系下“风骨”的审美构思过程
2021-12-23李想,马晨
李 想,马 晨
(宁夏大学 人文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一 “风”“骨”之审美特征阐释
研究“风骨”的内涵首先应当明确其概念性质。《风骨》篇原文道:“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1“]风清骨峻”是一种审美特征,刘勰认为具有这种审美特征的文章才能取得“篇体光华”的效果,因而可以说“风”“骨”是两个具有审美性的概念。关于这一点,原文还有大量佐证之处,如“文风清焉”“骨髓畯也”“风力遒也”,“清”“畯”“遒”都是对“风”“骨”审美特征的描述。其实,《文心雕龙》中“风骨”独立成篇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刘勰是借用了前人的人物品藻和品画的美学术语“风骨”来论文的,所以文论中的“风骨”也应该是一个美学范畴[2]。综上,可以明确“风骨”是审美概念。
对于作为审美概念的“风”“骨”的审美特征,学界未有定论,多数学者认为“风清骨峻”是其主要审美特征,表现在文章中就是爽朗劲健的文风。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进行深入阐释,有人认为《风骨》篇是从内质美的角度,对“情”与“辞”作出了规定,“风清”是对“情”的内质美的规定,“骨峻”是对“辞”的内质美的规定[3]。也有人认为,“风”指“风清”,即文章思想感情表现的明朗性,“骨”指质素而劲健有力的语言,两者的风格特征是气势刚健,措辞精要[4]。这些观点其实还是“风清骨峻”的思路。然而通过对《风骨》篇原文的解读可以发现“风”“骨”的审美特征不止于此,对此,本文拟进行补充分析。
(一)“风骨”共同的审美特征:刚健有力
刘勰说:“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5]其中,“风骨不飞”对应的是“负声无力”,可以理解为没有了“风骨”也就没有了力,间接说明“风骨”是有力的。而“刚健既实”直接指出优秀文章的重要标准是“刚健”,据此可以推论“风”和“骨”共同的审美特征是:刚健有力。所谓“锤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6],正体现了文章具有“风骨”后刚健有力的状态。应当明确,刚健有力是“风骨”所共有的,可以将其看成一种基础性审美特征。除此之外,“风”和“骨”还包含一些独有的审美特征,只有将这两方面结合,才能准确阐释“风”和“骨”各自的整体审美特征。
(二)刚健感人、清越骏发的“风”
对“风”的审美特征阐释可以从“情”入手。《风骨》开篇说:“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7]说明“风”是教育、感化的源泉,可以理解为“风”具有强大的情感感染力,以至于可以达到教育、感化他人的目的。又说:“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8“]遒”字可以理解为刚健有力,因而可以说,“风”产生的情感感染力的特点是:刚健有力。因此,从“风”的角度看,它必须具有刚健有力的感染力以感化他人,可以将其审美特征概括为刚健感人。综上,“风”的第一个审美特征可以概括为“刚健感人”,在文中的关键字是“遒”。
“风”与“意”“气”的关系是理解其另一审美特征的关键。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说:“其曰:‘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者,明言外无骨,结言之端直者,即文骨也;意外无风,意气之骏爽者,即文风也。”[9]表明“意”对“文风”影响巨大,但黄侃先生强调了“意”却轻忽了“气”。从“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10]可以看出,刘勰对于“意”和“气”同样重视,《风骨》篇专门引用了曹丕和刘祯关于“气”的论述,认为他们“并重气之旨也”,显然是在强调“气”对“风骨”的重要作用。关于“气”的含义,叶朗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讲道:
曹丕《典论·论文》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这里的“气”,就是指艺术家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它包含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因为按照哲学上的元气自然论,人是由元气产生的,“人含气而生”,“气凝为人”。人的身体是气(“气者,身之充也”),人的精神、智慧也是气(“精神本以气血为主,血气常附形体”)。“气”是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本源。艺术家的艺术创造活动,也就是“气”的运化。它既是生理活动,也是心理(精神)活动,是艺术家整个身心协调一致的活动[11]。
刘勰在文中大量引用曹丕的论述说明赞同其观点,据此,可以依照《典论·论文》,将《风骨》中的“气”也理解为艺术家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原文中“务盈守气”“索莫乏气”等说法正是对艺术家生命力与创造力的呼唤,而“气号凌云”“骨劲而气猛”则强调了生命力与创造力的“辉光”。因此,作者的“意”和“气”对“风”都有很大影响,所谓“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12],“清”字可以理解为“清越骏发”,意为只要作者情意充实、体气高妙,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在创作中就能达到风行水上、自然成文的境界,使文章表现出充沛的生命力和高度的自由,表现出清越骏发的“风力”。综上,“风”的第二个审美特征可以概括为“清越骏发”,在文中的关键字是“清”。
(三)事义充实、言简辞健的“骨”
对于“骨”的审美特征阐释可以从“言辞”入手。刘勰说“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13],意为组织语言要准确精当,不能拐弯抹角、词不达意;又说“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14],表明他对精炼简洁的语言表达和谨严有序的言辞结构的推崇。另外,联系前文可知,刘勰赋予“风骨”刚健有力的审美要求,表现在“骨”上就是将言辞运用得刚健有力。从“锤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15]可以看出,对语言的锤炼和言辞的刚健是相辅相成的,因此,“骨”对于言辞的要求是表达简洁凝练、结构严谨有序和审美刚健有力三个方面。所谓“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16],“明”指“风清”,展现了“风”清越骏发的审美特征;“健”指“骨峻”,表明通过精简凝练、严谨有序、刚健有力的言辞可以使“骨”取得“峻”的审美特征,而此处的“峻”可以概括为“言简辞健”。综上,“骨”的第一个审美特征可以概括为“言简辞健”,在文中的关键字是“峻”。
阐释“骨”的另一审美特征可以从“事义”入手。《附会》篇说“事义为骨髓”,只能说明“事义”是“骨髓”,而不是“骨”。“骨髓”并不等同于“骨”,而是“骨”的内在因素,因此,“事义”也是“骨”的内在组成部分。具体来讲,“骨”是“结言”的结果,在“结言”过程中往往以“事义”作为其内在组织材料。至于“事义”的来源,《风骨》篇第四段说“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17],与前文“思摹经典”遥相呼应,可以证明“事义”是从经典中提炼出来的。从经典著作中提炼的作为“骨髓”的丰富“事义”,为“骨”的成形奠定了基础,所以刘勰评价潘勖的作品“骨髓畯也”。这个“畯”不同于“峻”,不能理解为言简辞健,而应该是事义充实。“事义充实”包括文章思想深刻和观点坚实有理两个方面,也正因此,文章具有强大的逻辑说服力,可以教育、感化他人。综上,“骨”的第二个审美特征可以概括为“事义充实”,在文中的关键字是“畯”。
总结来说,《文心雕龙》“风”和“骨”的审美特征有相同之处:刚健有力,但区别更明显。“风”的整体审美特征可以概括为与“情”密切相关的“刚健感人”和与“意”“气”密切相关的“清越骏发”,在原文中的关键字是“清”和“遒”。“骨”的整体审美特征可以概括为与“言辞”密切相关的“言简辞健”和与“事义”密切相关的“事义充实”,在原文中的关键字是“峻”和“畯”。
二 “风”“骨”之内涵阐释
关于《文心雕龙》中“风骨”的内涵,学界众说纷纭。黄侃先生有“意辞说”,刘永济先生有“情志事义说”,一些学者认为“风骨”是概括艺术风格的概念,也有学者认为“风骨”是一种美学标准。以上说法各执其词,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
对于“风骨”内涵的阐释应从刘勰写作《风骨》篇的用意入手。《风骨》开篇说“《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18],这里所谈的“风”直接传承自《诗经》。《毛诗序》曰:“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19]就是要求文章起到一种鼓动、讽谏、教化的作用。《风骨》篇正是探讨文章怎样才能发挥这种作用,而得到的结论是:要有“风骨”,即通过“风骨”表达文义,以达到“风教”的目的。因此,如何通过“风骨”表达文义成为文义论述的重点,可以说,刘勰作《风骨》篇就是借对“风骨”的阐释,详细解答如何将文义表达得既富有艺术感染力又富有逻辑说服力以达到“风教”的目的。如何表达文义其实就是构思与创作问题,因此,刘勰写作《风骨》的意图可以定义为,通过对“风骨”的阐释,解答如何构思创作,文章才能发挥“风教”的作用。
明确这一点再仔细研读原文,可以发现《风骨》篇大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段,阐释“风骨”,涉及构思问题;第二部分是第二段,阐释“风骨”和“采”的关系,涉及构思与着迹的文字表达问题;第三部分是第三段到第四段,阐释如何进行实际创作,属于创作论。其中,“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则“虽获巧意,危败亦多”[20],明确了创作要以对“风骨”的构思为基础(段落参考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因此,《风骨》篇应是构思创作论,刘勰在文中阐释了好的文章需要“风骨”“采”“新意”等要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风骨”,它是其余两个要点的基础,也是全文的中心论点。此外,应当明确“风骨”属于构思范畴,而不是创作范畴。分析原文可知,“风骨”与“采”结合可以成就“文笔之鸣凤”,说明“风骨”和“采”是属于同一级别的不同概念,而“采”是文字表达概念,隶属创作范畴,那么“风骨”就应该属于构思范畴。
《风骨》云:“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21]可知,“风”和“骨”在文人执笔创作之前就已经成形,且指导铺辞述情;又因为“风骨”具有审美特征,属于审美概念,隶属构思范畴,因而可以将其大致确定为作家审美构思后所得的结果。“风”的审美特征是刚健感人、清越骏发;“骨”的审美特征是言简辞健、事义充实,刘勰对于“风骨”的描述其实就是探讨如何构思出具有“风骨”的文章,因此,对“风骨”内涵的阐释应从审美构思角度出发。从审美构思角度论“风骨”之内涵前人已有研究,并得出结论:“风”可以描述为刚健感人的思路;“骨”可以描述为端直的构思定型后的言语结构系统[22]。这一观点基本正确,但由前文可知,“风”的审美特征不仅有刚健感人,还有清越骏发;“骨”的审美特征也包括言简辞健、事义充实两个方面。因此,结合前文对“风”“骨”审美特征的分析和之前学者的观点,可以将“风”描述为刚健感人、清越骏发的思路;将“骨”描述为端直的构思定型后事义充实、言简辞健的言语结构系统。
三 现代话语体系下“风”“骨”的不同面向
关于“风”“骨”不同面向的阐释,宗白华先生在解释“风骨”时提出的观点可资借鉴。原文如下:
我认为“骨”和词是有关系的。但词是有概念内容的。词清楚了,它所表现的现实形象或对于形象的思想也清楚了。“结言端直”,就是一句话要明白正确,不是歪曲,不是诡辩。这种正确的表达:就产生了文骨。但光有骨还不够,还必须从逻辑性走到艺术性,才能感动人。所以“骨”之外还要有“风”。“风”可以动人,“风”是从情感中来的。中国古典美学理论既重视思想——表现为“骨”,又重视情感——表现为“风”。一篇有风有骨的文章就是好文章[23]。
可知,宗先生也认为“风骨”是对如何表达文义的分析,并进一步指出,这一方面需要逻辑性和思想,可以概括为“理”(表现为“骨”),另一方面需要艺术性和情感,可以概括为“情”(表现为“风”),简言之,需要逻辑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兼备。
一些学者借此发挥,认为“风”侧重于“情”,即作者的主观情怀,“风”的形成,是情感的活动和形象思维的结果。“骨”侧重于“理”,来自充实的思想内容和严密的逻辑思维活动。“骨”是指充实的“义”(思想内容)[24]。这一观点有待商榷,然可取之处甚多。首先,“风”和“骨”虽然不是作者的主观情怀和思想内容,但和它们有着密切联系,将其分类划分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其次,将“风”的思维方式确定为形象思维,将“骨”的思维方式确定为逻辑思维,显然过于武断,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综合、模糊的,不是分析的清晰的,因而“风”“骨”的思维方式并非单一的、绝对的,但这种划分已经涉及“风”和“骨”在思维运作上的各自偏向,极具启发性。再次,认为“风”的成形需要情感活动和思维活动两个条件、“骨”的成形需要充实的思想内容和思维活动两个条件的观点基本正确。这是因为,只有充沛的情感并不能形成“风”,此时的情感具有散乱性、狂热性、无目的性,只有经过思维规划,才能具有整体性、形象性和情理性,进而才能形成清越骏发、刚健感人的思路(风)。只有充实的思想内容也不能形成“骨”,此时的思想内容具有冗杂性且言辞并未锤炼,同样需要思维规划,使思想深刻、言辞凝练、结构严谨,进而才能形成事义充实、言简辞健的言语结构系统(骨)。明确这几点对分析“风骨”的不同面向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这个思路再回到原文,“故练于骨者,析词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25],说明“骨”的作用是“析词必精”,使文章具有逻辑说服力;“风”的作用是“述情必显”,使文章具有艺术感染力。因而可以确定,“骨”侧重于对言语的组织,要有充实的事义为基础以“说理”;“风”侧重于对情感思路的规划,要有充沛的情感为基础以“述情”。关于“风”“骨”的建构方法,刘勰道:“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26]可以明确,“骨成”就必须结言端直、事义充实、繁杂有序,这就需要与言辞有关的思维进行构思规划;而“风清”必须意气骏爽、文思通畅、情感充沛,这也需要与情感有关的思维的运作。至于两种思维的具体形式,受制于时代局限,刘勰无法理清,然而借助现代话语,引入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概念,或可解决这个难题。
形象思维的主要特征是永远伴随着美感感情态度,即正确的“情”,它是通过感性形象来反映和把握事物的思维活动。形象思维离开了情感因素,离开了它的中介、推动作用,也就没有形象思维,也就没有艺术创作[27]。逻辑思维,即借助于语言形式(或谓自然语言)表达的思维。其具体表达方式,既可以是口头语言,也可以是负载于文字、符号、图表及其他多种形式的载体所表达的非口头语言[28]。可知,形象思维主要面向情感,而逻辑思维主要面向言辞。因而可以说,以“述情必显”为目的的“风”的成形所需要的主要是形象思维,以“析词必精”为目的的“骨”的成形所需要的主要是逻辑思维。这里需要明确,艺术家的整个思维活动必须包括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两方面。这两者常常是相互渗透和交织在一起进行着的[29]。也就是说,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是对立的统一,两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因此,“风”和“骨”所运用的思维就绝不能是单纯的形象思维或逻辑思维,而是两种思维的交互作用。“风”的成形也需要逻辑思维,由“风辞未练”可知“风”需要辞藻来表达,因而对“风”的梳理一定要事先考虑语言表达因素,这其中必定有逻辑思维的参与。“骨”的成形也要用到形象思维,形象思维的显象思维形式(形象思维的思维形式之一,参见杨春鼎的《文艺思维学》)所针对的正是形象语言的描述,要得到作为言语结构系统的“骨”也离不开这种思维形式的运作。因此“,风”“骨”对不同思维的运用只有主要、次要之分,而无绝对界限。本文由于篇幅有限,只针对“风”“骨”的主要面向进行具体分析。
综上,为了达到“风教”的目的,“风”要在构思后的思路中产生由充沛的情感和骏爽的意气所取得的艺术感染力,审美上的表现是刚健感人、清越骏发;“骨”要在构思定型后的言语结构系统中产生由坚实的依据和严谨凝练的言辞所取得的逻辑说服力,审美上的表现是事义充实、言简词健。艺术感染力来源于“情”,主要通过形象思维产生;逻辑说服力来源于“理”,主要通过逻辑思维产生。因此,“风”的主要面向是“情”和形象思维过程;“骨”的主要面向是“理”和逻辑思维过程。刘勰在写作《风骨》时虽然没有清晰地认识到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存在,但已经意识到好的文章应具有艺术感染力和逻辑说服力两个方面。因此,他将“风”“骨”进行区分论述,“风”偏向于“情”,而“骨”偏向于“理”,两者具有艺术性和逻辑性的不同面向,这是其思想的亮点,也为借助现代话语体系中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对“风”“骨”具体成形过程的解读提供了理论依据。
四 现代话语体系下“风”“骨”的审美构思过程
首先明确,审美构思不同于总体构思,“风”“骨”不是对文章整体的谋篇布局,而是在情感充沛的基础上对清越骏发、刚健感人的思路的梳理,以及知识足备的基础上对事义充实、言简词健的言语结构系统的组织。因此,风”和“骨”的成形其实就是其审美特征的成形,思维的具体运作应以对审美特征的塑造为要点。
(一)基础:充沛的情感和充足的知识储备
先分析“风”。《风骨》篇开头说“《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30],直接说明“风”具有感染力,是教育、感化的源泉,暗示“风”与“情”有着密切联系。又说“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31]、“深乎风者,述情必显”[32],表明“风”有“述情”功能,可以理解为“风”将充沛的情感通过创作表达出来,使文章极具感染力,以达到教育、感化他人的目的。因此,“风”的塑造过程中思维运作的基础是充沛的情感。再分析“骨”。由前文可知,“骨”的一个审美特征是事义充实,而事义是从经典中提炼出来的。因此,要取得事义充实的审美特征,就必须“思摹经典”,获得充足知识,以便在需要的时候有选择地提炼,使文章思想深刻、论点坚实有依据。所以,“骨”成形过程中思维运作的基础是充足的知识储备。当然,正如前文所说,充沛的情感和充足的知识储备只是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风”“骨”的成形还需要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运作。
(二)“风”成形过程中形象思维的运作
1.形象思维与刚健感人之“风”
刘勰认为,“风”之力的表现是“结响凝而不滞”,“凝”定指抒情确切,“不滞”指抒情生动[33],进而才能“述情必显”,取得“刚健感人”的审美效果。做到这一点就要用到形象思维。形象思维的具体方法可以概括为比、兴、虚构、夸张、典型化[34]。关于“比、兴”,刘勰有着深刻的见解,他在《比兴》篇指出:“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35]刘勰认为,“比”就是比附物之性,“兴”就是起兴人之情。比附其兴,就是按照不同事物间相类似的关系来突出其中某一事物的特点,这就使得抒情确切;兴起其情,就是根据事物间曲折微妙的关系来寄托所要表达的意思,进而使得抒情生动[36]。而虚构和夸张方法运用的是想象的思维形式,可以充分调动读者丰富的想象力,达到引发联想、突出形象、渲染情感、深化主题等目的。典型化是作家运用形象思维创造典型艺术形象的方法,其最终目的指向是利用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来鼓舞人、引导人。形象思维的这些方法都与“情”相关,且强调艺术感染效果,对其灵活运用便可使“风”取得刚健感人的美学风貌。
2.形象思维与清越骏发之“风”
刘勰认为“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为文贵在“气号凌云”,切忌“思不环周、索莫乏气”,由此可见,清越骏发之“风”的成形关键在于“意”“气”。关于“意”,《神思》篇说“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37],“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38]。由前一句可知“意”来源于思,是思想的结果,后一句说“意”“翻空”“易奇”,说明“意”侧重于表虚的联想和想象。综合两个方面,可以将“意”理解为艺术家对外物进行形象的理性认识后所获得的观点。而结合前文可知,“气”是艺术家的生命力与创造力,要使这两个与艺术家紧密相关的概念取得“骏爽”的效果,就需要形象思维的参与。杨春鼎先生在《文艺思维学》中将形象思维的具体形式概括为三种:意象、想象、显象。意象是形象识别的基本思维形式,它不是客观事物表象的被动反映,而是包含着思维主体对客观事物能动的认识,属于一种形象的理性意识[39]。意象源于艺术家主动的思考,是对被动接收的表象的再加工,既有形象性,又有概括性,因而只有经过意象的思维形式才可以得到骏爽的“意”。想象是在思维主体的头脑里进行的意向的组合运动,是形象创造的基本形式。创造性思维过程中的想象活动,不是形象感知记忆的简单复现,而是在主观思想情感的支配下,能动地进行的意象加工组合运动,把原型意象转化为可供语言描述的再造意象[40]。这种经过想象而产生的再造意象,能够体现思维主体的思想情感。因此,想象可以展现艺术家思想情感中的生命力,并为其创造力的发挥提供舞台,经过想象的思维方式可以取得“气号凌云”的效果。综上,形象思维的思维形式可以建构骏爽的“意”“气”,再加上该思维中比、兴以及虚构和夸张等方法对于艺术家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挥,就能使文“风”产生清越骏发的审美效果。
(三)“骨”成形过程中逻辑思维的运作
1.逻辑思维与事义充实之“骨”
根据前文,刘勰认为“思摹经典”才能事义充实,说明事义是从经典中提炼出来的,这就需要充分利用逻辑思维。逻辑思维是一种理性思维,具体思维形式包括概念、判断、推理,逻辑思维方法也就是在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判断、推理的思维方法,可以概括为分析法与综合法、比较法与分类法、归纳法与演绎法、抽象法与具体法[41]。逻辑思维在“骨”成形过程中的运用,表现为通过判断、推理的思维形式对经典中的事义进行理性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提取出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在这一过程中运用的方法主要是分析法、比较法和抽象法(即将完整的感性具体材料转化为抽象的思维规定),经过提炼后运用到文章中的事义可以呈现出一种内涵之美。这种内涵之美首先表现为事义与主题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根据刘勰的说法,文章是“应物斯感”,并要达到“风教”的目的,这就决定了作家必须对各种经典进行严格逻辑甄别与分析,通过比较各类经典在表现主题上的优劣作出取舍,提炼出最能表现主题的事义。其次,这种内涵之美还表现在它可以为文章观点提供坚实的依据。提炼出的事义不仅要与主题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还必须能够支撑主题所表达的观点。再次,这种内涵之美还表现在作家在提炼过程中,会在事义的启发下不断深化思想,从感性、具体的材料中抽象出本质与精华,进而使文章厚重而深刻。综上,这种内涵之美可以概括为事义充实,可以明确,在逻辑思维运作下,“骨”将会呈现出事义充实之美。
2.逻辑思维与言简辞健之“骨”
“瘠义肥辞”则“无骨之征也”,因此,文章的言辞必须简洁凝练且用词要做到“结言端直”。“结言端”是指文章在义理(内容)上的要求,具体是写文章在义理上要符合正义,不可歪言邪说;“结言直”是指文章在文理(表达)上的要求,具体是写文章在文理上要做到指事确切,不可泛泛而谈[42]。做到以上两点就需要逻辑思维的运作。逻辑思维利用概念、判断、推理的思维形式对“言辞”进行锤炼,提取出经典中的“正义之言”,以精简凝练的文字进行表述,在这个过程中运用的方法是分析法、归纳法和具体法(即将思维由抽象转化为具体,并以具体材料表达出来),其结果是使言辞获得一种内涵之美。这种内涵之美首先表现在言辞的简洁凝练上,是通过分析归纳、删繁就简、舍弃“肥辞”而取得的“析词必精”的效果;其次,表现在言辞的刚健有力上,是经过锤字炼句,使字句“坚而难移”,从而展现出的一种刚健之美;再次,表现在篇章结构的谨严有序上,刘勰所说的“繁杂失统”是指逻辑混乱,它的出现也会使文章“无骨之征也”。因此,对于篇章组织的“大结构”需要运用逻辑思维使其谨严有序,以求获得“骨之力”,这一过程需要借助逻辑思维“缀虑裁篇”,以理性思考谋划“大结构”布局,充分利用该思维的各种方法,取得“刚健既实,辉光乃新”的效果。综上,这种内涵之美可以概括为言简辞健,可以明确,在逻辑思维的运作下,“骨”将会呈现出言简辞健之美。
五 结语
明确《风骨》篇是构思创作论,“风骨”是审美概念,对于文学创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神思》篇对构思的解读仅限于空泛分析和经验杂谈,而《风骨》篇为创作明确了构思方法和审美倾向,指出了“文笔之鸣凤”的要点,并给出了创作的具体方法,进一步完善了刘勰的创作理论。本文对“风骨”审美构思过程的分析正是要提取出《风骨》篇的审美构思要点,从而详细阐释文章创作构思时的基础、方法和过程,为作家思路的梳理和言辞的铺排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当然,文章引入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是两个超越时代的概念,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不会意识到这两种思维方式的作用。因此,本文只是将现代思维概念与刘勰审美构思论结合的一种尝试,文章的分析基于对《文心雕龙·风骨》篇原文的解读,又注入了现代话语因素,所得观点旨在对文艺创作的理论建设有所帮助,在此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