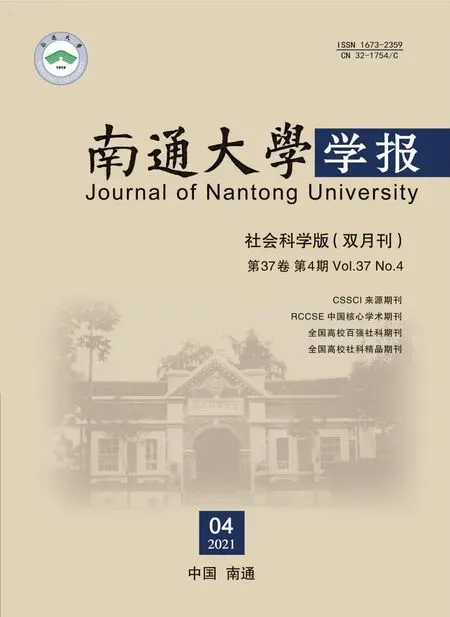“左联”记忆研究的视角转换与方法革新
2021-12-23高兴
高 兴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茅盾曾经宣告:“‘左联’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光荣的地位,它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先驱者和播种者。”[1]1纵观“左联”(全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研究史,虽然“左联研究一度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镇”,然而“左联研究的冷热起伏也十分显著”[2]1。时至今日,“左联”研究的重要性愈加突出,需要通过“左联”研究来促进红色文化基因“与各个时代的精神融合”,从中获取“不断砥砺前行的巨大动力和能量”[3];此外,由于现代文学社团的研究尚显薄弱,而“‘左联’使得现代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有了真正的分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翻开了新的一页”[4]246,所以,加强“左联”社团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1980 年前后,“左联”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尤其是产生了一大批“左联”盟员回忆录,其中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鲁迅纪念馆、上海文艺出版社等机构编纂的“左联”回忆文辑(如《左联回忆录》《“左联”纪念集(1930—1990)》等)。随着“左联”史料的厚积与丰富,“左联”研究也日趋深化,曹清华、陈红旗、贾振勇、孔海珠、汪纪明、王宏志、王锡荣、姚辛、张大明、张大伟、张广海、张小红、周国伟等学者对“左联”进行了多维度的考察,共同推动“左联”研究向前发展。虽则如此,今天的“左联”研究依然有待开掘,王锡荣提出“目前的左联与左翼文学运动研究,亟需在史料考辨和理论深化两个方向上努力探索”[5]10;另外,就“左联”史料考辨而言,王锡荣认为“非常混乱”的“‘左联’的回忆录”已构成“‘左联’研究的陷阱”之一[6]。张广海亦指出“左联”盟员的历史回忆“难免有含糊不清或彼此矛盾之处,甚至难免存有修饰或伪装”[2]10。那么,如何看待“左联”盟员回忆的学术价值?怎样从新的理论视角解读“左联”记忆现象?可否通过“左联”记忆现象的解读来促进“左联”研究方法的革新?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超越“陷阱”:“左联”盟员回忆的多重价值
王锡荣在考察“左联”盟员回忆材料的过程中发现:某些历史当事人“对于当时的情况,或语焉不详,或漏落甚多,甚至自相矛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回忆人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感觉对记忆进行解说”,于是,“回忆的史实就会被修正、变形”,从而导致“研究者对历史的误判”,他将这种情形称之为“‘左联’研究的陷阱”[6]。对“左联”回忆录的真实性及其史料价值提出质疑的学者并非王锡荣一人,20 世纪80 年代,丁景唐便已批评了一些“不负责任的‘回忆录’”所造成的“混淆视听、以假乱真的不良后果”,然而,与此同时,丁景唐又将“同时代人的回忆录”看成一种“‘活’资料”,并且肯定了这种类型的文献资料“可以补文字记载之不足”以及“确证”其他史料“历史意义”的独特价值[7]。从诸多学者关于“左联”盟员回忆录的评价当中可以看出:治学严谨的“左联”研究者一般不会轻易地将盟员回忆录视为绝对可靠的历史文献,他们大多意识到了当事人记忆信息发生扭曲和变形的可能性,只不过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他们才有意或无意地借助盟员的回忆来重构“左联”历史活动的局部细节。整体观之,在看待“左联”盟员回忆录的史料价值方面,研究者的态度存在一定差异:盟员回忆录既可能被当作损害研究客观性的“陷阱”,也可能被赋予一种佐证史料之可靠的附加值。
就文本内容的客观性与可信度而言,回忆录确实不及历史文献。记忆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类的记忆非常脆弱,即使回忆者自认为准确无误的记忆信息当中也可能出现种种偏差,因为“我们对现实的错误感知会被植入记忆系统,并在以后会被回忆起来,尽管这些回忆根本无法客观地反映现实”[8]44。除了生理学方面的因素之外,人类记忆还受“视点”和“意义”的支配,“人是以‘自己特有的视点’经验着事件”[9]15,故而“记忆并不是对过往事件的忠实复制”,每个人的回忆都是“对事件或信息的重新构建”[10]130-131。鉴于人类记忆在保存信息方面带有很多缺陷,当事人回忆的内容不能被看成确凿无疑的史料,若仅凭盟员的个体回忆来推究“左联”历史事实,极有可能坠入心理学家所说的“记忆错觉、自信错觉的陷阱”[8]135。从盟员的回忆内容中识别记忆“陷阱”,这种现象在“左联”研究史上不乏其例,诸如王锡荣对夏衍忆述的“左联”筹备细节的质疑、张广海对冯乃超回顾的鲁迅与革命文学家结盟经过的纠正、张大伟对阳翰笙回忆的“文委”负责人名单的甄别、姚辛对潘梓年自述的“左联”领导人身份的澄清……这些案例充分说明当事人的回忆并非重构“左联”历史的客观依据,如果一定要借助回忆性资料来考察“左联”史实,那么,研究者就应该像王锡荣所说的那样:“首先倚重、采信第一手的史料,即原始的记载和文献”,必须将当事人的回忆内容“与第一手记载相互质证”[5]405,当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应以原始记载和当时文本为准”[5]228。
如上所述,回忆录不属于客观性较高的历史文本,对“左联”回忆录进行甄别与考证,最大限度地还原“左联”历史原貌,这当然是极有价值的研究工作。然而,任何研究对象均能从不同的维度加以观照,“左联”的史学研究方法与其他类型的研究方法之间并非相互排斥的关系,在以往的史学研究方法之外,我们能够而且有必要从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层面来拓展“左联”研究视阈、丰富“左联”研究的既有成果。就此而言,重新审视“左联”回忆录的研究价值,探究“左联”记忆变迁、重塑、定型、接合的规律,对于当前的“左联”研究方法转换而言,不失为一种新思路和新策略。
事物具有多面性,回忆录“存史”的弱点却也可能意味着它在别处之优点。由于人类的言语行为总是“与特定的语境有关联,也有构建现实的功能,更具有某种社会目的”[11]44,我们可以对回忆录进行话语分析,从回忆录中发掘当事人置身于既定历史语境中的“在场”意识,辨析每位当事人面对各种历史场景的文化立场、主观态度和心理情感。假如历史当事人对某些具体事件的记忆表现出方方面面的扭曲或偏差,那么,这些“扭曲”与“偏差”反而更能彰显回忆者的思想意识和主体心态,如此“内隐”的话语信息在那些看起来准确无误、高度一致的史料文献中是难以勘探的。更何况,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回忆,除了回忆者自身的因素之外,回忆还受社会框架和时代语境的形塑,其流变与重构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大众文化心理的发展规律。以冯雪峰的“左联”记忆为例,在所有写过回忆录的“左联”盟员当中,冯雪峰回忆信息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广受研究者之认可,王宏志评价“冯雪峰的回忆文字,一向以来可信性很高”[12]120,王锡荣称赞“冯雪峰是一个十分严肃的历史讲述者和见证人”[5]210。然而,事实表明冯雪峰的记忆并不缺少波动,譬如冯雪峰对“左联”盟主鲁迅往事的忆述便有若干“版本”,其中包括鲁迅与李立三见面场景的三次叙述(1951 年、1967 年、1974 年)、对1936 年的鲁迅与他重逢情景的两次描述(1952 年、1966 年),每次回忆内容均有出入。有学者指出:冯雪峰关于鲁迅的回忆体现了“记忆的组织”之规律,回忆者有意使用了“叙事的情境化”“真话只说一半”“改写与‘有意漏记’”等多种“叙事策略”,通过记忆的“再造”,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13]。无论如何,该事件已能说明:即使像冯雪峰这样严谨的回忆者也无法避免记忆的选择性与不稳定性,他的回忆常常随着心态波动而发生嬗变。另外,冯雪峰的回忆还受到时代语境和社会思潮的规约,仔细研读冯雪峰撰写的回忆材料便能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冯雪峰对“左联”社团信息的回忆越来越详细,而他对“左联”盟员个人经历的记忆似乎趋于淡化(他常对别人坦言自己“记不清楚”)。但也有例外情况,即:冯雪峰的回忆越来越凸显鲁迅对于“左联”成立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试想:在冯雪峰回忆“左联”的年代,任何一位文人都不能不考虑“30 年代文艺”的性质定位、鲁迅的文化身份等重大问题,而且,也正是在那个时期,文学文本与作品版本的修改甚为常见。置身于这样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冯雪峰忆述鲁迅及“左联”的方式既呈现了他个人的心理意识和话语风格,同时也反映了社会背景与文化思潮对于文人群体的精神规约。假如研究者只在乎冯雪峰记忆信息的客观性与准确性,便很难挖掘其回忆内容渗透的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意蕴。
“左联”盟员记忆之所以蕴含多重价值,乃因人类记忆不只具有存储信息的作用,同时也拥有意义建构的功能。在文化记忆研究者看来,前者属于“无人栖居的记忆”,后者指向“有人栖居的记忆”,此记忆的特色在于“群体关联性、有选择性、价值联系和面向未来”[14]147。以此观之,将“左联”盟员“变形”或“残缺”的回忆看成“陷阱”的观点,或许片面地理解了人类记忆的功能。实际上,“左联”盟员的回忆不仅存储了历史信息,同时也饱蘸着左翼文艺战士的身份意识、生命情怀和精神信仰。对于“左联”盟员记忆的研究不应当局限于纯粹史实的考证,也就是说,研究者不能只关心“左联”盟员回忆资料的历史发掘功能,还要重视“左联”盟员记忆在社团研究、文化反思、社会实践等方面的意义诠释价值。更何况,即使从史学研究的视角来看,“左联”史的建构同样需要当事人的回忆作为有益的补充,因为某些与“左联”有关的历史问题无法通过文献调查求得解决。例如“左联”盟员身份的辨识一直缺少统一的认定标准,“左联”本来就没有严格的加盟手续,部分当事人甚至无法说清楚自己与“左联”的关系,有人认为自己“也是,也不是”盟员[1]845,有人指出“只能证明某人确系成员,无法否认某人不是成员”[1]839,还有人主张“广义一些来看”盟员身份[1]851。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解读当事人为“左联”发展而亲历坎坷的记忆,藉此重构“左联”社团的精神谱系,要比刨根问底地追查某个当事人是否正式加入“左联”的事实更有意义。总之,无论“左联”盟员的历史回忆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我们都应当从多种视角观照和探究它们,就算某些盟员的回忆内容与史料记载不相符,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其判定为“陷阱”而断然弃之不顾。甄别“左联”盟员的记忆对于史实的“变形”或“扭曲”固然必要,但我们不能停留于此,而应当继续追问:“左联”盟员记忆“变形”的现象何以发生?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天的人们应当如何看待前人的“左联”记忆?
二、关注“我们”:“左联”记忆研究的主体意识
迄今为止,无论在古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学科领域,文学社团的研究相当不足。学者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文学社团研究既不同于具体作家研究,也区别于文学流派研究。杨洪承指出:“文学社团不同于文学流派,前者的群体意向比后者更强烈、更自觉,群体思想、行为更趋于规范和统一性的追求。”[4]20朱寿桐强调“文学社团是文人的集合体,文学流派是风格的集合体”[15]2。总而言之,“文学社团”是具有内部凝聚力的文艺界人士的“群体”或“集合体”,社团成员在身份立场上表现出一定的“我们”意识,“尊崇共同的价值信仰和文学观念”[16]85。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左联”的社团主体意识强烈是其他社团无法比拟的。无论在“左联”的理论纲领、宣言通告、演讲决议等重要文献里,还是在“左联”盟员的文学作品以及文艺批评中,均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我们”形象频繁闪现。从社团发展史来看,“左联”曾经吸纳多个文艺团体,除创造社和太阳社之外,还包括洪灵菲、戴平万和林伯修等人在内的“我们社”,这个曾经“推动了普罗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的“独立而富有特色的文学社团”[17],选择了一个极具左翼文化象征色彩的名称“我们”,从中可以窥见整个左翼文人群体对于集体身份的自觉认同。
“左联”社团的主体意识在全体盟员的文化实践和文学话语中烙下了深深印痕。朱寿桐发现“共同的价值取向,相近的观念形态和类似的艺术趣味”构成了“左联”社团成员“集体的文化形式”,它对全体盟员的精神理念产生导引作用,甚至能够使“个性特别明显的作家”甘愿“掩藏起自己的个性”,连“独立性最强”的鲁迅也主动挥写大量文学批评文字以强化“左联”社团形象[18]。有资料显示,“左联”时期的茅盾也接受了这种“集体的文化形式”之影响,有人研读茅盾于1927 年至1934 年之间撰写的作家论,从茅盾的批评文本中觉察到了“‘我’与‘我们’的变化”,认为茅盾笔下的“我们”是“‘左联’集体意志的表征”[19]82,宣明“加入‘左联’,既是茅盾趋向于集体的标志,也是其作家论前后阶段的分隔标志”[19]86。在文学创作领域,“集体的文化形式”影响“左联”作家话语表达方式的典型案例当属诗歌体裁。众所周知,左翼诗歌当中最为常见的抒情主体是“我们”,殷夫以及“中国诗歌会”成员的作品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尤值一提的是,殷夫曾经写下一首题为《我们》的诗歌)。然而,侧重以“我们”为抒情主体的左翼诗歌易于遭到文学史家的指摘,批评者认为这些诗歌的“主体”往往“并非诗人自己,而是奉行战斗集体主义的群体”,从而担忧《我们》这类诗歌可能导致“‘群体’中‘我’的感情与个性的消失”以及“诗歌创作中诗人主观世界的消失与对艺术个性的忽略。”[20]353-355其实,采用“我们”作为抒情主体不一定导致诗歌艺术个性的消解,正如在叙事文学作品中,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叙事模式“本身并无优劣之分”,“每一种聚焦叙事方式都可以在作品中成功地运用,产生各具特色的优秀作品”[21]111。与此类似,左翼诗人怀着真挚的情感态度,将自我人格融入“我们”这个社团主体,这使得他们的“集体主义”表达方式包含独特的艺术个性。尽管左翼诗歌的抒情主体发生了“由‘我’向‘我们’的主动迁移”,但是“左翼诗歌有属于自己的创作逻辑和审美合法性”[22]。种种情况表明:“集体的文化形式”作为一种社团主体意识,它已深度融入“左联”盟员的价值观念、文艺思想和审美心理之中。
既然“集体的文化形式”对盟员精神世界产生了普遍的规约作用,这便意味着过去的那种只关注盟员个体记忆而忽视社团集体记忆、只聚焦社团人事记忆而罔顾“左联”文化记忆的研究路线有失偏颇。为了探究“集体的文化形式”规约下的“左联”记忆规律,研究者可以根据需要,适当借鉴国外学者提出的集体记忆理论与文化记忆理论的相关观点与方法。
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理论指出“记忆事实上是以系统的形式出现的”,认为“只有把记忆定位在相应的群体思想中时,我们才能理解发生在个体思想中的每一段记忆”[23]93。哈布瓦赫特别强调“个体记忆”与“群体记忆”不可分割的关系,即“我”的记忆来自“我们”记忆的“一个部分或一个方面”,因为“我”是在“我们”的框架中作出思考和讲述往事的,“如果人们不讲述他们过去的事情,也就无法对之进行思考。而一旦讲述了一些东西,也就意味着在同一个观念体系中把我们的观点和我们所属圈子的观点联系了起来”[23]94。由于“集体记忆往往依托于群体而存在”[24],群体的解散意味着集体记忆面临解体的危机。如果按照“集体记忆”理论的观点来看“左联”盟员的记忆现象,我们便不再满足于过去所习见的个体记忆研究视角,并且产生新的思考:“左联”盟员共享的历史语境是否影响他们的记忆方式?对于“左联”社团的身份认同会不会造成盟员与非盟员的记忆差异?“左联”内部的思想规范和话语系统能否调控盟员的个体记忆?诸位盟员参差错落的记忆是不是有助于勾勒“左联”社团历史图像?等等。如此看来,今后的“左联”记忆研究应当对盟员的集体记忆给予更多关注,质言之,我们需突破“左联”盟员个体记忆研究的思维定势,从“社团”的整体视角来考察“左联”盟员的集体记忆,即“左联”社团记忆。
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理论将“集体回忆”划分为“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两种形式。在这二者当中,“交往记忆”是指“刚刚逝去的过去的回忆”,它是“人们与同时代的人共同拥有的回忆”,这种记忆“随着它的承载者而产生并消失”(例如“代际记忆”)[25]44。“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的关系更为密切,“对于文化记忆来说,重要的不是有据可查的历史,而只是被回忆的历史”[25]46,群体“通过对自身历史的回忆”而“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它带有“某种神圣的因素”,注重“交往的典礼性”[25]47。从记忆的形式和媒介来看,“交往记忆”与人际交往和日常生活有关,它是“存在于人脑记忆中的鲜活回忆”;而“文化记忆”重视“庆典仪式性的社会交往”,它常常诉诸“象征性的编码”及“展演”[25]51。依据文化记忆理论的观点,个体成员对于“集体”或“我们”的身份认同并非自然达成,需借助仪式、节日、纪念碑、文字、图画等各种载体才能实现。显然,文化记忆理论可为“左联”记忆研究增添不少新论题,诸如:“左联”盟员的交往记忆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发生了何种变化?历史当事人的哪些记忆被淡化或消解、而哪些记忆反而被突出或强化了?不同时代的人们是如何回忆和纪念“左联”的?“左联”盟员的“代际记忆”与后人对“左联”的“文化记忆”有何差异?从“左联”历史叙述话语的嬗变轨迹中能否看出社会大众回忆“左联”的文化心态?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可以推进“左联”社团的学术研究,还可以强化“左联”在集体记忆中的精神映像,避免“左联”的文化传统逐渐淡出民众视野,从而彰显“左联”研究的主体意识和人文精神。
综上所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左联”是拥有强烈的主体意识的文学社团,“集体的文化形式”始终深刻而牢固地扎根于“左联”盟员的精神世界,考察“左联”记忆不能不顾及这一重要特征,研究者不得不关注盟员的“我们”意识对其历史记忆的深层调节功用。因此,从当前的“左联”研究格局来看,改变以往常用的孤立式、分散性的个体记忆研究方法,将单个盟员的“左联”记忆置于社团记忆的框架之内,合理借用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的理论观点来探索“左联”社团记忆的特点与规律,在此基础上检视社会大众(包括盟员在内)对于“左联”社团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展现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凝聚力和影响力,该项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三、追踪“影响”:“左联”记忆研究的意义生成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研究,朱寿桐呼吁“把它纳入历史的范畴,以便从一个切要的也是可行的角度揭示中国新文学发展的规律”[15]19,但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他的建议是:“现代文学史上的每一个有重要影响的文学社团,其组成方式,内在结构,运作模态都不完全相同,因此,对它们的研究应当采取不同的学术策略。”[15]47-48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各有千秋,研究者确实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特点选用合适的方法。以“左联”为例,依据“左联”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等历史文献中的自我定位可以明显看出,“左联”并非一个纯粹文学性的社团,而是为了社会大众福祉顽强战斗的文人团体,其文化意义更为突出,用王锡荣的话来说,“左联”这个社团“不仅是文学团体,而且是文化旗帜,是社会民主力量的旗帜”[5]271。由于“左联”的文学观念“具有强烈而鲜明的政治实践品格”[26],我们不宜采取纯艺术的批评立场来审视“左联”,而要关注它对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建设的历史影响,基于文艺的多维属性来评价“左联”的历史意义。王宏志批驳了西方学者低估“左联”作家文学成就的偏见,非常睿智地指出作品的艺术性并非“左联”作家追求的主要目标,因此“不一定要以创作的文艺性或审美性作为首要或惟一的考核标准”[12]145。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现代文学社团,“左联”研究的重心在哪里?杨洪承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发展史是一部文学意识形态史”[4]28,他阐明现代文学社团“在文学与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之间生成了自己的‘中国形象’”[4]34,并且将“现代中国作家群体的‘中国形象’结构”看成“文化传导链”或“‘文化传导’的接力棒”[4]44。该观点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研究来说颇具理论指导意义,“左联”及其记忆研究尤其需要追踪该社团的历史“影响”,揭示左翼文化精神在现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史上形成的“传导链”或“接力棒”。
文学社团研究的视角可谓多种多样,例如对社团历史状貌的考证与辨析,对社团人事关系的梳理和描述,对社团权力构成的分析和阐述,等等。但是,从“记忆”的视阈考察文学社团具有不可或缺的学术价值,因为“记忆”现象涉及主体对抗“遗忘”的精神努力,并且“记忆”的“选择性”又反映了主体对于“意义”的追寻、对于“身份”的认同,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寻思:人们回忆了哪些文学社团?为什么要记住这些文学社团?怎样回忆这些文学社团?如何言说记忆中的文学社团?这些问题实际上都与文学社团的“影响”因素有关。从“记忆”的视角研究文学社团,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它能较好地揭示文学社团在社会文化史上的精神投影。应当承认,通过考证、统计、测量等方法“还原”文学社团历史面目的研究路线必不可少,但是,若固守这种研究范式而拒绝方法革新,便可能将文学社团当作凝固不变、缺少意义生成能力的静态对象,而且,笃信价值中立的研究者只想成为文学社团的发掘者、勘探者和判断者,不愿以历史同情的目光洞察文学社团在情境演变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建构意义。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从“记忆”的视角研究文学社团,恰好能够促进主体之间的精神互动,凸显文学社团在情境变换中的文化建构意义。文化记忆理论认为:“文学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一种文化的主导性意义生成过程的一部分,它跟别的象征体系不断互动。”[27]415借助文化记忆的透视镜,梳理文学社团的“意义生成”过程,可以辨认文学社团对于社会文化体系的影响方式及效果,如“左联”社团记忆在当代中国是怎样发挥左翼文化传导作用的。
“左联”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意义,首先体现为阐扬盟员集体记忆蕴含的左翼文化精神。按照“左联”社团的自我定位,以及鲁迅对“左联”历史使命的表述,均可得知:“左联”的奋斗目标鲜明地诠释了中国左翼文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捍卫广大民众福祉的文化理想。作为文学社团的“左联”在1930 年代便无形消散了,而它代表和张扬的“左翼”文学与文化精神却一直赓续至当代。方维保考察左翼文学“红色意义的生成”,发现“当左翼革命延展至整个20 世纪的时候,左翼文学是随之延展的”,他主张“把左翼文学的研究放到整个20 世纪的大历史中来考察”[28]13-14,这说明“左翼”精神影响之深远。左翼文化精神的绵延与传承不仅见于作家的文学创作,更呈现在“左联”盟员的社团记忆中。依照文化记忆理论的观点,“四十年”的时间距离非同寻常,“对于集体回忆来说,四十年标志着一个节点,即一次危机”,此时,“不想随着时间消逝”的“自传性的回忆”必须转化为“文化回忆”,“其手段便是集体记忆术”[25]237。巧合的是,“左联”成立四十年之后,研究者开始走访“左联”盟员,邀请冯雪峰、楼适夷等盟员回忆“左联”往事,这些盟员对于“左联”社团的回忆表现出浓厚的“纪念”意识。虽然某些盟员的回忆仍带有人事纷争遗留的情感痕迹,但在谈及“左联”社团的战斗历程时,盟员们一致肯定“左联”的革命理想和崇高信念,无论是冯雪峰、胡风、楼适夷、吴奚如,还是周扬、夏衍、徐懋庸、沙汀、任白戈等人,他们的“左联”记忆莫不如此。平心而论,“左联”盟员关于社团人事关系与历史活动的记忆固然宝贵,然而,盟员对于“左联”精神的回忆以及“左联”身份的重构亦不能等闲视之,前者属于“交往记忆”,后者指向“文化记忆”。迈入新时期之后,在一些文化、教育、学术机构的组织下,“左联”盟员纷纷通过访谈录、回忆录、纪念会、座谈会等形式阐发“左联”文化精神,成为20 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亮丽风景线。周扬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宣告:“我们今天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以‘左联’为代表的左翼文化运动是耸立在中国现代文化史、文学史上的丰碑!”他呼吁当代人“接过前辈们手中的笔,坚韧不拔地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的历史继续写下去”[29]。对于“左联”盟员传递下来的左翼文化“接力棒”,现代文学研究者应当予以重视。
长期以来,“左联”记忆研究者比较看重文献资料的史学价值,与“左联”记忆有关的文化现象受到轻忽,这些文化现象包括“左联”的纪念活动以及“左联”社团形象的经典化,等等。其实,对于回忆对象的“纪念”、将回忆对象写入词典或历史教科书,这些行为包含着重大意义,人们正是通过这些特殊方式来表达“身份认同的重构”和“记忆的改造”,在“共同的回忆”与“共同的遗忘”中“定义我们自己”[14]62。若要追踪“左联”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内在影响,不能不检视人们是如何纪念“左联”以及怎样将“左联”写入历史文本的。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实属少见。关于“左联”纪念活动的考察,汪纪明的专著《文学与政治之间:文学社团视野中的左联及其成员》对此作出一番有益的探讨,但该著侧重于对“左联”纪念活动“政治色彩”的定性研究[30]68,未涉及“左联”纪念与社团记忆的关系问题。至于“左联”社团形象的经典化问题,研究者更少触及。我们知道,文化记忆的构建离不开经典文本的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的文本”在经典化的过程中逐渐取得“规范和定型的价值”[25]91,随着社会历史语境的更新,人们对于这些文本的解读与评价也会发生变化,而追踪这种变化轨迹,能够呈现回忆对象的意义生成规律。事实上,“左联”社团形象已被写入诸多历史文本,譬如姚辛的《左联画史》《左联词典》《左联史》、刘小清的《红色狂飙——左联实录》等“左联”社团专史,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中国现代社团辞典(1919—1949)》《中国文学艺术社团流派辞典》《中国社团党派辞典》《中国现代文学辞典》等多种工具书。这些带有“经典化”意图的文本当中,均有“左联”社团的性质定位和形象描述,它们对于“左联”社团的注解或诠释暗含“权威”色彩,显示社会大众在各个时段对于“左联”社团的文化记忆特点。通过对“左联”纪念文章、“左联”史、“左联”词典的“互文性”研究和话语分析,我们有望探明“左联”文化意义在中国社会场域中的历史生成法则。
四、结语
“文学研究的追溯方向是功能、社会意图、历史语境、社会成员,以及种种实现社会意图的技术,这些因素始终存在复杂的互动。”[31]文学研究应当高度关注社会成员与历史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文学主体意识所反映的社会发展规律。文学社团的研究需要考察社团“主体”,因为“文学社群形成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的主体活动”[4]5。在分析文学社团“主体”现象的过程中,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却又不能局限于人事纷争、文人聚会、办报出刊等“交往”层面的事实研究,还要阐释社团成员的身份归属、集体记忆、文化认同等因素交织而成的主体精神。文学社团运行期间,其成员通常表现出显在的“我们”意识,而一旦社团解散,这种“我们”意识唯有通过集体记忆的发掘与勘探才能重现。作为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学社团,“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革命文化团体,是“中国20 世纪上半叶革命文化的代表”[5]258,为了赓续左翼文化传统,我们应当研究“我们”的“左联”记忆,藉此重构和接续“左联”主体精神,真正发挥左翼文化“传导链”或“接力棒”的重要功能。
就文本内容的客观性与可信度而言,回忆录不及历史文献,但是,“左联”盟员的回忆并非一定构成学术研究的“陷阱”,因为“人们的记忆具有高度选择性,记忆的呈现过程可能会告诉我们关于记忆主体更多的东西,比如他们的现在、他们的期待和否认,而不仅仅是实际发生过的事情”[27]413。研究者应当改变过去那种纯粹史学研究的目光,将研究视角从“冷”史实转向“热”记忆,即:从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当事人以及后来者的“左联”社团记忆,对“左联”盟员回忆录、“左联”纪念文章、“左联”史以及“左联”词典等多种类型的历史文本采取“互文性”分析和话语分析的方法,设法追踪“左联”意义生成的历史轨迹,使“左联”研究不再囿于“考据学的真实”,从而为当代中国人展现“有人栖居”的、属于“我们”的“左联”社团形象。以此种方式研究“左联”,充分表明“历史、文学和记忆在这里是一个联系紧密的同盟”[14]83。由于“文学写作并非只有一个求真标准,文学价值受多种因素制约,如时代精神、社会心理、思想观念、体例范式”[32],重视“左联”记忆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探索“左联”记忆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将会促进我们对中国新文学史的认知和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