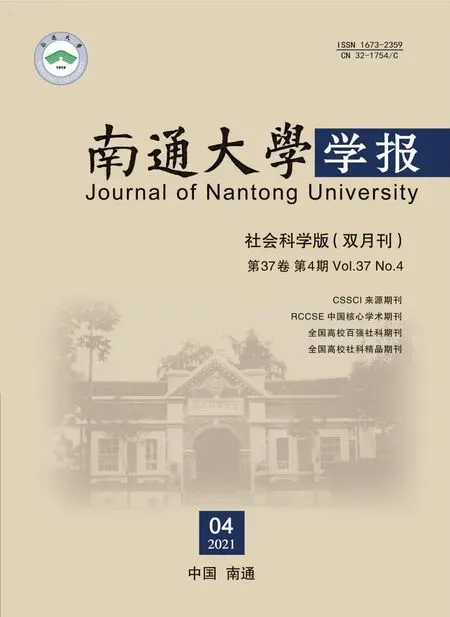汪曾祺的水情结与小说创作
2021-12-23靳新来
靳新来
(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水,是生命的源泉。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水,人类文明的起源与兴衰无不和水相关。中西方文化都存在着“水崇拜”现象,而中国尤为突出,有学者指出:“由于中国上下几千年一直处于农耕经济社会,农业对于水的过分倚重,又使得中国人对水的崇拜有增无减,而且愈演愈烈。”[1]2而中国文学的发源及演化也得益于水文化的涵育,《诗经》中仅《国风》中描绘水滨泽畔生活的诗作就有四十余篇,而以水起兴的篇目更不在少数。水文化长河激流扬波,绵延至现代而不绝,不少作家的创作都与水结下不解之缘。废名的《菱荡》《河上柳》《桥》等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与水交融在一起;孙犁的小说创作多以冀中平原的白洋淀水乡为背景,作品如水一般质朴明净;沈从文更是把自己生命与文学智慧归功于水,他说:“水和我的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作品倾向不可分。”[2]218在这类作家当中,汪曾祺无疑是极为突出和重要的一位,他的小说与水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可以说来源于作家内心深处的一种水情结。“情结是存在于个人无意识中的情感、思想、知觉和记忆的一个有组织的群体或群集。……情结的核像一种磁铁把各种经验都吸引到它那里。情结可以变得很有力量,甚至可以像一个单独的人格那样动作。”[3]107水情结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与中国“水崇拜”文化传统有着深层和隐秘的联系,凝聚了作家个人从小的生活经验。对此汪曾祺也有自觉,他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4]185可以说,水情结对于汪曾祺独特文化人格、精神世界、审美意趣等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决定了其小说创作的艺术追求、个性风貌,非常值得研究和探讨。
一、风景:在水一方
“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5]339这是汪曾祺对自己得意之作《受戒》的解说,其实也是他整个小说创作最突出的题旨。基于此他相应地给小说创置了一个美好的环境背景,大量书写风景。而内心深处的水情结使得汪曾祺认定有水才会有美、有健康、有和谐……所以他说:“我的小说以水为背景,是非常自然的事。”[6]313水,首先是作为一种风景在汪曾祺小说中展现的,往往在文本中占很大比重,以至于《大淖记事》因此而遭到非议,有人指责小说前三节一味描绘风土人情,第四节才开始写人,比例有失重之嫌。其实,风景的发现正表明汪曾祺审美主体意识的觉醒。日本学者柄谷行人认为:“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7]19当时“伤痕”“反思”等文学思潮风起云涌,汪曾祺却没有闻风而动、亦步亦趋,而是遵从自我专注于爱和美的表现,由此发现了风景。这种创作来自作家内心深处,是一种“无视外部”而耽于美学趣味的书写。而对于有着深厚水情结的汪曾祺来说,这样一种“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风景书写,深情妙笔之处时有水波泛起,也就不足为奇了。
汪曾祺小说展现了一个清澈开阔、生机勃勃的水乡风景世界,动人的地方总少不了水:“大淖是一片大水,由此可至东北各乡及下河诸县。水边有人家处亦称大淖。这是个很动人的地方,风景人物皆有佳胜处。”(《鸡鸭名家》)有水的地方总是充满生机:“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芳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芳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大淖记事》)水边人家的生活幸福祥和,就说《受戒》里的小英子家吧,三面临水“像一个小岛”,这里花草杂陈,树木相间,瓜豆蔬菜,四季不缺,鸡鸭成群,牛不生灾;一家四口各安其事,率性而为,怡然自得,而又和睦相处,其乐融融。就这样,风景与人事相得益彰,活脱脱构成一幅诱人的“农家乐”画卷。类似的风景书写在这篇小说中比比皆是,以至于在曹文轩看来“整篇《受戒》都是风俗画”[8]52。
集纳式的风景书写使得汪曾祺小说有些另类,但是人物毕竟还是居于文本中心,保证了小说文体不至于发生变异。法国学者居伊·德波认为:“景观不是影像的聚集,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9]3汪曾祺小说的风景书写,往往是与人物刻画交融在一起的。在最引人入胜的那些爱情故事里,水作为一种风景将爱情映衬得异常美丽。《小学校的钟声》中的“我”漂行于水途,邂逅一位长有两酒涡的女教师。在“我”眼中,女教师纯洁美好,像早晨静静流淌的运河水那样清鲜而甜净。一个少年的爱恋便在水边自然萌生了,而水渲染出这份朦胧情感的圣洁。《受戒》中明海和小英子在水上相识,一见面小英子就把剩下的半个莲蓬扔给明海来吃,二人的距离一下拉近了,这时小说特别写到船桨拨水的声音:“哗——许!哗——许!”这柔柔水声,正应和着这对男女的心灵律动。而此后两人情感发展一直伴随着潋滟水波:水田里,小英子的一串美丽的脚印搞乱了明海的心;在城乡间往返的船上,他们的感情随着泛起的水花而激荡;最终一叶小舟载着他们划进芦花荡,水草丰美之处成了他们爱情的伊甸园。《大淖记事》写的是巧云与十一子的爱情故事,其中最美的场景是这对恋人的沙洲幽会,纯真的爱情在水气月光之中得到升华:
十一子到了淖边。巧云踏在一只“鸭撇子”(放鸭子用的小船,极小,仅容一人。这是一只公船,平常就拴在淖边。大淖人谁都可以撑着它到沙洲上挑蒌蒿,割茅草,拣野鸭蛋)上,把篙子一点,撑向淖中央的沙洲,对十一子说:“你来!”
过了一会,十一子泅水到了沙洲上。
他们在沙洲的茅草丛里一直呆到月到中天。
月亮真好啊!
大淖长河,水滨泽畔,四季轮回,生命常青,美好的情感、健康的人性如水长流,生生不息。爱情故事总是与水相生相伴,美丽的风景、美丽的故事、美丽的情感,都少不了泱泱水气、柔柔水声,于是乎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有“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种书写模式经《诗经》固定下来,早已成为一种“原型”,由此生成的文脉代代相传,绵延不断,南朝以后逐渐在江南获得发扬光大。北宋秦观专擅“艳情”之词,即是对这一文脉的赓续和发扬,清代词论家冯煦即指出他的词“悄乎得小雅之遗”[10]55,延续的是《诗经》之余韵。那首《鹊桥仙》写牛郎织女七夕会,留下了“柔情似水”的千古名句,而汪曾祺的《大淖记事》描绘巧云与十一子在沙洲上幽会,因了云影水光的渲染而显得如诗如画、如梦似幻。这横跨近千年的神似和重叠不是偶然巧合,而是一支江南文脉的深沉绵延,对此胡河清指出:“高邮是江南水乡,所以把水的温软多情作为作品的底色,已成为一种文学上的传统。”[10]56这种文脉传统,无疑属于荣格心理学中的“集体无意识”“原型”范畴:“它不是从个人那里发展而来,而是通过继承和遗传而来,是由原型这种先存的形式构成的。原型只有通过后天的途径才有可能为意识所知.它赋予一定的精神内容以明确的形式。”[11]54以水写爱情这种“明确的形式”正来源于一种“原型”,汪曾祺感应心底水情结的召唤,以富有个性化的书写而激活了这一“原型”,同时也是对它的再发现和突破。他对“在水一方”爱情的书写既是个性化的,又是集体的、民族的;他表达了自我,又超越了自我而成为荣格所推崇的“更高意义上的人即‘集体的人’,是一个负荷并造就人类集体无意识精神生活的人”[12]247。从这一角度来看,汪曾祺在1980 年代复出于文坛,之所以未湮没于时流而独树一帜,是因为他的精神执着于一种“原型”、一种“传统”,是因为他的小说传达了“集体无意识精神生活”而契合民族文化和审美心理,从而赢得了广泛读者,具有了恒久的艺术价值。
二、人物:柔情似水
水情结使得汪曾祺小说常常以水为背景,更赋予小说人物以浓郁的“水气”,正如他自己所说:“记忆中的人和事多带点泱泱的水气,人的性格亦多平静如水,流动如水,明澈如水。”[6]313正因为人物具有“水气”,所以有些篇什“即使没有写到水,也有水的感觉”[4]185。
中西方关于水的理解和感悟有所不同,西方由水达到一种超验观念,而中国哲人由水找到的是对生命实在的基本理解,正如美国学者艾兰所说:“当孔子惊叹‘水哉,水哉’的时候,他没有敦促他的弟子去冥想全能上帝(Almighty)的无边伟力,而是去沉思独特地展现在他眼前的生命源泉。”[13]41汪曾祺崇尚水,而且一再强调是“流水”“流动的水”,说到底,他崇尚的是一种蓬勃盎然的生命力。汪曾祺笔下的水乡人在潺潺流水的滋润和洗礼下,几乎没有受到教条的规约和异己力量的扭曲,而是任意挥洒着生命活力,从而具有了深刻的“水气”。他们那丰沛的生命活力,犹如流淌于民间大地上的河水一样恣肆随性而又连绵不息,兼容并包而又生机盎然。水果小贩叶三搜罗到最好的水果,总是首先给画家季匋民送去,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爱他的画(《鉴赏家》);流浪艺人王四海本来周游四方,却为了心爱的女人脱班改行在小城留了下来(《王四海的黄昏》);骡马贩子宋侉子挣到钱就一股脑花在妓女身上,快花完了便跨上踢雪乌骓骏马扬长而去(《八千岁》);水手陈泥鳅专门救人捞尸,水性超绝却有随时被淹死的心理准备,所以有钱不是喝酒赌博就是散财济贫,既不置产业也不娶老婆(《故里三陈·陈泥鳅》);菜农薛大娘“偷”汉子,面对闲言碎语不但没有收敛,反而理直气壮地宣称“快活”原则(《薛大娘》)……水乡的男男女女不以教条为忤,不为物质所拘,而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吁求,将生命本能轻松释放出来。这样的生命状态是多么地合乎“水性”:自在、自然而又蕴涵着自由的精神。
与崇尚野性蛮力这一脉现代文化思潮相异的是,汪曾祺表现的生命状态多趋于平静、柔美。他自己就说:“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14]281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汪曾祺笔下的水乡人往往有着顺天知命、恬静自足的特点。就说追求异性,无论是王四海、宋侉子,还是薛大娘,都是顺应本心,率性而为,没有惊天动地的爱恨情仇。更有不少乡民随遇而安、淡泊笃定:从早到晚纳鞋底的侉奶奶、日复一日收字纸的老白、年复一年劳作的戴车匠……他们在凡俗生活中透露出的那份从容淡定与柔顺坚韧,恰恰显示出生命的真谛。对此,有学者作了这样的总结:“在汪曾祺笔下,生命的意义首先表现在自然的流淌之中,表现在对生活和生命的随顺中,表现在对人性的顺从中。”[15]244在平平淡淡的生活长河中顺其自然的流淌,内里却涌动着生命的活力,这里的“水性”呈现出一种静水深流所特有的美。
汪曾祺眼里的家乡水是“柔软”的,汪曾祺笔下的家乡人则往往有着一腔似水柔情,即使男性也缺少应有的阳刚之美,而多少带些阴柔之气。《受戒》中的明海、《大淖记事》中的十一子在恋爱交往中始终是被动,多少有些懵懂不解风情(巧云就怪十一子:“你是个呆子”),他们给人的印象更多的是温和、柔顺、纯真。当然,汪曾祺笔下最具阴柔之美而又最富光彩诗意的人物,还是那一个个少女形象,主要有小英子(《受戒》)、巧云(《大淖记事》)、高雪(《徙》)、崔兰(《水蛇腰》)、刘小红(《熟藕》)、王小玉(《百蝶图》)等。对她们汪曾祺是怀着满腔柔情来刻画的,这来源于他的一种少女崇拜心理,他曾经说:“与其拜佛,不如膜拜少女!”[16]51这其实是他心底水情结的反映。法国学者巴什拉认为:“由朴实的想象和由诗意的想象赋予水的几乎总是女性特征。”[17]15在文化人类学里,水属于阴性物质,具有女性的原型象征意义。而少女无疑是最富女性特征的,汪曾祺崇拜少女,便将水至纯至柔的阴性之美赋予她们身上,作家曹文轩就说:“那些女孩儿——如小英子、巧云,都是些柔情的女孩儿。”[8]66请看《大淖记事》对巧云的肖像描写:
巧云十五岁,长成了一朵花。身材、脸盘都像妈。瓜子脸,一边有个很深的酒窝。眉毛黑如鸦翅,长入鬓角。眼角有点吊,是一双凤眼。睫毛很长,因此显得眼睛经常眯睎着;忽然回头,睁得大大的,带点吃惊而专注的神情,好像听到远处有人叫她似的。
以上描写显然不再是传统写实性的肖像刻画,借此表征某种性格,而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美化,刻意制作一个“美的极致”的标本。所以,胡河清有言:“‘巧云’者也,就是汪曾祺梦中的织女。”[10]56这入梦而来的仙女,当然是一种理想化的女性,她不染人间烟尘,娇媚柔弱,多情善感,说是“柔情的女孩儿”,还不如说是“柔情的化身”。要将这种“美的极致”表现出来,对于深具水情结的汪曾祺来说,除了借助于水意象还会是什么呢?单就巧云这一形象来说,沙洲茅草丛中献身于十一子,无疑是她满怀柔情的淋漓释放,直如月光泻地,清水流转。而月也好,水也罢,皆属阴性,至柔至纯,所以古诗云“月光如水水如天”。如此说来,写月也是写水,这一场景分明是对秦观名句“柔情似水”绝妙演绎,是汪曾祺水情结驱动下的自我心灵抒发,而情结“具有超个体的‘集体’性质,它是种族的共同的心灵的遗留物。它不是个体在后天经验中获得的,而是本能遗传的。它不为个人所觉察、所意识,然而却处处制约着个人的精神、心灵和行为方式”[18]59。所以,这里没有所谓的模仿、借鉴,不是在明确参照、依傍下进行的创作,而是在水情结的制约下对一种集体记忆的暗暗契合,是对一种绵长文脉的无意识传承和发扬。这一场景之所以充满迷人艺术魅力,原因就在于此。巧云这一形象作为“柔情的化身”而被充分艺术美化和幻化,汪曾祺笔下的少女形象莫不如此,她们依水而生,契合着水的品性,充盈着水的灵气,纯净得透明,美丽得脱俗,静如处子,动若脱兔,在文本之间随情流转,灵光弥散。她们与其说是一种性格,不如说是一种美的象征、一种情感的标本,反映了汪曾祺独特的艺术观和审美观。曹文轩说得好:“汪未将这份柔情仅仅用在女孩儿的身上。柔情含在他的整个处世态度之中,含在作品的一切关系之中。”[8]66汪曾祺崇拜水,崇拜少女,少女所表现出来的似水柔情是他心目中“美的极致”,也是他审视整个世界的基本态度。
三、文体:行云流水
汪曾祺小说中风景水波潋滟,人物则洋溢着“水性”,二者相得益彰,共同表现“美”和“爱”。汪曾祺认为:“景物、环境,都得服从于人物,景物、环境都得具有人物的色彩,不能脱节,不能游离。”[19]199所以,汪曾祺虽然爱写风景,却不是为写景而写景,而是将其有机纳入小说叙事肌理之中,与人物水乳交融,浑然一体。重要的是“在这种底蕴深厚的背景与人物关系的基础上,汪曾祺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叙述方式”[20]300。
这种叙述方式的独特性,用汪曾祺自己的话说就是“贴着人物写”,也就是“不能离开人物,单写作者自己的感受”[21]193,而小说中的人物不过是些小人物、凡俗之辈,他们的生活注定没有什么大波大澜。汪曾祺贴近人物,尊重实际,只能采用平铺直叙的叙述方式,他说:“平铺直叙是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不搞突出,不搞强调,不搞波澜起伏,只是平平常常地,如实地,如数地把生活写出来。”[22]209所以,汪曾祺基本上是按照生活原生态的多维流动来叙事的。小说《受戒》就颇具代表性,作者开篇即介绍荸荠庵,引出主人公明海,交代其出家原委、过程,一直写到他入门受戒、与小英子的情感发展,以此构成故事主干,贯通全篇。这中间又插入“当和尚”的地方风习、县城的市井人情、荸荠庵的位置和格局、众和尚的日常起居和性格喜好,还有英子家作为水乡居民而具有的独特地理风貌和生活方式,等等。而这些穿插成分又旁枝斜出,牵扯出其它生活细节。比如介绍庵中生活,就顺势描写了几个和尚的情态,特别是年轻的三师父仁渡,英俊潇洒,以“飞铙”“花焰口”等绝技赢得不少姑娘的芳心,时常惹些风流韵事,这些妙趣横生的细节都一一插入文中。这样,写景与写人相结合,而叙述方式“近似随笔”[23]461,由此形成的小说结构则呈现出“行云流水”般的“随便”:“结构尤其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样写。”[24]80恰似一瀑流动的水而不拘一格,随物赋形,舒放自如,浑然天成,难怪汪曾祺说:“《受戒》写水虽不多,但充满了水的感觉。”[14]281个中奥妙,主要就在于小说整体结构具有水的风范和品格。
汪曾祺小说的叙述方式当然不是单一的,但终不脱平铺直叙之底色,结构也颇“随便”,小说却充满诗情画意,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小说的语言。在汪曾祺那里,语言不再单纯是形式、艺术,还具有本体论意义:“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14]281于是他放言:“写小说就是写语言。”[25]217他追求的是水的境界:“流动的水,是语言最好的形象。”[25]223大致是指语言俗白平常而又富有神韵,也就是汪曾祺所说的“要在平平常常的、人人都能说的,好似平淡的语言里边能够写出味儿”[26]226。他的小说总是以普通口语为主体和质地,弃辞藻,少夸饰,恰似水的无色无嗅,看似平常,但是一经有机串联组合,一句句铺衍开来,一层层荡漾开去,形成一道道“语言流”,渐渐就有了“味儿”。试看小说《岁寒三友》写景片段:
这天天气特别好。万里无云,一天皓月。阴城的正中,立起一个四丈多高的架子。有人早早地吃了晚饭,就扛了板凳来等着了。各种卖小吃的都来了。卖牛肉高粱酒的,卖回卤豆腐干的,卖五香花生米的、芝麻灌香糖的,卖豆腐脑的,卖煮荸荠的,还有卖河鲜——卖紫皮鲜菱角和新剥鸡头米的……到处是“气死风”的四角玻璃灯,到处是白蒙蒙的热气、香喷喷的茴香八角气味。人们寻亲访友,说短道长,来来往往,亲亲热热。阴城的草地被踏倒了。人们的鞋底也叫秋草的浓汁磨得滑溜溜的。
这里写的是市民赶路赏焰火的场景,大量运用的是日常口语、简单叙述、精省白描。其中小吃写到了七八种,仅列举名称,一无修饰,浅白平常。但是连用八个动词“卖”,与之组合成一个个短峭“的”字短语,前呼后拥,一贯而下。整个段落以散句为主,中间杂以成语、偶句和叠音词,长短不一,错落有致,于是乎节奏跳脱,音韵起伏,本身就蕴含着一种与民众生命活力同构的动感韵律,将小城热闹欢快的气氛表现得逸趣横生、异常传神,一幅民间大众狂欢图卷在读者面前铺展开来。这里的语言是艺术,但谁又能说不具备一定的“内容性”呢?
饶有意味的是汪曾祺写语言也讲求“贴着人物写”:“作者的心要和人物贴近,富同情,共哀乐。什么时候作者的笔贴不住人物,就会虚假……即作者的叙述语言也须和人物相协调。”[14]287从叙述方式到语言表达,汪曾祺都是以作品人物为本位,叙述者不是高高在上,随心所欲地塑造人物,更不会将人物看作思想观念的传声筒,而是把话语权交还给人物,让人物在“说话”中自我亮相,而叙述语言也尽可能与之相协调,这也就是巴赫金所谓的“用他人的规矩来规范自己的世界”[27]67。如此“规范”之下,叙述者退场隐身,这不仅恢复了小说人物的主体性,也是对读者的尊重。对此,汪曾祺是有充分自觉的:“现代读者是自由的,他不愿听人驱使,他要用自己的眼睛看生活,你只要扼要地跟他谈一个人,一件事,不要过多的描写。作者最好客观一点,尽量闪在一边,让人物自己去行动,让读者自己接近人物。”[28]224由此汪曾祺与1980年代主流的“伤痕”“反思”小说家们拉开了距离。就说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王蒙,在汪曾祺看来,其小说创作更多是“不贴着人物写”[29]311。王蒙以表现政治生活为主,总是不失时机地离开人物,表达思想观点,赋予作品以政治意义。小说《杂色》中的那匹老马竟然为作者代言:“我只需要一次,一次机会,让我拿出最大的力量跑一次吧。”这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抒怀,应和了主流意识形态所期望的“向前看”:为革命事业而继续奋斗。叙述者以革命者和主人翁的姿态帮助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新的运作,作者也由此实现作品的政治命意。这样,读者的反应就被纳入文本之中,构成隐蔽的叙事对象,小说隐含着一种“对话机制”。说是“对话”,其实作者是居高临下地宣讲和鼓动。而在汪曾祺小说中,这种“对话机制”是不存在的,叙述者是“隐身”的,于是乎像王蒙小说之类的“伤痕”“反思”文学所蕴含的政治意义、社会意义被“抽空”了。而汪曾祺小说的意义就在于没有“意义”,有的只是情绪、意趣和氛围,堪称汪曾祺所赞赏的“无意义诗”[30]271。卡尔维诺说:“文学上的一切虚构,写出来比讲出来更容易让人记住。”[31]332“意义”依靠“讲”,需要灌输给读者;而“诗”只能写,端赖读者去想象、去品味。汪曾祺小说“意义”被“抽空”,正具备了卡尔维诺所珍视的“轻”品格,有力反拨了长期以来中国文学的超负荷之“重”,悄然改写了新时期文学的叙事逻辑。
卡尔维诺心目中“轻”的形象是“风和云”[31]319,这在汪曾祺那里该是“行云流水”吧,苏东坡的这一行文风格为他倍加推崇,“文章写到这样,真是到了‘随便’的境界”[24]80。他还说:“传统的,严格意义的小说有一点像山,而散文化的小说则像水。”[32]78山为重,水为轻。汪曾祺着意打破传统进行小说文体创新,有充分的理论自觉而高度认同于“水”的品性,在叙述、结构和语言等方面都以“流水”作为范式而心追手摹,而对于自己心仪激赏的小说,他也每每誉之为“流水”。西班牙作家阿索林并非一位小说大家,却为他一生钟爱和膜拜,原因在于“他的小说像是覆盖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14]288。他盛赞乃师沈从文的长篇小说《长河》写得像“流水一样”,更是将废名的《竹林的故事》直接看作“是一篇富有诗意的生活的‘流水’”[33]78。这样看来,“流水”也应该是他自己孜孜以求的小说文体风格,他的独特小说文体似可命名为“流水体”。至于其成因,说到底还是得自作家内心深处的“水情结”,汪曾祺自己就说:“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的风格。”[14]281
四、人格:智者乐水
汪曾祺小说充满水气,独具一格,是由他独特的人格决定的。汪曾祺很赞同布封的名言“风格即人”,并且进一步解释说:“作品的形式是作者人格的外化。”[34]71对此汪曾祺有着高度的理论自觉,他在《小说的散文化》一文中有这样的论述:
散文化小说的作者大都是抒情诗人。散文化小说是抒情诗,不是史诗。散文化小说的美是阴柔之美,不是阳刚之美。是喜剧的美,不是悲剧的美。散文化小说是清澈的矿泉,不是苦药。它的作用是滋润,不是治疗。
汪曾祺对“散文化小说”没有进行理论界定,而主要是描述其文体特征,但不难看出他对于创作主体有着足够重视:他劈头即点明“散文化小说的作者大都是抒情诗人”,意味着这些文体特征得自作家主体,这里虽未使用“人格“风格”之类的字眼,却明显是在二者之间画上了等号。循此理不难推出:汪曾祺创制出“流水体”小说,是因为他具有与之相应的文化人格。小说既然富有“阴柔之美”,那么作家人格当属“阴柔”型,恰如该文所称“这一类小说的作者大都是性情温和的人”,汪曾祺举例说:作为“孤独、悲愤的斗士”的鲁迅“同时又极富柔情”,才写出了《故乡》《社戏》这种散文化小说。这可视为汪曾祺的夫子自道,他本人其实就是这类“极富柔情”“性情温和的人”。这种人格当然是由诸多因素铸成的,笔者在此无意全面探讨,只是强调郁结于汪曾祺心底的水情结有着不可忽视的特殊作用。
汪曾祺的故乡高邮属于江南水乡,大运河南北贯穿,高邮湖位于西部,数百条河流纵横交织,全境近一半面积为水域。生于斯长于斯的汪曾祺从小就被水包围着,他说:“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4]185。水,孕育了他的生命,也滋润了他的心灵,其后他踏入尘世,萍踪不定,每每回忆起家乡,回忆起儿时,总是少不了水。故乡水在汪曾祺心目中充满柔情:“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14]281其实,这不过是汪曾祺有意无意的美化,因为饱含浓浓乡情,回望人生来路总免不了如梦似幻,会有意无意地滤掉些沉重和苦涩。而一旦回到现实,同样是家乡水,追叙起来却是另外一副模样。1980 年代初,汪曾祺有一次回乡探亲,临近家乡路遇一个六十多岁的无赖拦车向乘客讨钱,让他作呕。在这种情绪下他写下散文《故乡水》,文中的故乡水竟然了无诗意,全是带给乡民的灾祸,他自述一次大水灾“死了几万人。离我家不远的泰山庙就捞起了一万具尸体”[35]404。所以,故乡水本来有两副面孔,但是更多时候汪曾祺是避实就虚,展现其柔美的一面。这种主观性很强的回忆,不再是一种乡情追怀,更是在与水的依存关系中认同了水对自己精神人格的滋养。对此,学者费振钟有这样的认识,“汪曾祺意识到的‘水’,已不仅仅作为与人的存在方式相对应的形态,被‘鉴戒’,被‘评价’,而是作为对人的姿态性的‘规范’,从而具有更为普遍的、客观的精神文化价值”[36]199。正是在这一点,我们想到了“智者乐水”这一古语。故乡水在汪曾祺心目中极富柔性,正如老子所言“天下莫柔弱于水”,无怪乎这里出生的秦少游,会将词写得那样柔媚婉约。同样,水文化的滋养也造就了汪曾祺的不无阴柔的个性气质。值得注意的是汪曾祺领受水的精神启悟,达到对于“精神文化价值”的认同,并非像乃师沈从文那样惯于独自临水遐思,而总是联系着对家庭和亲人的回忆,充满着世俗温情。汪曾祺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平易随和,淡泊宁静,无意于功名利禄,而嗜好琴棋书画、花鸟鱼虫。这显然迥异于一介腐儒“仁者”。俗话说“仁者乐山”,而这样的父亲哪里有一点儿壁立千仞、森然肃重的山之模样呢,他那么随性悠然,该是被水包围和濡染而深得“智者乐水”之三昧的江南文士吧。对他汪曾祺没有敬畏,有的只是敬爱、亲昵,“没大没小”厮混一起,竟然谈恋爱写情书都与他头碰头商量,终至于“多年父子成兄弟”。汪曾祺对父亲极为认同,该是在与之相处的点点滴滴中领悟了江南水文化精神,逐渐成为像他一样传承江南传统文脉的“智者”。除了父亲,家庭和家族中的女性对汪曾祺也有着不小影响。汪曾祺幼年丧母,却没有因此而缺失母爱,反而得到更多女性的关怀:两位继母对他疼爱有加,视如己出;还有二伯母、干妈、女佣人“大莲姐姐”等都给予他别样的关心呵护。有那样一位如水随性的父亲,又这样在众多女性环绕中成长,汪曾祺自然也就濡染了更多阴柔之气,内心充溢了更多的柔情更多的爱。带着这样一份柔情回忆家乡,故乡水当然会被略去凶险的一面,而像亲人一样“总是柔软的,平和的”。就这样,在汪曾祺心目中,故乡水与亲人水乳交融不可分,拥有一个共同的形象:“爱”与“美”。
敏感于“爱”与“美”的人,有诗人、艺术家的潜质,却不免单纯柔弱,会付出比常人更大代价来应付现实的磨难和挑战。有研究者论及汪曾祺说:“19 岁离开家乡前的他一直都生活在那个近似天堂的高邮小城中,心灵因此变得纯洁明净,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大风大浪,这必然养成了他善良文弱、安分守己的天性,也使他完全无力应付社会的黑暗和历史的悲剧。”[37]177应付社会磨难,对于文弱书生汪曾祺来说,更多是时时眷顾故乡,精神寻根,当然是“在水一方”。除了故乡水还能是什么呢?柔柔清波充盈着爱,泛动着美,帮助他度过社会劫难,抚平精神创伤。小说《看水》写的是水见证了少年小吕的精神成长,汪曾祺说:“《看水》那篇东西里的小孩实际上就是我。”[38]71这篇小说其实是作者的精神疗伤,他所依靠的是水;《受戒》追记的是“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芦花荡乃人生温柔之乡,小说是汪曾祺“文革”中尴尬处境解脱后的自我精神抚慰,所依靠的还是水……水情结潜藏于心底,每每在主人困窘无助时外化并升华为一篇篇名作佳构,而在曹文轩看来:“柔情是一种最高贵也最高雅的情感。”[8]67难怪这些小说是那么恬静、温婉和雅致了。就这样,汪曾祺通过回忆和想象抹去人生的浮流和蹉跎,进入到由文字营造出的一方精神家园,在安宁和谐的水世界中安妥下自己的灵魂。面对种种社会劫难,汪曾祺不是硬碰硬去抗争,而是在顺应中以柔情淡化矛盾,消解冲突,走向安宁与和谐,具有水的风范,显示出“智者”的本色。
“文如其人”,鲁迅在金刚怒目的一面“同时又极富柔情”,才写出了《故乡》《社戏》这种散文化小说;而汪曾祺可以说整个处世态度中都充满柔情,人格使然,顺乎本性。他年轻时即致力于小说散文化的文体变革,他宣称:“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28]461靠什么呢?创作才华自不必说,主要靠的还是禀赋人格,其中那份由水情结升华出来的柔情,柔中有刚,绵绵不绝,不断“冲决”因袭已久的小说定式。“诗缘情”,专擅叙事的小说因感情丰盈而走诗化、散文化,这种小说文体探索在汪曾祺晚年终于大功告成,实现了其艺术夙愿“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39]165。《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等名篇已然成为经典而载入文学史册。“智者乐水”,这些独具审美品格的“流水体”散文化小说,由汪曾祺这种深具水情结而“极富柔情”“性情温和的人”创制出来,这再好不过地诠释了“文如其人”的文学理念。
五、结语
汪曾祺是一位经传统水文化濡染的“智者”,“极富柔情”的人格成就了那么一种极具审美性的散文化小说,这是他在1980 年代文坛一经复出即获普遍瞩目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在于,汪曾祺小说重续了被历史之潮冲断已久的“京派”文学传统,正如丁帆指出的那样:“它标志着一种美学风范的回归,也就是从废名、沈从文开始的‘田园诗风’乡土情结的‘还魂’。”[20]297孙郁也说:“从废名到汪曾祺,有一个精神的承传。”[40]80关于这种“魂”、这种“精神”,人们可能有不尽相同的理解和界定,但其根柢与中国“水崇拜”文化传统有着深刻的联系,这是不可否认的。而且,由此在作家内心积淀而成的水情结,对他们的小说创作起到潜在而制导性的作用,于是专注于“爱”与“美”,钟爱少女形象,文体散文化——汪曾祺与废名、沈从文两位先辈有着高度一致。
汪曾祺师承废名、沈从文二人,又以江南文脉相对接而有所超越。具体说来,他们一个亲禅,一个近道,小说中的水世界或有“桃花源”的隐逸色彩,或有非正统的山俗野趣,而汪曾祺以儒生自命,又得江南俗文化之熏染,小说中展现出的水世界少了些许田园风、传奇性,多了一份生活现象的凡俗性、平淡性,更具民间大地的情味。就这样,在1980 年代初,政治生活还占据文学创作的绝对主导地位,汪曾祺使得日常生活浮出了文学的地表。而且水情结升华而成的从来都是一种高贵的柔情,汪曾祺怀着这种情愫重返文坛,又有力地冲击和中和了当时“潮流内”的热烈的、急切的、感伤的情感,改写了文学的叙事逻辑、话语系统。另外,比起废名、沈从文两位前辈,汪曾祺对于内心的水情结的体认更自觉,感应其召唤而进行小说文体变革也更自觉,并且大获成功。凡此种种,都改变了“新时期”文坛格局。对此,丁帆给予了文学史意味的评价:“汪曾祺小说的复现是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多元化趋势的第一次认同……真正让新时期小说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并直接影响了‘寻根小说’以及‘先锋小说’的创作。在此意义上,汪曾祺扮演了一个‘先驱者’‘引路人’的角色。”[20]296如果从创作主体来看,谁又能否认汪曾祺的水情结在其间起着不可或缺的深刻作用呢?特别是与“寻根小说”的关系,有研究表明:“‘回忆’‘风情习俗’和‘传统文化’成为汪曾祺与‘寻根小说’的契合点,所以,我们说‘寻根小说’与汪曾祺之间,存在着很深的艺术血缘关系。”[20]302这其中的“传统文化”不可不包含“水崇拜”文化传统,这不正是我们民族重要的一支文化根脉吗?在现当代文学发展中,汪曾祺起着承先启后的独特而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