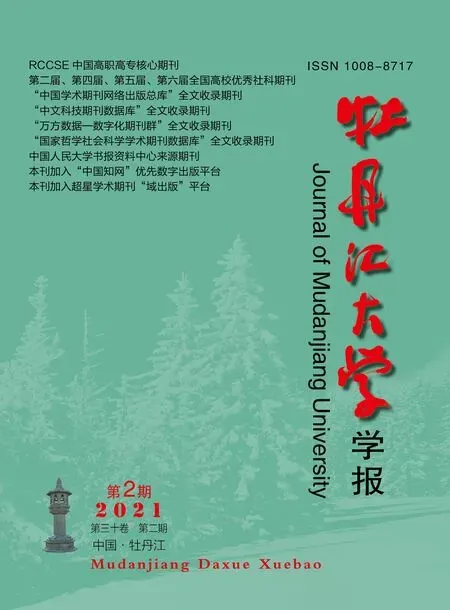《霸王别姬》中程蝶衣的悲剧重奏
2021-12-22王馨梅
王馨梅
(陕西理工大学 ,陕西 汉中 723001)
由李碧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霸王别姬》,故事从清末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影片讲述程蝶衣(张国荣饰)、段小楼(张丰毅饰)、菊仙(巩俐饰)三人近乎五十年的感情纠葛。程蝶衣无疑是整部剧的焦点,他用一生阐释“人生如戏,戏如人生。”[1]对师哥超出普通师弟关系的情感与菊仙对段小楼男女之间的情愫相互交织,一定程度上成全了程蝶衣艰辛又极富传奇色彩的生命之诗。程蝶衣从《霸王别姬》京戏中感悟“从一而终”,不惜用整个生命坚守“虞姬”的人生信念。“不疯魔不成活”是真诚的生命个体对束缚的礼教和时代发出的呐喊。歌德曾说:“艺术要通过一个完整体向世界说话。”[2]电影《霸王别姬》在时间层面跨越了半个世纪,其中的信念、人物、意境都独具审美内涵,如同一个完整体传递着生命的悲剧美。
一、“戏中戏”信念悲剧
电影艺术语言主要包括声音、叙事、画面、蒙太奇手法等。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安麦茨提出:“所谓套层结构是指电影故事中的故事,即戏中戏,与画中有画,小说中谈小说一样。”[3]《霸王别姬》本是京剧中的经典曲目,电影将此运用到电影的名称上。电影的内容采用“戏中戏”的套层结构,舞台上讲述饰演“霸王”和“虞姬”的命运,现实中展现两位名角儿在风云变幻的大历史背景下的个人命运。通过极富个人特色的戏剧语言,看到程蝶衣终未出戏的悲剧人生。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4]历史上的楚霸王临死之前对命运所发出的感叹让我们为他和虞姬情比金坚的爱情所震撼。舞台上气势威武的“楚霸王”段小楼走下万众瞩目的舞台,并没有“真霸王”的心胸与壮志。“楚霸王”项羽内在精神内核“从一而终”没有在段小楼的生命中得到传承。相反,剧中“虞姬”程蝶衣无论是在京戏还是在现实中都用生命坚守“从一而终”。面对段小楼与菊仙的男女之情,程蝶衣对师兄说:“你忘记我们是怎么唱红的吗?还不是师傅那句‘从一而终’。”[5]提醒师哥对待京戏和人都要一心一意,同时含蓄表达对师兄难以向世人言说的特殊情感。面对师兄的抛弃,他说:“说好的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6]影片末,他与师兄最后一次排练对两人没有共同登台的日子计算的精确都表现出这位“真虞姬”对于戏剧和师哥无可替代的爱和忠贞不渝的信念。文革特殊时期,段小楼大肆揭露、污蔑程蝶衣力求自保。与“楚霸王”那句“虞兮,虞兮,奈若何”[7]形成反差,成为对“假霸王”表里不一的强烈讽刺。
“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8]一开始程蝶衣念错戏词吃了不少苦,差点断送了他的戏路。最初的“虞姬”与他本人仍属于两个不同的生命个体。重复念错戏词,程蝶衣被师兄用烟袋锅儿捣嘴巴,满嘴流血。惨绝人寰的惩罚彻底使少年时期的“小豆子”完成性别转换。“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9]数十年再未念错戏词,“虞姬”“程蝶衣”融为一体。影片末,历经半个世纪沧桑的师兄二人排练曾经名震一时的《霸王别姬》,没有正式的戏台,起初的默契也被生活无情打磨后消失。“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最后一次念错戏词与最初学艺时形成呼应,程蝶衣大半辈子的心酸涌上心头,“虞姬怎么演,也都有一个死”[10],“虞姬”和自己只因戏交织,入戏太深幡然顿悟。“我本是男儿身”,一辈子的艰辛皆源于此句。“虞姬”与“程蝶衣”两个角色分离,一句“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从程蝶衣的整个悲惨人生来看,形成嘲讽,一切皆是虚妄,“不疯魔不成活”,程蝶衣终未出戏,拔剑自刎,与“虞姬”拥有共同的结局,“戏中戏”与现实重合。“要想人前显贵,您必定人后受罪。今儿个是破题,文章还在后头呢。”[11]小小年纪的程蝶衣被老师傅以惨无人道的方式教学,本以为一日熬成“角儿”就可以不再遭受人生之苦,谁知被师傅说中。给袁四爷唱戏、给日本人唱戏、被师哥揭发,让原本热爱京戏的程蝶衣丧失希望。成为京城“名角儿”没有改变程蝶衣的悲剧人生道路,一时风光换来一生孤独和悲凉。小时候所受的学艺之苦只是悲剧人生的开始,也就是师傅说的“破题”一语成谶。一众弟子深受封建礼教压迫,小癞子出逃后被师傅毒打,吃完私藏的所有糖葫芦,亲眼目睹小豆子被毒打后上吊自杀。少年不经事的弱小生命被无情的封建规矩束缚、压制,最终走向死亡。程蝶衣虽没有因礼教压迫走向“死亡”,但是被迫植入的教条“信念”缠绕着他一生,他没有逃出“从一而终”“不疯魔不成活”的预言,深受毒害却不自知。
二、“戏痴”悲剧形象美学
“电影的美学特点之一就是空间中的时间与时间中的空间结合,影像和运动成为电影最重要的特征。”[12]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认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13]《霸王别姬》整个电影时间跨度较大,便于我们在较短的时间里观察、思考人物整个生命轨迹。空间与时间交织,人物形象在行动和变化中被塑造、影响。程蝶衣形象在整个影片中处于不可忽视的中心位置,属于所有矛盾的中心,他个人形象具有较大的美学价值。
程蝶衣出生于烟花柳巷,生母艳红把他送到戏班。“实在是男孩大了留不住,这才投奔您来了,您只要留下他,怎么着都行。”[14]戏班虽不是什么高贵职业,总能提供最基本的温饱。为让戏班师傅顺利收程蝶衣为徒,艳红不惜将他多出来的指头用菜刀剁掉——六指儿变五指儿。小时候的“小豆子”从剁掉手指开始人格独立性已经被阉割,变成真正的“女娇娥”。戏班子里的众多学徒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小豆子、小癞子、小石头”以简单、毫无性别特征的代号命名。底层残酷的生存方式让“小癞子”式的弱者丧失对生活的希望,底层小学徒面对惨无人道的生存法则以最无力的抗争方式——自杀来放弃生命,既是抗争也是对命运不公的觉醒。处于这种成长环境中,同伴之间容易产生相互依赖,程蝶衣对师兄段小楼产生情愫皆在情理之中。第一次听师兄说菊仙,他立即表现出对这位从未谋面的风尘女子深深的厌恶。时刻提醒师兄要“从一而终”,对京戏和他这个师弟都要一生独一,不能三心二意。“从一而终”是程蝶衣的人生信条,他用此方式要求自己也要求别人。师兄不再是儿时为他遮风挡雨的“小石头”,而他还是依附于师兄的“小豆子”。“楚霸王”要去追寻自己的幸福,“我是假霸王,你才是真虞姬。”[15]“虞姬”终未出戏,百般阻拦无果。“京戏”和“楚霸王”师兄是程蝶衣毕生所爱,菊仙和段小楼成亲标志着程蝶衣对爱情美好憧憬的破灭。站在窗外偷窥菊仙和段小楼,凸显被成长环境阉割后,程蝶衣畸形的婚恋观念。黑格尔提出:“当有限的外在感性形式无法承载强大的内在精神时,它就必然会发生扭曲甚至毁灭。”[16]躲在阴暗的角落,露出阴冷、令人惧怕的眼睛窥视别人的生活,与舞台上勇于表达爱的“虞姬”形成反差。难以置信,受万人追捧的程蝶衣面对自己情感时,内心深处所表现出异乎常人的扭曲。陈凯歌自己说程蝶衣真的是那种可以称之为疯子的艺术家,他这样的痴人,一旦走下舞台,走进现实的人群中,注定是孤独的,注定是寂寞的。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天真、他的诚实,甚至是他的偏执和嫉妒,都很美,很真实。受人诬陷后,明知自己受爱慕者帮助不会有牢狱之灾,仍沉迷于大烟静观师兄为自己四处奔走。程蝶衣不再是小时候单纯的“小豆子”,他不希望师兄因成家而忽略自己的存在,想方设法引起别人的同情和重视,赢得心理上欺骗他人的愉悦。
文革前夕,风云变幻。为保全个人安危,菊仙、段小楼销毁家中与“四旧”相关的一切旧物。古董酒杯发挥完自己最后一次功用后被无情地摔碎。程蝶衣不能再登台唱戏,失去师兄后又失去京戏,双重打击使他再也没有追求美好的动力。精神家园不复存在,华丽的戏服被程蝶衣点燃。看似漫不经心的举动,实则表达“戏痴”适者生存的无奈和优秀传统文化被毁灭的痛心。特殊的年代,在始料不及的灾难面前往往最能看到人性原本的样子。曾经的京城名角儿,现在的“牛鬼蛇神”,角色翻转形成讽刺。面对拷问,段小楼为自保,对生命中最爱他的人造成了不可磨灭的打击。揭露菊仙出身于风尘,诋毁程蝶衣与袁四爷不被世人所接纳的非比寻常的关系,不堪回首的伤心往事彻底将程蝶衣儿时记忆中处处保护他的师兄形象毁灭,一切值得回忆的美好都成为幻影。“假霸王”将人性的丑恶、自私、苟且暴露无遗。人间找不到答案就问苍天“你楚霸王都跪下来求饶了,那这京戏他能不亡吗?”[17]程蝶衣恨“假霸王”的虚情假意,鄙视只求苟且的人生态度。“我揭发姹紫嫣红,我揭发断壁残垣。”[18]激烈斗争中,比起“假霸王”歇斯底里的揭发和诋毁,程蝶衣仍然将段小楼所有的不幸归咎于菊仙,大肆宣扬这个女人的卑劣,同时,自己的人生悲剧也全施压在和他一样出生低微的弱女子身上。站在道德之上,鞭笞他人的不幸。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任何事物,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19]程蝶衣超乎常人的反抗方式令“虞姬”的美,转换成人性的恶。菊仙和程蝶衣都是被“假霸王”抛弃的“虞姬”,所有真挚、热爱在残酷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程蝶衣短暂的一生无疑充满不幸与悲凉,被生母抛弃,遇到保护自己的师兄却也最终遭受背叛,甚至在自己临死前才发现自己“又不是女娇娥”而产生身份认同。“要想人前显贵,您必定人后受罪。”为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童年的程蝶衣“吃得苦中苦”却终究没有逃脱命运的捉弄,为戏痴狂为戏而死。失去自我、所爱、人生,不断失去的人生不曾回头。
三、时代悲剧“意境”
黑格尔:“遇见一件艺术作品,我们首先见到的是它直接呈现给我们的东西,然后追究它的意蕴或内容。”[20]《霸王别姬》不仅是一部经典电影,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军阀混战为起始,一直延续至20世纪80年代,程蝶衣属于被时代裹挟前进的芸芸个人。个人命运与时代交融而因此被改写。戴锦华认为:“中国的历史不是一个相衔于时间链条中的进程,而是一个在无尽的复沓与轮回中彼此迭加的空间,一所万难轰毁的铁屋子,或一处历劫岿然的黄土地。于是,历史成了一个在缓慢的颓败与朽坏中的古旧舞台,而年代、事件与人生,则成了其间轮演的剧目与来去匆匆、难于辨认的过客。”[21]变幻无常的时代浪潮中,中国的历史变迁反映在李公公、袁四爷昨日是高高在上的既得利益者,今日则沦为阶下囚,接受时代的审判与惩罚。李公公坐在冰凉的青石板上迎接新中国成立,袁四爷临死前仍不减当年“贵族”傲气,他们的结局没有引起观影者足够的同情,当年张扬跋扈历历在目,甚至要为他们的下场拍手称快。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提出关于理想悲剧定义:“最完美的悲剧里,情节结构不应该是简单直接的,应该是一种复杂曲折的,并且他所摹仿的行动必须是能引起哀怜和恐惧的。因此摹仿的人应该是在道德品质和正义上并不是好到极点,但是他的遭殃并不是由于罪恶,而是由于某种过失或弱点。”[22]程蝶衣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能引发我们的悲悯和恐惧,原因在于他生性单纯,即使被师兄抛弃,自己所爱的京戏被践踏却仍然保持“从一而终”,对毕生所爱坚贞不渝,保持真性情。特殊年代里,人人都在自保,只有程蝶衣在乱世仍然保持赤子之心的冲动,不计个人得失说出怎样的京剧才是“美”,勇敢捍卫“美”的纯净与真实。“真性情”敢于说真话而遭到迫害,我们为他所受的苦难鸣不平。同时程蝶衣的遭遇也让观众心生恐惧,我们因剧中人的遭遇而引发对自身命运的思考,如何在命运这双看不见的‘手’的捉弄中既保持初心,又可以在乱世存活。从小收养的小四儿变成对立敌人,亲情随即破碎。一系列的复沓与轮回搅碎了程蝶衣平静的一生。英国学者斯马特在《悲剧》中说到:“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反抗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23]程蝶衣为自己筑起的“桃花源”是那样的弱不禁风,若逆来顺受,作一个识时务的“俊杰”便可以平安无事,戏中的“虞姬”和现实中的程蝶衣都有“傲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她们的悲剧也正是源于此,正是坚毅地反抗,加剧外界对生命本体的挤压。时代的一粒尘埃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如王国维所言“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深浅而已”。[24]《人间词话附录》中也提到,有意境的作品应当是有言外之味,弦外之响。言外之意越多,则意境越深,言外之意越少,则意境越浅。整个《霸王别姬》的时代背景看似默不作声,个人的命运无奈地被翻转、重塑。电影中所有人的命运笼罩在时代的意境中,像是有一双“手”捉弄那些坚韧抗争的弱者,没有人逃出宿命的安排。《霸王别姬》虽是一部电影,然而它自身所要表达的关于生命的意义值得不同时代的人去思考。刘登瀚主编的《香港文学史》针对李碧华小说的这一特点这样写道:“李碧华的小说并不是一般的纯言情小说,它们有比爱情更丰富的内涵,在历史的、社会的、美学的、哲学的层面上所给人的思考,是一般的言情小说所不能比拟的。”[25]通过电影,我们看到不同时代雕刻在个人身上的印记,无关乎好坏。电影用特别的方式记录一代人的历史。
结语
电影如诗一样奇妙,它虽不如真实世界现实,却在一定空间里合情合理地凿开生命的一扇窗,我们透过时间的裂缝看到关乎他人的人生,似乎很遥远却又因戏里人物的悲剧而同情和恐惧,由此拉近他们与我们的距离。一部好的电影在每个时代都能奏出属于时代的乐章。《霸王别姬》是一首关于人性、人生的诗,戏剧语言、人物、时代背景组成电影整体。假亦真时真亦假,人物故事的“真”与“假”无从探究,符合一切事物应该有的样子,遵循生命本体的内在规律,个人与时代交织的悲剧在新时代背景下也依然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