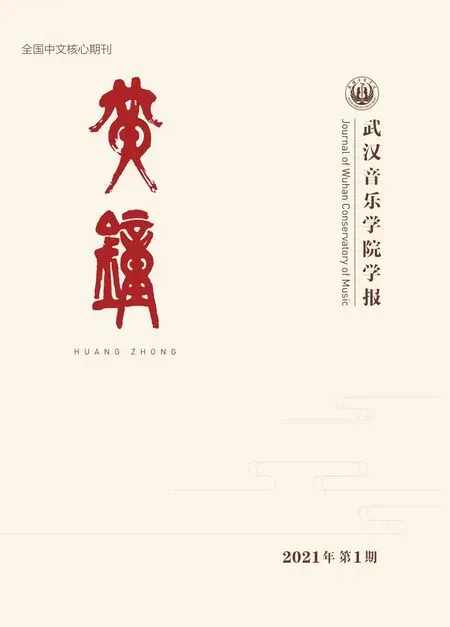孔子的礼乐言论新解——“以礼让为国”“成于乐”“朝闻道”三则为中心
2021-12-06孙尚勇
孙尚勇
孔子言论有相当一部分长期未获确解,连带而及的是,孔子的礼乐政治思想亦未能获得普遍认知。朱维铮认为其主要原因是,以《论语》为代表的相关文献记载,没有给出孔子言论的背景,甚至没有给出对话者。①朱维铮:《历史的孔子与孔子的历史》,《走出中世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5页。文献记载过于简略,这是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如果能从意义指向上进行恰当分别,或可获得对孔子部分言论的准确认知。孔子言论大致可以区别为较为明确的两类:第一类关注一般的社会生活,着眼于中下层个体;第二类关注上层的政治运作和文化传统,着眼于群体。《论语》所载“以礼让为国”“成于乐”和“朝闻道”三则言论,属于上述第二类,所论乃孔子关于治国理政孰先孰后的整体考量,代表了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本文拟就这三则言论的内涵谈一些个人的新的认识,庶可准确把握孔子的礼乐之道。
一、以礼让为国:孔子的理想政治
《论语·里仁》: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②[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二,《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2页。
皇侃疏:
言人君能用礼让以治国,则于国事不难。故云何有,言其易也。故江熙曰:范宣子让,其下皆让之。人怀让心,则治国易也。
若昏暗之君,不为用礼让以治国,则如治国之礼何。故江熙曰:不能以礼让,则下有争心,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唯利是恤,何遑言礼也。③[三国魏]何晏集解、[南朝梁]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49页。
此后注家都以《左传·襄公十三年》君子曰“让,礼之主也。范宣子让,其下皆让”④[春秋]左丘明撰、[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二,影印[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六册),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年,第555页。为依据,将“礼让”解释为以礼谦让,将“为国”理解为治理国家。这一传统的理解大有疑问。
首先谈“为国”。
讨论如何治理国家,《论语》多用“为政”一词。此类材料很多,兹举三条如下: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⑤[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一,《四书章句集注》,第53页。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⑥[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一,《四书章句集注》,第59页。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⑦[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七,《四书章句集注》,第142—143页。
与“为政”相关的,又有“问政”,这些材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政”的内涵。如: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⑧[宋]朱熹:《论语集注》卷六,《四书章句集注》,第135—136页。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⑨[宋]朱熹:《论语集注》卷六,《四书章句集注》,第139页。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⑩[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七,《四书章句集注》,第146页。
以上各例中的“政”,相当于今天所说的行政。古有“八政”之说,或解为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⑪《尚书·洪范》,[唐]孔颖达等疏:《尚书注疏》卷十二,影印[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一册),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年版,第171页。或解为饮食、衣服、事为、异别、度、量、数、制。⑫《礼记·王制》,[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疏附[唐]陆德明音义:《礼记注疏》卷一三,影印[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五册),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年版,第269页。据上可知,孔门讨论较多的“为政”,即从政,指从事具体的行政事务管理。
故在孔子那里,“为政”只不过是治理国家的一个方面。孔子曰: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⑬[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一,《四书章句集注》,第54页。
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遯心。——《礼记·缁衣》⑭[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疏附[唐]陆德明音义:《礼记注疏》卷五十五,第927页。
这两处记载,意思相近,以“政”“刑”“德”“礼”为治理国家的四项手段,“政”是其中的一种。这四项手段,孔子亦别为两类:“政”和“德”属于预先引导的手段,“刑”和“礼”则属于强制性后续手段。《礼记·乐记》曰:“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⑮[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疏附[唐]陆德明音义:《礼记注疏》卷三十七,第667页。简单比照便知,上引子路问“为政奚先”,孔子所云“名”“言”“事”“礼 乐”“刑罚”诸 项,“名”“言”“事”皆当属于“政”的内容。《乐记》较《论语》所载,以“乐”取代了“德”。《礼记·乐记》又曰:“乐者,所以象德也。”⑯[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疏附[唐]陆德明音义:《礼记注疏》卷三十八,第678页。“乐者,德之华也。”⑰[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疏附[唐]陆德明音义:《礼记注疏》卷三十八,第682页。“乐章德。”⑱[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疏附[唐]陆德明音义:《礼记注疏》卷三十八,第684页。故孔子所说“导之以德”“教之以德”,实即“导之以乐”“教之以乐”。朱熹曰:“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⑲[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一,《四书章句集注》,第54页。故综合孔子和《乐记》的说法,“德”是国家治理的根本,其推行者首先为礼和乐,“政”为具体实施推行的手段,“刑”则属于防范措施。故孔门所论“为政”指如何行政,即治理国家的具体行政措施。
除“以礼让为国”之外,孔子和弟子还谈及与“为国”意思相近的“为邦”。如: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论语·子路》⑳[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七,《四书章句集注》,第145页。
朱熹注:“为邦百年,言相继而久也。胜残,化残暴之人,使不为恶也。去杀,谓民化于善,可以不用刑杀也。盖古有是言,而夫子称之。”据朱注,“为邦”合教化、行政和刑罚而言,涵盖了“为政”。但我们注意到,“为邦”不仅仅是治理邦国,而更多指向了治理天下。《论语·卫灵公》记载了另外一条“为邦”的材料: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㉑[宋]朱熹:《论语集注》卷八,《四书章句集注》,第164—165页。
孔子回答颜回“为邦”之问,谈到了正朔、车服和乐舞制度,跟谈论“为政”迥然相异。与之相近的,又有孔子回答子张问“十世”:
子张问曰:“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㉒
孔子论“十世”,所谈是他视作国家根本制度的礼仪问题,显然亦与上文所举孔子回答弟子时人“为政”“问政”大不相同。故朱熹注“颜渊问为邦”曰:“颜子王佐之才,故问治天下之道。曰为邦者,谦辞。”
根据上面的讨论,可以确定,“以礼让为国”之“为国”与“为政”不同,并非处理国家行政事务的意思,而是在讨论天下国家的根本制度问题。
弄清“为国”的涵义,“以礼让为国”的“让”字就容易理解了。《论语》他处所见“让”字,大多可以解释为谦逊。如子贡所言“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㉓《论语·学而》,[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一,《四书章句集注》,第50—51页。,子曰“当仁不让于师”㉔《论语·卫灵公》,[宋]朱熹:《论语集注》卷八,《四书章句集注》,第169页。。但“以礼让为国”之“让”却不能简单理解为谦逊。《论语》中有一处跟“以礼让为国”近似的说法——“为国以礼”: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夫子哂之。……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论语·先进》㉕[宋]朱熹:《论语集注》卷六,《四书章句集注》,第131—132页。
此处的孔子“为国以礼”云云,意谓用礼来治理国家,“让”是应有之义,子路“率尔而对”显得太不谦逊。表面看,“以礼让为国”,只是在“以礼为国”四字中加上了一个“让”字,但两处表述的意义指向却大不相同。朱熹注以为“让者礼之实也”㉖[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二,《四书章句集注》,第72页。,即让是礼的精神实质。然《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掌“十有二教”,其前四项为:“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郑玄注:“阳礼,谓乡射、饮酒之礼也。”㉗[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十,影印[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三册),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年版,第151页。由此可知,“让”不过是乡射和乡饮酒一类“阳礼”的核心精神,“让”并不能概括“礼”的所有层面,故朱熹“让者礼之实也”的说法可能不得要领。
上引《论语·里仁》的一段材料中,孔子两次使用“以礼让为国”,说明他有意在“以礼为国”之外突出强调“让”,结合前面对“为国”的讨论,可知这个强调的“让”字不能理解为一般层面的谦逊之意。循着这个思路,我们会发现,孔子对泰伯的表彰很有意味:
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㉘《论语·泰伯》,[宋]朱熹:《论语集注》卷四,《四书章句集注》,第103页。
综合观之,孔子“以礼让为国”的言论,其内涵是探讨“以天下让”的根本制度问题。
传世文献中,孔门明确谈论禅让的记载并不多。郭店楚简《唐虞之道》详尽讨论了禅让制度的流行、废止及其优越性,为我们正确理解孔子“以礼让为国”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支撑。其中有曰:
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故昔贤仁圣者如此。身穷不贪,没而弗利,穷仁矣。必正其身,然后正世,圣道备矣。故唐虞之道,禅也。
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上德则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贤则民举效而化乎道。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如此也。㉙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125页。
“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此句将作为社会政治根本制度的“禅”提到了无以复加的最高等级,可见孔儒对禅让制的推崇。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㉚《论语·子罕》,[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五,《四书章句集注》,第110页。“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㉛《论语·述而》,[宋]朱熹:《论语集注》卷四,《四书章句集注》,第98页。对礼乐继承者的天命的自信,是孔子提倡以禅让“为国”的心理基础和栖栖以求的内在动力。与《礼记·礼运》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的诘问,既体现了孔子对理想政治的渴望,也体现了孔子在当世对自己政治理想的坚持。孔子的理想政治即“仲尼祖述尧舜”,其政治理想则是退而求其次的“宪章文武”。㉜《礼记·中庸》,[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疏附[唐]陆德明音义:《礼记注疏》卷五十三,第899页。《唐虞之道》对禅让的极力推崇,与孔子理想的政治制度高度契合。㉝
二、成于乐:孔子的政治理想
《论语·泰伯》: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㉞[宋]朱熹:《论语集注》卷四,《四书章句集注》,第105页。
何晏集解:
苞氏曰:“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也。”
氏曰:“礼者,所以立身也。”
孔安国曰:“乐,所以成性也。”㉟[三国魏]何晏集解、[南朝梁]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第107页。
皇侃义疏:
此章明人学须次第也。云“兴于《诗》”者,兴,起也,言人学先从《诗》起,后乃次诸典也。所以然者,《诗》有夫妇之法,人伦之本,近之事父,远之事君故也。又江熙曰:“览古人之志,可起发其志也。”云“立于礼”者,学《诗》已明,次又学礼也。所以然者,人无礼则死,有礼则生,故学礼以自立身也。云“成于乐”者,学礼若举,次宜学乐也。所以然者,礼之用,和为贵,行礼必须学乐,以和成己性也。注孔安国曰乐所以成性。王弼曰:“言有为政之次序也。……”侃案:辅嗣之言可思也。且案《内则》明学次第,十三舞《勺》,十五舞《象》,二十始学礼,惇行孝悌。是先学乐,后乃学礼也。若欲申此注,则当云:先学舞《勺》舞《象》,皆是舞诗耳。至二十学礼后,备听八音之乐和之,以终身成性,故后云乐也。㊱[三国魏]何晏集解、[南朝梁]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第107页。
以上苞氏、孔安国、江熙和皇侃诸人,皆认为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之说在讨论个体学习乃至历练成就的先后次序,独有王弼一家以为“言有为政之次序”。皇侃虽然认识到“辅嗣之言可思也”,事实上却否定了王弼的见解。但皇侃的论证并不可信。《礼记·内则》:“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郑玄注:“先学《勺》,后学《象》,文武之次也。成童,十五以上。”㊲[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疏附[唐]陆德明音义:《礼记注疏》卷二十八,第538页。对照《内则》原文和郑注便知,皇侃“先学《勺》舞《象》,皆是舞诗”,既有意回避了“诵《诗》、舞《勺》。成童舞《象》”之前的“学乐”二字,亦纂改了郑玄注,强以“舞《勺》”“舞《象》”为诗,是“诵”的对象。这种为疏解注义,而不顾经典文本和前人正解的荒谬做法,颇令人难以想象。
王弼之外,中唐韩愈和李翺的意见亦极具启发。《论语笔解》卷上:
韩曰:三者皆起于《诗》而已,先儒略之,遂惑于二矣。李曰:《诗》者,起于吟咏情性者也。发乎情,是起于《诗》也。止乎礼义,是立于礼也。删《诗》而乐正《雅》《颂》,是成于乐也。三经原一也,退之得之矣,包氏无取焉。㊳[唐]韩愈、李翱合注:《论语笔解》(及其他两种),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0页。
韩愈和李翱将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理解为孔子删《诗》,以述西周礼乐文化。此说当得之于《史记·孔子世家》等文献有关孔子删《诗》的记述,较前人的解说更进一步。
王弼和韩李之外,古代其他注家的意见,大体为宋儒和后来研究者所继承或发扬。朱熹注:
乐有五声十二律,更唱迭和,以为歌舞八音之节,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查滓。故学者之终,所以至于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德者,必于此而得之,是学之成也。按《内则》,十年学幼仪,十三学乐诵《诗》,二十而后学礼。则此三者,非小学传授之次,乃大学终身所得之难易、先后、浅深也。㊴《论语·泰伯》,[宋]朱熹:《论语集注》卷四,《四书章句集注》,第105页。
钱穆说:
乐者,更唱迭和以为歌舞,学其俯仰疾徐周旋进退起迄之节,可以劳其筋骨,使不至怠惰废弛;束其血脉,使不至于猛厉偾起。而八音之节,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学者之所以至于义精仁熟而和顺于道德者,每于乐得之。是学之成。㊵钱穆:《论语新解》,《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289页。
杨伯峻说:
孔子所谓“乐”的内容和本质都离不开“礼”,因此常常“礼乐”连言。他本人也很懂音乐,因此把音乐作为他的教学工作的一个最后阶段。㊶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1页。
李泽厚说:
“成于乐”,就是要通过“乐”的陶冶来造就一个完成的人。因为“乐”正是直接地感染、熏陶、塑造人的情性心灵的。……“成于乐”之所在“兴于诗”“立于礼”之后,是由于如果“诗”主要给人以语言智能的启迪感发(“兴”),“礼”便是给人以外在规范的培育训练(“立”),那么,“乐”便是给人以内在心灵的完成。㊷李泽厚:《华夏美学》,北京: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52页。
以上,朱熹以为孔子此所云“乐”为“更唱迭和,以为歌舞八音之节”,“成于乐”则是指“学者之终”,即掌握了“更唱迭和”等,便意谓学者“学之成也”。朱熹援引了《礼记·内则》的相关内容作为说明。《内则》原文如是:“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衣不帛襦袴。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㊸[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疏附[唐]陆德明音义:《礼记注疏》卷二十八,第538页。朱熹注意到《内则》十三岁学乐、诵《诗》,二十学礼,是先学乐,后诵《诗》,后学礼,与孔子兴诗,立礼,成乐,二者次序不同,故他强调指出孔子此处所言“非小学传授之次,乃大学终身所得之难易、先后、浅深”。但朱熹忽略了最为重要的问题:孔子所说次序与《内则》个体学习次序之间差异的根本原因可能不在于小学或大学的不同。《礼记·学记》曰: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㊹[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疏附[唐]陆德明音义:《礼记注疏》卷三十六,第649页。
《学记》此段所论正是个体学习的成就,七年学习为“小成”,通过九年学习达到“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是为“大成”。然而达到“大成”,仍不是“大学终身所得”,“大学之道”要求个体能够做到“化民易俗”,使近悦远怀。可知,朱熹以“兴诗立礼成乐”说的是“大学终身所得之难易、先后、浅深”,亦不确。
总体来看,传统对“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主流理解着眼于个体教育和个人学习的先后次序,然而这一理解却与《礼记·内则》和《学记》所言个体养成的诗礼乐次序无别显相违背。《周礼》和《礼记》的另外一些记载同样表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所论决非个体受教育者的成就问题,也决非教学工作的次序问题。《周礼·春官宗伯》: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列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㲈》《大夏》《大濩》《大武》。㊺[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十二,第336—337页。
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教乐仪:行以《肆夏》,趋以《采荠》。车亦如之。环拜,以钟鼓为节。㊻[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十三,第350页。
大胥掌学士之版,以待致诸子。春入学,舍采,合舞。秋颁学,合声。以六乐之会正舞。以序出入舞者。(郑玄注:“春始以学士入学宫而学之合舞,等其进退,使应节奏。”“春使之学,秋颁其才艺。所为合声,亦等其曲折,使应节奏。”“大同六乐之节奏,正其位,使相应也。言为大合乐习之。”“以长幼次之,使出入不纰错。”)㊼[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十三,第352—353页。
籥师掌教国子舞羽龡籥。㊽[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十四,第367页。
《礼记·王制》曰: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㊾[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疏附[唐]陆德明音义:《礼记注疏》卷十三,第256页。
《礼记·文王世子》曰:
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皆于东序。小乐正学干,大胥赞之。籥师学戈,籥师丞赞之。胥鼓《南》。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庠。㊿[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疏附[唐]陆德明音义:《礼记注疏》卷二十,第392—393页。
以上《春官宗伯》所记为大司乐、乐师、大胥和籥师教国子乐德、乐语和各类乐舞,可知“乐”是始教的科目,不是教育或学业终得成就的标识。《王制》所记《诗》《书》《礼》《乐》四教是同等的,只是教授时节有别,并无次序先后的不同。《文王世子》所记则更为详尽全面,规定教育世子和学士要按照季节时令,春夏教手执干戈的武舞,诵《诗》习弦,秋冬教手执羽籥的文舞,读《书》习礼。文舞二舞是古代乐的最高形态,《诗》《书》礼俱在,西周教育各项是同时进行的,证明从一般的教和学的角度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理解为教学的次序是不对的。
孔子所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如皇侃等人所论,是始于《诗》,中于礼,终于乐,这一点没有疑问。但很明显,始《诗》中礼终乐与先秦时期个体教育教学实践中《诗》、礼、乐先后无别不相符合。那么,孔子所云《诗》、礼、乐的先后次序,其意义指向究竟何在?答案只能从王弼“言有为政之次序”一句当中去寻找。兹将王弼的解说具引于下:
言有为政之次序也。夫喜惧哀乐,民之自然,应感而动,则发乎声歌,所以陈诗采谣,以知民志风。既见其风,则损益基焉。故因俗立制,以达其礼也。矫俗检刑,民心未化,故又感以声乐,以和神也。若不采民诗,则无以观风。风乖俗异,则礼无所立。礼若不设,则乐无所乐。乐非礼,则功无所济。故三体相扶,而用有先后也。〔51〕[三国魏]何晏集解、[南朝梁]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第107页。
王弼所言“为政之次序”,首先为“陈诗采谣”,其次为“因俗立制,以达其礼”,其次为“感以声乐以和神”。若换用先秦两汉儒学所使用的概念,王弼所理解“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内涵便是:采诗、制礼、作乐。
从孔子追逐实现个人政治理想的层面来理解,“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之“兴于《诗》”,显然是针对《诗》来说的,而且只能是针对经他整理过的《诗》来说的。孔子将《诗》视作新的礼乐政治实施教化的起点和基础。《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曰:“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世道者孝悌,说之以义而观诸体,成之以文德。”〔52〕[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7页。此处“先以《诗》”即“兴于《诗》”,但“先以《诗》”却不能理解为一般个体教育教学从《诗》开始,而是面向整个社会推行《诗》教,以《诗》来教化天下,培养人们普遍的“文德”。
《礼记·乐记》曰:
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干戚之舞,非备乐也,孰亨而祀,非达礼也。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乐极则忧,礼粗则偏矣。及夫敦乐而无忧,礼备而不偏者,其唯大圣乎。〔53〕[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疏附[唐]陆德明音义:《礼记注疏》卷三十七,第668、670页。
以上材料证明孔儒视礼乐为治天下之途径和天下大治的表征,可见王弼的理解合于孔门对西周王道政治的认知。如此,将孔子所云“成于乐”之“成”理解为《乐记》“王者功成作乐”之“成”,可谓顺理成章。《论语·阳货》曰: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54〕[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九,《四书章句集注》,第177页。
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言治小何须用大道也。”又:“道,谓礼乐也。乐以和人,人和则是使也。”又:“戏以治小而用大道也。”皇侃义疏:“牛刀,大刀也。割鸡宜用鸡刀,割牛宜用牛刀。若割鸡用牛刀,刀大而鸡小,所用之过也。譬如武城小邑之政,可用小才而已,用子游之大才,是才大而用小也。故缪播曰:惜其不得道千乘之国,如牛刀割鸡,不尽其才也。”〔55〕朱熹注:“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礼乐,则其为道一也。但众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独行之。故夫子骤闻之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戏之。而子游以正对,故复是其言,而自实其戏也。”〔56〕[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九,《四书章句集注》,第177页。不论各家解释哪一种更合于孔子和子游对话的意旨,我们都能从中读出孔门对礼乐治国的重视。问题在于,子游以弦歌教化武城,孔子为什么要嘲笑说“割鸡焉用牛刀”呢?揣其意,一则处处弦歌之声,近于将乐视作一种享受,这自然是对乐教的偏离;二则,子游推行乐教太急,当如孔子所说先推行《诗》教。
王弼解说的唯一不足是未能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与其言说者孔子紧密联系起来。由孔子的政治理想及其汲汲以求的政治实践来看,这三句话所讨论的是治国教化的次序先后问题,要求“为政”教化所遵循的步骤为:第一步推行《诗》教,第二步制礼,第三步作乐。
三、朝闻道:理想失落之后的感慨
孔子关于“道”的言论,以《论语·里仁》中“朝闻道,夕死可矣”一句最难索解。何晏集解:“言将至死不闻世之有道也。”皇侃疏:“叹世无道,故言设使闻世有道,则夕死无恨,故云可矣。”〔57〕[三国魏]何晏集解、[南朝梁]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第47页。朱熹注:“道者,事物当然之理。苟得闻之,则生顺死安,无复遗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时之近。”〔58〕[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二,《四书章句集注》,第71页。以上何晏和皇侃仅以“不闻世之有道”“叹世无道”作解,并未理会“道”本身的涵义。朱熹以“事物当然之理”来解释“朝闻道,夕死可矣”之“道”,则意谓着早晨认识到了“事物当然之理”,傍晚就可以安然死去。这当然很难令人信服。〔59〕廖名春:《〈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章新释》,《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第151—155页。
“朝闻道”之“道”,或当理解为孔子当世汲汲以求付诸实践的政治理想。孔子曰:
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60〕《论语·雍也》,[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三,《四书章句集注》,第90页。
朱熹注:
道,则先王之道也。言二国之政俗有美恶,故其变而之道有难易。程子曰:“夫子之时,齐强鲁弱,孰不以为齐胜也,然鲁犹存周公之法制。齐由桓公之霸,为从简尚功之治,太公之遗法变易尽矣,故一变乃能至鲁。鲁则修举废坠而已,一变则至于先王之道也。”愚谓二国之俗,惟夫子为能变之而不得试。然因其言以考之,则其施为缓急之序,亦略可见矣。〔61〕《论语·雍也》,[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三,《四书章句集注》,第90页。
程颐和朱熹都将齐鲁一变至于道的“道”,理解为“先王之道”,诚然不错,但孔子所说的齐和鲁则未必均为孔子当时的齐和鲁。程颐将孔子的话与“太公之遗法”和“周公之法制”联系起来,可能是想到了《史记·鲁周公世家》的这段记载:
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62〕[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835页。此故事的较早形态见载《吕氏春秋》卷十一和《韩诗外传》卷十。《吕氏春秋》曰:“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太公望曰:‘鲁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齐国。鲁日以削,至于觐存,三十四世而亡。”(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55页。)
周公对齐鲁后世运命的慨叹,与孔子由齐至于鲁而至于道的路线设计正好相反。周公似乎没有后来秦始皇“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63〕[汉]司马迁:《史记》,第300页。的不朽追求,周公看到了历史的轮转和迁变,而孔子则渴望文化传统的延续甚至重现,故他希望由齐政之“简其君臣礼,从其俗”,回复到“变其俗,革其礼”的鲁政,由此浸浸乎周政。齐鲁一变至于道的话大约是齐景公和晏子适鲁见孔子,或孔子适齐之时所说。孔子希望齐景公能够改革齐国的政俗,他认为那时的齐国稍加变革,便可以达到西周初年鲁国之政,由此进阶,即可达于西周之政。
《史记·孔子世家》载鲁哀公六年(前489年),孔子在陈绝粮,他自己一度似乎也对执守的“道”产生了疑惑。他说:“《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相同的话,他先后问了子路、子贡和颜回,颜回的对答最令孔子满意,亦最能说明问题。颜回曰:
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64〕[汉]司马迁:《史记》,第2327页。
颜回理解的孔子“至大”之道,显然指的是孔子意欲兴复西周礼乐的政治理想。颜回“道既已大修而不用”之“不用”一语,恰是孔子一生的遗憾。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65〕《论语·子路》,[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七,《四书章句集注》,第145页。其后楚昭王派兵迎接孔子,孔子至楚。昭王欲任用孔子,楚令尹子西的一番话当更能说明孔子所持守之“道”的现实指向。子西曰:
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66〕[汉]司马迁:《史记》,第2328页。
子西的言论,证明他担心孔子得到土壤封地而成为王者。孔门弟子对孔子之可能成为王者,亦极其认同。南宫适的一番话和孔子的反应最具代表性: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耕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论语·害问》〔67〕[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七,《四书章句集注》,第150页。
朱熹注:“禹受舜禅而有天下,稷之后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盖以羿奡比当世之有权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谓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与,故俟其出而赞美之。”〔68〕《论语·害问》,[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七,《四书章句集注》,第151页。鲁哀公六年(前489年),孔子63岁,本年前后也是孔子周游列国最为困顿的时候。此时孔子发出“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深长感慨,合乎情理。
孔子对如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仅如上所述,在机会到来时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现实途径,他还规定了个人追求政治理想的知识和修养准备。孔子说: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69〕[宋]朱熹:《论语集注》卷四,《四书章句集注》,第94页。
《礼记·少仪》:“士依于德,游于艺。”郑玄注:“德,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艺,六艺也。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孔颖达疏:“案《周礼》,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彼注云:至德,中和之德,覆焘持载含容者也。敏德,仁义顺时者也。孝德,尊祖爱亲。”〔70〕[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疏附[唐]陆德明音义:《礼记注疏》卷三十五,第630、631页。参照朱熹注,这句话说的是志向“道”需要做到:持守得到的东西,不违背仁,“玩物适情”于礼乐射御书数之“艺”。朱熹以为“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此章言人之为学”〔71〕《论语·述而》,[宋]朱熹:《论语集注》卷四,《四书章句集注》,第94页。,这一理解并不错,但未免看轻了孔子所视以为志向的“道”。孔子“志于道”之“道”,同样应该理解为孔子的政治理想。
《论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72〕[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三,《四书章句集注》,第77页。又:“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朱熹注曰:“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归之叹也。”〔73〕[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三,《四书章句集注》,第81页。孔子在“道不行”之后,曾设定了两个选择:一是浮海,一是归乡。浮海,是要隐居起来,不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归乡,是为了整理文献,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于通过述作典籍来保存和发扬西周一代文化。故孔子周流四方而栖栖以求的“先王之道”,亦即孔子“吾其为东周”的政治理想。
“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74〕[汉]司马迁:《史记》,第2302页。,周游列国无所成,孔子终于返回鲁国。早年奔波导致身体渐衰,孔子渐渐自觉所志向的“道”不再有实现的可能。孔子曰: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75〕[宋]朱熹:《论语集注》卷四,《四书章句集注》,第94页。
朱熹注:“孔子盛时,志欲行周公之道,故梦寐之间,如或见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则无复是心,而亦无复是梦矣,故因此而自叹其衰之甚也。”此处所注“周公之道”正是“先王之道”。孔子又曰: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76〕[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五,《四书章句集注》,第111页。
朱熹注:“凤,灵鸟,舜时来仪,文王时鸣于岐山。河图,河中龙马负图,伏羲时出,皆圣王之瑞也。”此处朱熹说凤鸟河图为“圣王之瑞”,回避了孔子是否圣王的问题。应当说,在新的时代继承和推行西周礼乐,是孔子所追求实现的政治理想,是孔子“道”的现实目标。
结 论
“以礼让为国”的内涵是探讨“以天下让”的根本制度问题,这与孔子的理想政治密切相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讨论的是治国理政以教化天下的先后次序:第一步,以《诗》教为中心,培养整个社会的“文德”;第二步,因俗制礼;第三步,功成作乐。这是孔子当世汲汲乎奔走渴望实现的政治理想。“朝闻道夕死可矣”,是孔子王道政治理想失落之后所发出的深长感慨。这三则言论集中体现了孔子的礼乐之道。
《礼记·礼运》载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谓小康。”〔77〕[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疏附[唐]陆德明音义:《礼记注疏》卷二十一,第412—414页。孔子理想中的政治在“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以礼让为国”体现的是孔子的理想政治,对应于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孔子明确认识到“今大道既隐”,时势不可回复,于是退而力求未来政治可以恢复到“三代之英”“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体现的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对应于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将孔子与苏格拉底、佛陀和耶稣并列为人类思想范式的四大创造者,认为孔子的根本思想是“借对古代的复兴以实现对人类的救济”〔78〕[德]雅思贝尔斯:《大哲学家》(修订版),李雪涛主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28页。。以孔子的根本思想是希望“实现对人类的救济”,无疑抓住了孔学的精髓,但将追求“古代的复兴”视作孔子“实现对人类的救济”的途径却未必正确。孔子的“兴于《诗》”意在继承复兴西周文化,“立于礼”却是因应新的时代而创制新礼,“成于乐”则要求新的时代有新的告成之“乐”,后二者的要义在于以继承为基础推出新的政治和文化。孔子终生与弟子为学奔走,开创了对未来中国文化影响深远的儒家学派。然楚令尹子西“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的话表明,在时人眼中,孔门不仅仅是一个学派,也是一个颇有政治追求的共同体。但可能令孔门弟子也深感诧异的是,孔子去世之前却没有指定继承人。〔79〕《孟子·滕文公上》曰:“昔者孔子没,……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四书章句集注》,第264页。)《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史记》,第2678页。)这或许标志着孔子对“家天下”的警惕。由此似可推测,在孔子的设想当中,在《诗》教养成文德,治定功成,制礼作乐之后,他所欲推行的根本制度正是“以礼让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