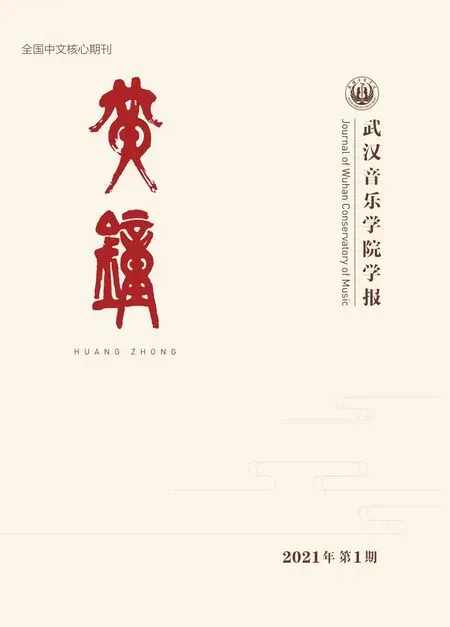思想史视域下的杜佑礼乐观研究——以《通典》为例
2021-12-06王维
王 维
杜佑(公元734—812年),字君卿,唐代中期政治家、史学家,出身于名门望族,曾任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杜佑历经三十余年独自撰写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通典》,该书记叙了上自唐虞三代下至天宝末年的政治经济、礼乐刑法等各项典章制度的变迁历史。全书共二百卷,分为九门,其中包括食货十二卷、选举六卷、职官二十二卷、礼一百卷、乐七卷、兵十五卷、刑法八卷、州郡十四卷、边防十六卷。①[唐]杜佑:《通典》之王文锦《点校前言》,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页。当代学者们从中唐史学、制度沿革、经世致用等多个角度对《通典》进行了研究,下面本文将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论文进行简要评述。
葛兆光在《杜佑与中唐史学》一文中从中唐政治危机的角度指出,杜佑写作《通典》“重在从历史沿革方面总结历史以达到‘施诸有政’的目的”②葛兆光:《杜佑与中唐史学》,《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第9页。。该文归纳出杜佑的三方面史学成就,一是将“政书”与“史书”结合,形成了崭新的制度史体裁;二是把儒学中重实际的思想与《管子》重经济的思想相联系,提出了“食货为首”的见解;三是认为杜佑具备明确的历史进化观。
本文认为杜佑创立制度史体裁不仅是一次历史理性的政制总结,更是在政治动荡、经济衰微的中唐转折时期所进行的一次大胆的精神飞跃,其目的是为了超越混乱的世俗价值,确立神圣维度中的绝对价值。杜佑提出“食货为首”的思想,也不单是出于经济现实的考量,而是试图从食货经济这一人人所需的生存角度切入,引发人们对于食货之本的思考。
朱维铮在《论“三通”》中指出“唐代统治者重视向历史‘问政理成败所因’,是同实现封建制度法典化的过程相联系的,结果影响到史学一个新领域的开辟,即《通典》式的静态研究渐成风气”③朱维铮:《论“三通”》,《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5期,第46页。。他认为杜佑对制度史的书写是为唐代政治文化的统一和稳定提供法理依据。但朱维铮指出杜佑将《周礼》作为治国法典,是“属于不可能实现的幻想”④朱维铮:《论“三通”》,第48页。。本文则认为杜佑通过王官之学中“政教合一”制度的深入探究以及对礼乐仪式背后天人关系的重新阐释,将唐代士大夫的执政能力和德性品质在礼乐思想中进行重塑,并以此为起点试图建立个人、社会、国家之间的精神联结,这些不属于“幻想”,而是一种超拔的境界。
郑祖襄在《〈通典·乐典〉述评》中对杜佑《通典·乐典》的音乐观、音乐史观、音乐史书体例、史料来源、音乐史学价值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该文认为“作者在当时‘经邦治用’的史学思想指导下,主张恢复雅乐,排斥胡乐,并以历史经验来评判现实,充分发挥了史学著作的现实意义。”⑤郑祖襄:《〈通典·乐典〉述评》,《音乐艺术》1996年第3期,第13—17页。对于杜佑为何以及如何“恢复雅乐,排斥胡乐”的问题,文章的阐述稍显简单。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寻杜佑礼乐思想产生的精神依据,揭示杜佑礼乐思想的政治功用及其现实效力,以期将杜佑礼乐观研究推向深入。
正如唐代官员李翰为杜佑所写的《通典序》所言:
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今古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⑥[唐]杜佑:《通典》卷一《食货》,王文锦等点校,第1页。
李翰评价《通典》之作“问而辨之,端如贯珠”,形容该书内在逻辑严密,从头至尾像珠子一样贯穿始终。那么,《通典》中的统一逻辑体现在哪里?我们首先看一下杜佑的谋篇布局。
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⑦[唐]杜佑:《通典》卷一《食货》,王文锦等点校,第1页。
杜佑将“食货”居于首要位置,但又在“礼”典用力最多,共一百卷,加上“乐”典七卷,“礼乐”占了全书篇幅的一半以上(全书共二百卷),而对于唐代最为棘手的边防问题却放到了最末。杜佑通过这样的章节安排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先来看一下食货与教化的关系问题。
一、“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
“食货”关乎人的经济生活,“教化”触及人的精神旨归,两者之间孰轻孰重的确让人感到困惑,这是一个价值两难的问题,那么杜佑对这一问题是如何处理的呢?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是以食货为之首……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⑧[唐]杜佑:《通典》卷一《食货》,王文锦等点校,第1页。
杜佑首先指明“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并引用了《管子》和孔子的话来加以补充说明。对于杜佑表述的教化与衣食的关系,有学者认为管子的理财思想影响了杜佑,并指出杜佑“食货为先”的思想体现了他的现实改革倾向。⑨葛兆光:《杜佑与中唐史学》,第9—23页。也有学者认为杜佑“将兴礼乐说得高于一切,恰好否定了开篇就引用的《管子》关于仓廪衣食与礼乐荣辱关系的名言”⑩朱维铮:《论“三通”》,第48页。,认为这是“杜佑思想体系的症结所在”⑪朱维铮:《论“三通”》,第48页。。凡此种种,或褒或贬,莫衷一是。那么杜佑究竟如何看待教化与食货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需要深入到《通典·食货》的上下中去寻找答案。
谷者,人之司命也;地者,谷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谷则国用备,辨其地则人食足,察其人则徭役均。知此三者,谓之治政。夫地载而不弃也,一著而不迁也,安固而不动,则莫不生殖。圣人因之设井邑,列比闾,使察黎民之数,赋役之制,昭然可见也。⑫[唐]杜佑:《通典》卷一《食货》,王文锦等点校,第3页。
杜佑指出,粮食掌管着人的生命,大地关系着粮食的生长,君主负责治理人民。有了粮食则国家需用就具备,辨明土地则粮食生产就充足,考察人口则徭役分配就均匀。知道了这三者,就可以称之为稳定的政治。杜佑在粮食、土地、人口三者中格外强调了土地的重要性,“夫地载而不弃也,一著而不迁也,安固而不动,则莫不生殖”是说大地承载着万物,不可轻易离弃,一旦显露出生长的迹象就不要迁移,安定稳固之后更不要任意流动,只有这样才能使得生命繁衍绵绵不息。
这里可以看出,杜佑的经济思想首先建立在对于土地的无上尊重之上——“地载而不弃”。大地是食货的赋予者与承载者,没有大地的承载,没有上天的给予,人们的生存所需将无从而来,生活根基也无从建立。杜佑以古代圣人为例说:“圣人因之设井邑、列比闾”,圣人因循着大地显露给人的生命信息来设置井邑、分列乡里。此处的“因之”十分重要,杜佑没有说“圣人设井邑、列比闾”,其目的就是为了着重表达圣人的一切所为都是沿着土地的存在与供应基础上进行的因势利导,绝不是单单凭借着一己之力而努力为之。当确立了土地为本的原则之后,考察人口数目、制定赋役制度就变得“昭然可见”了。
因此,在杜佑的观念中所有田赋制度、社会制度在制定之前都要明确土地才是一切制度的根本,尊重土地,就是尊重生命的价值源头。而明确了生命的价值源头,才能真正实现对于生命本身的尊重和保护,这就是杜佑所言“一著而不迁也,安固而不动,则莫不生殖”的原因所在。
在杜佑的思想中,食货经济建立的基础是拜天地所赐而非人力所为,在其所举的大禹与周文王的例子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大禹划分的九个政治区域都是以各地的水土特点作为参考(“禹平水土,别九州”⑬[唐]杜佑:《通典》卷一《食货》,王文锦等点校,第3页。参见[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禹贡》“禹别九州,随山濬川,任土作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页。)。“周文王在岐,用平土之法,以为治人之道,地著为本,故建司马法。”⑭[唐]杜佑:《通典》卷一《食货》,王文锦等点校,第4页。所谓“平水土”“平土之法”就是根据各地水土情况的不同,划分出不同的区域,以此保证人与土地之间能够建立稳固的生存关系(“地著为本”杜佑按:“地著谓安土”⑮[唐]杜佑:《通典》卷一《食货》,王文锦等点校,第4页。),在此基础上再形成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密切联系,最终达成社会成员共同维系的一种社会结构。⑯北宋学者李觏曾在其所著的《李觏集·平土书》中指出:“土地,本也。耕获,末也。”([宋]李觏:《李觏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3页)。李觏根据古代经传归纳出二十种关于“平土之法”的解释,并以三张图的比喻作为辅助说明:“一曰王畿千里之图,二曰乡遂万夫之图,三曰都鄙一同之图。”(第213页)在李觏眼中,平土之法就是围绕周王、百姓、卿大夫所拥有的土地为中心而推行的政治制度。杜佑十分不满商鞅“隳经界、立阡陌”的经济行为,认为其“虽获一时之利,而兼并踰僭兴矣”⑰[唐]杜佑:《通典》卷一《食货》,王文锦等点校,第3页。。在杜佑眼中,商鞅的土地改革仅是为了满足人的一时之利而破坏了人与土地之间的情感连接,人们一旦失去了对于土地本身的敬畏,只将土地作为满足欲望需要的工具,结果必然引出土地兼并以及对自我本分的僭越。
由上可知,杜佑的经济思想是将“天地之所在”作为所有社会关系建立的前提基础,人们需要对天地之本葆有一种精神上的敬畏和行为上的遵从。杜佑所言“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实际上并不是将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作为教化的根本,他想要表达的是教化需要“行”出来,而不是“讲”出来,教化需要在人最本质的生活中体现出来,也就是透过人的衣食生活来彰显。如何彰显呢?“地载而不弃也”,只有将大地奉为生存所需的真正来源并与之建立永不背弃的内在联系,人们才能在生存困境面前拥有坚定的信念、明确的目标、踏实的行为,而不会为了眼前的利益轻易离弃土地,也不会任意妄为僭越稳固的社会秩序。
有学者说杜佑倡导井田制、均田制是“落后于时代的观点”⑱剑光、国慰:《杜佑思想局限性述论》,《思想战线》1994年第4期,第88页。,这一说法并没有注意到作为三朝宰相的杜佑对于唐代社会问题的深切忧虑,倡导井田制不是让人们恢复古时的经济制度,而是为了重建人们与天地之间的信仰联结。杜佑引用管子的话:“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就是告诫人们在仓廪实、足衣食的物质满足中要学会感恩天地的赐予,学会明白荣辱源自生命的价值而非生存的本能。
杜佑在解释完“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之后,并没有马上说到礼乐教化的问题,而是紧接着强调“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那么,职官与教化、与衣食是什么关系呢?在《进通典表》中杜佑说到自己“尚赖周氏典礼”⑲[唐]杜佑:《通典》卷一《食货》,王文锦等点校,第1页。,是说其学说秉承了《周礼》王官之学的制度传统。近代学者章太炎曾在《文史通义》中,将周代王官之学归纳为两点特征——“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即职官承担了政治实践与思想教化的双重任务。
然既列于有司,则肆业存于掌故,其所习者,修齐治平之道,而所师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⑳[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卷二《内篇二·原道中》,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1页。
为何杜佑在食货与教化之间要加入职官的设置呢?我们知道食货关系到人的生存需要,这一点无需额外教导,人人都能明白,但要想将人的生存需要让位于天地自然的神圣需要(即以天地为本),并不是人人都能理解并做到的,于是就需要一批拥有高贵德性品质的职官们来承担这一思想教化与政治实践的艰巨任务(“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由于职官的设立关系到人之信仰根基的建立,因此如何选举具有优秀品质的职官也就成为杜佑在“食货”之后将要论述的问题。
回过头来再看《通典》一书的结构布局,我们会发现杜佑的写作对象实际上针对的是国家的政治担纲者,其前后章节都是围绕着如何重塑政治担纲者的精神信仰与政治使命来进行的。㉑[唐]杜佑《进通典表》:“自顷纂修,年涉三纪,识寡思拙,心昧词芜。图籍实多,事目非少,将谓功毕,有愧乖疎,固不足发挥大猷,但微臣竭愚尽虑。凡二百卷,不敢不具上献,庶明鄙志所之。尘黩圣听,兢惶无措。谨奉表以闻。臣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参见[唐]杜佑:《通典》,王文锦等点校,第1页。因为只有经历了生存的考验(食货),品质考核(选举)与政治磨砺(职官)之后,政治担纲者们才能真正体悟和感知到礼乐仪式背后的精神实质,这就是《通典》将食货为首,以礼乐为重的原因所在。下面我们重点谈谈杜佑的礼乐观。
二、“古雅莫尚,胡乐荐臻”
音乐学者在对杜佑乐论思想的研究中,常常将“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政治局势与杜佑对待“胡乐”所持的否定观念进行比照,认为杜佑“把政治上胡人入侵、叛乱归咎于胡乐的传入,虽是属儒家文人的迂腐观点,但在当时安史之乱之后,一大批士大夫痛定思痛,议论朝政的时候,却是一种很流行的看法”㉒郑祖襄:《〈通典·乐典〉述评》,第14页。。其依据主要出自杜佑《乐典·乐序》中的论述。
周衰政失,郑卫是兴……而况古雅莫尚,胡乐荐臻,其声怨思,其状促遽,方之郑卫,又何远乎!爰自永嘉,戎羯迭乱,事有先兆,其在于兹。㉓[唐]杜佑:《通典》卷一四一《乐典》之“乐序”,王文锦等点校,第3587页。
我们发现在上面的引文中,杜佑不仅否定胡乐,还将胡乐与郑卫之音相提并论,可见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那么这种关联又是什么?它们与外族入侵又有何关系?在《乐典·乐序》开篇杜佑就指出:“夫音生于人心,心惨则音哀,心舒则音和。然人心复因音之哀和,亦感而舒惨”㉔[唐]杜佑:《通典》卷一四一《乐典》之“乐序”,王文锦等点校,第3587页。,音乐是从人心中产生的,音乐反过来也可以影响人心。但杜佑又指出人心往往呈现出一种嬗变性,“是故哀、乐、喜、怒、敬、爱六者,随物感动,播于形气,叶律吕,谐五声”㉕[唐]杜佑:《通典》卷一四一《乐典》之“乐序”,王文锦等点校,第3587页。。言外之意,由不稳定的人心产生的音乐并不具有绝对的价值依据,在此前提下杜佑提出了他的礼乐观。
舞也者,咏歌不足,故手舞之,足蹈之,动其容,象其事,而谓之为乐。乐也者,圣人之所乐,可以善人心焉。所以古者天子、诸侯、卿大夫无故不撤乐,士无故不去琴瑟,以平其心,以畅其志,则和气不散,邪气不干。此古先哲后立乐之方也。㉖[唐]杜佑:《通典》卷一四一《乐典》之“乐序”,王文锦等点校,第3587页。
此处之“乐”主要是指祭祀神灵祖先的乐舞仪式。杜佑首先强调礼神之乐与随物感动而生的音声之间的不同在于,礼神之乐可以超越语言的限制(“咏歌不足,故手舞之,足蹈之”)。那么超越语言意味着什么?当代学者刘小枫曾经这样谈到人与语言的关系:“人是语言的存在,人与历史时间的现存世界的关系首先由语言确立下来,要超逾现存世界的历史时间,就得超逾语言。语言的言说暗含着历史时间形态,超逾言说,也就超逾了历史时间”㉗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16页。。可见,礼神之乐超越了语言也意味着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人们通过礼乐可以进入到无限的神圣世界当中,或者说礼乐就是神圣价值的象征形式。
杜佑所谓“以平其心,以畅其志,则和气不散,邪气不干”,意思是说当人们沉浸在礼神之乐中的时候,就会切身体验到绝对的神圣价值的临在与确定(“以平其心”),它能够满足人们内心深处对于真实意义的无限渴求(“以畅其志”),这是来自经验世界的音乐所无法企及的境界(“和气不散,邪气不干”)。杜佑看到了人性的不牢靠(“随物感动”),所以试图通过梳理历史境遇中的历代礼乐制度,把握礼乐传承的思想脉络、重塑其精神实质。“所以古者天子、诸侯、卿大夫无故不撤乐,士无故不去琴瑟”,唯有礼乐可以使人的心性连接到真实的价值所在,保守人心不至偏离价值本源,这也是古代先哲立乐的根本原因。在杜佑的观念里,外族入侵、政治动荡的真正原因不是来自胡乐和郑卫之音的音乐形式本身,而是此类音乐所表征的世俗世界的价值观念带给人的信仰动摇与精神嬗变。
为了进一步说明上述问题,杜佑在《乐典》的书写中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具体论述:第一部分“历代沿革”,从历史角度对各朝各代的礼乐制度进行梳理;第二部分对十二律、五声八音等的概念由来、音律调性规律进行分析并对各种歌舞形式加以归类整理;第三部分对政治实践中的礼乐仪式进行了具体阐述。在《乐典·乐序》中杜佑特别例举了唐贞观时期所作的《破阵乐》。
圣唐贞观初作《破阵乐》,舞有发扬蹈厉之容,歌有粗和啴发之音,表兴亡之盛烈,何谢周之文武,岂近古相习所能关思哉!㉘[唐]杜佑:《通典》卷一四一《乐典》之“乐序”,王文锦等点校,第3588页。
杜佑用唐初所作《破阵乐》的例子意在表明礼乐传统不在于形式上的固守,而在于内在精神上的契合,“表兴亡之盛烈,何谢周之文武”。唐太宗曾对此曲有过如此评价:“(《秦王破阵乐》)所以被于乐章,示不忘于本也。”㉙[唐]杜佑:《通典》卷一四六《乐典》,王文锦等点校,第3719页。太宗之意是说《破阵乐》彰显的并非其本人的威名,而是战功背后那种“发扬蹈厉”的精神价值。杜佑对此段话进行了小字补注:“其后,若殿廷奏,天子避位,公卿以下坐宴者皆兴焉”㉚[唐]杜佑:《通典》卷一四六《乐典》,王文锦等点校,第3719页。。是说殿廷演奏《破阵乐》的时候,天子需要回避皇位,但公卿以下坐宴者都可以继续欣赏。天子为何避位?原因就在于太宗所言的“示不忘本”,《破阵乐》中“发扬蹈厉”的精神显发源自上天的福佑以及公卿众臣的辅弼而非天子的个人所为,所以“天子避位”就是以实际行动来表明天子“示不忘本”的谦卑态度。
由此可见,杜佑在《乐典》开篇以“破阵乐”为例,意在提醒人们礼乐的价值不在于仪式本身,而在于通过礼神之乐建立天人之间的精神连接(“示不忘本”),这才是政治秩序得以完善的根本。在《乐典》的“历代制造”部分,杜佑引用了《贞观政要·礼乐》中唐太宗与杜淹的一段关于礼乐的对话,也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
太宗谓侍臣曰:“礼乐之作,盖圣人缘情设教,以为撙节,治之兴替,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此乐。陈之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之将亡也,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也。以是观之,盖乐之由也。”太宗曰:“不然。夫音声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欢者闻之即大悦,忧者闻之即大悲。悲悦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人必苦,然苦心所感,故闻之则悲耳。何有乐声哀怨,能使人悦者悲乎。今《玉树后庭花》、《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当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㉛[唐]杜佑:《通典》卷一四三《乐典》,王文锦等点校,第3654页。
太宗指出:“礼乐之作,盖圣人缘情设教,以为撙节,治之兴替,岂此之由。”表面看来唐太宗认为礼乐是圣人根据人的情感设立的教仪,只是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与政治兴替无关,特别是那句“悲悦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更让学者们认为此段话表达了太宗“对‘淫乐亡国’论的有力批判”㉜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第606页。。但结合前面唐太宗对《破阵乐》“被于乐章,示不忘于本”的叙述,以及杜佑将此段太宗的礼乐观穿插在唐代礼乐制度沿革的叙述当中,便不难发现杜佑引述太宗此段话的用意是为了支撑礼乐仪式背后所表征的神圣价值观。
“治之兴替,岂此之由”是在提醒众臣,尽管礼乐仪式是圣人为世人的行为处事设立的教仪标准,但作为国家政治的担纲者们所要关注的并非“援情设教,以为撙节”这一世俗层面的内容。因为“悲悦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世俗之人往往随心所欲,人心与音乐的关系极不稳定,国家政治是无法建立在极易变动的人性根基之上。要想让国家政治趋于稳固就需要通过礼乐仪式明确永恒不变的神圣价值、坚固人们的信仰根基,这样即便《玉树后庭花》《伴侣》之曲四起,“公必不悲矣”。因此,如果把这段内容看做是太宗“对‘淫乐亡国’论的有力批判”就很容易忽视唐代政治担纲者们的政治意图。那么,顺着这一问题问下去,淫乐究竟能否亡国?俗乐与礼乐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在杜佑有关“郑声”的话题上有着详细的论述。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杜佑引用了《汉书·礼乐志》中的史料,武帝时期的礼乐“然未有本于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㉝[唐]杜佑:《通典》卷一四一《乐典》,王文锦等点校,第3594页。,武帝时期的礼乐既没有以祖先神灵作为敬拜对象,又没有按照传统的音律规律进行演奏,所用朝廷内外的礼乐仪式全以“郑声”为曲调,由此导致人心不古、政治陵夷(“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沉湎自若,陵夷坏于王莽也”㉞[唐]杜佑:《通典》卷一四一《乐典》,王文锦等点校,第3595页。)。此处的“郑声施于朝廷”表面上是民间音乐嵌入到宫廷礼乐当中,实则意味着汉代礼乐所表征的神圣价值被世俗价值所侵染,由此导致了价值取向的偏差和内在秩序的破坏。
历代儒家学者对于郑卫之音的排斥,并非源于对民间音乐本身的误解,而是出自他们对于人性脆弱本质的深刻洞察。正如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回答颜渊问治国之法时所言:“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侫人。郑声淫,侫人殆。”㉟[三国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211页。“乐则《韶舞》。放郑声”的本意是为了持守礼乐精神中的神圣价值,以防嬗变之人性在没有神圣的光照下走向迷失与沉沦。因此,无论是前文御史大夫杜淹所言的“前代兴亡,实由此乐”,还是太宗所言的“悲悦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实际上两者并不矛盾,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除去世俗价值的干扰、确保礼乐仪式中神圣价值的纯正与完美,因为这关涉到国家精神根基的稳固。与郑卫之音相似的还有胡乐乱华的问题,为了解释这一问题杜佑列举了北魏宣武皇帝始爱“胡声”的例子。
自宣武已后,始爱胡声,洎于迁都。……抚筝新靡绝丽,歌响全似吟哭,听之者无不凄怆。……皆初声颇复闲缓,度曲转急躁。按此音所由,源出西域诸天诸佛韵调,娄罗胡语,直置难解,况复被之土木?是以感其声者,莫不奢淫躁竞,举止轻飙,或踊或跃,乍动乍息,跷(羌娇反)脚弹指,撼头弄目,情发於中,不能自止。论乐岂须钟鼓,但问风化浅深,虽此胡声,足败华俗。……。盖惊危者,势不久安,此兆先见,何以能立!形貌如此,心亦随之。亡国之音,亦由浮竞,岂唯哀细,独表衰微。操弦执籥,虽出瞽史;易俗移风,实在时政。㊱[唐]杜佑:《通典》卷一四二《乐典》,王文锦等点校,第3614—3615页。
我们可以看到杜佑对“胡声”的排斥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胡声带给人的生命感受是“听之者无不凄怆”的精神虚妄。其次“此音所由,源出西域诸天诸佛韵调”,在信仰上“此音所由”完全偏离了华夏祖先传承的精神根基,再加上“感起声者,奢淫躁竞,举止轻飚”,杜佑看到这一异域音调里面潜藏着与华夏正声产生内在分裂的危机,也看到了这种内在分裂将要带给人们信仰价值的混乱,“虽此胡声,足败华俗”,而这种信仰价值的混乱最终将演变为整个国家的分裂与覆亡,杜佑因此断言“亡国之音,亦由浮竞”。杜佑一再重申“胡声”本身不足以亡国(“岂唯哀细,独表衰微”),但胡声所导致的精神失序(“亦由浮竞”)足以摧毁一个国家的灵魂构建,这也是杜佑指明“操弦执籥,虽出瞽史;易俗移风,实在时政”的原因所在。
杜佑排斥胡乐的思想与唐王朝的民族矛盾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而与胡乐背后的思想意识形态息息相关,如果胡乐能够以华夏礼乐的内在精神为旨归的话,杜佑对之并不反对。比如杜佑在唐代燕乐的记录中就包括了四夷之乐,“凡大燕会,设十部之伎于庭,以备华夷:一曰燕乐伎,……二曰清乐伎;三曰西凉伎,四曰天竺伎;五曰高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安国伎;八曰疏勒伎;九曰高昌伎;十曰康国伎”㊲[唐]杜佑:《通典》卷一四四《乐典》,王文锦等点校,第3687—3688页。。此外杜佑也引用了《周官》中有关四夷之乐的话语:“韎师掌教韎乐,祭祀则帅其属而舞之(舞之以东夷之舞。韎、音妹),大飨亦如之”㊳[唐]杜佑:《通典》卷一四六《乐典》,王文锦等点校,第3722页。。周代的祭祀礼乐当中早已将四夷之乐纳入其中。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保融合各族文化的同时不至于偏离本族的精神信仰?答案就在于“先王”“韎师”的引导,韎师掌管着礼乐的内在精神与外在形式,当精神信仰达成一致的时候,无论华夏礼乐还是四夷之乐都将发出多元而完满的颂赞,正如杜佑所言:“作先王乐,贵能包而用之。纳四夷之乐者,美德广之所及也”㊴[唐]杜佑:《通典》卷一四六《乐典》,王文锦等点校,第3722页。。
余 论
杜佑《乐典》在第一部分谈完了历代沿革的礼乐制度问题,又在第二部分归纳了十二律、五声八音的概念来源、乐悬制度以及各种宫廷民间的音乐舞蹈形式。那么,杜佑第二部分的写作与第一部分的“历代沿革”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首先看一下他对“十二律”的解释。
先王通于伦理,以候气之管为乐声之均,吹建子之律,以子为黄钟,丑为大吕,……阳管有六为律者,谓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此六者为阳月之管,谓之律。律者,法也,言阳气施生,各有其法;又律者,帅也,所以帅导阳气,使之通达。㊵[唐]杜佑:《通典》卷一四三《乐典》,王文锦等点校,第3632—3633页。
从上面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杜佑对十二律的解释是建立在自然秩序的基础之上,“先王通于伦理,以候气之管为乐声之均”,先王将自然世界的气息运转、时间规律都通过乐律的方式予以确定下来,并以此为标准运用于各种事物当中,“夫推历生律制器,规圆矩方,权衡平准”㊶[唐]杜佑:《通典》卷一四三《乐典》杜佑注,王文锦等点校,第3632页。原文出自[汉]班固:《汉书·律历志》,[唐]颜师古注:“夫推历生律制器,规圆矩方,权重衡平……”,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32页。。所有这些乐律规律都关联着世间万物的生命成长,比如杜佑对黄钟之名进行了这样的描述:“黄者,土之色,阳气在地中,故以黄为称。钟者,动也,聚也。阳气潜动于黄泉,聚养万物,萌芽将出,故名黄钟也。”㊷[唐]杜佑:《通典》卷一四三《乐典》,王文锦等点校,第3633页。从中可以看出,“黄钟”的概念体现出一种生命孕育的开始。后面的五声八音等概念也基本遵循着这一自然为本的原则。那么结合前文有关历代礼乐沿革的记叙,杜佑这一章节的结构安排有何用意呢?
杜佑对于历代礼乐制度的记录隐含着礼乐制度与神圣价值之间的关联,一旦这种绝对的价值意义被郑声或是胡乐所预表的世俗价值所动摇,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政治失序与人心失衡。而第二部分的乐律原则体现的是一种自然秩序原则,“以候气之管为乐声之均”,乐音的标准依旧来自上天的给予——阴阳之气,也就是说自然乐律理论与历代礼乐制度都有着共同的神圣价值来源。可以看出,杜佑是在通过礼乐制度所代表的政治秩序以及乐律理论所象征的自然秩序的阐述中,为唐王朝的现实政治提供法理依据,也在为唐中叶的社会思想提供必要答案,因此在《进通典表》中杜佑这样写道:“由是往哲,递相祖述,将施有政,用乂邦家”㊸[唐]杜佑:《通典》之《进通典表》,王文锦等点校,第1页。。
唐代中期经过安史之乱的打击之后,国家面临着外族入侵、藩镇割据、朝廷腐败等等内忧外患的问题。据《剑桥中国隋唐史》研究表明,唐代藩镇割据的局面源自8世纪初地缘政治的改变,当东突厥人、契丹人、吐蕃人的军事势力崛起时,带给唐廷极大的军事压力,为了与邻邦保持一种制衡关系,唐王朝在边境地区建立了大规模的防御体系,这也导致了藩镇的普遍建立以及后来由于职业军人权力的扩大而引发的割据局面,最终形成了地方对于中央权力的威胁。㊹[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21—424页。作为唐朝宰相的杜佑实际上面临着双重考验,究竟应该维护唐朝帝王的政治权力还是维护华夏文明的政治传统?面对党项联合吐蕃进犯唐境,杜佑说:
传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管子曰:“国家无使勇猛者为边境。”此诚圣哲识微知著之远略也。今戎丑方强,边备未实,诚宜慎择良将,诫之完葺,使保诚信,绝其求取,用示怀柔。来则惩御,去则谨备,自然彼怀,革其奸谋,何必遽图兴师,坐致劳费!㊺[晋]刘昫等撰:《旧唐书·杜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890—3891页。
杜佑看到了在党项图谋入侵的危机背后同样隐藏着唐廷军事将领之间的权力争夺(“边将邀功,亟请击之”㊻[晋]刘昫等撰:《旧唐书·杜佑传》,第3979页。),因此杜佑首先要确立的并不是唐王朝的领导权威而是文化权威(“何必遽图兴师,坐致劳费”;“传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与杜佑在《乐典》中所记述的历代礼乐制度以及乐律原则在观念上是完全一致的,即将重建政治担纲者的精神信仰与生存价值作为首要原则,这一信仰就来自对于天地之本的遵从与敬畏,这也是他在《通典·食货》中提出“地载而不弃”的原因所在。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曾言:“唐人所缺乏者,乃是一人生全体最高理想之领导”㊼钱穆:《民族与文化》,参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7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31页。,两位相隔千年的思想家可谓惺惺相惜。
正如前文所言,《乐典》的乐律理论中所蕴含的秩序原则来自宇宙自然的秩序本身,杜佑将这些乐论理论放置在礼乐制度的史料当中,其目的正是为了说明政治秩序与自然秩序之间的一致,而所有这些秩序的根本在于以礼乐为表征的人神关系(或曰天人关系)的建立。当国家的精神根基确立之后,藩镇割据、外族入侵都将不再形成对于国家的真正威胁,由此我们也就理解了杜佑为何把“边防”放到了《通典》全篇最末的位置,正如杜佑所言:“中国遂宁,外夷亦静”㊽[晋]刘昫等撰:《旧唐书·杜佑传》,第3980页。。
杜佑礼乐观在唐由盛而衰,藩镇割据、外族入侵的历史嬗变时期出现,其原因可以归纳为:首先,通过历代礼乐制度的梳理,试图重寻礼乐制度背后的价值依据,即人神关系(或者说天人关系)的确立;其次,杜佑通过音律概念的界定,期望将天人关系与自然规律进行整合,以此为唐王朝的政治法典找到法理依据;第三,无论是胡乐还是郑声,其音乐形式本身并不是被杜佑排斥于外的,真正令其感到痛心的是由这些音乐所引发的人的精神价值的偏离和灵魂世界的失坠。重提儒家礼乐观,乃历任三代宰相的杜佑在他的礼乐观中寄望于一种神圣价值的临在,因为唯有确立了精神领域的绝对价值,才有可能重拾中唐社会散落的人心。
杜佑以其近五十年的宦海生涯,完成了《周礼》王官之学中“治教无二,官师合一”之政治德性品质的塑造,如李翰所称:“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㊾[唐]李翰:《通典序》,[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第2页。正因为有着如此心性之磨练,杜佑才会在国家危机面前做出了何为高贵的政治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