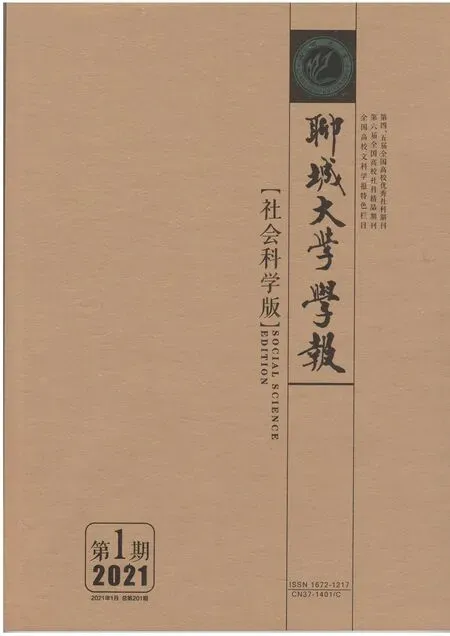瓦尔特·本雅明与19世纪巴黎的“寓言”
2021-12-03李超
李 超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与早期沉浸在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辨和玄妙神学体验中来拯救被现代性打破的传统不同,进入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由于受卢卡奇、拉西斯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本雅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从神学的角度转向了辩证唯物主义。与此同时,本雅明在1927年旅居巴黎时对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路易·阿拉贡小说《巴黎的乡下人》的阅读则直接诱发了本雅明“拱廊街”的研究设想。到1940年,差不多十四年的时间里,本雅明始终专注于“拱廊街”这一宏伟的计划。在本雅明看来,“巴黎是19世纪的首都,而拱廊街又是巴黎的‘首都’:资本主义的一切秘密都隐藏在那些数不胜数的玻璃橱窗中,一切繁荣的景象都微缩在五光十色的高大拱廊之下。”①赵文:《国外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中认识论基础研究》,国家社科基金最终成果,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年,第175页。正是通过对19世纪巴黎的“寓言”批评,一方面发现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的构成秘密,另一方面反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大众的生存与希望。
一、走向“寓言”的批评
“寓言”作为本雅明理论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贯穿于其思想阐释始终。从最早的《德国悲剧的起源》到“拱廊街计划”,寓言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本雅明来说,寓言不仅是一个修辞甚或诗学的概念,不仅是艺术作品的形式原则,即用类似的观念取代一个观念的比喻方式,而且是一个审美概念,一种绝对的、普遍性的表达方式,它用修辞和形象表现抽象概念,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有机模式,它指向巴罗克悲剧固有的内涵。”②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文选》,陈永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6页。在巴洛克戏剧中,无论是悲剧形象,还是艺术形式都是破碎断裂的。本雅明通过对其分析,企图通过极端的寓言形式来实现真理的表征。随后,在其后期的“拱廊街计划”中,这种寓言的表达从文学世界走向了现实生活。他希望通过“对时代生活的寓言式解读从而使这个时代的真理内容透过其物质内容的表象而显现出来”①西奥多·阿多诺等:《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郭军、曹雷雨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3页。。于是在其计划的主要篇章《发达资本主义抒情诗人》中,作者把一系列的“辩证意象”,如文人、波西米亚流浪汉、拾垃圾者等在其构成的总体里以一种寓言的方式进行了审视,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实,并寻求在废墟上进行拯救的方法。正如本雅明自己的一个著名的比喻一样:寓言在思想的国度里如同废墟在物质的国度里。因此,物质世界废墟、破碎形象的表达,需要不断通过寓言的方式进行把握,在把握日益堆积的废墟中——现代资本主义统治下的物象与人像正是废墟加剧的表象世界——看到真理的曙光,找到一种把人类从十九世纪唤醒的方式。而真理,希望的表达,恰恰需要通过寓言对客观世界的把握。
然而正是这种一以贯之的“寓言”批评,使本雅明不自觉地走向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批评实践。本雅明虽然没有通过传统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但在这种“寓言”的书写下,通过思考“辩证意象”中表层形式/潜层形式之间的隐喻关系,从而打破了理性主义支配下的二元认识论,践行着一种唯物主义批评。
进而言之,如果马克思通过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在政治经济学层面对社会现实构成一种辩证唯物主义批评,那么本雅明通过表层形式/潜层形式对19世纪巴黎的分析,则在美学—心理学抻面走向一种唯物主义批评。于是我们发现在本雅明所剖析的十九世纪的巴黎都城以及城中的人都拥有着两副面孔。他们既统一又相互对立,共同寓言这座城与人的精神状态。本雅明在对波西米亚人、游荡者、拱廊街、西洋景等进行寓言批判时,一方面看到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城市化水平不断加快,整个社会的日新月异与欣欣向荣。与此同时在这些不断造就的现代性成果的浅层形式背后,本雅明又看到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存在的缺陷以及堆积的现代性废墟对现代性虚假表象的颠覆。
二、城中人的“寓言”展示
在对《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的思考中,本雅明为我们展现了各色的现代人形象:文人,波西米亚人、职业密谋家、游手好闲者、拾垃圾者。而本雅明通过具体刻画第二帝国巴黎的文人与市场,游荡者与人群的关系,来对现代人的精神本质进行了寓言展示。在对文人与市场的关系分析中,本雅明为我们展示了文人异于大众的矛盾心态。他首先看到文人的铮铮傲骨,看到他们隐秘地反抗着社会,拒绝作品商品化,与俗文学同流合污,保留着强烈的自律意识。他们在巴黎街道自由散漫的行进中、与大众的纠缠中寻找着文章的主题。本雅明将文人比作拾垃圾者:“两者都是在城市居民酣沉睡乡时孤寂地操着自己的行当,甚至两者的姿势都是一样的。纳达尔曾谈到波德莱尔‘僵直的步态’,这是诗人为寻觅诗韵的战利品而漫游城市的步态;这也必然是拾垃圾者在他的小路上不时地停下、捡起碰到的垃圾的步态”②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06页,第57页。。如拾垃圾者漫游于城市,从被人群扔弃的愈垒愈高的垃圾中,看到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下,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的废墟一样,文人在僵直的步态下,仿佛看到了商品交换价值正取代使用价值的异化现实,他们试图挣脱,但显得无能为力。本雅明在看到文人的圣洁、自律的表象同时,却又看到他们朝不保夕的生活:“他们像游手好闲之徒一样逛进市场,似乎只是为了四处瞧瞧,实际上却是想找一个买主。今天高喊‘为艺术而艺术’的波德莱尔,明天已变成‘艺术与功力不可分割’的鼓吹者,他以这样的方式保留着文人的姿态”③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06页,第57页。。波德莱尔经常把文人,首先是他自己,比作娼妓。随着资本主义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文人开始无奈地卖掉自由的灵魂与思想去换取贴衣果腹的物质资料。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报纸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订金的降低,为了维持报社的收支,广告占用了报纸大量的版面。此外开设专栏,登载大量的连载小说,以吸引大众的眼球,提高销量。专栏的巨大市场给撰稿人提供了巨额的报酬,并帮助作家赢得了名声。于是文人趋之如骛,纷纷与报刊签订合同。1845年,大仲马与《立宪党人》及《快报》签了合同,获得了高达至少六万三千法郎的报酬。文人在获得自己的巨额经济回报的同时,也拓展了自己的政治话语权,如大仲马1846年在政府邀请下到突尼斯为殖民地做宣传。然而在这些文人光鲜亮丽的背后,却有一只市场的黑手在操控着,而那些贪婪的出版商也只有一笔订金到账后,才肯接受他们的稿子。
本雅明对19世纪文人处境鞭辟入里的“寓言”展示,除了借助于波德莱尔以及他的诗歌进行展开,也融入了更多的自我意识。与19世纪早期的波德莱尔相比,身处19世纪晚期的本雅明,文人的处境也变得更加艰难。在起草“拱廊街计划”之前,身为犹太人的他,生活充满颠沛,经历着流放与拘留,经济上的窘迫也使他不得不得以卖文为生。这种种糟糕的境遇,使他深切地体会到波德莱尔笔下文人的孤独与无奈,也更加能理解波德莱尔把文人喻为为钱而干的缪斯的迷茫的痛苦。
而在对游荡者与人群的关系的思索中,本雅明继续深化着他对现代人精神状态思索的主题。游荡者总是出现在有人群的地方,他们与大众始终保持着一种极为复杂的矛盾关系。游荡者行走在人群中,一方面,他仍然保持着清醒的自我意识,看到在技术主义的冲击下,个体的情感一点点丧失,并且被工具束缚着手脚;另一方面,他把大众看成一切,在现实中并不与自己对立,而是相互融洽,因此这些人群给他带来了强烈的吸引力。正如如瓦雷里在观察写道的“住在大城市中心的居民已经退化到了野蛮状态中去了——就是说,他们都是孤零零的。那种由于生存需要保存着的依赖他人的感觉被社会机制磨平了”①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第162页,第158页。。人群,由聚集在街道的众多人组成人流,他们中有高贵的人,商人,业务代理人,也有工人。对于那些上等阶层的人的刻画,本雅明引用爱伦坡在《雨天》中的表述:
“他们的头都微微有些秃,那只长期习惯用来架笔的右耳朵奇怪地从根上竖着。我看到他们总是用两手摘下或戴上帽子,他们戴着表,还有一根样式古朴实在的短短的金表链。”他对于人群运动的描写更加惊人。“远处,人数众多的过往行人带着心满意足的生意人的举止,似乎一心只想着在人丛中走自己的路……如果被人撞了,他们便大度地向撞了他们的人鞠躬,并露出非常迷惑不解的神色。”②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第162页,第158页。
在本雅明看来,资本主义统治下,即使是上等阶层的人,他们也成为金钱的奴隶。在对剩余价值追逐的过程中,他们已经精疲力竭,精神满满被非人性的东西所统治,于是当他们在人群中撞到他人,他们向被撞的人鞠躬,呈现出了对金钱所采取的姿态;身体也呈现物化趋势,身体上仅有的空间都被这些追求利润所必备的手段所控制,如耳朵上架的笔、手上配戴的手表。
对人群中的主要成员工人的分析中,本雅明从马克思那里看到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下工人令人痛心的生存境遇。工人不再是工具的主人,而成为被工具奴役的对象。作为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他们像赌徒掷筛子一样每次运动都重复着相同的动作,并且上一次和这一次没有必然的联系。在这样自动化运动的规约下,工人强迫着自己不断适应机器的运动节奏,机械地表现着自己的身体,于是在身体主体性丧失的情况下,工人也丧失完整人性所必备的东西。当他们走出工厂走向人群中,机器强制下机械的表现仍然没有褪去,人群中行走的工人彼此也不存在交流,谁也不会看上谁一眼,只是遵守着交通规则,在人行道靠右边的行人区行走着。
面对人群呆滞、刻板的精神状态,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首先与人群保持应有的距离,看到了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异化的生存本质,但同时他们却情不自禁地走向人群,和人群保持亲和的关系。关于这方面,本雅明在《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中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本雅明看来,人群首先成为游荡者最新的避难所,在人群中,游荡者可以消灭自己的个人痕迹,也不需要保持完美的行为;其次,人群也是游荡者最新的麻醉药,正是面对街道两侧橱窗摆放的精美商品,游荡者移情于它们,在那一瞬间体会到了陶醉的本质。此外,游荡者通过从人群借来的陌生人的孤独来填满那种“每个人在自己的私利中无动于衷的孤独”给他造成的空虚。由于上面种种的原因,我们看到游荡者奋不顾身地投向人群中,他们不再把人群看作敌视的力量,相反人群成为一些有强烈吸引力的形象。正如爱伦坡在《人群中的人》中所描述的,坐在咖啡馆窗口的游荡者,看到窗外喧嚣如海的人头,也产生了想冲出去的冲动,使自己汇聚在人群中,尽情地享受人群所带来的湮没,陶醉。
于是,本雅明在写作以“论波德莱尔”为主题的两篇文章——《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巴黎》《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时通过寓言的方式将文人与资本主义市场,游荡者与人群盘根错节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折射出作为现代人的他们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迥异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文人与游荡者身处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被异化的现实所蒙蔽,能够看到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工具加紧对人控制;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使文人只是出版商手中的谋取钱财的工具,种种残酷的现实让他们精神上游离这个社会。然而,由于要应付日常维持基本生存的开销以及抵挡不住商品的麻醉与刺激,文人又走向了商品世界,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统治。就这样,文人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一种“在而不属于的”矛盾关系。针对人群,本雅明并没有直接以自己的角度进行描写,而是借助游荡者的目光以及游荡者与他的关系进行论述。本雅明通过对人群中从事不同职业的人的论述,看到了触目惊心的现实。机械化的行动、木讷的表情、呆滞的目光、不善言语的嘴角构成了人群中各色人的基本特征,他们处在这个城市的中心,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在为城市留下光鲜亮丽外表的情况下,自己却再也不能摆脱掉那种根本上非人的构成机制。
三、巴黎城市空间的“寓言”批评
《巴黎,19世纪的都城》是本雅明“拱廊街计划”的一篇纲领性文件。本雅明在1930年写给肖勒姆的信中表示“拱廊街是我的全部斗争和全部思想的舞台”①刘北成:《本雅明思想肖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8页。。本雅明的“拱廊街计划”本计划写六章:《傅立叶和拱廊》《达古勒或全景》《格朗维耶或世界表现》《路易菲利浦或内部》《波德莱尔或巴黎街道》《奥斯曼或路障》,但是他在后期只是进一步阐述了关于波德莱尔的那一部分。无论是拱门街、西洋景还是世界博览、内部世界,都是本雅明对巴黎城市空间进行审美批判的对象。本雅明对它们与文人、闲逛者、拾垃圾者的分析共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寓言”批评。在对巴黎城市空间的批判过程中,本雅明一方面看到资本主义商品世界的本质,另一方在金醉迷离的都市中看到觉醒的因素。
1855年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在巴黎举行,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成为商品的海洋,商品从此登上了使人膜拜的宝座。商品的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成为大众追逐的对象,人们沉醉于欲望满足所带来的快感,同时随着纺织业贸易的繁荣,钢铁在建筑中的广泛应用,拱廊街作为现代化程度的标志在19世纪的巴黎拔地而起。本雅明曾借用一份巴黎导游图上的话这样描述它:拱廊街是一个新的工业奢侈品的设计……玻璃做屋顶,大理石的过道经过这个建筑群街区,她的所有者联合起来作了这种开发。这些从顶上采光的过道的两旁排着最为雅致的商铺,以致这样的拱廊街市成了一个城市,甚至一个世界——微型世界。在本雅明看来,巴黎既是一片精致的废墟,又寄托着人类的梦想。
如本雅明所说的:“任何一部记录文明的史册无不同时又是一部记录残暴的史册。”①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文选》,陈永国等译,第426页。拱廊街的耸立,标识着现代建筑文明的兴盛,外表的富丽堂皇,折射出的是众多无名工人的日夜操劳。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屈从于资本家,承担着远远少于自己薪水的沉重劳动。钢铁、玻璃在建筑中的广泛使用,在他们眼中不会产生美感,更多的是冰冷的色调所带来的恐慌,臂膀所需承受的重量进一步增加,身躯也变得日趋佝偻;机器的出现,也只能馈赠他们自动化的行动、呆滞的神情。这样野蛮的现实让人们联想到古埃及修建金字塔的奴隶的心酸,秦王朝筑长城的尸横遍野。世博会的兴起,资本主义商品世界的蓬勃兴起,商品成为人争相迎娶的对象,时尚被确立为崇拜商品的方式。这一方式的确定,使时尚从商品的边缘地位上升为众人追逐的目标。但正如格朗德维埃对时尚本质所揭示的:“时尚是与有生命力的东西相对立的。它将有生命的躯体出卖给无机世界。与有生命的躯体相关联,它代表着尸体的权利。屈服于无生命的性诱惑的恋物欲是时髦的核心之所在。”②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第200页。这样,人类作为有生命的物种不得不屈从于那些无生命的无机物,大众一方面面临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所带来的肉体上的残酷剥削,另一方面也经历着精神、情感被商品化的威胁。
然而面对都市巴黎所呈现的废墟的表象,如同鲁迅在《希望》中所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本雅明同样在现代性的废墟堆积之上看到了“反抗现代性”的可能,即一种“梦”的辩证意象。“梦”对于本雅明来说是新旧意识的混合物,一方面它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与新兴的生产方式相关。拱廊街、商品也是他在梦的情境中将新旧意识混合而产生的意象,这也表明梦幻意象与他以后所运用的辩证法形象有结构上的相似性。从永久性建筑到转瞬即逝的时尚,他既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拜物教化的现实存在,又看到对抗商品社会拜物教化本质所留下的乌托邦印记,看到了人类挣脱资本主义奴役的历史客观可能性。正如本雅明引用米歇雷的格言所说“每个时代都梦想着下一个时代”。巴黎城市中拱廊街、时尚,在本雅明的梦幻体验下,变成了人们把握神秘的现实世界的一把钥匙,变成了人们梦想新的生产方式的源泉与动力。这样,“梦就变成了一种不受约束的经验的介质、一种与思维的陈腐肤浅性相对立的知识源泉”③西奥多·阿多诺等:《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郭军、曹雷雨译,第150页。。
与此同时,本雅明也注意到巴黎人私人空间的 “殖民化”。关于私人领域的“殖民化”,哈贝马斯在《公众舆论结构的转型》中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详细的阐释。他追溯了从古希腊到资产本主义社会“文学公共领域”的衍变历史。在具体探讨19世界中叶以后文学公共领域的深刻转型时,他看到“一旦文学公共领域在消费领域内部发展起来,私人领域内部事务与公众交往之间的分离就不复存在了。业余消费时间成为工作时间的补充,这样,原有的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这里,哈贝马斯主要探讨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制导下,文化活动具有了商品的性质,一方面被商业侵染的集体活动越来越难以形成公共领域,另一方面大众传媒的冲击,资本向私人领域的渗透,公众私人阅读的空间也不复存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边界也就此消亡。相比法兰克福学派新生代的哈贝马斯,本雅明虽然没有详细探讨文化活动领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发生的变化,但已经意识到经济、科技造成人内部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正如他在《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所刻画的一幅讽刺的寓言画:
从路易菲利普时代以来,资产阶级就力图弥补自己的大城市私人生活的没有意义的本质。他们在四壁之内寻找这种补偿。尽管资产阶级不能令其世俗生命永垂千古,但他们却将保存日用品的遗迹视为一种荣耀的事。他们愉快地将各类物品登记,诸如拖鞋、怀表、温度计、蛋杯、餐刀、雨伞之类,他们都竭力盖起、罩起来。①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第106页。
普通市民通过保存日用品的遗迹来对抗私生活的去意义化,但本雅明以“收藏者”的姿态看到这种私有制意义上的占有,不仅不能防备内部世界被瓦解的发生,反而被技术进步囚禁得更加严实,使商品摆脱使用的枷锁。这种反抗的姿态,被本雅明看作是一种西西弗斯式的反抗。在对内部世界惊悚的物化景观、市民愚昧庸常的反抗进行批判的同时,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本雅明也意识到内部世界要避免殖民化,普通市民不仅需要拥有这个对象,而且要把它们从市场上分离出来,在恢复它们自身的使用价值的同时,把它们从实用性的单调乏味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同样具有“革命”的意义。相比于马克思走向发动“阶级斗争”的政治革命,本雅明的这一“姿态”式的抵抗可以看作在哲学上进行着对统治已久的二元认识论进行着革命。他自己以一种别具一格的“收藏家”的姿态,通过“杂乱无章、随意地一放”的方式,使事物的事实性从一种囚禁中获得解放,对抗着私人领域被殖民化的危险。
结语
尽管本雅明后期的“拱廊街计划”是一部未竟之作,上述也只是以“寓言”这一概念为出发点对“拱廊街计划”中围绕“巴黎都城”与“城中的人”的书写进行了分析,但是从中还是能够看出后期本雅明对前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其一,他继承了在《德国悲剧起源》中应用的寓言理论,在随后的波德莱尔与拱廊街这部分内容中,仍然实践了这一理论,通过对大都会巴黎都城寓言呈现,以此来寻求拯救现代社会的深层症状。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本雅明,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者布莱希特、阿西娅·拉西斯、卢卡奇的影响,积极吸取马克思主义中对他有益的思想,并与历史唯物主义探讨的是同一类难题:力图了解资本主义。通过对文人、闲逛者、群众、拱廊街、个人居室等等一系列辩证意象的分析,本雅明走向了对发达资本主义现实的分析与思考,通过社会日常生活的全景去寻求唯物主义的方方面面,并使它自己完全潜入细节的阐释之中。但本雅明并不满足于了解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一场意识形态的批判,而是在其后的《历史哲学论纲》中,他“走出书房”提出了自己对革命的设想。他告诫人们摆脱历史主义的束缚,强调共产主义,远不是人类未来的某个目的,而切切实实就可能出现在当下,从而彻底走向了一条历史唯物主义道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本雅明在将都市大众文化作为辩证意象展开寓言批判时,他对大众文化的辩证态度:他既不完全肯定,也不彻底否定,而是在大众文化的废墟中,寻求真理的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