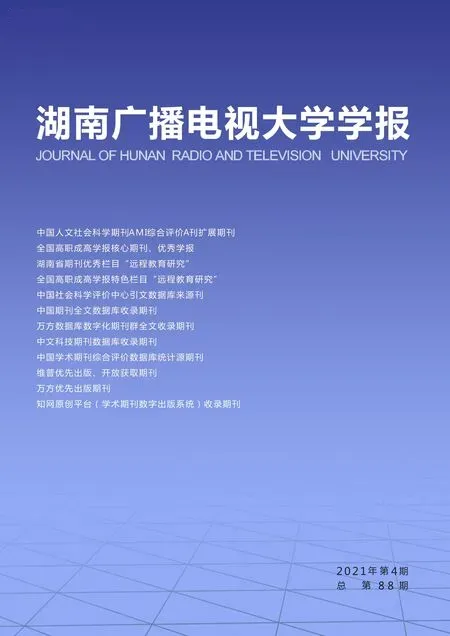失败的主体:《白鲸》中的欲望书写
2021-12-01李婉婷
李婉婷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00)
《白鲸》是一部有关欲望及其带给人毁灭性灾难的小说。此处的欲望是拉康所认为的欲望,即欲望就是要求减去需要所得的差[1]。其中所谓的要求是主体对爱的一种无条件的需要,但这种需要总是不能得到充分满足,因而在需要与要求之间便存在着主体无法拥有却又不想放弃的剩余物。这种剩余物就是真正的欲望——一个不可能被满足却又因为这种不可能时刻操控着主体的存在。由于这种操控,主体成为自我主人的尝试必然以失败告终,沦落为一个“被划杠的”分裂的主体。
不同于其他悲剧,有关欲望的悲剧是注定失败的悲剧。在欲望面前,主体注定是失败的主体,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种根本上的不可能性。这种不可能性在《白鲸》中通过莫比-迪克与亚哈的交互关系得到了多层次展示。作为对象a和菲勒斯能指的白鲸,本质上是不存在的——它是主体对于幻想中丧失之物的回溯性重建,因而是不可战胜的。亚哈对它的敌意实则是源自一种想象性的认同,即对具有神性的、全知全能的白鲸形象的认同。然而无论是将白鲸视作敌人还是视作认同对象,终究都只是一种误认。亚哈逐渐意识到,这场生死斗争并非他与白鲸之间的私人恩怨,而是存在一个第三者同时操控着斗争的双方乃至所有人,这便是拉康所说的欲望。与拉康不同的是,麦尔维尔依旧相信人与他者之间能够建立一种和谐共处的关系。这种信念又为《白鲸》这部充斥着矛盾与不祥之兆的小说带来了一线希望之光。
一、从认同到攻击:亚哈镜像自我的碎裂
镜像阶段是拉康主体哲学中重要的一环,涉及“自我经由认同于其自体的形象而形成的过程与机制”[2]27。这种形象虽然以统一体的幻想将主体整合为一,促进了“我”的结构化,但由于这个自我的镜像是从自己的外部以疏离自身的形式接受的,因而无论这个形象能够给不确定的主体以多少确定性,它仍是与自身有差异的外来的他人的形象[3]。这种原初异质物的介入为主体之后的自我完善埋下了隐患,使得主体对于那些满足自我理想的形象总是从认同转向攻击。
既然镜像阶段涉及自我认同的过程,我们便可以根据镜像理论从亚哈的认同对象入手,反向推测其欲望本相。亚哈船长的认同对象有许多,包括太阳之子、亚当、神、国王等,这些形象的共同特征是具有神性。小说中同样不乏对于白鲸的神性的描写。如当裴廓德号偶遇耶罗波安号时,耶罗波安号上的震教派先知加百列称白鲸为神,并劝亚哈不要捕杀它,否则会落得悲惨的下场[4]264。由此可见,亚哈在攻击白鲸的同时也在认同它,甚至这种认同才是其攻击白鲸的根本原因。
亚哈攻击白鲸的前提是对它的认同。他真正的欲望并非杀死白鲸,而是成为白鲸。从根本上看,这种认同是对拉康所说的菲勒斯能指的认同。也就是说,杀死白鲸并非亚哈的欲望本相,成为菲勒斯才是他真正的欲望。按照拉康的三界框架①,菲勒斯同样分为想象的菲勒斯、象征的菲勒斯以及实在的菲勒斯。在拉康看来,对想象的菲勒斯的阉割正好是实施阉割的象征的菲勒斯的符号化[5]628。因想象菲勒斯被阉割所形成的创伤在进入象征界后被符号化,通过这样的转换,菲勒斯能指就从负向价值转化为正向价值,补偿了想象对象的缺失。这意味着对于菲勒斯的追寻是亚哈试图填补自己缺失部分的尝试。这既是对身体缺陷的弥补,又是对存在层面欲望的匮乏的填补。
劳伦斯曾将《白鲸》中名为“法衣”的那一章称为“整个世界文学中描写阳物崇拜的最古老的片段”[6]195,这不无道理。麦尔维尔对于抹香鲸的描绘在许多地方都与菲勒斯相似,如以实玛利对大鲸尾巴的形容:“底端的直径约近一英尺,黑得像魁魁格那个黑檀木的偶像约约一样。说它是一个偶像吧,倒也真像,可是说得更恰切些,倒像是古代的偶像。这样一个偶像,跟在犹大的玛迦太后的秘密的丛林里找到的那东西一模一样。”[7]587玛迦太后崇拜的神之名为亚舍拉,是为亚述掌管生育繁殖的女神,与其相应的男神名为巴力。在《圣经》中,亚哈的王后耶洗别所拜的神正是巴力神。由此可见抹香鲸与菲勒斯存在内在联系。
遗憾的是,尽管追寻菲勒斯是为了填补自身的缺失,但这种追寻却只能以失败告终。拉康曾给出有关菲勒斯的算法:菲勒斯等于负一的平方根[8]。略过繁复的运算过程不谈,该等式不过是要说明主体及主体欲望的不可能性:菲勒斯就是那个被阉割后缺失的部分,实则是一种空洞的填补工具。麦尔维尔对抹香鲸额头的描写体现了菲勒斯的否定性:“感到有一种比之看到其它任何生物的额头更具有非常恐怖的神力。因为任何一点都教人看不真切,一点也看不到那明显的面貌;它既没有鼻子,眼睛,耳朵,也没有嘴巴,面孔;总之,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什么都没有;它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有如辽阔的苍穹的前额,莫名其妙地打着褶裥,不声不响地一折下去就叫小艇、大船和人都送了终。”[7]487麦尔维尔在这一句话中一连用了六个否定词来强调抹香鲸额头给人的空乏与缺失感。
亚哈的镜像认同终究只是一个幻觉、一种误认,这是自我在结构之时由于他者这个异质物的镶入所决定的。主体注定要为虚幻的、异化的自我身份问题所困扰。以亚哈为例,他与自己想象的认同对象之间永远横亘着一条残缺的右腿。这条缺失的右腿不断提醒着他与完美的认同对象之间的差异。当然,即使右腿没有残缺,他将自己视为神的观点也依旧是一种误认。而误认总有被揭穿的一天。当亚哈发现自己与认同对象之间的差距后,想象性的认同便转为猛烈的攻击。此时,白鲸成为阻碍他获得完整性的最大威胁,因而他必须通过捕杀的方式从对方那里夺回自我的主导权。
仅仅是这种发现还不足以导致真正的攻击。亚哈船长有着异于常人的偏执,正是这种近乎妄想症的气质才使他走上了命运为他铺好的道路。以此而论,亚哈与拉康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病例埃梅有着类似的症状②。亚哈的妄想症一方面体现在他所认同的超人形象以及他对自我的认知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他对白鲸之恶的夸大中。他的偏执使他的世界完全成为鲸的形状,世界就此成为他复仇的对象,失去了任何其他的可能性与希望:“我自己就浑身都漏了。……不但全是些漏桶,而且是漏船里的漏桶;这比‘裴廓德号’的处境还更来得糟,老朋友。”[7]664他将自己完全禁锢在想象界,停留在自我封闭的幻觉之中,这样的固执使他在捕杀白鲸的同时也对自己的生命造成了戕害。
白鲸是亚哈的菲勒斯欲望,但又不只是他的欲望。它还象征着水手们对财富的欲望和以实玛利想要追寻真相的欲望。麦尔维尔曾说:“想要写出伟大的作品,就需要有伟大的题材。”[4]376对鲸题材的关涉也象征着他想要成为像莎士比亚那样伟大的作家的欲望。可以说,鲸象征的是所有人的欲望。而它与亚哈之间的斗争同时也喻示着人们与自我欲望的搏斗。
二、主体的困境:注定失败的复仇
在《白鲸》中,麦尔维尔毫不避讳地指出了亚哈所具有的偏执狂性格,形容他是个疯狂的偏执症患者[4]153。然而作为反抗姿态的体现,亚哈的偏执也具有积极的作用。尽管他将自己封闭在想象界的行为有逃避象征界现实环境的嫌疑,但他的自我封闭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象征界权威的否定与拒绝。亚哈很好地体现了拉康的伦理学旨趣,即“不要向欲望让步”[5]97。“我决不会像小学生对那些欺弱凌善的恶徒那样说——去找些跟你身材差不多的人干吧!别来打我!”[7]236这表明亚哈知道对手比自己强大,尽管“你已经把我敲倒了,我又爬起来了”[7]236。亚哈勇敢地回应了欲望的召唤,但他的复仇终究还是失败了。这也是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亚哈的偏执使他无法向他人敞开心扉而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之中。如果说哈姆莱特的犹豫是试图维持三界平衡的尝试[9],那么亚哈的偏执与行动力展现的则是他陷于想象界无法自拔的困境。亚哈可以说是爱默生自助精神极端化的体现,当自助精神发展到唯我论的程度,精神、情感或身体的死亡便成为他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是一部书写异化生活的作品。这种异化来自过多地乃至神经质地依赖于某人自己。”[10]105亚哈在自我疯狂中失去了自身的印记,这个印记来自人在象征界中与他人的交互与联系。由于把这个印记排除到自己的外部,在成功建构了一个强大的自我形象后,亚哈又沦落为一个无法知道自己是谁的无情的人。
亚哈的失败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即人之欲望的本相决定了人注定是失败的主体。拉康的对象a说明了这一点。对象a是引发欲望对象或者说使某个对象成其为欲望对象的东西。它是一种不可能之物,一种根本性的匮乏。主体在自己的欲望之路上一次一次地追逐对象a的踪影,可就是无法将它召唤到眼前。小说中的白鲸就是亚哈的对象a,它神出鬼没且自始至终都没把亚哈放在眼里。这种冷漠的态度与亚哈的偏执和疯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让人明白谁才是真正的主人。小说最后对白鲸的三次捕杀也是高度象征化的,主体总是与对象a失之交臂,如裴廓德号的前两次追杀。而在最后一次的捕杀中,双方终于碰面,但却是以除以实玛利之外的船上人员死亡为代价——也唯有死亡才能将主体带到对象a的面前。这意味着除了死亡之外,主体每一次对欲望的追寻都以失败告终。
不仅主体的追寻总会失败,就连主体追寻的行为本身也是身不由己的。“哎,现在是它在追我,而不是我在追它啦。”[4]461在拉康对爱伦·坡《失窃的信》的解读中,他指出辗转于王后、大臣与迪潘手中的这封信才是故事中真正的主体。他认为这封信正好阐明了他的思想,即能指决定着主体,而非主体自己掌控着自己[2]65-66。拥有强大意志的亚哈下意识感受到的那种受制于人的绝望便源于此,“是什么欺诈的、隐藏的统治者和君王,和残酷无情的皇帝在控制我,才弄得我违反一切常情的爱慕,这么始终不停地硬冲、硬挤、硬塞”[7]762。
美国评论家蔡斯曾说麦尔维尔的人物都在追寻真相。确实,麦尔维尔对真相问题极为热衷③[11]。按照上述分析,这个真相可以说就是有关欲望的真相。存在于实在界的欲望之真相作为前语言的存在本是无以言表的。小说中的抹香鲸作为欲望之真相的代表同样无以言表:抹香鲸本身没有舌头,且表现出一种“莫测高深的缄默”[7]488。然而,如同对象a会从实在界来到想象界与象征界一样,真相的声音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泄露出来。
在弗洛伊德和拉康那里,口误与梦呓成为人无意识泄露真相的裂隙。而在《白鲸》中,起到这种功用的则是人物比普的疯话。比普的疯话无人能懂,因为他的语言不是象征界的语言,而是来自实在界的言说。亚哈说在比普身上看见了有关自我疯狂的真相,这是因为他在比普混乱的语言与疯狂中看见了自我欲望的本相。在他一系列英雄狂想式的认同对象中,终于加入了他真正的认同对象——一个被欲望折磨几近崩溃的人。他想要像空气一般自由,却负债累累。这个债是他为了追寻自己的欲望而亏欠他人的债,如同麦克白的弑主一样是无法象征化的幽灵,将永远缠绕着他,使他永远得不到自己想要的。
但亚哈异于常人之处在于他敢于应对欲望的召唤,即使是以毁灭为代价,也绝不向欲望低头。他勇敢地面对命运,同时又被命运无情地嘲弄。更为残忍的是,越是像亚哈一般勇于反抗欲望的人,越是会受到它无声的嘲笑,这里透露出麦尔维尔对于执着精神的谨慎态度。他在亚哈身上见证了人类最伟大的自由精神朝故步自封的盲目个人主义发酵的全过程,因此他借以实玛利之口提醒人们不要太相信自己的本事,要警惕自我偏执的欲望之火。
三、亚哈困境的破除:“人类大团结”与晦暗中的平衡
麦尔维尔之所以会如此审慎地对待亚哈的偏执,是因为他看到了亚哈执着精神的两面性。当执着精神与偏执狂式的反抗精神混合并走向极端时,就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劳伦斯曾形容裴廓德号是由一个疯子带领的理性主义大军。亚哈的疯狂与比普不同,这是一种用理性包裹着的危险而狂躁的疯狂,是麦尔维尔在《水手比利·巴德》中所提到的那种与生俱来的本质性的疯狂。如果说斯达巴克代表的是美国人的实用主义精神,那么亚哈所代表的正是这种精神走向极端后所显露的疯狂本相。
实用主义是美国的本土哲学,美国人重新定义了真理,认为“有用即真理,真理即有用”[12],否定绝对真理的存在。实用主义并非无中生有,它其实是将一种向来如此的美国经验上升成理论,这种经验深深地根植于他们早期的宗教信仰之中。马克思·韦伯认为,新教思想中努力工作而摒弃享乐的精神乃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的重要特征[13]。这种思想在亚哈身上被放大为对捕鲸之外所有事都漠不关心的极端态度。本来积极行动与勇敢反抗是他的优秀品质,然而极端的实用主义精神又使他在对他人的遭遇无动于衷的同时,也不允许自己有丝毫松懈,只能被动地被白鲸的能指链一路拖行,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与亚哈一样,麦尔维尔本人也始终处于一种躁动不安之中。他不断地出海、归家、出海,却始终找寻不到理想中的温柔乡。他们的行动都未将他们带往任何地方,正如小说中指出的有关探索的灾难一般。美国是富有探索精神的国家,西进运动不仅拓宽了其版图,也将一种乐观的探索精神注入了它的灵魂。但如果探索的旅程是为了一些梦想中虚无缥缈的东西,或是痛苦地追击那迟早要泛上人类心头的魔影,这样的航行就只会将我们引向徒劳的迷宫,或是教我们中途覆灭[4]198。
然而麦尔维尔并非看不见一点出路。与拉康不同,他认为人与他者之间的兄弟情谊或许能成为走出亚哈困境的办法。拉康认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并非如科耶夫或黑格尔所说的是两个主体间的关系,而是欲望与欲望对象的关系。自我对他人的想象性认同实则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最根本的侵凌性就是欲望他人消失[5]598-599。这意味着在想象的层面,所谓人类共存根本不可能。然而,麦尔维尔却将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视为对抗残酷生活的手段,这种兄弟情谊也可以称为“人类大团结”。“人类大团结”并非指稳定的社会秩序,“而是一种相对自由的田园牧歌式的关系。它是在一些出于相同的目的而被暂时聚集起来的人之间所产生的,理想而个性化的对于人类命运的共同承担”[10]106。在小说中,以实玛利与魁魁格之间便具有这种亲密的关系。在名为“猴索”的那章里,两人被绑在同一条绳子的两头,配合完成危险的剖割大鲸的工作。“这样,一根细长的暹罗绳子就把我们连结在一起。魁魁格就是我的难分难舍的孪生兄弟,我随便怎样都无法摆脱这条麻绳需要负担的危险责任了。”[7]448此外,在“手的揉捏”那章中,以实玛利在与船员们共同挤压鲸油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一种亲密美妙的情谊。他们手叠着手,互相挤压着,仿佛在互相确认对方心中也有与自己同样的情愫。而麦尔维尔用捕鲸者这一身份取代国别身份,使来自不同国家的人都亲如兄弟并在联欢会中欢歌热舞的设想,同样也是对“人类大团结”的情景展现。
麦尔维尔对于晦暗中平衡的强调,可以看作是走出亚哈困境的另一条出路。如果说“人类大团结”意在维持外在的关系平衡,那么晦暗中的平衡则是为了保持内在的心理平衡。所谓晦暗指的是麦尔维尔对于事物所持有的一种暧昧不明的态度。在小说中,这种含混主要是通过对矛盾观点的展示来表现的,而矛盾也被视为《白鲸》最重要的主题之一。麦尔维尔曾分析霍桑的黑暗性力量,认为这种力量源自加尔文教的原罪观。因为当人在衡量这个世界的时候,多少都需要一点罪恶来使天平平衡。以此而论,平衡或许是比矛盾更重要的主题。在“喷泉”那章中,有关彩虹的描写直接体现了平衡主题:彩虹的出现需要朦胧的水汽作为背景。在“我”充满疑惑的头脑中,对于真相的直觉偶尔击中“我”,像是从天堂射入迷雾中的一束光。正是在这种疑虑与直觉的混同中,“我”既不成为一个信徒,也不做异教徒,维持了“我”自身的平衡[4]310。可以说,亚哈的问题便是他太想揭开欲望真相的面纱,却不管自己能否承受,因而失去了生活的平衡术。事实上,真相并非人能承受的。各种矛盾与晦暗不明的存在就如同幕布一样遮挡住了可怕的真相,使人能够在象征界存活。换句话说,尽管主体注定是分裂的主体、失败的主体,但人之存在最重要的本就不是胜利,而是对于生命之平衡的维持。
当以实玛利与裴廓德号的老板签约时,后者向他形容亚哈是“不敬神却又像神似的人物”[4]68。从他的表述里我们能一窥当时社会信仰的衰落:神被人所取代,从名词变为形容词。这样的转换当然有利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然而人们在庆祝他们的胜利的同时,也失去了许多东西:他们忘记了有比个体存在更高更大的东西,个体也能够在其自身以外更高更大的东西中找到他自身的完整性。这便是为何亚哈的偏执在激发他的同时又使他走向毁灭。
也许,麦尔维尔正是感受到了这种隐患,才在书中设置了比比皆是的不祥之兆。而这些不祥之兆除了预示裴廓德号的悲剧外,也同样预示了人类的悲剧,就像劳伦斯所说这是“我们白种人时代的厄运”[6]200。然而,至少在《白鲸》中,麦尔维尔尚未放弃所有希望。我们总是能透过迷雾般笼罩的厄运发现一道彩虹,它指向幸福的存在。像亚哈那样陷于自己的幻想中是不可能得到幸福的,幸福“存在于妻子,心坎,床上,桌上,马背上,火炉边和田野间”[7]584。
四、结论
正如拉康认为《哈姆莱特》是一部关于欲望的悲剧一样,《白鲸》也是一部有关欲望及其带给人的毁灭性灾难的悲剧。亚哈的欲望是成为像莫比-迪克般充满神性的大主宰。换句话说,他真正的欲望不是杀死白鲸,而是成为白鲸。与之类似的是船员们对于亚哈的欲望。他们追随亚哈并非仅是因为受压迫或是利益驱使,亚哈身上的英雄气概在振奋人心的同时自然也成为船员们心之向往的理想。还有以实玛利,一个精神上的孤儿,在他的无意识深处始终寻找着母亲,因而他将亚哈、裴廓德号、大海都视为象征性的母亲。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欲望都逃脱不了欲望本质性的匮乏与不可能。亚哈与船员最终失去了生命,以实玛利虽然活了下来,却又一次成了孤儿。
主体对于欲望的追求必将以失败告终。即使是亚哈这般勇敢反抗欲望的人,也因将自我封闭在想象界而渐渐沦为欲望的玩物。对于麦尔维尔而言,走出这一困境的方法不是反抗,而是竭力维持平衡。他看到了资本主义过度发展给人带来的偏执症,也看到了人如果过分执着于某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会落入怎样的结局。因而他强调平衡的重要性,强调人不能故步自封于自我的执念,而应在与他人的和谐友爱中获得幸福,然而这样的理想最终似乎也消散在了一种不可能之中。在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水手比利·巴德》中,对于平衡的强调被还原为一种政治上的中庸主义思想,比利·巴德的死成为维护这种平衡的牺牲品,麦尔维尔似乎已失去了他在《白鲸》中对于平衡的信心。
注释:
①三界即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想象界在一般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人的主观世界,它是一个前语言领域。当婴儿开始运用语言来表达自我的需要时,他便进入了象征界。象征界受能指的统治,主体的欲望只能通过能指的转喻与隐喻得到失败性的满足。而拉康关于实在界的观点则更为复杂,他将实在界称为一种缺场的在场,是一个不存在的存在。实在界一方面支撑着我们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也破坏着我们的现实。需要注意的是,拉康三界学说中的主体不是从一种秩序阶段性地过渡到另一种秩序,而是在三种秩序的交叉中不断滑动。
②埃梅本来将女演员Z夫人视为人格理想,但在她的文学事业失败之后,理想与自我的距离与虚幻关系就暴露出来。这一镜像所反映的不再是一个完美统一的自我,相反,它映衬出自我的另一方面,即缺乏,并激起焦虑与仇恨的负面心理体验。当埃梅的刀刺向对方时,她所要否定的是对她的否定,她想消灭的正是她内心的虚无。在无意识层面,亚哈对白鲸的攻击同样遵循了这样的逻辑。
③在1849年写给戴金克的信中,麦尔维尔认为即使是莎士比亚也并非完全诚实,事实上在这难以忍受的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做到完全诚实,直到《独立宣言》的诞生。也就是说他将真实看作是美国人的优势,是美国精神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