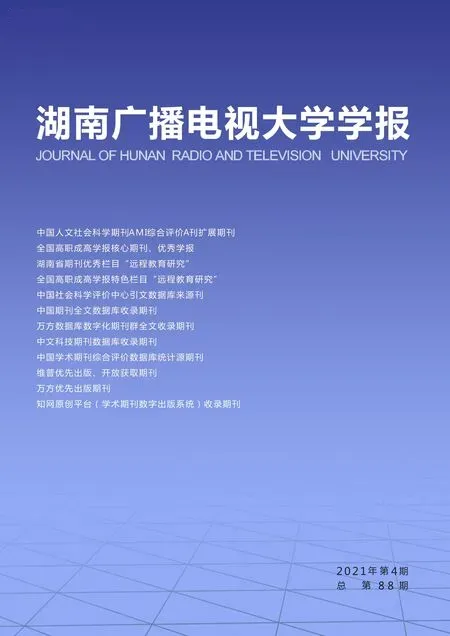漆树与割漆匠共生模式研究
——基于陕西龙头村的田野调查
2021-12-01海燕
海 燕
(宁夏大学法学院,宁夏银川 750021)
植物作为一种自然和文化产物,在人类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漆树是我国重要的经济树种,早在数千年前古人就开始种植漆树和使用生漆。生漆是漆树的自然结晶,作为天然树脂涂料享有“涂料之王”的美誉。生漆主要依靠人工割收,割漆匠是以割漆作为生计方式的职业群体。笔者对漆树与割漆匠共生模式的关注源于对陕西龙头村的田野调查。在田野调查时发现,龙头村的漆树割口形状、割漆工具与湖北金龙坝村的不同,龙头村的割漆匠一致认为漆树是宝树,长在山里能防止水土流失,割收生漆能创造经济价值,漆树割口是割漆匠与漆树的交流窗口。在他们心目中,漆树不仅是植物,亦是共同成长和交流的伙伴。回顾对漆树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病虫害防治、根苗培育、品种研发等方面,对割漆匠的研究则侧重于割漆技术改进和对割漆过程的描述,尚未发现关注割漆匠与漆树关系的研究成果。
近年来由于国家政策调整,经济作物更替,漆树数量减少,割漆匠数量减少且年龄偏大,但仍应看到漆树种植对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有着重要作用,割漆匠对于漆树种植、生漆割收、我国漆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生漆是漆树延续生命的“血液”,割漆是割漆匠的重要经济来源,是其维持生活的重要物质基础。将漆树与割漆匠以生漆为媒介形成的共生模式作为切入点,关注漆树与割漆匠的关系,实质上是聚焦人与植物的关系,这同时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延续生物多样性的例证。基于以上缘由,本文拟结合田野调查资料,对漆树与割漆匠的共生模式进行阐述。
一、变迁范畴下的漆树与割漆匠
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以及政策的引导,人们的思想观念转变,受教育程度提高,生计方式多样化,漆树与割漆匠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可分为改革开放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20世纪末至今三个阶段。
(一)改革开放前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发展不平衡。为了发展经济,国家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开展工业建设,工业产品(如缝纫机、农机具、车船、五金件、电气设备等)需求量增大。生漆作为优良防腐剂,涂到工业产品表层有防腐防潮效果,能延长其使用寿命和提高其利用率,由此生漆的需求量增大,价格持续走高。在生产队里,漆树是“摇钱树”,割漆匠是“财政大臣”,龙头村结合自然优势大量种植漆树,配有专业人员进行育苗、病虫害防治,选出2—3名社员当职业割漆匠,通过割收生漆提高经济收入。
在人民公社时期,广大农村实行单一的集体所有制,农村的生活消费品按工分配,收入差别很小[1]15。生产队会根据相关规定奖励完成任务的割漆匠,割漆匠家庭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现年76岁的某割漆匠说:“那时我们为生产队搞经济建设,地里种的粮食、宰杀的牛羊肉都分给社员,没啥子卖钱,就靠卖生漆获取经济收入。那时在生产队,割漆匠可算是个人物。苦累时吼两嗓子漆山歌,觉得很美气。”78岁的某割漆匠也证实了这一点:“那时割漆是生产队的副业,我从1960年开始割漆到1980年休刀,割了20年漆。割漆匠在生产队待遇比较好,完成任务后生产队会多分60斤大米或者苞谷、2条毛巾、2块肥皂作为奖励。”说明割漆匠的收入高于一般社员。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过去,每一种生计方式都是人与大自然的交流对话,割漆匠与漆树之间形成约定,体现为以割漆匠为主体、漆树为客体的主客体平等精神和自愿原则,以交换生漆的形式实现,对漆树生长与生命的维护是割漆匠给予漆树的回赠。
共生模式聚焦割漆匠的社会道德与社会价值,折射出漆树的树体与灵魂,增强人与物之间的维系力,形成人与树的超社会体情感和状态。人与物之间应该有一套或建立一套“不同生计手段的组织方式或交换方式”[2]314,割漆匠与漆树经过长时间磨合、了解形成了稳定的交换方式。由于漆树根浅藏于土地表层,蓬松的土壤更有利于根的发育、生长、延伸,化肥的不合理使用、病虫害、割口位置与数量对漆树的生长和寿命都有影响。割漆匠根据漆树习性进行维护,农闲时挑农家肥给漆树松土施肥,每年农历四月初把漆树周边杂草清理干净,打钉子或绑架,便于攀树。“足不足,一十六”,一棵漆树无论分泌的漆有多少,最多割16刀。割口太大、太宽、太多、太深,会造成树叶蜷缩、干枯,漆树也会慢慢死亡。所以,割漆匠不能得“红眼病”,不能割“黑心漆”,这是对割漆匠行为的约束。每种行为模式都渗透着文化因素,但文化有着自身的演化力量,而不仅仅是基因和自然环境互动的结果[3]。这一实践传承是割漆匠与漆树之间的信约交换,是人与自然跨物种的文化交流,从而完成生漆从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的转变,割漆匠也从中获取经济收益。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
哈里思认为社会文化系统的演化主要是人类生活对物质条件的适应[2]154。割漆匠为了物质需要与其所处环境进行了更好的协调互动,在适应自然环境的同时也在适应国家政策调整与经济发展要求。20世纪80年代,农村地区开始改革,逐步实行以家庭承包为核心的农业经营制度,实现了农业生产微观组织的重构,农户取代生产队成为农业经济的细胞[1]89,身份从社员转化为农民。被束缚于土地的农村人在改革开放后实现人员流动和产业转移,农民身份不再单一。生产队里的职业割漆匠呈现出农、工、商三业并举的生计结构。土地包产到户后,种植经营自主化,割漆匠春季种地,夏季割漆,农闲时做一些小本生意。有些农民分到的田地里有漆树,可以碰生漆的村民跟着老割漆匠学割漆,有些会割漆的人认为割漆收入高于种地收入,就会在山上种植漆树,导致割漆匠数量增多。当时生产队里30多户人家,19户人家有割漆匠。也有一部分老割漆匠不再割漆,正如现年74岁的某割漆匠所言:“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后我就不再割漆,主要是漆树都按地按户分配到不同家庭,有的农民将漆树砍了种地或承包给其他人割,我没有漆树割就开始种地,遇到建桥修路、修水库时就去做工,也能挣好多钱,一年家里开销就够了。”说明农民生计方式受国家政策调整的影响。每一种生计方式都是人们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有效适应,从而达到稳定、均衡的状态,并产生相应的生计文化。斯图尔特认为文化有个核心中枢对生态适应特别敏锐,并将生计技术、生产、控制和分配食物及其他稀缺物品的社会组织视为文化的核心中枢[2]154-155。
割漆是割漆匠家庭的重要经济来源,占据其家庭经济收入的较大比重。割漆匠夏季割漆来钱快,上午上山割漆,下午就能换成现金。某割漆匠妻子讲述割漆:“我老汉苦得很,以前割漆就为三个娃子上学学费,一年几百块钱的学费要交给学校。我们都是农民,地里种的庄稼都吃了,没来钱的路,就靠我老汉一年割漆卖钱供养娃娃上学。要不是割漆卖钱,我就得卖粮食来供养娃子,那我家就没啥揭锅。总的来说,割漆收入还是好一些,我家修房子花了近40万元,割漆卖钱攒大部分,向银行贷了小部分。封顶后装修钱都是老汉夏天割漆、其他时间做木工挣的钱。”63岁的刘某包产到户后成为割漆匠,他说:“我割了20多年漆,日子过得还好。割漆来钱快,拿到钱会给家里置办一些物件,还会给家里买猪子养。以前家在山上,地里种啥东西也能收获,割漆可以解决家里燃眉之急,同时还可以有一些积蓄。”说明这一时期人们对土地种植的安排多样化,以种植收益高的经济作物和粮食为主,割漆是经济创收的重要方式。由于漆树从种植到收益需要8到10年,周期长,占地多,很多农民不会选择种植漆树。割漆匠割漆的树主要从其他村民手中租或买,数量总体上相对稳定,但与人民公社时期相比数量减少,主要是因为在新漆树种植量减少的同时,之前种植的老漆树进入枯死期。割漆匠坚持优先保护漆树的原则,采取减少割口、歇年或轮休的方式,增加割口愈合时间,延长漆树生命。漆树在经历生长与枯萎这一自然过程的同时也在与人类交流,割漆匠与漆树之间的沟通主要是通过时间相互传递信息,对漆树这种生物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是割漆匠们共同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财富,也是实现漆树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源泉。
(三)20世纪末至今
20世纪末至今,由于外出务工人员增多,农村学子大中专毕业后大部分留在城市,农村劳动力减少。加上割漆苦、周期短、漆树少,年轻割漆匠进城务工,只有年龄较大且没有一技之长的老割漆匠还在割漆。如今很少有年轻人会割漆,这一传统生计行当步入活态传承的“寒冬”。很多地方成立生漆专业合作社,但从事割漆和种植漆树的人依然是那些老割漆匠,平均年龄超过60岁。他们对漆树有着深厚的感情,以前条件艰苦他们靠割漆养活一家老小、培育子女,年老时割漆则是他们持续的习惯。保护、延长漆树寿命就是维持割漆匠的生活现状,这是割漆匠的群体价值认同和集体意识。
在人与自然共生共长共存的实践关系中,随着社会变迁,割漆匠与漆树共同经历数量增多之后持续减少的历史过程。割漆匠数量下降,主要是由于割漆辛苦且周期短,而外出务工收入稳定。漆树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有:一是由于漆树自身生命周期为25—30年,自然死亡增多;二是割口过多,位置不合理,漆树割收期缩短;三是退耕还林后很多割漆匠搬离原住地,漆树疏于管理加快死亡;四是病虫害导致漆树在育苗期与生长期存活率低。
二、共生范畴下的漆树与割漆匠
漆树与割漆匠聚焦于生漆和割漆阐释共生的文化意蕴。割漆匠就如挑夫,其“扁担”两边是漆树的生命和割漆匠的生活。共生就是人与树共存、互惠,折射出漆树生命与尊严的同时亦透射出割漆匠的生活与精神,说明人类向自然索取时须节制、有度,向善而生,自然则给予人类友好的馈赠。割漆匠生计体系与漆树生命过程保持一致,他们之间以互惠的方式维持平衡。在这一特殊的关系结构中,割漆匠依赖生态环境,以大山为家、以漆树为伴的生活状态滋养了他们纯朴善良、不贪心、割取有度、坚持坚韧的品格,这是与生存环境、生计方式长期共存的产物,在深层次上则是对漆树以及其它植物的尊重。在人与树的共生中,每一位割漆匠都恪守共同的文化守则,漆树也同样遵循自然规律,这也是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和融合的过程。
生漆是割漆匠与漆树的互惠基础。生漆是漆树分泌的汁液,也是延续其生命的“血液”,适当“放血”有益于其生长,部分漆树甚至因没有及时“放血”而“胀死”。割漆匠是漆树“血液”循环的负责人,同时通过割漆养家糊口,从而形成超社会体的共生模式。在人的社会交往中讲究礼尚往来,尤其注重贵重物品的象征性流动,人际关系的建立与物的再分配同步进行,并遵循共同的文化准则,即交换意味着共同的价值标准[2]311。在人与物的交换中,交换物是人关注的焦点,在割漆匠与漆树的交换过程中聚焦于生漆,互惠关系延续至今。在特有的生态环境和特定情境中,割漆匠与漆树“约定”交换条件与制度,漆树的生产、传递与割漆匠的生存、发展紧密相关,使他们的生命、生活以及财富积累可持续,从而创造出共同的文化代码。虽说文化是社会性对话的工具与意义,但文化在人与自然物之间的主体性表达依然是自然之物所需要的生命意义,即使这是自然物的自然选择或者是无意识的行为,因为有了人的参与赋予其仪式与意义,人们就可以认为其中进行了文化传递。
(一)生漆品质折射漆树的生命与尊严
植物作为重要的自然和文化产物,对人的生活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正如林奈通过对经济学原理的探索,认为对自然的精确研究可以增加国家的财富[4]。植物学家研究本土居民对当地植物的利用与关注其价值时,认为植物是“绿色黄金”,而取自漆树的生漆是商品,被称为“黑色黄金”。生漆从割口刚流出时是乳白色,接触空气后变成褐色,最后成为黑色,故有“白如雪,红如血,黑如铁”的说法。《平利县志》称誉生漆:“漆液清如油,光亮照见头,搅动琥珀色,挑起如钓钩。”[5]这是人们对生漆质量的赞美。高质量的生漆与优质的漆树、生漆的割收密切相关。
1.优质漆树。漆树的出漆量、生长寿命都与生漆质量相关。割漆匠判断漆树质量主要看三个方面,即叶子、土壤、割口。一般情况下叶子绿、割口少就是好树。漆树生长和分泌生漆需要阳光、蓬松的土壤、适宜的湿度,沙土、黄沙土、黑沙土等土质生长的漆树出漆多,黄泥巴土质黏性大,生长的漆树出漆少。割漆匠们总结出漆树种植的经验口诀:“坡地跑树根,漆树长得茂;平地水泡根,活不出几日。”优质生漆产自好漆树,漆树研究者会将优良漆树的根进行培育,提升成活率,扩大栽植面积,从而提高优质生漆的产量。
2.生漆的割与收。割漆有特定流程,即放水、插捡子、开漆口、收漆,这一过程不仅考验割漆匠的技艺,也是割漆匠以刀为笔、以漆树为纸的写实创作,主要体现在割口和收漆环节。一要割口位置准。割漆匠初学割漆从判断割口位置开始,练就视漆树漆路如看人体筋络的眼力,总结出“凹漆凸水”的辨别方法。割口时讲究一半水路、一半漆路,从而达到出漆多、保护树的目的,这是对割漆匠技术、刀工、眼力、经验的综合考验。经过长期实践,割漆匠总结出适应当地环境的割漆知识,以口耳相授的方式代代相传,如:“头刀正,二刀扭,三刀四刀对老口”;严禁在一条线上割口,避免割断“大动脉”“经路”,阻断营养物质输送导致漆树死亡。二要两手都会握漆刀。握漆刀方式和割口倾斜度影响割漆速度。三要讲究割口形状。割口大小、宽窄是衡量割漆技艺的重要标准,如何使割出来的漆液朝着一个角度流出且出漆多,其诀窍是割口形状要呈直八字形,也称为V字形,这种割口简单易学、方便操作,但割口宽大不易愈合。割漆匠为了割口快速愈合就需要在V字形的割口中间留下一道树皮,看起来像牛鼻子,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牛鼻子割口。由于这种割口割起来费时费力,很多割漆匠不会或不愿意割,仅有少数60岁以上的老割漆匠掌握这一技能。已过古稀之年的某割漆匠说:“牛鼻子形割口养树,一棵漆树,人家割5年,我能割10年。漆树活得久,我收的漆就多,漆树主人收入也多。”四要掌握收漆时间并注意安全。一般开口四小时后开始收漆。收漆时将漆桶挂在左手腕或脖子上,右手取下插在左手中,左手的拇指与食指夹住塑料叶(割漆匠用较硬的塑料剪成形状、大小如同较大树叶的塑料片用来接漆,相对于贝壳,塑料叶更轻更方便携带)或贝壳,将生漆倒入漆桶,并用刮漆板将漆刮干净。收漆安全主要是指割漆匠的自身安全和生漆安全,收漆时要上树取下接漆壳,整个过程中要防止脚打滑或在路上发生倒漆伤人事故。68岁的某木匠在包产到户后成为割漆匠,他说:“我第一年割漆是在伏天,皮肤沾到漆就烂。大太阳底下,衣服穿上热得受不了,脱了就沾漆,皮肤烂了被汗一泡就疼得受不了,还不敢用手去抓,一抓烂得更多,也没啥子办法可治,就得忍着。有一次我把漆收完了,是割的三遍刀了,漆树出漆量大了很多,那一天能收五六斤。在回家的路上爬一道坎子时没抓稳,身体向后一仰,漆桶里的漆就全部泼到我身上,当时就没管漆,急忙将衣服脱得只剩下大裤衩。我的速度是快,可腿上、肚子上还是沾到了漆,肚子上的皮肤烂了一些,腿上沾漆的地方有些红肿。等把身体弄好后才去找漆桶,提起漆桶发现倒得没剩多少。我也没办法只能回家,走到门口一听家里来了客人,穿着大裤衩不能直接进门打招呼,就从后屋翻墙进去,洗了脸,换好衣服出来,亲戚以为我才起床。从那次以后我就小心了很多,但两条腿上留下了漆疤子,漆疤子很疼。”说明收漆时存在一定的危险,需要注意安全。
(二)割漆收入透射割漆匠的生活与精神
每一种生计方式的选择都与地方性知识、当地生态环境紧密相连,人与植物的关系实质上体现了当地人对生物资源加以利用与保护的历史过程。生存技艺是对传统实践经验的传承与创新,割漆就是割漆匠的集体记忆,通过关注其文化行为,展示集体欢腾,割漆浓缩着割漆匠群体的社会与文化。
平利县民间谚语有“家有千株漆,有吃又有衣”[6]之说。随着时间推移,不同时期割漆对割漆匠及其家庭具有不同的意义。早期割漆匠以割漆为生,割漆收入对其家庭具有重要影响。割漆匠传承上一代的割漆技艺,通过割漆赚取人生的第一桶金置办家业、培养子女。割漆匠在改革开放前的生活条件高于一般社员,完成任务后能获得工分、物质及精神奖励。如今依然在割漆的67岁的某割漆匠说:“我一个人三个月割几百斤漆,生产队奖励50斤谷子、180斤麦子。按任务算,1斤漆给1斤麦子,还可以平价去粮站买粮食,加上凭工分分的粮食,一家老小一年口粮就够了。割漆是苦活路,身上要掉两层皮。所以,割漆匠是生产队的一级劳动力,待遇好。我在割漆的第二年就起(盖)了这个房子。”说明割漆匠割漆对于组织与个人都有好处。实行联产承包后农民有了土地,割漆依然是来钱快、补贴家用的好活路。务农的割漆匠种地收获粮食和蔬菜,割漆收入则用于家庭琐事、孩子学费、医药费用等开支。他们用记忆、技艺与漆树及周边的环境交流,形成默契的共生关系。依然在割漆的某割漆匠说:“割漆时觉得无聊就吼两嗓子漆山歌,吓走猛兽,招来伙伴。有时候看着从小割到老的漆树,就想起自己也老了,漆树就成为伴儿。累了,就坐在漆树边儿和它说说心里话,看着漆树一茬一茬老了,枯了,我的一辈子也剩得不多了。”漆树与割漆匠一起成长,是生命与生活中的伙伴,是排解孤独与困难的知己,是守山护林的搭档,一起变老,相互守护。
漆树浑身都是宝,树籽可榨油,树叶可作药材,木材坚实耐潮可用于制作家具或农具。现在的年轻人会在割漆的基础上创收,将漆树的经济价值最大化。在田野调查中,2010年成为割漆匠且年龄最小(36岁)的某割漆匠说:“去年和今年卖漆收入超过4万块钱,只用了80天,一天大概收入500多元。我是边割边学习漆树相关的知识,对家里的老漆树进行研究,将籽、叶、木的实用价值、药用价值同步开发,明年春天准备试种20亩,进一步扩大种植面积与种植数量。”年轻割漆匠对漆树价值进行综合开发,拓宽漆树的创收途径,开始实现对种植漆树这一生计方式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每一代割漆匠都有其使命与责任,他们的生活、生计与漆树休戚与共,更是地域文化的创造者。割漆匠结合本地漆树的品种与特性,割出不同形状割口,唱着漆山歌,这更是一种文化象征,割漆匠群体因为这些支配性符号被动员起来。虽然95%以上的割漆匠已年过半百,但他们依然为漆树种植、生漆割收贡献力量。
三、关怀范畴下的漆树与割漆匠
生命内涵在不同学科中有着不同的表达,其意义体现包含生物层面有生命迹象的物,社会层面的各种关系的总和,精神层面的自我认知与超越,需要关注、观照的是生命存在的实质性价值,即自然生命、社会生命、精神生命。赫舍尔在《人是谁》中指出:“人存在于他的思想之中,特别是存在于他认识或理解自身的方法之中。”[7]这是人的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亦是其自我认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漆树本是有生命的物种,人在精神层面赋予漆树以精神生命。割漆匠与漆树在共生过程中诠释了生命哲学的现实意义,达到了人与树和谐共生。
(一)人树平等是尊重生命的情感表达
割漆匠与漆树以生漆为媒介相联系,绝非纯粹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而是涵盖了比物质更高层次的情感需要,充分体现了对生命的关怀。割漆匠以其直观的行为、朴素的文化认知映射出人类的道德、爱以及万物平等的价值理念。文化传承的最好方式是成为人的生存机制,“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最主要的内涵,而且也是我们最多的外在表现,我们个体和群体的特性”[8]。传承包含生计秩序、技艺体系以及文化精神等,要求人去除人类中心主义,抛弃自然中心主义,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物共生的状态,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每一棵漆树存活期间产漆,每一位割漆匠割收生漆、过好自己的生活以实现自身及生产的可持续。其间人与物的情感交流体现了物之有灵,情感平等是维持秩序的需要,亦是情感交换的互惠原则[9],体现了人的关照与物的付出的互惠合作。割漆匠对漆树的情感表达主要体现在选定割口位置、把控割口大小等实际行动中,漆树对割漆匠的情感反馈以出漆量多、寿命延长来表达,他们“在追求共同目的的前提下,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对方所表达出来的需要”[10]。
(二)祭拜仪式是敬畏生命的文化事实
仪式是由古老传统习俗沿袭而来的集体行为方式,表达人的某种普遍体验或共同体验。马尔库斯认为,人类学家长期以来把仪式当成观察情绪、感情以及经验的意义灌注的适当工具[11]。仪式是富有地域性的文化传承载体,也是一个民族、族群、地缘群体传统文化的产生与延续,其实是一种历史性选择和记忆的结果[12]。割漆匠这一传统生计群体每年会在夏至前举办开刀节,在漆树林边焚香、燃烛、奠酒,杀雄鸡沥血,取鸡血滴于漆刀或者擦拭漆刀,称为祭刀,寓意开割顺利。割漆匠叩头跪拜,向山神献祭礼,念祷词,祈求山神、树神保佑割漆匠平安。祭刀仪式是割漆匠与大山、漆树的对话与交流,也象征一年的割漆生活即将开始。仍在割漆的58岁的某割漆匠说:“每年在割漆前我把路清扫干净,把支架搭好,刨树皮,放水,在正式割漆时我还会带上香到各个山头去拜山神、土地神、树神等,祈求保佑我及家人平安、健康。”老割漆匠还会传授“不割黑心漆,护好生漆树;不钉钢钉,多绑木脚架;生漆不掺假,保证漆质量”的行为规范和价值理念。象征符号的社会影响在于它们的指示能力[13],使行动者与情境和谐融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割漆匠通过祭刀、祭拜山神等仪式向大山、土地、森林、树木表达尊重与感恩之心,仪式作为社会文化事实揭示了割漆匠深层次的价值和情感。
(三)割口形状是对生命关怀的实际行动
割漆匠割的每一刀都包含着责任和使命,漆刀划下的是生命的脉搏,出漆的同时要保证漆树生命有尊严地延续,每一个割口都是割漆匠与漆树共同的审美需要。走进漆树林,映入眼帘的是大小不一、形状相似的割口,看似简单,实则富有深意。虽然一眼望去都是V字形割口,走近细看其实并不完全相同,有的割口略有收紧、纹路较窄、倾斜度小,是胜利的标识,这样割口的创伤面小,易于愈合;有的割口略宽,割完16刀后看上去像一张笑脸,纹路较宽利于愈合。经验丰富的老割漆匠认为牛鼻子形割口不仅有利于割口愈合,还要让以牛王生漆为代表的平利生漆能够牛气恒通。割漆匠们认为漆树是通人心的树种,每一刀都是在为漆树文身或文眉,要让漆树的妆容更耐看、生命更长久,通过割口和纹路也能看出割漆匠的内心。漆树有其繁衍的方式,或靠根须自然生长,或落籽入土发芽后破土而出,生命轮回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割漆匠的漆刀,割口过多、过深、过长都会伤到漆树,割口恰如其分是表达对漆树生命的尊重。如今很多割漆匠已经老了,他们对生命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认为漆树也应该有尊严地享受每一刀,割口的愈合应与人的审美相协调,像关照人一样关怀漆树的生命。
四、结语
物质世界孕育精神世界,人所持有的社会心理、审美、价值观体现为一定的生存智慧或生态智慧。每一个生命都在经历自身与外界博弈的过程,除去自然环境变化、病虫害侵蚀,漆树生命周期一般是20—30年。对于健康的漆树而言,生命长短掌握在割漆匠的漆刀尖上、钉子眼里。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有道德的割漆匠是漆树的福音,也是生漆质量的把控者。割漆匠割漆解决了生计问题,合理把握漆刀延续了漆树生命,这种和谐共生模式是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历史延续,割漆匠在认知生命、尊重生命、超越生命的过程中赋予漆树以生命价值与意义。人与物之间的共生模式反映特有的文化传统与文化事实,割漆匠以其生计方式、技能技艺、智慧美德,进而体现出人(割漆匠)对物(漆树)的生命关怀,也为人类学视域下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