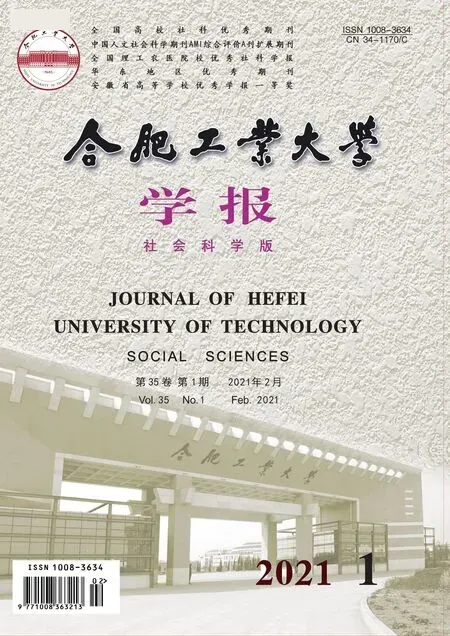环境伦理视野下的霍根小说评析
2021-11-30吴伟萍郑闽玉
吴伟萍,郑闽玉
(闽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一、引 言
琳达·霍根(Linda Hogan,1947-)来自美国印第安契卡索(Chicksaw)部落,是当代最重要的土著美国作家(Native American Writer)之一。迄今为止,霍根已经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包括《卑劣灵魂》(MeanSpirit, 1990)、《太阳风暴》(SolarStorms,1995)、《力》(Power, 1998)、《靠鲸生活的人》(PeopleoftheWhale,2008);七本诗集,包括 《呼唤自己归家》(CallingMyselfHome,1978)、《女儿,我爱你》(Daughters,ILoveYou,1981)、《望穿太阳》(SeeingThroughtheSun,1985)、《药之书》(TheBookofMedicines,1993)、《人的困境》(RoundingtheHumanCorners,2008)等;还有短篇小说、回忆录、散文集、戏剧、评论等在内的十几部作品。霍根已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American National Book Award)、美国图书批评家协会奖(American Book Critics Association Award)、科罗拉多图书奖(Colorado Book Award)、美国土著作家团终身成就奖(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of American Native Writers)等。此外,霍根在2007年入驻契卡索族名人堂(Chickasaw Nation Hall of Fame)。部落文化、社会问题、女性问题、环境问题等主题不断地出现在她的创作中。其中,霍根也从环境生态层面对土地和动物表达了深切的关注。
20世纪中期以来, 工业文明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与此同时,它也造成了自然资源的严重浪费和地球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如, 生物种群数量减少、地球升温、全球冰川融化、山林火灾等一系列生态危机,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恶化问题给人类敲响了警钟,已成为全球共识,环境伦理由此开始形成了。环境伦理是“环境在满足了人类的生存需要之后,人类如何去满足环境的存在要求或存在价值,而同时人类满足自身的较高层次的文明需要。”[1]环境伦理之父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1933-)认为,“自然生态系统是不以人类的主观偏好而存在的,它具有内在的运行规律和客观的内在价值。人类对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肩负一种道德责任和义务。”[2]103环境伦理与现实中的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直接相关,它源于世界范围内工业文明和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状态的改变。对此,人类在从事与自然有关的活动时,需要考虑到如何处理与周围的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遵循环境伦理尺度,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生态系统之间和谐共存,促进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二、人与土地
美国享有国际声望的科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作为生态学领域的先驱者,对与土地相关的伦理议题有着深入的观察与思考。在 《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1949)一书中,他首次提出“土地伦理”(Land Ethics)这一概念,被称为“土地伦理之父”。他认为,“需要一种全新的伦理,一种处理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在土地上生长的动物和植物之间的伦理观。伦理观演变的下一步,是把已有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扩展到生物圈中的生物共同体的非人类成员。”[3]23利奥波德阐述了土地伦理的核心思想,那就是,“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3]204土地伦理倡导曾经作为万物之主的人类,必须毫无条件地退回到与生物共同体中非人类成员一样平等的位置。在生物圈中,人类必须与非人类成员彼此竞争又彼此合作以获得共同生存和最大的可持续发展。土地伦理是环境伦理的视角之一,它是一种全新的、以土地为整体的伦理观,它的产生极大地推动了环境伦理的发展。人类是自然界中唯一具有道德主体意识的群体,必须怀有一种自然使命感和生态良知,为实现人与土地的和谐共生而担当责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土地伦理的提出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在 《大自然的权力: 环境伦理学史》(TheRightsofNature:AHistoryofEnvironmentalEthics,1989)一书中,美国思想史学者纳什(Roderich Frazier Nash,1939-)这样评述,“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发展为一种应该由伦理道德原则调节或制约的关系,这种观点的产生是当代自然思想史中最不寻常的发展之一。”[4]
印第安人自从踏足美洲大陆开始,他们就全身心地融入于大自然之中,在意识里,他们本能地属于大地。印第安人把大地比喻为自己的“母亲”,那是源于他们对土地最持久,也是永恒的敬畏之情。如,《黑麋鹿如是说》(BlackElkSpeaks,1932)一书中如此呈现:“我们来自大地,与自然为伴,终生都与一切鸟兽草木一起伏在大地的胸腔上,像婴儿似的吮吸着乳汁。”[5]424这是当时印第安先知黑麋鹿(Black Elk)(1863-1950)为美国诗人奈哈特(John G.Neihardt,1881-1973)所口述的、关于印第安人与土地和谐共处的自然图景。对印第安人来说,土地不仅是养育了他们,更多地是意味着土地本身所焕发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霍根写道,“印第安人把栖息的土地称为‘圣地’(spirit dwell),它是有生命的,拥有着巨大的力量。岩石、泥土、云母、矿物及大地上河水、空气、动植物等其他种类的东西都有一个纯粹的灵魂,而且都与治愈相关。”[6]从人类与自然关系来看,大地上的山丘、石头、湖泊、昆虫、飞鸟、草木,甚至最细小的雪花也不例外,皆与印第安人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息息相关。土地意识深植于每个人心中,使得他们时刻意识到自己在大自然中的位置以及与自然万物的内在联系。因此,印第安人把对土地的认同感也自然而然地融入自己部落的共同信仰中,这也很好地诠释了缘何印第安作家作品中更倾向于关注土地与家园等主题。对此,美国生态批评家布伊尔(Lawrence Buell)认为,“只有人们对一片土地获得综合的了解和对这片土地的忠诚, 这片土地上独特的自然生态景观才能永续存在。否则,就会被人类自身的活动所改变, 最终会导致毁灭。”[7]霍根小说中描写的土地上的自然景观蕴含着独特的文化内涵,此外,小说中的主人公也都与自己生活的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小说《力》中,奥秘希多(Omishto),这个名字意为“一个观察的人”(The One Who Watches),她生活在大沼泽地区(Taiga Land),处在白人文化和土著文化的夹缝中。她说:“阿玛的房子就坐落在这片云朵浮现的地方,被丛林包围着,看起来很破旧。但这片地方成为阿玛的至爱,也是我的至爱。”[8]7小说《靠鲸生活的人》讲述了海洋对阿斯卡族部落人世代生活的意义。“我们靠着海洋居住,海洋是伟大的,部落有关于海洋的歌,部落人对着海洋唱歌。”[9]9印第安人相信万物有灵论,与自然的关系更被视为是一种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关系。正因为如此,他们视土地不仅是养育人类的“母亲”,更是会给人类带来无穷生命力和无限希望之所在的源泉。小说《恶灵》中呈现了印第安人赖以生存的土地被任意支配滥用,变成了高尔夫球场、狩猎场以及废物堆放处的画面。霍根在小说中对自己部落的土地被滥用和受到破坏表达了深切的关注。印第安人遵循“仰天承顺,而不乱其常”的共生循环的、朴素的土地伦理观。这种朴素的土地伦理观是一种对自然道德应然性的阐发,那就是顺从天伦之理,继而敬畏自己脚下的土地,人类才会以不占有任何东西的方式拥有自然万物,共享来自大地的、整体而持久的恩赐。19世纪50年代,北美西南部苏夸米什(Suquamish)部落大酋长西雅图(Chief Seattle,1786-1866)在其著名的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Thislandissacred)的演说中如此表述,“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这片西雅图土地的每一部分都是神圣的。每一处沙滩,每一片耕地,每一座山脉,每一条河流,每一根闪闪发光的松针,每一只嗡嗡鸣叫的昆虫,还有那浓密丛林中的薄雾,蓝天上的白云,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和体验中,都是圣洁的。”[10]这是土地保护方面最为动人心弦的演说辞之一,它阐释了人与土地、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血肉关系,更是体现了印第安人朴素的土地伦理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土地塑造了美国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精神以及身份认同。
印第安人善待土地,但是他们与土地上非人类生命和谐共生的土地伦理智慧却无可避免地不断受到了外力的冲击。小说《太阳风暴》展现了人与土地相互依存的关系,土地因被围堤筑坝蚕食,“最终使得族人陷入土地伤痕带来的困境里”[11]181。土地上的生态景观被片段化了。“动物和鱼类的迁徙、采食、繁殖的地点路径都被改变了,鲟鱼也少见了,一些动物也消失了。众多的树林变成了成堆的木屑,曾经游泳的河流水量也少了。”[11]225当女主人公安琪拉回到了自己曾经的家园,见证了家族长辈们生活的地方已经物是人非,家园一片衰败。她痛心说道,“土地、水流、动物和树木,一切都被破坏。生活正在被夺走,离开了这些自然元素,没人能活得充满人性像个真正的人。”[11]324她团结当地的部落人共同参与到保护土地的正义行动中。小说 《恶灵》中呈现了印第安人土地被大肆开采,族人被恶梦困扰,他们无奈中求助豪斯(部落中的预言师、水源占卜者、治愈者和部落之火的看护者)的解释与治愈。豪斯告诉族人:“土地被开采扰动了自然环境,干扰了人的睡眠。”[12]39以上这些都是人类中心主义行为违背土地伦理的真实写照。霍根借助不同的小说表达了对土地遭受不可逆转的毁损以至荒败的痛心疾首以及对自然环境不断恶化趋势的极大的关注。地球历经40亿年的漫长演变,形成一个适宜人类生存的星球,是宇宙的奇迹。而人类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和意图改造自然,适应自身的需要,致使土地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损毁,人类共同的家园遭到了一步步的毁坏。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观表明,人类与动物、植物、水、土壤等处在一个共同体当中,彼此之间相互依存。人类绝不是土地的主宰者,与自然界中其他成员是共生的关系,共同分享土地的恩泽。对此,他呼吁,“人类要有一种生态良知,对土地保护应负天然的责任和义务。”[3]217
回望人类历史的长河,可以发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自然始终是被人类征服与改造的对象,其结果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断恶化, 人类生存的前景也蒙上了越来越多的阴影。生而平等的道理谁都能接受和认同,但如果强调人类应该转变为土地共同体(土壤、气候、水、生物)中平等的一员,恐怕就没多少人会接受和认同了。这主要是“人是万物之灵” “人是自然中心”观念使然。随着土地生态的恶化,人类开始逐渐意识到人与土地共同体之间具有生存论意义上的关联。“土地伦理改变了人类的角色,使人从土地共同体的征服者转变为共同体中的普通成员和公民。”[3]240利奥波德倡导的“土地伦理”呼吁从伦理道德上约束和限制土地破坏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们善待土地共同体、保护土地共同体的责任感。它是对人们外在的道德要求和促使人们自律和自省的一种精神力量,是引导人们以生态审美的视角去审视土地共同体的一次质的飞跃,为人们开启了对待土地的另一种方式。霍根在作品中呈现出的土地遭到破坏是需要全球人共同反思的问题。在实践层面上,真正有益的力量需要将来源于印第安人传统的自然价值观和土地伦理智慧真正融入现代文明的生活之中,引导人们为人类与土地和谐共生的未来提供一种思维模式,引领人们朝着与环境的健康发展步调一致的方向去实施科学而合理的生态行动,这一点尤为重要。
三、人与动物
北美大陆多样纷呈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印第安人古老而独特的文化、礼仪和宗教信仰。这是他们认识和表征外在世界的主要方式。印第安人认为动物是他们早期的祖先、守护者和精神导师。北美印第安人的部落中,广泛存在的图腾(totem)崇拜文化反映了他们崇拜动物和追溯祖先的思想,也是凝聚部落生命力和活力的方式。霍根小说《太阳风暴》讲述了海狸如何创造自然万物的故事。“海狸创造了人类,并与人类达成了一份神圣的契约。海狸为人类提供鸟、鱼和其他动物。相应地,人类应该按照契约管理好这个自然界。”[11]231在自然界混沌蒙昧阶段,印第安人把对大自然的崇拜真正融入到生活中,怀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将动物与人类等同视之,捕猎动物仅止于满足生存需要的数量。小说《靠鲸生活的人》中,描写的是美国西北海岸的印第安部落阿斯卡族人的生活状况。这里的人被称作“靠鲸生活的人”,是一个靠捕鲸生活的族群,他们的生活与捕鲸紧密相连。因此,“他们崇拜鲸,一生都与鲸鱼相伴。鲸鱼是他们的生命的源泉和生活的希望。”[9]54他们相信鲸鱼是自己的祖先,对他们来说,融入海洋并与海洋和谐相处是他们的信仰,也是他们保存真理和传统的独特方式。在《土著科学: 相互依存的自然律法》(NativeScience:NaturalLawsofInterdependence,2000)一书中,卡杰特(Gregory Cajete)认为,“印第安人凭着一种动态和兼容的态度去认识动物的自然世界。因而,人类、动物与灵性现实之间的区分并不大。”[13]印第安人坚信山川有情、动物有灵,并与人类形成在灵性上牢不可破的关联。动物之于他们,不是征服的对象,而是最亲密的朋友。因而,他们捕杀动物的时候会愧疚。然而,人类自诩为大自然的主宰,为了满足自己的时尚、娱乐、口腹之欲等边际利益,竟然使得一个物种因人类的自私与贪婪而灭绝。人们总是先捕杀,再反思,反思之后又是捕杀,从来不愿意去考虑捕杀野生动物会带来怎样的后果,甚至也不愿意去考虑人类自身生存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非人类种群多样性的消失以及生态系统稳定持久性被破坏背后呈现出来的是人类对待自然的恶的本质。
生态问题是因人而引起的,有其人性根源,它不单单是因为科技发展或科学管理滞后而导致的问题,更是一个伦理问题、哲学问题和信仰问题。环境伦理涉及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它包含了两个决定性概念,一是伦理行为概念,为了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它必须扩大到对生命和自然界本身的关心;二是道德权利概念,它必须赋予生命和自然界按照生态规律永续存在的权利。几千年以来,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一直主导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这种价值观直接改变人与自然的原始关系,在改善人类生活环境和提升人类生活质量方面曾经发挥过决定性作用。然而,这种价值观逐渐走向极端,充斥着人是万物的尺度和人类利益至上的论调。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征服和开发自然一度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自然资源被严重浪费,自然环境受到严重的破坏。此外,还给动物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各类动物制品极大地满足着人类的物质需要,如,北美早期发展史上著名的毛皮贸易,极大地满足了欧洲国家追求时尚的需求,但却导致北美大陆的海狸、野牛等动物濒临灭绝。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伦理观认为,人类是大自然的价值主体,非人类动物只是为人类而存在的,只有工具价值,其核心观念是“除了人类,其他动物是不具有道德权利的”[10]103。人类对动物道德权利的界定割裂了自我与动物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带有强烈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不但没有被质疑,而且伴随着人类迈入工业文明时代,并一直延续至今。在《太阳风暴》中,充满征服欲的人们总是想要去操纵那兼具野性与力量的熊。“如果熊反抗,它便遭人憎恨。但如果它不反抗,人们又会因为它的软弱而鄙视它。”[11]46当人们想要征服和伤害熊时,是否曾想过“熊是古老森林中的北极光,属于人类某些未知的神秘”[11]54。印第安人把熊看作是充满灵性智慧和人性关怀的生命体,是他们一生中的灵性导师,直觉、身体疗愈、意识、强大、自由、梦想、死亡和重生都是熊身上所能折射出来精神。人们试图征服熊的盲目与狂妄的意识背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伦理观的根深蒂固。野生动物的灭绝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因为野生动物的灭绝大部分是人类行为造成的。对此,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已提出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理念,呼吁人类正确对待动物,他们成了动物保护的支持者和宣扬者。他们看待人类与动物关系的立场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动物道德地位的肯定以及动物伦理思想的产生。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是最早提出将动物纳入人类的道德共同体中的第一人。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IntroductiontoPrinciplesofMoralsandLegislation,1789)一书中,边沁谴责了人类违反了大自然的规律,对自然界实施了暴虐统治。他认为,“可能有一天, 其余动物生灵终会获得除非暴君使然就决不可能不给它们的那些权利。”[15]由进化论所激发起的知识剧变也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动物权利意识。美国早期环保运动的领袖缪尔(John Muir,1838-1914)认为,“进化的知识足以使文明人转变对非人类物种的态度,建立新的伦理学, 修正人类对待一切动物的行为已成为必然。”[16]20世纪中期,人类在见证了工业文明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被其所带来的生态危机所困扰,正是在这个历史阶段,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开始萌芽进而逐渐发展。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在1923年出版的《伦理与文明》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敬畏生命的伦理原则。他对伦理学重新加以界定,其核心是人类对世界及其遇到的所有生命的态度问题。他认为,生命是神圣的,人类应该将道德伦理的适用范围和道德关怀的对象延伸至所有的动物和植物身上。“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达到其最高度的发展,是善的本质;毁灭生命,损害生命,阻碍生命的发展,是恶的本质。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它才是伦理的。”[17]102史怀哲敬畏生命伦理原则的出发点是由生命的神圣性所唤起的对于生产的敬畏之心,开创了动物伦理的先河。随后,美国著名伦理学家,世界动物保护运动的倡导者辛格(Peter Singer,1946-)一直与环境组织合作,致力于保护环境和改善动物生存环境。辛格关于动物解放的观点集中体现在《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1975)一书中,他把“物种歧视”(speciesism)与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联系起来,提出反对“物种歧视”的伦理主张。他这样认为,“平等作为一个道德理念要求我们必须同样给予动物的利益同等分量的重视”[18]。辛格在伦理学的高度上对动物的道德地位进行了论证,提出要从人类思想根源深处放弃对动物的虐待,消除“物种歧视”,由此揭开了善待动物的新篇章,掀起了现代西方动物解放运动的高潮。
专事于研究西方文化的美国学者玛拉穆德(Randy Malamud)阐释了西方文化对诗歌中动物形象建构的影响。在《诗化动物与动物精神》(PoeticAnimalsandAnimalSouls,2003)一书中,他认为,“对西方文化中人与动物对立的关系来说,印第安部落文化中的动物精神是对其的一种拓展式的修正”[19]。印第安文化中所反映的动物精神不仅体现了人与动物之间的一种生态审美伦理关系,而且还赋予了动物在自然中的主体性地位。小说《靠鲸生活的人》真实展现了一幅阿斯卡族人从传统捕鲸仪式中获取智慧和力量的过程。他们把鲸鱼视为部落的神灵,捕鲸之前,要斋戒和祈祷,族人首先要被称为“灵魂守护者”(spirit-keeper)的章鱼精灵献上最好的供品,之后,章鱼精灵被放回海洋之中并随之消失。这就意味着“章鱼精灵愿意帮助他们,赐给他们丰富的鱼类、捕鲸收入等”[9]30。印第安人怀着梦想,通过这样神秘的捕鲸仪式寄托了对动物的恩赐得以延续的一种企盼。他们深知,对动物过度的渔猎只会导致动物的消失,因而,他们珍视周遭的一切动物。在《太阳风暴》中,露丝写信告诉朋友托马斯,“现在是鲑鱼成长繁殖的季节,它们是那么美。我一只都不想杀,我只用它们来讨个温饱。”[11]42为了生存的基本需求,他们准许恭敬地捕杀和食用动物,不索求过度,始终如一地恪守向自然获取但不贪求的猎人信条。四季的轮替规约着人生的步伐,生命遵循天地的循环而运行,对于如何有效地维持自然生态的平衡印第安人有着自己的一番理解。相比之下,美国评论家哈格洛夫(Eugene C.Hargrove)这样评价,“西方文明不但没有很好地把第安部落的传统渔猎文化保存下来,反而发展起一种为娱乐而非为食物捕杀野生动物的传统。在这一传统庇护下,猎人大可以没有任何罪恶感地从捕杀野生动物的狩猎中获取快乐。”[20]西方文明与印第安文明在对待动物的态度上显然是截然相反的。小说《恶灵》 中,贝拉(Belle)遇到从东部城市而来的装满已死去的一卡车赤腹鹰。在她看来,这些赤腹鹰“就像一群弱小的人,被猎杀后堆放在卡车里将要送走”[12]109。猎人准备卖掉这些鹰,商贩再把这些鹰送往城市的野生动物标本店出售,从中谋取暴利。贝拉竭尽全力阻止猎人肆意捕杀野生动物的行为。猎人只是辩解道,“那只是一群鸟而已”[12]109。贝拉因为暴力阻止而伤及了猎人,结果被警察带走,送进了监狱,成为扰乱和平的暴民。小说也记述了一位探险家在森林和大草原中大规模捕杀野生动物的劣迹,他在探险游记中写道,“这儿猎物十分丰盛,是个捕猎的好去处。”[12]267以此鼓动和邀请更多的人来到这些地方捕猎野生动物。小说《太阳风暴》中,艾格尼丝(Agnes)告诉安琪,“这个地方仅存的一些离群的狼和狐狸也被毒死了”[11]24。小说《力》中,奥秘希多(Omishito)是一个16岁女孩,她从父辈的教诲中得知美洲豹是自己部落的自然与氏族之神,部落人和美洲豹有着与生俱来的血亲关系。然而,她目前只真正见过一次美洲豹。她的母亲痛心说到,“在上一只美洲豹被汽车撞了之后,它们都从这里离开了,剩下的都是些体弱多病的。”[17]3奥秘希多生活的地方,“附近有清泉,西班牙人曾经把它称为青春之泉。但是,现在这里的泉水与整片土地一同被污染了,那涓涓细流之水你连一小杯都不敢去喝。”[8]23“美洲豹只剩下这么少,跟我们泰珈族人一样少。剩下有多少,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个数字,但只知道它们是濒危的。”[8]58美洲豹数量急剧减少显然与人类急于求成、破坏生态环境以及对待动物的态度息息相关。霍根小说中所展示的印第安人善待动物与敬畏生命的伦理体现出他的对于一切生灵的深切的人文主义关怀,同时也在警示世人,只有负起生态伦理责任,转变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认同自然万物的价值,才有希望挽救野生动物濒临灭绝的状态。
毁灭生命, 损害生命, 阻碍生命发展,就是恶的行为。对于动物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取决于人类社会当时所持有的道德观,而非事实上动物之间是否有着本质的不同。动物界中老虎捕食猪、鹿、羚羊、水牛等并不考虑它们是否痛苦,但这个事实并不能作为支持人类也可以无须考虑动物的痛苦而对它们进行肆意捕杀。理由是,道德准则毕竟只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在动物世界中并不存在。人类在生命共同体中应负起的生态伦理责任的最根本原则是不让生命痛苦,不恶意破坏、干扰和毁灭生命体的存在。人类作为道德关怀的主体,必须平等地考虑所有生命个体的道德利益。因此,每一个人在面临伤害到生命的时刻,都必须判断一下,这是否是基于生活的必需而不可避免。生命迹象蓬勃旺盛源于生物的多样性,而生物的单一性也是导致生命难以存在或者兴旺的直接原因。所以,“人类不管以何种方式导致某些种群的灭绝,都是阻断了生命长河的奔流,因为它杀死的不是动物个体,而是整个生命形式。”[2]386生物圈是一个万物结合在一起的生命共同体网络。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卡普拉(Fritjof Capra,1939-)关于生命的网络关系也提出了新的见解。在《生命之网》(TheWebofLife,1996)一书中,他认为:“生命的本质就是一个网络。所有的生命形式,无论是动物、植物、微生物,也无论是生命个体、物种、群落,都是由网络组成的。人类共同体的健康生存,也必须依赖于全球生态系统这个最大的生命网络的可持续性。”[21]某种意义上,敬畏生命是一个关乎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终极问题,这需要人们在实际生活中践行,而并非只是纯理论的陈述。
四、结 语
霍根作品持续关注自然生态恶化给土地和动物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从人类中心主义和印第安自然价值观之间的矛盾视角去思考人类与土地、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这种思考并非是一味提倡印第安部落本土的认知体系,更多地是从生态意义的维度去反思现代人所面临的环境危机的根源。人类作为自然界唯一的道德主体,不仅应该从合乎道德的角度考虑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而且更要从合乎道德的角度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从而唤醒人们去秉承一种环境伦理的观念以善待土地与动物。这不仅对自然环境的改善而且对地球上一切人类生命和非人类生命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霍根为世人传递了印第安部落中深植于族人心中的人与土地、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意识以及人与自然万物相互连结的意识,这是霍根作品中所蕴含的环境伦理智慧。这种智慧汇集了一种饱含历史文化内涵的批评、一种富有现实批判精神的批评以及一种拥有道德和责任的批评。霍根无疑是一位具有坚定的环境伦理批判意识的作家,其作品充分展现了弘扬环境伦理的创作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