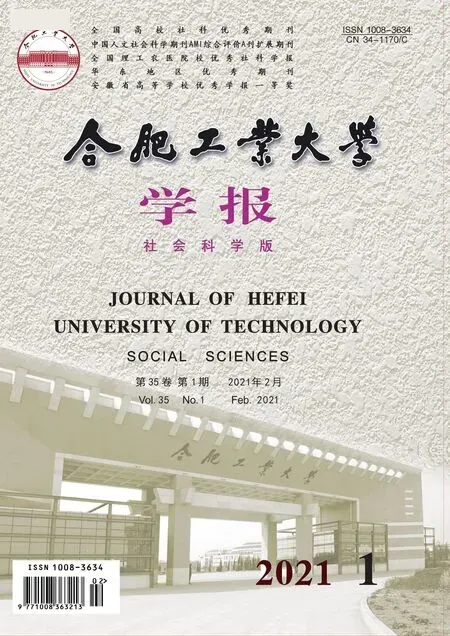“成熟”之旅:《天黑前的夏天》中的女性与年龄主义话语
2021-11-30吕佩爱李子阳
吕佩爱,李子阳
(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092)
一、引 言
随着20世纪末期西方国家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现象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与文化冲击在文学界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 1919-2013)作为一名极具社会情怀的作家,创作了很多以中老年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她用细腻辛辣的笔触描摹出女性在面临年龄危机时对自我、婚姻以及家庭的困惑与洞见,表达出对女性社会生存体验的高度关注。《天黑前的夏天》(TheSummerBeforetheDark, 1973)是莱辛极具影响力的代表作之一,并且先于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者掀起的“年龄认同”思潮,对女性与年龄歧视的抗争进行追寻与探讨。小说对一个中年女人的心灵进行了深度探索。女主人公凯特早已习惯了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然而当丈夫和儿女们都忙着计划各自的暑假行程时,她怅惘若失,顿感悲凉。于是,在疑惑与彷徨中,她走出家门,踏上了属于自己的旅途。有的学者把这部小说看作“一个当代聪明的——如果是困惑的——妇女对聪明的女人们的指南”[1],也有学者对小说中的成长主题进行探究,认为凯特通过回忆和夏天的旅程实现了自我救助和精神上的重生[2]。不过,诸多研究忽略了作品中凯特作为女性对其自身老龄化过程的体验和抗争,故而缺少对性别和年龄话语体系的关注。
性别与年龄是人类普遍的生理特性,亦是个体固有身份的重要元素。它们既是自我身份建构的核心,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聚焦于文学作品中的老年角色与主题,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芭芭拉·弗雷·韦克斯曼(Barbara Frey Waxman)对20世纪70年代这一特定的文类重新定义,她在德语“bildungsroman”(青少年成长小说)的基础上,杜撰出“reifungsroman”一词,为老龄化主题小说的解读提供新的研究平台[3]2,我国学者林斌教授将其译为“成熟小说”(1)林斌教授于2013年首次提及这一文类时,使用了“中老年成长小说”这一译法,以取得与“青少年成长小说”对仗、类比的效果。在2018年时,林斌教授对此文类再次深入探讨,运用了“成熟小说”这一译法。参见林斌《“恐老症”与都市生活的隐形空间:一个好邻居日记中的越界之旅探析》,载《外国文学》2013年第5期,第30页;林斌《老龄化的文学表征与身份政治——“成熟小说”之源流探析》,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8年第2期,第30页。。“成熟小说”的创作对象主要为中老年女性,这种创作形式颠覆了成长小说中的线性叙事结构和传统的叙事模式,采取辗转迂回或碎片化的叙事结构以及对梦境的描述等叙事技巧,通过内心独白、回忆闪现、自由联想等方式实现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融合,打破了青少年与老年人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状态,与“衰老”的概念对抗,颠覆男权中心的社会权力机制,以期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的“无年龄界限的乌托邦”的理想[4],呼吁共同人性的回归。
《天黑前的夏天》被韦克斯曼誉为“成熟小说”的文本典范。莱辛在创作中通过记忆与现实穿插的叙事模式,运用大量动物意象等象征的艺术表现手法,描绘出凯特面对中年危机时的心路历程,以及寻求自我认知与新的自身发展时的坎坷旅程。本文试图从“成熟小说”的角度,解读凯特对传统中年女性角色的解构以及对旅途之后归家的新的女性角色的建构。女性在面临中年危机时,需要承认“年龄主义”不是由生理特性决定,而是年龄身份的社会、文化建构特质,本质上为一种社会建构,但是“身份会发生变更,而‘自我’作为多重身份的叠加与重组,是通过身份交替得以体现的”[5],作者莱辛利用凯特在夏天时从脱离家庭到回归家庭的人生经历对既定的老龄化社会的“符号话语”进行挑战,在跳跃、反复、分裂式的语言表述中传达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中年女性对爱与理解的渴望,以及对既定的个人社会文化身份的抗争。
二、心向远游——逃离“金色池塘”(2)《金色池塘》是奥斯卡经典影片,于1982年上映。该片讲述了老年人与年轻人两代人之间的感情危机与化解,呈现了老年人面对衰老与死亡时焦虑的心理状态。“金色池塘”一词在美国文化中现已成为宁静而乏味的老年生活的代名词。
“中老年成熟小说”虽然在主题展现和叙事模式上与“青少年成长小说”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所谓“成熟”与“成长”的概念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定文化内涵。林斌教授认为,对于青少年而言,“成长”意味着人生新阶段的迈入,通过人际交往不断形成新的自我认知,熟悉成人社会的行为道德准则,进而取得新的、明确的社会身份,是一个建构身份的过程。然而,对于中老年而言,“成熟”虽然意味着对自身同一认知和身份界定的自然延续,但是不同的是它要求解构与建构同步进行[3]32。在小说《天黑前的夏天》中,凯特被塑造成一个被社会性别角色深刻内化的中年妇女形象,她意识到自己的社会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降低。对于逐渐走向老年的凯特来说,中年时期是一个过渡期,她的生命状态正悄然发生改变。凯特的“成熟”被界定为认识并超越年轻女性与年老女性之间的传统界限,在适应与之前截然不同的生命状态的过程中实现全新的自我认知。在这个过程中,她需要不同的人生体验来克服“恐老症”,以获得消解这一界限的策略。
凯特在内心独白中不断介入第三人称叙事,以警示自己即将在几个月内接受衰老的事实。她的思绪漂泊不定,不时地在当下的“五月份”和“去年”“今年”当中辗转往复,过去的记忆与现实的情景展现了她的空巢焦虑与无所依附的心理状态。莱辛突破了传统的直线型叙述方式,通过内心独白的并置与心理时间的交叉叙述,有力地展现出凯特在不同时期内的自我定位的变化,传达了凯特对衰老的焦虑与对未来无所适从的痛苦与迷茫。自结婚以来,凯特一直以家庭为中心,同时她也是家庭的中心,孩子与丈夫对她的需求给了她很大的满足感。然而,她在与小儿子争吵时,小儿子指责她的过度关心令人窒息,这令凯特愤怒而震惊。她幡然醒悟,面对即将成年的孩子,自己的过度母爱会使人产生抵触情绪。她试图摆脱母职对她的影响,而丈夫出差与孩子夏令营的时间成为凯特外出旅行的契机,她出租了自己的房子,从私人空间进入公共空间,开启了新身份的尝试与体验。她的夏日旅行带给了她三个新身份,从职业女性到婚外恋人再到租客,在不断老去的岁月里她超越了特定的年龄、性别角色限制,获得了不同以往的人生体验。
凯特离开家庭后的第一个身份是职业女性。她在国际食品组织上班,感受到了与之前不同的生活变化:作为一名翻译,她比自己当医生的丈夫迈克尔薪水还要高;她有自己的工作圈,生活不再以家庭为中心;她用赚来的薪水重新打扮了自己,买了新衣服,做了新发型,依旧具有女人的魅力;家人对她的工作十分认可,并且在她离开家庭之后,一切都在正常运转着。然而,凯特逐渐发现,在自己扮演职业女性的角色时,“她摇身一变又开始重操旧业:成了保姆,或护士……还有母亲”[6]27,她在不知不觉中承担起了帮助公司职员和参会者解决一些琐碎问题的职责。由于协调能力突出,凯特得到了世界各国代表的赞赏,查理也因此提升凯特来做大会的组织工作。其实,凯特在家庭和工作中扮演的角色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她的持家才能在工作岗位上体现为较强的协调能力,在开展组织工作时游刃有余,仿佛一位隐身的母亲,凯特在工作中逐渐变成“润滑剂”和“调解员”[6]214。凯特在工作中逐渐发觉,自己身为女性,在处理人际关系以及琐碎的办公事务时能够起到协调作用,除此之外,她能够决定的事情微乎其微。凯特从家庭的私人空间迈入工作时的公共空间,虽然实现了经济独立,却并未触及女性解放的实质与女性地位的根本改变。
凯特在工作之后开始了旅行,她的第二个身份是婚外恋情人。她在国际食品组织的工作即将结束时结识了美国青年杰弗里,对丈夫出轨的报复心理使得凯特想实现精神与身体的双重解放与狂欢,她与杰弗里相约去西班牙旅行。她牢记自己的新身份是情人,然而这并不是一段浪漫的旅行,凯特依然没有摆脱母职身份的禁锢。在相对保守的西班牙,凯特出挑的打扮十分显眼,她与杰弗里的年龄差距引来了路人的猜忌,他们并不像是处于恋爱关系的情侣,他们的通奸行为让周围的人们嗤之以鼻。两人之间的相处模式也令凯特尴尬为难,凯特婚后贤妻良母的形象深入内心,照顾孩子与关心丈夫已经成了凯特的习惯,这样的亲密相处模式自然延续到了她与杰弗里的关系中。她做不到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诉求,要求杰弗里与自己做爱,只能温柔地凝视他。出乎意料的是,杰弗里几乎一直处于生病的状态,凯特自然流露出的关怀与照料让她仿佛回到了之前在家中的角色。整个旅途呈现出一种混沌的病态:昏睡、炎热与颠簸,呕吐与大把的药片,充满了疲惫与挫折,一切都与凯特的初衷背道而驰。她希望自己能够暂时逃避婚姻问题却无法不在意社会道德的谴责,她刻意避免充当母亲的角色却又迫不得已。情人的身份并没有使凯特脱离母职,反而充满了焦虑与煎熬。
凯特的最后一个身份是租客。她在结束与情人的旅行之后到莫琳的公寓与莫琳同住,成了一名租客。渐渐地,凯特的身体逐渐恢复健康,她也逐渐摆脱了抑郁的心境,等待暑假结束之后回归家庭。但是,儿子蒂姆来信说要提前回家,凯特的“头脑飞快运转起来”[6]200,她要给不同的人发电报,和房客恩德斯太太沟通,打电话给一家送日用品的商店,安排通用清洁公司打扫卫生……她的这一系列举动让同住的年轻女孩莫琳萌生了对婚姻的恐惧,拒绝了男友菲利普的求婚,她喊道:“叫我做什么都行,我宁可一个人过一辈子,也不愿变成那个样子。”[6]201凯特幡然醒悟,她又重新回到了自己希望脱离的过去之中,这也是年轻的莫琳即将迈入并且抗拒的生活。凯特在过去的几个月走了很长的路,但是她的旅程依然没有结束,在“天黑”之前她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想清楚,于是她推迟了回家的安排。凯特面对失恋的莫琳,并没有充当一位善解人意的安慰者,而是对她讲述了自己的婚姻与家庭生活、人际交往以及从未对别人提起的“海豹之梦”。凯特与莫琳之间的年龄差距并没有使她们成为类似于“母女”的相处模式,反而发展成了一种近似于“闺蜜”的关系。在凯特与莫琳的交谈中,困扰凯特已久的“海豹之梦”也有了结局,她在与莫琳进行对期待的婚姻生活的换位思考时,意识到了母职的社会性别规范。她自从成为一名母亲后,就一直在学习如何成为一位母亲,从而忘掉了自己的追求,放弃了本真的自我。凯特与莫琳提到,自己最快乐的时光是在儿时,当她回忆童年时光时,却注意到了在大街上,一个年轻的妈妈带着两个孩子,手推车里的孩子泪痕满面,而落后的男孩子显然是被母亲打过,脸上的掌印清晰可见,表情愤怒。落后的男孩厌倦了母亲的指责与威胁,挣脱了母亲的手,摔在地上并哭喊起来,手推车里的小孩子也跟着放声大哭,随即母亲崩溃,也开始哭泣。这一幕令凯特幡然醒悟,意识到一味地沉浸于母职只会让女性丢失自己的生活,变得可悲。此时此刻,凯特不想再遵循文化养成的社会规范,她不再惧怕衰老,不再惧怕重新回归家庭,当莫琳在婚姻面前徘徊不定时,她拿起行李箱走出了莫琳的公寓。
莱辛通过凯特的三种新身份,刻画出中年女性在面对逐渐不被需要的母职时所产生的焦虑与茫然,同时也清晰地揭示了母亲是女性被迫接受的角色,母职也是女性难以摆脱的心理习惯。社会文化规范限制了凯特在担任新角色时的自我认同,而当年老的女性将自身解放投入到公共空间并承担工作职位,抑或寄托在浪漫爱情中,都无法实现新的自我定位,只能是“润滑剂、调解员及全能的家庭安慰者”[6]214。只有意识到年龄与性别的社会建构性,打破女性必须拥有母职的传统观念,才能在走向衰老的岁月里远离“金色池塘”。凯特在成为“租客”的第三个身份时,在年轻女性的经历中反思并意识到了母职是令她焦虑和恐惧衰老的根源之一。母职虽然是人类繁衍与社会价值传承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但女性如果一直沉浸于此,就会在遭遇年龄歧视时面临精神危机。随着家庭与社会对年长女性母职的需求降低,女性的自我意识是对年老女性衰弱、无所事事的刻板印象的削弱与挑战,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工作、生活中,女性在奉献和扮演不同角色的过程中都应牢记自身的存在。凯特的角色突破是克服“恐老症”的开始,她最终离开莫琳的公寓暗示她今后会以积极活跃的新角色回归家庭,从而消解中年与老年之间的界限。
三、分裂与重塑——消解“美丽神话”
当凯特在“漫长而痛苦的时光”[6]5里经历了一段逐渐衰老的过程,她不仅仅意识到母职对自己女性身份的禁锢,还敏锐地察觉到了自己衰老的外表和她日益降低的社会价值之间的联系,当女性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失去年轻的容貌时,就会面临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危险。女性气质是女性身份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美国著名女性主义者奥米·伍尔夫曾在专著中深入探究了社会对于女性美貌的现代观感和理解。她认为“美丽”的概念是男权社会压迫女性所遗留下来的最顽固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父权制与异性恋霸权使女性必须维持性吸引力和符合男性审美标准的美貌。“美貌的神话”以一个女性无法企及的美丽模版来评判女性,使得女性陷入一种自我悔恨当中。伍尔夫认为“这种文化隔离了女性与自己的身体和性欲,而女性对自己的外在形象几乎丧失了选择权”[7]。莱辛在塑造凯特日渐衰老的人物形象时,揭示了女性渴望“被凝视”的特质,反映了这种社会理想化规范的审美范例对女性的束缚。然而,凯特在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夏日旅行后,解构了这种对理想化自我的期待,并且逐一打破了虚幻的镜像。镜像象征着女性建立在他人与男性评价之上的虚幻自我与真实的主体自我之间的分裂,呈现为一种被扭曲和异化的形象,小说通过三种不同的镜像来描述凯特从与真实自我的分裂到重塑自我的过程。
第一种是有像之镜。莱辛通过镜子来反映女性的自我评价,“这种认同则是以镜像为依托,镜像定义或者塑造了‘我’的身份”[8]。当凯特成为一名职业女性时,她站在商场的镜子前打量自己:“这女子的身材还和做姑娘时一样,胖瘦不过一两斤;一头漂亮的深红色头发——当然是染过的颜色,因为头发白得很快。”[6]32起初她对自己的形象尤为满意,通过化妆、染发等手段可以保持自己青春常驻,还和年轻女子一样富有魅力。从少女时代开始,凯特就把自己的外在形象编码为被男性凝视的对象,她好似一张被男性绘制而成的美丽图像,而并非内在与外在一并呈现的女孩。她把自身的理想化身份建立在满足男人的审美、欲望与快乐的身体之美的形象之上。在青春期时,凯特是“娇滴滴的一个小姑娘,像朵山茶花,雪白的肌肤,浓密的深红色头发,一袭白色绣花亚麻裙子,粉颈香肩半裸,坐在游廊的摇椅里”[6]13。她以性感的玉足为傲,并将自己有意识地定位为在场的男性无法将目光和幻想远离的性对象。在国际食品组织工作时,凯特注意到,在休息厅里,每当她坐姿慵懒而不美观,男人们就好像将她视为空气而看不见她。但是当她穿着优雅漂亮,性感地坐着,男人们就都会对她体现出极大的兴趣,凑上前来与她搭讪、聊天,尽管他们会略微失望,凯特并不像他们想象中的一样年轻。在小说的最后一章,凯特穿着肥大宽松的夹克经过工地时,并没有工人注意到她。而当她脱下夹克,展示出里面修身的黑裙,并整理好自己的发型,用一条方巾将头发扎起,展示自己的身段与富有女人味儿的特征时,她再次经过工地,不出所料地得到了工人们的口哨声,引起了他们强烈的注意。凯特将自己的身体形象视为美丽源泉,反映了父权社会通过对审美角度的干涉与掌控,建构起符合男性审美的女性角色,以实现对妇女权力的控制。然而,在挫败的旅行过后,大病初愈的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倦容满面,头发蓬乱且长出了白发,她认为自己是一个无法吸引男人目光的女人,任何服饰与妆容都不能给予她自信。这一幕与之前凯特在商场的镜子里打量的自己形成了鲜明对比,她对自我外貌的高度关注反映了容貌在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女性自我,而女性的内在价值也受到了其服饰风格的影响。尽管凯特现有的服饰与妆容与她的喜好不符,她也不会遵从自己的内心,因为她的穿衣打扮与娱乐交友都符合一位中产阶级太太的标准,她的存在是以社会和家庭的需要为前提的。莱辛通过有像之镜揭示了女性的性价值决定了其社会价值,而中年女性则因容貌逐渐衰老而面临着社会价值逐渐降低的残酷境遇。
第二种是戏剧之镜。当凯特通过他人的目光来确定自身的主体性时,莱辛通过安排一场戏剧来实现凯特的自我觉察,而凯特的自我觉察是在疯癫的状态下实现的。这场戏是屠格涅夫的《村居一月》。凯特刚一入剧场就显得十分怪诞:“一个女子引人注目地坐在剧院前排,引来不少观众对她行注目礼。有的人一半时间在看她,一半时间在看戏。她显得格格不入,怪模怪样,像虚构的人物一样,穿着粉色袋子似的裙子,腰间随便系了一条黄色丝巾,头发乱蓬蓬的,有红有白,憔悴的脸蜡黄蜡黄,瘦骨嶙峋,两眼冒着愤怒的火光,嘴里嘟嘟囔囔:‘噢,垃圾!有俄国味儿,胡说吧?哼,全都是扯淡!她一面嘀咕一面在位子上扭来扭去。”[6]149生病后的凯特在看戏时显得异常怪异,她在看戏过程中不断喧哗、与演员隔空对话,在座位上摇摆晃动,与周围的氛围格格不入,其他人都认为她疯了。实际上,凯特通过如此疯癫的状态实现了自我突破,她同时扮演着观众与演员两个角色。作为观众,凯特不再是“被凝视”的对象,拒绝继续处于客体的位置;而作为演员,她意识到,演员会扮演很多角色而永远不拘泥于其中一种,她们总是变换着服饰和发型,用不同的方式说话走路,然而自己结婚之后,多年以来只扮演着一种角色——迈克尔·布朗的太太,而布朗太太的角色让她多年以来忽略了自我。戏剧的女主人公娜塔莉娅的经历宛如一面镜子,使凯特认清了虚假的自我,即符合社会规范的自我。“多年来,凯特因为在众多不同的镜子面前,花了很多时间”[6]156,社会文化对女性气质的刻板印象导致了凯特在自我愿望和社会规范之间的分裂。这场戏成了逐渐年老的凯特生命历程中的转折,她第一次成了主角,撕下了多年来身为客体的虚假面具。重温这场戏,凯特对女主人公娜塔莉娅的理解有了一个飞跃,娜塔莉娅使她看清了自己的处境。四年前她曾经与自己的丈夫迈克尔一同观看,当时的她认同娜塔莉娅,因为那是凯特的理想自我,凯特认为娜塔莉娅的庭院就像自己的家一样,也接受戏剧中的情感变迁。但此时此刻,凯特在经历了中年危机和婚姻危机的双重精神压力下再次观看此剧,她的态度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仿佛看到了愚蠢的自己,对于衰老的焦虑使她企图抓住青春不放,一直生活在虚假与自欺中,用符合社会规范的自我长期掩盖内心的真实需求及欲望,最终造成身心分离,始终活在幻想中。这场戏在打破凯特幻想的同时,也是她实现自我觉察的开端。莱辛大量运用了“焦虑”“背叛”与“痛苦”等词语表达了凯特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怀疑与批判,反省了女性气质对自己的消耗与侵蚀,意识到了女性在社会文化中的客体性,从而丢失了自己的主体存在。
小说的最后一种镜像关系是镜像人物。心理学家罗伯特·罗杰斯(Robert Rogers)曾经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文学作品中的镜像人物进行了研究,他认为镜像人物是人物心理矛盾冲突的投射,能够帮助作者塑造难以直接赋予作品中某一人物的潜在性格。在文学作品中,镜像人物互为对方的第二个自我。凯特与玛丽即是小说中的一对镜像人物,玛丽一直存在于凯特的意识里,不时地影响凯特的行动与决策。玛丽并没有参与凯特的夏日之旅,在现实当中是缺席的,但是却在叙事中无处不在,仿佛跟随着凯特的影子,是凯特潜在的欲望。她们被塑造成完全不同类型的两种女人,凯特是典型的“家庭天使”,而玛丽对待婚姻则保持着开放性的态度,也不会刻意隐瞒自己结婚以来的风流逸事。玛丽与社会教化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否定社会道德规范的种种约束,她不认为自己有义务为丈夫恪守忠贞,不看电视和戏剧,却沉迷于动物、冒险和侦探小说。凯特复杂的心理活动通过玛丽率真的人格以一种合理化的形式充分展现,当凯特遭受小儿子蒂姆的指责时,她想到玛丽从来都是由孩子照顾;当她决定与情人杰弗里去西班牙旅行时,她想到玛丽多年来与很多情人发生关系。玛丽一直存在于凯特的潜意识当中,暗示凯特受到了来自本我的挑战。罗杰斯认为,人格分裂反映了强烈的内心冲突,人们往往期待作家用镜像人物来描写彼此极度敌对的状况[9]。表面上,凯特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否定玛丽的种种作为,实际上,玛丽则代表了凯特内心的真实欲望。玛丽否定了传统的爱情观念,否定了家庭观与母职在女性身份中的重要地位。莱辛通过镜像人物的塑造彰显了凯特分裂的心理状态,突出了女性被压抑的欲望,同时也通过玛丽微妙地提供了女性在面临社会客体地位时的自救方法与出路。
凯特通过有像之镜反思,自己只是被男性“凝视”的对象,是社会审美塑造出的他者;她通过戏剧之镜,实现了自我觉察,撕下了多年来身为客体的面具;玛丽犹如一面内心之镜,折射出凯特的真实欲望与另外一种生活和出路。凯特的分裂是女性应对年龄主义的防御机制,通过三种镜像关系的发展凯特实现了自我重塑。
四、追寻突破——重释“海豹之梦”
“成熟小说”不仅在题材上对老年弱势群体的身份与自我认同给予关注,在叙事特点上也有着鲜明的文类特点,致力于打破年轻与年老之间二元对立的界限,作者往往会通过特定的艺术手法来凸显主人公所面临的社会境况与“成熟”的过程。《天黑前的夏天》中一个重要的艺术特点就是象征性,其中,最鲜明的意象就是凯特的梦境——“海豹之梦”。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中,象征是“建立于潜意识原型之上的”“有意义”的意象[10]。当人们陷入某种不可调节的强烈矛盾时,就会通过梦中的意象对被压抑的思想进行释放,同时也可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凯特面对残酷的现实与压抑的自己,对梦中海豹援救的同时也是在潜意识里营救自我。“我所有的外在表现,工作、旅行、以及婚外恋……所有的这些,不过是……梦的素材。真的。这个梦……靠我白天的经历提供营养。像一个胎儿。我只是刚刚才明白而已”[6]206,莱辛通过凯特贯穿整个夏日的“海豹之梦”来暗示凯特的精神轨迹,生动模拟出走向衰老的凯特面对逐渐降低的自身社会价值与年龄主义时实现新生的心路历程。
“海豹之梦”的第一个作用是引领凯特追寻真实的自我。这个梦境在小说中共计出现了15次,贯穿故事始终。梦境始于凯特成为职业女性,到国际食品组织工作不久。她的住所十分狭小,只有几件生活必需品,“干干净净,对她没有一点感情”[6]28,与她的生活境况极为相似,象征凯特被剥夺、不被需要的人物形象。在这样的环境下,她第一次梦见海豹:“原来是只海豹,搁浅了,正无助地躺在阴凉山坡边一块干燥的大石头上,痛苦地呻吟着。她把它抱了起来。很沉。她问它还好吗,能为它做什么。它呻吟了起来,她知道得把它送回水中,于是抱着它朝山下走去。”[6]28海豹搁浅无助的境况象征着凯特孤立无援的处境,她就如同这只海豹一样身处陌生的环境当中,焦虑无助,奄奄一息,等待着他人的援助。而凯特对梦中海豹的救助象征着自我治愈的开始,“那个梦变得和史诗的开篇一样,简单直接”[6]28。“史诗”预示着凯特追寻自我之旅的开端。在和情人杰弗里去西班牙的旅途中,凯特梦见自己抛弃了海豹,海豹独自向遥远的大海前行。之后凯特因为愧疚又找回了它,在空无一人的木房子里给海豹淋水,同时还惦记着拾柴火、准备食物、整理冬天的衣服。在楼上,凯特见到了她的情人,于是再次把海豹抛弃在了浴室。凯特多次对海豹的抛弃象征着对自我救赎的犹豫不决,她没办法在扮演好贤妻良母的同时打破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去大胆追寻真实的自我。但当她与楼上的情人如胶似漆,沉浸在炽烈的爱情中时,却坚决地对情人说:“对不起,我很想跟你在一起,但我得先把海豹送回海里”[6]98,暗示凯特在渴望被关注、被需要、被爱的同时,坚定追寻真实自我的决心。在凯特的情人杰弗里生病时,凯特有大量的时间独处,这时的梦境又发生了变化。她梦见自己和海豹一同在罗马竞技场里,狮子、豹子、狼还有老虎对他俩穷追不舍,在凯特坚持不下去时,这些凶猛的野兽又变得越来越少,直至消失不见。这些紧追不舍的野兽象征着凯特的责任与母职等,是她拼命想摆脱的桎梏,而在竞技场与海豹逃命则表明,她想拯救与追寻的自我命悬一线,她必须做出决断。这些动物意象表明凯特内心的冲突与矛盾,但在激烈的挣扎之后,她选择奋力奔跑,继续追寻自我,让“野兽”从她的世界里逐渐淡出。
“海豹之梦”的另外一个作用是让凯特直面自己的衰老,不再沉浸于年轻时的记忆,不再逃避。随着年龄的增长,凯特“渴望过去,但想到过去又很烦恼”,“家的温暖将他们(自己与家人)牢牢封闭在一个地方:过去。”[6]122即使在离开家的旅行暑期,她也总是沉浸在家庭温馨和谐的印象之中,认为自己是整个家庭的中心,丈夫和孩子们都需要她,相比于离过婚的玛丽,她要幸福得太多,即使丈夫出轨也不能打破她对家庭美满的虚幻记忆。凯特独自在旅馆,在回忆中陷入了梦乡。在梦中,她带着海豹来到了一个积雪覆盖的寨子,她遇见了国王,在村民们羡慕的眼光中与国王拥抱亲吻、翩翩起舞。不久以后,国王又拉了一位年轻的女子舞蹈,她被国王抛弃并被关进了牢房,国王与年轻姑娘的舞蹈与乐声在她心里留下沉重一击,她便整日郁郁寡欢,而国王却指责她不懂生活的规则。梦中的情景正是凯特自以为幸福美满实则充满瑕疵与痛苦的婚姻生活的真实写照。梦中的国王影射凯特的丈夫迈克尔,在结婚之初,俩人达成共识,认为激情既然不能永驻,她们就要开诚布公,把婚姻危机扼杀在摇篮里。于是凯特阅读了大量书籍,但她阅读的书籍大部分都是让妇女平静而有耐心地面对家庭琐碎,用包容的眼光看待丈夫的出轨,这导致在他们结婚的第十年,凯特欣然接受了迈克尔的婚外恋情。迈克尔对自己的艳遇愈加开诚布公,但凯特却一直自我催眠,沉浸于幸福美满的婚姻幻象之中。凯特的梦以一种类似于童话故事的叙述方式,一针见血地让她明白自己婚姻的真实处境,使凯特在追寻自我的过程中突破了过去的自我,不再沉浸于年轻时温暖的记忆,正视了丈夫的错误以及自身衰老的处境。
除了小说中最重要的海豹意象,作者还创作了很多其他意象来展示凯特的心路历程。在小说的第一章,面对自身逐渐变老的境遇,凯特每每在提到未来时,她都会感到“寒风”的袭来。“举例说吧,大约在三年前,他们就讨论过‘未来寒风’这一现象,可事到临头,他们也没描绘出蓝图或备好原因说明……”[6]20寒冷的状态表现出凯特对迫近的空巢的畏惧心理与无可奈何。另外,凯特还把结婚前的自己自嘲为“一只白色的大肥鹅”[6]88,在英语的用语习惯中,鹅有着愚蠢的隐喻。凯特婚前生活在父母的庇护下,对外界的认知与看法也受到祖父的影响,缺乏自己的主见与想法,对婚后的生活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导致多年以来成为了“女佣和脚垫……瘸子和废物”[6]92。多年来对家庭的奉献与委屈自己,使凯特觉得“自己像只受伤的小鸟,被健康的同类生生啄死;又像一只动物,遭残忍的孩子戏耍玩乐”[6]94。在旅途时,凯特也称病后的自己为猴子。在西方文化中,猴子擅长模仿,因此被用来讽刺人类的盲从与虚荣行为,小说中的猴子象征凯特认同并被禁锢于社会文化规范当中。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凯特梦见与自己同住的女伴莫琳变成了一只金丝雀,被关在笼中,却奋力挣扎着。金丝雀是被人类观赏的对象,象征女性在社会上“被凝视”的特质与客体地位。这些动物意象生动传神地表达出女性在社会上的弱势地位与无助的状态。
莱辛用大量的象征手法刻画出凯特所处的不同境况与心理经历。凯特不断通过“海豹之梦”获得自我认知,又在与海豹共处的过程当中追寻真实的自我,从而进行人格整合,实现突破,度过中年危机。凯特最后拯救了海豹,让海豹回归大海,结束了梦境,自己也重新回归了家庭。与以往不同的是,凯特在回家之前没有刻意去给自己的头发做造型,她喜欢直发,之前却不得不把头发烫成大波浪以符合中产阶级太太的身份,并且不断染发以掩盖一头长发中随着年龄而肆意生长的白发。最终,她只是扎起了自己的头发,一缕白发若隐若现。回家时,她是一个有着老态的衰老女人,不再尝试变得年轻,不再取悦他人的目光。
五、结 语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专著《走向成熟》中对社会老龄化现象进行了深刻反省,并首次指出老年公民被主流社会边缘化,被视为“另一个物种”的残酷现象[11]。于是,“成熟小说”在这样的社会潮流中应运而生。事实上,与老年相关题材的文学作品大多出自女作家笔下,不仅仅是因为75岁以上的老龄女性的人数远超于男性,更在于父权社会带给女性的性别与年龄的双重压迫。在20世纪后半叶的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中,年龄主义加入了性别主义的行列,参与到了社会变革中。从女性的身份政治关注年龄主义,更能使女性个体克服对自身即将成为“老年他者”的恐惧心理,超越自身的性别、年龄限制建构新身份。
莱辛作为“成熟小说”的代表作家,在文本创作中以不断挑战中老年女性刻板印象的方式融入了自身老龄经历的丰富体验。小说《天黑前的夏天》通过讲述凯特的夏日之旅来揭示走向衰老的女性面对逐渐降低的社会价值时的真实境遇,描摹出女性在习得社会性别与面对年龄歧视时的痛苦与屈辱,重新思考了女性气质中的母职、容貌等传统道德观对中产阶级女性的束缚。然而,年老女性的处于社会中的他者地位不仅仅是社会规范造成的,还是女性甘愿与之共谋的结果。凯特的回归标志着女性气质在老龄化社会文化中的重塑与转型,女性可以同时扮演母亲、妻子以及中年女人的角色,并且保持自我。只有认识到了个体身份的社会建构性,并致力于改变社会文化结构,才能超越特定的性别文化角色限制,挑战并消解社会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