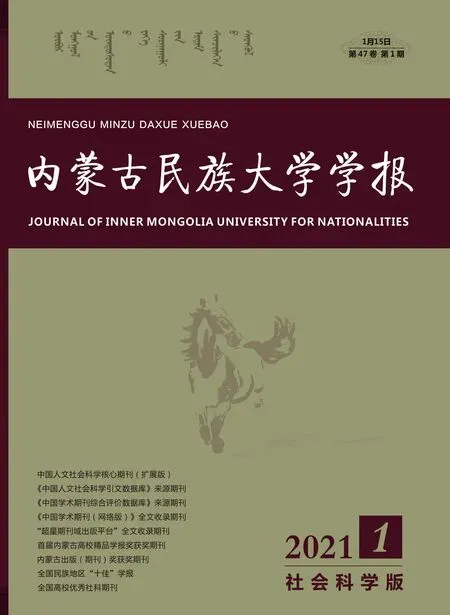古埃及与阿克苏姆的文明交往
2021-11-29田明苏玉雪
田明,苏玉雪
(内蒙古民族大学法学与历史学院,内蒙古通辽028000)
古埃及与阿克苏姆的文明交往是地中海贸易圈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主要是因为两地区的文明交往为东地中海地区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两种文明的交往与碰撞并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在长时段的历史背景之下所形成的物质文明交流的结果。国内关于两地区文明交往的研究少之又少,至今仍没有专门性的文章发表。虽然国外学者对两种文明的交往进行了相关性研究,但仅仅是从非洲史的研究角度出发,所以本文试图突破固有的非洲史框架研究,将两种文明放到古代文明交往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论述,试图分析和总结两地区文明交往所产生的影响。
一、文明交往的历史渊源
研究古埃及与阿克苏姆两种文明的联系,必须对两种文明交往的历史渊源进行分析。因为从时间上对比,古埃及与阿克苏姆两种文明并不属于同一历史时期;从历史地理角度来分析,两种文明并不发源于同一地区,可是一条尼罗河将位于上下游的两个地区联系在一起,加之古代贸易的发展使两个地区的联系变得更为密切。所以研究此问题不能单纯地从一个角度出发,应该多维度地观察古埃及与阿克苏姆两种文明之间的联系,从而进一步深入思考两种文明的交流与碰撞对周围地区所产生的影响,因此对古埃及与阿克苏姆两种文明交往的历史渊源进行系统的梳理是十分有必要的。
首先,从时间上对比,埃及文明远远早于阿克苏姆文明。然而,关于两种文明的往来历史上并没有明确的史料来证明,所以古埃及与阿克苏姆两种文明的联系显得非常模糊,但通过近期考古资料的不断被发现,分析得出:古埃及与阿克苏姆两种文明在史前时代就有了一定联系。大约距今1万年之前,居住在埃塞俄比亚地区的游牧民族,从厄立特里亚北部到哈雷里一带地区的岩石上,刻着他们那些无脊隆的长角牛角图像,他们的畜群和同一时期在撒哈拉地区和尼罗河流域饲养的畜群相似。[1]264从考古挖掘出的农作物分析,古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地区也具有一定的联系,埃塞俄比亚的古代人民在史前时代就开始驯化动物、培育植物,埃塞俄比亚地区品种繁多,通过对野生植物物种的对比分析,植物栽培历史十分悠久。尽管对埃塞俄比亚地区的考古记录还没有追溯到阿克苏姆时期以后的历史,但关于物种多样性的类似观点也同样适用于小麦和大麦。虽然可以确定是这些物种最初是从北部引入埃塞俄比亚的,但今天在该地区种植的大多数品种在其他地方都是不为人知的。[2]壁画的发现证明了埃塞俄比亚与尼罗河流域两地区的古代居民很早就有了往来,且考古挖掘出的农作物表明:史前时代两地区的居民就已经发生了长距离的贸易往来与物品交换。
其次,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分析,两地区都位于非洲板块的东北部,埃及最南端的边界与阿克苏姆北部疆土是相连的,又因为尼罗河贯穿南北,所以两种文明存在着一定的地域联系。阿克苏姆包括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等国,在罗马帝国时期,这里属于阿克苏姆王国的辖地。[3]关于蓬特地区的地理位置至今虽未被确定,最权威的看法就是指在现在的索马里半岛或者是埃塞俄比亚地区。[4]菲利普斯在《蓬特和阿克苏姆:埃及与非洲之角》一文中从古埃及与其他邻国的关系角度出发,通过贸易往来、商品交换及宗教传播等方面论证了蓬特与阿克苏姆是埃塞俄比亚地区的先后不同的文化关系。[5]由于蓬特与阿克苏姆都位于埃塞俄比亚高原,所以蓬特与阿克苏姆文明同属于埃塞俄比亚文明。
最后,古代对外贸易的发展使两种文明产生了一定的交融。公元前4000—前2000年埃塞俄比亚地区出现了大量的规模较小的集中定居点,涌现出来的酋邦领导人或首领可能受益于与古埃及的贸易联系,古埃及称此地区为“蓬特地区”,而“蓬特”的商人把黄金、木材、芳香油和兽皮经红海出口到埃及。[6]约公元前2400年第五王朝的第八任法老杰德卡拉·伊塞西(Djedkarelsesi)统治时期一直持续到约公元前1200年拉美西斯三世(RamesesⅢ)统治时期,埃及与蓬特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一直以来从未间断过。新王国时期,埃及与蓬特贸易的往来主要集中在哈特舍普苏特时期,她通常被描写为“和平主义者”,除了远征蓬特外,对努比亚以及西亚地区也进行了多次军事活动,来巩固图特摩斯一世的军事成就。《古代埃及史》叙述道:“我的南边的边界扩张到蓬特,……我的东部边界扩展到亚细亚的沼泽地,而亚细亚人在我的统治之下,我的西部边界扩展到马努(西方)山。……我从捷赫努(利比亚)得到贡品……”[7]401这些史料是古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地区往来的真实写照,反映了两种文明往来具有较深的历史渊源。
托勒密统治时期的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地区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红海贸易进行的,托勒密二世对红海沿岸进行了开发,此时的经济、政治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发展。托勒密三世在第三次叙利亚战争之后在阿杜里斯港(今厄立特里亚)树立了凯旋的铭文反映了猎象活动的情况(现存的阿杜里斯铭文是公元6世纪科斯马斯在阿克苏姆统治者要求下而制作的临摹)。[8]托勒密时期,埃及的势力范围发展到了埃塞俄比亚地区,并在此建造了阿杜里斯港。《非洲通史》中写道:“在我们公元前三世纪中叶,托勒密二世修建了费拉德尔菲斯城,即阿杜里斯港,他之后即位的托勒密三世尤尔杰蒂斯又把这个港口扩建,老普林尼在公元75年也认为这个港口是重要的停泊港之一,他还曾提到到住在距红海5天路程的大山中靠猎象为生的众多阿萨切人部落。”[1]264由此可知,托勒密统治时期的埃及已经成为东地中海贸易圈的中心,于是埃及通过红海贸易与埃塞俄比亚地区建立了贸易联系。托勒密统治时期的埃及随着克利奥普特拉七世的去世而灭亡,埃及由此进入了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罗马帝国时期的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地区之间的联系也从未间断过,而此时的阿克苏姆王国还处于它的初始阶段。考古发掘显示,在阿克苏姆发现了有几件来自埃及的物品,如布鲁斯给他自己设计了具有古罗马艺术特色的荷鲁斯雕像,在埃塞俄比亚地区的不同地点都发现了一些蓝色彩陶或山茱萸的护身符雕像。在阿杜利斯挖到了一个像一艘船的埃及玻璃圣甲虫雕刻,时间要追溯到很晚。两地区之间联系的其他迹象是科斯马斯在阿杜里斯抄写的托勒密三世铭文和刻在了一根石柱上的一个安柯标志[9]52,这些考古资料的发现,也证明了两地区之间存在着一定联系。虽然蓬特仅存在于埃及人的记录中,但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这为后来古埃及与阿克苏姆的交往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从物种种类与贸易交往的角度来分析,古埃及与阿克苏姆的联系时间可以进一步向前追溯并且交往范围变得更加广阔。随着经济往来及政治势力范围的不断扩大,文明间的交往与碰撞也随之增加,这也为古埃及和阿克苏姆之间的文明交往源起提供了可能。
二、贸易往来的路线探索
自古以来,古埃及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交往不断,由于两地区距离的缘由以及考古资料出土,古埃及与阿克苏姆文明交往的表现主要以经济交往为主。由于双方长期的贸易往来,于是就产生了两条贸易路线:一条是沿着尼罗河而进行的陆上贸易路线,另外一条则是沿着红海沿岸进行的海上贸易路线。
首先,关于尼罗河流域进行的陆上贸易路线的存在,大多数学者众说纷纭,本文认为该路线是真实、存在的。因为早在法老统治时期的埃及就已经形成了沿着尼罗河而进行的尼罗河贸易路线,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航海技术的提高,加之人们想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求奇珍异宝以及后来红海贸易的发展,这些都是导致尼罗河陆上贸易路线衰落的原因。在托勒密统治下的埃及积极开展红海贸易,与此同时,努比亚的库什也是红海贸易中的转运者。库什人纳巴达与麦罗埃国家通过居住在努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阿杜里斯港取得印度的胡椒、棉布,东非的香料和黑檀木,中非的象牙、毛皮和黄金也经过这里运到埃及,沿着尼罗河路线运到托勒密城和贝仑尼塞港。[10]48杰克·菲利普斯在《蓬特和阿克苏姆:埃及与非洲之角》中也证明了该条路线的存在,其文中这样写道:“这不是在埃及最南端发现的唯一物品。苏丹境内的尼罗河以东地区近年来才开始发掘,但考古结果改变了我们对该地区的看法。长期以来下努比亚地区一直被视为埃及、努比亚金矿(库什金矿)的来源地,甚至还发现了法老统治时期的矿区,而该碑文的发现使陆地线路得以确认。”他还认为阿斯旺是埃及南端重要的省份,是埃及的南大门,也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门户以及由海上进入非洲腹地的唯一通道,也就是说这里是古代埃及向南扩张以及南部国家向北进入埃及的一个重要关隘。通过这座城市,阿克苏姆与罗马统治时期的埃及建立起了陆上路线。公元6世纪时期,拜占庭帝国历史学家普罗柯比乌斯记录:一个没有任何障碍的旅行家从阿克苏姆到阿斯旺要花上30天,这篇文章以及其他文章记录了从阿杜里斯到阿克苏姆的旅行不超过八天到十五天。[5]该条线路的存在与发展,证明了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地区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经济往来,双方的经济往来带动了尼罗河流域的商业贸易往来,随着红海贸易的发展,该条路线也随之衰落。
原始资料的出现与考古资料的挖掘,也进一步证明了这条路线存在的真实性。科斯马斯的《基督教风土志》记载了阿克苏姆王国(The Arksum Kingdom,今埃塞俄比亚)等红海地区的国家与民族,在海上丝路阿拉伯海及印度洋中的重要地位。“从拜占庭到亚历山大里亚50站,从亚历山大里亚到大瀑布群(Cataracts)30站;从瀑布群到阿克苏姆30站;从阿克苏姆到埃塞俄比亚凸出地,大约为50站。埃塞俄比亚凸出地即是出产香料的巴巴利地区(索马里)。……巴巴利人便前往内地经商,带回许多种香料,如乳香、肉桂、菖蒲,以及其他许多商货,此后他们又将这些商货从海路运往阿杜里(Adule)、希米雅提国、印度和波斯。”[11]《阿杜利塔姆纪念碑》中也提到了从阿克苏姆到埃及的陆上线路,证明了该路线是当时重要的贸易路线,并且著名的历史学家普罗柯比也记录了从阿克苏姆到厄勒藩汀需要花费30天来进行一个无障碍的旅行。[9]57上述史料都印证了陆上贸易路线存在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两地区的贸易交往也为努比亚地区与阿克苏姆的贸易往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其次,就是红海贸易路线的开展,其发展历史悠久。法老统治时期的埃及就开始探索到达红海沿岸的贸易路线,托勒密统治时期的埃及由于红海贸易的发展,其贸易范围继续向南推进,其势力范围到达了非洲之角,这也证明了此时的埃及在古代世界史上具有较高的历史地位。罗马帝国时期以埃及为中心形成了属于罗马独有的贸易范围,所以本文认为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的埃及处于东部地中海贸易的中心,同时也是重要的贸易中转站。
法老时期的贸易路线最著名的是法老运河,公元前1380年塞提一世时,此处就出现了狭长的水道,河床很浅。尼科法老时(公元前672—前664年)修筑了沟通尼罗河和红海的运河工程(未完成),更大可能完成这项工作的是波斯国王大流士。[7]569托勒密统治时期埃及运河的修建,《阿拉伯通史》中记录:“当埃及在托勒密人的统治下再变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与南阿拉比亚人争夺海上霸权。托勒密二世(公元前285—公元前246年)重新修复了由塞索斯特列斯于大约一千七百年前在尼罗河和红海之间所创凿的尼-红运河。托勒密人商船进入红海,表示希姆叶尔的商业活动已开始结束。”[12]由于托勒密王国强大的军事实力,这使托勒密王朝向埃塞俄比亚扩张提供了条件。托勒密三世时已经征服到了埃塞俄比亚地区,并建立了阿杜里斯港,此港口的建立更加证明了托勒密王朝时期的势力范围到达了埃塞俄比亚地区。
托勒密统治下的埃及也积极地开展海上贸易,公元前275年红海和尼罗河之间的运河又重新被开通,运河联结尼罗河的皮留辛支流和红海,改称为托勒密运河,这时埃及大力开展远到瓜达富伊角(Cape Guardafui)①的贸易,运成批的埃塞俄比亚绵羊,从红海沿岸运进大象以供作战。在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使者的推动下,菲拉德尔弗斯也向孔雀王朝派过使者狄奥尼索斯。托勒密五世时丧失了叙利亚,加之内陆地区象牙资源的枯竭,面对着意大利对阿拉伯和印度商品的与日俱增,这就迫使埃及转向南方海路。[10]47斯特拉波(公元前54—公元24年)亲眼见到过米渥斯·霍尔莫斯启航前往印度的船舶,最多只有20条船敢于横渡阿拉伯湾,走出海湾的地界。然而,现在有更大的船队甚至远航到印度和埃塞俄比亚边境,从那里把贵重的货物运回埃及,然后再从那里前往其他地方;因此,现在可以收到双倍的关税,既有进口税,又有出口税。对于贵重的商品,征收的关税也重。实际上,国家拥有垄断权,因为亚历山大城不仅是大多数这类商品的储存地,而且也是向外界供应商品的来源。[13]由此可知,法老统治时期的埃及就已经开辟了到达红海沿岸的贸易路线,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的埃及把红海贸易路线继续向南推进。
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的埃及对外贸易达到了空前繁荣,在此时的阿克苏姆、阿杜里斯、马塔拉、哈维拉-阿瑟劳(在阿斯比-代拉地区)以及德卜勒-达莫发现的东西,并非埃塞俄比亚本地的物品,其中一些通过贸易来到这个国家,特别是来自埃及,其中包括双耳细颈壶、玻璃器皿碎片、一块美玉(在阿杜里斯发现)、铜制灯具和一架铜天平及其砝码(在阿杜里斯与阿克苏姆都有发现)。[1]300—301本文认为挖掘出的玻璃器皿是通过红海沿岸运来的,因为玻璃器皿易碎,经过陆上的尼罗河贸易路线可以运输货物,可是从阿克苏姆到阿杜里斯有一段路程是陆路贸易,把大型易碎器物想要从阿克苏姆运到阿杜里斯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只能从红海贸易海运运往埃及,于是阿杜里斯港就成了红海贸易的中转站。考古发掘出的物品也印证了这一观点,米奥斯·霍尔米斯(Myos Hormos)和贝雷尼克(Berenike)的建立都是为了促进贸易,最初是为了从非洲进口大象供军方使用,后来跨越过印度洋。对于托勒密统治时期的贝雷尼克,贸易关系是通过两耳细颈酒罐来体现的,这种两耳细颈酒罐来自埃及境内,只有少数的外国船只来自罗兹岛。有系统的、有经济动机的长距离的印度洋贸易似乎始于公元前30年,大型陶器在阿杜里斯地区大量被发掘,来自公元1世纪的贝雷尼克和库塞尔(Quseir),[14]所以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的埃及处于东部地中海贸易的中心,同时也是重要的贸易中转站。
通过对两条贸易路线的整理发现,两条贸易路线都是在古代经济与贸易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第一条是沿着尼罗河进行的陆路贸易路线,历史悠久,其价值不言而喻。第二条是沿着红海海岸所开发的海上贸易路线,它主要是在贸易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之下进行的,这也为后来的罗马—拜占庭时期的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说两条路线的存在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但由于史料匮乏,两种文明之间的经济联系与贸易发展还需要更多的史料来加以佐证。
三、文化往来的交流互动
关于非洲文明的发展,布鲁代尔评价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处于“一种正在形成的人文主义”阶段,从此人们陈述非洲的价值有了一定的可行性。[15]地处东北非的两个地区,古埃及和阿克苏姆有着深厚的地域联系以及长时间的贸易交往,本文认为双方的往来为两种文化的交往与互通提供了一定的契机。因为物质交往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会间接地带动文化的交流,所以两种文明的文化交流与发展构成了古代世界文化宝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两地区的文化往来不断向人们诉说着独有的文化价值。罗马—拜占庭帝国统治时期的埃及与阿克苏姆两地区文明发展显得别具一格,罗马—拜占庭统治时期的埃及,在固有的文化基础之上衍生出了具有罗马—拜占庭帝国风格的埃及文化,而位于非洲之角的阿克苏姆同样处于文明交汇处,两种文明的交往与碰撞为后来的阿克苏姆文化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奠基作用。二者的文化往来最明显的表现是在宗教方面;另外,随着近几年来考古物品的出现,在碑文、语言、文字及瓷器等方面的往来也有显现,所以两地区的文化交往时间可以进一步向前追溯,并且文化间的交流与发展使埃及文化由相对封闭变得相对开放,使古代东北非文化呈现出多种文化共存并荣的局面。
关于两地区的宗教往来,本文将从两方面进行讨论。
首先,基督教传入阿克苏姆之前的双方宗教的往来,阿克苏姆的宗教信仰表现为多神崇拜,两者的文化联系具有一定的间接性。如有南阿拉伯半岛的月神豪巴斯、阿克苏姆传统的埃塞俄比亚崇拜、象征着太阳和月亮的标记出现在阿克苏姆以及马塔拉的石碑上以及在阿克苏姆的石碑上雕有埃及的生命长寿的象征,与崇拜哈托尔、普塔、荷鲁斯等神有关的物品以及圣甲虫等等,这说明信奉埃及-麦罗埃宗教的人在一段时期中曾在阿克苏姆、阿杜里斯以及马塔拉居住。[1]307从宗教信仰方面来看,埃及与阿克苏姆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埃及的原始宗教对基督教未进入阿克苏姆之前的宗教具有一定间接性的影响。
其次,基督教传入阿克苏姆以后,双方的宗教联系则表现为阿塔纳修斯在非洲的传教、埃塞俄比亚教会与科普特教会之间的直接联系。公元4世纪,埃扎纳统治时期的阿克苏姆王国把基督教立为国教,阿克苏姆也由此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关于阿塔纳修斯的传教:有一位弗拉门提乌斯的教徒有一次前往亚历山大拜见大主教阿塔纳修斯,告诉阿克苏姆主教对基督教颇为友好,希望阿塔纳修斯派一位主教前往,考虑到弗拉门提乌斯懂那里的风俗和语言,阿塔纳修斯就认命他为阿克苏姆的主教。这就使亚历山大教会的势力超过了帝国的南部边界,也确立起了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会之间持续1600多年的联系。[16]152自弗拉门提乌斯传教以来,阿克苏姆王国的宗教就已经成为亚历山大大主教的管辖范围,并接受那里派来的主教和规定的教会法规。因此阿克苏姆的历代国王和历代主教自然变成了基督教一神论的支持者,因为这一理论在埃塞俄比亚又起了另一个名字叫作特瓦杜(TEWAHDO)。[1]317察尔西顿会议之后,为了避免孤立,埃及的“一性论”主义转化为大规模的传教运动,主要集中从亚历山大经红海到非洲之角的贸易路线上。在南方埃塞俄比亚教会保持着与科普特教会的联系。4世纪,阿克苏姆转变了宗教信仰,埃塞俄比亚教会的第一位主教弗拉门提乌斯由阿塔纳修斯任命。到了6世纪,埃及教会再度加强了与埃塞俄比亚教会之间的联系,著名的就是502年九圣徒抵达埃塞俄比亚,在九圣徒之中除了埃塞俄比亚人还有叙利亚人,主要目的是力图恢复和扩展帕克米提乌斯修道院的影响,这些人将《圣经》译成了埃塞俄比亚语。他们的热情影响了统治阶级,532年埃塞俄比亚国王出兵海迈提王国,为受迫害的基督徒报仇。非洲之角成为埃及文化的附庸,[16]180所以古埃及宗教对阿克苏姆宗教信仰的影响有理有据,埃及与阿克苏姆教会之间传教与互动是两种文化联系的一种体现,这也证明了在基督教传入阿克苏姆后两者的文化联系发生了直接的碰撞与交融。
考古发掘使两者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密切,使二者的文化联系时间得以向前追溯。在阿杜里斯并没有发现任何与埃塞俄比亚高地相关的陶瓷品,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村庄已经被遗弃。可惜的是,4部分合适的样本都无法用C14来测定。在这种情况之下,阿杜里斯的器皿与顶部是黑色的碗与烧杯联系在一起。公元前1000年的陶瓷集合群在这一地区是普遍的,并且在以前的阿杜里斯是没有的。波纹式的印记是通过贝壳边缘获得的,出现这种集合群在阿杜里斯是非常典型的,这可以追溯到与之相似的公元前2000年吉布提遗址、古瑟兹遗址和埃及红海沿岸遗址,埃及中王国时期的集合群是从南部红海地区进口的。更有趣的是,在埃及和也门的蒂哈马发现了阿杜里斯早期阶段传统的袋装陶器罐集合群,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17]通过考古资料的挖掘显示,两种文明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建立起了联系,而且时间早于古代晚期。另外,在埃及发现了埃塞俄比亚石碑,石碑上出现了阿克苏姆铭文,täkale’Aksum(am the founder of Aksum)被译成“阿克苏姆的建立者”(仅是残片)。[18]所以本文认为出现在埃及的埃塞俄比亚石碑和出土的陶器证明了两种文明之间存在着相应的联系,虽然翻译出来的碑文具有很小的说服力,但“阿克苏姆”词汇的译出,证明了古埃及与阿克苏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文化交往。
双方文化联系的其他方面还表现在语言和文字的使用,阿克苏姆有几种供文人和宫廷使用的文字。在阿克苏姆的石碑石柱上,有些铭文只使用一种文字或者用萨巴文,或者用盖埃兹文,有时也用希腊文,但很少三种文字同时使用。萨巴文是萨巴各部落使用的字母,人们认为这些部落是阿克苏姆人的祖先之一。传统著作中把他们说成涅盖德约克坦(约克坦部落),今天的阿姆哈拉人、提格雷人、古拉盖人、阿尔戈巴人和哈拉里人(阿德雷人)都是他们的后裔。当时在国际上通用希腊语,它也被引进了阿克苏姆,因为当时阿克苏姆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方面和拜占庭帝国都有联系,特别是采用了希腊式的国王名字如佐斯卡勒斯、阿菲拉斯、安迪比斯、松布罗图斯等等,在他们统治时期,联系也更加密切。而到了公元6、7世纪,阿克苏姆的官方语言就是盖埃兹语(起初没有元音符,后来才加上),即所谓阿加伊齐安语,当地人给这种语言起了另一个名称,意即解放者的语言。这种语言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有用的线索,但并不能分明它确切的属于哪一个种族。这是因为,当地人有的可能是闪米特人的后代,阿克苏姆国籍,但文化却是希腊的另外一些人,其祖先可能是贝札人或布勒米人,出生时是努比亚人或努比亚籍,但他们的文化却属于埃及的。[1]323所以,本文认为出生时是努比亚人(或努比亚籍)的这些人,最终将埃及文化间接地传入阿克苏姆,其文化对阿克苏姆的语言和文字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综上所述,古埃及与阿克苏姆的文化联系呈现出阶段性和多元化的两种特点。基督教传入阿克苏姆之前,双方的文化交往具有一定的间接性;基督教传入阿克苏姆后,双方文化交往具有一定的直接性。考古资料的发掘显示,两者的文化联系还表现在语言、文字及瓷器等多方面的往来,而且在埃及发现了埃塞俄比亚的碑文,使二者的文化联系变得更为密切,这些都是双方的文化联系的有力证据。
四、结语
古代东北非地区交汇的古埃及和阿克苏姆,都是比较相对闭塞的国度。一条贯穿南北的尼罗河从埃塞俄比亚高原出发向北流入地中海,把两地区联结到了一起,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文明交往与碰撞。埃及文明主动传播,阿克苏姆则被动接受。两种文明的交往涉及经济、政治及文化的三个方面:史前时代,由于长距离的物品交换,两地区人民就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往来。法老时期,由于埃及实力强大,双方交往呈现了一种暴力交往的态势。托勒密统治时期,双方的联系主要是通过红海贸易进行的,故双方的往来主要以经济交往为主。罗马—拜占庭的埃及与阿克苏姆因为基督教传播的缘由关系更为密切,并且此时的东北非文化呈现出一种文化共存并荣的局面。总之,古埃及与阿克苏姆两种文明的往来体现出了一种双向互动的交往态势,双方经济、文化的交往成为了红海贸易以及地中海贸易圈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埃及为中心,使东地中海地区呈现出了网格状的文明交往格局。
[注释]
①瓜达富伊角(索马里语:Gees Gwardafuy)是位于东北非国家索马里巴里州的一个海岬,瓜达富伊角位于接近亚丁湾、印度洋中之也门属索科特拉岛的内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