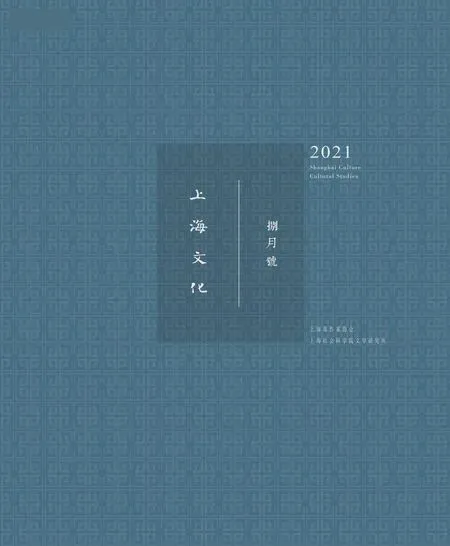民间祭祀系统的构建与反思
——评李天纲《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
2021-11-26朱麟钦
朱麟钦
20世纪80年代对于中国的乡村社会(rural society)来说是一段重要的全面重建时期。经济的复苏、基础设施的建设、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教育文化的普及对宗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①Thomas David Dubois, Local Religion and Festivals, in John Lagerwey and Pierre Marsone (ed.), Modern Chinese Religion II:1850-2015, Leiden: Brill, 2016, p.394.李天纲于2017年出版的专著《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下文略作《金泽》),其田野调查的对象——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正是处在这一“宗教复兴”的时代背景之中。此外,就其历史沿革来说,它还具有其他重要的参考价值:“金泽镇地处江南核心地带,这里历来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信仰体系……是江南市镇由传统到现代,从本土向全球过渡的普通例子。”②李天纲:《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40-47页。李氏通过对金泽地方志、寺庙建筑等历史物质资料以及现实宗教活动的田野考察,以明清时期与20世纪80年代后的“宗教复兴”作为划分研究时段的节点,试图概括江南地区民间宗教及祭祀的发展脉络及其在地化体系,并以此对民间宗教等概念进行反思与重构。
一、围绕中国宗教之定义的两类桎梏
宗教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它的出现伴随着两种天然的研究意识:一方面,为区别于神学,宗教科学研究者需要避免由自身信仰与宗教背景带来的对研究对象的主观偏见;另一方面,学者们极力强调比较视野下的宗教学研究对于揭露单一研究视野之缺失的重要性。③F. Max Müller,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Religion,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73, p.16.因此,emic与etic,内在与外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角度成为当今宗教研究在方法论上首先需要面对和探讨的问题。④Thomas N. Headland, Kenneth L. Pike, Marvin Harris (ed.), Emics and Etics: The Insider/Outsider Debate, California: Sage Production, 1990, pp.28-83.李氏长期深耕于跨文化视野下明清时期中西礼仪之争的相关研究,尤其是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本土的儒教学者围绕经典和术语的探讨,使得他敏锐地意识到中国语境下“宗教”与“民间宗教”概念在迻译过程中产生的歧义。在《金泽》一书的绪论中,关于这两个关键概念的背景与问题就被率先展示出来:“上层儒、道、佛三教和下层信仰之民间宗教,到底谁可以代表‘中国宗教’?既然民间宗教是一个从迷信逐渐演化过来的近代概念,那它和同时存在的儒教、佛教、道教三教的关系究竟如何?”①李天纲:《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第8-9、40页。这两个问题不仅是对海外中国宗教研究现状的一种回顾和反思,更是全书对金泽镇民间宗教构成与祭祀传统进行研究的起点。换句话说,李氏正是通过金泽镇这一江南典型的个案来试图寻找“中国人的宗教生活及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②谢军、钟楚楚主编:《胡适留学日记》,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32、31页。如果在理论的范畴中进行归纳,那么这两个问题就表现为内与外两种对中国宗教定义本身的桎梏。
第一,围绕宗教概念的外在桎梏。我们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中国语境下的“宗教”是一个经由翻译而被引入的外来现代术语。③曾传辉:《宗教概念之迻译与格义》,《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5期。与此同时,即便是在西方的语境中,religion一词的意涵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学科范畴中也存在着差异。因此,在面对宗教定义本身与中国语境的适配难题之前,我们必须对这一术语定义的沿革进行还原。在拉丁语文献中,针对religio就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西塞罗(Cicero)认为,religio源于legere(聚集、辨认)一词,它代表了一种对诸神的虔诚崇拜。与此相对,基督徒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则把religio与ligare(连结)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人与神之间存在的一种虔诚的关系。④John Scheid (ed.), Rites et Croyances dans le Monde Romain, Vandoeuvres-Genève: Fondation Hardt, 2006, pp.39-40.前者突出了宗教概念中的仪式与行为,而后者则强调了信仰的重要性。⑤Georges Dumézil, Idées Romaines, Paris: Gallimard, 1969, pp.47-59.此后,基督教神学在西方语境中牢牢控制住了对宗教的解释权。即使到了20世纪,当学者们有意识地从理性和人文的立场将宗教从神学移入科学的范畴之中,将原本被神学排斥在外的迷信、巫术和异教仪式纳入研究的视野之中时,基督教依然发挥着它在漫长历史时期内对宗教本身产生的深远影响。其中,最为典型也最为重要的例证,就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对于“宗教”的定义,他强调:“宗教是一种与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与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与仪轨将所有信奉它们的人结合在一个被称之为‘教会’的道德共同体之内。”⑥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4页。也正是基于基督教会模式所生发的这样一种强调组织性与系统性的强共同体结构,使得杨庆堃以结构功能的分析方法把中国宗教划分到“分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中。⑦杨庆堃:《中国社会宗教》,范丽珠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页。因此,第一种桎梏可以被概括为由于基督教对于宗教概念之影响,使得学者们对于中国宗教定义的偏颇。针对这一点,李氏在《金泽》一书的绪论与第四章中,不仅系统地梳理了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们早期对于中国宗教的看法,还详细列举和分析了近代以来海外学者就中国宗教体系提出的不同见解。其中,他结合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与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等学者的观点,深刻而精彩地辩驳了杨庆堃提出的“分散性宗教”。通过对“三礼”、《周易》等历史文献的研读,李氏发现周代儒教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塑造了一套繁复而严格的祭祀制度和规定,并且这套相对成熟的祭祀体系在两汉之后被断断续续地流传下来。因此,他认为:“儒教和民间宗教并不是一种不加组织的信仰,不过组织方式与西方教会不同而已。”①李天纲:《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第248、252、254、205-254、175、248、361页。更进一步来说:“中华宗教的组织性主要在于它有完整的祭祀体系。”②李天纲:《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第248、252、254、205-254、175、248、361页。
第二,民间宗教与祭祀的内在桎梏。周代在封邦建国的政治形态之下延续了夏、商的祠祀,构建了一套等级森严的“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祭祀体系。秦统一六国后对原诸侯国各地不同的神祠进行了收编,国家祭祀统一交由“太祝”进行管理,其余则属于“不领于天子之祝官”的地方官方祭祀。③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82页。汉代儒生在重构和复兴周孔之道的基础上,逐步扩充和完善了国家祀典的内容与祭祀的仪轨。与此相对,那些未被纳入官方祭祀体系中的、不当祭与不合礼制的祭祀则被统称为“淫祀”。对于正/秩祀与淫/私祀的区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于官方或国家宗教与地方或民间宗教这两者之间关系的认知和判断。李氏在第三章与第四章中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对这种既有的划分提出了质疑。他敏锐地注意到,一方面,国家控制了天、地、封禅等大型祭祀活动,并借由行政等级体系安排官员有序地引导地方的重要祠祀活动——也就是说,这是一套自上而下的国家儒教祭祀体系;但另一方面,“在国家宗教之外,地方信仰还有很大的空间,中央祀典之外还存在大量民间祭祀”,④李天纲:《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第248、252、254、205-254、175、248、361页。这些祭祀活动具有很强的地方性特征,对特定的共同体产生持续而重要的宗教影响,因而其中一些淫祀被官方接纳而成为正祀,并得以在全国范围内立祠崇拜。正是基于这一点,李氏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淫祀和正祀之间并非总是对立,常常是兼容并蓄,时时转换……这种自下而上的模式,或许才是中华宗教的主流。”⑤李天纲:《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第248、252、254、205-254、175、248、361页。除此以外,相对于学理深厚的儒、道、佛三教体系,民间宗教与祭祀往往被认为是一种非理性的存在。李氏将这样一种认知归置到宋、元、明时期孔孟之道的背景之中。与强调祭祀与仪礼的周孔之教不同的是,宋代以后的孔孟之道在升格孟子的同时,更加“注重以心性论为表率的伦理境界”。⑥李天纲:《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第248、252、254、205-254、175、248、361页。不仅如此,三教在学理上的共通与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这一时期宏观概念上的中国宗教哲理性特征的刻板印象。也就是说,理性与非理性的划分,成为区别中国宗教与民间宗教的一种可能的依据。李氏全然反对这样的观点,在他看来,民间信仰与三教之间的关系绝不可以被这样武断地割裂开来。与此相对,三教与民间宗教之间的合一性在《金泽》一书中被反复强调:“民间的各类信仰,儒、道、佛的寺庙住持交叉,各类神祇(佛、仙、鬼、圣人、老爷、忠烈)的祭祀混杂,‘三教合一’以后又难以划分。”⑦李天纲:《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第248、252、254、205-254、175、248、361页。在第六章中,李氏着重分析了三教通体的形成以及三教与民间宗教的关系。在他看来,“儒、道、佛的共同基础,在于民众的基本信仰。说‘三教合一’,毋宁说是中国的各种宗教生活原本就植根于基层的民众宗教”。⑧李天纲:《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第248、252、254、205-254、175、248、361页。
围绕着这两个关于宗教、中国宗教以及民间宗教在概念及认知上的问题,李氏通过将宗教回归祭祀的方式从基督教中心主义的、非官方的与非理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由此,在一项制度化的、官民融合的、三教合一的金泽镇在地宗教研究成为可能的同时,广义上的中国宗教或汉人宗教问题也就自动被纳入讨论的语境之中。
二、金泽镇的地方宗教系统
在对历史文献和宗教理论进行研读与讨论之后,《金泽》的另一半则回归到田野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之中。李氏把中国宗教的问题与民间宗教联系起来,再把民间问题聚焦到一个典型的地方个案研究上。这种研究路径对应于许多现代汉学研究中所采用的“在地化”视角,把中国宗教在地理概念上区分为三个层级:国家、区域和地方。①Thomas David Dubois, Local Religion and Festivals, in John Lagerwey and Pierre Marsone (ed.), Modern Chinese Religion II:1850-2015, Leiden: Brill, 2016, p.372.为此,围绕祭祀作为中国宗教组织性与系统性之依据的核心观点,李氏在第一、二、七、八章中集中阐述并讨论了金泽镇现代民间祭祀生活,再从地方研究辐射到江南区域的民间信仰系统。这一套体系在大体上可以被划分为神祇体系、空间秩序和信众团体这几个部分。
首先,金泽镇的神祇体系可以被概括为“一朝阴官”的行政官僚传统与信众约定俗成的敬祝次序。根据李氏的调查研究,金泽镇当地流传着朱元璋为阻止金泽生人进位帝王,挑选当地神祇封为“一朝阴官”的故事。从皇帝、丞相、皇叔一直到州府县官,官方的行政体系被完整地复刻到地方神祇的阶序排位上。职位的高低彰显了这些神祇在阴曹地府里掌握各级权力及其所能显现威力大小的不同。不过,由于相关考古材料与史料的匮乏,我们无法获知这些排序的依据究竟为何,也不能确定这些规定究竟是由谁来制定的。李氏在书中尝试为我们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一朝阴官的编排,是参照神祇在信众心目中的法力以及原先的祭品官阶一起决定的。”②李天纲:《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第256、40页。不过,在之后对江南地区“烧十香庙”的描述当中,金泽镇人对于烧香次序的安排与解释却与此产生了出入。在对香头的访问调查中,烧香顺序是从杨震庙(州官)开始,以土地庙、总管庙(粮官)、关帝庙、二王庙(皇叔)和颐浩禅寺为主要顺序。其背后的逻辑在于祭祀对象所管理事务对信众自身而言的重要程度,以及寺庙位置的相互毗邻关系。李氏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性,而只是强调了神祇在被管理过程中的系统化与信众祭祀行为中的系统性,并以此来反驳民间神祇与庙宇信仰散乱无章的观点。事实上,对散乱神祇的系统化处理与信徒们自主选择的敬祝方法恰恰对应于上层与下层之间的两种不同的互动模式。由官方认定、赐予特定神祇的地位与民间个人福祉攸关的神祇价值之间存在的异同,也许是对神祇在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功能演变与地方信仰之变化进行研究的重要方向。
李氏在论证神祇系统与寺庙祭祀系统的过程中忽略了系统之形成在历时性上存在的异同与复杂性,而在对民间祭祀的空间秩序的共时性研究中,他的论证则要详细与完备许多。根据李氏的说法,我们可以从金泽镇的祭祀与信仰体系中辨别出“本土(local)—地方(regional)—全国(national)—全球(global)一共四层关系”。③李天纲:《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第256、40页。其中,较低层级的祭祀系统主要由儒教祭祀传统中“祖祭”与“社祭”这两套体系组成。“祖祭”的祭祀对象为一个宗族的共同祖先,宗祠与祖庙是其祭祀活动的核心场所,它是以家为基本单位并逐渐扩大的宗法共同体祭祀系统。而“社祭”则包含更大的范围,它往往是村、乡、镇等较小的行政单位空间内被少数人特定祭拜的本土信仰。祭祀的对象可以是地方传说中的人物,或是与地方职业或在地生产相关的功能性神灵,各村乡都有属于自己地方的社坛供村民举行祭祀活动。李氏将社祭的系统统称为“地域共同体祭祀”。①李天纲:《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第403、261、385、414页。至于更高层级的祭祀,其崇拜的对象往往是由官方赐敕承认而被广泛传播和设立的神灵。由此,李氏通过对江南地区各州、府、县、镇神祇信仰的考察划分了三个不同等级的体系:共享的全民坛庙、地方神祇系统、本土的社坛与宗祖庙。不过,他在对金泽镇进行田野调查时又发现,这些在地理空间上的区分以及在祭祀与信仰上的限制是有限的。金泽镇不仅拥有在地的宗祠祖庙以及“杨老爷”这样的地方代表性信仰,还拥有如“关帝”这样的全民共享的重要神祇。因此,金泽镇的特殊性就体现在:一方面,它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地方信仰的特点,体现出“由庙定界”的各地差异性;另一方面,江南地区交通的发达又使得“民众早就突破了社坛,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组织其区域性的信仰秩序”。②李天纲:《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第403、261、385、414页。到明代以后,江南地区的通商与传教活动,使得地方宗教信仰共同体的影响更进一步推向了全国乃至全球。在这个意义上,因信仰共享而造成的界限模糊并不意味着民间宗教在地方的普及形式是散乱无章的。
江南市镇的信仰系统在很大范围内与官方全民信仰体系共享,这是长期互动而逐渐形成的结果。李氏将这种自发的信仰系统的成型归纳为这样两种方式:一是地方礼请上一层级的神祇下乡立祠,以“分神”的方式分享官方的祠祀权力;二是地方根据自己的传统与需求自建私祀。对于金泽镇这一个案来说,前者对于地方的信仰影响力有限,虽然像“关帝”这样的神祇也被立庙供奉,但民众主要信奉的仍旧是一些未被纳入官方祀典之中的地方性神祇,这也可以从“烧十庙香”的次序排位上窥见一斑。因而李氏得出了一个结论:“金泽镇的祠祀体系基本上属于民间自己建立的私祀系统。”③李天纲:《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第403、261、385、414页。关于私祀形成的原因我们如今很难得到确切的答案,这是因为通常被官方认可的神祇,其庙宇或地方志中会留有碑刻和谕祭的文字资料,而民间私立的淫祀则大多依靠世代传说来保留其起源的可能性与神圣性。基于这一点,李氏对金泽镇民间私祀的组织性及系统性的考察更多集中于对具有“神圣天赋”的香头及其所领导的社、坛、会、道、门等各类民间机构的研究。在《金泽》的第七章中,李氏就提到了在金泽镇沿袭春秋两祭习俗发展而来的“廿八香讯”和“重阳香讯”中姚庄镇“先锋社”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个全部由男性组成的社会组织每年两次来到金泽镇的庙会进行“抢老爷”的宗教祭祀活动。他们传承了“扎肉提香”的会社传统,是“江南地区赛会传统的活化石”。④李天纲:《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第403、261、385、414页。与热衷于集中在一起共同组织和筹备大型祭祀活动的男性不同,李氏从男女性别与分工的角度发现,扮演香头的女性群体更多地负责日常祭祀、法事以及乡村信徒的事务,不会有意识地自发形成一个专门的民间宗教机构。对此,李氏的结论认为:“民间信仰(祭祀和法事)基本是女性在张罗,是一种弱组织;民间宗教(社、坛、会、道、门)大多是由男性来管理,是一种强组织。”①李天纲:《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第415、448页。
我们必须注意到,为了驳斥涂尔干的宗教教会论以及杨庆堃对中国宗教之分散性的论断,李氏在对金泽镇的田野材料进行选取与论证的过程中不断强调民间宗教与祭祀活动中的组织性与系统性特征。然而,这些材料与论证的结论之间往往产生矛盾。具体来说,“一朝阴官”的神祇系统在如今并未被严格遵守,民众自发形成的“烧十香庙”也没有被确定为一种统一的约定。如果信众各自之间烧香的顺序存在差异,那么关于这一传统背后存在组织性与系统性的逻辑就无法成立。至于空间秩序,周孔之道的宗族祠庙系统已经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损毁,更高一级的社坛寺庙则更多地体现出神祇共享的特征。因此,历史文献与传统中所形成的空间与神祇等级体系实际上并不能完全对应于金泽镇宗教祭祀生活的现状。最后,对于信众团体而言,除了“先锋社”这一仅存的例证以外,李氏对于男女香头在祭祀活动中的分工的讨论很难与组织或民间机构的强弱关系联系在一起。简言之,李氏更多地关注历史文献、地方传统中民间宗教的组织性与现实田野材料之间的相同点,而省略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分歧。
三、祭祀:汉人宗教的核心
在《金泽》一书的最后一章中,作为对涂尔干的回应,李氏以近乎相同的标题表达了自己在研究过程中的野心:构建和阐述汉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而这种基本形式就是由官方与民间共享的、继承于周孔之道的祭祀制度。为此,李氏主要从祭祀的对象与祭祀的方式这两个方面进行详述。
首先,针对祭祀的对象,李氏从儒教的“魂魄论”入手,以历史文献中的丧葬仪式与江南地区“做七”的民间风俗为研究材料,强调了汉人宗教生活中对于死后世界的构想。具体来说,汉人相信人死后为鬼,埋葬尸身是为了安抚鬼魂回归大地。这种丧葬方式与死后的祭拜都体现出生人与死人之间可以通过祭祀仪式进行沟通。但更加复杂的是,如果我们采用武雅士(Arthur P. Wolf)的划分方法,那么汉人宗教中生人死后的状态可能会导向三种不同的结果:祖先、鬼祟和神灵。②武雅士:《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彭泽安、邵铁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2-173页。李氏在这里注意到了鬼祟的部分。书中以金泽镇淫祀“三姑庙”为例,“庙里供的是一个常常作祟,使人患病的女鬼”。③李天纲:《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第415、448页。根据信徒的说法与地方传说,陈三姑娘因生前犯淫而被父亲沉溺而亡,因此,她是一个被排除在宗庙范畴外的、无法配享祭品的厉鬼亡魂。与祭祀正神祈求庇荫不同的是,江南地区信众祭祀陈三姑娘的目的是对她进行安抚,以避免灾祸降临自身。李氏由此发现了江南民间信仰的另一特征:“神鬼相分”。也就是说,人们虽然对鬼神都进行祭祀,但祭祀的目的却不相同,并且在一些大型宗教活动中依靠正神来对鬼祟进行压制。然而,李氏却未能更加深入地对鬼祟与祖先就死后异同的问题进行探讨。在这一点上,武雅士针对“鬼—祖先—神”提出的“陌生人—亲人—官僚”的模型则更加具体。通过对三峡镇灶神、土地公和城隍等地方神灵的田野研究,武雅士发现,除了被特别神化的个人,其他的神灵大多都具有官僚属性,其职能或是监管家族,或是管理一个社区的纠纷与灾祸。这种行政官僚体制在神灵系统中的复刻是中国宗教现象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①Vincent Goosaert, Bureaucratie et Salut: Devenir un Dieu en Chine, Geneva: Labor et Fides, 2017.与受到共同祭拜的神灵不同,鬼与祖先处于类别划分的另一端。武雅士认为两者之间的差别十分模糊:“一个特别的灵物究竟被看作鬼还是祖先,取决于特定人的观点,一个人的祖先可能是另一个人的鬼。”②武雅士:《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第151页。这种奠基于庞大而复杂的宗族关系之上的对祖先与鬼的供奉,一方面表明了亲人血统延续与子嗣祭祀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显示族人在苛刻的继承制度下对无人祭祀的陌生亡灵的宗教处理。
其次,在祭祀方式的部分,李氏主要论述了在金泽镇民间祭祀活动中混合出现的血食、素食和香这三种类型的祭品及其供奉的意义。金泽镇的民间信仰具有共享特征,儒、道、佛三教的神祇都在这里立庙立祠,然而,其祭祀方式却各有不同,具体体现在祭品的选择和使用方式上:“当代的佛教、道教……都是‘素祭’,杨震庙却是‘血食’。”③李天纲:《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第458页。血食或肉食在儒教传统中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地位,诸如太牢、少牢和馈食这样一些在儒教经典中根据祭祀的等级进行划分的不同种类的祭品无一例外都是由动物组成。这一方面是因为从周代到两汉的饮食结构中,谷物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主要食物,价格昂贵的肉类只有相对富贵的阶层能够消费;另一方面,儒教祭祀仪式中强调用气味来吸引和供奉神灵,而牺牲中的血与内脏就是“气”最为旺盛的部分。④胡司德:《早期中国的食物、祭祀和圣贤》,刘丰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6-29页。这些被用来与神灵沟通而具有神圣性的肉食,也在政治范畴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周天子在祭祀后对胙肉的分配就对应于中央权能与地方诸侯之间具有宗教特质的政治联系。⑤Jean Levi, The Rite, the Norm and the Dao: Philosophy of Sacrifice and Transcendence of Power in Ancient China, in John Lagerwey and Marc Kalinowski (ed.), Early Chinese Religion, Leiden: Brill, 2009, pp.645-652.与此相对,道教和佛教则拥有明确的禁杀、食素的戒律规定。李氏在这一部分的着墨不多,仅归因于宗教的教义不同,而没有针对儒教素祭与道教、佛教素祭之间的异同点进行深入讨论。事实上,儒教祭祀中存在以素食作为祭品的情况,一方面可能是出于现实经济层面的考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谷物的馨香之气同样能够达到沟通神灵的效果。正是基于这一点,道教和佛教在不同程度上接纳了由素食——谷物、花果、香料、酒等——引发馨香之气,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焚香仪式。与此同时,道教与佛教还在一定程度上突出和变革了儒教经典中在丧葬和祭祀仪轨中关于饮食斋戒的禁忌。其中,道教的“天师道”以维持和延续净化为目的把儒教“变食”与“禁五荤”的规定更加明确地表达为“天道恶杀而好生”的食素最佳论。⑥Vincent Goosaert, L’interdit du Boeuf en Chine: Agriculture, Ethique et Sacrifice,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2005, pp.37-57.
最后,就祭祀的意义问题,李氏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影响,他着重强调了祭祀的目的是通过祭品这个中介物以及共餐的方式,达到人与神的共享、共融状态。然而,祭祀意义在理论范畴内的探讨进行已久,祭祀宴席上通过祭品共享达成人神沟通的理论只是多种观点中的其中一种,而除此以外,围绕祭祀的目的与意义,还有诸如马塞尔·莫斯之“礼物论”、①Henri Hubert, Marcel Mauss, Essai sur la Nature et la Fonction du Sacrifice, Année Sociologique, 1899, 2, pp.29-138.雷内·基拉尔之“暴力论”②Réne Girard, La Violence et le Sacré, Paris: Bernard Grasset, 1972, pp.22-43.和乔治·巴塔耶之“耗费论”③Georges Bataille, Œuvres Complètes, Paris: Gallimard, 1976, 7, pp.279-311.等理论模型,并且已有学者利用这些不同的理论对中国宗教祭祀进行了分析和研究。④Mark Edward Lewis, 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李氏没有采纳其他的理论来阐释汉人祭祀,可能是由于他对祭祀在达成现实功利目的的成效方面保持怀疑,因而更加倾向于认同古代经典中儒生们理性化的解读,强调祭祀在精神层面上的人神沟通功能。也正是由于李氏运用理论模型的单一,生发出另一个问题,即理论本身与田野资料的解读之间产生了矛盾。在对金泽镇杨震庙的祭祀描述中,李氏提到:“远道而来的信徒们从家乡带煮过的整个猪头、整条肉排来祭祀。回家后,全家、全族重烹再食这些回锅肉……(食用的目的是为了)沾染福气,不生病。”⑤李天纲:《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第465页。这个案例本身有两个细节被李氏忽略了。其一,信众们与祭祀神灵“杨老爷”并没有共餐。这是因为,信徒们是在祭祀活动结束以后回到家里才食用这些祭品的,并且这些祭品经过了“重烹”这一“返俗”(profanatio)的过程。这与古罗马公共献祭的仪轨十分类似,在神接受祭品之后(litatio),牺牲的内脏(exta)属于诸神,而剩余的肉则以“返俗”的方式回归到人类的财产范畴之中。⑥Nicole Belayche, Religion et Consommation de la Viande dans le Monde Romain: Des Réalités Voilées, Food and History, 2007, 5,pp.29-43.其二,信众们明确地表达出食用回锅祭肉的功利性目的,也就是说,他们正是因为相信祭祀行为本身的功利性功能才进行了这样的重食仪式。
李氏从民间祭祀的角度出发,以小小的金泽镇为轴心,辐射了整个江南民间宗教信仰的圈层,并以此概括整个中国乃至近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围绕宗教与民间信仰的相关研究。除了在地理空间的层面进行探索以外,本书宏大的论述与分析还旨在构建一套以祭祀为核心的汉人宗教体系。严格来说,李氏把握住了祭祀这个天然具有系统性与组织性的宗教实践,通过祭祀体系来重新思考中国三教合一与西方基督教中心主义两种语境下宗教与民间宗教的概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理论模型构建的需要与祭祀实践本身的复杂性使得李氏无法在《金泽》这一本书中对所有可能的问题逐一进行解答,也无法全然专注于金泽镇庞杂多样的田野材料中。正如他在绪论里对中国宗教研究现状的反思一样,《金泽》或许就是他从神圣性角度直接研究信仰及其相关内容的一次开创性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