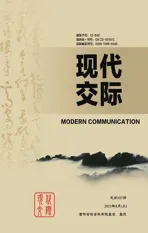《红高粱》英译本的语篇衔接研究
2021-11-25赵兰
赵 兰
(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8)
随着功能翻译学派的兴起和发展,翻译研究也逐渐从以“信”为本重点强调文本对等的传统翻译论发展到注重运用语篇分析理论审视翻译成果的阶段。李运兴将从语篇分析的视角来考察翻译活动称为“自成体系的体现特定交际过程的源语语篇和译语语篇为适应某一翻译情境而出现的对应关系”[1]。
韩礼德和哈桑在Cohesion in English一书中提出,最好把语篇看作语义单位(semantic unit),即不是形式而是意义单位。衔接是语篇的重要特征之一。[2]他们认为,衔接存在于语篇内部,并且维持着语篇的意义关系,将衔接定义为“将语句聚合在一起的语法及词汇手段的统称,是语篇表层的可见语言现象”[3]。由此可见,衔接充当语篇形成的纽带,衔接手段运用得恰当与否,影响着译作的质量和读者对语篇信息的接收、认可。
一、原著和译作简介
本文选取的是作家莫言创作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及葛浩文的英译本。该小说主要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我爷爷”余占鳌在山东高密东北乡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人生故事及与“我奶奶”戴凤莲之间的爱情故事,表现了高密人民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顽强生命力与血性以及保家卫国的爱国之情。
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从事翻译工作三十余年,共翻译了五十多部中国作家的小说。他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增删改写,从而为译作增添了灵活性和创新性,这使其译介的作品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也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高中国文学及作家的知名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目前也被公认为英语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因此,由他翻译的《红高粱》(Red Sorghum)在海外的接受度较高。
二、衔接手段的体现和处理方法
韩礼德和哈桑在Cohesion in English 一书中将衔接手段分为语法衔接和词汇衔接,其中语法衔接包括:照应、代替、省略和连接词;词汇衔接分为重复和搭配。本文将从《红高粱》英译本中选取相关语料来分析差异及相应的处理方法。
(一)照应
1.人称照应
人称照应是一种用人称代词复指上文(anaphoric reference)或预指下文(cataphoric reference)出现的名词的衔接手段。汉英人称代词都可分为第一人称代词、第二人称代词、第三人称代词、反身代词、关系代词及其他人称代词,汉英的这些人称代词在功能上没有太大差别,但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这种非对应的关系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汉语中存在第三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通常由第三人称代词+数词/“们”构成,如“他/她/它们两个”,“他/她/它(们)俩/三个”,而英语用“they、their、them”来表示第三人称代词复数。其次,汉语中的反身代词“自己”用法多(照应、强调、泛指),分布自由(可出现在主语、宾语、附加语、主语补足语、定语等位置上),而且既可以受到本管辖语域内先行语的约束,也可以跨过本管辖语域受到长距离约束。相较之,英语的反身代词在用法、分布、和指称上则受到较大的限制。[4]另外,汉语中的其他人称代词,如“大家”“人家”都是第三人称用作泛指,而在英语中需要根据语境来选用人称代词。
例1a:母亲安慰着小舅舅,自己也忍不住抽泣起来,姐弟二人,紧紧搂抱着,哭成了一团。[5]166
例1b:Mother,who was trying to comfort her baby brother,started to sob,too.They hugged each other tightly as their sobs and tears merged.[6]196
在这个例子中“姐弟二人”是复指“母亲和小舅舅”且是第三人称的复数,在译文中将其直译为“they”来复指上文的“mother”和“her baby brother”。
例2a:奶奶三十多年的历史,正由她自己写着最后的一笔。[5]75
例2b:She is writing the final page of her thirty-year history.[6]63
此例原文中的“她自己”回指的是“奶奶”,在翻译时不能采用与英语对应的表达“herself”,而是根据其充当的语法角色将其转换为“she”。
2.指示照应
指示照应是指说话者通过指明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远近来确定所指对象。在英语中常常运用“the”“this”“that”“these”“those”“here”或“there”等词构成上下文的衔接。在这一点上汉语和英语存在着一些差异。首先,汉语中没有冠词。汉语的特指通常通过“这”或“那”放在所指的名词前;而英语的特指通过“the+名词”就可以实现。其次,汉语中的“这”和“那”与英语中的“this”和“that”在所指的时空概念上没有太大的差异,近指(“这”“this”),远指(“那”“that”),但是在实际使用中,英汉两种语言在指示代词的选择上会不同程度地受心理因素的影响。[7]这使得汉语中的“这”“那”不能和英语中的“this”“that”相照应。
例3a:那人把奶奶放到地上,奶奶软得像面条一样,眯着羊羔般的眼睛。那人撕掉蒙面黑布,显出了真相。[5]62
例3b:The man placed Grandma on the ground,where he lay a limp as a ribbon of dough,her eyes narrowed like those of a lamb.He ripped away the black mask,revealing his face to her.[6]74
在本例中,原文的“那人”表示特指;因此,在翻译时,用表特指的“the”来与“那”对应,用“the man”来对应“那人”。
例4a:那男人又萎萎缩缩地坐到凳子上。这一夜,奶奶始终未放下手中的剪刀,那个扁头男人也始终未离开方凳。[5]60
例4b:She glared intently at the man,who recoiled and curled up on the stool again.Grandma didn't set down her scissors once that night,nor did the man climb down from his stool.[6]72
在这个例子中,原文中的“这”依然用英语中的“that”而非“this”来对应。这样处理的原因在于,原文想通过“这”这一表示较近时间和空间的指示代词来营造故事是“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从而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使读者拥有亲眼见证故事发生的感觉。而译文用“that”这一表示远指的指示代词来表示故事已经发生了,并且表述的是叙述者“我”提到的事;因此,若原文的指示代词包含一定的修辞效果,翻译时要着重考虑译入语的表达习惯,从而进行转化。
(二)替代
替代包括名词性替代、动词性替代和分句性替代。名词性替代是指用名词性替代词来替代一个名词词组或中心词,英语中的名词性替代词通常是“one”“ones”“the same”“so”,汉语中通常用“的”“者”“同样(的)”“一样(的)”。动词性替代是指用动词性替代词来替代句子中重复出现的动词,英语中的动词性代动词包括代动词“do”,复合代动词“do so/that/this/the same”及替代句型“so+do+主语”,汉语通常用“干”“来”“弄”“搞”。英语中的分句性替代包括替代词“so”或“not”来替代充当宾语的that从句及用“if so”或“if not”来替代条件从句,而汉语一般用“(不)这样”“(不)这么”“不然”“要不”。汉语中存在替代衔接这一衔接手段,但由于其重意合,而英语与之相反,常使用替代来避免重复使行文简洁、有力。翻译时,此方面的差异在处理衔接时不能被忽视。
例5a:奶奶又把另一个碗甩出去,这个碗碰到墙壁上,在下落时破为双片。[5]76
例5b:She picked up another bowl and heaved it;this one hit the wall and fell to the floor in two pieces.[6]92
在例子中,原文中的“碗”是重复出现的,翻译时,为了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用名词性替代词“one”来代替前文的“bowl”。
例6a:吹鼓手们从腰里摸出外曾祖父赏给他们的一串串铜钱,扔到那人脚前。轿夫放下轿子,也把新得的铜钱掏出,扔下。[5]41
例6b:The musicians reached into their belts,took out the strings of copper coins Great-Granddad had given them,and tossed these at the man's feet.The bearers lowered the sedan chair to the ground,took out their copper coins,and did the same.[6]50
在上面的例子中,原文中重复出现的“扔下铜钱”这一动作,在译文中用英语的复合代动词“did the same”来对应。
(三)省略
省略主要是指上下文已提到的、交际双方可以填补的、但不在特定地方出现的成分。[8]省略这一衔接手段汉语中常用,因为汉语重意合,语义的连贯和语境的映衬,使隐含的逻辑关系贯穿全句。而英语是形合语;因此,在翻译汉语的省略句时,要将其省略的内容用符合英语语法和表达习惯的词语补充或添加上。
例7a:余占鳌躺在劈柴上,()蓬头垢面,()破衣烂衫,()像个叫花子一样,用两只冰冷的眼睛盯着我奶奶。[5]130
例7b:From his firewood perch,Yu Zhan'ao,who looked liked a dirty-faced,ragged beggar,stared at Grandma with a cold glint in his eyes.[6]153
在本例中,原文的()中虽省略了主语“余占鳌”使“蓬头垢面”“破衣烂衫”“像个叫花子一样”变成了形式上的无主句,但不影响这句话语义的传递。翻译这句话时,将原句省略的主语用“who”这一关系代词补上,将三个修饰的短语处理为并列成分进行翻译。
例8a:“司令,要是日本人奸淫我姐妹,当不当杀?”任副官问。
“杀!”余司令回答。[5]48
例8b:"Commander,if a Japanese raped my sister,should he be shot?"
"Of course!()"Commander Yu replied.[6]58
在本例中,原文中的画线的“杀”是“淫奸我姐妹的日本人当杀”的省略表达,是一个对上文疑问句的肯定回答,在明晰这一省略用法的作用后,在翻译时将“杀”处理为既符合原文语义,又符合英语语法要求的“of course!”。
三、结语
本文对中篇小说《红高粱》英译本中衔接手段进行了分析,重点讨论了英汉两种语言在照应、替代、省略等语法衔接手段中的差异,并归纳出处理此方面的差异时主要采用的方法为增添、删除和转换,从而使译文在再现原文内容时,也能顺应译入语语篇的衔接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