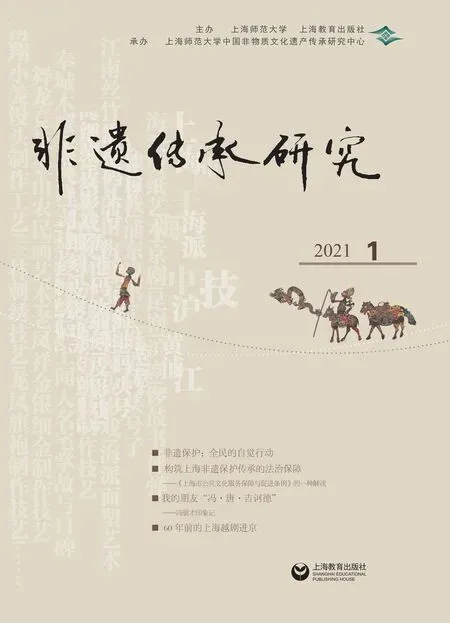中小学“非遗进校园”课程的研究现状与反思
2021-11-25林加
林 加
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非遗的传承离不开非遗传承人,他们担负着“传”和“承”的双重任务,他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传承者和传播者。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由官方认证的传承人应该在什么空间传承和传播非遗?笔者认为,学校应当是非遗传承、传播的重要空间,学生群体应当成为非遗传承和传播的参与力量。2011 年,我国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其中第三十四条规定:“学校应当按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2014年,教育部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指出要加强对学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将书法、戏曲、中华传统节日和习俗、家乡生活习俗、传统礼仪、经典民间艺术、各民族艺术等与非遗有关的内容纳入学校教育,强调要联合非遗传承人进行相关师资培养,建设人才队伍。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要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进一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要推进戏曲、书法、高雅艺术、传统体育等进校园,让传统文化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始终。2020 年,教育部在关于“非遗进校园”工作常态化建议的答复中提出,“非遗进校园”工作要常态化、持续化。
在政策的引导下,非遗传承人进入高校开设工作室,开设课程,举办活动,许多专家学者参与非遗进高校的讨论,比如丁永详、马知遥和徐艺乙等在论文中讨论非遗进高校的意义、方法和途径等。中小学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非遗进校园”活动,相关实践案例的研究十分丰富。这些研究多从“非遗以何种形式进校园,进入校园的内容是哪些,进入校园的目标和依据是什么,进入校园的效果怎么样”等角度进行讨论,这其实是将“非遗进校园”作为课程或者课程活动来进行研究。本文从公共民俗学的角度出发,从课程编制的视角,综述近年来中小学“非遗进校园”的相关研究,讨论“非遗进校园”的目标、内容、形式和评价等,并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考。
近十五年来,国内关于中小学“非遗进校园”的研究主要关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形式和课程评价四个方面。其中在课程目标方面,主要讨论了“非遗进校园”课程目标体系的建设,指出要从“非遗的保护传承”和“学生能力培养”两个维度出发,结合学生不同年龄层次的特点,设计目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在课程内容和形式方面,集中关注中小学非遗教育的实践案例,进而探讨课程内容框架的设计,探索更多适合非遗的课程形式。在课程评价方面,关注课程的成果和效果,并尝试选取一些角度来测试教学效果,探索建设评价体系的可能性。总的来说,中小学“非遗进校园”的相关研究对课程内容和形式的关注度高,研究成果多,对课程目标和评价的研究关注少。这使得当下“非遗进校园”缺乏可落地、成体系的课程目标引导,导致课程评价标准制定无依据,缺少可操作、有效果的课程评价体系,进而导致对课程形式的体系化认知不足,过度关注非遗校本课程而忽略对其他课程形式的研究,导致不适合开设校本课程的非遗项目进校困难;课程内容框架不均衡,体现为艺体类和岁时节日类非遗实践案例多、研究关注多,传统礼仪等实践案例少、研究关注少。所以,中小学“非遗进校园”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课程体系建设的研究,尤其需要关注课程目标和评价体系的研究。
一、课程目标相关的研究
2014 年,教育部颁布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评价、教学保障等层面提出了在中小学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指导意见。《纲要》指出,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教学内容要以汉字、书法、古诗文与经典、爱国仁人志士故事、中华历史、中华传统节日和习俗、家乡生活习俗、传统礼仪、经典民间艺术、各民族艺术、生活习惯与行为规范、传统体育活动等为主要内容。这些内容都直接或者间接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联。2020 年,教育部在关于“非遗进校园”工作常态化建议的答复中,以校园非遗传承基地、师资队伍培训、课程教育体系和组织保障与支持等内容为重点,介绍了近年来“非遗进校园”的工作,提出了教育部下一步的工作计划,这就是“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顶层设计,丰富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形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持续推动‘非遗进校园’常态化、规范 化”。
谭宏立足《纲要》设计了我国非遗教育传承的教学目标体系。他指出:第一,在幼儿阶段进行非遗的启蒙教育,培养幼儿成为非遗的热爱者;在少年阶段进行非遗的认知教育,培养少年成为非遗的认同者;在青年阶段进行非遗的能力教育,培养青年成为非遗的传承者。第二,中小学非遗教育的目标体系既要关注教育维度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又要关注文化传承维度学生在非遗传承保护工作中的角色转变。[1]
彭兆荣、路芳梳理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开展非遗教育的经验,提出了我国建设非遗教育体系的必要性,指出非遗教育体系需要一个达成共识的国家标准和程序。[2]张莹莹在博士论文中较为细致地讨论了非遗如何结合国家颁布的美术等相关课程标准来建设课程资源系统。[3]此外,还有诸多硕士、博士论文讨论如何在国家标准的指导下确定非遗相关课程的标准。但是总体而言,专门讨论中小学“非遗进校园”的课程目标体系设计的论文比较少,民俗学者的研究参与也很少。缺少成体系、有序列具体内容的研究。中小学“非遗进校园”需要体系化的课程目标,这个课程目标体系既要关注课程对非遗传承保护的意义,又要关注对校园教育尤其是学生能力培养的意义。这就需要研究者从公共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相关的民俗学理论和课程编制等教育学的理论和方法角度出发,对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和教学实践案例等进行进一步研究和分析,以完善目标体系的建设。
二、课程内容相关的研究
2005 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发布,制定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保护体系。2006 年国家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下简称“国家级非遗名录”),确立了民间文学、传统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十个方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框架。截止到2018 年,我国一共公布了五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本文将结合国家级非遗名录的内容框架,梳理近年来“非遗进校园”的主要课程内容。
本文按照研究论文的数量,将中小学“非遗进校园”的课程内容分为三类:艺体类非遗课程、岁时节日和民间文学非遗课程、传统手工技艺和传统礼仪相关的非遗课程。
1.艺体类非遗项目是“非遗进校园”课程内容的主流
艺体类非遗是指各级非遗名录中的有关传统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的项目。研究艺体类非遗进校园的论文数量多,探讨细致。这些论文集中讨论了艺体类非遗项目与校园必修的音乐、美术、体育、劳技等课程结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从国家政策、国家课程标准和五育并举的角度论述艺体类非遗项目进校园的必要性;从学科知识和学科能力培养以及实践案例的角度阐述结合的可能性。同时也有许多研究指出,当下艺体类非遗进校园缺乏相应的理论体系,如非遗知识体系、非遗教育理论体系等。李勤总结了当下美术课程中渗透非遗内容的实践状况,指出当下美术非遗特色课程的零碎状态和不可复制性,介绍了以软陶为载体的特色课程的开发,关注非遗课程与美术课程标准、美育和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关系,设计了相应的教学活动和评价体系。[4]丛密林、邓星华讨论了体育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与进入中小学实践传承的路径与方法,指出了中小学进行体育文化遗产教育需要构建理论体系,概括了在中小学开展体育文化遗产教育对教育和遗产保护的意义。[5]
2.岁时节日和民间文学相关的非遗项目广受民俗学等领域的相关研究者关注
岁时节日类非遗项目是指各级非遗名录中“民俗”类别下的中国各民族的传统节日、节气相关的内容。这些研究内容主要讨论岁时节日类非遗项目对学生德育、劳动教育和学科知识能力教育的重要意义,以及岁时节日类非遗项目对校园活动和综合实践的开展、校园文化的建设以及校本课程的开发的意义与注意事项。萧放在研究中系统地阐释了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意义,指出传统节日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重要性。[6]这为传统节日文化进入基础教育提供了理论保障和智力支持。王枬、黎天业立足学校校本课程建设,详细地界定了传统节日课程的概念,论述了在基础教育中推进传统节日课程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从传统节日课程的目标、内容、类型和学习方式等角度系统地介绍了在基础教育中如何开展传统节日的教育。[7]高扬元、米满宁立足学校的德育,阐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资源的开发、挖掘和整理,有助于校园德育的开展。[8]成雪君、卢群赞提出将节气文化与中小学劳动教育结合,丰富学校劳动教育课程的内容和形式。[9]此外,还有大量硕士、博士论文围绕各民族传统节日和节气文化进校园展开研究,涉及语文、生物、历史、美术等基础科目。陈琳讨论了民间故事与语文教学的联系,并从语文教学的实践性和综合性角度论述了民间故事进入语文教学的可能性,还从语文教师的角度简要论述了将民间文学作为课程文化资源的意义。[10]当然,还有许多学位论文讨论如何将民间文学作为资源进入中小学教育。
3.传统手工技艺、传统礼仪等非遗项目成为“非遗进校园”课程内容的研究案例少
这类非遗项目与学校劳动教育、美育、德育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尽管实践层面的案例较少,实践效果一般,但是也有研究者关注。齐皓等在论文中详细介绍了陶艺教育对中小学素质教育的意义,总结了学校对陶艺教育的需求,并从教学资源、教材、课程形式等角度提出了开展中小学陶艺教育的建议。[11]傅小芳、丁宇红从劳动课程的政策和实施保障、课程体系、师资队伍三大方面介绍了苏州中小学劳动教育课程与非遗结合的情况。论文详细介绍了课程体系,并列举了苏州将刺绣、金砖制作工艺、茶艺等非遗内容融入劳动课程,形成区域劳动教育的特色内容。[12]金东海、关琳介绍了当下学校礼仪教育面临的问题,指出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当下的冲击,建议在学习西方礼仪时要关注传统礼仪文化精髓,保留传统礼仪文化遗产,构建身份认同,避免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迷失。[13]
4.小结
综合搜集的研究材料来看,艺体类非遗课程的研究数量多,多以实践案例为中心展开研究,研究者主要是一线的教育实践者,多为学校的音乐、体育、美术教师和相关教育专业的硕士、博士。岁时节日和民间文学类非遗课程研究数量较多,多不以实践案例为中心,研究者主要从事民俗学相关的研究,相关课程案例主要是为其民俗学相关研究提供支撑材料。传统手工艺和传统礼仪相关的非遗课程研究数量少,实践案例也少。所以目前中小学“非遗进校园”课程的内容体系不均衡,反映出目前大部分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工作的研究者和实践者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知识,具体表现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我国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关非遗项目的类别等相关内容的了解不足或不够深入。这也就使得“非遗进校园”课程内容的选择往往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并没有通过系统的设计和深度的考量来制订均衡的课程内容框架,不利于在校园语境下开展全面的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
三、课程形式相关的研究
就本文搜集的研究材料来看,“非遗进校园”的课程形式基本分为三种:非遗校本课、融入非遗资源的校园各学科课程、非遗实践活动课。
非遗校本课是学校借助非遗资源开设具有特色的校园选修课程形式。刘世军指出,在开发非遗校本课程时,要科学设置课程,系统编写教材,保障校本课程能落地、有效果。[14]杨向奎等人在研究中介绍了如何利用西和乞巧节结合语文课程学习的目标,设计非遗校本课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15]吴永平以具体的案例讨论了如何将京剧文化、地方或族群文化等编制成非遗校本课程。他认为非遗校本课需要制定相应的学习目标,编制合适的学习内容,让学生在学习非遗的同时,达到德育、美育等教学目标。[16]
融入非遗资源的校园各学科课程是学校借助非遗资源来帮助校内学科教学取得更好教学效果的课程形式,可以让非遗资源有机融入校内学科教学。张思认为非遗资源是一种独特的学科教学资源,他讨论了校内的美术、语文、地理等学科如何借助非遗资源,在完成学科自身教学目标的同时拓展学生的学习视野。[17]
非遗实践活动课是指利用非遗资源进行班级和校级活动、组织学生社团、开展校外综合实践等的课程形式。王艳娟、尤吉等人讨论了将岁时节日类非遗作为重要资源,开展学校德育美育活动和校园文化建设,指出“非遗进校园”在德育、美育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教育方面具有双重意义。[18][19]此外,也有学校借助非遗资源创办学生社团,带领学生到校外进行非遗相关的综合社会实践。
“非遗进校园”的三种基本课程形式构成了“非遗进校园”的课程形式体系:德育层次为主的实践活动课,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非遗校本课和智育层次为主的融入非遗资源的校园学科课程。这种体系化的“非遗进校园”课程形式,有助于非遗教育的课程形式在学校教育教学中进行较为全面的覆盖,使“非遗进校园”取得更好的效果。但是就本文搜集的研究材料来看,绝大多数学校在开展“非遗进校园”时并没有成体系地设计非遗教育的各种课程形式,往往只有其中一两种形式。
四、课程评价体系的基本缺失
各类非遗项目借助不同形式进入校园,如何检测是否实现了相关的课程目标?教学是否有效果?这就需要讨论“非遗进校园”的课程评价体系。《纲要》明确指出:“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评价和督导机制。研究制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评价标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价指标体系的重要内容。”2019 年,中国教育学会制定并发布《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指导标准》(以下简称《指导标准》),在第四部分“实施建议”中,从评价目的、评价原则、评价方式与方法三个角度为建构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评价标准给出了建议,强调评价要以“中小学传统文化课程内容为中心”,评价要坚持“兴趣导向、持续推进、全面发展”三个原则,评价要关注“主体的多元化、方法的多样化和过程的动态化”,为中小学传统文化课程评价体系和标准的建设提供了方向性建议,为后续研究和制定具体的评价框架和内容奠定了基础。
邓旭等人基于成都市蜀龙学校传统文化课程的实践个案,提出了“基础与拓展合一”的评价体系。他们将蜀龙学校的传统文化课程评价体系分成“基础课程评价”和“拓展课程评价”两个板块,既设计了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又设计了学校职能部门对教师的评价。从“学习投入过程与表现、个性品质发展以及学业检测成绩等”来评价学生的基础课程,从“学习态度、课堂表现、学习成果以及学生反思”来评价学生的拓展课程,给不同的评价项目设定了不同的分值,以综合量化打分和质性评价来综合评定。[20]这样的评价体系关注到多元主体、多维内容和多样评价方式,但是在评价内容框架的设置上,对传统文化内容本身的关注不够,也就是说并没有关注传统文化教育是否达到了认识和理解传统文化的效果,是否对文化传承起到作用。曲雪梅在其研究中则充分考虑了区域推进“非遗进校园”时,如何设计评价标准和体系来检测教育教学的有效性。她在研究中将评价体系分为“课程的评价、实施的评价和效果的评价”,[21]这其实是在时间线的推进上对“非遗进校园”课程的开发与设计、实施和教学成果进行评价。她给每一个阶段的评价设计了简要的内容,并强调最终的“效果的评价”一定要坚持多元评价标准。曲雪梅的研究从课程的视角对区域推进“非遗进校园”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设计和论述,尤其是对课程内容和课程实施的框架设计比较全面。但是在课程目标和课程评价上,似乎又仅仅只关注了“非遗进校园”对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意义,忽略了对学生能力发展与培养的意义。此外,在众多“非遗进校园”的研究文献中,大多数并没有进行评价体系的讨论与设计,在一些专门讨论书法、京剧等某一类艺术类“非遗进校园”的硕博士论文中会提及一些评价,但是大多缺少对评价体系的探讨和设计。
五、综述、反思与建议
综合前文,从课程编制的视角出发,我们认为目前中小学“非遗进校园”存在这些问 题:
第一,课程目标体系缺少研究和建构,导致课程缺少方向,无法在文化传承与校园教育上获得双赢,影响课程的持续性。
第二,课程内容架构缺少总体设计,看似百花齐放,实则集中在艺体类非遗项目,内容相对单一,影响课程的丰富性。
第三,课程形式的体系不健全,形式上过于依赖非遗校本课,导致不适合校本课的项目难以入校,也无法充分发挥非遗在中小学的教育作用。
第四,课程评价体系的缺失导致课程有效性不可测且不可知,影响课程的持续性和常态化。
对“非遗进校园”的“校园”的理解不全面,是产生这些问题的核心原因。
“非遗进校园”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内容进入校园。这个“校园”不单单指物理空间,更是指校园语境,即当非遗进入校园这个物理空间时,要考虑非遗与校园内的各个主体之间的互动,考虑非遗与校园内整个教学生态的有机联系。“非遗进校园”需要课程编制的视角,以课程或者课程活动的角色进入中小学校园。它绝不仅仅是一场文化展演或者文化体验。所以在中小学开展“非遗进校园”,需要充分讨论和研究“课程目标体系、课程内容框架、课程形式体系和课程评价体系”的相关内容。我们建 议:
第一,中小学“非遗进校园”的课程目标体系需要关注“非遗文化保护传承”和“学生能力培养”两个基本维度,民俗学者和教育学者应当积极主动地参与“非遗进校园”课程目标体系的建设,设计符合国家政策导向和各地校园实情的总体目标框架,对框架下的细则提出方向性建议,并积极参与指导具体内容的制定。
第二,做好非遗名录中非遗项目向“非遗进校园”课程内容的转化工作,做好“非遗进校园”课程内容资源库的建设和研究,对专业性较强的传统礼仪等内容进行普及材料编写,为各地开展非遗各类教材的编写提供支持和建议,促进非遗不同类别的项目均衡地进入中小学校园,避免艺体类非遗过多,而其他类别不足的现象。
第三,进一步探索并完善“非遗进校园”的课程形式体系,在做好非遗校本课建设的同时,充分发挥实践活动课的优势,将学生带往非遗传承基地、实践基地,进行传统手工技艺等难以进入校园物理空间的非遗项目的学习。进入非遗传承基地学习本身符合教育部等国家相关部门的规定,这些校外学习空间是校园教育生态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校外非遗基地学习非遗,也是“非遗进校园”的重要形式。加大对非遗资源融入校内学科课程的研究,促进非遗与各学科的有机融合,真正做到《纲要》呼吁的学科课程全覆盖,将教育内容体现到德育、语文、历史、体育、艺术等主要课程中去。只有让非遗进入学科教育教学,才是真正进入家长、学生和教师所认可的校园,才能真正做到非遗传承与校园教育共赢。
第四,教育学和民俗学相关研究者应当关注“非遗进校园”的课程评价标准的建设,在现有的“戏曲进校园”“书法进校园”等框架相对完备的单项非遗进校园的基础上,拟定出“非遗进校园”整体的评价标准基本框架,结合各地的“非遗进校园”教育实践完善和验证评价标准的内容,让“非遗进校园”的效果可测、可知。当然,“非遗进校园”课程体系的研究、设计和实践是一项庞大的任务,需要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但是只要我们坚持研究和实践,最终一定可以让非遗真正进入校园,进入学生的大脑和心灵,达到文化传承和校园教育双赢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