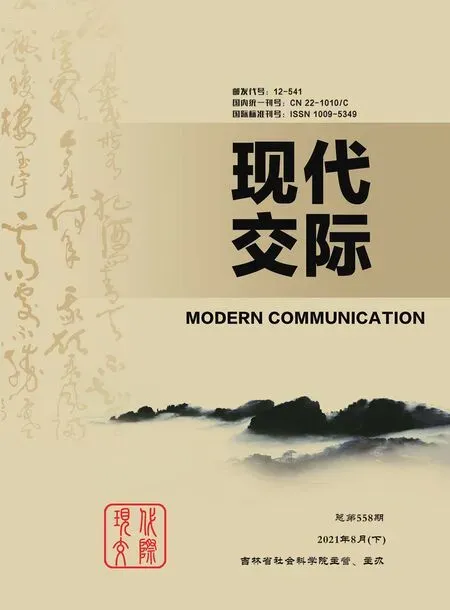自由始发、困境和归宿
——基于弗洛姆自由思想
2021-11-23张涵婷
张涵婷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 安阳 455000)
埃里希·弗洛姆认为人类的存在和自由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尤其在近代人类历史文明中,人类始终在追求真正的自由,并将摆脱政治、经济等外在束缚作为争取自由的核心。而在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明都有了长足进步,人类也迈进了更加民主化、独立化、个体化的阶段,但人们没能享受真正的自由,甚至出现了孤独、恐惧等逃避自由的心理状态,这点引人深思。自由,究竟缘何成为人们逃避的对象,这俨然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经济问题,其在蕴含人文关怀价值的同时,究竟在人的心理层面上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一、自由的始发——前个体化阶段
在个人生命的历史中,自由是人存在的特征。人把自身看作独立的存在物,在对自身的认识和评价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修正其对自由含义的理解。最初,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浑然一体,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个人身心功能的发展,人们将逐渐意识到自身与自然、社会、他人相分离。虽然人对“自己是独立的个体”有部分的意识,但仍和自然界、社会有密切的联系,仍将自身看作周围世界的一部分,在这里将这一时期称作“前个体化阶段”。
(一)家庭组织中的自由
从生物学角度来说,人从出生之后就成了一个崭新的个体,与母亲的身体处于相分离的状态。但从功能层面上来说,婴孩与母亲的关系并没有达到彻底的分离阶段,他们仍需要母亲的照料和养护,即儿童与母亲是一体的。家庭组织给孩童提供了安全的保护,以及周围世界相联系的基本条件。但家庭教育和要求并不妨碍和压抑孩童对外界产生兴趣,他们虽然意识到与周围世界、人相异,却并没有明确体会到“别人”与自己的真正区别。
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曾经提出三个重要概念,即“本我”“自我”和“超我”,分别代表了本能的我、现实的我和理想的我。人们在儿童时期总是与父母、家庭维持着密切的情感联系,自我才刚刚形成,并随个人身心的发展而得到不断加强,但并没有强固到能够指挥本我的程度,此时儿童就需要通过借助父母、家庭的力量来压制本我的冲动,父母所展现出的权威在儿童看来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不管是对于父母家庭的教育,还是其他权威类似的刺激,儿童都足以将其纳入自己的“宇宙”,这个宇宙是孩童生命的一部分,服从于它与两个个人完全分离时的那种服从状态有着本质差别。换句话说,孩童的“宇宙”与世界仍是不可分割的关系,没有个人行动的必须和责任,也就用不着害怕,他们不必独自面对外界的危险和压力。正是这种内心无压力的心理状态,使得人们在孩童时期享有最初的自由,其所感、所想、所为、所识皆出自本心,世界对于这一阶段的人来说,意味着无限的可能。
(二)传统社会中的自由
从社会发展历史方面来说,在传统社会中,个人与自然、部落、宗教浑然一体,这些原始的组织、纽带为人类提供了有组织的整体固定位置,个人将自身定位于原始部落、组织、共同体的一部分。在此类的传统组织中,个人能够与周围社会、自然世界建立一种和谐无间隙的联系。
弗洛姆认为,西方中世纪的人们是不自由的,但他们并没有感觉深入骨髓的孤独,因为传统社会中的人一出生,就在社会中拥有固定位置,身处一个结构稳定的整体中,给人们提供了自在明确的生活意义。[1]人们获得了一种生存的安全感,在生活上有明确安全的保障。个人身处颇具限制的社会范围之内,事实上能够在劳动和情感方面拥有很多自由来展示和表达自己。由此可见,在中世纪的西方传统社会里,传统的社会秩序、固定不变的社会地位、宣扬福音的教会等,在给人以原始束缚的同时,给予了完全的安全感和明确的自我定位,使得人们在享有一定范围内自由选择生活方式,虽然自由是以牺牲个体性为代价的自由。
二、自由的困境——个体化阶段
弗洛姆认为,先于个体化进程存在,并导致个人完全出现的纽带称为“始发纽带”,诸如家庭、原始组织、宗教共同体等纽带给人们带来归属感和安全感。[2]然而,随着个人逐渐从“始发纽带”中解脱出来的同时,需要面临新的任务和挑战,即对自我进行重新定位,人由此成为真正的“个人”,并致力于寻找新的不同于“前个体化阶段”更为安全的存在状态和方式,此时的自由含义与“前个体化阶段”的有所不同,也就是说个人在挣脱“始发纽带”的安全束缚的同时,真正进入“个体化阶段”。
(一)自由成为权力的面具
一切权力斗争都反映了某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追求,弗洛姆认为欧美历史争取自由的阶级斗争都有积极的一面,如废除专制统治,解开封建束缚。自由的斗争往往是在被压迫阶级和特权阶级之间进行,而自由的结果则是权力所有人的更替,自由作为人类社会中政治斗争的工具,作为一面旗帜号召人们反对压迫获取自由。讽刺的是,一旦权力到手,当初挥舞自由旗帜的领导者却举起权力的大棒,成为新的统治阶级。这种自由掩盖下的权力欲望使得人们在自由的斗争中屡战屡败,归根结底,真正的自由实现的基本条件不仅依赖于外在的专制统治的废除,更依赖于人的权力欲望的根除。
从心理学层面来看,人们内心的权力欲望来源于软弱,而非力量。对此,弗洛姆明确指出了一点,“权力”具有两层内涵,一方面是拥有统治的能力,并有统治的权力;另一方面是拥有权力做某事,是指有能力去做,能够做到。[3]其中,后面一种含义是指人在能力方面是否胜任,这与统治无关。尽管看起来自由在人类的权力斗争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屡屡成为人们争取权力的旗帜,但一旦了解到其中所包含的自由与权力欲望的关系,就不难明白自由在阶级斗争中注定最终被抛弃的原因,那是具有权力欲望的人们在政治斗争中利用自由的面具把戏,也是人在个体化阶段面对自由问题的孱弱表现。
(二)自由成为难以忍受的负担
在经历个体化的过程中,人总被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因素所影响,弗洛姆指出,如果整个人类个体化进程所依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没能为积极意义上的个体化实现提供基础,人们同时又失去了为他提供安全的那些纽带,这种滞后便使自由成为一个难以忍受的负担。如封建社会的社会现实虽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精神相悖,但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并不妨碍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做出具体的个人主义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从传统纽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越来越独立和自主,但个人在被赋予最大程度的自由时,也同时被切断自身和他人之间的纽带,自由成了难以忍受的负担,个人反而陷入到了孤立和焦虑之中。
人在个体化进程中,在心理层面上将呈现出与之前不同的生命状态,首先,个人从“始发”纽带中解脱出来,意识到自己身为个体与别人是相分离的,会产生一种微不足道的无力感,对生命产生越来越多的怀疑。其次,作为个体,在失去“始发”纽带的束缚同时,拥有了自由管理自己的权利。这种自我领域为个人的自由提供了舞台,个人倾向于在孤独中展开自我交流,在独立的思考中接近完整的自我,但对不懂独处的人来说,这种孤独的自由会成为最难忍受的负累。再次,个人在处理内在世界之外,还要处理外在世界的疏离问题,人摆脱大自然的束缚,冲破宗教等神秘因素的控制,不断地取得政治自由、经济自由等。如经济方面,社会允许并期望个人获得经济成功,这种成功甚至成为个人的生活目的,而在人人皆敌的经济竞争中,个人有可能成功,有可能失败,个人与外界走到对立面上,个人在世界中的自我定位是充满挑战且变动的,随之而来的孤独感可见一斑。
三、自由的归宿——后个体化阶段
自由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人类的历史发展存在于追求自由的过程中,从前个体化阶段到个体化阶段,个人在理解和追求自由上不断变化。针对人类追求自由的本性和逃避自由的行为矛盾,弗洛姆提出要从积极意义上来追求“自由地发展”,进而创造性地提出一个个体化阶段的人处理与世界关系的解决方案。
(一)消极自由:两种逃避机制
1.放弃自我的权威主义机制
“始发纽带”的瓦解,人的个体化出现和完成,均是无法扭转的客观事实。人们失去“始发纽带”,失去安全归属,只有再次寻找新的“纽带”来代替。于是出现逃避自由的一种方式,即为了获得自我欠缺的力量,放弃自我的独立性,需要依傍于自身之外的某人或某物,即“权威”,这个“权威”是指个人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将对方看作比自己更具优势的个体,但不仅仅是指财产、身体等方面的优势。权威主义包括外在、内在和匿名等多种存在形式。外在权威是易于发现的,其存在命令、责令似的指示,内在权威则更为隐蔽,常常以责任、良心、道德等面目来伪装。匿名权威比外在权威和内在权威更具影响力,它装扮成常识、科学、舆论等形式,对于人们的行为不必施加任何压力,就可以达到完美的束缚效果,因为这些内化了的权威所营造出的氛围充斥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就没有摆脱此类束缚的意识了。
2.消除自我的机械趋同机制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在政治、经济相对开明的民主氛围中,个人从外在的限制和束缚解脱出来,个人也理所当然地保存其完整的个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大多采用机械趋同的方式来逃避自由,所谓机械趋同就是指个人为了融入周围的社会环境中,为了能够与他人、自然、社会建立和谐的联系,而不惜放弃自身所独有的个性,而去承袭社会文化模式所给予他的人格特性,从而减少自由带来的孤独和焦虑感。机械趋同具有隐秘性的特征,一方面个人在此心理机制的主导下,会从主观意识上认为自身是自由的,另一方面个人会不断地失去自我和批判意识,其真正的个性和自我感觉也会受到压抑。现代社会的人们总认为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意志是自由的,但弗洛姆通过催眠实验发现,很多人主观上认为是自己的思想意识内容,实际上是被灌输和影响的。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感受到的不安和恐惧感可以在这种机械趋同的方式中得到宽解,只要将自己的所思、所感、所想塑造成别人期望的状态,自己就可以获得安全感和归宿,但同时也放弃了原本的自我,与真正的自由也失之交臂。
(二)积极自由:追求自发活动
弗洛姆对自由问题的思考不仅着手于社会历史发展层面,还从心理学层面剖析了他对自由思想的见解,他坚信真正的自由是可以实现的,认为获得自由的方法在于一种自发性的活动,即他所提倡的“积极的自由”存在于人的自发性活动中。自发活动不是强制性的活动,而是代表了爱与自发,属于自我活动的自由开展,其中的思想观点、感情内容和行动目标都是一种真实的表达。[4]
首先,“爱”是自发性活动的核心。“爱”可以使得人们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是在保存个人自我和肯定他人的独立性的基础之上,与他人联系在一起,又不泯灭自我的个性,属于一种自发地肯定他人,爱他人的能力。正如弗洛姆所说:“生产性地爱一个人,意味着关心这个人,感到这个人的生命……生产性地爱意味着对所爱者的成长付出劳动,加以关心、负有责任。”[5]
其次,作为自发活动的要素——劳动,是一种全面发展自我个性的途径。这种劳动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将不必依赖于权威或是他人认同,而能得到安全感和归属感。例如,艺术家算是能自发表现自己的人,他们的思维、感觉和行为都是自我的呈现,他们在创造性劳动中不断肯定自我,以促使自我与他人、自然恢复形成了联系,诠释并获得了自身及生命的意义。
再次,诸如爱、创造性劳动等自发性活动在对自我个性进行肯定和确证的同时,还可以使得个人与自然、社会融为一体,人若能将拥有强大力量的自我作为倚仗,将更有能力去积极地生活,以填补个性的维持与孤独不安感之间的鸿沟。个人的力量和安全从爱、创造性劳动等自发性行为中获得,那么这种新的安全既没有建立在依赖外部世界的某种力量对自身保护的基础上(如权威主义),又没有建立在压抑自身以求外部认同的基础上(如机械趋同),而是建立在于保存个人完整性和个体性的基础上。这种积极自由模式下提供的安全也不同于在“前个体化”阶段下的安全,人在“前个体化”阶段下接受家庭、部落、宗教组织等“始发”纽带给予的安全和归属感的同时,是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而弗洛姆在“后个体化”阶段提出的自发性活动下的安全则不仅以个人自由为前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追求自由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