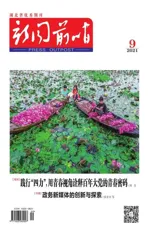从青年亚文化角度探析网络综艺的全新表达
——以《说唱新世代》为例
2021-11-12江安航胡亦琳姜洪伟
◎江安航 胡亦琳 姜洪伟
一、研究现状
对于青年亚文化和网络综艺节目(以下简称“网综”)的研究时间跨度较短,近十年来逐渐出现针对这两方面的期刊和论文。笔者采用网上搜索、查阅字典等方式对青年亚文化和网综的相关词汇进行了查阅。通过万方数据库查阅文献汇集材料,发现以往该领域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出发。
首先,从青年个体成长的角度。作为当下最流行的网络节目样式之一,以青少年为主要受众群体的网综节目,组成了青年亚文化中重要的一环。柳静在《综艺节目的文化分析》中提到:“受青少年生理和心理的影响,青年亚文化呈现出对传统和精英文化的抵抗及非主流的文化特色,在综艺节目中则表现出青春感性冲动和青春偶像崇拜的特点。”
其次,从青年亚文化的角度。网综对于青年亚文化的影响是复杂的,学者们有的将网综视为一场“狂欢”,深入剖析了“狂欢”现象的特征和影响;有的从传播学和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网综的受众的心理。
第三,从商业化角度。“‘消费’是一种青年亚文化行为的基本功能和社会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消费主义的普及,亚文化群体与商业机构之间通过“消费”体现了多种互动关系。”多位学者对于网综背后的产业链和营销策略进行了分析。
总之,我国对于青年亚文化和网综的相关研究有前辈做铺垫,但其中针对《说唱新世代》的研究并不多,本文将紧紧结合这一部网综展开分析。
二、《说唱新世代》及青年亚文化概况
(一)《说唱新世代》流量和口碑双丰收
《说唱新世代》是哔哩哔哩(简称“B站”)出品的首档说唱音乐类节目,该节目在B站获得了良好的回馈和口碑,在众多说唱类节目中脱颖而出,收获了豆瓣9.2分的好评。节目宗旨是“万物皆可说唱”,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说唱歌手,齐聚“说唱基地”。他们将通过层层公演考核,以音乐创作和竞演表现,决出代表新世代发声的“世代表达者”。
(二)青年亚文化的定义及背景
青年亚文化一般指社会阶层结构框架里不断出现的那些带有一定“反常”色彩或挑战性的青年新兴社群或新潮生活方式。在平台和对象上与网络亚文化有相似之处。它的亚文化属性使其不同于以主流文化为基础的广大青年文化。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04亿。而在我国网民的年龄结构中,10-39岁的网民占60%以上。这些年轻人的开放性、分散化、互动性等特点,使青年亚文化在网络环境中更好地成长。同时,各类移动终端的繁荣发展为亚文化的生长提供了优良的发展条件。
三、青年亚文化视域下《说唱新世代》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从内容、年龄段、表达形式的角度阐述青年亚文化的多元性
1.不同年龄段呈现了青年亚文化的不同特征
青年群体的年龄段可进行细分,不同年龄段的青年群体呈现出的亚文化态势不同。这一点在《说唱新世代》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85后”选手的个人作品饱含对人生的释然与和解,他们为人处世也更加世故和老练;而“95后”选手的作品中则展现出更多对社会现象和所处环境的思考;不少“00后”选手选择通过作品传递他们对当下人生阶段的思考。这种代际差异让我们也看到了亚文化传播方式的多元化态势,在这种亚文化环境中,青年的思想和行为必然更加多元化、个性化。
2.《说唱新世代》节目中选手表达思想的形式多元
在《说唱新世代》这样一档艺术性、娱乐性较强的综艺节目中,选手表达思想的形式也十分多元。例如,同样是反映社会问题,Subs的《画》中描绘了一幅乌托邦的美好景象,情感真挚感人;而螺丝刀组合的作品《叫爸爸》的歌词中,用戏谑的语气描绘出了生活中处处想走捷径的人的心理,从反面讽刺、抨击了这种不劳而获的行为。
另外,节目的赛制也给予了选手充分的展现机会。《说唱新世代》以展现出选手们最真实的一面为宗旨,设计了对抗性的规则,既鼓励选手按照给定的主题即兴创作,也充分给予了展现以前的作品的机会。
(二)青年亚文化的标出性促成商业化收编
“标出性”由布拉格学派的俄国语言学家特鲁别茨柯伊提出,本意在于突出非常规项。应用在人文社科领域时,主流文化即为常规项,亚文化即为非常规项。让受众关注和了解亚文化的过程即为“标出”。
对于青年亚文化进行“标出”的过程展示了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不同之处,将其边缘化和非正常化了,但往往正是这样的标出现象,将“聚光灯”照在青年亚文化上,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
嘻哈文化以《中国有嘻哈》、《说唱新世代》等综艺节目为代表,在资本的推动和受众市场娱乐的导向下,使一部分受众的视线转向亚文化音乐,即对嘻哈文化进行“标出”。《说唱新世代》节目播出之后,平台紧接着对选手们的官方账号进行了宣传,并推出了后续综艺《造浪》《造浪》是哔哩哔哩出品的首档说唱厂牌音乐旅行节目,嘉宾为《说唱新世代》排名前八的选手,节目播出后反响优良。《说唱新世代》的记忆点不仅在相关视频弹幕中大量出现,甚至会出现在与嘻哈无关的视频中出现,形成了独特的“贷人”文化。
当一个处于标出项的青年亚文化经过了某个综艺节目的聚焦和重构之后,将会逐渐向主流文化靠拢,被主流文化收编。在网络综艺领域,节目制作方会针对亚文化靠拢的过程,构建一个逐渐成熟的商业化产业链。为了赚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将不断有节目制作者通过该产业链策划下一次亚文化的标出,形成循环。
四、青年说唱爱好者群体认同的构建的新表征
(一)“抵抗性”方式改变
20世纪70年代时,嘻哈音乐诞生在美国纽约的黑人贫民区,当时贫富差巨大,种族歧视严重,该地区社会动荡,矛盾和冲突层出不穷,嘻哈音乐创作的初衷是为了表达和发泄情绪,主题多为批判社会和纸醉金迷,带有青春期特有的抵抗和叛逆的色彩,由此形成嘻哈文化原本的“抵抗性”。
不难发现,《说唱新世代》中很少出现言辞锋利、充满攻击性的音乐,甚至一些歌手在访谈中坦言,来到这个节目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竞争,而是为了交朋友或者宣传作品的,总决赛季军沙一汀表示“我是来玩的,我只想认识想要认识的人和喜欢我的人。”选手万赛文也说:“即使把我先淘汰了,只要我能把自己的作品留下来,也是一件好事,音乐被大家听到就好。”节目中唯一一位在采访时向其他选手“宣战”的选手被观众戏称为“稀有物种”,但他在节目后期也坦言自己被“感化了”,交到了很多朋友。
青年亚文化的抵抗性不再呈现为激进的正面冲突,而是将其表达需求融合到语言、动作、旋律以及节奏等符号之中,将选手对个人经历、社会现象的思考用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给抵抗性赋予了温和的特质,赋予了话题的厚度和深度。
例如,选手Subs的作品《我不想死在20岁》创造于大专院校毕业后对未来感到迷茫之时。歌词并不攻击任何人,只是蕴含了青年人对于人生和未来的思考,真实地表现出了他在结束学业后对未来的无措感,想要逃避现实,但挣扎后还是担起了责任,勇敢追梦的经历。在歌曲解析访谈中,他说:“我想让别人感受到我的‘丧’,也想让别人感受到我的力量。”
(二)“边缘性”向中心逐渐靠近
被“标出”的亚文化群体向主流文化群体靠近,是双方相互作用的,亚文化群体需要靠近主流文化的机会,而主流文化则通过吸收亚文化变得更多样繁荣。青年亚文化为了宣扬自身,需要向受众展现自身文化魅力的机会,寻求更多关注。例如嘻哈文化中音乐创作者们需要流量和平台,《说唱新世代》在B站独家播出,B站作为“亚文化的乌托邦”如今已成为国内最大的原创音乐社区之一,包含大量音乐创作者和受众,可以为说唱爱好者提供平台。此外,与腾讯、爱奇艺、优酷等视频网站不同的是,靠推广“二次元文化”起家的B站本就是青年群体的聚集地,其用户对于亚文化更加包容,该群体借助这个平台张扬自己的文化,向主流文化靠近。主流文化需要满足更多、更广人群的个性化需求,因此需要不断寻求创新,与亚文化进行一定的融合。
结语
无论是亚文化还是主流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一部分人愿意为之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创造出专属于一个时代的经典和辉煌,反映出其中的深层社会原因。嘻哈文化正是如此,在《说唱新世代》节目中,制作者以“万物皆可说唱”的观念为指导,呈现了青年亚文化的多样性、标出性,该文化的抵抗性发生了改变,嘻哈音乐作品的风格不再是单一的、锋利的、纸醉金迷的,它反映了社会问题和对人生和世界的思考,赋予了亚文化积极的厚度和深度,促进亚文化向主流文化改变。
注释:
[1]柳静:《综艺节目的文化分析》,山东师范大学2011年学位论文
[2]董中锋:《新媒体背景下娱乐节目狂欢现象研究——以〈奇葩说〉为例》,华中师范大学2016年学位论文
[3]唐文杨:《从传播学看网络节目〈奇葩说〉的文化表达》,暨南大学2016年学位论文
[4]张宁、唐嘉仪:《商业逻辑与青年亚文化生产:网综节目的批判话语分析》,《新媒体研究》2019年第2期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0)[EB/OL],http://www.cac.gov.cn/2020-04/27/c_158953547037858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