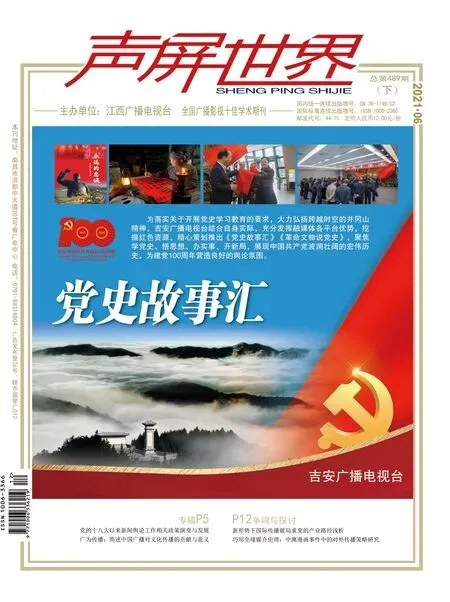西方视域下的东方形象研究
——以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电影《末代皇帝》为例
2021-11-12丰鹏程
□ 丰鹏程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1941年3月16日出生于意大利帕尔马,意大利导演、编剧、制作人,曾因其执导作品《巴黎最后的探戈》荣获第4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提名,他在1986年进入到紫禁城内重要场所拍摄电影《末代皇帝》。中国当然也有导演能够拍出这种大气磅礴的影片,不过能够在电影中成功融合中西特色的人,全世界范围内都屈指可数。得益于托鲁奇西方的表达方式,《末代皇帝》才能够在奥斯卡上横扫千军,提名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等9项大奖,并全部获奖。这也是迄今唯一一部能在奥斯卡上斩获压轴大奖最佳影片,具有中国血统的电影。该电影有效地吸纳众多中国文化,并获得了大量国外观众的好评,提升了海外公众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从文化传播的效果来看,该电影毫无疑问是十分成功的。
《末代皇帝》中的“中国元素”的应用
《末代皇帝》以传统中国美学概念为基础,同时结合了西方艺术思维。电影色彩充满着东方的神秘,细腻悠扬地描绘着中国近代的历史,但同时也展现着西方艺术角度的魅力,用西方独特的视角表达了这个时代丰富与深厚的感情,并将其运用于电影创作中,给予受众全新视听体验。然而在传播过程中,电影的中国元素对国外受众的影响依然是十分复杂的。
《末代皇帝》中的中国建筑文化。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传统的中式建筑占据着重要地位,蕴涵着丰富民族审美理念与民族情怀,实质上是一种当代文化实体化的体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社会风貌和文化底蕴。在影片中充斥着大量的建筑镜头,从一开始的皇宫再到宫殿外的棚户,金碧辉煌的宫殿与破烂不堪的棚户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体现了一个封建王朝末期不同阶层物质上的极度不平衡。与此同时,外表看似金碧辉煌的宫殿内部也显得陈旧不堪、冷冷清清,与城墙外熙熙攘攘的热闹情形同样形成了鲜明对比。随后溥仪被日军挟持进伪满洲国时,所住的场所为中西结合式建筑,后来日本战败,他被引渡回中国进入战犯管理所,被释放后又成为一名园丁,在电影的结尾又回到了皇宫。整部电影穿插着中国建筑的变化,毫无疑问含蓄地衬托出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化,皇宫象征着封建落后,而伪满洲国中西结合的官邸却体现出了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现状,而到了新中国之后又能体现出当时百废俱兴的面貌。电影将这种变化与溥仪的个人命运交织在一起使得人物内心世界以最恰当的形式展现,一方面让国外观众更加确切的了解到中国建筑特色的同时,另一方面让国外受众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跌宕起伏。
《末代皇帝》与藏传佛教文化。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是指传入西藏的佛教分支。满清尚未入关前为了更好地统治蒙古诸部,促进民族融合,满洲人开始信封蒙古人信奉上百年的藏传佛教,藏传佛教的历史地位达到了最高峰,因而将藏传佛教定为国教。在影片中多次出现藏传佛教的元素,在对北京街头的描写中伴随着红衣喇嘛的身影。在溥仪与文秀王妃的新婚仪式上,作为背景的墙壁上布满了金色的佛像;在溥仪被日本人扶植成伪满洲国皇帝时,在登基仪式上,溥仪的周围也被一群红衣喇嘛围绕。毫无疑问,影片中宗教的显现体现了电影文化的多样性。通过这些描述,贝托鲁奇向人们展示一个华丽而又神秘的东方国度,让观众逐渐了解中国的多元民族文化。
《末代皇帝》中东西方形象对比
被弱化的虚构的“东方”。在西方学者“东方主义”的视角下,所谓的东方其实是一个与西方对立的虚构的形象,有着本质的差异,从而使得西方群众以一种同情的、带有文化偏见的眼光去看待东方。在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中,西方虚构了一个东方,通过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将东方虚构为所谓的“他者”,在东方主义学者看来,东方是脆弱的、愚昧的、毫无理性存在的。
片中有大量的镜头描写情节将华人描写成一副值得同情的可怜形象,尤其是女性。整个影片中,人们可以看到东方女人的典雅、含蓄,压抑自己内心情感与欲望的形象,然而东方女人地位却十分卑微。在电影的开头中,一群禁军骑马驱入醇亲王府,一名长官模样者开始宣读慈禧太后的懿旨,将尚为幼儿的溥仪送入紫禁城。醇亲王妃作为溥仪生母,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被送进驶向紫禁城的马车,心里万般不舍却又无可奈何,嘱咐奶妈阿嬷照顾好年幼的溥仪,母子间的亲情在国家命运面前显得无足轻重。在随后的情节中,得知醇亲王妃去世的消息后,溥仪连看母亲最后一面的权利都没有。在她的一生中与儿子相处的机会都不到几次,作为一位母亲醇亲王妃是悲哀的。东方的悲剧描写勾起西方看东方的欲望,也为后来西方作为救世主身份入场埋下伏笔。
“救世主”形象的“西方”。影片中除了中国文化的应用外,同时也会夸大西方。比如影片中出现的一个重要人物,溥仪的西方启蒙导师——庄士敦,而影片中的庄士敦是作为一个典型的西方文明的形象来审视中国封建社会的文明。除此之外,庄士敦同样被描绘成一个来自西方的拯救者形象,影片中这种形象给人影响最深刻的莫过于庄士敦赠给溥仪自行车这一情节。当溥仪看到这辆自行车后说道:“自行车对你有害。”庄士敦却不以为然:“对你有害?胡闹!”庄士敦说的时候带着一丝疑惑和对无知的鄙夷,这是一种先进对落后的讽刺,在标榜着西方的文明科学的同时侧面凸显出东方的愚昧与落后。庄士敦是溥仪——一国之君的老师,这意味着西方正在教化开导愚昧无知和落后的东方。溥仪骑上自行车时显得尤为开心,旨在表明了西方给东方带来了先进的文明,东方人民欣然接受并乐在其中。然而,影片中所描绘的西方形象不仅仅限于一个东方文明教化者的角色,当东方陷入危难之时,西方形象还会变成“东方救世主”的角色。当溥仪的生母去世时,作为儿子的他却不能前去吊丧探望,内心极度痛苦的他爬上了宫殿的屋顶,而底下的大臣太监宫女急得团团转却不知所措。这也从侧面显现出东方在解决问题方面显得束手无措。而庄士敦作为一个典型的西方形象的象征,他先是有序地组织了乱作一团的大臣和太监们,随后勇敢地爬上墙头劝说并解救溥仪。导演运用了一个仰拍的镜头,将庄士敦这一个角色衬托得尤为高大,整个画面意在说明西方在拯救东方。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东方显得毫无头绪、不知所措,而西方则是镇定自若、井然有序地解决问题。每当溥仪遇到疑问和麻烦时,庄士敦都会给出意见并对其进行帮助,庄士敦常常用自己的西方思想对溥仪进行灌输说教。总体来说,影片中许多场景所表现出的大多是西方文化相对于东方文化的优越性,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文化“征服”了东方文化。
《末代皇帝》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启示
随着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如何运用电影中的中国元素,提高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影响力,提高话语权,从而达到对外传播的目的,对于影视工作者来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电影《末代皇帝》中对于中国元素的运用与创新,给予人们重要启示,当运用中国元素进行文化传播的创作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中国元素对外传播仍属于初级阶段,需要有效转型。就文化符号而言,国外受众更容易理解熊猫、绿茶、中国龙等具象符号。但是,对于一些抽象符号,诸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词汇,还是存在难以理解的问题。因此,从电影的角度来说,我们应当采取系统性的方法,循序渐进,以国外受众内在兴趣为驱动,在初级阶段的传播过程中融入大量的浅显的文化符号,在达到一定效果后逐步通过对于生活方式的记录与描述,加强国外受众对于中国文化的认知程度,引出中国特有的哲学观与价值观,从而进行更深层次的文化符号传播。
积极引导西方创作者讲述“中国之美”。从受众分析角度上讲,东西方在价值观和文化上存在较大差异,在创作作品的过程中同样大相径庭。西方创作的影视作品大多偏向个人主义,即将个人与情节交织在一起推动故事的发展,而中国创作者则偏向于集体主义,表现的是一群人或者一个集体乃至所处的社会的跌宕起伏。大部分西方受众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所以在解读作品时会以自带的西方价值观加以审视,势必会导致一定的由文化不同而引起的偏差,从而难以达到积极传播的效果。应该让一部分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西方创作者去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内涵,能够在电影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充分考虑中西方文化差异,立足不同国家、不同地区观众审美意识,以更为开放的思维、包容的态度、适宜的方式创造影视作品,尽量避免传播过程中产生“文化折扣”的现象,完成本土文化弘扬与传播。通过西方的视角去解读东方,可以让海外受众更容易接受东方文化的同时增强该作品的说服力。
在电影中的中国元素进行了广泛而又细致的处理。与此同时,在对于人物形象刻画上,更多的是以西方个人主义思维,将溥仪个人的跌宕起伏与整个剧情的走向相结合,一个人带动电影情节的发展。这样对于西方受众来说,既能够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化,又能够引发他们对中国文化内涵的理解与思考,在不影响价值观的情况下,更多的宣扬“共性”可以使中国文化发展在西方受到更多的包容与认可。而一个来自于西方的创作者对中国文化的解读传播正是将“共性”扩大化的一种形式,西方创作者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实际承担的是一个文化中转站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受众可以通过由西方视角解读的中国去逐渐了解中国,在理解的过程中相对于直接的中西方思想碰撞更容易去接受和理解中国文化,从而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思考中国文化,以此来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因此需要积极引导一批西方创作者,让他们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并以此来达到对外传播的目的。
打破刻板“中国印象”,重塑积极“中国形象”。在大多数西方电影中,华人形象多为负面,在《末代皇帝》中也能够清晰地看出这一点,比如老态龙钟、拖着尖细嗓音的太监,奴颜婢膝,毫无阳刚之气。女性的身份地位也同样十分卑微低下,对于命运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低头接受并往往只是被看作“男人的附属品”。即便是身为一国之君的溥仪,也是像牵线木偶一样任人操控,毫无自我可言,而作为西方代表的庄士敦则是一副身材魁梧的救世主形象。东方的“愚昧”“落后”与西方的“理性”“先进”形成二元对立。由于西方的大部分人没有太多机会来到中国,他们了解中国的途径只能来自于官方媒体或影视作品,而由于意识形态差异和政治分歧,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显得困难重重。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能够通过电影中的东方人物形象打造为一个现代积极的正面形象,毫无疑问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是非常有帮助的。
结语
爱新觉罗·溥仪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殖民扩张、文化传播高峰期和英语逐步确立语言霸权的20世纪早期。由于20世纪的历史政治格局,大量的西方影视作品有着“西方至上”的文化偏见,同时对于中国形象存在扭曲丑化的现象,导致国外群众对中国文化内涵的误解。如何扭转西方受众对中国文化的刻板印象,还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由表及里的长久过程。影视传播工作者应当以加大对外传播、改善世界上的东方形象为目标努力制作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优秀文化作品,从而达到中国文化传播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