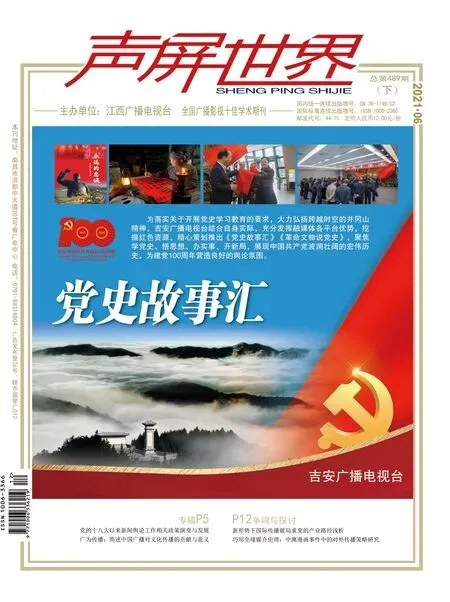跨国合作在东亚电影全球化背景下的作用研究
2021-11-12丁颖杰
□ 丁颖杰
东亚电影全球化是必然的,首先东亚电影的历史背景、意识形态都是具有民族特性,这是与西方电影的不同点。其次在一定程度上,东亚电影的兴起也分散了好莱坞的经济地位,但东西跨国合作(指被好莱坞大量制作的东亚电影)是好莱坞为了不让自己的经济分散而制作的。然而,许多东亚的评论家期待东亚电影被好莱坞制作,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东亚电影击败传统好莱坞大片的一种方式。越来越多的日本、韩国和中国电影被变成了高调的好莱坞电影,于是东亚电影全球化的局面迅速形成,跨国电影合作越来越频繁,包括东西跨国合作和东亚内部跨国合作。因此,在讨论东亚电影时,跨国主义逐渐成为了一个默认的概念,因为越来越多的电影、制作团队以及电影文化都涵盖了跨国的概念。跨国将电影文化和经济形式相结合,打破了一些国家固有模式的限制性,并且扩大东亚电影市场。跨国合作可能会掩盖权力不平衡的现象,尤其是在政治方面,比如在移民和侨民完成的跨国合作电影中可能会出现差异政治。这也侧面展示了东道国文化和母国文化之间的关系,不难看出跨国电影内部与全球之间相互联系。除此之外,这类由侨民制作的跨国电影既揭示了他们的工作能力与经验又挑战了民族特权地位。跨国合作的另一个弊端是,许多技术人员和艺术人员在跨国交流与合作中其实并没有充分考虑跨国电影的美学、政治背景等各个方面。
跨国合作的出现也是全球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Bergfelder认为,“跨国”替代了“全球化”。因为全球化通常是许多国家跨越国界维护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关系,而跨国同样是多样性的交流规模。但不同的是,跨国主义更加明确国家内部的变化及外部的影响,尤其是对民族国家(the nation-state),只是跨国电影工作者可能会忽视民族国家的特性。实际上,“跨国电影”的概念不能仅仅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和规定性的(prescriptive),因为所有过境电影(all border-crossing films)都将包含权力和政治相关的问题。因此,不能仅从概念的角度理解跨国电影,还必须与具体领域相结合去看待问题,以便充分探讨和揭示权力和政治立场的动态。
跨国作品在国家背景方面的作用
跨国电影研究与跨国电影的权力动态是平行的,并且跨境是这两者的基础,跨国合作的作品本身就具有固有的特点和标签,只是跨国合作使他们加强或者丢失。跨国合作的电影中,基于国家背景且还原性最高又保持固有特点的代表作之一就是《末代皇帝》,它是由意大利、英国和中国合作拍摄的,音乐是由日本坂本龙一主要创作。它是基于历史对过去的高度再现,尽管在影片中也创作了新的故事线,但是这些创作的“虚构的艺术”是为了让主要人物更加突出,使历史的记忆更加清晰。整部电影都是完全以中国的历史背景为基础创作的,也是跨国合作中加强国家背景并保持固有特色的代表作之一。
还有一些电影制作者会改变一个国家电影文化的固有观念,尽管这部电影背后的国家特色存在于该国家的边缘,但如果追溯背景的起源它远远超过其范围。跨国合作会使电影的国家背景模糊,无法明确区分具体某一国家的电影特点。比如电影《你好,之华》,由日本导演岩井俊二编剧和导演,由中国演员出演,中国香港导演陈可辛和日本导演岩井俊二一起监制,中日一起制片并由中国出品。在电影中中国观众无法识别本土性,国际观众也会对电影的属性产生困惑,原因就是岩井俊二弱化了中国的地方特性,相反加剧了日本电影的属性。
跨国作品在剧本创作方面的作用
在剧本创作方面,关于跨国作品的电影属性问题其实是不太明确的。因为故事都是基于人发生的,他们是不分国界的。每个国家的科技进步、时代进步、社会进步等也大部分都为相近时间段内进步的,尽管电影制作者需要考虑每个国家不同的社会背景。从话语的角度来看,时效(prescription)是话语(discourse)的一种形式,描述(description)是另一种话语形式,但是指令性(prescriptive)和描述性(descriptive)之间的区别是人为的。还以电影《你好,之华》为例子,无论在任何国家,大部分中学时代的学生都缺少社会斗争意识,电影中的人物放在任何国家背景里都是相对成立的。因此,岩井俊二将情书的重要元素——“信”,延续到该电影里。他只是用新的演员面孔(中国演员)和过去的经典镜头及故事情节相结合,完成现在与过去的紧密联合。
电影中的“信”不仅追寻逝去的生命和时间,而且还形成了一种比较——“科技”与“人文”“过去”和“现在”。“信”对于大部分国家而言都代表了过去,所以《你好,之华》也间接体现了当今时代的“怀旧病”。电影中人物通过写信与现在抗衡,是因为他们不敢接受未来憧憬的破碎,就像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电影中,岩井俊二运用了大量的逆光镜头与美学完美结合,揭示了青春的极度纯粹,而齐格蒙特·鲍曼称它为“逆托邦”。
回到剧本创作方面,在东亚电影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产出的东亚电影《你好,之华》,其实最初该电影的创意源自日韩合作的2017年为雀巢咖啡拍摄的小型广告类电视剧,单集15分钟共4集,叫做《昌玉的信》。后来这个剧本被中国和日本分别拍摄,英文名字都为Last Letter,分别是中国的2018版本和日本的2020版本。对比中日韩三个版本,他们都各自存在内部细微的文化差异。比如,韩国版本放大婆媳关系,中国版本以血缘和传承为主要表现方面,日本版本以姐妹之间的感情为主并添加了当地民俗服装元素。这个剧本不仅被不同的国家合作拍摄,而且他们都根据自己国家的社会背景微微调整,使作品更加生动。
跨国电影提出问题。除此之外,导演除了通过剧本叙述故事之外,还会通过文本创作和跨国合作的作品揭示历史问题。比如《咖啡时光》(2003年),这是台湾导演侯孝贤的日语电影,是为了纪念小津安二郎诞生100周年而制作的。侯孝贤没有用小津安二郎“小结式的重点归纳总结”的电影风格,而是用纯文本化的方式表达。该影片的情节更加戏剧性,虽没有小津安二郎对于电影生动化的细节描绘,但整部电影都充斥着满满的“中国诗”的意境。
跨国电影的视觉空间和城市空间。视觉空间方面,许多电影进行跨国合作时都会在视觉上生产出一种地方性特点,但这种视觉地方性的前提是物质生活与话语想象空间之地域性的抽离,即“无地域空间”。在“去地域化”的语境中,空间其实是可以生产出来的,如《你好,之华》中,岩井俊二选择中国大连为拍摄地,他尽量避免大连标志性的建筑。整部电影里大部分取景都为室内,比如学校、图书馆等,再加上中近景浅焦镜头里虚化的背景环境,地域性被弱化,这是在物质生活层面的视觉空间的体现。在话语想象层面上,岩井俊二通过信件的传递完成了地理上的世界,从法国圣米歇尔山的修道院,到巴黎的凡尔赛宫。与此同时,整个电影中演员的台词都为普通话而不是选择方言,所以话语空间的地域特征也被弱化。因此不难发现,跨国电影在完成视觉空间上的无地域性特点时,一种存在内部差异全球化的整体想象出现了,它使城市空间变得更加单一,即“全球单城性”(unicity)。它是指世界逐渐变成一个具有单一性特点的社会与文化背景的世界,因为在文化背景和社会实践中,跨国合作时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同存异。
东亚电影和好莱坞的关系
在东亚电影全球化的背景下,除了东亚内部跨国合作外,更早的是东西跨国合作,其中东方电影和好莱坞的合作更为密切,它的出现也是因为市场需求。东亚电影与好莱坞的互动有这几种主要类型,分别是武侠片、泛族裔片、跨国合作和重拍。首先,武侠片在美国电影市场是有一定位置的,甚至在西方国家也非常流行,比如李安的《卧虎藏龙》、张艺谋的《英雄》、周星驰的《功夫》等。因为这些电影不仅具有东方魅力,而且还具有唯一性。其次,亚裔电影工作者的大量出现是由于他们挑战了国家内部的传统结构以及无视了身份构成才促使跨国联盟的形成。这两种合作类型的东亚电影都集中地表现了一种“亚洲美学”,一种具有异国情调、女性化和神秘的“亚洲美学”。这样似褒实贬的东方主义的论调是有代表性的。西方的电影学者之所以有这种错误印象,是和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不够了解东亚电影的语言魅力有关。相比之下,他们更关注的是东亚电影的视觉效果,所以才会产生对电影理解的认知偏差。
追踪东亚电影的跨国轨迹发现一个趋势是许多电影评论家期待和满意好莱坞与东亚电影的合作,好像跨国合作满足了部分东亚电影由本国的边缘到国际市场中心的蜕变。比如,小成本制作的东亚电影被好莱坞投资成为备受瞩目的跨国合作的作品。即使许多电影工作者承认跨国电影在制作方面得到很大的帮助,而且也接受东亚电影在跨国合作中的市场份额被交换,但是话语权不平等的现象仍然存在。实际上,在东亚电影和好莱坞的跨国合作中,好莱坞还是更有话语权的。比如《艺妓回忆录》(2005年)和《最后武士》(2003年),这类电影都满足了好莱坞对东亚电影的跨国想象。不难看出,好莱坞以实现扩大全球利润为前提,对跨国合作的东亚电影实行语言霸权。与此同时,它还忽视了族裔和种族差异,甚至试图加剧不同国家中政治紧张的局面。比如,在电影《艺伎回忆录》中,让中国女演员扮演日本的艺伎角色。
除此之外,来自好莱坞的跨国主义为电影和导演都提供了移植(transplantation)的可能。实际上重拍是好莱坞在21世纪的全球战略,而且它在最大程度上凸现了好莱坞的生产机制。重拍是电影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集中体现,也代表了未来几十年中美国和东亚各国之间对于知识产权的争夺。黑泽明的《七武士》(1954年)就被重拍为西部片《伟大的七个骑手》(1960年),这成功地为好莱坞扩大东亚市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所有的重拍强度和密度都不及2002年开始的重拍东亚电影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2006年马丁斯科塞斯根据吴宇森的《无间道》改编为《无间行者》不仅拥有较高的票房而且囊括电影奖项,成为首次得到国际电影节认可的好莱坞重拍东亚电影的影片,尽管它的口碑是具有争议的。
为什么会出现东亚电影热、好莱坞重拍的局面?首先,东亚电影的成本较低,版权费用足以让制作电影的工作者收回成本。除此之外,那些期待重拍的东亚电影人会主动地预估好莱坞市场的喜好,甚至是美国观众乃至全球观众的喜好,主动审视自我完成符合他们审美的作品,而不是以独立的眼光对待电影作品和电影市场。其次,东亚和美国有着共同的消费品味和共同的消费特征。因为每个国家不同的文化的特点皆为消失或存在,但存在的前提就是商业化,不仅以多样性去适应市场全球化的特点而且以异国情调为卖点去满足全球化市场的需要。当然大部分被重拍的电影已经好莱坞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午夜凶铃》。最后,重拍片实际成为好莱坞外包工,重拍东亚电影会简化好莱坞制作电影的过程,并且节省时间及成本。最重要的是市场调研已经在东亚市场完成,这不仅加强了好莱坞在电影界的地位而且提高了它的国际竞争力。这种局面的形成会导致东亚电影受损,因为重拍的东亚电影失去了民族特性与属性以及东亚文化的多样性。因此跨国电影流开始出现,东亚电影逐渐全球化,跨国电影流(transnational cinematic flow)是由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力量组成的。
中日韩:“东亚电影”的产业探索
在跨国电影流的背景下,近几年出现了泛亚洲电影的实践。泛亚洲电影的实践的目标是通过合作收复被好莱坞占领的电影市场,并以商业的方式增强吸引力。其实泛亚洲电影也是在当下产业环境下被迫形成的趋势,可以完成人才分享、跨国投资与制作,这些都是为了巩固电影市场。除此之外,泛亚洲对于制片和观众而言是当下的流行趋势,也是被东亚电影产业视作维系市场全球化的商业策略。
实际上,《如果·爱》(2005年)就是泛亚洲歌舞片,该片由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印度以及日韩共同合作完成,它被视作陈可辛“泛亚洲电影”实践的集大成者。《你好,之华》也是陈可辛监制,但它不是泛亚洲电影,而是东亚电影。像上文提过的该电影的剧本被中日韩三个国家分别拍摄,实现了“一本多拍”的现状。此前也有“一本多拍”的成功案例,比如《奇怪的她》(韩国,2014年)分别被东亚的五个国家翻拍。可见,一个剧本被多次拍摄的制片模式,标志着中日韩三国乃至亚洲多国迈向了更加深入的电影产业合作领域,它是有益于东亚电影全球化及东方电影合作的发展。
结语
总之,由于东亚电影的兴起加速了东亚电影全球化的局面,这是东西方在电影界的博弈和交流,于是跨国合作的方式和东亚电影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随后因为跨国合作中好莱坞与东方的电影合作频繁出现,出现了“泛亚洲电影”的实践。从批判的观点出发,跨国电影制作仍使作品和各个国家之间有隔阂,无论是在国家背景还是民族文化方面,但是差异的多元化可以明显地比较出各个国家的独特性。除此之外,由于各个国家的审查制度多样化,它局限了跨国电影的表现形式,但又使这些作品的政治立场凸显出来。
跨国作品是有影响力的,它颠覆和改造了跨国合作中各个国家的潜力甚至将历史现象通过作品反映出来。跨国合作是需要大量资金周转的,因此好莱坞才会将重拍或投资拍东亚电影作为全球性战略,而吸引投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有国际认知度的明星、最好的制作团队以及商业价值高的剧本。因为好的票房才有投资回报率,而这些方面大都有票房保障。因此,大制作的电影票房往往是高的而口碑是不固定的。这会改善整个电影产业的经济状况,但也会出现一种常见的状况为高票房差口碑,但小成本投资合作的跨国电影往往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