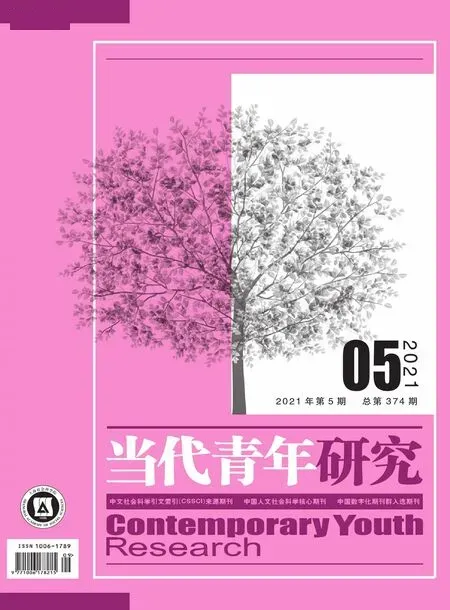超越经济主义:“民主评议”与解放初期天津青年搬运工人改造
2021-09-30刘炜
刘 炜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1949年初接管天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迅速开展对搬运工人的改造。为了大幅降低商品流通成本,并充分掌握运输系统的领导权,共产党人推翻了多年势力割据的脚行把头,鼓励青年搬运工人自发组建运输服务站。然而,搬运工人只局限于本服务站的经济利益,陷入了“经济主义”的困境。不但割据之势未减,而且运价仍旧居高不下,工人无法统一调度。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共产党人开始推行“民主评议”的改造策略。仅半年后,天津全市总运费降低了约七成,新政权建立起新的运输公司,实现了全市运输业的统一调配。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评议”的改造策略,使搬运工人克服了“经济主义”倾向,大幅降低运输成本,并取得了天津运输业的领导权。
一、经济主义问题的形成:从脚行到工人服务站
在共产党人接管政权前,脚行是天津规模最大的民间组织之一。根据天津解放前夕的统计,全市共有227家大小脚行,3032个把头,6万余搬运工人,总人数占到天津产业工人的两成有余。接管天津的共产党人很快意识到,运输系统的效能高低将直接关系到城市商品流通的恢复与发展;由于脚行组织在运输系统中长期处于支配地位,形成了抬价勒索、强装强运等诸多积弊。全面改造由脚行把持的天津运输系统虽势在必行,但并非易事,因为经营多年的脚行组织具有势力纷争割据与复杂身份网络的特征。
首先,脚行组织之间纷争多年,形成了割据之势。国民政府时期,虽有“天津运输业职业公会”,但脚行之间仍有明确的经营范围划分。如饭市脚行与树记脚行,占据海河两岸盐坨地区,分管海河沿岸的盐运往来。[1]除了“地界把持”外,业务对象、日期与货物种类有时也会成为脚行经营范围划分的依据。[2]由此,小脚行的地盘只是几座建筑或几条街巷,大脚行则能控制整个铁路车站或大码头,并经营自己的货场。[3]随着脚行数量日益增加,势力范围划分愈发细密,脚行之间的利益之争在所难免。当遭遇抢夺地盘时,脚行把头会动员或强迫搬运工人出动械斗。
其次,脚行内部与脚行间逐渐发展出一个稠密而复杂的身份网络。在全市3032名脚行把头中,有大把头901名。这901名大把头的社会身份样式繁多:有422名青帮成员,301名参加了国民党、三青团,有154名参加了“军统”组织控制的“忠义普济社”。[2]脚行把头所担当的多重身份既方便其与天津上层结成同盟关系,也有助于将势力触角伸向其他社会领域。对小把头而言,一旦与强大的把头结盟,就能扩大他的经营范围并减少不必要的冲突。这种身份认同有时也是普通搬运苦力找工作的必要条件。比如,为了在码头工作,必须先成为帮派头目的徒弟。帮派成员的身份在强化把头和苦力的等级关系的同时,也明确了两者的庇护关系。[3]这一身份网络犹如黏合剂,将原本充满张力的各大脚行组织粘连起来。
政权鼎革临近春节,装卸业务量骤减,一部分搬运苦力过年关没有着落。初入天津的共产党人旋即成立运输事务所,通过座谈、访问、开会等方式,动员青年搬运苦力推翻把持多年的脚行组织,筹建属于搬运工人自己的服务站。以七村装卸脚行为例,新组建的服务站成立了15个组,每组7至14人,共推选组长15人,并由各组提出候选代表名单,由全体工人投票,选出代表5人。不仅如此,根据运输事务所规定,只有符合“工作积极能为大家服务”“不自私自利、老实正派”“确属劳动工人且与旧工头无联系勾结”的工人才可担任组长或代表一职。①天津市财经委员会,《市运输公司、搬运工人委员会工作总结》,天津市档案馆馆藏资料(以下简称:津档),77-3-2243,第24页。到1949年5月5日,天津全市共组建起18个搬运工人服务站。
然而,令党员干部始料未及的是,以工人服务站为主体的运输系统非但未能形成统一定价与统一调配,还表现出明显的“经济主义”倾向。也就是说,每个工人服务站只着眼于自身服务站的“狭隘”的经济利益,而不愿为更“广泛”的政治利益服务。例如,二区在建立服务站之后,工人在要求政府革除把头剥削制度的同时,也主动提出商民不能自行卸货的要求。工人们力求运输事务所划清服务站与服务站之间的经营界限,不可互相侵犯。[1]
为了维持服务站的有序营运,运输事务所只能规定从运费中抽出5%作为管理费。然而,服务站的工人代表大多只希望管理费用多多益善,不但对申请工作的搬运工人未加甄别,而且常常强制要求其加入。许多原先并非脚行苦力的闲散人员也被吸收入站,全市搬运工人总数顿时庞大起来。为了避免为数众多的搬运工人因失业而导致社会纠纷,运输事务所不得不暂时默许其划分地界,只对不合理的收费行为(如过街费等)先行取消,待以后逐步改进。②同①,第27页。不仅如此,被公推出来的工人代表与工人队长大多又扮演起“新把头”的角色。大部分的工人代表和队长公然从总运费中抽成3%~15%挪为己用。据不完全统计,在五区的代表和队长中,贪污腐化者竟占到80%。③天津市公用局,《市运输公司1949年搬运工人工作总结》(1950),津档,152-1-16,第74~75页。全市运费仍然居高不下,这难免又引起天津商人的不满。
二、文献综述:经济主义问题与社会主义策略
天津搬运工人改造所遇到的经济主义困境,实际上源自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一个经典问题:如果工人阶级要最终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在阶级意识上必须从“自在阶级”上升到“自为阶级”。[4]换句话说,从斗争形式来看,“自在阶级”只从事分散而自发的经济斗争,而“自为阶级”则致力于有意识有组织的旨在消灭剥削的政治斗争,若要克服工人阶级的经济主义困境,就需要弥合“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之间的“缝隙”。然而,从为经济利益而斗争提升到为集体的政治目的而斗争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意识却易于走向经济主义的困境。诚如列宁所言,“经济主义者将工人阶级的任务局限于追求诸如更高工资与更好工作条件的经济斗争,并断言政治斗争只适用于自由资产阶级。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认为政党仅需要遵循运动与入会的自发过程”。[5]拉克劳和墨菲(Laclau&Mouffe)也认为,“工人阶级具有走向分裂的强有力倾向,工人贵族的崛起、工会的工人与非工会的工人之间的对立、不同的雇佣阶层相对立的利益”无一不是萌发经济主义问题的重要条件。[6]
针对经济主义困境,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之道。其中,罗莎·卢森堡提出了自发性策略。在观察俄国工人阶级反对沙皇专制的革命后,卢森堡发现罢工的三种特征:第一,是革命的经济面向与政治面向存在持续的相互强化过程。第二,罢工是由局部到整体的演变过程,也就是说,针对局部经济需求的运动会转变为抗争的一种典型或象征,进而点燃和催生其他领域的运动。第三,罢工具有不可预期性,无法预期出现的时机与扩展和普及的形式,超出了运动领导者的控制和组织能力。[7]
与之不同的是,列宁认为,要通过自觉性策略才能使工人阶级消除经济主义倾向。对列宁而言,自发性策略的局限在于工人只受资本主义思想体系支配,不能在运动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因而需要从外部,也就是经济斗争之外,向工人灌输阶级意识,使工人生成自觉性。而这种阶级意识的灌输来源则是由革命知识分子所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政党)。[5]
在卢森堡的自发性策略与列宁的自觉性策略的基础上,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又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的策略。葛兰西将文化领导权视为对意识形态支配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主导阶级通过“神秘化”的方式使从属阶级产生“虚假意识”。主导阶级对从属阶级的支配方式并非是制裁或强迫,而是取得从属阶级的认同或同意。这一同意过程通过“阵地战”而非“运动战”来实现,即通过学校、媒体等公民社会中的培养机构。由知识分子组成的革命性政党为从属阶级提供新的概念工具和“批判意识”,打破并建立新的文化领导权。[8]然而,从天津搬运工人改造的现实语境来看,并不充分具备运用以上社会主义策略的条件。首先,由于工作性质使然,搬运工人通常地域分散性广,工作时间弹性大,不易组织大规模学习,不完全符合葛兰西所说的“阵地战”的条件。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就工人身份而言,经典的社会主义策略,无论是自发性或自觉性策略,还是文化领导权策略,之所以能有效施行,因为都隐含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假设:将工人阶级视为没有身份差异的统一体,虽然这种统一时常具有象征性意义。与此不同的是,搬运工人身上所呈现的复杂身份网络实质上消解了阶级的同一性。
这一工人阶级的身份多样性视角已被后继学者所关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来自裴宜理对20世纪20年代上海工人罢工的观察。她发现工人阶级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共产党人会灵活利用工人的帮派身份组织罢工。以纺织工人为例,共产党人通过歃血结拜活动等方式,建立和巩固工会,并在罢工斗争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然而,在团结码头搬运工人进行罢工的过程中,工人的流动性、行业内部的分裂以及把头的权威,反而使共产党人在工人中的开拓收效甚微,帮会身份成为了“壮大革命势力的重大障碍”。[9]这与建国初期天津共产党人改造搬运工人的实际困境可谓如出一辙。

表1 社会主义策略工人身份的不同类型
诚如郭圣莉所述,解放初期的共产党人实际上运用阶级净化机制,消解了基层骨干的复杂身份,实现了基层社会身份的统一化。更需要看到的是,消解和统一阶级身份的过程,其实也是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换句话说:“新政权一方面……清除敌对异己力量, 保证组织人员对国家的忠诚……另一方面,将社会问题予以这一清除过程中加以解决……通过它构建国家的社会基础体系。”不仅如此,这一阶级净化过程的实施重点“不是阶级敌人的具体身份与活动,而是依据不同时期工作重点的不同在这种身份活动和阶级敌人之间构建实质的联系。这一联系使潜在的敌人不断的现实化, 从而构成以打击敌人的方式整合社会的机制”。[10]初入天津的共产党人运用“民主评议”策略,在实现阶级净化的同时,彻底根除了经济主义问题。“民主评议”策略也为阶级净化机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微观基础。
三、“民主评议”与青年搬运工人改造
在组建工人服务站后,党员干部意识到:“脚行头子很容易打倒……最难解决的是行会主义和封建割据,(它们)在工人中不仅已成为群众性的东西,工人的思想难以打通,即使在干部中有时也打不通,他的社会基础是很深的。”④天津市公用局,《市运输公司1949年搬运工人工作总结》(1950),津档,152-1-16,第28页。而造成这种表现为“行会主义”与“封建割据”的经济主义困境,其深层原因实际上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身份认同,诸如青帮的师徒关系、黑旗队的兄弟情谊、国民党和三青团的主从故交关系等。组建“各自为政”的服务站体系显然无法攻破这座传统身份的堡垒。为了彻底改造搬运工人,天津市委决定组建执行改革任务的两大重要机构:搬运工会与运输公司。前者的任务主要是在全市范围内重新甄别搬运工人,并组织和培养工人积极分子,为后续的“民主评议”做准备;而后者的目标则是通过“民主评议”的改造策略,统一合理运价,统一调配工人,公平利益分配,提高运输能效。
(一)“民主评议”的前期准备
1949年6月间,天津市委成立了搬运工人工作委员会,着手在搬运行业中广泛了解实际情况。经讨论研究,最终确定了运输系统改革的政策宗旨,即“团结全体工人,消灭封建压迫与剥削,取消封建割据和帮派行会”。⑤天津市总工会编,《天津工运史资料》(第三册),津档,44-1-1094,第19页。截至1949年8月底,已吸纳工会成员31200多人,建立支会103个。如何通过加强基层小组的组织工作,成为这一阶段市搬运工会的工作重心。
1.甄别工会成员
为了消除由传统身份关系而建构起来的行会主义思想,针对工会基层小组内部的身份甄别与骨干筛选工作势在必行。工会干部们逐渐意识到,在与脚行剥削制度的斗争过程中,“一些过去行为不正、历史不清、能说会道的分子……充当了‘积极分子’;同时亦有个别正派的工人,当选干部之后,开始贪污、不民主、脱离群众”。⑥同④,第106页。这些组织中的真正落后分子,整天喊打倒脚行之言,却行取而代之之实。
为了尽可能将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基层工会的同时,也让更为可靠的工人担当起骨干分子,市搬运工会展开了全市支会的民主生活与会员审查工作。这项重要工作旨在“净化”工会队伍的阶级成分,主要由工人通过民主化的方式进行互相审查。“开始有的会员对干部有意见不敢提出,经过发动,互相间进行了批评,不但对支会委员提出批评,而且对分会脱离生产的老干部当面提出批评。”因为搬运工人的流动性很大,彼此之间不相识,阶级异己分子或许能凭一时伪装进入工会来。但经过一段工作,等他们原形毕露,工人群众自然就可以把这些分子甄别出来。
审查工作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大致可分为三类:(1)伪军警、黑骑队、国民党、三青团、青红帮之类的身份复杂人员;(2)脚行头、车主或畜主等有基本生活来源的人员;(3)过去恶迹昭著的行凶分子、贪污分子或惯偷。⑦同④,第107-108页。如在铁路装卸工会的工人审查中,共有87人被清除出工会,其中有65名脚行把头,9名不劳而获人员,3名职业小偷。另外,一批运输工会的落后工人代表与工人队长,三轮工会的车厂主,以及国民政府时期的警察和工会负责人全都被洗刷出工会队伍。等各区支会相继完成了内部审查工作,市搬运工会才着手分发会员证,不再让已被驱逐出工会的落后分子有机可乘。
2.培养工人积极分子
在搬运工会的实际组建过程中,进行工人的阶级教育更是持之以恒的核心工作,因为只有持续的阶级教育才能持续涌现出可靠的工人积极分子,进而才能不断深入基层工会工作。然而,在基层工会建立之初,绝大多数搬运工人对何为中国共产党只有模糊的认识。他们将政权变革前后的差别简单归结为解放后的工作条件有了改善。[11]
为了有效提高搬运工人的思想水平,1949年8月,各区支会普遍组建起针对阶级教育的学习组织。比如,运输二分会参加学习的就达600~700人。起初,这种学习组织多以小组为单位,或几个小组合并起来,自由结合。少则6~7人,多则十几人,利用工作闲暇,做定时或不定时的学习。学员之间互相鼓励,先进带动后进。后来,除了建立这类学习小组之外,各区支会又组织起人数较多的业余学校,规模少则20~30人,多则70~80人。以大班授课的方式,讲解一些与搬运工人的阶级思想和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议题,诸如工会问题、搬运工人与交通规则、社会发展史,等等。教授者多为分会干部或之前毕业的学员,并涌现出一批学习骨干。
更需要看到的是,这种业余授课方式常常带有轮训的性质。每次以支会为单位,抽取其中的支会干部与少量工人轮流参加。如果一个支会来参加学习的共有70人,那么,这一般是由每个小组各抽出2人的总和。考虑到工人的学习小组虽经组织起来,但由于缺乏指导,加之平日工作又忙,流动性又大,因而时常不能坚持下去,“尤以三轮工人,往往走到自流或强制”的地步。[1]所以,在繁重的工作与学习压力下仍能持续兼顾的学习骨干,就可以看成是工作可靠并有意向党靠拢的工人积极分子了。
到1949年9月份,从业余学校的培训班规模来看,全市搬运工会的积极分子数量已达到200人左右。[11]这些通过阶级教育而被选拔出来的积极分子,固然对改造基层干部、改造工人内部思想作风大为有益,但与此同时,搬运工会仍要求积极分子不能脱离生产。早在服务站的组建过程中,党员干部就已清醒地认识到,工人代表一旦脱离生产,不仅会养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而且也是贪污腐化的重要根源之一。所以,“不能因为他们是积极分子或支会干部,把一切工作推给他们办,使他们过分的耽误生产时间,影响到生活,不能坚持下去,使积极分子变成消极分子,倒下去,这是很重要的”。另外,市搬运工会的干部在鼓励积极分子的优点的同时,也会时不时批评他们的缺点。只有这样,“才能在群众中使积极分子,起他们的积极作用”。[1]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系统的文化启蒙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搬运工人积极分子对党的政治认同。
(二)“民主评议”的改造策略
在搬运工会成立后,天津运输系统仍面临两大难题:其一,如何达到运力与货量之间的平衡。也就是说,过剩的运力供给不但会造成劳动力的浪费,而且还会影响运价,并最终影响到工人的生活水平;搬运工人眼下又是城市经济生产不可或缺的有生力量,理想的状态是在搬运工人规模与待运货品数量之间基本做到供求相抵。其二,在维持甚至增加搬运工人现有收入的情况下,如何大幅降低运价。
1.在搬运工人中开展“民主评议”
为了解决这两个难题,只有将相对低效的现有运输系统重新编队重组,才能进一步整合全市现有运力。1949年8月,天津市委决定由运输事务所组建天津市运输公司,并抽调得力干部,组成编队工作组。自1949年9月1日起,开展全市范围的搬运工人编队工作。在党员干部看来,无论是“改善劳动机构”,还是“实行合理运价”,都只是“我们完成任务的具体办法”。而“打破封建割据”与实行统一调配才是“我们的政治任务”。由此,为了达到这一根本的“政治任务”,就“必须同时进行发动群众,反贪污,改善劳动机构,实行合理运价的斗争”。⑧天津市总工会编,《天津工运史资料》(第三册),津档,44-1-1094,第19页。运输公司的党员干部正是通过民主评议的方式完成了这一改革任务,并加强了搬运工人的政治认同。
在编队开始前,运输公司的编队工作组会同搬运工会,预先成立评议小组。每组配备工作团干部及工会干部3~5人,这些干部大多源自工会阶级教育所培养出的工人积极分子。除此之外,评议小组还会吸收7~9名该区的一般工人作为群众评议员。显然,评议的首要目的是要把藏匿在服务站中的阶级异己分子与贪污分子清理出工人队伍,而熟悉内情的评议员则被赋予权力,去一一确认队内与组内存在哪些行为不端的小团体和组织,哪些队员有过贪污行径,等等。[11]这意味着,身肩重任的评议员必须符合相对严格的基本筛选条件:第一,雇工或只拥有一辆车的车主;第二,工龄在2年以上。这样就保证了被指定的评议员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阶级成分进步,并为大家所熟知。当然,评议员也少不了另一项必备的条件:已经成为“思想纯洁、工作积极、忠实坦白、诚恳直爽”的工会会员。这样就把拥有传统身份的阶级异己分子与思想落后的贪污分子排除在了人选范围之外。⑨天津市公用局,《市运输公司1949年搬运工人工作总结》(1950),津档,152-1-16,第8~9页。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评议员的发现与产生绝大部分是编队干部们开展预先调查的实践结果。早在编队之前,运输公司的党员干部与五区的工人积极分子就已深入各分队了解情况。首先,在人员材料的调查上基本做到一一比对,也就是说,将分队工人的情况记录与派出所的户口登记册做详细比照,筛选出拥有传统身份的全部人员。其次,在与工人谈话的过程中,“找出较好的工人,争取教育他,提高其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分化其内部封建集团组织”。第三,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分队的运输情况与过往历史,干部们往往会找到既熟悉内情又忠诚老实的老工人,进行个别谈话,针对性地询问各类落后分子的真实情况,并“作为我们的调查员,给他们布置调查工作任务”。[1]由此,编队干部在获取大部分背景材料的同时,也易于发掘出相对可靠的评议员人选。
在评议员确定后,编队干部会通过集体训练和思想准备工作的方式,端正评议员的态度,并向他们解释合格队员的7条基本标准:“(1)脚行头,土棍恶霸,曾欺压过工人的:甲、必须悔改前非,工人同意,准其参加。乙、即使悔改,而不实际参加劳动者,亦不准其参加。丙、即使悔改,其家生活富足者,亦不准其参加;(2)商家大车,以此为投机事业者,其车看工人情况,酌量处理,其本人不准其参加;(3)农民大车不准参加;(4)逃亡地主不准参加;(5)已经转业的搬运工人,不准其参加,如转业摊贩暂以谋生者除外;(6)不劳而获,老头寡妇小孩,老弱残废不能工作者,劝其出队,酌量给以解职费;(7)解放前不是搬运工人者,不准其参加。”⑩天津市公用局,《市运输公司1949年搬运工人工作总结》(1950),津档,152-1-16,第9~10页。
以五区各分队的编队过程为例。开滦矿工人代表臧某某、蔡某某等集体盗卖煤斛多达140吨。另外,除了服务站抽取5%的管理费,他们还假借办公之名,从工人的运费中抽取5%。更有甚者,臧、蔡等人竟随便动用公款,另雇游散汽车4辆,加入平日运输,为的是从中抽取30%。这类工人代表账目从未公开,也不许工人过问,几天之间就贪污公款185600元。五区不劳而获的代表“先生”共有84人,导致工人负担很大。为了弥补因抽成而减少的收入,工人们在承揽业务时不得不再次抬高运价。在未编队前,承揽业务与分配工作的权利完全掌握在工人代表手中,这就直接造成老实肯干的工人领不到活,而蛮横调皮的工人或与他们有往来的工人才能分配到好工作。
在明确摸清了五区的种种问题后,编队干部们随即集合五区全体队员召开评议大会。在会上,干部们首先详细说明了编队的好处。他们先估算出工人每日的平均运输量,并按照当时的市价与工人的基本需求,制定出合理的运输价目表。如五区编队后规定:按玉米面换算,3里以内每车每吨货物运价12斤,5里以内15斤,10里以内18斤。因搬运工人劳动量大,食量也大,需要细粮助长力气,所以,每日三餐至少需要6斤玉米面。成家以后,工人家中一妻两子女生活在都市中,一切都指望工人收入,而每日一家的生活费最低12斤玉米面。此外,如疾病、工作不稳定,以及衣服鞋袜、用具折旧、赡养等日常费用,都需从运费中支用。按照日常货物量每天运两次,3里以内每人每日所得9.6斤玉米面,5里以内12斤,10里以内14.4斤。⑪天津市财经委,《运输公司关于运价及搬运费用问题的计划、方案、报表》,津档,77-3-2726,第13页。较之平日里屡受工人代表的抽成与欺压,这样的价目表基本保障了个人和家庭生计,自然获得了绝大多数工人的拥护。另一方面,新的运价大约只占到服务站时期的三成。这意味着,势必要有人来承担过去“浪费”那70%部分的责任。
在联系了广大工人利益的基础上,编队干部们开始充分发挥评议员的积极作用。如第三组进行评议时,由评议员当场指出工人代表臧某某侵吞公款,剥削工人。经会上决议,将其扣留,并移送人民法院审理。当然,整个评议过程最为重要的还是要经过绝大部分的工人群众同意。只有充分发挥群众的民主力量,才能“打击并教育坏分子,团结真正的劳动工人,整齐工人自己的队伍”。[1]
2.逐区重组
除了在单个服务站内部进行编队重组,以打破工人的经营割据思想,运输公司同样也将注意力集中在不同服务站之间的区隔上。在完成对三、五、八、九、十一区的编队工作后,运输公司的党员干部开始与公司私营企业以及车站码头等有多余托运物资的卖主订立合同,统一负责托运业务。就像干部们所说:“做了一点再做一点,这样对我们自己是稳步前进,对封建割据是蚕食政策。”考虑到封建割据的核心即是“个人利益的饭碗问题”,所以干部们掌握住工人个人利益这样中心一环,“在不妨害他的饭碗条件下施行统一调配车辆”。比如,东站与东西货厂的货多,但运输力少,外调一部分运力来补充其不足,对工人饭碗无多大妨碍,本地工人易于接受。为此,运输公司将三、八、九、十一区的一批无活干的工人调到东西货厂谋生,并借机向工人进行了教育说:“你们无饭吃现在给你们找饭吃,还是统一调配车辆好吧,今后其他地区工人到你这里来,你也不可以再施行封建割据。”
等到又完成几个区的编队工作后,运输公司就开始实行全市统一调配车辆的计划,亦即“把所有托运物资,完全控制在我们手里,把公司私营企业托运物资,直接交由我们转运,我们掌握了物资,我们即可随意调配车辆”。那时,工人因为直接受惠于运输公司,自然容易接受领导。除此之外,对于那些游离于服务站系统的散车,比如由不劳而获的脚行头子、妇孺老少私自雇人运输,运输公司均暂时置之不理,对这些人采取不宣而战、分别处理的办法。也就是说,“较好的脚行头,能劳动者酌量编入队内给以一定工作,有钱者可劝其转业经商等,分别团结分化蚕食的分别处理,使他们都有饭吃,有步骤的稳步前进”。当然,酌情吸纳的前提是,“对运输力及货物托运对象,两项对比加以核算,足以维持工人生活”,否则,干部们一律杜绝随意吸收工人的现象发生。由此,自1949年11月下旬起,全市运输系统都由运输公司统一调配、统一定价。据测算,公司设置5%的管理费,每日平均为1300余万元,按现价750元折合玉米面17333斤,约计一个月的收入为3亿9千万元,折合玉米面519991斤。由此可知,天津市全月的运费需要78亿元,全月78亿元的运费减去了80%的运价。如果换算成100%的运费,每月则需要390亿元。现在每月减去了312亿元的运费,也就是每月为天津工商业节约了312亿元的运输成本。⑫天津市公用局,《市运输公司1949年搬运工人工作总结》(1950年),津档,152-1-16,第22页。
截至1949年10月28日,全市搬运工人总数下降到45711人。换言之,相比于1949年8月28日的统计数据,通过转业等方式,搬运工人总人数已下降近三成,大大提高了全市的运输效率。[12]更为重要的是,从11月下旬开始,天津的平均运输价格比服务站系统在1949年4月7日所定的价格,降低了80%。⑬同⑫。[5]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旨在“统一合理定价”与“统一组织调配”的运输公司基本实现了天津运输系统的彻底改造。
与传统社会主义策略的理论视角不同,研究揭示了“民主评议”策略在克服工人阶级“经济主义”问题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对解放初期天津搬运工人改造的案例分析,着重考察了中国共产党运用“民主评议”策略的具体实践过程。在甄别工会成员与培养积极分子的基础上,初入天津的共产党人广泛开展搬运工人评议与重组工作,扭转了工人中存在的“经济主义”倾向。最终,在大幅降低全市运价的同时,实现“统一合理运价”与“统一运输调配”,取得了天津运输系统的领导权。研究发现,与既有理论中的社会主义策略相比,“民主评议”策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差异之处。第一,在实施条件上,“民主评议”策略将工人身份的多样性而非统一性视为解决“经济主义”问题的主要依据,使“抽象”的工人阶级变为“现实”的工人阶级;第二,为达到纯化工人阶级与解决相应社会问题的目的,共产党人旨在消解工人的帮派身份而非利用帮派身份;第三,“民主评议”策略兼有“运动战”与“阵地战”特征,通过轮训培养工人积极分子,并在公开的评议过程中,迅速获得绝大部分工人群众的同意,充分发挥群众的民主力量,纯化工人阶级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