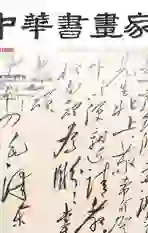零公里
2021-09-21刘庆祥
刘庆祥



经过两个小时的飞行,从厦门机场转乘大巴,在通往闽西的高速公路上,向一块镌刻着“零公里”的石碑进发。那里是一次远征的地理坐标,铭记着一个政党的初心。
一
南国初冬,没有北方的萧瑟。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的闽西,山峦耸峙,群岭连绵,一片青碧从眼前铺展开去。晴空朗日下,原野静谧安然,这里已经没有一丝当年战火硝烟的痕迹。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车内回响着杨洪基低沉雄浑的男中音,歌声与毛主席这首《菩萨蛮·大柏地》的豪迈相得益彰,使人心生肃然。
毛主席诗词,再现了当年眼前景色和巨人的遐思。苍穹之下,雨后初霁,关山如黛,彩虹高悬,不知是谁,扯下彩虹,当空炫舞,舞出了满天云霞。一番渲染之后,关山与村舍本应披霞戴翠,却因弹痕累累变得愈发“好看”,更与“当年鏖战急”、生死难料岁月形成反差。十几岁时,虽然对这首词闭目能诵,却无法理解其中的真意。直到此刻,恍然顿悟,当年主席看到斜阳之下的似火云霞,恰似已经点燃的革命圣火,正在形成燎原之势。诗中蕴含的是巨人才会有的浪漫主义情怀。
车载电视里传来婴儿的哭声。抬头看去,电视镜头里,路边瓢泼大雨中,透过几名红军女战士油布雨伞撑开的雨幕,一个女人躺在担架上产下了一名女婴。产妇,面色苍白,军装全湿,头发打成绺,滴下的不知是雨水还是汗水。她脸上勉强挤出的一丝微笑,似是女儿出生的喜悦,又像是对惊慌失措人群的安慰。刚刚降生的女婴,父亲是共和国缔造者之一,妈妈是位著名巾帼英雄。这个被“神祇”眷顾的孩子,福祉却没有随之降临。在她嗷嗷待哺之时,离开了妈妈的怀抱,被送入一户寻常百姓家。从此,那个孱弱的生命消失在茫茫人海。共和国成立后,那位特殊的“女婴”,虽然没有被遗忘,却没有受到一丝父母光环的恩泽,更没享受一天都市生活的优越。这一别,她与父母再没相见。她与亲生父母,在两条平行线上走了一生,却没有再牵过一次手,她的人生一直没能走出闽西的大山。在闽西这块红色土地上,这样的故事,当年不知发生过多少。
二
大巴在向前行驶。从漳州、龙岩到上杭,眼前是开阔的四车道高速公路,窗外是武夷山余脉。一片葱茏掩映着道道山岭,此起彼伏。相向而来的一片绿色,从车旁飞速掠过。前方,大山深处,是此行的目的地,是那些革命先驱走出大山的起点。
目视窗外群山,想象着当年红军在高山密林里的情景。脑海中萦绕着诸多疑问,高速公路时代,当年红军穿梭征战的小径呢?大概已经被丛生的荆棘湮没了吧?
经常出差,养成一种习惯。出发之前,喜欢打开谷歌地球,查找目的地的地理风貌和具体方位,闽西地区地理位置是最难寻见的。城镇和村庄,隐匿在山岭形成的褶皱里,一片莽莽苍苍之中,呈现出一个个斑驳小点儿,恰似滄海一粟。一眼便知,这是一个避难求存的好去处,这里的居民,也无一不是因避难到此。我还知道,就是这片丛林抚育了摇篮中的中国革命力量。
三
下榻上杭开元客家酒店,站在酒店广场,即可遍览上杭县城。这座千年古城风貌,和很多城市一样,湮没进一片现代建筑中。绿道,镶嵌于汀江两岸,是近年上杭县打造的沿江风景带。落日余晖里,汀江这条客家人的母亲河,在两岸盎然绿意簇拥下,澄净如练,散发着温暖仁厚的晖光。绿道沿江,美如缎带,如织游人漫步在汀江两岸,一派闲适祥和。
在开元酒店小住期间,时常到此散步。有时,面对汀江瞭望沉思,希望唤起叙写当年的灵感,眼前已经难以寻觅它曾经的样子。与当地人攀谈,当年红军的往事,已经少有人知道,即使略有了解,也只是细枝末节。90年前,万名地方武装,肩扛云梯,手持大刀长矛,配合毛泽东、朱德主力红军攻打上杭县城的战斗情景,难以与眼前这座美丽县城联系在一起。那些往事,似眼前的江水,随着时光河流已经远逝。
出酒店,广场左侧是客家族谱纪念馆,这座占地35000平方米的建筑里,承载着客家人和畲族人的历史,还寄存着他们避居大山的背景故事。
1929年初春,这里来了一支特殊军队。他们脚穿草鞋,有的头戴斗笠,有的身披蓑衣。身上的军装五花八门,有的身穿国民革命军的服装,有的身穿农民起义军服装,有的直接是当地农民装束。虽然春寒料峭,他们中很多人已经把裤管撕掉,改成粮袋背在身上,长裤变成了短裤。一些人的上衣,因撕掉袖子补背襟,以至于背襟越补越厚,衣袖却越撕越短,长袖变成了短袖,到达闽西时已经个个衣衫褴褛。他们来到这里,却不为偏安一隅,而是怀揣伟大梦想,这些人就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工农红军。他们从井冈山到赣南,再到闽西,在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中,已经艰苦转战两个月。
长汀一战,红军取得入闽第一战胜利。击毙国民党军十七军六师第六混成旅旅长郭凤鸣,缴获大量物资粮饷。没收反动豪绅的财产、向富商筹借军饷,筹得大洋5万元,红军经济状况得到根本好转。在长汀,红军战士第一次发放军饷,每人拿到4块大洋和一顶斗笠。郭凤鸣的军服厂,被改造成红军被服厂,毛泽东、朱德、陈毅亲自参与设计,生产出我军建军史上第一套军装。
红军女战士,经过长达数月的转战奔波,在长汀得到修整,手里拿到4块大洋,压抑已久的爱美之心被唤醒。有位当年的女战士回忆说:“四块大洋,是我生来头一次有这么多钱。”她拿上这些钱,来到被称作“红色小上海”的长汀街上,花一块钱,买了毛巾、牙刷、袜子、皮底布鞋等,剩下的钱,放进背包珍藏起来。一时间,头戴八角帽,身着灰布军装,裤脚绑着裹腿,英姿勃发的红军女战士,成了长汀街上的一道风景。
红军所到之处,贴标语,搞宣传,搭台演出,开仓分粮接济百姓。城镇街道,随处可见用红色油漆书写的“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等标语,到处一片鲜红,“像过年似的”。不少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军,红军队伍,迅速由2000千余人壮大到4000多人。
四
唐代诗人李贺《梦天》中有:“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正如诗中描述,时光荏苒,倏忽之间,距离那场革命风暴已近百年。
今天,从天外鸟瞰地球,已经无须通过想象,仅靠一只鼠标,上天入地只在恍然之间。在谷歌地球上,武夷山像一条巨蟒,横亘闽赣两省之间,它的南端,一片葱茏掩映着山冈,俨然一方净土。在这样的宁静背后,人类社会在阶级分化与博弈中,经历着海潮般的汹涌与更迭,美好的祈愿恰如教堂和庙宇里传出的和谐乐章,始终无法平抑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19世纪40年代,儒家文化濡养下的东方,正酝酿着一场剧烈风暴。这里,经过了两千年沉寂与封闭,发酵出升腾的热流,在地面形成“负气压”。一股西方势力,随着“气压”牵引,带着海洋的阴冷潮湿乘虚而来。它们相互作用,形成强大气旋,中华大地刮起强烈飓风,矗立两千多年的封建大厦陷入风雨飘摇。大山再也阻断不了世界的纷扰,这里也失去素有宁静。伴随这股西方潮流而来的还有一颗马列主义种子,它经北方毗邻之国而来,被中国共产党人带到了这里,从此生根发芽。随之,一场革命运动在这里兴起。
就那段历史,与人产生过一次争论。那个人说了这样一句话:“把人家的财产抢了,分了,砸了,甚至把人给杀了,总不能说是对的吧?”
这个让很多人产生疑惑的问题,我把它带到了闽西。
走进这片大山,发现它早已失去旧有样貌,百年时光,让那段历史蒙上了厚厚尘埃。千寻百度终于发现,毛泽东的《调查报告》承载着那段历史的真相。从其中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看到了那些疑惑的答案。
迄今为止,我从没有发现哪个人像毛泽东那样钟情于调查研究。自1927年至1934年红军长征,7年战争岁月,毛泽东共进行过9次调查,写下数十万字的《调查报告》,仅《寻乌调查》就长达8万多字。字里行间透着他对那些文字的执念。《寻乌调查》报告前面有这样的一段话:“我过去做过七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的手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横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寻乌水,从桂岭山盘古隘一带山地发源,经澄江、吉潭、石排下、车头、留车,流入龙川,下惠州,故寻乌水乃是东江的上游……”这样的叙述,如不是通读原著,很难感觉到这是一份《调查报告》的内容。
“先生,借点钱给我吧!”
“没有啊。”
“那借点谷子给我吧!”
“没有啊。”
“吃不上饭了,总得借点儿啊!”
“倒是有油,可是那是儿子家的啊。”
这又是《寻乌调查》中一段地主与农民的对话,反映出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向地主借债时的情景。这里面地主农民各有算計。农民希望借钱或粮食,地主则愿意借给油。因为油不仅利高,农民借到也舍不得吃,还得到集市卖掉换回粮食。
《寻乌调查》,五章三十九节,洋洋洒洒8万字,像是一本百科全书。地理位置、历史沿革、行政区划、自然风貌、水陆交通、土特产品、商业往来、商品种类、货物流向、税收制度、人口成分、土地关系、阶级状况、剥削方式、土地斗争等等,无所不有。《寻乌调查》像幅赣南地区社会图景,为研判当时革命形势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今天,依然能从中看到当时“干柴遍野,处处生烟”的社会境况。
武夷山另一侧,闽西上杭县有一个才溪乡,当年曾被誉为中共苏区“第一模范区”。1933年,毛泽东在这里也做过一次调查。
五
走进才溪,当年那些百年老屋的砖墙上,依稀可见“打土豪分田地”“国民党是土豪绅”“扩大红军”“冲破敌人经济封锁”等标语。才溪区苏维埃旧址、列宁堂,这些没收归公的地主老宅,依然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
列宁堂,是一座砖木结构客家风格民居,原为王氏地主家的宅院。1929年农民暴动没收充公,成为才溪区工会办公地,为纪念列宁诞辰60周年命名为列宁堂。这座老宅的东厢房,有一个大约四五平方的房间,里面放着一张小桌,一把竹椅,还有两个条凳支撑床板搭建的简易木床,这里就是毛泽东第三次才溪调查的临时居所。
在才溪,毛泽东白天下公田干活,闲暇帮红军家属挑水劈柴,晚上与群众促膝谈心,了解民情。农民家夜晚昏黄的灯光里,缭绕的烟雾笼罩着他伟岸身躯,闲谈中,一阵阵笑声不时从农舍飘出;井台旁边,他边洗衣服边与群众攀谈,家里人口,土地田亩,水稻蔬菜无所不及;列宁堂里,几张桌凳,依稀让人想起区乡干部在这里开调查会的情景,那些音容笑貌就在眼前。翻开史料,红军烈属林俊,苏维埃干部王兴旺,贫苦农民银连子、孔菊姑、太生子等等,每一个名字都连着一段毛泽东走访调查的故事,其中饱含着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感情,至今散发着穿越时光的温暖。
怎么发动群众应征当红军?红军家属如何照顾?干部选拔如何进行?怎样组织妇女、老人搞生产?一系列问题在这里得到解答,为红色革命根据地建设提供了范例。
十几天时间,毛泽东在列宁堂几平方米的东厢房里,就着油灯的光亮,写下了数万字的《才溪乡调查》。《报告》中记载:“长冈乡全部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至四十五岁)四百零七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三百二十人,占百分之七十九。上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至五十五岁)五百五十四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四百八十五人,占百分之八十八。”“第一模范区”干部群众参军参战的热情,和这块土地为红色革命根据地所做贡献,由此窥见一斑。
六
1935年,国民党统治下的闽西,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6月18日这一天,风和日丽,长汀街上少有的安静,中山公园附近传来一阵嘹亮歌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那是一个人在引吭高歌,用中文、俄文交替歌唱。歌声虽然带着特有的悠扬,在当时的恐怖气氛下高唱这样的禁歌,还是不由令人心生惊悚。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总书记瞿秋白临刑前留下的绝唱。
他是一位坚贞革命者,气质里更是一个文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他虽然不是厥功至伟,但面对国民党的劝降,他对党表现出的忠贞不渝态度和就义时的从容,成就了一场完美浪漫主义悲剧,完成了人生典雅谢幕。
在他的长文《多余的话》中写道:“我小时候,确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维持。”以此剖白自己的生活态度。
他确实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保持了绅士的体面。据国民党行刑官、时任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回忆:瞿秋白生命的最后一个多月,除了面对劝降谈话,每天都是刻章、写诗、习练书法,再就是用毛笔写那篇长文《多余的话》。時间一久,敌人防范意识渐淡,有人开始向他求取书法作品或印章,他每每有求必应。在与敌人相处一个多月里,他甚至得到了三十六师师部各级军官的敬重,这大概是他行刑前得以维持“绅士体面”的缘由了。
临刑前,有人到瞿秋白的囚室,将蒋介石的处决电令交予瞿秋白,他只淡淡看了一眼,面色没有一点变化,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行刑时不要毁坏他的面部。9时20分左右,瞿秋白在政训处长蒋先启的陪伴下,走出他住了一个多月的房间,仰面看了一下四周,走出大门,在场的人既震惊,又感动。
在瞿秋白纪念馆,有一幅瞿秋白行刑前的遗照。看到这幅照片时,我不由惊诧,这哪是刑前遗照,分明是一幅郊游时的闲适之作。他身穿修身的黑衣白裤,两腿自然分立,两手背于身后,站在一座亭子前,姿态从容优雅。一头短发,使他更显年轻,俊秀的脸略微上扬,目视着前方,双唇微闭挂着浅笑,一副悠然自得。
据说,就是在身后这个亭子下,他开始的人生告别仪式。面对四碟小菜和一壶酒,他主动邀人陪饮,见无人上前,便开始自斟自饮,席间不时起身面对敌人高谈阔论,发表演讲。餐毕,他起身缓步来到亭子不远处一片草地,回头面对行刑人员微笑着说:“此处甚好。”而后,背对人群安然坐定,枪声响过,他的人生终止在36岁那个年头。
七
在地球上,无处不铭刻着关于人类的记忆;在闽西的群山中,无处不有先烈们的血迹;地处连城与长汀交界的松毛岭,就是一座用鲜血熔铸的丰碑。
1934年9月,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历时一年的第五次反“围剿”终告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组织战略转移,为保证战略转移顺利实施,中央红军组织了长征前的最后一役——松毛岭阻击战。
中央红军红九军团、红二十四师6000余人,加工人师、地方赤卫队和群众支前队伍总共约3万人,在松毛岭一线设防,与国民党6个整编师、1个炮兵团共7万多人,展开殊死激战。
敌人在强大炮火和飞机配合下,向红军阵地反复冲击。红军只能以落后的轻武器,依靠险要地形进行拼死抵抗。在敌人狂轰滥炸中,红军阵地和指挥所几乎全部被摧毁,战况极其惨烈。据支前民工回忆,当他们送饭到松毛岭唐牯脑,阵地上的100多个红军,已经没有一个人会吃饭了,阵地被炸平了,壕沟看不到了,指挥所的地堡也没有了,碎瓦片子到处都是,只剩下几个伤员已经奄奄一息。他们赶紧帮救护队砍伐毛竹做担架,把9个重伤员抬到长汀南山的钟屋村红军野战医院。
经过七天七夜激战,雨后的松毛岭战场惨不忍睹。所有的水都混着血、漂着尸。飞机轰炸中,红军战士的皮带、衣服被炸得满天飞,挂在高高低低的树上,有些烈士的断肢飞出去三十米远……
整个战役过程中,地方政府积极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兵员源源不断得到补充。据当时的《红色中华》报道:9月26日,战事正处于最激烈的阶段,长汀县紧急动员新战士1300名,向着2000人的目标奔进。由于战局紧张,当地群众参军支前踊跃,大部分新兵和支前人员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松毛岭战役,牺牲的万余名红军战士和地方赤卫队员,几乎都成了无名烈士。红24师几乎全部阵亡,团职及以下军官无留下姓名,今天资料里所能查到的只有师长周建屏一人。
1934年9月30日,红九军团就是在这里举行告别群众大会,正式撤出松毛岭战场。为钟屋村赤卫模范连、少先队发放枪支弹药,跟随部队一起转移,当地干部群众就地疏散。后来,赤卫模范连、少先队都被编入红九军团,他们和数万闽西儿女一起汇入长征大军。长征结束的时候,他们中86%的人长眠在了长征路上。有人说,在二万五千里漫漫征途中,每五百多米就有一位闽西儿女的尸魂。
红军长征后,陷入白色恐怖的松毛岭,漫山遍野都是红军尸体,无人敢收敛掩埋。腐尸招致红头苍蝇压弯了树枝,随之瘟疫暴发。松毛岭附近村民,不顾生命危险,偷偷组成“无祀会”,发动群众上山就地掩埋烈士遗体。随后,再次收敛红军遗骸,购置金盎、大缸,选择“风水宝地”,挖出方圆一百余平方米的深坑,对红军烈士集中入殓安葬。下葬之时,当地群众按客家人习俗,举行了隆重“倒粥”祭祀仪式。此后,仍有烈士遗骨陆续被发现,这项为烈士安葬遗骨的工作,在村民中代代相传,一直持续至今。
我终于见到了“零公里处”纪念碑,它位于钟屋村(现中复村)“观寿公祠”门前。碑身由一块约一米高的不规则石块雕刻而成,不是想象中的高大庄严。第一眼看到它,心里似生出了一种淡淡落寞。再次审视,它又像一件伤痕累累的圣物。残缺的碑身,恰如一名勇士的身躯,那些粗粝的斑痕像是无数只眼睛,它们在注视着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诉说着那些曾经的故事。
责任编辑:陈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