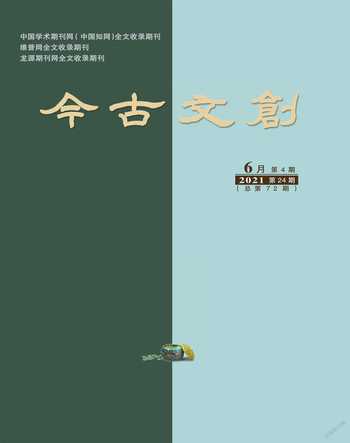“后文本” 研究的力作
2021-09-10李永
李永
【摘要】《〈三国演义〉诠释史研究》一书,以历史上对《三国演义》的种种解读为研究对象,是首部对其诠释历史进行梳理的著作。该作关注“后文本”,开拓了《三国演义》研究领域;关注诠释者,注重探求不同诠释特点形成的原因;在结构模式、写作思路上该书也有独到之处,是《三国演义》研究史上一部独辟蹊径的力作。
【关键词】《三国演义》;诠释史;读者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4-0034-02
《〈三国演义〉诠释史研究》是郭素媛教授近年倾心之作,是首部从诠释学视角关注《三国演义》的著作。该作上编纵向梳理了自明清到现代诠释者对《三国演义》的解读及海外的诠释情况;下编横向梳理了《三国演义》社会功能、思想、人物的诠释及戏曲、曲艺等艺术形式的解读。该作紧扣历史语境,详细分析了《三国演义》在各历史阶段的诠释特征,新意迭出,为《三国演义》研究乃至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开辟了新领地。
一、关注“后文本”,开拓了《三国演义》学术研究新领地
近代以来,《三国演义》研究专家灿若星河,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国演义》研究更是不断突破前人的研究范式,取得了不少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总起来看,前人对《三国演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作者生平、籍贯考证;小说版本考证;小说文本研究,包括内容、主题、艺术手法、人物形象等;交叉学科研究,如传播、接受等,总体呈现从作者、作品转向读者及外围的研究趋势。从诠释学的视角关照《三国演义》,体现了这种研究转向。20世纪70年代末,加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传到中国,其理念很快渗透到文学研究之中,诗学研究是较早采用此种理论的。郭教授则是较早将哲学诠释学运用到小说研究之中,在绪论中作者表示:“哲学诠释学对读者在文本意义生成过程中重要性的强调使我们从过去的思维定式中走出来,将读者阅读的后文本时代作为文学作品研究的重要领域。” ①采用诠释学理论对《三国演义》解读,将《三国演义》“后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大大开拓了《三国演义》研究的新领地。
该作对《三国演义》诠释史做了全面梳理,总结了各历史阶段诠释特点。第一章明清小说评点家的评点诠释,对小说评点家的评点特点做出了评价。嘉靖壬午本对《三国演义》的定位是“羽翼信史”之通俗史书;“导愚适俗”是余象斗之书商型评点;“嬉笑怒骂”是叶昼之文人型评点;“奇书”“才子书”是毛评本和李渔评本之综合型评点。明清评点家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评点诠释,体现出了从比附经史的文本诠释到表达生命体验的个性诠释的转变轨迹。以上对《三国演义》各评点本诠释特点的评价,言学界所未言,令人耳目一新。
第二章为明清社会思潮与《三国演义》诠释,探讨了主流意识形态、个性解放思潮、“实学”思潮对《三国演义》诠释的影响及呈现出的不同诠释特点。主流意识形态使《三国演义》诠释具有了理学化和伦理教化色彩,个性解放思潮下的《三国演义》诠释则具有了“心学”色彩,“实学”潮流下的诠释更多具有了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及考证辨伪的色彩。
第三章近代《三国演义》诠释,在近代社会思想文化转型中,《三国演义》的诠释呈现出了复杂面貌,晚清文人仍然重视传统价值观的诠释,维新派、革命派则重视小说社会、宣传价值的诠释,五四学人注意运用西方人文理论,摒弃了以往感悟式地评点,开启了诠释新时代。
第四章現代《三国演义》诠释。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研究者主要围绕“阶级性”和“人民性”对《三国演义》进行解读,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三国演义》的人民性进行了肯定,并认同其向人民普及了历史知识、智慧谋略的作用。同时采取二元对立的方式对作品中“正统思想”及人物形象进行了解读。新时期以来《三国演义》出现了主体阐释的多样化、文化阐释的丰富化等可喜的诠释局面。
二、关注诠释者,深究不同诠释特点形成之因
“哲学诠释学认为,作为一种自律性存在的文学作品,其意义的实现必须有理解者的参与性理解,而阅读便是一种理解者积极参与文学作品文本的主动行为和创造行为,文学作品的意义就是在对本体论事件的阅读和理解中发生和实现的。” ②其中作为阅读主体的读者无疑是诠释学的核心概念。该书认为:“诠释的过程实质上是读者从自己的历史性出发去解读文本,并在与文本的沟通中形成文本意义的过程。” ③由此该书极其重视诠释者,并将诠释者定位在明清小说评点家、晚清名士、维新派、革命派、近代学者及现代学人身上,对诠释者的生存背景、诠释方式及诠释特点等进行了详尽辨析和梳理,同时诠释者不仅仅限定在国内,海外国家的诠释也被纳入研究范围,另外也不仅仅限定于小说的读者,还包括三国戏曲、曲艺、电视剧等“间接读者”,如此便大大扩大至了诠释者的范围,古今中外都有《三国演义》的诠释者,各种文艺形式也是《三国演义》的诠释者,这是对西方诠释学中限定的突破。
注重读者时代背景及历史性可以说是该书的重要特征,因为在哲学诠释学理论中,读者的历史性或者“前见”是诠释学的重要因素之一。“意义的获得从来就不是文本中的作者的原义或是读者的前见解,而是作者与读者二者‘对话’的结果,是二者视域的融合,是一件新的事情。” ④对读者前见解的挖掘,可以探求诠释特点形成之因,很有可能挖掘出学术新观点。《三国演义》诠释史是历代读者对《三国演义》解读的历史,破解这些不同解读的成因也是《三国演义》诠释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由此便需要结合时代背景分析解读读者的“前见解”。
如该书深究了毛评本《三国演义》的时代语境及毛氏父子的“前见解”,对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的动机和思想基础提出了新的解释。通过分析,该书认为明末清初小说评点繁盛局面的影响是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的主要动机,他们评改的思想基础则是儒家传统伦理道德观和人物形象塑造的文学典型观。另外在第三章的第四节:“避重就轻——胡适对《三国演义》的批判”,该节通过分析胡适的个人处境,探讨了胡适等人否定《三国演义》的原因。在《〈三国志演义〉序》中,胡适认为《三国演义》没有文学价值,提出想象力薄弱、人物形象塑造失败、不会剪裁等观点。但是该书作者发现了胡适这些观点与其本人其他小说评论观点存在抵牾之处,在分析了胡适观点的矛盾表现后,作者认为胡适是以西方文学为榜样,以其取法“西洋”的新文学理论为准绳,对《三国演义》进行了批判。同时作者还发现胡适对《三国演义》的语言和思想倾向也进行过批判,但却没有写入《〈三国志演义〉序》中,这种避重就轻的情况出现,实质上是胡适构筑“白话文学史”的需要。
三、该书的其他写作特色
该书除了以上鲜明特点外,还具有不少有意义的写作特点,现仅择三点说明。
其一,点面结合,详略得当的写作模式。《三国演义》成书至今有六百余年,期间对其的诠释更是浩如烟海,不可计数。如对《三国演义》诠释历史内容进行面面俱到地分析,是不可能完成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所以该书采取了点面结合的研究方法,选取历史上具有代表性、创见性的诠释观点进行评析,对读者最为关注的《三国演义》思想、人物、艺术等的解读进行梳理,而忽略诠释观点模糊或者意义不大的诠释材料,在去芜存菁的原则下,更能精准把握《三国演义》诠释史的发展脉络和总体特征。
其二、纵横结合的结构方式。该书采取横纵结合的论述结构。纵向以时间为序,分明清、近现代、新中国成立后三个历史阶段及海外诠释情况梳理《三国演义》的诠释史,是对《三国演义》诠释史的总体把握,有助于总体把握各个阶段《三国演义》的诠释特征、诠释观念的变化。横向上,选取《三国演义》中历来备受关注的诠释对象进行细致分析,重点将《三国演义》社会功能、“拥刘反曹”思想、关羽、曹操等人物形象及三国题材的戏曲、曲藝、电视剧等诠释对象单独进行诠释史的梳理。通过纵横结合的梳理,既明了《三国演义》诠释史的总体特征,又能突出《三国演义》重要研究议题的诠释流程,有利于《三国演义》诠释史和诠释特征的体现。
其三,注重历史发展传承的写作思路。作者在梳理诠释演变过程中,注意以历史演变的眼光看待各诠释观点的历史定位,如分析“拥刘反曹”思想诠释史,首先用了一节回顾了“拥刘反曹”思想历史渊源。因为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关于“拥刘”和“拥曹”的观点早已并行于世。因此作者从两个层次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脉络梳理。
在代表社会上层意志的史家态度中,经历了西晋陈寿的尊魏为正统,到东晋习凿齿尊汉,到北宋司马光尊魏为正统,到南宋朱熹尊汉为正统,元代之后,随着朱熹理学思想官方地位的确立,汉为正统便逐渐成了主流;在代表社会下层意志的层面,三国故事以传说、私家著述的方式不断流传,民间“拥刘反曹”的情感倾向十分明显。其后作者又分析了民间和官方对待“刘曹”不同态度的原因。正因有了之上的梳理,才顺理成章地引出了之后明清时期、新文化运动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新时期诠释者对“拥刘反曹”思想的阐释。这种思路在对关羽、曹操、诸葛亮等人物阐释中也得到了贯彻,可见完整清晰展现诠释史是作者始终遵循的写作思路。
该书也存在不足之处,限于篇幅,对戏曲、说唱、电视剧等诠释史梳理不全,对其诠释史的解读不够;其中有的小节对问题的分析解读也不够充分,给人意犹未尽之感。但瑕不掩瑜,该作仍是《三国演义》研究中独辟蹊径的力作。
注释:
①③郭素媛:《〈三国演义〉诠释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②李建盛:《诠释学与作为本体论的文学阅读事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60页。
④张同胜:《〈水浒传〉诠释史论》,2007年山东大学博士论文,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