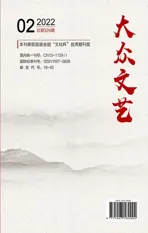理性与权力的辩证法
——略论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的批判与误读
2021-07-12
(武汉大学,湖北武汉 430072)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对理性和权力关系的关注与求解。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写的《启蒙辩证法》最清晰地将这一紧张关系呈现之后,哈贝马斯在对其批判解读的基础上实现了理性主义范式转换,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批判理论学派内部对《启蒙辩证法》的讨论。在充分肯定哈贝马斯对理性与权力关系求解的合理性和超越性的同时,我们必须承认批判理论如若继续发展必须直面两个困境,其一是理性批判的性质决定了研究仍须回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形而上学批判中去,其二是理性和权力关系的规范性基础——现代性依然需要直面后现代的挑战与冲击。这决定了今天我们仍需回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中理解理性和权力的辩证关系,为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哈贝马斯的解读。本文从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中理性与权力辩证法关系的具体解释、理论假设和理解方式三方面入手,层层推进,以期找到理解理性与权力的辩证法的钥匙。
一
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的解读集中体现在《交往行为理论》和《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前者重在建构,后者重在解构。哈贝马斯批判的核心观点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理性理解为受权力支配的工具理性,这样做不仅犯下了“把反理性作为其自身有效性的基础”的严重错误,而且“根本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摆脱目的理性的神话暴力”。哈贝马斯的解决办法是将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在他看来,工具理性在整个现代性中的增长,尽管十分危险,但却可以被交往理性主导的生活世界的逐步合理化所抵消,这为理性批判权力提供了规范基础,由此便可以纠正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工具理性与理性、理性与权力的错误融合,也一扫他们对现代社会的悲观论调。我们暂且不谈哈贝马斯的尝试是否成功,而是将目光聚焦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的解读上。
哈贝马斯的批判大体隐含着对理性与权力的辩证法的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有简单化的倾向。哈贝马斯认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笔下的“启蒙的辩证法”仅仅只是绝对的否定,他们通过将理性下降为工具理性,达到对启蒙理性的彻底揭露,从而展现出对现代社会的绝对悲观与全面批判。“在文化现代性中,理性最终被剥夺了其有效性要求,并与纯粹的权力等同起来……权力要求和有效性要求已经同流合污了”。第二种解释哈贝马斯将启蒙的辩证法理解为一种“有规定的否定”,认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暗含着对积极的启蒙概念的呼吁,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个积极的概念便是交往理性。对此有学者也指出,“如果把理性等同于工具理性,那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关于启蒙自我反思的呼吁就毫无意义。这里暗含着对另一种理性概念的诉求,一种包含‘不同于支配理性’的理性概念,这正是交往理性或对话理性的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哈贝马斯为启蒙辩证法所寻找的出口。
事实上,在笔者看来,哈贝马斯的这两种解释似乎自相矛盾。第一种解释所面临的挑战是,尽管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经常用目的性或工具性的术语谈论启蒙理性,但他们对启蒙理性的批判似乎比这更普遍,甚至同样适用于交往理性。“整个概念的逻辑秩序、概念的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相互发展、相互统一都表现为现实的相互关系,即分工。……由统治发展而成的社会分工使一切被统治者得以自我持存。”概念思维、逻辑规律等等都是交往理性的概念中保留下来的东西。如此一来,即使是理性的话语思维本身也呈现为一种内在的等级权力关系,由此看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不一定认可交往理性。总之如果沿着这种路径解释下去,第二种解释也难以成立,因为启蒙辩证法中理性与权力的关系是如此消极与悲观,以至于它与启蒙理性的所有积极概念都不相容,包括交往理性。
至此而论,哈贝马斯在批判中无意中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理性批判推到的一个极致,这意味着在启蒙的概念中,理性必然下降为权力,理性与权力关系的解决没有出路可循。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解释在无意之中都暗含了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即韦伯的合理化悖论——表现为理性和权力复杂关系的启蒙理性的内在悖论,应该在更高层次的辩证程度上得到解决或和解。哈贝马斯明确指出,在批判理论的理论史上,“《启蒙辩证法》是接受马克斯·韦伯的关键。”它所要解决的也正是马克斯·韦伯所留下棘手难题。但存在的问题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或许根本没有接受韦伯那种关于人类理性的二分法,“启蒙的辩证法”也不是用来解决合理化悖论的方法,哈贝马斯为启蒙辩证法所预设的这一理论前提本身并不成立。现在让我们集中在哈贝马斯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关于这一理论假设的批判与解决上。
二
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理性悖论的解决主要存在两种批判倾向。首先,哈贝马斯指出,《启蒙辩证法》的处理方式是将启蒙理性还原为纯粹的权力关系进而批判他,这是“对西方向现代性转变和由这一转变释放出来的理性和规范潜力的过度简化”。其次,哈贝马斯指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实际上是通过将启蒙等同为权力,达到对启蒙理性的全面、抽象的否定,这导致了启蒙批判的自我毁灭的本质。他认为这种对理性批判能力自我毁灭的描述是矛盾的,因为“它在描述时依然要用已被宣判死刑的批判。它用自身的武器来谴责启蒙的总体化。”换言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要进行的是对启蒙理性的总体性批判是相互矛盾的,因为这一批判仍要借助于理性的概念的思维语言。对此,有学者指出,哈贝马斯是在指责“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陷入了一种施为性矛盾,即启蒙的思想内容是极权主义的,表达启蒙的方式却是理性的。”
哈贝马斯的批判面临两个问题。第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目的不是通过将理性还原为权力和统治而陷入这一悖论,相反一开始他们就是为了阐明启蒙的矛盾本质,也就是启蒙理性与统治权力的纠缠关系。第二,启蒙的概念结构中确实存在着内在矛盾,阿多诺也承认这一矛盾。但这一矛盾首先是一个实质性矛盾,即这是理性内在具有的不可避免的,间接表现为一种施为性的矛盾。因为阿多诺的哲学的全部就在于对概念的施暴,对非同一性的追求。
到这里我们已经清楚,启蒙的辩证法是一种阿多诺式的辩证法,而不仅仅是黑格尔的“有规定的否定”。“通过绝对的否定,黑格尔……最终将整个否定过程的已知结果,即系统和历史上的整体性,假设为绝对的,从而违反了禁令,屈从于神话。”在这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清楚地与黑格尔划清界限。黑格尔的辩证法从绝对理念出发,最后又回到绝对理念,实际上是把一个已知的结果作为理性历史发展的终点。而在阿多诺这里,辩证法的矛盾不能解决。正如阿多诺后来在《否定辩证法》的导论中所指出的:“辩证法的名称首先告诉(人们),对象不会完全进入概念中,它与传统的符合论规范处于矛盾中。……矛盾是同一性不真实的标志,即在概念中领悟概念物不真实的标志。”概念意味着普遍和同一,但被压抑的那些非概念同样是构成概念意义的非同一的部分,因此概念必然走出概念,否定自身。在《启蒙辩证法》中,根据概念思维的同一性,启蒙从反权力又走向权力,只有通过启蒙的自我反思,在不断地否定中摆脱同一性的逻辑支配,实现积极意义上的启蒙概念。因此启蒙的概念本身并不是野蛮的或极权主义的;相反,它是非常矛盾的,它包含了堕落到野蛮和极权主义的可能,但它也包含了其他潜力,这种潜力可以但不仅限于艺术模仿,总之它是对自己倒退倾向的一种开放性的反思,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实际上是为启蒙树立一面自我反思的镜子,让其不断突破自我。
相反,哈贝马斯的解决办法倒像是重新接受了韦伯对于人类理性的二分法,于是合理化悖论从启蒙理性本身的概念中转换成一个由策略理性控制的系统和一个由交往理性主导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对立。换言之,哈贝马斯否认启蒙有内在的辩证法,并将启蒙内在的辩证法转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二元对立。这也表明在哈贝马斯看来,启蒙理性本身不存在悖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它既包括资本主义市场和官僚行政的系统方面的发展,也包括生活世界方面的交往理性的发展。系统虽然正日益受到权力的渗透与威胁,但生活世界为批判权力关系提供了规范基础,这样哈贝马斯就通过将矛盾外化转移成功地解决了韦伯的合理化悖论。
三
哈贝马斯与阿多诺的差异体现了他们对辩证法的不同认知,这根源于哈贝马斯与阿多诺对启蒙辩证法不同的理解方式。第一种理解方式是概念维度,即启蒙与统治的关系是一个概念性的关系,因此启蒙向统治的回归是必然的。这种理解带来的结果是,人们担心要么没有出路,要么即使有出路,也只能通过回归到对艺术模仿中去。这一种方式是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的理解。第二种理解方式是历史维度,即启蒙理性沦为权力支配的工具并非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理性被权力支配的事实可以通过现代性的规范性转型来找到出路,为此哈贝马斯找到了人与人之间交往资源。这一种方式则是哈贝马斯自己的立场。
事实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解释应该是二者的结合。一方面,启蒙的辩证法是以概念的方式呈现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始终是在形而上学内部开展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不过,这个概念的悖论并不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对启蒙理性的完全否定的理解中得出的结论,相反,呈现这一概念的悖论是他们的中心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提出的那个摆脱权力的交往理性的概念并非阿多诺的本意。另一方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反对那种声称知道历史发展的消极的历史哲学。长期以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神话早已是启蒙,启蒙又倒退回神话”的人类文明史的叙述常常被看作是对现实极权主义历史必然性的一种消极叙述,“批判理论这种新版本的核心,是这样一种历史哲学,阿多诺希望借助它来解释极权统治的这种历史性的来临。”但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现实的极权统治为出发点,却以对积极启蒙的诉求为终点,“启蒙不仅仅是启蒙”,“掌握着自身并发挥着力量的启蒙本身,是由能力突破启蒙的界限的”,极权主义和野蛮主义不是无法克服的历史必然,也不是理性的终点。虽然启蒙概念不可避免地与权力关系纠缠在一起,因而本身包含着倒退的种子和萌芽,但可能并不代表必然,极权主义不是启蒙预设的一个结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希望和可能,尽管可能只是一种态度和立场。也正因如此,我们仍需接纳交往理性,这样才能为现代性的进步提供新的可能性。
哈贝马斯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差异呈现出两代批判理论截然不同的风貌和气质,这两代人之间的差异清楚地表现为一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后形而上学批判和形而上阵营内部批判的差异。但无论是现代性的捍卫者还是批判者,承认理性与权力的不可调和的辩证法,保持一种反思而非进步的立场,都是同样重要的。《启蒙辩证法》给我们指明的方向是,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既需要牢记启蒙理性的危险,又不能放弃对启蒙理性的承诺。